|
|
杂文 》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上海男人怎麽了? 》
序:呼喚真品文化批判
秦林 Qin 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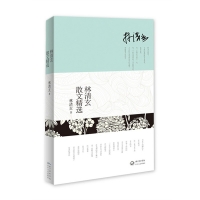 序:呼唤真品文化批判 序:呼唤真品文化批判
序:呼喚真品文化批判
文/陳 嵐 這幾年,寫書的人真的越來越多了,但能讓我讀進去的書卻越來越少了。再看看出版行業的報紙,占據着排行榜的書籍無非兩類:一類是被冠予英文名作者、國內市場超常運作的書;一類是美女帥男明星槍手杜撰的書。乍看文壇人才輩出,書市熱熱鬧鬧,然而真正高品味的書籍卻比圖書品種匱乏的計劃經濟年代更難求,陷入了麯高和寡尷尬境地。我看僅從提高全民文化素質來着眼的話,這未必是件好事。 文化的繁榮並不意味着文化的進步。真正的文化進步應該基於主流文化在公衆中的認可度。主流文化的內涵極其深遠,就其作品表現手法而言,要麽宏揚,要麽批判。現在的尷尬是:兩頭都缺。恰恰是“另類”文化成了現象,成了時尚,成了市場,成了尢物。什麽是“另類”?“怪、酷、奇、俗”四個字即可概而括之。明智的讀者也應該能從這四個字當中感受到“另類”文化究竟是什麽樣一種基調。如果這種基調長此以往地占有絶對的受衆群體,這也未必是件好事。 其實,我所說的以批判手法體現主流文化的書籍也不是沒有。比如前些年,批判地域部落群體中人格文化與生活習性之鄙陋的書籍就頗成氣候,因這些書籍大抵格調嚮上,作者大都賦有愛之深、痛之切的之舉,所以受到針砭的地域部落群體,無涉者一笑了之,有涉者大可照書反思,也可爭鳴。這類的書籍再多些,未必不是件好事。 去年初,秦林給我寄來一本他的當時新作,叫《朋友會咬人》。同樣是批判手法,秦林“得罪”了“出門靠朋友”的社會期許,這無疑需要相當的勇氣。我作為該書的讀者之一,就從中找到了好幾個我的朋友的身影,儘管出於某種顧慮,秦林聲言批判的力度有些拘淺,但從該書的入題定位而言,那種“味道”已經出來了。必須承認的是,搞文化批判難度是較大的,它不算冷門,但總是給人帶來沉重。因此批判的客體乃至度的把握,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在這個基礎上能構想出讓人動容的主題,這咱批判就已經成功了一半。我想,像《朋友會咬人》這類的文化批判讀物若能多推出一些,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還是秦林,又給我送“東西”了:這回不是書,是稿子。書名叫《打死不做上海男人》。囑我斧正並作序。一見書名,足知其批判鋒芒,我就和他打趣:“你不做上海男人,沒人逼着你做,你不用死!”你說他回答一句什麽?“有機會我還是想做上海男人的,因為我不會被‘打死’。”妙哉!真是後生可畏!我衹差沒稱他為“智者”了。 和《朋友會咬人》一樣,寫《打死不做上海男人》同樣需要相當的勇氣。這本書洋洋十餘萬言的批判,雖算不上句句珠璣,卻也難覓挖若、嘲諷、漫駡、譏笑和詰難,但這絲毫不會影響文化批判的力度。其中,“關於‘精明’芻議”一篇尤顯個性。作者通過“精”不在“明”處、“精”於算計、“精”於細巧、“門檻精”有多精等四個論點,強有力地支撐了“芻議”的主體,顛覆了多年來根植於人們概念中“上海男人最精明”的社會公論。此外,“一個優勢VS三大弱點”、“舉輕若重的性格標簽”也堪稱重量級批判,文似調侃,又能撓到要命的痛處。這和好比用一張帶菌的砂紙摩挲上海男人的臉的竜應臺的《啊,上海男人》相較,就讓人好接受得多了。讀其文便見拳拳之心,即使發現有過頭之處,也不至於煸着火氣呼啦呼啦往心頭灌了。 如果不生火氣生什麽呢?有則改,無則勉——這句話秦林在書中沒有說到。算是我替他嚮上海男人說了。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是一本文化批判的書。文中鮮見“好話”,這很正常。如果要求這本書像寫八股文那樣,先表揚幾下,再抽幾鞭子。那就不叫文化批判,叫總結報告。況且,作總結報告,嚮來不是搞文化批判的人的風骨。也不是秦林的風骨。 是為序。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資料來源】西苑出版社 |
|
|
| 序:呼喚真品文化批判 | 在國人怨忿聲裏簇起的東方之都 | 發端於清末民初的“文詬” | |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 | 上海男人何以成為衆矢之的 | 土著人與移民矛盾的形成 | | “上海男人”在外地人心中的分量 | 你用什麽招呼外地朋友 | “海派”版本的排外 | | 國人為什麽愛“爆”上海男人的笑 | 何必與“全國人民”“為敵” | 當小氣已成慣性 | | 瑣碎難以長大志 | 有一種虛偽叫“驚豔” | “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 | | 審視“上海紳士” | 啥叫“新上海男人” | “走樣的贊語”是褒還是貶 | | 絶非空穴來風 | 說你“中性”你別急 | 怕什麽莫過於怕老 | | 講衛生講到潔癖 | 無畏的“嘴仗” | “小資”者“常樂” | |
|
第 I [II] [III] 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