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春秋类 》 春繁露 》
一
董仲舒 Dong Zhongshu
 春秋繁露 卷一 春秋繁露 卷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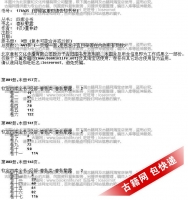 春秋繁露 卷一 春秋繁露 卷一
一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舒,《春》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庸知其非正經,《春》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着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着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爾也。""《春》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不昧,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計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治則四鄰賀,國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之至也。君子不恥其,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
《春》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偶之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之道也。
《春》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世也。《春》之於世事也,善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王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遍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於外者也,應其治時,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歌詠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好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譏文公以喪取。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之論事,莫重於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祫祭,以鼕納幣,皆失於太蚤,《春》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先,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着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之序道也,先質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禮,玉帛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朝,辭令乎哉!'樂樂,鼓乎哉!'引而之,亦宜曰:喪喪,衣服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逾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之大義也。
《春》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者,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之可肥轢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去厥"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着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見,以其宜滅絶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牘見,非《春》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見者,亦不宜見也而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盾誅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赴問數百,應問數,同留經中,翻援比類,以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見,而問曰:'此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案盾事,而觀其心,而不刑,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枸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藥也;子不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之不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責在而不討賊者,弗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筲之民,何足數哉!弗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責之,以繅枉世而直之,繅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繁露》 漢·董仲舒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