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诗歌评论 》 詩病五事 》
詩病五事
轍 Su Z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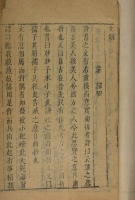 诗病五事 诗病五事 诗病五事 诗病五事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踞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綿》九章,初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怨,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予曰有奔奏,予曰有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絶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麯江麯。江頭宮殿鎖門,細柳新蒲為誰緑?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顔色。昭陽殿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天仰射,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註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伐之事,其於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骸撐拄。末乃取,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1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瀋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顔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也不改其樂”,雖窮早卒,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致七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之。由此觀之,大邦、巨室,非為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法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併》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姦。姦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懷清。禮義日以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併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1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玻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輯錄
【三和張安道讀杜集〈用其韻。〉】
我公不世,晚歲道尤高。與物都無著,看書未覺勞。微言精老易,奇韻喜莊騷。杜叟詩篇在,唐人氣力豪。近時無瀋宋,前輩劉曹。天驥精神穩,層結構牢。竜騰非有跡,鯨轉自生濤。浩蕩來何極,雍容去若遨。高真命將,毳亂始知髦。白也空無敵,微之豈少褒。論文開錦綉,賦命委蓬蒿。初試中書日,旋聞鄜疇逃。妻孥隔豺虎,關輔暗旌旄。入蜀營三徑,浮江寄一艘。投人慚下,愛酒類東臯。漂泊終浮梗,迂疏獨釣鰨誤身空有賦,掩脛惜無袍。軸今何益,零丁昔未遭。相如元世,惠子謾臨濠。得失將誰怨,憑公付濁醪。
【集一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兄詩有味劇雋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長韻風吹忽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遑請。相思半夜清唱,醉墨平明照東剩詩到,適在省中。南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郊一飯歡有,去歲此時初到潁。
【集四題韓駒秀詩】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集二十一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徭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為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為樂也。時太常少鄉李君簡夫歸老於,出入於鄉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而不。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為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為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蕭然,饘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噶閭,不避勞辱,未而以足聞。陳人喜花,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為,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爭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篇,分為二十。
【集二十一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蒣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錄之,以遺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貧,東西遊走。性剛纔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米一束帶見鄉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年,為獄吏所圍困困苦,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跡,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一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集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節錄)】
(軾)徙知湖州,以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蘖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置之死,鍛煉久之不决。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之間,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三集一讀舊詩】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在,賞音他日更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三集二讀舊詩】
老人詩思如枯泉,轆轤不下甕盎。舊詩展驚三年,粲然佳句疑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藜羹稻飯嗟獨便。飽食暇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三集三讀樂天集戲作五絶】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絶,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凝師,院猶存楊柳枝。春絮飛一念,我今無日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為二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註池塘,畫舫飛橋映緑楊。潩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竹自成園,我亦墻陰數百竿。不共伊煙斗北斗斗量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欒城應詔集四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麯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以為如此,故其論委麯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於《禮》、《春》,然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禮》、《春》之嚴矣。而況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跡,而下及於飲食床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緑,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惟鳩居之”;“喓喓草,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其事。蓋其為學亦以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固有“比”也,而皆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爾,意有所觸乎。”當此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靁》,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靁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欒城應詔集九民政上·第一道】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蹠趑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友。朝廷之上,難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耘播之勢,而述其歲終倉廩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業。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之桎桎,積之慄慄。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救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其利,而教之使其樂,亦如是。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市,而頑民不悛。夫鄉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襢背受笞於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邪?惟其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以共事,此則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為,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