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名鄭天梅,1980年生,現居杭州,於外企工作。 |
|
作者: 獨孤紅 Dugu Hong
作者:獨孤紅
第一章 一剪梅
第二章 翔雲之燕
第三章 宦門癡女
第四章 聲威震四海
第五章 高絶白衣客
第六章 慧眼識英雄
第七章 石傢莊驚豔
第八章 一把好火
第九章 英雄伴美人
第十章 素心鐵膽
第十一章 不凡之交
第十二章 息事寧人
第十三章 藝高人膽大
第十四章 變生肘腋
第十五章 虎落平陽
第十六章 泣血情
第十七章 南柯夢醒
第十八章 香車載得美人去
第十九章 乍喜還悲
第二十章 佳人夜訪
第二十一章 長白行
第二十二章 雪夜之戰
第二十三章 伊人來
第二十四章 血灑長白 |
|
詩人: 李白 Li Bai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伫立,
宿鳥歸飛急。
何處是歸程?
長亭更短亭。 |
|
詩人: 溫庭筠 Wen Tingyun
小山重疊金明滅,
鬢雲欲度香腮雪。
懶起畫娥眉,
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
花面交相映。
新貼綉羅襦,
雙雙金鷓鴣。
--唐 溫庭筠 |
|
詩人: 李清照 Li Qingz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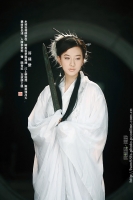 菩萨蛮 菩萨蛮
夾衫乍著心情好。
睡起覺微寒,
梅花鬢上殘。
故鄉何處是?
忘了除非醉。
瀋水臥時燒,
香消酒未消。 |
|
詩人: 李清照 Li Qingzhao
歸鴻聲斷殘雲碧,
背窗雪落爐煙直。
燭底鳳釵明,
釵頭人勝輕。
角聲催曉漏,
曙色回牛鬥。
春意看花難,
西風留舊寒。 |
|
請鑒賞:
|
|
| ①詞牌名。原為唐代教坊麯名,後用為詞牌。雙調,四十四字,前後闋均押兩仄聲韻轉押兩平聲韻。②麯牌名。屬北麯正宮。字句格律與詞牌前半闋相同。用在套麯中。 |
|
| 唐 教坊麯名。後用為詞牌。又名《子夜歌》、《重迭金》。小令四十四字,前後闋各兩仄韻轉兩平韻。 唐 蘇鶚 《杜陽雜編》捲下:“ 大中 初……其國( 女蠻國 )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麯’。” 明 楊慎 《丹鉛總錄·詩話·菩薩鬘》:“ 唐 詞有‘菩薩蠻’,不知其義。按小説, 開元 中, 南詔 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號‘菩薩鬘’,因以製麯。” |
|
| 麯牌名。屬北麯正宮。字數與詞牌前半闋同,用在套麯中。 |
|
| 宋 代稱伊斯蘭教徒為菩薩蠻,阿拉伯文的音譯。 宋 朱彧 《萍洲可談》捲二:“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 中見呼蕃婦為菩薩蠻因識之。” |
|
| 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 : 詞篇名。相傳為唐代李白作。上片渲染山林清寒傷心之景,下片由景入情,寫閨中思婦伫立盼望遊子歸來的哀傷。全篇意境蒼涼,筆法渾厚,結尾含蓄不盡,是給人以深刻啓迪的最早文人詞之一。 |
|
| 菩薩蠻(鬱孤臺下清江水) : 詞篇名。南宋辛棄疾作。題為“書江西造口壁”。造口,在今江西萬安西南。詞中回顧了南宋初年的歷史恥辱,用“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表達對故土的眷戀,用“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表明收復失土的信念。 |
|
| 唐教坊麯名,後用為詞牌。亦作菩薩鬘(mán),又名《子夜歌》、《花間意》、《重疊金》等。唐宣宗(李忱)大中年間(公元847--859年),女蠻國派遣使者進貢,她們身上披挂着珠寶,頭上戴着金冠,梳着高高的發髻(jì),號稱菩薩蠻隊,當時教坊就因此製成《菩薩蠻麯》,於是《菩薩蠻》就成了詞牌名。菩薩蠻雙調四十四字,前後闕均兩仄韻轉兩平韻。另有《菩薩蠻引》、《菩薩蠻慢》。又:麯牌名。屬北麯正宮。字句格律與詞牌前半闋同,用在套麯中。 |
|
菩薩蠻·閨情 (唐) 李白
〔題考〕 【杜陽雜編】:「大中初,女蠻國貢雙竜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麯﹞,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唐音癸簽】、【南部新書】略同。又【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丞相假飛卿所撰密進之,戒以勿泄。」唐時俗稱美女為菩薩,菩薩蠻酋稱女蠻。當時教坊,譜作麯詞,遂為詞名。後楊升庵改蠻為鬘,失其本矣。後人又名為﹝重疊金﹞、﹝子夜歌﹞、﹝巫山一片雲﹞等,非特於詞名來源無涉,且﹝子夜歌﹞另有正調,而﹝巫山一片雲﹞更易與別調﹝巫山一段雲﹞相混,殊屬無取。
〔作法〕 本調四十四字,為詞調中之最古者,即以五七言組成;通篇兩句一韻,凡四易韻,兩平兩仄。第一、二句即為七言仄句。第三句為仄起之五言句,換用平韻。第四句為五言拗句。後半第一句為平起仄韻之五言句。第二句為仄起仄韻之五言句。第三、四句與前半第三四句同。此首相傳為太白創作,但這兩首詞沒有收入宋本《李太白集》,而始見於宋人筆記,是否李白作品,頗滋後世疑問。明代鬍應麟、鬍震亨等已疑為後人偽托。現代學者也頗多不信為李白所作,一個主要理由是唐代前期文人詞尚處在萌芽狀態,文辭體製,都較簡樸,而這兩首詞卻是用雙調,換韻,語言精練,描寫細緻,在藝術上很成熟,顧按上述,調之創始,在唐 大中初,則白又何以見此詞調?【詞苑叢談】謂:「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屑為,寧肯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絶類溫方城輩,蓋晚唐詞嫁名太白耳。」按諸上,引【北夢瑣言】與此說相合。近世鬍適作【詞選】亦云然。
定格:
平林漠漠煙如織,
⊙○⊙●○○▲ (仄韻)
寒山一帶傷心碧。
○○●●○○▲ (協仄韻)
暝色入高樓,
●●●○△ (換平韻)
有人樓上愁。
●○○●△ (協平韻)
玉階空伫立,
⊙○○●▲ (三換仄)
宿鳥歸飛急。
⊙●○○▲ (協三仄)
何處是歸程,
⊙●●○△ (四換平)
長亭連短亭。
⊙○○●△ (協四平)
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作者:辛棄疾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餘,山深聞鷓鴣。
全部註釋
1.造口:一稱皂口,在今江西萬安縣西南六十裏。
2.鬱孤臺:在今江西贛縣西南。《贛州府志》:"鬱孤臺,一名賀蘭山。隆阜鬱然孤峙,故名。"清江:此指贛江。
3. 長安:代指都城汴京。
這是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詞人任江西提點刑獄、駐節贛州時寫的詞。羅大經《鶴林玉露》雲:"南渡之初,虜人追隆佑太後禦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由此起興。" 辛棄疾登上鬱孤臺,回想四十七年前金兵長驅直入江南、江西腹地,南宋幾乎滅亡之事,從奔騰的清江之水,想到了當年隆佑太後一行匆匆逃竄的蹤影,以及因傢國破亂而灑下的痛楚之淚。由水及淚,意象轉換極為自然。"青山遮不住"兩句,表達了詞人對抗金恢復的堅定意志。煞拍兩句,蓋有豪興逸懷,當此日暮江景,畢竟憂思難擋,愁從中來。《鶴林玉露》認為結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而鄧廣銘則認為;蓋深慮自身恢復之志未必即得遂行,非謂恢復之事决行不得也。"似乎鄧說更契合稼軒詞境詞心。全詞用的是比興手法。周濟《宋四傢詞選》說:"藉山怨水"。它以山水起興,一掃傳統《菩薩蠻》小令富豔輕靡之格,而出之以激越悲壯之音,令人耳目一新。梁啓超評此詞說:"《菩薩蠻》如此大聲鏜鞳,未曾有也。"(《藝蘅館詞選》)總的來說,這首詞熱情洋溢,,慷慨激昂,富有收復失地,統一祖國的感情。
【年代】:宋
【作者】:李清照——《菩薩蠻》
【內容】:
歸鴻聲斷殘雲碧,
背窗雪落爐煙直。
燭底鳳釵明,
釵頭人勝輕。
角聲催曉漏,
曙色回牛鬥。
春意看花難,
西風留舊寒。
【註釋】:
歸鴻:這裏指春天北歸的大雁。
碧:青緑色。
背窗:身後的窗子。
鳳釵:古代婦女的一種首飾。釵名有時因釵頭的形狀而異。
人勝:古時正月初七為“人日”,剪彩為人形,故名人勝。勝,古代婦女的首飾。
角:古時軍中樂器。有彩繪者,也稱畫角。
漏:古代滴水計時的器具。
牛鬥:即牛宿(二十八宿之一,相當於摩間羯座之一部分)、鬥宿(二十八宿之一,相當於人馬座一部分)。非一般的所說北斗星和牽牛星。
【賞析】:
此詞當為李清照南渡後的作品。上片寫黃昏後的室內外的景象,及永夜思念家乡的情景。下片寫拂曉室內外的景象和女主人難以看到梅花的惆悵,不言愁而愁自見。不假雕飾,意境幽遠。
【年代】:宋
【作者】:李清照——《菩薩蠻》
【內容】:
風柔日薄春猶早,
夾衫乍著心情好。
睡起覺微寒,
梅花鬢上殘。
故鄉何處是?
忘了除非醉。
瀋水臥時燒,
香消酒未消。
【註釋】:
風柔:指春風和煦。
日薄:指日光淡薄。
乍著:剛剛穿上。
瀋水:通沉水 即沉香。香料名。
【賞析】:
此詞當為李清照後期的作品。寫女主人在一個早春白日對故國鄉關無限懷念的深情。李清照的懷鄉詞,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技巧都有很高的價值。應得到我們今人的特別珍重。
菩薩蠻 (無名氏)
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嚮庭前過,
含笑問檀郎①,花強妾貌強?
檀郎故相惱,須道花枝好。
一面發嬌嗔,碎挼②花打人。
【註釋】
①檀郎:晉代潘嶽小名檀奴,姿儀美好,舊因以“檀郎”或“檀奴”作為對美男子
或所愛慕的男子之稱。
②挼:揉搓。“挪”的異體字。
【評解】
這首《菩薩蠻》,生動地描繪了折花美女天真嬌癡的神態,謳歌男女間的愛情。寫
得流麗自然,面又細膩入微。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民歌風味。
溫庭筠《菩薩蠻》
溫庭筠
小山重疊金明滅①,鬢雲欲度香腮雪②。懶起畫蛾眉,弄妝③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綉羅襦④,雙雙金鷓鴣⑤。
[註釋]
①小山:指屏風上雕畫的小山。金明滅:金光閃耀的樣子。
②鬢雲:象雲朵似的鬢發。度:覆蓋。香腮雪:雪白的面頰。
③弄妝:梳妝打扮。
④羅襦(rú):絲綢短襖。
⑤鷓鴣:這裏指裝飾的圖案。
[評解]
這首《菩薩蠻》,為了適應宮廷歌伎的聲口,也為了點綴皇宮裏的生活情趣,把婦女的容貌寫得很美麗,服飾寫得很華貴,體態也寫得十分嬌柔。仿佛描繪了一帽唐代仕女圖。
詞的上片,寫床前屏風的景色及梳洗時的嬌慵姿態;下片寫妝成後的情態,暗示了人物孤獨寂寞的心境。全詞委婉含蓄地揭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並成功地運用反襯手法。鷓鴣雙雙,反襯人物的孤獨;容貌服飾的描寫,反襯人物內心的寂寞空虛。表現了作者的詞風和藝術成就。
[集評]
張惠言《詞選》捲一:此感士不遇之作也。篇法仿佛《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捲一:飛卿詞如“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
張燕瑾《唐宋詞選析》:這首《菩薩蠻》不僅稱物芳美,也具有“其文約,其詞微”的特點,富有暗示性,容易使人産生種種聯想。
《中國歷代詩歌各篇賞析》:在這首詞裏,作者將許多可以調和的顔色和物件放在一起,使它們自己組織配合,形成一個意境,一個畫面,讓讀者去領略其中的情意,這正是作者在創造詞的意境上,表現了他的獨特的手法。
菩薩蠻
朱淑真
山亭水榭秋方半,鳳幃寂寞無人伴。
愁悶一番新,雙蛾衹舊顰。
起來臨綉戶,時有疏螢度。
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
朱淑真詞作鑒賞
朱淑真本人的愛情生活極為不幸,作為一位女詞人,她多情而敏感。詞中寫女主人公從缺月獲得安慰,不啻是一種含淚的笑顔。無怪魏仲恭在《朱淑真斷腸詩詞序》中評價其詞為“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同豈泛泛者所能及”。
“春秋多佳日”山亭水榭“的風光當分外迷人,但詞人卻以極冷漠的筆調作出此詞,因為”良辰美景奈何天“,消除不了”鳳幃“中之”寂寞“——獨處無郎,還有什麽賞心樂事可言呢?”鳳幃“句使人聯想到李商隱《無題》詩中的名句:”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如此情狀,叫人怎不顰眉,怎不愁悶?有意味的是,詞人使”愁悶“與”顰眉“分屬於”新“”舊“二字。”舊“字以見女主人公愁情之久長”新“字則表現其愁情之與日俱增。一愁未去,一愁又生,這是”新“;而所有的愁都與相思有關,這又是”舊“。”新“”舊“二字相映成趣,更覺情深。
輾轉反側,失眠多時,於是乃有“起來”而“臨綉戶”似乎是在期待心上人的到來。然而戶外所見,衹不過“時有疏螢度”而已,其人望來終不來。此時,女主人公空虛寂寞的情懷,是難以排遣的。在這關鍵處,詞人又卻又寫出了一絲安慰,也算是自慰吧!詞人給她一點安慰,一輪缺月,高挂中天,並賦予它人情味,說它因憐憫閨中人的孤棲,不忍獨圓。“多謝”二字,癡極妙極。同是寫孤獨情懷,蘇東坡在圓月上做文章:“不應有恨,何事長嚮別時圓”;朱淑真則在缺月上做文章“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移情於物,怨謝由我,真有異麯同工同妙。此詞最有興味之所在正是結尾兩句。
菩薩蠻
張先
憶郎還上層樓麯。
樓前芳草年年緑。
緑似去時袍。
回頭風袖飄。
郎袍應已舊。
顔色非長久。
惜恐鏡中春。
不如花草新。
張先詞作鑒賞
這是一首以感春懷人為內容的閨怨詞。它運思、謀篇方面自出機杼,別具一格,推陳出新。全詞以顔色貫穿全篇,並用以巧妙運思、穿針引綫。詞之上片着眼於顔色的緑與緑之相同,使空間隔絶的近處芳草與遠方行人相連結,使時間隔絶的今日所見與夕日所見相溝通,從而使樓前景與心中情融會為一,合為詞境。下片着眼於顔色的新舊差異,使回憶中的昔時之袍與想像中的今日之袍相對照,使身上衣與境中人相類比,使容顔之老與花草之新形成反比。起首“憶郎還上層樓麯”一句通過閨中少婦登樓望遠的視綫,把她的一顆愁心送到遠方遊子的身邊。登樓望遠是古詩詞中常用的意象,多從空間落想,悵望行人此去之遠。第二句“樓前芳草年年緑”,則從時間落想,因見芳草“年年緑”而悵念行人遠行之久。這句詞肉於淮南小山《招隱士》賦“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及王維《山中送別》詩“春草明年緑,王孫歸不歸”,暗含既怨遊子不歸又盼遊子早歸的復雜意味。
上片末兩句,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個“緑”字為橋梁,從“芳草年年緑”到“緑似去時袍”,由望景過渡到懷人,感今過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從芳草之緑生發聯想,勾起回憶,想起郎君去時所着衣袍的顔色,並進而追憶其人臨去依依、回首相望時,衣袖隨風飄動的情景。這一細節深深印她的記憶之中,時時都會重現眼前,如今,因望見芳草緑、想到“去時袍”,當初的一幕幕又分明似眼前了。從這兩句詞,即可以想見詞中人當年別郎時的留戀,也可以想見其今日“憶郎”時的惆悵。牛希濟《生查子》詞中的:“記得緑羅裙,處處憐芳草。”可與這兩句詞參讀,不同的是:張先詞就居者立言;牛詞則擬居者口吻以囑咐行者。
過片兩句,緊承上片的三、四兩句。詞筆不離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樣是寫那件緑色的衣袍,但上兩句是回憶去時的袍色,這兩句是想象別後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時間上拉回到過去,後者則把萬縷柔情空間上載送到遠方。同時,這兩句又與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兩字遙相呼應,也是從時間落想,暗示別離之長久。正因別離已久,纔會産生衣袍已舊、怕那去時耀眼的緑色已經暗淡無光的推測。又從袍之舊、色之褪,觸發青春難駐、朱顔易改之感。於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鏡中春,不如花草新”兩句,把詞意再推進一步。詞中人之所惋惜、恐懼的是一個意義更深廣、帶有永恆性的人生悲劇,而不僅僅是一次別離的痛苦。離別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終有歸來之日,日後相逢之樂還可以補償今日相思之苦;至於人生短促、歲月無情,而居者與行者都會分離中老去,這卻是無可輓回、無可補償的,正所謂“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顔辭鏡花辭樹”(王國維《蝶戀花》)。這兩句詞,則對照眼前“芳草年年緑”之景,怨嘆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還會開;草枯了,明年還會緑;而人的青春卻一去不復返了。鏡中的春容衹會年年減色,不會歲歲更新。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白頭吟》)說的也是這樣的意思。
此詞謀篇方面句句相承、環環相扣。上片因“憶郎”而“上層樓”,因“上層樓”而見“樓前芳草”,因芳草之“緑”而回憶郎袍之“緑”,再因去時之“袍”而想到風飄之“袖”。首句與次句的兩個“樓”字,緊相扣合;次句與第三句的兩個“緑”字,上下鈎連;第四句的“袖”字固與第三句的“袍”字相應,句中的“回頭”兩字也暗與第三句的“去時”兩字相承,針綫綿密,過渡無痕。下片雖另起新意,卻與上片藕斷絲連。因三、四兩句回憶起去時之袍,過片兩句就進一步想象今日之袍;過片兩句的上、下句間,則是因衣袍之“舊”而致慨於“顔色非長久”。接下來的兩句,更因袍色之不長久而想到“鏡中春”也不長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緑”句,而有感於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脈絡井然,層次分明。
菩薩蠻
杜安世
遊絲欲墮還重上,春殘日永人相望。
花共燕爭飛,青梅細雨枝。
離愁終未解,忘了依在前。
擬待不尋思,則眠夢見伊。
杜安世詞作鑒賞
這首閨怨詞抓住具有特徵性的事物,含蓄委婉,獨具特色。
起筆“遊絲欲墮還重上”,詞人就抓住空中飄搖不定的“遊絲”來大做文章,是頗具匠心的。“遊絲”,也就是“睛絲”、“飛絲”、“煙絲”,是一種蟲類吐出的極細的絲縷,飄浮空氣之中,如果天氣晴朗,陽光璀璨,有時還可發現這種“遊絲”空中閃着水晶般透明的耀眼的光澤。作者通過這一細微的事物反映出癡情少女內心的微妙的波動,反映出這位少女對春天、對青春和對生活的熱愛。此詞“遊絲”一句,含蓄麯折,一語雙關。它表面上似寫景,實際卻寫少女的心境,用的是“諧音隱語”手法。詞裏“遊絲”,正是有意與“相思”的“思”字雙關。這一句形象地說明,少女的相思之情跟天上飄飛不定的“遊絲”一樣,一忽兒,象是要墜落下來;一忽兒,又扶搖直上。剛剛平靜下來的內心,也因此捲起了感情的漣漪。這不僅增強了詞的韻味,同時它還把詞中的景、事、情串接一起,使全詞意境和諧完整。
第二句:“春殘日永人相望”。說此情況下,“相望”的時間也隨之增長了。“春殘”,點明季節,春歸而人未歸。“日永”,白晝廷長。“花共燕爭飛,青梅細雨枝”二句是對“春殘”的補充,同時,它又是“人相望”的必然結果。雖然這位少女“相望”的是“人”,但因“人”千裏之外,可望而不可及,她所能見到的便衹能是落紅伴着雙飛的紫燕紛紛飄墜,是被雨滋潤過的梅枝上的青青梅子。這兩句還兼有映襯與象徵作用。花落春歸,燕已飛回,而人卻杳無歸期。
過片“離愁”二字,很自然地成為上下片轉折過渡的關鍵,並具有畫竜點睛的妙用。“離愁”與“遊絲”上下呼應。“離愁”因有“遊絲”的映襯而顯得鮮明具體,“遊絲”以“離愁”為內涵愈加顯得充實。因之,即使相望很久,都未能衝淡她的“離愁”,故曰“終未解”。不僅如此,詞人還補足一句:“忘了依前。”“忘了”二字之下省略了一個賓語,即末句的“伊”。即使你想方設法去忘卻他,可他還是跟從前一樣,清清楚楚地再現於你的眼前,再現於你的心頭。
接着又寫了兩句:“擬待不尋思,剛眠夢見伊。”以申明此意。“不尋思”即“忘了”,“夢見伊”即“依前”。作者不是正面表達她渴望與所思之人夢中相會,而是以“擬待不尋思”先跌一筆,再以“剛眠夢見伊”點出正意,來一個否定之否定,運筆新奇,因而就更引人入勝。
這首詞格調清新自然,情真意切,運思手法頗得民歌風韻,有語淺而意深之妙。
菩薩蠻
孫洙
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
上馬苦匆匆,琵琶麯未終。
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
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孫洙詞作鑒賞
起首“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摧人去!”這兩句是牢騷話:剛剛二更時分,城樓上還要敲三通鼓纔天亮,何必這麽死命地催人走呢!據宋洪邁《夷堅甲志》捲四,翰林學士孫洙某晚正太尉李端願傢歡宴,有美女侍妾奏樂助興,恰逢此時朝廷宣召,心下不願,故出怨語。“何須抵死催人去”就是本此而發的牢騷。說:“尚有三通鼓”,而不說已過二更,表示離天亮還早,希望多玩一會兒。但留連不捨之意橫遭阻抑,自然轉化為憾恨之情。“抵死”,猶言死命、拚命,形容竭力。對於皇帝宣召,竟是如此不情願,可見這夜宴是何等令人留戀。“上馬苦匆匆,琵琶麯未終”,一邊匆匆上馬,一邊卻還戀顧那美妙的琵琶聲,深以未聽到麯終為憾。琵琶的誘人魅力來自那位彈奏的女子,言外藴含着對其人的深情眷戀。然而迷人的女樂,終究抵不住皇命的催逼,他衹得無可奈何地上馬離去了,但那聲聲琵琶似乎一直縈繞耳際。上片四句,一氣流註,節奏快速,皇命催人、刻不容緩的氣氛頓出,從而反襯出詞人不願從命而又不敢違命的矛盾感情。
過片寫主人公戀戀不捨,人雖已上馬,心尚留筵間,一路上還出神地回頭凝望。但馬跑得快,老天更不湊趣,又下起蒙蒙細雨,眼前衹覺一片模糊,宛如織就一張漫天的愁網,連人帶馬給罩住了。“廉纖雨”,蒙蒙細雨。“無邊絲雨細如愁”,這廉纖細雨,既阻斷了視綫,又攪亂了心緒;藉景語抒情,情景湊泊而有醖藉之致。“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玉堂,翰林院的別稱。玉堂供職是作者平時所自以為宋寵的,今夜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無聊和索寞。從一個充滿美酒清歌的歡樂世界,硬生生地被拋到宮禁森嚴的清冷官署,其懊喪和惱恨可想而知。“玉堂今夜長”,大有長夜難捱之感。對照開頭“城頭尚有三通鼓”,同時對於時間的感受,竟有如此不同的心理變化。這一起一結也自然形成兩種情境的鮮明對比,使這首小詞首尾相顧,有回環不盡之妙。
菩薩蠻
李師中
子規啼破城樓月,畫船曉載笙歌發。
兩岸荔枝紅,萬傢煙雨中。
佳人相對泣,淚下羅衣濕。
從此信音稀,嶺南無雁飛。
李師中詞作鑒賞
此詞作於詞人嶺南卸任之時。全詞景色清麗,感情深摯,意境深遠。
詞為“題別”而作,通篇圍繞一個“別”字做文章。上片起句寫臨別前情景。詞人將要離開廣西了,黎明之前子規鳥就不住地啼嗚,把他從夢中喚醒。他舉頭看看窗外,一彎殘月高挂西天,好像是被子規啼破了似的。這一句寫出了早起之景、臨別之時第、歸去之思和離別之情。乍看上去,出語自然;細細吟味,含意無窮。第二句寫詞人乘着華麗的官船將要出發,雖為寫實,但實中帶虛,所謂“曉載笙歌”者,乃是以“笙歌”兼指吹奏笙歌的樂妓,用語甚美,耐人尋味。三、四兩句尤為入妙。畫船清澈的江中從容而行,衹見兩岸荔枝,嬌紅欲滴;蒙蒙煙雨,籠罩萬傢。這完全是畫境,同時也是詩境,讀之令人陶醉。
過片二句寫別情。佳人,謂畫船中樂妓。這裏不僅補足“笙歌”一詞之意,而且進一步發抒離思。一位清正的地方官將要離任了,佳人也無法輓留,與詞人相對而泣,滾滾熱淚,濕透羅衣。這裏讓佳人把惜別的淚水傾瀉出來,雖不夠含蓄,但熱烈真誠。
結尾二句,係預想別後情景,對不可能繼續通信表示擔心。“嶺南無雁飛”,據陸佃《埤雅》雲,雁飛不過衡陽,因南地極燠。廣西嶺南,故鴻雁更難飛到。此處運用鴻雁傳書的典故,符合當地特點,顯得十分妥貼。
此詞妙選詞煉字、首句“子規啼破城樓月”中的“破”字便是範例。子規、城樓、月,本是三個互不相幹的概念,然着一“破”字,遂連成一體,形成渾一的境界。
菩薩蠻
王安石
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
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
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
王安石詞作鑒賞
此詞為作者晚年隱居江寧半山之作。《能改齋漫錄》雲:“王荊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中疊石作橋,為集句填菩薩蠻。”全篇用前人詩句雜綴成詞,使之如出己口,真正為自己表情達意服務,敘寫自己的閑適生活與故作放達的情懷。
開首“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二句明白地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環境與身份。往昔重樓飛檐、雕欄畫棟的官宦居處換成了築籬為墻,結草作捨的水邊茅屋;如今窄衫短帽的閑人裝束取代了過去的冠帶蟒服。作者從九重宸闕的丹墀前來到了水邊橋畔的垂楊裏。對於這種遭際的變化,王安石似乎采然種安然自適的態度。一個“閑”字渲染出淡泊寧靜的生活環境,也點出了作者擺脫宦海遠離風塵的村野情趣。兩句閑雅從容,雖然是從前人詩句中摘錄而成,但指事類情,貼切自然,不啻如出己口。
接着“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兩句是寫景:一夕春風來,吹開萬紫千紅,風光正似去年。但是,作為一個曾經銳意改革的政治傢,他對花事依舊、人事已非的感慨,就不僅僅是時光流逝、老之將至的嘆息,更包含着他壯志未酬的憂愁。因此,即使看似閑適的生活裏,自然界的月色風聲,都會引起這位政治傢的敏感與關註,而被賦予某種象徵的意義:“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作者醉酒晝寢,再不必隨班上朝參預政事,生活是如此閑逸,但是,酒醒夢回,陪伴他的並不是清風明月,而是風吹雲走、月翳半規的昏沉夜色。
最後二句自然地歸結到閑情上:“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作者自問自答,寫得含蓄而餘韻悠長。據馮贄《雲仙雜記》引《高隱外書》雲:“顒攜黃柑鬥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可見王安石的寄情黃鸝,不僅是表現鳥語花香中的閑情逸趣,更是顯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塵拔俗的耿直人格。
此詞與王安石晚年的詩作相似,以精煉的筆墨描繪了美麗如畫的湖光山色。詞中營造出清雋秀麗、悠閑恬靜的意境,以此來抒發灑脫放達之情,以求得精神上的慰安和解脫。詞人描繪春景時,無典故,不雕琢,語言清新、自然,數筆就勾出一幅鮮明秀麗、清俊嫻靜的畫面,其中有日景、夜景,有青山緑水、花紅柳翠的明麗色彩,也有流水潺潺、黃鸝鳴囀的聲響,而作者的形象就淡入這畫面中。全詞安逸恬淡的生活情景中寄寓着政治傢的襟懷心志,嫻雅流麗的風格中顯示出作者的才情骨力,體現了王安石詞素潔平易而又含蓄深沉的詞風。
菩薩蠻
晏幾道
哀箏一弄湘江麯,聲聲寫盡湘波緑。
纖指十三弦,細將幽恨傳。
當筵秋水慢,玉柱斜飛雁。
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
晏幾道詞作鑒賞
此詞藉寫彈箏來表現當筵演奏的歌妓心中的幽恨。
詞的上片暗寫湘靈鼓瑟的典故,點出“幽恨”;下片並未具體展開寫幽恨,衹寫弄箏的情態,而幽恨自見。黃蓼園謂此詞“末句意濃而韻遠,妙能藴藉”。
起筆一句先寫彈奏。箏稱之為“哀箏”,感情色彩極為明顯。“一弄”,奏一麯。麯為“湘江麯”,內容亦當與舜及二妃一類悲劇故事有關,由此可見酒筵氣氛和彈箏者的心情。“寫盡湘波緑”,湘水以清澈著稱,“緑”為湘水及其周圍原野的色調。但緑色彩分類上屬冷色,則又暗示樂麯給予人心理上的感受。
“寫”,指彈奏,而又不同於一般的“彈”或“奏”;似乎彈箏者的演奏,像文人的用筆,雖然沒有文詞,但卻用箏聲“寫”出了動人的音樂形象。
上片歇拍兩句,讓人想到彈箏者幽恨甚深,非細彈不足以盡情傳達,而能將幽恨“細傳”,又足見其人有很高的技藝。從“纖指”二句的語氣看,詞人對彈箏者所傾訴的幽恨是抱有同情的,而所傳之幽恨即是雙方所共有的。詞之上片,着重從演奏的內容情調方面寫彈者。
下片轉寫彈者的情態。“當筵秋水慢”,“秋水”代指清澈的眼波。“慢”,形容凝神,指箏女全神貫註。“玉柱斜飛雁”,箏上一根根弦柱排列,猶如一排飛雁。飛雁古詩詞中,常與離愁別恨相連,同時湘江以南有著名的回雁峰。因此,這裏雖是說弦柱似斜飛之雁,但可以想見所奏的湘江麯亦當與飛雁有聯繫,寫箏柱之形,其實末離開彈箏者所傳的幽恨。“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春山,指像山一樣彎彎隆起的雙眉,是承上文“秋水”而來的,用的是卓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西京雜記》)的典故。女子凝神細彈,表情一般應是從容沉靜的,但隨着樂麯進入斷腸境界,箏女斂眉垂目,凄涼和悲哀的情緒還是明顯地流露了出來。
這首詞以回蕩飄忽的筆勢,刻畫一位哀豔動人的彈箏藝妓——小蓮哀豔動人的形象。全詞以“哀箏一弄湘江麯”摹然開篇,又以“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驟然收筆,中間不平鋪直敘而抓住最富有表現力的動作、神態來寫,極具藝術感染力。
菩薩蠻
魏夫人
溪山掩映斜陽裏。
樓臺影動鴛鴦起。
隔岸兩三傢,出墻紅杏花。
緑楊堤下路,早晚溪邊去。
三見柳綿飛,離人猶未歸。
魏夫人詞作鑒賞
此詞寫景以抒情,情因景生,描繪了思婦盼望遠行丈夫歸來的情思。全詞緊緊圍繞一個“溪”字構圖設色,表情達意,寫得清新自然,不落俗套,饒有情韻,耐人尋味。
首句“溪山掩映斜陽裏”寫斜陽映照下的溪山,側重點於“溪”字。次句“樓臺影動鴛鴦起”,補足上文,進一步寫溪中景色。夕陽斜照之下,溪中不僅有青山的倒影,而且還有樓臺的倒影,還有對對鴛鴦溪中嬉水。上句專寫靜景,下句則動中有靜。“樓臺影動”,表明溪水微風吹拂之下,蕩起層層緑波,樓臺的影子也仿佛晃動一般。再添上“鴛鴦起”一筆,整個畫面就充滿了盎然生趣。
三、四兩句寫兩岸景色,這條溪水的兩岸,衹住着兩三戶人傢,人煙並不稠密,環境自然是幽靜的。至此,上面所說的樓臺原是這幾戶臨水人傢的住宅,全詞意脈連貫,針綫綿密。這句為實寫,下一句便是虛寫,如此虛實相生。深院高墻,關不住滿園春色,一枝紅杏花,帶着嬌豔的姿態,硬是從高高的圍墻上探出頭來。此句的妙處於一個“出”字,詞以“出”字形容紅杏花,寫出了春天的勃勃生機,意味雋永。
詞的下片,轉入抒情,但仍未脫“溪”字。溪水旁邊,有一道長堤,堤上長着一行楊柳,暮春時節,嫩緑的柳絲籠罩着長堤,輕拂着溪水,而魏夫人作為臨水人傢的婦女,是經常從這裏走過的。“早晚”一詞,並非指時間的早和晚。張相《詩詞麯語辭匯釋》捲六雲:“早晚,猶雲隨時也;日日也。”其義猶如舒亶《鵲橋仙》詞“兩堤芳草一江雲,早晚是西樓望處”。
古代,水邊柳外,往往是送別的場所。據《宋史·曾布傳》,曾布於神宗元豐中,連知秦州、陳州、蔡州和慶州。陸遊《老學庵筆記》捲七也說:“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主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雲:”使君自為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這期間,曾佈告別傢人,遊宦外,可能連續三年。此處,當指魏夫人填詞述懷。結尾二句說明她溪邊已徜徉了三年,年年都見過一次柳絮紛飛。從柳絮紛飛想到當年折柳贈別,這是很自然的。”三見柳綿飛“是實語,而着一”猶“字,便化實為虛了,這樣,哀怨之情,離別之恨,便隱然流於言外。
此詞聲律上極具特色,八句中兩句一葉韻,如“裏”與“起”、“傢”、與“花”、“路”與去、“飛”與“歸”,均押韻工整;且兩句與兩句之間又平仄交錯,如上片四句“裏”與“起”是仄聲韻,“傢”與“花”是平聲韻;下片“路”與“去”是仄聲韻,“飛”與“歸”是平聲韻,讀來十分諧婉,再加上語言曉暢,詞句清麗,較好地抒寫了貴族婦女溫柔敦厚而又婉麯纏綿的感情。
菩薩蠻
回文。夏閨怨
蘇軾
柳庭風靜人眠晝,晝眠人靜風庭柳。
香汗薄衫涼,涼衫薄汗香。
手紅冰碗藕,藕碗冰紅手。
郎笑藕絲長,長絲藕笑郎。
蘇軾詞作鑒賞
東坡的回文詞,兩句一組,下句為上句的倒讀,這比起一般回文詩整首倒讀的作法要容易些,因而對作者思想束縛也少些。東坡的七首回文詞中,如“郵便問人羞,羞人問便郵”、“顰淺念誰人,人誰念淺顰”、“樓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樓”、“歸不恨開遲,遲開恨不歸”等,下句補充發展了上句,故為妙構。這首回文詞是作者“回時閨怨”中的“夏閨怨”。
上片寫閨人晝寢的情景,下片寫醒後的怨思。用意雖不甚深,詞語自清美可誦。“柳庭”二句,關鍵一“靜”字。上句云“風靜”,下句云“人靜”。風靜時庭柳低垂,閨人睏倦而眠;當晝眠正熟,清風又吹拂起庭柳了。同是寫“靜”,卻從不同角度着筆。靜中見動,動中有靜,頗見巧思。三、四句,細寫晝眠的人。風吹香汗,薄衫生涼;而涼衫中又透出依微的汗香。變化“薄衫”與“薄汗”二語,寫衫之薄,點出“夏”意,寫汗之薄,便有風韻,而以一“涼”字串起,夏閨晝眠的形象自可想見。過片二句,是睡醒後的活動。她那紅潤的手兒持着盛了冰塊和蓮藕的玉碗,而這盛了冰塊和蓮藕的玉碗又冰了她那紅潤的手兒。上句的“冰”是名詞,下句的“冰”作動詞用。
古人常鼕天鑿冰藏於地窖,留待夏天解暑之用。杜甫《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寫以冰水拌藕,猶本詞“手紅”二句意。“郎笑耦絲長,長絲藕笑郎”,收兩句為全詞之旨。“藕絲長”,象徵着人的情意綿長,古樂府中,常以“藕”諧“偶”,以“絲”諧“思”,藕節同心,故亦象徵情人的永好。《讀麯歌》:“思歡久,不愛獨枝蓮(憐),衹惜同心藕(偶)。”自然,郎的笑是有調笑的意味的,故閨人報以“長絲藕笑郎”之語。笑郎,大概是笑他的太不領情或是不識情趣吧。郎的情意不如藕絲之長,末句始露出“閨怨”本意。
這首詞格律、內容感情、意境等方面都符合回文詞的要求,同時又不失作者的大傢氣派,實為難得。
菩薩蠻
舒亶
畫船捶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
去住若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衹是人南北。
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舒亶詞作鑒賞
這是一首惜別詞。作者詞中以一推一輓之情勸住對方的眼淚,這種抒寫傷離恨別心緒的表現手法,與宋詞中寫離別時常見的纏綿悱惻、肝腸痛斷、難捨難分的情狀有所不同。
這首詞從送別寫起。捶鼓,猶言敲鼓,是開船的信號。船傢已擊鼓催行,而這一邊卻樓上把盞勸酒。“催”,見時間之難以再延。“留”,見送行人之殷勤留戀。一“催”一“留”,就把去和住的矛盾突出出來了,並且帶動全篇。“去住若為情,即由首二句直接逼出,欲去不忍,欲住不能,何以為情?這一問見別離之極度苦人。”西江潮欲平“的好處於沒有直接回答問題,而是由前面擊鼓催客、高樓把酒的場面推出一個江潮漲平的遼闊場景。句中的”欲“字包含了一個時間推進過程,說明話別時間頗長,而江潮已漸漸漲滿,到了船傢趁潮水開航的時候了。
換頭就江潮生發,潮水有信,定時起落,所以說“容易得”,然而它能送人去卻未必會送人來。一旦南北分離,相見即無定期故云“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結穴處一筆宕開,頗值得玩味。“此樽空”,遙承上片次句“把酒留君”,“樽空”見情不忍別,共拚一醉。但即使飲至樽空,故人終不可留,所以結尾則由嘆見面之難,轉思它日再會,發出“知君何日同”的感慨。
宋代曾季貍《艇齋詩話》評這首詞“甚有思緻”概因此詞藉江潮抒別情,不僅情景交融,同時還顯出情景與意念活動相結合的特點。詞“去住若為情”這樣的思忖後,接以“江頭潮欲平”,看上去是寫景,實際上卻把思索和情感活動帶進了景物描寫,那茫茫的江潮似乎融匯着詞人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浩渺的情思。
下片“江潮容易得,衹是人南北”仍不離眼前景象,而更側重寫意念,以傳達人物的心境。結尾二句雖然表現為感慨,卻又是循上文章活動繼續發展的結果。
所循的思路應該是:今日樽空而潮載君去,但未知潮水何日能復送君歸來。依然是情景和思忖結合。詞中以回環往復的語言節奏,來表現依依不捨、綿長深厚的“思緻”。
菩薩蠻
黃庭堅
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着無人喚。
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
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黃庭堅詞作鑒賞
據此詞原序所說,這首《菩薩蠻》當是戲擬王安石集句詩之作。
開首二句以極自然輕盈的筆法描繪了一幅閑適悠雅的溪橋野漁圖。一片氤氳迷蒙的山嵐水霧中,是煙是雨,叫人難以分辨,真是空翠濕人衣。溪邊橋畔,有漁翁正醉酒酣睡,四周闃無聲息,沒有人來驚破他的好夢。“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化用杜甫“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長”(《西郊》)和“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絶句二首》)這句詩。兩句詩不僅從字面看放這裏十分熨貼,而且從原作的意境看,也與這首詞情相合,更重要的是通過這詩句的媒介,將讀者導嚮了杜甫的詩境,這些詩境又反過來豐富了這首詞本身的意藴。這樣便活畫出整個風光明媚生機勃勃的春世界。
“江山如有待”為作者移用的杜甫《後遊》中的詩句,作者嚮往大自然的美好,卻推開自己不說,而從對面着筆,將自己熱烈的感情移植到無生命的江山自然上,通過擬人化的描寫,表現“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那種人與自然交流相親、物我不分的情感意緒。這樣,詞上下片意境相應,衹將前面“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詞意發展為對自然生活的嚮往與追求。作者自然地想到了開隱逸風氣的陶潛,遂又隨手拈來了杜甫的另一句詩“此意陶潛解”(《可惜》),將自己對山川自然的企慕之意,又落實到對這位拋棄榮利的田園先哲的景仰上,從而挑出了全詞隱逸的主題。
杜甫感嘆生不逢時,恨不能詞的最後二句“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接住杜甫“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杜甫《可惜》)詩意,表明自己的態度,他不學杜甫的感慨而是步先哲的後塵。作者决心歸隱,但到底去何方,卻無可告,不過如隨之而去,一定會明白他的蹤跡。這一結語將上面貫串下來的情志意趣,結束得非常工穩,飄逸而含蓄。
這首詞全靠直接剝錄他人詩句而成,雖非作詞之正道,卻也頗有移花接木之妙。
菩薩蠻
賀鑄
彩舟載得離愁動,無端更藉樵風送。
波渺夕陽遲,銷魂不自持。
良宵誰與共,賴有窗間夢。
可奈夢回時,一番新別離!
賀鑄詞作鑒賞
此詞突破了嚮來以山、水、煙、柳等外界景物來喻愁的手法,把難於捉摸、無影無蹤的抽象愁情表現得具體可感,生動形象。全詞從上片的奇特聯想,無端怨責,到下片的文心起伏,一波三折,寫有情人分別後思想感情的一係列變化,極為細膩真實。尤其是“因思成夢。夢回新別的設想,更是抓住了情的關鍵。
起首一句“彩舟載得離愁動”,“彩舟”,是行人乘坐之舟。長亭離宴,南浦分攜,行前執手,一片哀愁,而今蘭舟已緩緩地離開了碼頭。然而這位行人的心頭卻還是那樣悲哀,他甚至覺得這載人載貨的舟上,已經裝滿了使人不堪負擔的離愁,真是聯想奇特,語新意深。
第二句“無端更藉樵風送之”“無端”,無緣無故,沒來由:“樵風”,典出《會稽記》。講的是鄭宏年輕時上山砍柴,碰到了一位神人。他嚮神人請求若耶溪上“旦,南風;暮,北風”,以利於運柴,後果如所願。此處用“樵風”,即有順風的意思。這一句寫的是:船藉着順風飛快地遠航而去,那伫立岸邊送行的心上人的倩影,很快就不可得見。詞人五內俱傷,哀感無端,不由地對天公産生了奇特的怨責:為什麽偏偏這個時候,沒來由送來一陣無情的順風,把有情人最後相望的一絲安慰也吹得幹幹淨淨呢!
第三句“波渺夕陽遲”,詞意由密轉疏,情中布景。詞人展望前程,天低水闊,煙波迷離。一抹夕陽的餘暉,沉沉的暮靄之中,看上去是那樣的凄涼。獨立蒼茫,一葉孤舟上煢煢孑立的行人遂生“銷魂不自持”的無限感慨!魂銷魄散,惝恍迷離,凄惻纏綿,無復生意。
換頭重筆另開,設想別夜的落寞惆悵。“良宵誰與共”,明知無人共度良宵而故作設問,突出了捨心上人而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和自己共度時光的執着癡情。“賴有窗間夢”句是說,衹有獨臥窗下,神思魂縈的夢境中才能和心上人再一次相見。一個“賴”字,說明詞人要把夢中的歡聚作為自己孤獨心靈的唯一感情依托。這兩句,一問沉痛,一答哀婉,有力地表現了自己別後的孤獨和凄涼。詞人煞費苦心地為自己構築了一個癡情而又感傷的希望,冷酷的現實面前,又不得不親手把它擊得粉碎。
結拍“可奈夢回時,一番新別離!”是說夢中的歡會誠然是纏綿熱烈的,無奈夢總是要醒的;而夢醒之後,一番夢會之歡欣恰又導致了“一番新別離”的痛苦!全詞以感慨作結,餘音不絶,抓住了愛情的關鍵,夢回新別離的痛苦更甚,如此作法,言盡而味不盡。
菩薩蠻
趙令畤
春風試手先梅蕊,頩姿冷豔明沙水。
不受衆芳知,端須月與期。
清香閑自遠,先嚮釵頭見。
雪後燕瑤池,人間第一枝。
趙令畤詞作鑒賞
此為詠梅之作。作者與蘇東坡過從甚密,東坡為愛其纔,曾薦其於朝。東坡因政爭遭貶謫時,作者亦受牽纍。此詞顯然是藉梅花以寓性情,並非徒然詠物之作。
詞之首句起筆不凡,以擬人手法寫春風似乎可以用她那靈巧的“手”,啓開冰封雪蓋的萬物,而且最“先”使梅花吐出了嫩蕊!“拭手”而先,仿佛是春風對梅花特別鐘情。句法峭勁,旋折有力。次句即繪出梅花的丰采:資色美麗(頩),冷韻幽香,相伴着它的是明沙淨水。這句七個字,“頩姿冷豔”寫梅花本身:“明沙水”顯示出一片冰清素潔、纖塵不染的環境。彼此映襯,更給人以豐姿枯、神采奕奕的感覺。這裏詞人賦予梅花明沙淨水的環境,有着深刻的寓意。
三四兩句,點出梅花的風骨、品格“不受衆芳知”,言梅,態度不卑不亢,從容而自矜。“端須月與期”,詞情突然揚起,說衹有月亮纔配與梅花作伴。前句抑,後句揚,抑揚之間,把梅花格調的高絶,推上頂峰。
下片層層推進地刻畫梅花的風神。前兩句與後兩句看似梅花與人分而言之,其實與人仍是刻繪梅花。“清香閑自遠”,梅花的香是“清香”,清幽而淡遠:“先嚮釵頭見”,女人們把梅花連同釵飾插頭上。這裏又用了一個“先”定,再現出她與衆芳的不同。“雪後燕瑤池”,想象瑰麗而神奇,極富藝術魅力。瑤池,相傳為西王母居住的仙境。“人間第一枝”,可以理解為即使天堂仙境,也有人間花魁—梅花,也可理解為梅花超凡脫俗,冰肌玉骨,豔絶群芳,如同那瑤池仙子一般清麗、孤高。
這首詞藝術構思和手法上頗具匠心,極具深沉流美、委婉麯折之妙。全詞融情於景,托物抒懷,通過塑造梅花冷豔幽姿、清香惹人。孤高冷傲的風流標格,寄寓了詞人的襟懷和性情,讀來回味無窮,一唱三嘆。
溫庭筠《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綉羅襦,雙雙金鷓鴣 .
譯文:
眉妝漫染
疊蓋了部分額黃
鬢邊發絲飄過
潔白的香腮似雪
懶得起來
畫一畫蛾眉
整一整衣裳
梳洗打扮
慢吞吞
意遲遲
照一照新插的花朵
對了前鏡
又對後鏡
紅花與容顔
交相輝映
剛穿上的綾羅裙襦
綉着一雙雙的金鷓鴣
賞析:這首《菩薩蠻》,為了適應宮廷歌伎的聲口,也為了點綴皇宮裏的生活情趣,把婦女的容貌寫得很美麗,服飾寫得很華貴,體態也寫得十分嬌柔。仿佛描繪了一帽唐代仕女圖。
詞的上片,寫床前屏風的景色及梳洗時的嬌慵姿態;下片寫妝成後的情態,暗示了人物孤獨寂寞的心境。全詞委婉含蓄地揭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並成功地運用反襯手法。鷓鴣雙雙,反襯人物的孤獨;容貌服飾的描寫,反襯人物內心的寂寞空虛。表現了作者的詞風和藝術成就。
菩薩蠻
黃庭堅
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着無人喚。
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
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黃庭堅詞作鑒賞
據此詞原序所說,這首《菩薩蠻》當是戲擬王安石集句詩之作。
開首二句以極自然輕盈的筆法描繪了一幅閑適悠雅的溪橋野漁圖。一片氤氳迷蒙的山嵐水霧中,是煙是雨,叫人難以分辨,真是空翠濕人衣。溪邊橋畔,有漁翁正醉酒酣睡,四周闃無聲息,沒有人來驚破他的好夢。“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化用杜甫“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長”(《西郊》)和“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絶句二首》)這句詩。兩句詩不僅從字面看放這裏十分熨貼,而且從原作的意境看,也與這首詞情相合,更重要的是通過這詩句的媒介,將讀者導嚮了杜甫的詩境,這些詩境又反過來豐富了這首詞本身的意藴。這樣便活畫出整個風光明媚生機勃勃的春世界。
“江山如有待”為作者移用的杜甫《後遊》中的詩句,作者嚮往大自然的美好,卻推開自己不說,而從對面着筆,將自己熱烈的感情移植到無生命的江山自然上,通過擬人化的描寫,表現“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那種人與自然交流相親、物我不分的情感意緒。這樣,詞上下片意境相應,衹將前面“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詞意發展為對自然生活的嚮往與追求。作者自然地想到了開隱逸風氣的陶潛,遂又隨手拈來了杜甫的另一句詩“此意陶潛解”(《可惜》),將自己對山川自然的企慕之意,又落實到對這位拋棄榮利的田園先哲的景仰上,從而挑出了全詞隱逸的主題。
杜甫感嘆生不逢時,恨不能詞的最後二句“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接住杜甫“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杜甫《可惜》)詩意,表明自己的態度,他不學杜甫的感慨而是步先哲的後塵。作者决心歸隱,但到底去何方,卻無可告,不過如隨之而去,一定會明白他的蹤跡。這一結語將上面貫串下來的情志意趣,結束得非常工穩,飄逸而含蓄。
這首詞全靠直接剝錄他人詩句而成,雖非作詞之正道,卻也頗有移花接木之妙。
菩薩蠻 韋莊
紅樓別夜堪惆悵,
香燈半捲流蘇帳。
殘月出門時,
美人和淚辭。
琵琶金翠羽,
弦上黃鶯語。
勸我早歸傢,
緑窗人似花。
人人盡說江南好,
遊人衹合江南老。
春水碧於天,
畫船聽雨眠。
垆邊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還鄉,
還鄉須斷腸。
如今卻憶江南樂,
當時年少春衫薄。
騎馬倚斜橋,
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麯,
醉入花叢宿。
此度見花枝,
白頭誓不歸。
勸君今夜須瀋醉,
尊前莫話明朝事。
珍重主人心,
酒深情亦深。
須愁春漏短,
莫訴金杯滿。
遇酒且呵呵,
人生能幾何。
洛陽城裏春光好,
洛陽才子他鄉老。
柳暗魏王堤,
此時心轉迷。
桃花春水淥,
水上鴛鴦浴。
凝恨對殘暉,
憶君君不知。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衹合江南老。
○○●●○○▲,○○●●○○▲
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
垆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
現代作品:
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 溫庭筠
小山重疊金明滅,
鬢雲欲度香腮雪。
懶起畫蛾眉,
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
花面交相映。
新貼綉羅襦,
雙雙金鷓鴣。
【簡析】
初日的光輝映着畫屏,屏山重重疊疊,金光閃爍。閨中人猶未起床,一抹烏雲般黑亮的秀發,拂揚在雪白重豔的腮上。雖然是無心緒不欲起床,終於還是懶洋洋的起來了。 但卻是慢騰騰地梳洗,妝扮,描畫蛾眉。畢竟是位美的女子。她的雙鬢簪了鮮花,對着妝臺上的座鏡從正面照,又拿着帶柄的手鏡從背後照,端詳簪花是否妥恰,同時,亦在顧盼自己的美豔。前後兩鏡交相輝映,花光與人面亦相互映襯。妝扮完畢,開始了一天的女工:綉羅襦。此時新貼的花樣,偏偏是成雙成對的金鷓鴣,她不禁心所感。
【菩薩蠻·大柏地】毛澤東
赤橙黃緑青藍紫,
誰持彩練當空舞?
雨後復斜陽,
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
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
今朝更好看。
菩薩蠻 陳剋
緑蕪墻繞青苔院,中庭日淡芭蕉捲。
蝴蝶上階飛,烘簾自在垂。
玉鈎雙語燕,寶秋楊花轉,
幾處箥錢聲,緑窗春睡清。
菩薩蠻 (五代)韋莊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衹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垆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賞析】
這是一首閨情詞。上片描繪庭院暮春景色,緑草滋蔓,苔深蕉捲,蝶飛簾垂,一派幽靜;下片寫“緑窗睡清”,因而聽到玉鈎燕語,幾處箥錢聲,表現閨中人的孤獨寂寞和淡淡的憂愁。本詞寫美人春日晝眠之景,刻畫細緻入微,環境烘托,氣氛渲染均極為成功。前六句層層推進,最後兩句輕輕一筆點題結篇,結構別緻,很受推賞。全詞寓情於景,溫婉柔媚,清新倩麗,體現了婉約詞豔麗的風格。 |
|
關於李白作這《菩薩蠻》之說最早見於北宋僧文瑩《湘山野錄》捲上。但是自宋代以來,就一直有人對各種詞選所收的李白詞半信半疑。上個世紀以來這個問題的討論變得更加的激烈,本人主要從麯調來源,版本問題,以及寫作風格,詞的發展來考證。
我們首先來看看《菩薩蠻》這個調名最早的來源,衆所周知,現存最早記載《菩薩蠻》的材料就是晚唐人蘇鶚所撰《杜陽雜編》捲下的一段文字:“大中初,女蠻國貢雙竜犀……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詞麯,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後來錢易的《南部新書》捲五,王灼《碧雞漫志》捲五,所載與此同。如果開元時即有這個麯調的話,那麽開元離大中相差130 餘年,中間竟然沒有一個人仿作此調,而到大中、鹹通間忽然盛極一時,“考諸文學演變之跡必無是理。”從文學的發展角度來看是完全不合理的。唐圭璋、潘君昭在《論詞的起源》一文中說:“《菩薩蠻》《教坊記·麯名表》及敦煌麯均有此調名,李白在開元、天寶時依調作詞完全有可能。”李從軍在賞析《菩薩蠻》詞時亦云:“《教坊記·麯名表》及敦煌麯均有此調名。《教坊記》作者崔令欽乃盛唐時人,書成於安史之亂後,所記乃開元時調名。可見盛唐時已有《菩薩蠻》麯。”但是我們查現有的材料發現,根據《中國古典戲麯論著集成·教坊記》,現存最早的《教坊記》刻本為南宋曾造所編的“類說本”且係“刪節選錄本”,故其“字句多有壓縮改動,不完全按照原書。”鬍適在《詞的起源》一文中對《教坊記》做了具體的考察,認為其中麯調多為“後人隨時添加”,因此“不可用來考證盛唐教坊有無某種麯調”的依據。這種觀點也得到了王國維的認可。後來《辭源》也持這樣的觀點,《辭源》(合訂本) 釋“教坊記”條“唐崔令欽撰。一捲。記述唐代教坊制度、軼聞及麯調來源等,以開元時事為多,並錄教坊大麯雜麯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據《說郛》,有所刪削,已非全書。”《辭海》(縮印本) 說《教坊記》“書約成於寶應元年(762) 後。”陰法魯即認為此書“可能經過後人訂補”。因此《教坊記》有麯名,並不能說明開元時已有此調名。
認為此詞為李白作品的學者一般都會引用《湘山野錄》中一段話“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瞑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伫立,宿燕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於子宣內翰傢,乃知李白所作。”這裏的“古集”應作“古風集”,詹鍈的《李白詩論叢·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辨偽》可以佐證,他作了詳實的考證後說“繆曰芑影刻北宋晏處善本李太白集《菩薩蠻》《憶秦娥》二詞均不載”,又說“晏處善本太白集,為宋敏求所裒集,曾鞏嘗考其先後而次第之。《湘山野錄》謂太白《菩薩蠻》原見於曾子宣傢藏《古風集》。子宣名布,為鞏之胞弟,所藏《古風集》有太白《菩薩蠻》,鞏豈有未見之理??既見之而不編入《太白集》,則《菩薩蠻》一詞必有可疑之點至明。”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北宋蜀刻本,該本屬宋敏求、曾鞏所編次之《李太白文集》30捲本係統,是元豐三年(1080)李白集的第一個刻本——蘇州本的翻刻本。該本衹將《清平調》3首、《白鼻靬》、《結襪子》等作品作為“歌詩·樂府”收錄,將“秋風清”作為“歌詩·雜詠”收錄,而沒有收錄《菩薩蠻》、《憶秦娥》、《連理枝》、《清平樂》等詞作。由此也可以做為一個佐證。
此詞的另一個爭論點就是“寫於鼎州滄水驛樓”。鼎州是今湖南常德的古稱,在沅江邊,離洞庭湖尚遠。楊憲蓋說是“李白的手跡”,那麽李白自己是否曾到此一遊? 這裏要談一下李白的生平遊蹤。李白詩文係年的研究,宋代即已開始,今天能見到的李白年譜有《翰林李太白年譜》(宋薛仲邕著) 、《李太白年譜》(清王琦著) 、《李太白年譜》(晚清黃錫王圭著) 、《李白詩文係年》(詹鍈著) 、《李白杜甫年表》(郭沫若著) 等等,其中,詹鍈所作年譜“於詩文係年,徵引豐富,考訂翔實,為諸譜之冠”,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更之”,我們查閱這些年表傳記以及根據詹鍈《李白遊蹤圖》可參看。李白一生從未到過常德,他所有的傳記裏也未提到他到過常德,李白的詩文裏也看不出他到過常德,怎麽會孤零零地冒出這麽一首《菩薩蠻》來呢!”從李白到魏泰已過去三百餘年,為什麽李白的手跡能獨獨被魏氏所發現呢?
從詞的風格和李白原有作品的風格來考究這首詞,甚至認為是“盛唐氣象”的另外一種表現,如李從軍認為李白的《古風》(四十六)與這首《菩薩蠻》的氣象相接近,因此斷定這首詞是李白所作。但我們看《菩薩蠻》全詞境界高遠,廣漠,而更有寂寞清冷、老氣橫秋的情感。這樣的作品與李白一貫的豪放飄逸的氣質並不相符合,明鬍應麟說“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因而單憑一首作品的風格及藝術特點很難斷定李白是這首《菩薩蠻》的作者。
另外從詞的發展角度看,現存而又可以確定的初、盛唐文人詞,均為詩而非嚴格意義上的詞,雖然盛唐時期音樂文化高度發達,但是“依麯拍填詞”卻是處於一種空白階段,因此我們可以認定盛唐時期是不曾有定型的成熟的詞體。但是這首《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竚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完全符合現在成熟的《菩薩蠻》(“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的平仄。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有所懷疑。
綜上所述,我認為這首詞不是李白的作品,應該是他人藉李白之名所作的。 |
|
|
|
〔題考〕 【杜陽雜編】:「大中初,女蠻國貢雙竜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麯﹞,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唐音癸簽】、【南部新書】略同。又【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丞相假飛卿所撰密進之,戒以勿泄。」唐時俗稱美女為菩薩,菩薩蠻酋稱女蠻。當時教坊,譜作麯詞,遂為詞名。後楊升庵改蠻為鬘,失其本矣。後人又名為﹝重疊金﹞、﹝子夜歌﹞、﹝巫山一片雲﹞等,非特於詞名來源無涉,且﹝子夜歌﹞另有正調,而﹝巫山一片雲﹞更易與別調﹝巫山一段雲﹞相混,殊屬無取。
〔作法〕 本調四十四字,為詞調中之最古者,即以五七言組成;通篇兩句一韻,凡四易韻,兩平兩仄。第一、二句即為七言仄句。第三句為仄起之五言句,換用平韻。第四句為五言拗句。後半第一句為平起仄韻之五言句。第二句為仄起仄韻之五言句。第三、四句與前半第三四句同。此首相傳為太白創作,但這兩首詞沒有收入宋本《李太白集》,而始見於宋人筆記,是否李白作品,頗滋後世疑問。明代鬍應麟、鬍震亨等已疑為後人偽托。現代學者也頗多不信為李白所作,一個主要理由是唐代前期文人詞尚處在萌芽狀態,文辭體製,都較簡樸,而這兩首詞卻是用雙調,換韻,語言精練,描寫細緻,在藝術上很成熟,顧按上述,調之創始,在唐 大中初,則白又何以見此詞調?【詞苑叢談】謂:「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屑為,寧肯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絶類溫方城輩,蓋晚唐詞嫁名太白耳。」按諸上,引【北夢瑣言】與此說相合。近世鬍適作【詞選】亦云然。
定格:
平林漠漠煙如織,
⊙○⊙●○○▲ (仄韻)
寒山一帶傷心碧。
○○●●○○▲ (協仄韻)
暝色入高樓,
●●●○△ (換平韻)
有人樓上愁。
●○○●△ (協平韻)
玉階空伫立,
⊙○○●▲ (三換仄)
宿鳥歸飛急。
⊙●○○▲ (協三仄)
何處是歸程,
⊙●●○△ (四換平)
長亭連短亭。
⊙○○●△ (協四平)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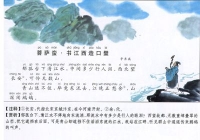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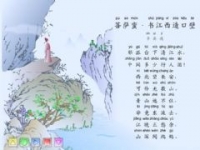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餘,山深聞鷓鴣。
全部註釋
1.造口:一稱皂口,在今江西萬安縣西南六十裏。
2.鬱孤臺:在今江西贛縣西南。《贛州府志》:"鬱孤臺,一名賀蘭山。隆阜鬱然孤峙,故名。"清江:此指贛江。
3. 長安:代指都城汴京。
這是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詞人任江西提點刑獄、駐節贛州時寫的詞。羅大經《鶴林玉露》雲:"南渡之初,虜人追隆佑太後禦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由此起興。" 辛棄疾登上鬱孤臺,回想四十七年前金兵長驅直入江南、江西腹地,南宋幾乎滅亡之事,從奔騰的清江之水,想到了當年隆佑太後一行匆匆逃竄的蹤影,以及因傢國破亂而灑下的痛楚之淚。由水及淚,意象轉換極為自然。"青山遮不住"兩句,表達了詞人對抗金恢復的堅定意志。煞拍兩句,蓋有豪興逸懷,當此日暮江景,畢竟憂思難擋,愁從中來。《鶴林玉露》認為結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而鄧廣銘則認為;蓋深慮自身恢復之志未必即得遂行,非謂恢復之事决行不得也。"似乎鄧說更契合稼軒詞境詞心。全詞用的是比興手法。周濟《宋四傢詞選》說:"藉山怨水"。它以山水起興,一掃傳統《菩薩蠻》小令富豔輕靡之格,而出之以激越悲壯之音,令人耳目一新。梁啓超評此詞說:"《菩薩蠻》如此大聲鏜鞳,未曾有也。"(《藝蘅館詞選》)總的來說,這首詞熱情洋溢,,慷慨激昂,富有收復失地,統一祖國的感情。 |
|
【內容】:
歸鴻聲斷殘雲碧,
背窗雪落爐煙直。
燭底鳳釵明,
釵頭人勝輕。
角聲催曉漏,
曙色回牛鬥。
春意看花難,
西風留舊寒。
【註釋】:
歸鴻:這裏指春天北歸的大雁。
碧:青緑色。
背窗:身後的窗子。
鳳釵:古代婦女的一種首飾。釵名有時因釵頭的形狀而異。
人勝:古時正月初七為“人日”,剪彩為人形,故名人勝。勝,古代婦女的首飾。
角:古時軍中樂器。有彩繪者,也稱畫角。
漏:古代滴水計時的器具。
牛鬥:即牛宿(二十八宿之一,相當於摩間羯座之一部分)、鬥宿(二十八宿之一,相當於人馬座一部分)。非一般的所說北斗星和牽牛星。
【賞析】:
此詞當為李清照南渡後的作品。上片寫黃昏後的室內外的景象,及永夜思念家乡的情景。下片寫拂曉室內外的景象和女主人難以看到梅花的惆悵,不言愁而愁自見。不假雕飾,意境幽遠。 |
|
【內容】:
風柔日薄春猶早,
夾衫乍著心情好。
睡起覺微寒,
梅花鬢上殘。
故鄉何處是?
忘了除非醉。
瀋水臥時燒,
香消酒未消。
【註釋】:
風柔:指春風和煦。
日薄:指日光淡薄。
乍著:剛剛穿上。
瀋水:通沉水 即沉香。香料名。
【賞析】:
此詞當為李清照後期的作品。寫女主人在一個早春白日對故國鄉關無限懷念的深情。李清照的懷鄉詞,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技巧都有很高的價值。應得到我們今人的特別珍重。 |
|
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嚮庭前過,
含笑問檀郎①,花強妾貌強?
檀郎故相惱,須道花枝好。
一面發嬌嗔,碎挼②花打人。
【註釋】
①檀郎:晉代潘嶽小名檀奴,姿儀美好,舊因以“檀郎”或“檀奴”作為對美男子
或所愛慕的男子之稱。
②挼:揉搓。“挪”的異體字。
【評解】
這首《菩薩蠻》,生動地描繪了折花美女天真嬌癡的神態,謳歌男女間的愛情。寫
得流麗自然,面又細膩入微。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民歌風味。 |
|
溫庭筠
小山重疊金明滅①,鬢雲欲度香腮雪②。懶起畫蛾眉,弄妝③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綉羅襦④,雙雙金鷓鴣⑤。
[註釋]
①小山:指屏風上雕畫的小山。金明滅:金光閃耀的樣子。
②鬢雲:象雲朵似的鬢發。度:覆蓋。香腮雪:雪白的面頰。
③弄妝:梳妝打扮。
④羅襦(rú):絲綢短襖。
⑤鷓鴣:這裏指裝飾的圖案。
[評解]
這首《菩薩蠻》,為了適應宮廷歌伎的聲口,也為了點綴皇宮裏的生活情趣,把婦女的容貌寫得很美麗,服飾寫得很華貴,體態也寫得十分嬌柔。仿佛描繪了一帽唐代仕女圖。
詞的上片,寫床前屏風的景色及梳洗時的嬌慵姿態;下片寫妝成後的情態,暗示了人物孤獨寂寞的心境。全詞委婉含蓄地揭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並成功地運用反襯手法。鷓鴣雙雙,反襯人物的孤獨;容貌服飾的描寫,反襯人物內心的寂寞空虛。表現了作者的詞風和藝術成就。
[集評]
張惠言《詞選》捲一:此感士不遇之作也。篇法仿佛《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捲一:飛卿詞如“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
張燕瑾《唐宋詞選析》:這首《菩薩蠻》不僅稱物芳美,也具有“其文約,其詞微”的特點,富有暗示性,容易使人産生種種聯想。
《中國歷代詩歌各篇賞析》:在這首詞裏,作者將許多可以調和的顔色和物件放在一起,使它們自己組織配合,形成一個意境,一個畫面,讓讀者去領略其中的情意,這正是作者在創造詞的意境上,表現了他的獨特的手法。 |
|
山亭水榭秋方半,鳳幃寂寞無人伴。
愁悶一番新,雙蛾衹舊顰。
起來臨綉戶,時有疏螢度。
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
朱淑真詞作鑒賞
朱淑真本人的愛情生活極為不幸,作為一位女詞人,她多情而敏感。詞中寫女主人公從缺月獲得安慰,不啻是一種含淚的笑顔。無怪魏仲恭在《朱淑真斷腸詩詞序》中評價其詞為“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同豈泛泛者所能及”。
“春秋多佳日”山亭水榭“的風光當分外迷人,但詞人卻以極冷漠的筆調作出此詞,因為”良辰美景奈何天“,消除不了”鳳幃“中之”寂寞“——獨處無郎,還有什麽賞心樂事可言呢?”鳳幃“句使人聯想到李商隱《無題》詩中的名句:”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如此情狀,叫人怎不顰眉,怎不愁悶?有意味的是,詞人使”愁悶“與”顰眉“分屬於”新“”舊“二字。”舊“字以見女主人公愁情之久長”新“字則表現其愁情之與日俱增。一愁未去,一愁又生,這是”新“;而所有的愁都與相思有關,這又是”舊“。”新“”舊“二字相映成趣,更覺情深。
輾轉反側,失眠多時,於是乃有“起來”而“臨綉戶”似乎是在期待心上人的到來。然而戶外所見,衹不過“時有疏螢度”而已,其人望來終不來。此時,女主人公空虛寂寞的情懷,是難以排遣的。在這關鍵處,詞人又卻又寫出了一絲安慰,也算是自慰吧!詞人給她一點安慰,一輪缺月,高挂中天,並賦予它人情味,說它因憐憫閨中人的孤棲,不忍獨圓。“多謝”二字,癡極妙極。同是寫孤獨情懷,蘇東坡在圓月上做文章:“不應有恨,何事長嚮別時圓”;朱淑真則在缺月上做文章“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移情於物,怨謝由我,真有異麯同工同妙。此詞最有興味之所在正是結尾兩句。 |
|
憶郎還上層樓麯。
樓前芳草年年緑。
緑似去時袍。
回頭風袖飄。
郎袍應已舊。
顔色非長久。
惜恐鏡中春。
不如花草新。
張先詞作鑒賞
這是一首以感春懷人為內容的閨怨詞。它運思、謀篇方面自出機杼,別具一格,推陳出新。全詞以顔色貫穿全篇,並用以巧妙運思、穿針引綫。詞之上片着眼於顔色的緑與緑之相同,使空間隔絶的近處芳草與遠方行人相連結,使時間隔絶的今日所見與夕日所見相溝通,從而使樓前景與心中情融會為一,合為詞境。下片着眼於顔色的新舊差異,使回憶中的昔時之袍與想像中的今日之袍相對照,使身上衣與境中人相類比,使容顔之老與花草之新形成反比。起首“憶郎還上層樓麯”一句通過閨中少婦登樓望遠的視綫,把她的一顆愁心送到遠方遊子的身邊。登樓望遠是古詩詞中常用的意象,多從空間落想,悵望行人此去之遠。第二句“樓前芳草年年緑”,則從時間落想,因見芳草“年年緑”而悵念行人遠行之久。這句詞肉於淮南小山《招隱士》賦“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及王維《山中送別》詩“春草明年緑,王孫歸不歸”,暗含既怨遊子不歸又盼遊子早歸的復雜意味。
上片末兩句,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個“緑”字為橋梁,從“芳草年年緑”到“緑似去時袍”,由望景過渡到懷人,感今過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從芳草之緑生發聯想,勾起回憶,想起郎君去時所着衣袍的顔色,並進而追憶其人臨去依依、回首相望時,衣袖隨風飄動的情景。這一細節深深印她的記憶之中,時時都會重現眼前,如今,因望見芳草緑、想到“去時袍”,當初的一幕幕又分明似眼前了。從這兩句詞,即可以想見詞中人當年別郎時的留戀,也可以想見其今日“憶郎”時的惆悵。牛希濟《生查子》詞中的:“記得緑羅裙,處處憐芳草。”可與這兩句詞參讀,不同的是:張先詞就居者立言;牛詞則擬居者口吻以囑咐行者。
過片兩句,緊承上片的三、四兩句。詞筆不離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樣是寫那件緑色的衣袍,但上兩句是回憶去時的袍色,這兩句是想象別後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時間上拉回到過去,後者則把萬縷柔情空間上載送到遠方。同時,這兩句又與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兩字遙相呼應,也是從時間落想,暗示別離之長久。正因別離已久,纔會産生衣袍已舊、怕那去時耀眼的緑色已經暗淡無光的推測。又從袍之舊、色之褪,觸發青春難駐、朱顔易改之感。於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鏡中春,不如花草新”兩句,把詞意再推進一步。詞中人之所惋惜、恐懼的是一個意義更深廣、帶有永恆性的人生悲劇,而不僅僅是一次別離的痛苦。離別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終有歸來之日,日後相逢之樂還可以補償今日相思之苦;至於人生短促、歲月無情,而居者與行者都會分離中老去,這卻是無可輓回、無可補償的,正所謂“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顔辭鏡花辭樹”(王國維《蝶戀花》)。這兩句詞,則對照眼前“芳草年年緑”之景,怨嘆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還會開;草枯了,明年還會緑;而人的青春卻一去不復返了。鏡中的春容衹會年年減色,不會歲歲更新。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白頭吟》)說的也是這樣的意思。
此詞謀篇方面句句相承、環環相扣。上片因“憶郎”而“上層樓”,因“上層樓”而見“樓前芳草”,因芳草之“緑”而回憶郎袍之“緑”,再因去時之“袍”而想到風飄之“袖”。首句與次句的兩個“樓”字,緊相扣合;次句與第三句的兩個“緑”字,上下鈎連;第四句的“袖”字固與第三句的“袍”字相應,句中的“回頭”兩字也暗與第三句的“去時”兩字相承,針綫綿密,過渡無痕。下片雖另起新意,卻與上片藕斷絲連。因三、四兩句回憶起去時之袍,過片兩句就進一步想象今日之袍;過片兩句的上、下句間,則是因衣袍之“舊”而致慨於“顔色非長久”。接下來的兩句,更因袍色之不長久而想到“鏡中春”也不長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緑”句,而有感於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脈絡井然,層次分明。 |
|
遊絲欲墮還重上,春殘日永人相望。
花共燕爭飛,青梅細雨枝。
離愁終未解,忘了依在前。
擬待不尋思,剛眠夢見伊。
杜安世詞作鑒賞
這首閨怨詞抓住具有特徵性的事物,含蓄委婉,獨具特色。
起筆“遊絲欲墮還重上”,詞人就抓住空中飄搖不定的“遊絲”來大做文章,是頗具匠心的。“遊絲”,也就是“睛絲”、“飛絲”、“煙絲”,是一種蟲類吐出的極細的絲縷,飄浮空氣之中,如果天氣晴朗,陽光璀璨,有時還可發現這種“遊絲”空中閃着水晶般透明的耀眼的光澤。作者通過這一細微的事物反映出癡情少女內心的微妙的波動,反映出這位少女對春天、對青春和對生活的熱愛。此詞“遊絲”一句,含蓄麯折,一語雙關。它表面上似寫景,實際卻寫少女的心境,用的是“諧音隱語”手法。詞裏“遊絲”,正是有意與“相思”的“思”字雙關。這一句形象地說明,少女的相思之情跟天上飄飛不定的“遊絲”一樣,一忽兒,像是要墜落下來;一忽兒,又扶搖直上。剛剛平靜下來的內心,也因此捲起了感情的漣漪。這不僅增強了詞的韻味,同時它還把詞中的景、事、情串接一起,使全詞意境和諧完整。
第二句:“春殘日永人相望”。說此情況下,“相望”的時間也隨之增長了。“春殘”,點明季節,春歸而人未歸。“日永”,白晝廷長。“花共燕爭飛,青梅細雨枝”二句是對“春殘”的補充,同時,它又是“人相望”的必然結果。雖然這位少女“相望”的是“人”,但因“人”千裏之外,可望而不可及,她所能見到的便衹能是落紅伴着雙飛的紫燕紛紛飄墜,是被雨滋潤過的梅枝上的青青梅子。這兩句還兼有映襯與象徵作用。花落春歸,燕已飛回,而人卻杳無歸期。
過片“離愁”二字,很自然地成為上下片轉折過渡的關鍵,並具有畫竜點睛的妙用。“離愁”與“遊絲”上下呼應。“離愁”因有“遊絲”的映襯而顯得鮮明具體,“遊絲”以“離愁”為內涵愈加顯得充實。因之,即使相望很久,都未能衝淡她的“離愁”,故曰“終未解”。不僅如此,詞人還補足一句:“忘了依前。”“忘了”二字之下省略了一個賓語,即末句的“伊”。即使你想方設法去忘卻他,可他還是跟從前一樣,清清楚楚地再現於你的眼前,再現於你的心頭。
接着又寫了兩句:“擬待不尋思,剛眠夢見伊。”以申明此意。“不尋思”即“忘了”,“夢見伊”即“依前”。作者不是正面表達她渴望與所思之人夢中相會,而是以“擬待不尋思”先跌一筆,再以“剛眠夢見伊”點出正意,來一個否定之否定,運筆新奇,因而就更引人入勝。
這首詞格調清新自然,情真意切,運思手法頗得民歌風韻,有語淺而意深之妙。 |
|
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
上馬苦匆匆,琵琶麯未終。
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
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孫洙詞作鑒賞
起首“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摧人去!”這兩句是牢騷話:剛剛二更時分,城樓上還要敲三通鼓纔天亮,何必這麽死命地催人走呢!據宋洪邁《夷堅甲志》捲四,翰林學士孫洙某晚正太尉李端願傢歡宴,有美女侍妾奏樂助興,恰逢此時朝廷宣召,心下不願,故出怨語。“何須抵死催人去”就是本此而發的牢騷。說:“尚有三通鼓”,而不說已過二更,表示離天亮還早,希望多玩一會兒。但留連不捨之意橫遭阻抑,自然轉化為憾恨之情。“抵死”,猶言死命、拚命,形容竭力。對於皇帝宣召,竟是如此不情願,可見這夜宴是何等令人留戀。“上馬苦匆匆,琵琶麯未終”,一邊匆匆上馬,一邊卻還戀顧那美妙的琵琶聲,深以未聽到麯終為憾。琵琶的誘人魅力來自那位彈奏的女子,言外藴含着對其人的深情眷戀。然而迷人的女樂,終究抵不住皇命的催逼,他衹得無可奈何地上馬離去了,但那聲聲琵琶似乎一直縈繞耳際。上片四句,一氣流註,節奏快速,皇命催人、刻不容緩的氣氛頓出,從而反襯出詞人不願從命而又不敢違命的矛盾感情。
過片寫主人公戀戀不捨,人雖已上馬,心尚留筵間,一路上還出神地回頭凝望。但馬跑得快,老天更不湊趣,又下起蒙蒙細雨,眼前衹覺一片模糊,宛如織就一張漫天的愁網,連人帶馬給罩住了。“廉纖雨”,蒙蒙細雨。“無邊絲雨細如愁”,這廉纖細雨,既阻斷了視綫,又攪亂了心緒;藉景語抒情,情景湊泊而有醖藉之致。“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玉堂,翰林院的別稱。玉堂供職是作者平時所自以為宋寵的,今夜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無聊和索寞。從一個充滿美酒清歌的歡樂世界,硬生生地被拋到宮禁森嚴的清冷官署,其懊喪和惱恨可想而知。“玉堂今夜長”,大有長夜難捱之感。對照開頭“城頭尚有三通鼓”,同時對於時間的感受,竟有如此不同的心理變化。這一起一結也自然形成兩種情境的鮮明對比,使這首小詞首尾相顧,有回環不盡之妙。 |
|
子規啼破城樓月,畫船曉載笙歌發。
兩岸荔枝紅,萬傢煙雨中。
佳人相對泣,淚下羅衣濕。
從此信音稀,嶺南無雁飛。
李師中詞作鑒賞
此詞作於詞人嶺南卸任之時。全詞景色清麗,感情深摯,意境深遠。
詞為“題別”而作,通篇圍繞一個“別”字做文章。上片起句寫臨別前情景。詞人將要離開廣西了,黎明之前子規鳥就不住地啼嗚,把他從夢中喚醒。他舉頭看看窗外,一彎殘月高挂西天,好像是被子規啼破了似的。這一句寫出了早起之景、臨別之時第、歸去之思和離別之情。乍看上去,出語自然;細細吟味,含意無窮。第二句寫詞人乘着華麗的官船將要出發,雖為寫實,但實中帶虛,所謂“曉載笙歌”者,乃是以“笙歌”兼指吹奏笙歌的樂妓,用語甚美,耐人尋味。三、四兩句尤為入妙。畫船清澈的江中從容而行,衹見兩岸荔枝,嬌紅欲滴;蒙蒙煙雨,籠罩萬傢。這完全是畫境,同時也是詩境,讀之令人陶醉。
過片二句寫別情。佳人,謂畫船中樂妓。這裏不僅補足“笙歌”一詞之意,而且進一步發抒離思。一位清正的地方官將要離任了,佳人也無法輓留,與詞人相對而泣,滾滾熱淚,濕透羅衣。這裏讓佳人把惜別的淚水傾瀉出來,雖不夠含蓄,但熱烈真誠。
結尾二句,係預想別後情景,對不可能繼續通信表示擔心。“嶺南無雁飛”,據陸佃《埤雅》雲,雁飛不過衡陽,因南地極燠。廣西嶺南,故鴻雁更難飛到。此處運用鴻雁傳書的典故,符合當地特點,顯得十分妥貼。
此詞妙選詞煉字、首句“子規啼破城樓月”中的“破”字便是範例。子規、城樓、月,本是三個互不相幹的概念,然着一“破”字,遂連成一體,形成渾一的境界。 |
|
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
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
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
王安石詞作鑒賞
此詞為作者晚年隱居江寧半山之作。《能改齋漫錄》雲:“王荊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中疊石作橋,為集句填菩薩蠻。”全篇用前人詩句雜綴成詞,使之如出己口,真正為自己表情達意服務,敘寫自己的閑適生活與故作放達的情懷。
開首“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二句明白地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環境與身份。往昔重樓飛檐、雕欄畫棟的官宦居處換成了築籬為墻,結草作捨的水邊茅屋;如今窄衫短帽的閑人裝束取代了過去的冠帶蟒服。作者從九重宸闕的丹墀前來到了水邊橋畔的垂楊裏。對於這種遭際的變化,王安石似乎采然種安然自適的態度。一個“閑”字渲染出淡泊寧靜的生活環境,也點出了作者擺脫宦海遠離風塵的村野情趣。兩句閑雅從容,雖然是從前人詩句中摘錄而成,但指事類情,貼切自然,不啻如出己口。
接着“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兩句是寫景:一夕春風來,吹開萬紫千紅,風光正似去年。但是,作為一個曾經銳意改革的政治傢,他對花事依舊、人事已非的感慨,就不僅僅是時光流逝、老之將至的嘆息,更包含着他壯志未酬的憂愁。因此,即使看似閑適的生活裏,自然界的月色風聲,都會引起這位政治傢的敏感與關註,而被賦予某種象徵的意義:“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作者醉酒晝寢,再不必隨班上朝參預政事,生活是如此閑逸,但是,酒醒夢回,陪伴他的並不是清風明月,而是風吹雲走、月翳半規的昏沉夜色。
最後二句自然地歸結到閑情上:“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作者自問自答,寫得含蓄而餘韻悠長。據馮贄《雲仙雜記》引《高隱外書》雲:“顒攜黃柑鬥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可見王安石的寄情黃鸝,不僅是表現鳥語花香中的閑情逸趣,更是顯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塵拔俗的耿直人格。
此詞與王安石晚年的詩作相似,以精煉的筆墨描繪了美麗如畫的湖光山色。詞中營造出清雋秀麗、悠閑恬靜的意境,以此來抒發灑脫放達之情,以求得精神上的慰安和解脫。詞人描繪春景時,無典故,不雕琢,語言清新、自然,數筆就勾出一幅鮮明秀麗、清俊嫻靜的畫面,其中有日景、夜景,有青山緑水、花紅柳翠的明麗色彩,也有流水潺潺、黃鸝鳴囀的聲響,而作者的形象就淡入這畫面中。全詞安逸恬淡的生活情景中寄寓着政治傢的襟懷心志,嫻雅流麗的風格中顯示出作者的才情骨力,體現了王安石詞素潔平易而又含蓄深沉的詞風。 |
|
哀箏一弄湘江麯,聲聲寫盡湘波緑。
纖指十三弦,細將幽恨傳。
當筵秋水慢,玉柱斜飛雁。
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
晏幾道詞作鑒賞
此詞藉寫彈箏來表現當筵演奏的歌妓心中的幽恨。
詞的上片暗寫湘靈鼓瑟的典故,點出“幽恨”;下片並未具體展開寫幽恨,衹寫弄箏的情態,而幽恨自見。黃蓼園謂此詞“末句意濃而韻遠,妙能藴藉”。
起筆一句先寫彈奏。箏稱之為“哀箏”,感情色彩極為明顯。“一弄”,奏一麯。麯為“湘江麯”,內容亦當與舜及二妃一類悲劇故事有關,由此可見酒筵氣氛和彈箏者的心情。“寫盡湘波緑”,湘水以清澈著稱,“緑”為湘水及其周圍原野的色調。但緑色彩分類上屬冷色,則又暗示樂麯給予人心理上的感受。
“寫”,指彈奏,而又不同於一般的“彈”或“奏”;似乎彈箏者的演奏,像文人的用筆,雖然沒有文詞,但卻用箏聲“寫”出了動人的音樂形象。
上片歇拍兩句,讓人想到彈箏者幽恨甚深,非細彈不足以盡情傳達,而能將幽恨“細傳”,又足見其人有很高的技藝。從“纖指”二句的語氣看,詞人對彈箏者所傾訴的幽恨是抱有同情的,而所傳之幽恨即是雙方所共有的。詞之上片,着重從演奏的內容情調方面寫彈者。
下片轉寫彈者的情態。“當筵秋水慢”,“秋水”代指清澈的眼波。“慢”,形容凝神,指箏女全神貫註。“玉柱斜飛雁”,箏上一根根弦柱排列,猶如一排飛雁。飛雁古詩詞中,常與離愁別恨相連,同時湘江以南有著名的回雁峰。因此,這裏雖是說弦柱似斜飛之雁,但可以想見所奏的湘江麯亦當與飛雁有聯繫,寫箏柱之形,其實末離開彈箏者所傳的幽恨。“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春山,指像山一樣彎彎隆起的雙眉,是承上文“秋水”而來的,用的是卓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西京雜記》)的典故。女子凝神細彈,表情一般應是從容沉靜的,但隨着樂麯進入斷腸境界,箏女斂眉垂目,凄涼和悲哀的情緒還是明顯地流露了出來。
這首詞以回蕩飄忽的筆勢,刻畫一位哀豔動人的彈箏藝妓——小蓮哀豔動人的形象。全詞以“哀箏一弄湘江麯”摹然開篇,又以“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驟然收筆,中間不平鋪直敘而抓住最富有表現力的動作、神態來寫,極具藝術感染力。 |
|
溪山掩映斜陽裏。
樓臺影動鴛鴦起。
隔岸兩三傢,出墻紅杏花。
緑楊堤下路,早晚溪邊去。
三見柳綿飛,離人猶未歸。
魏夫人詞作鑒賞
此詞寫景以抒情,情因景生,描繪了思婦盼望遠行丈夫歸來的情思。全詞緊緊圍繞一個“溪”字構圖設色,表情達意,寫得清新自然,不落俗套,饒有情韻,耐人尋味。
首句“溪山掩映斜陽裏”寫斜陽映照下的溪山,側重點於“溪”字。次句“樓臺影動鴛鴦起”,補足上文,進一步寫溪中景色。夕陽斜照之下,溪中不僅有青山的倒影,而且還有樓臺的倒影,還有對對鴛鴦溪中嬉水。上句專寫靜景,下句則動中有靜。“樓臺影動”,表明溪水微風吹拂之下,蕩起層層緑波,樓臺的影子也仿佛晃動一般。再添上“鴛鴦起”一筆,整個畫面就充滿了盎然生趣。
三、四兩句寫兩岸景色,這條溪水的兩岸,衹住着兩三戶人傢,人煙並不稠密,環境自然是幽靜的。至此,上面所說的樓臺原是這幾戶臨水人傢的住宅,全詞意脈連貫,針綫綿密。這句為實寫,下一句便是虛寫,如此虛實相生。深院高墻,關不住滿園春色,一枝紅杏花,帶着嬌豔的姿態,硬是從高高的圍墻上探出頭來。此句的妙處於一個“出”字,詞以“出”字形容紅杏花,寫出了春天的勃勃生機,意味雋永。
詞的下片,轉入抒情,但仍未脫“溪”字。溪水旁邊,有一道長堤,堤上長着一行楊柳,暮春時節,嫩緑的柳絲籠罩着長堤,輕拂着溪水,而魏夫人作為臨水人傢的婦女,是經常從這裏走過的。“早晚”一詞,並非指時間的早和晚。張相《詩詞麯語辭匯釋》捲六雲:“早晚,猶雲隨時也;日日也。”其義猶如舒亶《鵲橋仙》詞“兩堤芳草一江雲,早晚是西樓望處”。
古代,水邊柳外,往往是送別的場所。據《宋史·曾布傳》,曾布於神宗元豐中,連知秦州、陳州、蔡州和慶州。陸遊《老學庵筆記》捲七也說:“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主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雲:”使君自為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這期間,曾佈告別傢人,遊宦外,可能連續三年。此處,當指魏夫人填詞述懷。結尾二句說明她溪邊已徜徉了三年,年年都見過一次柳絮紛飛。從柳絮紛飛想到當年折柳贈別,這是很自然的。”三見柳綿飛“是實語,而着一”猶“字,便化實為虛了,這樣,哀怨之情,離別之恨,便隱然流於言外。
此詞聲律上極具特色,八句中兩句一葉韻,如“裏”與“起”、“傢”、與“花”、“路”與去、“飛”與“歸”,均押韻工整;且兩句與兩句之間又平仄交錯,如上片四句“裏”與“起”是仄聲韻,“傢”與“花”是平聲韻;下片“路”與“去”是仄聲韻,“飛”與“歸”是平聲韻,讀來十分諧婉,再加上語言曉暢,詞句清麗,較好地抒寫了貴族婦女溫柔敦厚而又婉麯纏綿的感情。 |
|
柳庭風靜人眠晝,晝眠人靜風庭柳。
香汗薄衫涼,涼衫薄汗香。
手紅冰碗藕,藕碗冰紅手。
郎笑藕絲長,長絲藕笑郎。
蘇軾詞作鑒賞
東坡的回文詞,兩句一組,下句為上句的倒讀,這比起一般回文詩整首倒讀的作法要容易些,因而對作者思想束縛也少些。東坡的七首回文詞中,如“郵便問人羞,羞人問便郵”、“顰淺念誰人,人誰念淺顰”、“樓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樓”、“歸不恨開遲,遲開恨不歸”等,下句補充發展了上句,故為妙構。這首回文詞是作者“回時閨怨”中的“夏閨怨”。
上片寫閨人晝寢的情景,下片寫醒後的怨思。用意雖不甚深,詞語自清美可誦。“柳庭”二句,關鍵一“靜”字。上句云“風靜”,下句云“人靜”。風靜時庭柳低垂,閨人睏倦而眠;當晝眠正熟,清風又吹拂起庭柳了。同是寫“靜”,卻從不同角度着筆。靜中見動,動中有靜,頗見巧思。三、四句,細寫晝眠的人。風吹香汗,薄衫生涼;而涼衫中又透出依微的汗香。變化“薄衫”與“薄汗”二語,寫衫之薄,點出“夏”意,寫汗之薄,便有風韻,而以一“涼”字串起,夏閨晝眠的形象自可想見。過片二句,是睡醒後的活動。她那紅潤的手兒持着盛了冰塊和蓮藕的玉碗,而這盛了冰塊和蓮藕的玉碗又冰了她那紅潤的手兒。上句的“冰”是名詞,下句的“冰”作動詞用。
古人常鼕天鑿冰藏於地窖,留待夏天解暑之用。杜甫《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寫以冰水拌藕,猶本詞“手紅”二句意。“郎笑耦絲長,長絲藕笑郎”,收兩句為全詞之旨。“藕絲長”,象徵着人的情意綿長,古樂府中,常以“藕”諧“偶”,以“絲”諧“思”,藕節同心,故亦象徵情人的永好。《讀麯歌》:“思歡久,不愛獨枝蓮(憐),衹惜同心藕(偶)。”自然,郎的笑是有調笑的意味的,故閨人報以“長絲藕笑郎”之語。笑郎,大概是笑他的太不領情或是不識情趣吧。郎的情意不如藕絲之長,末句始露出“閨怨”本意。
這首詞格律、內容感情、意境等方面都符合回文詞的要求,同時又不失作者的大傢氣派,實為難得。 |
|
畫船捶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
去住若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衹是人南北。
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舒亶詞作鑒賞
這是一首惜別詞。作者詞中以一推一輓之情勸住對方的眼淚,這種抒寫傷離恨別心緒的表現手法,與宋詞中寫離別時常見的纏綿悱惻、肝腸痛斷、難捨難分的情狀有所不同。
這首詞從送別寫起。捶鼓,猶言敲鼓,是開船的信號。船傢已擊鼓催行,而這一邊卻樓上把盞勸酒。“催”,見時間之難以再延。“留”,見送行人之殷勤留戀。一“催”一“留”,就把去和住的矛盾突出出來了,並且帶動全篇。“去住若為情,即由首二句直接逼出,欲去不忍,欲住不能,何以為情?這一問見別離之極度苦人。”西江潮欲平“的好處於沒有直接回答問題,而是由前面擊鼓催客、高樓把酒的場面推出一個江潮漲平的遼闊場景。句中的”欲“字包含了一個時間推進過程,說明話別時間頗長,而江潮已漸漸漲滿,到了船傢趁潮水開航的時候了。
換頭就江潮生發,潮水有信,定時起落,所以說“容易得”,然而它能送人去卻未必會送人來。一旦南北分離,相見即無定期故云“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結穴處一筆宕開,頗值得玩味。“此樽空”,遙承上片次句“把酒留君”,“樽空”見情不忍別,共拚一醉。但即使飲至樽空,故人終不可留,所以結尾則由嘆見面之難,轉思它日再會,發出“知君何日同”的感慨。
宋代曾季貍《艇齋詩話》評這首詞“甚有思緻”概因此詞藉江潮抒別情,不僅情景交融,同時還顯出情景與意念活動相結合的特點。詞“去住若為情”這樣的思忖後,接以“江頭潮欲平”,看上去是寫景,實際上卻把思索和情感活動帶進了景物描寫,那茫茫的江潮似乎融匯着詞人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浩渺的情思。
下片“江潮容易得,衹是人南北”仍不離眼前景象,而更側重寫意念,以傳達人物的心境。結尾二句雖然表現為感慨,卻又是循上文章活動繼續發展的結果。
所循的思路應該是:今日樽空而潮載君去,但未知潮水何日能復送君歸來。依然是情景和思忖結合。詞中以回環往復的語言節奏,來表現依依不捨、綿長深厚的“思緻”。 |
|
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着無人喚。
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
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黃庭堅詞作鑒賞
據此詞原序所說,這首《菩薩蠻》當是戲擬王安石集句詩之作。
開首二句以極自然輕盈的筆法描繪了一幅閑適悠雅的溪橋野漁圖。一片氤氳迷蒙的山嵐水霧中,是煙是雨,叫人難以分辨,真是空翠濕人衣。溪邊橋畔,有漁翁正醉酒酣睡,四周闃無聲息,沒有人來驚破他的好夢。“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化用杜甫“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長”(《西郊》)和“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絶句二首》)這句詩。兩句詩不僅從字面看放這裏十分熨貼,而且從原作的意境看,也與這首詞情相合,更重要的是通過這詩句的媒介,將讀者導嚮了杜甫的詩境,這些詩境又反過來豐富了這首詞本身的意藴。這樣便活畫出整個風光明媚生機勃勃的春世界。
“江山如有待”為作者移用的杜甫《後遊》中的詩句,作者嚮往大自然的美好,卻推開自己不說,而從對面着筆,將自己熱烈的感情移植到無生命的江山自然上,通過擬人化的描寫,表現“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那種人與自然交流相親、物我不分的情感意緒。這樣,詞上下片意境相應,衹將前面“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詞意發展為對自然生活的嚮往與追求。作者自然地想到了開隱逸風氣的陶潛,遂又隨手拈來了杜甫的另一句詩“此意陶潛解”(《可惜》),將自己對山川自然的企慕之意,又落實到對這位拋棄榮利的田園先哲的景仰上,從而挑出了全詞隱逸的主題。
杜甫感嘆生不逢時,恨不能詞的最後二句“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接住杜甫“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杜甫《可惜》)詩意,表明自己的態度,他不學杜甫的感慨而是步先哲的後塵。作者决心歸隱,但到底去何方,卻無可告,不過如隨之而去,一定會明白他的蹤跡。這一結語將上面貫串下來的情志意趣,結束得非常工穩,飄逸而含蓄。
這首詞全靠直接剝錄他人詩句而成,雖非作詞之正道,卻也頗有移花接木之妙。 |
|
彩舟載得離愁動,無端更藉樵風送。
波渺夕陽遲,銷魂不自持。
良宵誰與共,賴有窗間夢。
可奈夢回時,一番新別離!
賀鑄詞作鑒賞
此詞突破了嚮來以山、水、煙、柳等外界景物來喻愁的手法,把難於捉摸、無影無蹤的抽象愁情表現得具體可感,生動形象。全詞從上片的奇特聯想,無端怨責,到下片的文心起伏,一波三折,寫有情人分別後思想感情的一係列變化,極為細膩真實。尤其是“因思成夢。夢回新別的設想,更是抓住了情的關鍵。
起首一句“彩舟載得離愁動”,“彩舟”,是行人乘坐之舟。長亭離宴,南浦分攜,行前執手,一片哀愁,而今蘭舟已緩緩地離開了碼頭。然而這位行人的心頭卻還是那樣悲哀,他甚至覺得這載人載貨的舟上,已經裝滿了使人不堪負擔的離愁,真是聯想奇特,語新意深。
第二句“無端更藉樵風送之”“無端”,無緣無故,沒來由:“樵風”,典出《會稽記》。講的是鄭宏年輕時上山砍柴,碰到了一位神人。他嚮神人請求若耶溪上“旦,南風;暮,北風”,以利於運柴,後果如所願。此處用“樵風”,即有順風的意思。這一句寫的是:船藉着順風飛快地遠航而去,那伫立岸邊送行的心上人的倩影,很快就不可得見。詞人五內俱傷,哀感無端,不由地對天公産生了奇特的怨責:為什麽偏偏這個時候,沒來由送來一陣無情的順風,把有情人最後相望的一絲安慰也吹得幹幹淨淨呢!
第三句“波渺夕陽遲”,詞意由密轉疏,情中布景。詞人展望前程,天低水闊,煙波迷離。一抹夕陽的餘暉,沉沉的暮靄之中,看上去是那樣的凄涼。獨立蒼茫,一葉孤舟上煢煢孑立的行人遂生“銷魂不自持”的無限感慨!魂銷魄散,惝恍迷離,凄惻纏綿,無復生意。
換頭重筆另開,設想別夜的落寞惆悵。“良宵誰與共”,明知無人共度良宵而故作設問,突出了捨心上人而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和自己共度時光的執着癡情。“賴有窗間夢”句是說,衹有獨臥窗下,神思魂縈的夢境中才能和心上人再一次相見。一個“賴”字,說明詞人要把夢中的歡聚作為自己孤獨心靈的唯一感情依托。這兩句,一問沉痛,一答哀婉,有力地表現了自己別後的孤獨和凄涼。詞人煞費苦心地為自己構築了一個癡情而又感傷的希望,冷酷的現實面前,又不得不親手把它擊得粉碎。
結拍“可奈夢回時,一番新別離!”是說夢中的歡會誠然是纏綿熱烈的,無奈夢總是要醒的;而夢醒之後,一番夢會之歡欣恰又導致了“一番新別離”的痛苦!全詞以感慨作結,餘音不絶,抓住了愛情的關鍵,夢回新別離的痛苦更甚,如此作法,言盡而味不盡。 |
|
春風試手先梅蕊,頩姿冷豔明沙水。
不受衆芳知,端須月與期。
清香閑自遠,先嚮釵頭見。
雪後燕瑤池,人間第一枝。
趙令畤詞作鑒賞
此為詠梅之作。作者與蘇東坡過從甚密,東坡為愛其纔,曾薦其於朝。東坡因政爭遭貶謫時,作者亦受牽纍。此詞顯然是藉梅花以寓性情,並非徒然詠物之作。
詞之首句起筆不凡,以擬人手法寫春風似乎可以用她那靈巧的“手”,啓開冰封雪蓋的萬物,而且最“先”使梅花吐出了嫩蕊!“拭手”而先,仿佛是春風對梅花特別鐘情。句法峭勁,旋折有力。次句即繪出梅花的丰采:資色美麗(頩),冷韻幽香,相伴着它的是明沙淨水。這句七個字,“頩姿冷豔”寫梅花本身:“明沙水”顯示出一片冰清素潔、纖塵不染的環境。彼此映襯,更給人以豐姿枯、神采奕奕的感覺。這裏詞人賦予梅花明沙淨水的環境,有着深刻的寓意。
三四兩句,點出梅花的風骨、品格“不受衆芳知”,言梅,態度不卑不亢,從容而自矜。“端須月與期”,詞情突然揚起,說衹有月亮纔配與梅花作伴。前句抑,後句揚,抑揚之間,把梅花格調的高絶,推上頂峰。
下片層層推進地刻畫梅花的風神。前兩句與後兩句看似梅花與人分而言之,其實與人仍是刻繪梅花。“清香閑自遠”,梅花的香是“清香”,清幽而淡遠:“先嚮釵頭見”,女人們把梅花連同釵飾插頭上。這裏又用了一個“先”定,再現出她與衆芳的不同。“雪後燕瑤池”,想象瑰麗而神奇,極富藝術魅力。瑤池,相傳為西王母居住的仙境。“人間第一枝”,可以理解為即使天堂仙境,也有人間花魁—梅花,也可理解為梅花超凡脫俗,冰肌玉骨,豔絶群芳,如同那瑤池仙子一般清麗、孤高。
這首詞藝術構思和手法上頗具匠心,極具深沉流美、委婉麯折之妙。全詞融情於景,托物抒懷,通過塑造梅花冷豔幽姿、清香惹人。孤高冷傲的風流標格,寄寓了詞人的襟懷和性情,讀來回味無窮,一唱三嘆。 |
|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綉羅襦,雙雙金鷓鴣 .
譯文:
眉妝漫染
疊蓋了部分額黃
鬢邊發絲飄過
潔白的香腮似雪
懶得起來
畫一畫蛾眉
整一整衣裳
梳洗打扮
慢吞吞
意遲遲
照一照新插的花朵
對了前鏡
又對後鏡
紅花與容顔
交相輝映
剛穿上的綾羅裙襦
綉着一雙雙的金鷓鴣
賞析:這首《菩薩蠻》,為了適應宮廷歌伎的聲口,也為了點綴皇宮裏的生活情趣,把婦女的容貌寫得很美麗,服飾寫得很華貴,體態也寫得十分嬌柔。仿佛描繪了一帽唐代仕女圖。
詞的上片,寫床前屏風的景色及梳洗時的嬌慵姿態;下片寫妝成後的情態,暗示了人物孤獨寂寞的心境。全詞委婉含蓄地揭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並成功地運用反襯手法。鷓鴣雙雙,反襯人物的孤獨;容貌服飾的描寫,反襯人物內心的寂寞空虛。表現了作者的詞風和藝術成就。 |
|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衹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垆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賞析】
這是一首閨情詞。上片描繪庭院暮春景色,緑草滋蔓,苔深蕉捲,蝶飛簾垂,一派幽靜;下片寫“緑窗睡清”,因而聽到玉鈎燕語,幾處箥錢聲,表現閨中人的孤獨寂寞和淡淡的憂愁。本詞寫美人春日晝眠之景,刻畫細緻入微,環境烘托,氣氛渲染均極為成功。前六句層層推進,最後兩句輕輕一筆點題結篇,結構別緻,很受推賞。全詞寓情於景,溫婉柔媚,清新倩麗,體現了婉約詞豔麗的風格。 |
|
紅樓別夜堪惆悵,
香燈半捲流蘇帳。
殘月出門時,
美人和淚辭。
琵琶金翠羽,
弦上黃鶯語。
勸我早歸傢,
緑窗人似花。
人人盡說江南好,
遊人衹合江南老。
春水碧於天,
畫船聽雨眠。
垆邊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還鄉,
還鄉須斷腸。
如今卻憶江南樂,
當時年少春衫薄。
騎馬倚斜橋,
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麯,
醉入花叢宿。
此度見花枝,
白頭誓不歸。
勸君今夜須瀋醉,
尊前莫話明朝事。
珍重主人心,
酒深情亦深。
須愁春漏短,
莫訴金杯滿。
遇酒且呵呵,
人生能幾何。
洛陽城裏春光好,
洛陽才子他鄉老。
柳暗魏王堤,
此時心轉迷。
桃花春水淥,
水上鴛鴦浴。
凝恨對殘暉,
憶君君不知。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衹合江南老。
○○●●○○▲,○○●●○○▲
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
垆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 |
|
小山重疊金明滅,
鬢雲欲度香腮雪。
懶起畫蛾眉,
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
花面交相映。
新貼綉羅襦,
雙雙金鷓鴣。
【簡析】
初日的光輝映着畫屏,屏山重重疊疊,金光閃爍。閨中人猶未起床,一抹烏雲般黑亮的秀發,拂揚在雪白重豔的腮上。雖然是無心緒不欲起床,終於還是懶洋洋的起來了。 但卻是慢騰騰地梳洗,妝扮,描畫蛾眉。畢竟是位美的女子。她的雙鬢簪了鮮花,對着妝臺上的座鏡從正面照,又拿着帶柄的手鏡從背後照,端詳簪花是否妥恰,同時,亦在顧盼自己的美豔。前後兩鏡交相輝映,花光與人面亦相互映襯。妝扮完畢,開始了一天的女工:綉羅襦。此時新貼的花樣,偏偏是成雙成對的金鷓鴣,她不禁心所感。 |
|
赤橙黃緑青藍紫,
誰持彩練當空舞?
雨後復斜陽,
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
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
今朝更好看。 |
|
緑蕪墻繞青苔院,中庭日淡芭蕉捲。
蝴蝶上階飛,烘簾自在垂。
玉鈎雙語燕,寶秋楊花轉,
幾處箥錢聲,緑窗春睡清。 |
|
- : Pusaman
|
|
|
|
| 菩薩蠻二 | 菩薩蠻三 | 菩薩蠻四 | | 菩薩蠻五 | 菩薩蠻夏 | 菩薩蠻鼕 | | 菩薩蠻六 | 菩薩蠻磯 | 菩薩蠻秋 | | 菩薩蠻梅 | 菩薩蠻令 | 菩薩蠻荼 | | 菩薩蠻·詠梅 | 菩薩蠻·芭蕉 | 菩薩蠻秋興 | | 菩薩蠻祝壽 | 菩薩蠻春歸 | 菩薩蠻次韻 | | 菩薩蠻別意 | 菩薩蠻臘梅 | 菩薩蠻代贈 | | 菩薩蠻西湖 | 菩薩蠻重陽 | 菩薩蠻四首 | | 菩薩蠻回文 | 菩薩蠻有寄 | 菩薩蠻七夕 | | 菩薩蠻感舊 | 菩薩蠻荷花 | 菩薩蠻詠足 | | 菩薩蠻同前 | 菩薩蠻新月 | 菩薩蠻木樨 | | 菩薩蠻集句 | 菩薩蠻歌妓 | 菩薩蠻西亭 | | 菩薩蠻初鼕 | 菩薩蠻賞梅 | 菩薩蠻殘春 | | 菩薩蠻初夏 | 菩薩蠻春深 | 菩薩蠻芭蕉 | | 菩薩蠻喜雪 | 菩薩蠻遣興 | 菩薩蠻和韻 | | 菩薩蠻怨別 | 菩薩蠻簪髻 | 菩薩蠻熏瀋 | | 菩薩蠻來夢 | 菩薩蠻寫真 | 菩薩蠻命觴 | | 菩薩蠻披風 | 菩薩蠻照溪 | 菩薩蠻浥露 | | 菩薩蠻菊花 | 菩薩蠻歸思 | 菩薩蠻佳人 | | 菩薩蠻詠目 | 菩薩蠻驚夢 | 菩薩蠻落梅 | | 菩薩蠻江幹 | 菩薩蠻春感 | 菩薩蠻春雨 | | 菩薩蠻春愁 | 菩薩蠻荼蘼 | 菩薩蠻別恨 | | 菩薩蠻湖上 | 菩薩蠻小詞 | 菩薩蠻春閨 | | 菩薩蠻詠梅 | 菩薩蠻端午 | 菩薩蠻杏花 | | 菩薩蠻春曉 | 菩薩蠻沐發 | 菩薩蠻新秋 | | 菩薩蠻上元 | 菩薩蠻清明 | 菩薩蠻夜景 | | 菩薩蠻回紋 | 菩薩蠻擬古 | 菩薩蠻·夏閨怨 | | 菩薩蠻·宜興作 | 菩薩蠻·商婦怨 | 菩薩蠻王安石 | | 菩薩蠻·宿水口 | 菩薩蠻趙令畤 | 菩薩蠻十之八 | | 菩薩蠻十之七 | 菩薩蠻十之六 | 菩薩蠻十之五 | | 菩薩蠻十之四 | 菩薩蠻十之三 | 菩薩蠻十之二 | | 菩薩蠻十之一 | 菩薩蠻十之十 | 菩薩蠻送劉帥 | | 菩薩蠻澧陽莊 | 菩薩蠻木芙蓉 | 菩薩蠻宜興作 | | 菩薩蠻戲林推 | 菩薩蠻賦軟香 | 菩薩蠻題雲岩 | | 菩薩蠻湘東驛 | 菩薩蠻望行人 | 菩薩蠻過吳江 | | 菩薩蠻侄壽伯 | 菩薩蠻商婦怨 | 菩薩蠻壽夫人 | | 菩薩蠻宿水口 | 菩薩蠻西湖麯 | 菩薩蠻雙浮亭 | | 菩薩蠻採蓮女 | 菩薩蠻水晶膾 | 菩薩蠻花蹊碧 | | 菩薩蠻梅花句 | 菩薩蠻花間意 | 菩薩蠻立春日 | | 菩薩蠻鴛鴦梅 | 菩薩蠻題梅扇 | 菩薩蠻四首春 | | 菩薩蠻戲菱生 | 菩薩蠻題山館 | 菩薩蠻贈舞姬 | | 城裏鐘菩薩蠻 | 菩薩蠻般涉調 | 菩薩蠻中呂調 | | 菩薩蠻中呂宮 | 菩薩蠻大柏地 | 菩薩蠻黃鶴樓 | | 菩薩蠻·塞上秋望 | 菩薩蠻·花明月暗 | 菩薩蠻·平林漠漠 | | 菩薩蠻遊水月寺 | 菩薩蠻春晚二首 | 菩薩蠻晚雲烘日 | | 菩薩蠻酒半戲成 | 菩薩蠻施尉生日 | 菩薩蠻鬍教生朝 | | 菩薩蠻野趣觀梅 | 菩薩蠻戊辰重陽 | 菩薩蠻和詹天遊 | | 菩薩蠻丁醜送春 | 菩薩蠻蘇堤芙蓉 | 菩薩蠻春日山行 | | 菩薩蠻湖南道中 | 菩薩蠻送劉貴伯 | 菩薩蠻和子有韻 | | 菩薩蠻鄂渚岸下 | 菩薩蠻元夕立春 | 菩薩蠻賦玉蕊花 | | 菩薩蠻和夏中玉 | 菩薩蠻晝眠秋水 | 菩薩蠻十一之十 | | 菩薩蠻定空賞梅 | 菩薩蠻十一之九 | 菩薩蠻十一之四 | | 菩薩蠻十一之三 | 菩薩蠻十一之五 | 菩薩蠻十一之八 | | 菩薩蠻十一之七 | 菩薩蠻十一之六 | 菩薩蠻青陽道中 | | 菩薩蠻富陽道中 | 菩薩蠻正平梅雪 | 菩薩蠻餞田莘老 | | 菩薩蠻湖上即事 | 菩薩蠻詠酒十首 | 菩薩蠻可人梅軸 | | 菩薩蠻瑞蔭秋望 | 菩薩蠻玉山道中 | 菩薩蠻韻勝竹屏 | | 菩薩蠻題蓮花庵 | 菩薩蠻甲午秋作 | 菩薩蠻初鼕旅中 | | 菩薩蠻霜天旅思 | 菩薩蠻初鼕旅思 | 菩薩蠻秋老江行 | | 菩薩蠻秋雨船中 | 菩薩蠻政和丙申 | 菩薩蠻賦疑梅香 | | 菩薩蠻廣陵盛事 | 菩薩蠻和賀子忱 | 菩薩蠻夏景回文 | | 菩薩蠻寄趙使君 | 菩薩蠻代歌者怨 | 菩薩蠻述古席上 | | 菩薩蠻十一之一 | 菩薩蠻十一之二 | 菩薩蠻·雙韻賦摘阮 | | 菩薩蠻令·金陵懷古 |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 菩薩蠻次張秉道韻 | | 菩薩蠻坐中賦櫻桃 | 菩薩蠻雙韻賦摘阮 | 菩薩蠻戲呈周介卿 | | 菩薩蠻湖光亭晚集 | 菩薩蠻回文夏閨怨 | 菩薩蠻七夕般涉調 | | 菩薩蠻新城山中雨 | 菩薩蠻回文鼕閨怨 | | | 更多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