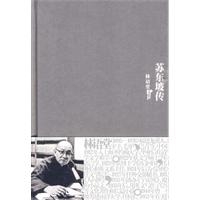 韩愈传 韩愈传
韓愈被列為“唐宋八大傢”之首,又將他與杜甫並提,有“杜詩韓文”之稱。
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謂“以文為詩”,別開生面,用韻險怪,開創了“說理詩派”的詩風。當然,他的詩也存在着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缺點,對後代有不良影響。
韓愈還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傢,他能逆當時的潮流,積極指導後進學習,他“收召後學”、“抗顔而為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特別重視教育和培養年輕作傢。
他在《答李翊書》一文中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傢的思想修養、人格修養強調作傢的道德修養和文學修養,對搞好創作的重要性。現存《昌黎先生集》四十捲、《外集》十捲。
韓愈作為修武人,曾多次遊歷縣境北部的百傢岩,在此曾作長詩《題西白澗》,由此使西白澗也成為百傢岩重要一景。 思想淵源於儒傢,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傢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淨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贊孟子闢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並無二緻。這些復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傢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衆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傢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於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苟”(《送窮文》)、“同工異麯”、“俱收並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衹以自嬉”(《送窮文》),對後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傢,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嶽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絶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絶《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傢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註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係年集釋》是另行係年的集註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註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雲、王元啓、瀋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文學作品 師說
【題解】
本文見《昌黎先生集》。為作者贈李蟠之作。主旨在於闡明師道。“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而為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題解】本文與《馬說》同是宣揚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寫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獨運,用“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比喻“大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贊頌烏重胤慧眼識賢、善於薦拔人才;又用“私怨於盡取”反襯烏公“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的難得可貴,似“怨”而實頌,且比正面稱贊更為有力。文中也不直寫溫生之賢能,而是從多方面敘說溫處士出仕後給東都帶來的“不良”影響,反面襯出其過人之才,十分含蓄而巧妙。
【原文】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纔,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纔,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置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盧。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
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緻私怨於盡取也!
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全文解釋】伯樂一經過冀北的原野,馬群就空了。冀北是天下馬最多的地方,伯樂雖然擅長相馬,怎麽能使那裏的馬群空了呢?解釋的人說:“我們說的空,不是沒有馬了,而是沒有好馬了。伯樂能識馬,一遇到好馬就把它挑去,馬群裏留不下一匹好馬。如果沒有一匹好馬,那麽說沒有馬,也不能算是假話了。”
東都洛陽,原本是士大夫的“冀北”。有真纔實學而隱身不仕的,洛水的北岸有一位,叫石生,洛水的南岸有一位,叫溫生。御史大夫烏公憑藉度使的身份鎮守河陽的第三個月,認為石生是個人才,就依照禮儀,把石生招入幕府。沒有過幾個月,又認為溫生是個人才,於是通過石生作媒介,又把溫生招入幕府。東都有真纔實學的人儘管很多,可是怎麽禁得起早晨挑選一個,把最好的帶走,晚上挑選一個,把最優的帶走呢?這樣一來,從東都留守、河南尹起,到各部門的主管和我們兩縣的官吏,如果政事上遇到疑難問題,或者辦案時遇到可疑點,找什麽人去商量妥善解决呢?辭官回鄉的士大夫們和誰一起遊玩呢?青年後輩又到哪裏去考究德行、請教學業呢?東來西往經過洛陽的官員們,也無法依禮到他們的住所去拜訪。像這樣也就可以說是:“御史大夫烏公一到洛陽,洛陽處士們的住所裏就沒有人了。”難道不行嗎?
皇帝處理天下大事,所托付、依靠出大力的,衹有宰相和將軍罷了。宰相為皇帝搜羅人才到朝廷,將軍為皇帝選拔文人武士到軍帳裏,如果這樣,要使國傢內外不安寧,那是不可能的了。我被束縛在這裏,不能自己引退,想依靠石、溫兩位的幫助度過晚年。現在,二位都被有權力的人要走了,這又怎能不使我耿耿於懷呢?
溫生初到,在軍門拜見烏公時,希望把我前面所說的,代為天下人祝賀;把握後面所說的,替我表示對選盡人才這件事的抱怨。
東都留守相公首先寫成一首四韻詩來贊美此事,我便依照他的詩意寫了這篇序。
【另附思想感情】本文大力贊揚烏公對人才的識別與憐惜舉薦,論述能識別人才者對人才的重要性。一是代為天下祝賀;二是對選盡人才這件事抱怨。其用意是大力贊揚烏重胤能識別人才,也是希望自己也能被發現、舉薦。
送李願歸盤𠔌序伯樂一經過冀北的原野,馬群就空了。冀北是天下馬最多的地方,伯樂雖然擅長相馬,怎麽能使那裏的馬群空了呢?解釋的人說:“我們說的空,不是沒有馬了,而是沒有好馬了。伯樂能識馬,一遇到好馬就把它挑去,馬群裏留不下一匹好馬。如果沒有一匹好馬,那麽說沒有馬,也不能算是假話了。”
【題解】
李願是韓愈的好朋友,生平不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鼕,韓愈在長安等候調官,因仕途不順,心情抑鬱,故藉李願歸隱盤𠔌事,吐露心中鬱抑不平之情。首段敘述盤𠔌環境之美及得名由來。結着三段藉李願之口,運用兩賓夾一主的手法,寫了三種人:聲威赫赫的顯貴、高潔不污的隱士和趨炎附勢的官迷,於映襯、對比中表達他對官場腐化的憎惡和對隱居生活的嚮往。
古人在朋友臨別時,常常賦詩為贈,“序”是闡述贈詩的緣由和意旨的。本文末段“歌曰”以下就是贈詩。歌辭極言隱居之樂,立意深刻而善藏不露,句式偶儷而富於變化,流暢生動,和諧可誦,有一唱三嘆的情緻。蘇軾《跋退之送李願序》一文說:“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餘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願歸盤𠔌序》一篇而已。平生願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原文】
太行之陽有盤𠔌。盤𠔌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𠔌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願居之。
願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纔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麯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闢而誅戮,僥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麯,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竜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祭十二郎文
【題解】
南宋學者趙與時在《賓退錄》中寫道:“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來傳誦不衰,影響深遠的祭文名作,不管我們對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評價,吟誦之下,都不能不隨作者之祭而有眼澀之悲。
【原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緻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衹。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傢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鬥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傢者,不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雲,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傢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於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野,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鼕。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以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屍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明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傢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野,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傢可幾而理歟!
進學解
【題解】
本文是元和七、八年間韓愈任國子博士時所作,假托嚮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在學業、德行方面取得進步,學生提出質問,他再進行解釋,故名“進學解”,藉以抒發自己懷才不遇、仕途蹭蹬的牢騷。文中通過學生之口,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學習、捍衛儒道以及從事文章寫作的努力與成就,有力地襯托了遭遇的不平;而針鋒相對的解釋,表面心平氣和,字裏行間卻充滿了鬱勃的感情,也反映了對社會的批評。按本文“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等語,凝聚着作者治學、修德的經驗結晶;從“浸沉醲鬱”到“同工異麯”一段,生動表現出他對前人文學藝術特點兼收並蓄的態度。韓愈作為散文傢,也很推重漢代揚雄的辭賦。本文的寫作即有所藉鑒於揚雄的《解嘲》、《解難》等篇,辭采豐富,音節鏗鏘、對偶工切,允屬賦體,然而氣勢奔放,語言流暢,擺脫了漢賦、駢文中常有的艱澀呆板,堆砌辭藻等缺點。林紓所謂“濃淡疏密相間,錯而成文,骨力仍是散文”,故應說是韓愈特創的散文賦,為杜牧的《阿房宮賦》、蘇軾的《赤壁賦》的前驅。文中有許多創造性的語句,後代沿用為成語。
【原文】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颳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雲多而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餘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傢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抵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鬱,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傢。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麯。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鼕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先生曰:“籲,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視八世孫羺,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雲。居東郭者曰鵕,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傢。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須,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
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傢、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巿井貸錢註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鬍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麯、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纍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决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緻,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試之,因免冠謝。上見其發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中書君,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雜說一《竜說》
韓愈
竜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竜也。然竜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𠔌,雲亦靈怪矣哉。
雲,竜之所能使為靈也。若竜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竜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
易曰:“雲從竜。”既曰:“竜,雲從之矣。”
【翻譯】
竜吐出的氣形成雲,雲本來不比竜靈異。但是竜乘着這股雲氣,可以在茫茫的太空中四處遨遊,接近日月,遮蔽它的光芒,震撼起雷電,變化神奇莫測,雨水降落在大地,使得山𠔌沉淪。這雲也是很神奇靈異的呢!
雲,是竜的能力使它有靈異的。至於竜的靈異,卻不是雲的能力使它這樣子的。但是竜沒有雲,就不能顯示出它的靈異。失去它所憑藉的雲,實在是不行的啊。多麽奇怪啊,竜所憑藉依靠的,正是它自己造成的雲。《周易》說:“雲跟隨着竜。”那麽既然叫做竜,就應該有雲跟隨着它啊!
註釋:
竜說:選自《雜說》,為其首篇,題目為編者加。 噓:噴吐。 伏:遮蔽。 景:通“影”。 神變化:語出《管子·水地篇》“竜生於水,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為蠶(蟲蜀)[說明,此為一個字zh ],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于云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 水:名詞用作動詞,下雨。 汩:漫。 雲從竜:語出《易·乾·文言》“雲從竜,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從:隨,跟隨。
雜說二《醫說》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雜說三《崔山君傳》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其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肋曼膚,顔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餘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雲爾。
翻譯:
作者談氏在他寫的《崔山君傳》裏說,那些聲稱自己如仙鶴般長壽能知往事的人,實在太荒謬了。但據我觀察,能夠盡到人的本性而不象禽獸那樣的人太少了,而這些人又憤世嫉俗、隱居避世,這是為什麽呢?昔時的聖人們,有的頭象牛,有的身體象蛇,有的嘴巴象鳥,還有的面貌象蒙倛那樣方而且醜陋,但是他們僅僅是與那些野獸外貌相似,而本性卻完全不同,我們能夠說他們不是人嗎?而有的人身材豐滿,皮膚細嫩滑澤,面色紅潤有如朱砂,美麗非凡,他們的外表是人,而本性卻象禽獸一般。那麽是否還能夠把他們稱作人呢?所以以貌取人,不如觀其言察其行來的正確。鬼神之說,我們儒傢弟子從不輕信,所以我就從這個故事中選擇了憤世嫉俗的一面,來發表一些感想而已。
雜說四《馬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衹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
馬之千裏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裏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裏之能,食不飽,力不足,纔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註釋】伯樂:春秋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擅長相馬。
衹:同“衹”,衹是。辱:受屈辱,埋沒。 駢:成雙成對。駢死:並列而死。槽櫪:原指養獸的食器,這裏指養馬的處所。
不以千裏稱也:不以千裏馬被稱道。以,把。稱,稱頌,稱道。
馬之千裏者:馬(當中)能行千裏的。之,助詞。此句“馬”和“千裏者”是部分復指關係。
一食:吃一次。或:有時。盡粟一石(shi):吃盡一石(dàn)粟。盡,全,這裏作動詞用,是“吃盡”的意思。石,十鬥為石。
食:同“飼”,喂養。
其:指千裏馬,代詞。能千裏:能走千裏。
是:這,指示代詞。
能:才能。
纔美不外見:才能和長處不能表現在外。見,同“現”,表露。美,美好素質
且:將。欲:想要,要。等:相當。不可得:不可能。得,能,表示客觀條件允許。
安:怎麽,哪裏,疑問代詞。
策:駕馭。之,指千裏馬,代詞。以其道:用(對待)它的辦法。
盡其材:全發揮它的才能。材,同“纔”,此指行千裏的才能。
鳴之:吆喝它。通其意:跟它的心意相通。
執策:拿着馬鞭。策,趕馬的鞭子,名詞。臨之:臨視着馬。臨,從高處往下看。
其:語氣助詞,加強反問語氣。 其:語氣助詞,加強肯定語氣。
【譯文】世上有了伯樂,然後纔會有千裏馬。千裏馬是經常有的,可是伯樂卻不經常有。因此,即使是很名貴的馬也衹能在僕役的手下受到屈辱,跟普通的馬一起死在馬廄裏,不能獲得千裏馬的稱號。
日行千裏的馬,一頓或許能吃下一石糧食,喂馬的人不懂得要根據它日行千裏的本領來喂養它。(所以)這樣的馬,雖有日行千裏的能耐,卻吃不飽,力氣不足,它的才能和美好的素質也就表現不出來,想要跟普通的馬相等尚且辦不到,又怎麽能要求它日行千裏呢?
鞭策它,不按正確的方法,喂養又不足以使它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聽它嘶叫卻不懂得它的意思,(反而)拿着鞭子站在它跟前說:“天下沒有千裏馬!”唉!難道果真沒有千裏馬嗎?其實是他們真不識得千裏馬啊! 傳世名言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馬 說》
·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韓愈治學名聯)
· 雲橫秦嶺傢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聽穎師彈琴》)
·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原毀》)
· 親之割之不斷,疏者屬之不堅。
·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送孟東野序》)
· 少年樂相知,衰暮思故友。
·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煙柳滿皇都。(《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 事業無窮年。
·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 (《師說》)
·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進學解》)
· 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師說》)
· 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師說》)
·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 聖人無常師。 (《師說》)
·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師說》)
·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調張籍》) ·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原道》) 韓愈墓地 韓愈墓位於河南省孟州市城西6公裏韓莊村北半嶺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臨黃河,是一片丘陵地帶。墓塚高大,有磚石圍墻,翠柏蓊鬱,芳草芨芨,棗樹成林。墓前有韓愈祠,明代建築,三進院落,韓愈雕像坐於祠中。
韓愈墓始建於唐敬宗寶歷元年(825年)。墓地處丘陵地帶,墓塚高10餘米,塚前建有祠堂,計有饗堂三間,門房三間。祠內共有石碑13通,記載有韓愈生平事跡等。墓前院內有古柏兩株,相傳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間孟縣知縣仇汝瑚碑記:"唐柏雙奇",左株高5丈,圍 1.2 丈;右株高4丈,圍1.1丈。 1986年11月,公佈為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韓愈一生創作了幾百首詩,對我國創作詩句有着深遠的影響。
韓愈紀念館
潮州韓愈紀念館
位於廣東潮州市城東筆架山麓,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著名政治傢、思想傢、文學家韓愈,由於嚮皇帝提出停止迎接法門寺佛骨到長安供奉的建議,觸怒了皇帝,被令處死,幸得宰相裴度等講情,改貶為潮州刺史。韓愈以戴罪之身,在潮七個多月,把中原先進文化帶到嶺南,辦教育,驅鰐魚,為民衆做了許多好事,被潮人奉為神,潮人並將筆架山改稱韓山,山下的鰐溪改稱韓江。
宋鹹平二年(公元999年)在通判陳堯佐的倡導下建立韓祠。祠宇據地高曠,構造古雅,占地328平方米,係雙層垂檐建築。其下層為展覽廳,上層闢為“韓愈紀念館”,閣前石砌平臺正中有2米多高的韓愈平身石像1尊。內分前後二進,並帶兩廊。後進築在比前進高出幾米的臺基上,內供韓愈塑像。堂上有對聯:“闢佛纍千言,雪冷藍關,從此儒風開嶺嬌;到官纔八月,潮平鰐諸,於今香火遍瀛洲。”祠內有歷代碑刻36塊,其年代最早者即蘇軾的《潮州韓文公廟碑》,從城南移此,置正堂南墻下。祠內前後二進梁柱,還分懸今人為重修韓文公祠所題寫的匾額。韓祠倚山臨水,肅穆端莊。1988年,原侍郎亭舊址又新建了“侍郎閣”(韓愈曾任刑部侍郎,人稱“韓侍郎”),蘇軾為此寫下了著名的《潮州韓文公廟碑記》,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遂成天下定論。周圍為歷代韓祠碑刻和韓愈筆跡。饒有趣味的是“傳道起文”的碑刻,因字形特殊,竟有多種讀法。庭園有碑廊,保存現代名人評價韓愈的書法碑刻。後山腰為侍郎閣,閣前有韓愈石雕頭像,閣內辭為韓愈生平展覽館。 陽山韓愈紀念館 位於廣東陽山縣境內,這是為了紀念曾任陽山縣令的大文豪韓愈而修建。展廳內挂滿了韓愈在陽山留下的手跡石刻及歷代文人景韓詩文的拓片。展廳內,有一張珍貴的韓愈全身像的拓片。在陽山韓愈紀念館內,存有肖炳堃的摩刻附有詩及詩序,詩及詩序富有激情,讀後讓人嘆為觀止。
韓愈傳(節選)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①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奬勵。
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闢②為巡官。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③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陽山令。
風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産、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之,疏奏,憲宗怒甚,乃貶為潮州刺史。
【註】①從:堂房親屬。②(bi):徵召。③宮市:原意指宮廷內所設的市肆。唐德宗貞元末年,宮中派宦官到民間市場強行買物,口稱“宮市”,實為掠奪。
10.解釋下列句子中加點的詞。
①尋登進士第( 不久,隨即) ②愈素不喜佛,上疏諫之( 嚮來,一嚮 )
11.用現代漢語翻譯下列句子。
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奬勵。
譯文: 韓愈因為自己是孤兒,從小就刻苦學習儒學,不需要等待別人鼓勵。
12.通讀全文,你認為韓愈具有怎樣的性格特點?
答: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
【譯文】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好像是東北遼寧省)。父親名叫韓仲卿,不做官也不出名。韓愈三歲的時候成了孤兒(難道母親也沒了?韓愈在祭奠侄子韓老成死的祭文中沒講明白,說衹能依靠兄嫂),被同族的堂兄撫養。韓愈因為自己是孤兒,小時候學習儒傢經典很刻苦,不像其他孩子那樣還需要奬勵來誘導。大歷(唐代宗年號766~779)貞元(唐德宗年號785~804)年間(因為其他年號都比較短),文壇風氣是比較崇尚古文,模仿楊雄和董仲舒的議論文,而獨孤及和梁肅被稱為模仿的最好,贏得了知識分子的廣泛尊敬。韓愈和他們的擁躉們交往,刻苦鑽研和模仿,打算靠這個成為當時有影響力的人物。在考取進士的時候,把自己的文章上交給多位國傢重要行政長官,曾擔任過宰相的鄭餘慶很欣賞他,積極地稱贊他,因此很快就出了名,很快就成了進士。
宰相董晉到大梁去工作,請韓愈作他的巡官。董晉的職員班子撤除後,徐州的張建封又慕名請他去做下屬。韓愈認為自己得到了承認,說話越來越直率,不去刻意躲避和忌諱什麽,他的品德專一而正派,不去從事一些世俗的人情交際。後來調他去做四門博士,在後來升為監查御史。德宗晚年的時候,朝廷中分了好幾派,宰相也不好好負責。宮市(就是太監到市場上明搶,白居易的《賣炭翁》就反映了此事,曾導致一名太監被憤怒的農民殺死,因為這個太監不但要搶東西,還搶人傢的驢子)的弊端很明顯,但諫官們反復提意見皇帝也不接納(因為搶的東西都是他自己用,德宗就是這樣一個目光短淺,自尊心超強和喜好姦佞的一個混蛋,可以說他在位時期,極大地動搖了地主階級的腐朽統治)。韓愈曾經寫了幾千字的文章極力批判這件事,皇帝不聽反而很生氣,把他從京官貶到連州(後來劉禹錫好像也被貶到這地方,好像屬於廣東省,當時屬於不發達地區,很邊遠)山陽縣做縣令,後來又轉到江陵府作政府科員。
元和初年(唐憲宗年號,805年以後,唐德宗的孫子,他在位期間對不服從的藩鎮手腕強硬,並取得了很多成績,逐漸恢復了朝廷的威望,史稱元和中興),召韓愈去做國子博士,後來又任命為都官員外郎(大概相當於什麽候補委員之類,宋代,員外幹脆成了土地主的代名詞)。但是華州刺史閻濟美因為公事停止了華陰縣令柳澗縣令的工作,但還讓他臨時擔任職員的工作。過了幾個月,閻濟美停職了,到公寓中去住,柳澗挑撥農民工去嚮他討要前年為軍隊服勞役的工資。後來的刺史認為柳澗做事不妥,上報朝廷,朝廷把柳澗貶為房州司馬。韓愈正好經過華州,聽說此事後,認為倆刺史合夥欺負人,就上書朝廷替柳澗開脫,韓愈的奏章被留在了皇宮中沒有處理。皇帝命令監察御史李某某考察這件事,發現了柳澗的罪惡,於是追加處罰,把柳澗貶到某處作尉官。朝廷認為韓愈在不清楚實情的情況下鬍說八道,又把他恢復成原來的職位:國子博士。韓愈自己覺得自己很有纔,但卻常被朝廷,丟在一邊,就寫了一篇《進學解》自我安慰:國子博士早晨到學校,把學生們召集來,教導說,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大傢趕上了好皇帝,都好好學習儒傢經典,不要擔心自己沒有出頭之日,還沒說完,學生中有人笑起來,說,您這是糊弄我們呢,我跟了您很久,您學習六藝非常的投入,排斥不符合儒傢精神的佛老思想,刻苦總結從古到今所有的經典,但您公衆面前既沒有威望,也沒什麽私人關係比較好的朋友,動不動就被貶官,日子過得很清苦,頭髮掉了牙齒鬆了,不去考慮這些反而教別人和你一樣?先生說了,你過來,我衹是說你自己努力就行了,至於會不會受重要,那是宰相們的事情。孟子和荀子都很牛查,但他們也不是沒有機會?我現在雖然文章言論並不是很恰當,皇帝大臣沒有收拾我,對我已經很眷戀了。政府中管事的人看到這篇文章很同情他,考慮到韓愈很有史學才能,委任他作比部郎中和史館修撰(編寫史書)。過了一年,又提升為考功郎中(可能是負責績效考評的人力資源部官員)知製誥(起草政令的人),然後封為中書捨人(差不多吧,也是起草公文的)
不久又有看着韓愈不順眼的人,提出他以前的舊事,說韓愈曾經降職到江陵府科員期間,荊南節度使(省級軍政長官)裴均對他很好,裴均的兒子裴鍔很平庸俗氣,最近裴鍔回傢看望父親,韓愈作了一篇序文送行,稱呼裴均的字(好像古代不興對兒子稱呼父親的字,具體搞不懂)。這種言論在朝廷傳播開來,因為這個韓愈又被貶為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817年)8月,宰相裴度擔任淮西宣慰處置使,兼任彰義軍(軍是行政單位,和州一級,水滸上害宋江的黃文炳,傢住無為軍)節度使,請韓愈作他的行軍司馬,賜給韓愈金紫的衣服。淮西和蔡這兩個地方平定之後,12月韓愈隨裴度返回首都長安,因為功勞授予他刑部侍郎(刑部副部長,定額好像是兩位),命韓愈編寫平淮西碑碑文,這篇文章中韓愈多數突出裴度的事跡,而當時進入蔡州捉拿吳元濟的,應該是李愬功勞最大,李愬很不服氣。李愬的妻子跑到皇宮中上告碑文不能反映真實情況,(李愬的父親是李晟,功勞很大,娶的老婆好像是公主),皇帝下令取消韓愈寫的這篇碑文,讓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編寫並刻石。
長安附近的風翔,有法門寺,法門寺中有座護國真身塔,塔中珍藏了釋迦牟尼的手指骨一節,傳說這個寶貝三十年開啓一次,每次開啓會保佑莊稼收成好,人民幸福和諧。元和14年(819年)正月,皇帝讓太監某某帥三十個人,去迎接佛骨,要在皇宮中保留三天,再送到各個寺院。無論是大臣和老百姓們,都跑去施捨(畢竟三十年纔一次,人生有幾個三十年?亂世之中求個平安吧),唯恐落在後面,老百姓就有因此而導致破産的,甚至燒掉頭髮燒灼胳膊去趕這個時髦,韓愈一嚮不喜歡佛教,於是上了一篇《諫迎佛骨表》(參見我另一篇文章)。
憲宗看了這篇文章十分生氣,過了一天出示給大臣們看,將要嚴厲處置韓愈。裴度和崔群說:韓愈雖然讓您生氣,應該判罪,但也是因為他內心很誠懇,不怕被您處置,否則他幹嘛這麽吃力不討好?請寬恕他以顯示您的大度,這樣會鼓勵其他上書言事的人。皇帝說,韓愈說我過度信仰佛教我可以寬容,他幹嘛說東漢之後皇帝信佛的都短命,這豈不是太荒謬了,作為臣子如此狂妄,不能原諒!於是大傢都嚇得不敢說話,以至於其他官員都認為韓愈罪有應得,隨便找了個藉口把韓愈貶官為潮州(今廣東潮汕吧?當年鰐魚泛濫成災,想必也是蠻荒之地)刺史。
韓愈到了潮陽,又上表給皇帝說:...
憲宗對大臣們說,昨天看了韓愈的表章,想起他勸諫我不要接納佛骨的事情,我發現他還是很愛我滴,我怎麽會不知道呢?(憲宗屬於一驚一乍的人物),但是韓愈作為臣子,不該說我信仰佛教就會短命,我是因為這個討厭他的隨便)憲宗打算重新啓用韓愈,所以先跟大臣們打個預防針,想看看大臣們如何反應。宰相皇甫鎛討厭韓愈的剛直,恐怕他被重用,第一個跳出來回答,韓愈終究是狂妄粗心,把他調到一個好一點的州郡吧,於是授予韓愈袁州刺史。
開始,韓愈得了潮陽,開始辦公,問到老百姓關心的事情,都說,本地西邊的湫水中有很多鰐魚,體型巨大,把老百姓養的傢畜將近吃光,所以老百姓都很窮。過了幾天,韓愈親自去看了一下情況,命令判官某某抱着一個豬一個羊,投到湫水中,並作了一篇祭鰐魚文,讓鰐魚們滾蛋,如果不聽就派人收拾它們,不要後悔。祝願完畢的那天晚上,湫水中忽然颳起了狂風,伴隨着打雷,幾天之後,湫水全部幹涸,從此潮州人再也不用擔心鰐魚。 袁州的風俗,男女到別人傢做僕人的(估計是少男少女的傢長藉了富戶的錢,把兒女作為抵押),如果超過期限不還錢,則做工的人就永遠做富戶傢的僕人。韓愈到袁州之後,增設了相關法律,贖出那些未成年人,還給他們的父母,改變從前的約定,禁止富戶這種搶男霸女的行為。
元和15年,上調韓愈為國子祭酒(國立大學的校長),轉去做兵部侍郎(國防部副部長)。正趕上鎮州亂兵殺死了州長田弘正,推舉王廷湊代理軍政長官。朝廷讓韓愈去安撫人心。韓愈到了之後,召集軍民,告訴他們什麽是正確,什麽是造反。慷慨陳詞,王廷湊在一邊聽了對韓愈很敬畏。後來又改任韓愈為吏部侍郎(國傢勞動部人事局副局長)。後來又改為京兆尹(首都長安市市長),兼任御史大夫(言官,負責嚮皇帝建議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因為韓愈不太去指定地點上班,,被御史中丞(根據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早先御史中丞這個官是御史大夫派去到皇宮中和皇帝做溝通的官)李紳(誰知盤中餐的作者)彈劾。韓愈沒有被查辦,不服氣,還是不去上班。李紳和韓愈都是脾氣性格急躁走極端的人,於是互相吵鬧,別人怎麽勸也不聽。於是皇帝各打五十大板,派李紳作浙西觀察使,韓愈改任兵部侍郎(國防部副部長)。等到李紳要去浙江之前,跑到皇帝面前哭訴,唐穆宗(很貪玩的一個皇帝)可憐他,於是讓李紳作兵部侍郎,韓愈作吏部侍郎。長慶(穆宗年號,白居易有白氏長慶集)四年12月死去,時年57歲,追認韓愈為禮部尚書(教育部部長),謚號為“文”,所以後世經常稱他作韓文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