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 诗人用外语撒谎
Acquired 2019-11-27
语言之意义的这一徒劳的承诺,就是它的命运,也就是,它的语法和它的传统。诗人是虔诚地接受这一承诺的幼儿,并且,他虽然供认承诺的空洞,但他也为真理而决定,他决定记住那样的空洞并填补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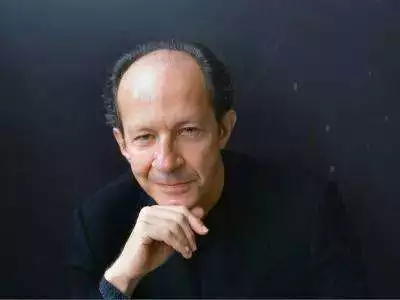
▼
独一者的观念
文 | 吉奥乔·阿甘本
译 | lightwhite
1961年,为了回答巴黎书商卡尔·弗林克(Karl Flinker)的一份关于双语制问题的调查,保罗·策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不相信诗歌当中的双语主义。是的,一种双重的语言的确存在,甚至是在许多当代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那些让自己如此欣然地适应当下文化时尚的作品里,它绚烂多彩正如它使用多种的语言。
“诗歌的独一性在于它是语言的命运。因此,它不能——请原谅我的这个平庸的真理,诗歌和真理一样,在平庸中太过频繁地迷失了自己——它因此不能是双重的。”
一个在布科维纳(那里,除了意第绪语外,至少还有四种其他的语言)出生并长大的说德语的犹太诗人,不会轻松地给出这个回答。在战后不久的布加勒斯特,考虑到他不应该用杀死其父母(他们死于一座纳粹集中营)的刽子手的语言写作,他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成为一个罗马尼亚的诗人(他在那一时期的罗马尼亚语诗歌已经保存了下来),但策兰简单地回答说:“一个人只有用他的母语才能讲述真理。诗人用外语撒谎。”
在这里,对诗人而言至关重要的语言之独一性的经验是什么?可以肯定,它不简单地是一个单语主义的问题,即使用母语来排斥其他的语言,并同时停留在和它们一样的层面上。它毋宁是但丁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心中之经验的问题,他说,母语是“心中的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一个语言。”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永远预设了词语的语言经验,换言之,我们说话,仿佛我们总已经拥有词语的词语,仿佛我们在拥有一种语言之前总已经拥有了语言(我们随后所说的语言从来不是独一的,而总是双重的,三重的,陷于元语言的无限后退之中的)。反之是另一种经验,即人在面对语言的时候绝对地没有任何的词语。我们对之没有任何词语的语言,不像文法的语言一样假装在存在之前就在那儿的语言,“心中的第一个并且是惟一的一个语言”,就是我们的语言,亦即,诗歌的语言。
这就是为什么,但丁在他的《俗语论》(De vulgari eloquentia)中并不追寻从意大利半岛的本土荒原上采来的这种或那种的母语,而只是追寻辉煌的俗语,它把它的芳香呼入了每一种母语而不和任何的一种母语相一致。为此,普罗旺斯诗人认识到了一种诗歌的类型,“杂诗”(descort),它证明了一种独一的、缺席的语言之现实,但唯有通过诸多习语构成的巴别塔,才能够实现。人类参与其中的独一者,作为唯一可能的母性真理,即普遍的真理,总已经分裂。在一个人抵达了独一之词的时刻,一个人必须挑边,一个人必须选择一种语言。同样地,当我们言说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某种东西——我们不能只说真理;我们不能只说我们说。
同这种,可以说,既被人划分又不可分享的独一语言的相遇,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了一种命运;这就是我们趁诗人虚弱之际,才能够从他那里夺来的得承认的真理。但这样的命运事实上如何能够存在,在那里,既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词语,也没有一种语言的同一?而这样的命运会对谁发生,如果那一刻我们都还不是言说者?幼儿,从没有像这一刻一样,如此地难以触及,如此地遥远,如此地没有命运:正如词语本身表明的,他站在语言面前,一无词语(拉丁语的幼儿infante指涉了infans,“不说话”)。命运仅仅关注这样的语言,当它面对世界的幼年时,它便发誓要能够与之相遇,要永远围绕着它说些什么,除了名字。
语言之意义的这一徒劳的承诺,就是它的命运,也就是,它的语法和它的传统。诗人是虔诚地接受这一承诺的幼儿,并且,他虽然供认承诺的空洞,但他也为真理而决定,他决定记住那样的空洞并填补它。但到那一刻,语言站在他的面前,如此地孤独,如此地被离弃给了自己,以至于它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加:“la poésie ne s’impose plus, elle s’expose”(诗不再强加,它暴露),正如策兰在一篇死后发表的文本中写道,这一次,是用法语。在这里,词语的空洞真正地填满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