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望《神曲》误译举隅
高文斌 學人Scholar 2019-1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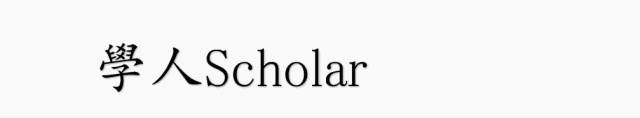

文 | 高文斌,学人Scholar学术观察员
作者授权首发,转载须取得授权
田德望译《神曲》为中国大陆最通行的《神曲》汉译本。然而以意大利文原文核查田译可知,田译错漏百出、极不可靠。本文主要核对田译《地狱篇》第一章开篇部分,也即《神曲》全篇最著名、最重要的部分。
在细校之前,有必要对《神曲》在中文世界的流传情况简要说几句。《神曲》浓厚的天主教色彩使其在中国缺少生根发芽的土壤。除非对天主教的神学传统有深刻的了解,否则一般的中国读者阅读《神曲》只能是白费功夫。即使在美国这样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一般读者理解《神曲》也是极吃力的,通常需要借助大量的“注疏”(commentary)。

田德望译本《神曲》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实际上,“神曲”这个题目本身已是误译。意大利原文为LaCommedia,直译应为“喜剧” ,所谓“神圣”(意大利文divina)乃是传布过程中加诸此作的赞词,而非但丁原意。在英译LaCommedia的传统中,通常译为TheDivine Comedy,以对应意大利文的LaDivina Commedia。这种翻译虽不完全准确,但是出于对约定俗成的赞词的尊重,亦无可厚非。不过所有的译者都必须突出“喜剧”一词。“喜剧”作为西方传统文论中一个有特定意涵的概念,用在此处包含了但丁深刻的匠心,乃是全诗的“诗眼”。限于篇幅,而且因为本文的读者非专门学者,我不想在此处做太多申论,但是总而言之,“神曲”的翻译是错误的。如果连标题都译错,而且若干年来陈陈相因无人指出、改正,就可见对这部西方文学奠基巨著的知识在中文世界是多么匮乏。本文出于方便考虑,暂且继续使用“神曲”一词。
我们下面来看《地狱篇》(Inferno)的第一个句子。意大利文原文如下:
Nel mezzo delcammin di nostra vita/ 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ché la diritta via erasmarrita.
这句诗是意大利诗歌传统中皇冠上的明珠,在意大利几乎人人都会背诵,田德望如果真得对意大利诗歌传统有深刻的了解,就不至于把意大利诗歌中最重要的一句译得如此不堪。我们且看田氏是如何翻译的:
“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道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
我无意故作情绪化的惊人之语,但是我不得不说,田德望的翻译实在“令人发指”。意大利热爱文学的朋友们听说这种离谱的翻译后,一定会拍案而起的。我先将这句诗正确的直译写出,然后再略作解说(我着重标出的就是田氏译错的地方):
“在
我们
人生的中途,我发现自己
再次
陷入黑暗森林,
因为笔直
的道路已然消失不见。”
但丁这句诗一上来,就把“我们”(nostra)和我(mi)对举,揭示出人生经验的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永恒矛盾。田氏在第一个小句中把nostra漏掉,委实令人费解。他的第二个小句说但丁“已经迷失了道路”,就更属于胡说。我猜测他的“已经”是对应意大利原文中的ritrovai,但是ritrovai里的前缀ri,明明是表示重复,其意为“再次发现”。此处的“再次”是有明确所指的,即但丁的生命在他爱恋的贝莉缇彩(Beatrice)出现前本是一团漆黑,在贝莉缇彩早逝后重又陷入了黑暗。如何能把“再次”曲解成“已经”,我也十分疑惑。这个三韵句的第三个小句第一个词为ché,即“因为”。但丁的原意是他之所以重陷黑暗森林,是因为笔直(diritta)的道路消失了。这么清晰明确的因果关系,在田译中竟然完全消失不见!最关键的形容词“笔直”也消失了!

Gustave Dore关于地狱篇Inferno的插图,1861
更有甚者。但丁这句诗之所以广为传诵,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触目惊心的直接性。一般的长诗一上来总要有”引言”或者“铺垫”,而但丁却单刀直入,突兀地把我们带入黑暗森林,这种写法在拉丁文中有一个专门的词,即inmedias res,可以直译为“直入事物中间”。但丁“再次发现”自己陷入黑暗森林,换言之在开篇的时候但丁就已身陷险境,至于他陷入此种境地的过程,诗人却刻意省略了,套用汉语文言文的说法,可说是“茫然不知其所由”。然而这种巧思却被田译彻底破坏。在这个译本中,但丁大大方方地“走进了”黑暗森林。而且田译想当然地以为但丁是先走丢了,然后才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森林,所以他把原文的第二和第三小句的顺序颠倒过来,造成一种完全违背但丁原意、毫无诗意可言的流水账!
限于篇幅,我无意在田译的错误上继续纠缠,姑且举一例以代其余。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田本《神曲》的第二个重要部分,即他的注释。正如我开篇指出的,由于《神曲》的特殊性质,没有详实的注释,读者是读不懂的。意大利出版的《神曲》,注释的篇幅通常数倍于原文。由于但丁原文十分晦涩,各个注家往往意见不一,所以当代的各种版本一般都博采众长,再适当加入该版本编者自己的意见。引述前辈注家的意见时,往往在括号里写出该注家的名字,这是基本的学术规范。田本的注释虽然比较详细,但是极具误导性。在我看过的各个注本中,从没有一个像田本这样武断的。比如在注释第一章“小丘”的寓意时,田的注7只有斩钉截铁的一行字:“小丘象征现世的幸福。”在浩如烟海的《神曲》注疏中,我不能排除若干注家可能把“小丘”理解为“现世的幸福”,但是我在意大利和美国转益多师,从未听过任何一位师长做这种解释。一般的解释是但丁想直接“登天”,但是因为罪孽未净,这才遭遇三兽拦路,被迫以退为进,先入地狱然后才依次进入炼狱、天堂。我选择这一处,目的不是争论哪种解释最正确,而是说明田氏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小丘是“现世幸福”,是严重违反现代学术规范的。读者读到他的注解,很容易产生误会认为这就是学界的主流观点甚至是唯一观点。

冥界的渡守者卡戎用船搭载死者的灵
而田注挂一漏万的武断,可说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在注38中,他说贝莉缇彩代表“神学和信仰”,维吉尔代表“哲学和理性”。维吉尔作为诗人,如何能代表“哲学和理性”,恐怕需要进一步论证,而贝莉缇彩作为但丁理想化的爱人,恐怕首先代表的是“爱情”,“神学和信仰”则是从作为基督教三美德(信、望、爱)之一的“爱情”(拉丁文caritas)中引申出来的。田本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对于读者的误导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他从这种武断见解推导出所谓但丁的“中世纪偏见”(注38),就属于特殊时代里反宗教的政治教条,时过境迁,更加不值一谈了。
田本的错误是极多的,我如果继续写下去,可以再侃侃而谈几千字。但是这种连篇累牍的论述只会让读者厌烦。我相信以上的论证已经说明为什么这个版本是极其不可靠的。对于流通在中文世界的几个其他译本,我没有细读,也就没有发言权。我倒是读过所谓“天才学者”吴兴华从意大利文直译的片段,其颠倒错漏与田本不相上下,虽然更有文采一些,但是也难称佳译。对“明星学者”的追捧,对学坛掌故的津津乐道,本身就是一种智识怠惰,说得严重些就是反智主义。翻译工作和学术工作都是苦差事,需要扎实的功底、卓越的才情、坐穿冷板凳的精神,而这些都不是新闻媒体乐意报道、一般读者乐意谈论的,所以一个严谨客观的学术共同体就格外重要。就意大利文学的汉译来说,这个共同体在中国大陆是几乎不存在的。田本之劣,在美国会迅速成为学术丑闻,而在中国竟然风靡数十年,成为所谓“权威译本”。我们的学术界,难道不应该有所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