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欣赏〡马•瓦尔泽【德国】:梅斯默的想法(上)
朱刘华〡译 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2018-10-08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年生于德国。1957年获黑塞奖,1962年获豪普特曼奖,1980年获席勒奖,1981年获毕希纳奖,1996年获荷尔德林奖。1998年10月再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早期作品如广播剧本《外面》《小规模战争》和小说集《房屋上空一飞机》等受卡夫卡影响,情节离奇。后转向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主要作品有《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烟》《克莱斯特茵三部曲》《爱的彼岸》《无家可归》《心灵的活动》《天鹅别墅》《爱的表白》《喷泉》等长篇小说、十多部剧本及其他体裁的作品。
《梅斯默的想法》问世于1985年,该书由许多出色的微型故事和警句组成,被评论界认为是作者最美的一部散文体小说作品。作者的目的是要写出“自传的第四维”,在暴露自己的同时又掩盖自己。书中的主人公梅斯默无疑就是作者的第二个自我。梅斯默滞留在某大都市的火车站,给一位老友打电话,对方却没有兴趣再与他交谈或会面,从而使他思绪绵绵。本书的情节被淡化到极致,但文中的每一句话都令人深思和回味。

梅斯默的想法
马丁·瓦尔泽作 朱刘华译
一
在我发出的所有声音中,我自己的声音最为低弱。
我的脸是一扇门,进得来却出不去。
什么都可以改变我。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岁月穿行过我的脸,像个征服者。
必须赞美隔开你的那堵墙。
我从一道日见缩小的缝隙外窥。昨天给我打来电话,今天却不打,此举多么卑鄙啊。
我着迷于短暂的,总觉得时间漫长。
他尽快赶走人们,然后坐下来。看来他过得好极了。他明知如此,但他感觉不到。
有人通知我他将来访,令我惊惶不安。我不想他来访。我不能这么明讲。直至他跨进门来,我的痛苦都在加剧。他进来时,我心受创伤。为了不让他感觉我实在无法忍受他的造访,我老在他想走时挽留他。直到凌晨三点,我俩都精疲力竭了,他才得以出去。我扑倒在床上,快活得泪流满面。
如果邻居正确理解一回一种噪声,那他以后每闻此声,就会明白我在干啥。
梅斯默的想法是一个胖女人的想法。这他心知肚明,有无证据他都无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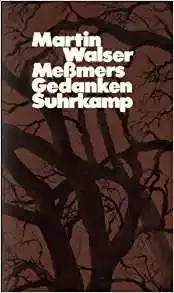
梅斯默的目的:自传的第四层次。这个意志薄弱者,他耍尽一切花招寻求逃避。思想:暴露和隐藏同样臻于极致。也就是一种既暴露又隐藏的语言。梅斯默认为,这是加利福尼亚的气候造成的。
只要他在这里,他就坚信会发生一场地震,这既有可能是沾沾自喜、自视过高,也可能是长期经验的结晶:最糟糕的事情老会发生在他身上。他每次都为那些跟他同登一架飞机的人们感到遗憾。就因为同他一道飞行,他们很快就得死去。离机时他仔细地打量众人。他安然无恙地抵达了美国,他想知道,为此他应该去向谁道谢。
每天去地震研究所。至今一切平安无事。深渊装出它还没察觉我处在世界最敏感部位的样子。我却感到被它觉察了。我日夜等候着来自安德雷亚斯褶皱的回音。被深渊觉察,感到你对灾难有吸引力,没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了。
自知被爱上了的感觉真是不一般,即使热恋上自己的是灾难。表面上谁也看不出那张裂缝的网络,它像神经系统一样密布在梅斯默的生活里。可那确实是裂缝。奇怪的是,一切看上去都还形影不离、和衷共济。可早就不是形影不离了。是他在维系着它们。他怎么样才能表现得不像个英雄啊。如果他不在暴风雨之夜离开格瑞茨勒峰林荫道上的房屋,就会有从地下喷薄而出的水和天上的龙卷风将他客居其中的这座房子毁灭。他仓皇而逃,为的是拯救C。值此暴风雨之夜,C的丈夫正在长岛痛骂他,因为他在这么个灾难之夜留下了C孤零零一人。梅斯默回答说,他是为了挽救C和那座房子才走的。共同经历过一切的C相信他。她的丈夫不信。
他虽然接纳每个人,却不是每个人都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眼前,浮现在眼前的只有一位,C。正面像。她,热情洋溢。他,爱走极端。
他,一颗火柴头。稍一摩擦就会燃尽。
地震之夜后的那个早晨,田鼠掘出的土丘前所未有的大。
回到家里,他在笔记本里写着:请别再走。你若还要走,请让我留在家里,我不想再跟着。
梅斯默认为,他得时刻做好会被人发现的准备。
我们沿着可爱的黑森林往前行驶。林谷像是在盛邀我前去隐匿。
我想隐藏自己。如果一个愿望如此频繁地袭来,我这样对待它就嫌不够严肃了。我一次次肆无忌惮地决定抗拒这一愿望。我接受暴露我自己的邀请。
人在旅途时,时间最缓慢,在家中最迅捷。因此应该一直旅行不止。
只因自己不强大,一个人需要忍受多少事啊!
他越来越经常言不由己。他渐渐地不得不承认,他不是他想做的那个人。抑或他应该继续要求自己做那种在能够脱口而出之前先得炮制一番的文章?
我耳朵里听到的东西,好像是讲给另一个人听的。我先得成为那个人,然后才能习惯。人们期望我这样。
一想到今天将不得不极力控制自己,他马上就因预感到那为此需要作出的努力而有些晕眩。
所有陷阱中最严重的陷阱是自我设置的那个。
最严重者之所以能发生,恐怕应归功于下列情形——我们可以逃避自我,躲进见证我们的毁灭过程的语言,变得无动于衷。随语言消亡。
堡垒。渗透。渗透结束。盯着渍印。需求消逝。围墙。遗物。颤动着化为乌有。静躺不动。融解。融解的经历。镇静自若。灾难立至。
暖气邃然中止。沉寂打破了。还有某物的一声叮当,这是金属的兴奋,然后是静谧无声,我听天由命。
他很喜欢自视为一位停止歌唱的音乐家。他的脑海里就像暖气凉却时那样喀嚓嚓响。
我是个不饮酒的醉汉。
他碎化为单独的句子;他将它们伪装成呼喊。
时光美好时我却不知其美好。
我的双脚伸在草里,有数百万脚趾。
我全身充盈着乐音,唱不出口的乐音。嘴巴张开,什么声音也出不来。
我穿行于林荫道。树叶在我身旁奔跑。
我老是只看到太阳落山。
我跌倒的次数比站起的次数多。
我小心提防,脚踩实地。我害怕地面坚硬。
我观看鸟儿如何被某种不会飞行的东西赶走。
孑然一身,了无声息。谁孤身一人,谁就悄然等侯。一旦感觉到了上帝,就放声高歌。看透自己后他又将再次噤声。
当你们劳作时,我让时间流逝进我很久以前放在炉火上的壶里。
设若冬天能停滞在冰里,春天以及一切就都不会来临。但今天,光线里,空气中,那光芒,那柔和,很快就会因风、温暖、肥沃、路线、死亡而陶醉。
协调者想不通的一切对一个点会产生什么影响啊。
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件,宛如接过一只充满气的气球。打开信笺,阅读,空气流逸,手里只留下垃圾。
我枯萎地挂在花瓶里回想湿润。钟声湿淋淋地敲响,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闪电多是打进我的大脚趾甲,无法加害于它。果汁的浪潮排山倒海。少女们被吸引了,拍打翅翼推波助澜。既然这已经结束了,怎么可能不全部结束呢?
我不停地拿两指合上眼睛。我就这样装成一个渴想啥也不再认识的人。
当我的困窘跟不上下一步,当我不知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冬天诞生在一只神奇的核桃里。这下每一种温暖都令我发冷。当我的四肢在种种寒冷里燃烧时,我发着高烧跑上山去,住在一月的森林里,和二月的风暴赛跑着,踏进松软的三月,递给它火。
我在世界上踽踽独行。我可以这么说。我跟其他人一样,没有伴侣。我负载着命运。这是时尚。不可能比我更普通的了。
当人们打开众动物皆毙死其中的笼子时,未来的日子非常可笑。那必须清除的粪便。那曾经溺爱的家当。粪便中全是个人用品。由个人用品变成粪便,周而复始。就连专家也很难区分。
没有胆小。我们不得不强鼓起脆弱的勇气。有些人甚至能用一张爱意殷殷的嘴巴接吻。
我思考一切,可它们只是倏忽掠过,头颅冷冰冰,像座久无人住的建筑。我在匹兹堡机场内感到不适应,就这么回事。
他在城市里走的时间越长,货物的呼喊就越令他难以忍受。越是不知所措,这呼喊就越是刺耳。仿佛一群行将沉沦的活物的呼救。但谁也不会心生恻隐。人们双手捂耳跑掉了。
一下子支付太多钱时那种受蹂躏的感觉。自惭形秽的感觉。就像是经过了一场放浪?
钱制造出一种恐惧的幻想,幻想中出现的除了钱还是钱。
梅斯默认为,钱从不属于任何人;除非它退出了流通。
我们既不会使用它,也不会有啥剩余。
那块绿地。令人羞愧的感觉立至:它是你的。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的恶果:相信能支付得起的一切都属于自己。
我的衣服多于我的需求。我有些鞋穿也没穿过,衬衫簇新。我的房间多于我的需求。我怕我不需要的东西会被人拿走。
我如此活跃。而且是在都柏林。这好像还不够。
我替商业银行感到遗憾,我在那里注销了我的户头。事情就是这样的。
可笑才是最美的。它是一顶不晃荡的王冠,因此戴在你头上正合适。
需要我帮助的人仍然不知所措。
我们每周会需要多少左拉啊?
现在我又可以坐下,让真实沿着我的油性皮肤跑下来了。
我希望,冒险发生于创作中,而不在行动中。
写作可以让思维速度减慢。如果我今天不借助写作刹住我的思维,它会将我带到某个我不想去的地方。
不可以留下。不同意发生的事情。但还是不抗争。没什么大不了的。看上去应该像是你在控制自己。应该让偶尔瞟你一眼的人感到你很温和。你感觉到暴力。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暴力,权力,强权。世界不会顺着你的意志发展。你让步。每个人都被了结。他应该对此点头称是。那是个漂亮姿势。大概源自英国。可能有无法估测的被了结的方式。但越来越少。这周围差不多没有了。在此确实得点头称是。沉默不语,但点着头——这要求不过分。
在潮湿的夏天应该扪心自问。我呼吸空气。氧气不等于一切。不幸是个气泡。它曾经多么轻盈啊。现在由于我的过失而消逝了。我何时还能干点儿什么?被碾成粉末,变成废物。像大多数人一样。但没有默契。就这么回事。跳跃?不。
涂着人造颜料的灰面孔。仿造的植物。我们以历史的舌头在玻璃下面讲着话。我们的毛发呻吟得那么低声,我们都快听不到了。
天空,一个无法放松的词汇。还有潜力。它们一文不值。我们很想像孩子一样天真。我们也呼喊,孤独地呼喊。
生活无论如何是美好的。头痛使之更美好。但此生大多数美好的东西都很短暂。因此有种对钟声的需求,对振荡、轰鸣、回音袅袅的需求。永无止息,过去的恐惧,美丽的恐惧。现在我生活着,毫无恐惧感。
时间在夜的苍穹里叮当作响吗?有什么需要被解放出来吗?我的耳朵老是欺骗我。它们将风声译成德语,给寂静画上句号。
即便在他的房间里,他也受到了他的超强对手的追踪。他不见其形,只闻其声。
当他头回听到那声音时,他跑向所有的窗户,关上它们,断定那声音不是来自室外。直到他躺在床上拿被子蒙住头时,他才断定,那声源不在屋里的某处,而在他体内。
我喜欢一位朋友对一些事情的不敏感,而我同我这类人对这些事卑鄙地敏感且为此无聊地骄傲、嘲笑那位无此变态者。
我不愿自己是现在这个样子。其他人都是这样子,这已经足够了。他们不停地倾诉心里话。他们讲的有关自己的事情,像是在讲我,我从中看出,我不愿像我现在这样子。也许其他人会助我一臂之力。他们让我重获新生。从我自身的体内为我接生。
我谎称很快乐。我谎称生活在一道愉快的霞光里。我的每一步都唤起一种舒伯特式的迷人的深沉感。我走到屋外,我谎称所有最受欢迎的机会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弯腰致敬了。我谎称每天令我最有趣的是得知没有我不成。我谎称从没想到过我如此的举足轻重。人人都需要我。竟有这种事!现在可别众人同时握我的手啊!我可不能一下子满足一切呀!可他们不放过我。被这么簇拥着,我恐怕能活到一百一十一岁,也没有一天会感到疲累。我将不知疲倦地满足一切期望。我的生命将成为惟一的一次吻合。我现在举着葡萄酒杯的样子——面对我的沉着酒杯得当场炸裂。它不炸裂。
让我们彼此扯谎吧,直扯到我们不知天昏地暗。让我们暂时不会受到伤害吧。
一个晴日的怒火。没有痛楚的冷嘲。无缘无故的愤懑。
我感到窒息,似有什么跃然欲出,但没有比这更空洞的了。表述的欲望幽灵似的。
我希望,四面满满的,我的头颅里不停下雪,由于一切全腐烂了,就没什么还会再腐烂。
怀疑自己不幸的感觉仅仅是源自自己的非分之想。或者他们已经让谁将所有罪责独揽了?
想象中的伤口鲜血淋漓,在公园的阳光下吮着冰棍,心灵充满了连环漫画的原型。我们可不可以不订房就继续前往巴赫曼国呢?除了间或有个被打败的孩子我们在此还会遭遇上什么呢?
自我指控的程序和自我辩护的程序——这是同一程序。我看不到怪罪和辩护之间存在区别。
梅斯默认为,连对自己也得缄默不语的,那便是真理。
面对那些他感到有些疏远甚或是没有好感的人,他强调他相信跟他们具有少量的共性,他强调得那么厉害,令对方都认为从没遇上过比这更相通的心灵了。就这样有一段时间他找到了朋友们。
为什么不能对你景仰的所有人立即说声好?有些人根本不喜欢别人尊重他们。
保留是我的真实生活。它像个滚烫的夹子盘踞在我的头颅里。
我不可以让人察觉的,那是我的素材。极尽伪装。而未曾撒谎,确切无误。我现在的形象实在是得变变了,那伪装就是多余的了。真理若是灾星,就得回避它。这颇具戏剧色彩。
你可以放心,我越是言词激烈,我所讲的东西就越不是我的意见。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我是如何努力证明一些我本人也不信的东西的。由于我不相信我想证明的东西,证明它真是困难。别人不是这样的吗?
每当我想讲“不”时,我都讲“是”。此乃事先练就,训练有素。不在语言的前沿阵地里的就是是。毋须我这一方面施加影响。
只要可能,我总是讲别人必然会最喜欢听的。有些人我一无所知他们喜欢什么。于是我就出丑了。
如果将一切统计起来,对方向我讲的要比我对他讲的少得多。结算时总是同样的赤字。因为我不能等。因为如果没人讲点儿什么,我马上就会很难为情。因为我什么都回答得太过详细。因为我相信,我有责任交谈。因此我永远获悉不了什么,总是讲得比我要讲的多。
如果我的行为表明,我注意到了对我作出的判断,那就太难堪了。
你得通过凑合而屈服。但你只能相信你是在欺骗,在扮演那个根本没觉得被伤害的人。扮演面对粗鲁无礼压根儿不会受伤害的那个人。你心想,你不是真的屈服。可无论你这么做时是怎么想的,凑合就是屈服。
从前,他确实跑了出去,光着脚,衬衫敞开着。他没在意。他喜欢这样一往无前。女人们,男人们,摩托车,无所谓。他没察觉。那是错的。他蹲在这个大都市里的这块礁石上。他试图靠少量的呼吸活下去。他不情愿地走进最近的电话亭给他的朋友N打电话。他身在火车总站,等着转车,但至少想打个电话。N敷衍着他,十分冷淡,听得出电话深深地打扰了他。他正要同大家出去吃饭。好,好,梅斯默急急忙忙地说道。这只是一种程序式的冲动,你到了X,就给N打电话,好了就这样了,再见。挂上了。他感觉到体内一切都在抽紧。他赞同这一痛苦的集聚。尽可能快尽可能小下去吧。微小到难以捉摸。他坐在站台的长椅上。过了差不多一小时,他才能让那痉孪消失;他才能够不仅坦然面对那疼痛,而且能问候它。就让它痛去吧。就让那疼痛在你体内。千万别反对疼痛。一张火车站长椅上的这么一种生命的绞痛简直就是最美的。疼痛,这是第四种艺术。位列音乐、绘画、作诗之后。也许甚至是第一位。对,第一位。还有什么能给人更多体验的东西吗?!更深刻?!更透彻?!你不必旅行、奔波、讲话,你可以坐在火车站的长椅上体验那形象丰富、紧张无比、多姿多彩、清晰明亮地流淌出的痛苦。幸运的人儿!你还想抱怨,现在你得赞美。你得赞美你的幸福。
我能控制自己。我可以满足了。我可以试着像个目空一切的人那样讲话。我可以孤零零像块石头。
就为了不唤醒他想谄媚对方的印象,他曾经伤害另一个人。实际上他是想谄媚他。N博士一出现,梅斯默就感觉到了那种想恭维他的冲动。因此他装腔作势,在他还没能作出决定之前,就向他喊出敌意的话语。那是在一次会议上。N博士走进早餐室。梅斯默喊得其他人都能听得见。他自己觉得勇敢。喂,大家请听清,我在伤害N博士,我不恭维他!他喊的差不多是这样的话:啊哈,这下我明白,我今天夜里为什么做噩梦了,原来是有您在这里!我以为您今天才到呢。这下我当然全明白了。同您共处一屋檐下,当然不会有好事!N博土一言不发,他一味地微笑。梅斯默希望N博士坐到他这一桌来。他向他讲话为的就是这个。但他却不可以流露出来。因此他必须伤害他。他无比激动地吞咽下了早餐。他独自坐在桌旁。N博士同其他人坐在一起。他们一再地哄堂大笑。
虽然打算极力避免,却偏偏讲出了那最伤害对方的话!仿佛想伤害的远不止于对方。通过给对方留下一心想伤害他的印象,而造成这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现在不立即殴打一个刚刚打过人、正在休息、喘气的人,我们就活不下去。当然也有双人决斗。这是一种得到认可的打斗形式。据说有规则。据说其中一人甚至会赢。
如果我能有张不带一丝微笑不带一丝寒意的脸多好啊。如果我能做到完全自然多好啊。我的脸太好动了。它不停地在滑来滑去,总有所表示。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们期望它表示的。它老献殷勤,殷勤过度。
因此他得去。梅斯默想,请你现在就向他们扮演一回劣者吧,屈服者,一个根本不值得考虑的人。他会大力逢迎他们。直至大家只能够笑着说:不,不,不,快别这么说了,这太过分了。他这么做了。没人笑。没人请他停下来。没人说这太过分了。情绪还从未这么好过。他们还从没对他这么友好过。梅斯默决定停留在这一角色上。
他每回都相信,这回终于好了。偏偏这一次出差错了。不管怎么说,这回是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这对于他是最有趣的:当他准备避免重蹈覆辙时,他又犯下一个全新的错误。他似乎有个最个人化的取之不尽的错误仓库。他每次都想问,还有多少啊。可这也会是个错误。
与我无关的礼物,我很容易道谢。但若有人送我什么我想要而没有的东西.我就很难谢出口。那时我就愤怒,疲塌,当场出乖露丑。
我的相信关系的能力立马消失。我毫不掩饰地保持矜持。那不可能是一种傲慢。我的矜持得到了回应。
每个人都心怀鬼胎地转向我。我为了我的目的应答。谈话是一席虚构。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虽然我闭口不提一切有可能伤害到他的东西,同其他人的接触也没有成功。
如果众人都像他对待大家的那样去对待他呢?那他会不会就失败了呢?
如果另一个人对我曲意逢迎。如果另一个人这么做,我会怎样谴责他啊?
梅斯默想,为了区分开来,你不必那样想,而是要不那样做。
谁试图让别人了解自己,就得准备遭到嘲笑。谁持有这种顾虑,就不会试图那么做。
你不属于你将自己当做其中一分子的那些人。在哪里遇到你,你就属于哪里。
使用词汇的那些人彼此没有区别。
我总是寻求能同众人和平相处。事实表明,这会招至忍无可忍。自己再也忍受不了自己了。再也不能跟自己和平共处了。
我不重视自己,而是重视我想讨他们喜欢的人。实际上我已经注意到他们现在必然是更轻视我而不是爱我。如果他们这时还能爱我,那他们会是些什么人啊?
我自我感到似在太阳面前逃遁的月亮一样贬值了。
我们得希望受到蔑视。设若我们受到尊敬,会给未来带来不祥。
当我们互不相关时.我们就都很幸福。
梅斯默认为,我不是个导热管。远不止于此。
他人越不能伤害我,他对我的伤害就越少。
他们若能摧毁,他们就摧毁。
对他人任何形式的亲近无不导致敌意。
被那些顺带揍你一顿的粗心人围捕。
如果你能成功地在逃跑时做出滑稽的动作,他们也许会停下来笑。你得利用这一瞬间,以求真能脱身。如果你不能逗得追赶你的人发笑,你就没机会了。
如果众人都像我这样,那就太可怕了。如果众人不是都像我这样,那也可怕。
我依赖于别人对我有个好看法。
未完待续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0年第6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