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礼孩: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 | 诗客观点
诗客 2018-09-04
诗
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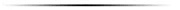
文_黄礼孩

黄礼孩
1.文学奖给了诗歌,感觉非常好
瑞典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国作家蓝蓝,她说起2011年10月6日这个让人期待的日子的一些细节:下午一点钟整,文学院主席皮特·英格伦德从那扇镶着金边的白色大门走出来,宣布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这是神圣的一刻,是让整个瑞典几乎都屏住呼吸的一刻。蓝蓝说,年年都是叹息声和喝彩声参半的文学院,今年就不同了,当皮特主席读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名字,是前所未有的一片惊叫和掌声,市区里也到处欢呼雀跃,电视上那些资深的记者和评论家都激动得快要失态了。特朗斯特罗姆终于众望所归,迎来伟大的时间。很多人知道他获奖后,都渴望去听一听他的感想,想了解他的生平和对诗歌创作的见解等等,但一切仿佛没有发生似的,诗人因为瘫痪丧失了声音语言,已经不能发声,不能表达自我,除了他通过夫人莫妮卡女士简短的答谢:“碰巧由你得到,当然是一件大惊喜,不过文学奖颁给了诗歌这件事让人感觉非常好”。以往文学奖的获得者都得为此接受采访或进行演讲,特朗斯特罗姆大概是仅有的获奖后不能发表演说的诗人吧。如果更早的时候把这个奖给他,或许就不一样了,但没有假设。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年把奖颁给他,尽管迟了,但没有像错博尔赫斯一样错过特朗斯特罗姆,没有错过给属于人类的大诗人颁奖。
2.词语间盛开的奇妙意象
1931年,特朗斯特罗姆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该校心理系任职,成为一名心理医生。23岁那年,他发表处女作《十七首诗》,轰动瑞典,文史学家扬·斯坦奎斯特评价他:“一鸣惊人和绝无仅有的突破”。此后诗人不断写作,到2004一共写出210多首诗歌。他是一个写得很慢的诗人,他开玩笑说如果他在中国三年会写一首诗。三年写一首诗歌肯定比他的同胞来中国用三个星期写一部小说要好得多。因为慢,所以精致,所以有质量,这也是特朗斯特罗姆写作的信条:在缓慢中让每一首诗歌通过词语的炼金术成为一流作品。这一点值得中国的一些诗人学习。现在很多人写诗,刚完成就匆匆忙忙拿出来发表,刚发表已被遗忘。庞德说过,“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特朗斯特罗姆是造境大师,他有中国人惜墨如金的秉性,他曾经说过:诗是以一当十的文体,它包容了感觉、记忆、直觉等一切元素……诗歌的对立面是松散的语言,比如发言时滔滔不绝的高谈……基于这样的认知,他多数时候着迷于短诗的写作,并在其间盛开多个意象,让崭新之物惊人地出场。他的《复调》就是一首意象缤纷的诗歌:“在鹰旋转着的宁静的点下/光中的大海轰响着滚动,把泡沫的/鼻息喷向海岸,并咬着自己的/海草的马勒//大地被蝙蝠测量的黑暗/笼罩。鹰停下,变成一颗颗星星/大海轰响着滚动,把泡沫的鼻息/喷向海岸。”这里诗意的生成是通过赋予事物于人的感官感受,一个事物被当成另一个事物的形象来处理,鹰、光、大海、泡沫、海草、蝙蝠等多个物象在一个空间里转化出多重的意境,物象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带来的是时间内部的一次次脉动。特朗斯特罗姆诗歌还是一个善于把所思所见合二为一的诗人,比如他在《舒伯特》一诗中就写到:我们必须相信很多东西,才不至于度日时突然掉进深渊。这样的诗歌闪耀着诗人的哲思,叫我们在庸常的生活中不至于迷失。
“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套用本雅明的话,诗歌的存在之地总是有着它别样的异象,而从孤独出发的诗歌是对自己遥远生命的回应,就在回响之间,诗意诞生了。我们来看特朗斯特罗姆的《足迹》:“夜里两点:月光。火车停在/平原上。远处,城市之光/冷冷地在地平线上闪烁//如同深入梦境/返回房间时/无法记得曾经到过的地方/如同病危之际/往事化作几点光闪,视线内/一小片冰冷的旋涡//火车完全静止/两点钟:明亮的月光,二三颗星星”,这首境遇孤独的诗歌,它亲近又疏离,在起伏之间适时让人进入沉静的梦境。阅读是一个奇妙的旅程,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光线下,阅读作用到心灵上的也是有瞬息万变的体会。在我远没有踏进瑞典那片北欧的土地前,阅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风暴》:“突然,漫游者在此遇上年迈/高大的橡树――像一头石化的/长着巨角的麋鹿,面对九月大海/那墨绿的城堡//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在厩中跺脚”,它带给我的是异乡人在九月沿着大海边的城堡漫游的陌生意境,但到了瑞典后,诗歌中的物象变得具体起来,比如楸树,它的果实就是叶子,火红的热情燃烧在蓝天之下,一瞬间让人迷失在难言的感动之中,仿佛命运经历风暴之后的平静和黑暗中听到的星星耳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特朗斯特罗姆,他就这样在写作中注入了全部的生命和人格,我更喜欢他在《果戈理》中写到的:此刻,落日像狐狸悄然穿越这土地/霎那间点燃荒草/天空充满了蹄角,天空下/马车如阴影/穿过我父亲电灯的庄园/……/看,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登上你的烈火马车吧,离开这世界。这样激情、力量、思想和感情所共生出来的诗篇,像他《黑色的山》:“独裁者的头像被裹在/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一样,也是异常出色的,弥漫着批判的勇气和英雄的气息。
3.诗歌是这个秋天芬芳的果实
想想,这样一位写出美妙诗篇的诗人,在他获奖之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和诗歌,如果不是因为他获奖,他也只是中国诗歌界少数人喜欢的诗人。但在别的国家就不同了,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欧洲更是为人们所喜欢。欧洲至今还保持着阅读的传统,你在咖啡店、地铁站、酒店、公园等场所都会看到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阅读,他们国家的书店也到处都是,但在我们中国情况是相反的。瑞典电台每天中午都会坚持播送一首包括特朗斯特罗姆等诗人在内的诗歌,还付丰厚的稿酬,但我们的电台、电视台会做吗?古代的中国是一个诗教国度,但现在我们的新文化传统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被物质的浪潮冲上现实之岸,这是非常可怕的。据调查,中国人一年阅读的平均时间排在全球的后面,即便我们有阅读,也是消遣的、轻松的阅读,跟心灵和思想没有多大的关系。诗歌这种跳跃的、隐藏的、感性的文体对更多人来说是畏途。我们国家的诗歌教育和审美也几乎等于零,诗人这个身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诗歌在这个曾经的帝国走向式微也是正常的。但诗歌的边缘化对于诗歌自身的发展却是好事,因为边缘反而让诗人远离功利的东西,安静回到内心,去观照命运和人生,去敬畏文字,写出优秀的诗歌。这一点连外国汉学家都认同,他们觉得当下的中国,诗歌的成就最高。从事诗歌始终是一个尴尬的事业,这些年引起关注的都是非诗因素发生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诗人,它是世界对诗歌的再次拥抱,但在中国,估计热闹一阵子又回到波澜不惊的日子去,回到庸常的生活去。诗歌那朵寂寞的花瓣只是独自开着。但从全球范围来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是诗歌艺术的胜利,诗歌又一次回归大众的视野、回到它应有的尊贵位置上来。尽管在辛波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15年,诺贝尔文学奖才回头看望一眼诗歌,但诗歌一直在人心里。在这个十月,阳光灿烂的日子,诗歌成为甜美的果实,它的芬芳终为人们所喜悦。
有人说,由于他的获奖而引发的热潮将迎来一阵模仿之风。优秀的东西都值得去模仿,人类的智慧就在模仿之中获得另一个新的开启。但真正的模仿者在模仿前,他/她已离开。其实,远在特朗斯特罗姆获奖之前已经有人模仿他的写作,就连1987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也说过:“我偷过他的意象。”杰出的大师都有个人自我的东西,也就是私人性的气息,别人怎么模仿也是模仿不来的。布罗茨基偷了特朗斯特罗姆的意象,但他写出的作品却异于特朗斯特罗姆,记得瑞典学院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一种以思想敏锐和诗意强烈为特色的包罗万象的写作。而给特朗斯特罗姆的颁奖理由是:通过凝炼、通透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经。优秀的写作者在别人那里看到的应是梦的影子,它激发你的感官世界,从而诞生另一个不同面容的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自诞生以来,约有十七位诗人获奖,在过去的岁月里,每一次获奖的诗人都会被引起新一轮模仿其写作风格的热潮,但不会诞生第二个写作风格雷同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诗歌注定是唯一的。
4.我们一起经历世界
特朗斯特罗姆说: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诗歌离不开记忆,因为传统是当代的一部分,是现在和过去共有的呼吸,诗人在做唤醒的工作,在做挖掘的工作,在做连接的梦想,为生活在当下。这一切就像他说的: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特朗斯特罗姆在《一个贝宁男人》一诗的最后写到:我来这里是为了/和一个举着灯/在我身上看到自己的人相遇。诗歌在他那里是相遇,自我于他人、自我与世界,还有自我与自我的相遇,诗人在这样的空间里揭示了世界的神秘。我喜欢这样一点一滴地进入特朗斯特罗姆的世界,就像一个意象奔向另一个意象。我感到自己也是一个守着一盏心灵灯火的人,我在某个地方遇见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把“诗歌与人·诗人奖”颁给这样的大师,是对自己坚持寻找精神明灯的追寻。2010年年底,我通过诗人、翻译家李笠先生告知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我有意向把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授予于他,以表达个人对他精湛诗艺的敬仰。没想到的是,特朗斯特罗姆先生非常高兴接受了我的美意,并第一时间把答谢辞写好传来,令我感动之余看到一个大诗人谦虚的美德。
“诗歌与人·诗人奖”是我2005年设立的一个诗歌奖项,表彰那些在漫长岁月中坚持写作,并越写越好,源源不断推出光辉诗篇的诗人,通过对诗人的推介让更多的人沐浴诗歌精神的光辉,为人类的智慧和心灵的丰盈做出努力。关心《诗歌与人》的朋友知道,《诗歌与人》创办于1999年底,创刊号推出70后诗歌,此后连续推出中间代、完整性写作、女性诗歌等专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2005年,我觉得作为一个民间刊物,它已完成一半,此时的刊物需要注入一些新的元素进来。利用刊物的影响力设立一个国际诗歌奖成为在我内心涌动最多的一个念头。2005年,在诗人姚风的帮助下,我把第一届的诗歌奖颁给了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先生。安德拉德是一位用诗歌去爱的诗人,他的歌唱和行走都是为了在大地扎根,他的诗歌是梦想和自然生命的链接,他的诗歌丰盈了人类的心灵记忆,让大地上可以居住的心勇往直前,正是他润泽人类精神的诗歌,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非儿的魅力;第二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我给了七月派最后一位诗人、87岁月的彭燕郊先生,彭燕郊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诗人,也是一位把美视为宗教的诗人,他的诗歌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旅程.写出了生命的真诚、自信与坚持,苦的折磨和爱的萌生让他的一生更为富有;第三届,我把奖给了张曙光先生。张曙光是一位有浓重叙事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歌结构精巧、平稳,语言倾向于沉重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的诗歌中会找到那个时代的苦难、荒谬和毁灭;第四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获得者是蓝蓝。蓝蓝是一位对事物保持温度和敏感力的诗人,她的诗歌从她的内心出发,抵达属于自己的天空和大地,她的诗歌呈现出宽阔的视野、奇异的想象、朴素的美感和丰盈的生命力;第五届的奖项则由俄罗斯诗人丽斯年斯卡娅获得,她是一个向内的诗人,她的诗歌是她生命的关照和心灵的拯救她在写作中倾注了独立的人格。她的诗歌直接能在瞬间产生多重的穿透力,很多时候又是一种亲切的倾诉和回旋流荡,她的诗歌一直坚持着她的苦难意识和对抗精神。她在不可避免的困境中迎向正义之光,这使得她在一生的写作中达到了自由的高度。
2011年的4月23日,在广州,我把“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授给特朗斯特罗姆先生,因先生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未能亲临领奖,有些遗憾,但通过李笠从瑞典带来的一部纪录片,我们看到诗人的风采如今,特朗斯特罗姆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家奖,他之前所获得的我的“诗歌与人·诗人奖”也得到提升和认同。不过,这更多的是一种巧合,如果有什么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经历了世界,我们与世界有着相同的价值审美眼光。大家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当初没奖时有一条规定,就是获奖者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这一点,我的奖与诺奖有了瞬间的交汇。没有理想主义激情,我也不会走到今天。多年来,有媒体说我是当代的浮士德,我更觉得自己是堂吉诃德,一个在风中行走的人。
5.特朗斯特罗姆是中国人的亲戚
很庆幸,2011年8月有机会随李笠等人去北欧参加几场诗会。这次瑞典之行,对于我而言重头戏是拜会特朗斯特罗姆,完成内心的隐藏的愿望。特朗斯特罗姆的中文译者李笠对此早有安排。李笠在瑞典生活二十多年,特朗斯特罗姆夫妇与他已经是老朋友了,确切说他们把李笠当成了儿子。2009年,蓝蓝、王家新、沈奇等中国诗人曾经去拜访过特朗斯特罗姆,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国作家万之等人跟他也有很深的交情。其实早在1985年,特朗斯特罗姆到访中国时,北岛作为中文的译者已与他相识,并陪同他游长城对此,北岛在他的《蓝房子》一文中有深切的回忆。特朗斯特罗姆后来一次到中国是1990年,由李笠陪同。特朗斯特罗姆对中国的食物很着迷,他慢慢的品尝如同写诗。特朗斯特罗姆的中国情结怪不得被朋友戏称他是中国人的亲戚。
30日,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瑞典的阳光柔软的照着,不远处的梅拉伦湖闪烁着蓝光、去看望一个心仪的人,应该选择一个楸树开始燃烧的日子,要带着花束的暖意。特朗斯特罗姆的家在斯德哥尔摩南岛斯第格伯耶街的小山坡上。一栋普通的居民楼,一架窄小的旧式铁栅电梯,由于坐不下那么多人,我们选择爬楼梯。就要看到自己喜欢的诗人,内心多少有些激动。特朗斯特罗姆的夫人莫妮卡女士在门口迎接我们。特朗斯特罗姆1990年中风后身体不是很灵便,他坐在沙发上静候我们,见到我们进来,他脸露笑容,眼睛放出光彩:那是诗人灰蓝色的眼睛,纯净、好奇。当我跟他对视时,我有走进他的内心的感觉,突然想起他写过的诗句:有那么一瞬间我被照亮。我心想,嘿,没错,他就是那个写出“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的亲切老头。
我们每一个人跟他亲切拥抱。我们参观了他的家:房子不是很大,大概一百平方米,书柜、钢琴占了一些空间,红色墙壁上挂着诗人女儿的摄影作品。他家里还挂有中国书法,摆设着一些小的雕塑,在细细品味间,一座艺术的花园在眼前盛开。我把从国内带来的有关他获得“诗歌与人·诗人奖”的报道一一展示给他,诗人看到自己的照片印在报上,不时用手指着照片,笑了。
诗人的妻子莫妮卡女士,她的优雅、热情一下让我们感受到八月北欧阳光般的亲切。在我到来之前,我早已通过照片见过莫妮卡女士。就在七月,李笠把我颁给特朗斯特罗姆的奖杯送到了瑞典时,李笠在他们家的花园拍下一张照片,是特朗斯特罗姆和莫妮卡端详奖杯的瞬间,他们之间的默契、专注、喜悦让我感动。这次见到莫妮卡,知道特朗斯特罗姆所有的生活起居饮食和护理都由莫妮卡负责,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样的一位女性用生命中所有的热情爱着自己丈夫,她无疑是伟大的。早在七十年代,特朗斯特罗姆在给美国诗人布莱写得一封信中说,他和莫妮卡每到月底就抖一抖他们衣柜里的衣服,看兜里有没有一些硬币。正是这样一位耐得住清贫的女性陪着托马斯走过漫长的诗歌时光,对于已经八十岁并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特朗斯特罗姆来说,唯有莫妮卡能懂得他的语言,当我看到特朗斯特罗姆看莫妮卡流露出的依恋,就知道他们之间爱才是特朗斯特罗姆最好的诗篇。特朗斯特罗姆右半身的中风是不幸的,但他拥有这样一位坚韧、乐观、大气的女性却是幸福的。当我拿起摆在他们家重要位置的奖杯补拍照片时,莫妮卡多次跟我说,特朗斯特罗姆很喜欢这奖,他珍惜这份来自中国的荣誉。
看得出,莫妮卡早已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三文鱼、熏鸡肉、牛油果沙拉、虾等,还有咖啡和甜品,女士们喝白葡萄酒,特朗斯特罗姆喝的是他喜欢的德国啤酒。席间,忘记是谁说起那天在哥特兰岛朗诵了特朗斯特罗姆的《车站》,大家马上意识到如此一个诗人相聚的时光怎能缺少涛歌呢?于是,我们自发朗诵起诗歌来,瑞典语、英语、中文在斯德哥尔摩的这个诗人家庭响起,飘向窗外蓝色的梅拉伦湖。我则用广东话朗诵了诗人的诗篇:三月的一天我到湖边聆听/冰像天空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在北欧的这个正午,诗歌是我们内心惟一的阳光,莫妮卡女士动情地说,已经很久没有人为特朗斯特罗姆举办过这样的诗歌朗诵会了!是啊,诗人尽管生活在寂寞的边缘,但他的作品从舌头中奔腾出来的是玫瑰之香,弥漫的是紫藤的味道,这声音里的时光起伏着天鹅绒一般的柔软。
好时光都是拿来纪念的,与特朗斯特罗姆夫妇待在一起的午后是一种温暖却流逝得很怏。怕影响老人休息,我们起身告辞。走到门口,突然感到,这一走,不知何时能再见到这位亲切的老人一那个时候。并没想过是来看一位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是来拜访自己设立的诗歌奖的获得者,来看望一位迟暮的诗歌英雄、一位仿佛被遗忘的世界老人一我再回头,看到诗人一个人坐在餐厅的凳子上的孤独侧影,内心有些难以走开。后来听随行的记者张凌凌说,她看见同去的诗人莱耳掉了眼泪。
6.“我不是空虚,我是空旷”
分别两个月后,有时会想起特朗斯特罗姆的家,一座他和他的夫人共有的孤独的花园,想起他在《维米尔》中写到的:“低语:我不是空虚,我是空旷”,内心多了一些宽慰,自己也变得明朗起来,为两个老人。幸运的是,在特朗斯特罗姆八十岁的日子里,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迎来了自己的时刻,然而他依然是那个蓝色眼睛的老人,他把时间折叠起来,直到光线追上他,现在追上他的是世界的眼光。尽管如此,诗人还走在通往意象和现实同在的新途径上,他活在诗歌的世界里:“我来了,那个无形的人,可能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以便生活在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