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 | 波德莱尔:想象,以戏剧化的名义展开
原创 钟晓武 三联生活周刊 2016-07-24
几天前,我和一个朋友在闷热的午夜的烧烤摊聊天。我们无意中聊到了另外一个朋友,三十多岁的年龄,延期两次后博士毕业,没有女友,生活无计,然而热切地关注着政治与家国命运,这种关切一度成为他所有生活展开的前提。“想象性问题的想象性解决”,对我这样的评价,朋友点了点头。然而,我接着说道,其实,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生活戏剧化的倾向,作为一种逃避或升华,寻求着自己的安慰与生存。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在24岁无聊而压抑的考研生活里,有次在午夜骑着自行车绕着学校周围的街道,一圈一圈无意义地绕行,忽然在思想深处,异常明澈地认识到鲁迅小说中吕纬甫对人生所做的苍蝇之喻:“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走了,但是只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这种戏剧化,在不少敏感而富有想象力的作者那里,甚至成为一种隐秘的内驱激情,在自觉的理论播撒之下,当这种意识被投诸到广阔世界的万千色相时,许多富有意味的细节与洞见便浮现上来,尽管这些讨论更多停留在美学意义上。波德莱尔的做派和整部《恶之花》,便给了我这种感受。

波德莱尔
当早年的沈从文将迫于生计的写作视为一种淫业,当张爱玲在小说中借主人公的口吻说出“婚姻不过是长期的卖淫”,当波德莱尔在散文《火箭》中写下:“爱情就是卖淫的欲望。甚至没有任何一种高尚的快乐不能还原成卖淫。在剧场里,在舞场里,人人都在一切众人之中找到快乐。艺术是什么?就是卖淫。置身于群众中的这种快乐,乃是在数的增加之中感到快乐的一种神秘的表现”,多数人都能看到其中所谓洞见与反抗的部分,但往往忽略了那种站在浪漫派对面的夸张而变形的情热。这一点,就像魏晋年间,嵇康对礼教的冷嘲与不屑。波德莱尔是真正的现代主义者,在浪漫主义孤独忧郁厌世的“世纪病”的余绪下,他以冷嘲与放浪形骸,成为首位“从大城市人群中寻求灵感”的诗人。

波德莱尔(Gustave Courbet 绘)
1855年4月7日,在写给《两世界评论》编者的信中,波德莱尔写下这样一段话:“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者,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一度,他拟将《自惩者》一诗,作为《恶之花》组诗的真正的结论。
“
自惩者
我要打你 没有憎怨,
没有恼怒,像屠夫一样!
像摩西击打磐石一样,
我要打得你眼皮里面
迸出很多苦恼的水,
灌溉我的撒哈拉沙土,
让我的鼓着希望的情欲
跳进你的咸苦的泪水,
像出海的船一样游泳,
在被我泪水灌溉的心里,
你那可爱的呜咽啜泣,
将像冲锋时擂鼓的声音!
我不是一个唱错的音符,
跟圣交响乐调子不合?
这不是由于摇我、咬我、
贪婪的冷嘲带来的好处?
冷嘲是我的尖叫的声音!
这种黑毒留进我血里!
我就是复仇女神自己
照看自己的不祥之镜。
我是伤口,同时是匕首!
我是巴掌,同时是面颊!
我是四肢,同时是刑车,
我是死囚,又是刽子手!
我是吸我心的吸血鬼,
——一个被处以永远的笑刑、
却连微笑都不能的人,
一个被弃的,重大的犯罪者!
(钱春绮 译)
”

Julio Pomar 绘
波德莱尔吸食鸦片,酗酒,纵欲,很快将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75000法郎遗产挥霍一空,成为巴黎街头的浪荡者,据一些研究者统计,在1842年至1858年的十多年间,他的住所换了十五次之多。另一方面,在法国2月革命期间,波德莱尔和人群走上街头,在巴黎街角挥舞步枪高喊“打倒奥皮克将军”(波德莱尔的继父)的口号,尽管在本雅明那里,“波德莱尔的政治洞察力在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这些职业密谋家,无论他同情宗教反动还是同情一八四八年革命,他的表述都是未经传达的,因而其基础都是脆弱的。”
某种程度上,波德莱尔的生活具有强烈的戏剧化色彩。本来,他出身于优裕的中产家庭,然而在忧郁的个性、动荡的时代、以及本质上对启蒙方案的反感等原因的促力下,他以放浪对抗堕落,进而在都市妓女、流浪者、拾垃圾者那里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
“
某夜,我躺在一个犹太丑女身旁,
就像一具尸体靠近另一具尸体。
在这卖身女的身旁,我不由想起
我求之不得的多愁的美貌女郎。
我想起了她那一种天生的威严,
她的眼光具备无限的活力和优美,
她的头发成为香气氤氲的头盔,
想起来就使我的爱情死灰复燃。
因为,我真会狂吻你高贵的肉体,
从你凉爽的脚吻到黑色的发丝,
打开你那深情厚爱的无限宝库,
如果在某个夜晚,哦,冷酷的女王,
只要你能自然而然地流出泪珠,
使你那冷冰冰的眸子暗淡无光。
(钱春绮 译)
”

“
拾垃圾者的酒
当那装有反射镜的路灯发出红光,
风吹得灯火摇摇、灯玻璃轧轧作响,
在老郊区的中心——污秽卑贱的迷宫,
那里动乱的因素使人类乱趱乱动,
常见到一个拾垃圾者,摇晃着脑袋,
碰撞着墙壁,像诗人似地踉跄走来,
他对于暗探们及其爪牙毫不在意,
把心中的宏伟蓝图吐露无遗。
他发出一些誓言,宣读崇高的法律,
要把坏人们打倒,要把受害者救出,
在那华盖一样高悬的苍穹之下,
他陶醉于自己的美德的辉煌伟大。
是的,这些尝够了他们家庭的烦恼、
厄于年龄的老大、困于工作的疲劳、
被巨都巴黎所吐出的杂乱的秽物——
大堆的垃圾压得弯腰曲背的人物,
他们回来了,发出一股酒桶的香气,
带领着那些垂着旧旗似的小胡子、
被生存斗争搞得头发花白的战友;
无数旗帜、鲜花、凯旋门,在他们前头
屹然耸立着,这是多么壮丽的魔术!
在那一大片军号、阳光、叫喊和铜鼓
吵得使人头痛的辉煌的狂欢之中,
他们给醉心于爱的人们带来光荣。
就这样,酒变成了耀目的帕克多河,
穿过浮薄的人生,泛着黄金的酒波;
它借人类的嗓子歌颂它酒的功德,
仿佛真正的王者来施恩统治世人。
为了给一切黯然等死的苦命老人,
安慰他们的暮气,消除他们的怨恨,
感到内疚的天主想出睡眠的法子,
人类又添上了酒,这位太阳的圣子!
(钱春绮 译)
”

Georges Seurat 绘
这些诗歌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而在于一种新美学的诞生——作为现代主义真正主体的英雄,不在历史与传奇之中,反而匿身于都市的角落之中。本雅明为波德莱尔在《酒魂》一诗中,在无产者身上认出古代斗剑奴隶的身影而欣喜:“为工资而工作的人们在每天劳动中获得的东西,不折不扣地正是那种使古代角斗士赢得喝彩和声誉的东西。这个意象是波德莱尔最精彩的洞见之一,它源出于波德莱尔对自身处境的思索。”
“
“我将使尊夫人高兴得眼目生辉,
使你的儿子荣光焕发,精神抖擞,
对这种跟生存竞争的脆弱之辈,
我将做增强战士的肌肉的香油。”
(钱春绮 译)
”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绘
更为内在的,波德莱尔发现了那种现代人独有的心理特质。19世纪的巴黎,已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大都市。与前现代的人相比,“人们每天遭际这么多人,彼此只照面而并不攀谈,彼此不了解对方,而又必须安然无恙地相处在一起。”本雅明将都市人流中接连不断出现而又消失的东西带给人的感受,称为“惊颤体验”,在他看来,《恶之花》中的《巴黎风光》就将“惊颤经验置于艺术创作的中心。”
“
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
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嚣
走过一位穿重孝、显出严峻的哀愁、
瘦长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
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群裳;
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
从她那像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
一样的眼中,我象狂妄者浑身颤动,
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 ——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钱春绮 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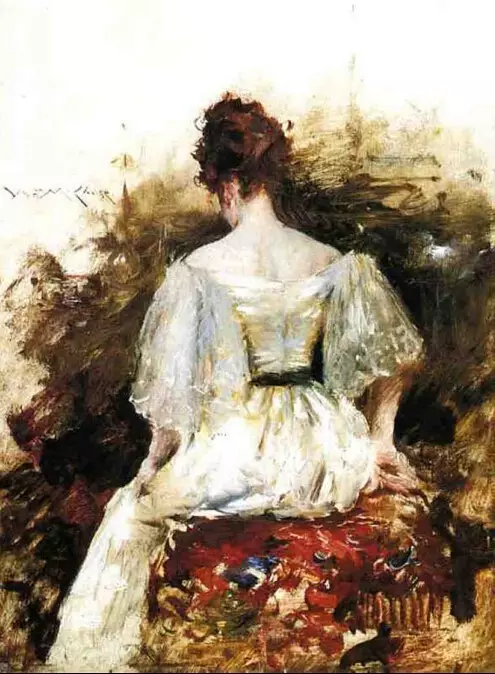
William Merritt Chase 绘
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本雅明多次提到这首诗,意在表现波德莱尔在都市大众中所感受到的迷人瞬间——那最后一瞥中产生的爱。而当今生活中那些稍纵即逝、变幻不定的美,也正是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定义。
事实上,波德莱尔对都市中的人群有着更为自觉的认识,收入《巴黎的忧郁》中的一篇散文诗《人群》中,他声称“享受人群是一种艺术”,而“众人,孤独:对一个活跃而多产的诗人来说,是个同义的、可以相互转换的词语。谁不会让他的孤独充满众人,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中孤独。”

波德莱尔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发现了波德莱尔与雨果的区别所在:“雨果将人群作为现代英雄史诗去赞赏,而波德莱尔为他的主人公在都市人群中找到了避难所;雨果把自己作为公民放在人群中,而波德莱尔却把自己作为一名英雄从人群中分离了出来。”某种程度上,波德莱尔的教诲,对处于大都市中繁忙辛劳的人群来说至关重要,谁没有学会在人群中感受孤独,谁注定无法适应现代都市的节奏,只能成为彻底的沦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