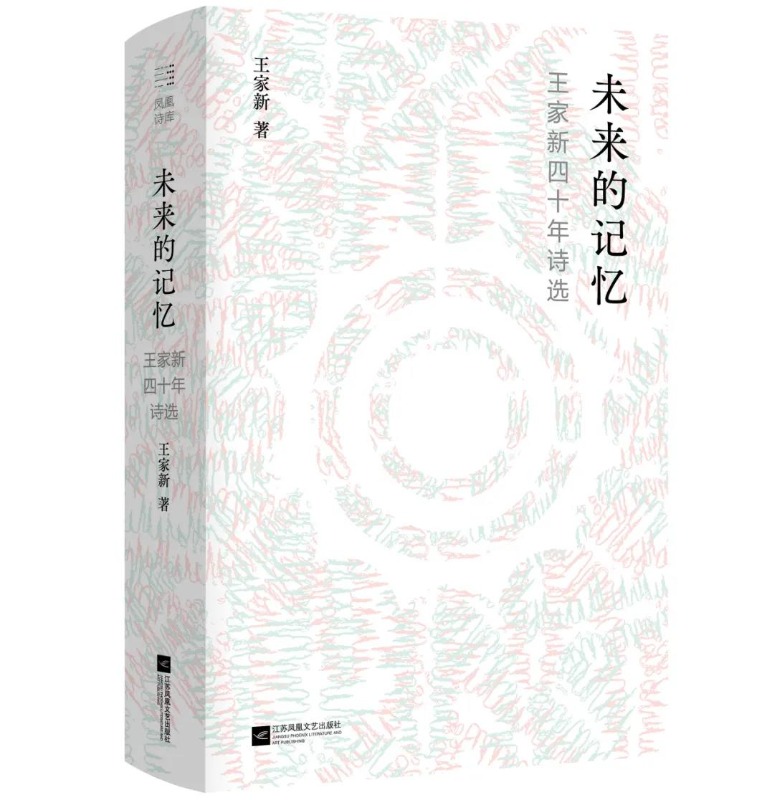 内容简介:作为“四十年诗歌成果”,《未来的记忆》精选了诗人王家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近年的二百多首(组)诗作,既代表了诗人不同阶段的艺术风貌,又充分体现了诗人近些年来创作的深化和进展,“其不舍叩问、超凡诗艺与独特的美学气质,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深具启示意义。”(第三届“李杜诗歌奖•成就奖”颁奖词,2018)《未来的记忆:王家新四十年诗选》 王家新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凤凰诗库” 2021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作为“四十年诗歌成果”,《未来的记忆》精选了诗人王家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近年的二百多首(组)诗作,既代表了诗人不同阶段的艺术风貌,又充分体现了诗人近些年来创作的深化和进展,“其不舍叩问、超凡诗艺与独特的美学气质,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深具启示意义。”(第三届“李杜诗歌奖•成就奖”颁奖词,2018)《未来的记忆:王家新四十年诗选》 王家新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凤凰诗库” 2021年6月出版
 王家新诗人,批评家、翻译家,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高中毕业后下放劳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先后出版诗集、诗歌批评、诗论随笔、译诗集三十多种,并编选出版有多部中外现当代诗选,为当代最有广泛、持久影响的重要诗人之一,其全部写作被视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启示录”(吴晓东语)。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出版,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诗歌节和文学交流活动,在国外一些大学讲学、做驻校诗人。曾获多种国内外诗歌奖、诗学批评奖和翻译奖。 图为王家新,2020年2月在瓦雷里故乡法国塞特
王家新诗人,批评家、翻译家,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高中毕业后下放劳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先后出版诗集、诗歌批评、诗论随笔、译诗集三十多种,并编选出版有多部中外现当代诗选,为当代最有广泛、持久影响的重要诗人之一,其全部写作被视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启示录”(吴晓东语)。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出版,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诗歌节和文学交流活动,在国外一些大学讲学、做驻校诗人。曾获多种国内外诗歌奖、诗学批评奖和翻译奖。 图为王家新,2020年2月在瓦雷里故乡法国塞特
《未来的记忆:王家新四十年诗选》诗选10首
风 景
旷野
散发着热气的石头
一棵树。马的鬃毛迎面拂起
骑者孤单地躺到树下
夕阳在远山仍无声地燃烧
一到夜里
满地的石头都将活动起来
比那树下的人
更具生命
1985
日 记
从一棵茂盛的橡树开始,
园丁推着他的锄草机,从一个圆
到另一个更大的来回;
整天我听着这声音,我嗅着
青草被刈去时的新鲜气味,
我呼吸着它,我进入
另一个想象中的花园,那里
青草正吞没着白色的大理石卧雕,
青草拂动,这死亡的爱抚,
胜于人类的手指。
醒来,锄草机和花园一起荒废,
万物服从于更冰冷的意志;
橡子炸裂之后,
园丁得到了休息;接着是雪,
从我的写作中开始的雪;
大雪永远不能充满一个花园,
却涌上了我的喉咙,
季节轮回到这白茫茫的死。
我爱这雪,这茫然中的颤栗;我忆起
青草呼出的最后一缕气息……
1992.10,比利时根特
田园诗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
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2004
晚 年
他已几乎度过了一生。
他从冬日的北京起飞,穿过黎明灰烬的颜色,
而在灰烬之上,透出珍珠色的光。
在血液的喧嚣中,
现在,他降临到一个滨海城市,
就在乘车进城的盘山路上,大海出现,
飞机下降时的耳鸣突然止息。
他看到更美妙的山峰在远处隆起。
他恍如进入到一面镜子中,
在那一瞬他听到
早年的音乐。
2005
塔可夫斯基的树
在哥特兰
我们寻找着一棵树
一棵在大师的最后一部电影中
出现的树
一棵枯死而又奇迹般
复活的树
我们去过无数的海滩
成片的松林在风中起伏
但不是那棵树
在这岛上
要找到一棵孤单的树真难啊
问当地人,当地人说
孤单的树在海边很难存活
一棵孤单的树,也许只存在于
那个倔犟的俄国人的想象里
一棵孤单的树
连它的影子也会背弃它
除非有一个孩子每天提着一桶
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
除非它生根于
泪水的播种期
2009—2012
冰钓者
在我家附近的水库里,一到冬天
就可以看到一些垂钓者,
一个个穿着旧军大衣蹲在那里,
远远看去,他们就像是雪地里散开的鸦群。
他们蹲在那里仿佛时间也停止了。
他们专钓那些为了呼吸,为了一缕光亮
而迟疑地游近冰窟窿口的鱼。
他们的狂喜,就是看到那些被钓起的活物
在坚冰上痛苦地摔动着尾巴,
直到从它们的鳃里渗出的血
染红一堆堆凿碎的冰……
这些,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恐怖的景象,
我转身离开了那条
我还以为是供我漫步的坝堤。
2003—2013
写给未来读者的几节诗
1
在这个雾霾的冬天所有我写下的诗,
都不如从记忆里传来的
一阵松林间踏雪的吱嘎声。
2
玛丽娜用鹅毛笔写作,
但有时她想,用一把斧子
也许可以更好地治疗头疼。
3
昨晚多多在饭桌上说:“写一首
就是少一首。”
我们听不懂死者的语言,
活人的,也听不懂。
2013.12.7
在韩国安东乡间
——给黄东奎先生①
谢谢你,先生,
谢谢你对我的诗伸出的
那根有力的大姆指。
你比我年长20岁,可是你的眼光
仍是那么敏锐。
你的额头在六月的光中闪亮,
我相信那即是智慧。
我们并排在山间走着,
我可以听到,我们经历的时间
就在我们彼此的身体中晃荡。
我们这是在韩国东部的乡间吗,
那只满山青翠中的鹧鸪,
怎么听也都是我在童年时听到的那一只。
我们登上屏山书院古老的台阶,
正值野栗树开花时节,
这石头有多光亮我的心就有多光亮,
这庭院有多荒凉我的心就有多荒凉;
当年的诵读声已化入河畔的细沙,
我们路过的疤结累累的松树
仍在流着脂泪。
你说你在翻译杜甫,
你问我“吴楚东南坼”②是什么意思,
我说那是两个国家的骨肉分离,
但它也在我们的身体中
留下了一种永久的疼。
但是现在山风拂面,在枣花的清香中,
我不忍去谈我们的那些经历,
不谈雾霾,不谈毒龙,也不谈
我为何写下那首“瓦雷金诺叙事曲”……
我们并排走着,伴着清泉潺潺,
好像受苦人也终会有所安慰;
(路边的桑椹落了一地)
你说明天你还会和我们一起去看海,
我说下次我陪你去岳阳楼吧,
我也从未去过那里。我不知道
它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风景,
但是到了那里,我想我们都会流泪的——
当我们开始一步步登临,
当一种伟大的荒凉展现在我们面前。
2014.6
注①:黄东奎(1938——),韩国著名诗人。
注②:出自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忆陈超
那是哪一年?在暮春,或是初秋?
我只知道是在成都。
我们下了飞机,在宾馆入住后,一起出来找吃的。
天府之国,满街都是麻辣烫、担担面、
鸳鸯火锅、醪糟小汤圆……
一片诱人的热气和喧闹声。
但是你的声音有点沙哑。
你告诉我你只想吃一碗山西刀削面。
你的声音沙哑,仿佛你已很累,
仿佛从那声音里我可以听出从你家乡太原一带刮来的风沙……
我们走过一条街巷,又拐入另一条。
我们走进最后一家小店,问问,又出来。
我的嘴上已有些干燥。
娘啊娘啊你从小喂的那种好吃的刀削面。
娘啊娘啊孩儿的小嘴仍等待着。
薄暮中,冷风吹进我们的衣衫。
我们默默地找,执着地找,失落地找,
带着胃里的一阵抽搐,
带着记忆中那一声最香甜的噗啾声……
我们就这样走过一条条街巷,
只是我的记忆如今已不再能帮我。
我记不清那一晚我们到底吃的什么,或吃了没有。
我只是看到你和我仍在那里走着——
有时并排,有时一前一后,
仿佛两个饿鬼
在摸黑找回乡的路。
2014.11.5
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录
圣女,
十二月党人忠贞的妻子,
无情的审判者,
永恒的未亡人!
在去香港的来回飞机上我读的
都是这本书!它的份量,
让我们降低高度,
紧贴着历史的浪花飞……
“我们一定要活到那一天,那哭泣和光荣的一天。”①
“娜佳②,我的娜佳,你在哪里啊。”
我的眼睛一片酸楚。
我又回到了那片恒古的冻土。
每刨一下,虎口震裂。
每刨一下,都绝望得想哭。
——你要刨出火星吗?
你能挖出那声音的种子吗?!
我一辈子都是这样一个苦役犯。
我也只能从我的歌哭中找到
我的拯救。
2016.6
注①:摘自阿赫玛托娃给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书信。
注②:曼德尔施塔姆对妻子娜杰日达的爱称。
这条街
我将不向大地归还
我借来的尘土……
——曼德尔施塔姆
1
在多年的动荡生活之后,
我也有了一条街,一条夹在居民区的小街,
一条我们已居住了五年的绿荫小街,
一条仍在等待我童年的燕子
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蝴蝶的小街。
2
这条街,每天我都下楼走一走,在金色的黄昏,
或是伴着夏日蝉鸣的绿色正午,
即使在写作的时候我也往往忍不住
望一眼窗外的这条街,好像它就是
两行诗之间不能缺少的空白。
3
现在,一个穿短裙的少女走过,而我希望
她轻快的移动就是静止,
就像永远走在希腊古瓮上的画里,
至少走慢一点,我要替杜甫他老人家多看她一眼,
我还想替老叶芝向她伸出手来。
4
就是沿着这条街,我买来每天的面包、青菜,
(有时则专门去给我们家的兔子买吃的)
哦,街头那家“杭州小笼包”揭锅时的热气!
还有那家幼儿园,我喜欢孩子们的尖叫如同我喜欢
放学后的安静:那永恒的寂静的童年。
5
难忘的春天(那是哪一年?),似乎一歩出小区,
街边铁栅栏內的桃花就绽开了,
梦幻般的,虽然只开了三天,
从此我这个苦役犯的眼前就飘着几朵彩云,
就飘着,哪怕是在雾霾天。
6
蹲着的修车匠,飞窜的快递员,站着发小广告的……
我向这一切致敬,不仅如此,
每年这条街上还走过敲锣打鼓送葬的行列,
每到那时,我就拉着儿子来到窗边,
好像是让他观看月球的另一面。
7
傍晚,街头烤红薯的糊香味。
(“巴黎的大街上没有烤栗子吃了”,艾吕雅)
正午,电线杆拉长的阴影。
初夏时分,老槐树洒下的謦香细碎花蕊,
一场场秋雨后,银杏树那金币般的叶子!
8
有时我一连数日埋头写作,不曾下楼,
但那条街仍在那里,拉开窗帘,啊,下雪了——
那一瞬,好像就是上苍对我们的拯救!
那一瞬,连我们家的小兔子,也和我一起
久久地伫立在窗前。
9
就是这条街,虽然它并非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只是为了孩子上学在这里租住,
但我爱这条街,爱这四楼上的窗户(它不高也不低),
爱街上的一年四季,爱它的光与影,
我的灵魂已带上了它们的颜色。
10
还有这街上的微风!每次梦游般出去时,
它就会徐徐拂来问候我的眉头。
它一次次使我与生活和解。而在闷热天,
它则好像把我带向了青岛或大连——
一拐过这条街口,就是大海与帆!
11
是的,我爱这条街,它使我安顿下来,
使我靠“借来的尘土”再活一次。
过生日的那晚,我想在这条街上一直走下去,
但它还不到五百米,我就来回走了三趟:
伴着天上的那颗让我流泪的小星。
12
而我爱这条街,还因为可看到远山(幸好它没有
被高楼完全挡住)——那是北京西山;
我爱它在黄昏燃尽后的黑色剪影,
爱街的尽头第一辆亮起的雪亮车灯,
它好像就从灵魂的边界向我驶来。
13
就是这条无名小街(你读了这首诗也找不到它),
就是面对它,我翻译了曼德尔施塔姆,
他居无定所,死于流放,却希望在他死后
那只“白色粉蝶”能在它的跨距间活着——
飞回到那个国度,飞回到那条街。
14
而“那条街”也就是“这条街”,正如
“这条街”也将变成“那条街”——
明年我们的孩子小学毕业,我们也将搬走,
但多少年后我会重访这里,我们的孩子也会——
我童年的燕子也许会跟着他一起到来。
2016.8.31-9.4,北京世纪城
黎明五点钟
黎明五点钟,失眠人重又坐到桌前。
堆满的烟灰缸。与幽灵的彻夜交谈。楼道里
永别的脚步声。如果我有了视力,
是因为我从一个悲痛之海里渐渐浮出。
第一班电车在一个世纪前就开过了,
鸟巢里仍充满尚未孵化的幽暗。
在黎明五点钟,只有劳改犯出门看到
天际透出的一抹苍白的蓝;
也有人挣扎了一夜(比如我的母亲),并最终
停止呼吸,在黎明五点钟,在这——
如同心电图一样抖颤的分界线。
2018.1.7
记一次风雪行
驱车六十公里——
穿过飘着稀疏雪花的城区,
上京承高速,在因结冰而封路的路障前调头,
拐进乡村土路,再攀上半山腰,
就为了看你一眼,北方披雪的山岭!
多少年未见这纷纷扬扬的大雪了,
我们本应欢呼,却一个个
静默下来,在急速的飞雪
和逼人的寒气中,但见岩石惨白,山色变暗,
一座座雪岭像变容的巨灵,带着
满山昏溟和山头隐约的峰火台,
隐入更苍茫的大气中……
在那一瞬,我看见同行的多多——
一位年近七旬、满脸雪片的诗人,
竟像一个孩子流出泪来……
2019.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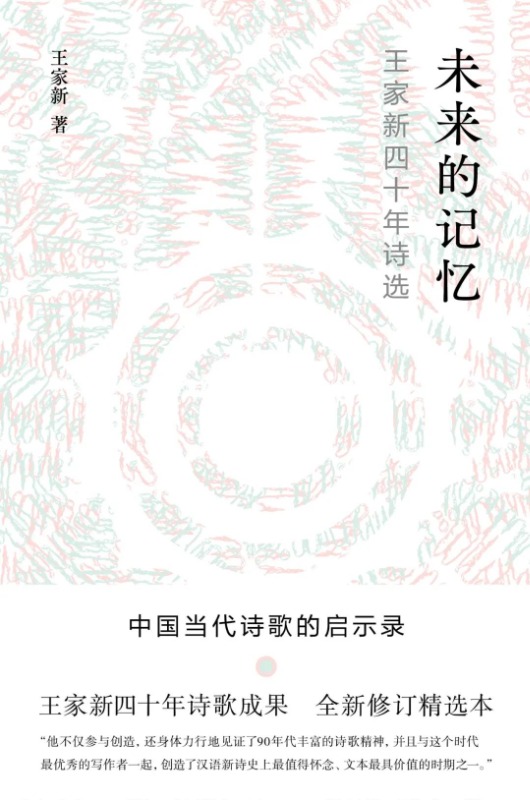 国内外部分对王家新诗歌的评论摘要
国内外部分对王家新诗歌的评论摘要
王家新在中国诗坛上的无法替代的位置正与他的执著和内在的深度相关。阅读他的诗,仅仅从技巧上把握是远远不够的。王家新的诗堪称是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它象征了诗歌领域的一种内在精神的觉醒。
——吴晓东
阅读王家新的诗,你会再一次意识到诗歌并非文学运动或历史事件的产物,而是一种独立个人的声音,在他这里则表现为一种高度警觉与内省的特质。王家新是保罗•策兰的中文译者,读他的诗能感受到类似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欧洲诗歌特有的那种向内回溯的力量……王家新的诗里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他有一种写箴言的天赋,比如《反向》、《另一种风景》和《冬天的诗》这些诗片段,它们令人惊奇,很新鲜,带有明显的他个人的专属性。……阅读《变暗的镜子》和王家新同时代其他诗人近年被翻译过来的作品,我感到重新睁开了眼睛。
——(美国)罗伯特•哈斯
“尴尬”对于创作者是一个很典型的词。在一个不断流失的世界里,诗人们已不能胜任使命。王家新属于少数一批坚持下来的诗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让步退缩。他的诗能够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歌创作。从他的诗中,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可以看到诗人从困境中带来了多少生命。
——(德国)顾彬
王家新是相对于一个时代的诗人。“需要怎样抑制自己,我们才能平静地走向阳台,并在那里观看历史?”(《反向•那一年》),诗人在扪心自问,但是,这何尝不是在询问我们这些目击过历史而肉体尚且“活着”的人。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自己在读到他在那时写下的《反向》时的复杂心情。但我预感到,一个真正从心灵上趋向伟大诗人气质的人,将会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
——程光炜
王家新诗歌的独特音质出现在九十年代初,那又是一个寻求或重构诗歌话语的时刻。是一代人创伤经验的核心。在此意义上,王家新是另一个北岛。这是我写下王家新的理由。
——耿占春
我和王家新从未谋过面,但对他的诗,特别是一些短诗,印象很深。他诗写得干净纯粹,意境幽远,一读就知道是多年努力所达到的境界。他的译诗也十分精细。我想他一直通过翻译来做两件事:一是力图跟自己心爱的伟大诗人保持相近的精神纬度,二是探测汉语的容度的深度。跟一些吃二三十年前老本的诗人不同,他越写越好,也会更好。
——(美国)哈金
王家新的诗细读了,质感强,饱满,有推进力,不是“新衣”诗所能比。
——张炜
王家新是一位行走于时代锋刃上的诗人。他的诗歌呈现出的是一个忠诚于经验与灵魂、随时向命运敞开的诗人。王家新的诗,尤其是近期的诗中,在语言上看上去不迷恋于词语的冒险,也不依赖于智力的编织,却能够使每一个造物在语言惠及之时得到令人惊异的揭示。他的写作为汉语诗歌找到了一种缺席已久的精神高度,并触及了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伤痛和隐疾。他用冰雪的声音款待我们,使我们得以澄清自己的内在。他给这个时代带来了份量。
——胡桑
王家新的诗里有一种“持志如心痛”的痛,有时这痛呜咽得如鲠在喉,有时爆发为“喉头爆破音”。他以全副怀抱,创造了自己热情、耿介、沉郁的诗人形象。在汉语新诗里,多少语言的泡沫破灭了,王家新却以其“诚”而立。
——朵渔
九十年代是王家新诗歌的辉煌期,他那个时期的书写极具艺术张力和饱满的精神……新世纪以来,王家新诗中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并呈现出发散的倾向,但他仍坚持直面现实的立场,“蘸取当下的幽暗写作”,以一种毫不浮夸的坚实而敏锐的语调贴近事物,大体上从“承担的诗学”转向了“辨认的诗学”。他以出自本色的但又往往是令人惊异的笔触表达丰富多变的生活……他的诗就像冰雪覆盖的树,内里黑暗但形体明亮,它仍在生长,并且愈是在冬日愈是焕发出勃勃生机。
——程一身
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王家新先生是一位由时间选出的代表。在他三十多年的诗歌生涯中走过的道路,犹如一串雪地上的足迹,显示了精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和艰难。他的诗以无畏的勇气分担了时代和事物的沉重,凭借心灵的力量把它们转化成了精神的收获,由此加重了现代汉语及其每一词语的分量。王家新先生富于洞察的诗歌想象力拒绝表面的华丽多姿,而一心专注于严肃、深邃、辽阔的境界,抵达了当代诗歌所抵达的最少人迹的远方。长久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广泛受惠于他的创作、批评和翻译。他的批评和翻译贯穿了与其诗歌同一的精神,它们一起以一种合一的力量有力地塑造了当代诗歌的面貌。
——深圳“第一朗读者•诗歌成就奖”颁奖词(2015,西渡执笔)
王家新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翻译家。多年来,他的诗已成为新诗史上的丰碑。他是创作生命力持续旺盛的诗人,其诗风度卓然,指涉深广,在先锋意识和个人襟抱的相互关照、锻造下诗外求道,追索时代的精神高标,常于胸次郁勃间脱身而出以就绝响,为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影像的别裁与重构提供了经典样本。其不舍叩问、超凡诗艺与独特的美学气质,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深具启示意义。
——第三届“李杜诗歌奖•成就奖”颁奖词(2018,胡弦执笔)
20210817 22:45:04
一本当代诗坛的重要诗选!
0 回复 查看 0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