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经验
诗歌 9/19
我想,我得着手干些什么了。现在我要学习去“看”。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却还一事无成。再说一遍我以前做的事吧:写过一篇关于卡尔帕奇的蹩脚论文,一部试图以含混的手法证明一些错误的剧本《婚姻》,此外还有几首诗。唉,要是过早地开始写诗,那就写不出什么名堂。应该耐心等待,终其一生尽可能长久地搜集意蕴和精华,最后或许还能写成十行好诗。
因为诗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感情(说到感情,以前够多了),而是经验。为了写一行诗,必须观察许多城市,观察各种人和物,必须认识各种动物,必须感受鸟雀如何飞翔,必须知晓小花在晨曦中开放的神采。必须能够回想异土他乡的路途,回想那些不期而遇和早已料到的告别;回想朦胧的童年时光,回想双亲,当时双亲给你带来欢乐而你又不能理解这种欢乐(因为这是对另一个人而言的欢乐),你就只好惹他们生气;回想童年的疾病,这些疾病发作时非常奇怪,有那么多深刻和艰难的变化;回想在安静和压抑的斗室中度过的日子,回想在海和在许许多多的海边度过的清晨,回想在旅途中度过的夜晚和点点繁星比翼高翔而去的夜晚。即使想到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回忆许多爱之夜,这些爱之夜各各不一,必须回忆临盆孕妇的嚎叫,脸色苍白的产妇轻松的酣睡。此外还得和行将就木的人作伴,在窗子洞开的房间里坐在死者身边细听一阵又一阵的嘈杂声。然而,这样回忆还是不够,如果回忆的东西数不胜数,那就还必须能够忘却,必须具备极大的耐心等待这些回忆再度来临。只有当回忆化为我们身上的鲜血、视线和神态,没有名称,和我们自身融为一体,难以区分,只有这时,即在一个不可多得的时刻,诗的第一个词才在回忆中站立起来,从回忆中迸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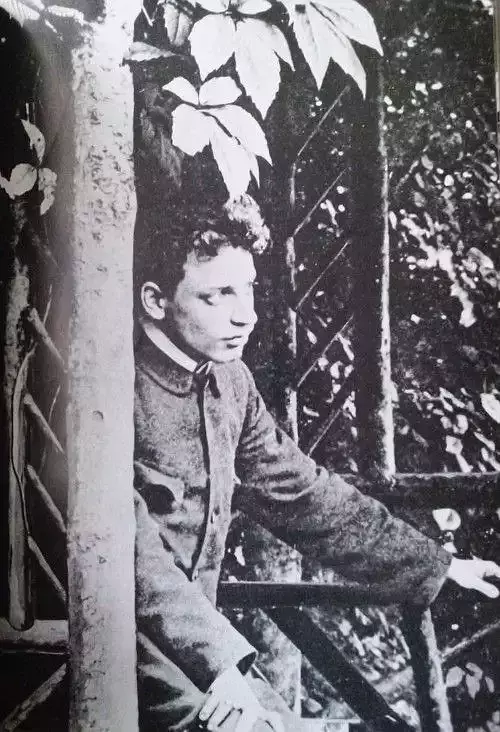
迄今为止,我写的诗却不是以这种方式问世的,所以多称不上是诗。——当年我编剧本时真是在无目的地瞎跑。我难道不是一个拾人牙慧的傻瓜,否则我怎么会需要一个第三者才能描述两个相互为难的人的命运呢?我那么容易地跌进了陷阱。我本该明白,这贯穿所有生活和文学的第三者,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第三者的幽灵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应该否定它。第三者属于自然的托词,这自然人一直在竭力使世人的注意力离开其最深处的奥秘。第三者是一架屏风,挡住了背后上演的戏剧。第三者是通向真正冲突的无声境界的入口处肆虐的喧闹。不妨认为,要谈论卷入冲突的双方,迄今为止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于上青天,而第三者正因为不真实才成了容易的任务,无论是谁都能完成。他们的戏剧刚刚开头,你就能察觉一种急躁,他们急于去找第三者,不能耐心地等待他的到来,好像一见到第三者,什么都好办了。然而要是第三者姗姗来迟,那该多么乏味无聊啊,没有第三者似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切都伫立着,停顿着,等候着。是啊,倘若一直这样淤滞壅塞、踌躇彷徨下去,该怎么办呢?剧作家先生,还有你们这些谙熟人生的观众,倘若第三者这深得人心的花花公子,这像万能钥匙一样介入所有婚姻生活的狂妄小儿失踪了,该怎么办?倘若他,举例来说,被魔鬼抓走了,该怎么办?倘若真的这样,那么你就会发现,剧院里不自然地空空如也。人们像堵危险的墙洞一样堵住这个空穴,只有包厢围栏里扑出的飞蛾在这无依无靠的凹膛里翩翩起舞。剧作家们再也不能住在别墅里悠哉游哉了。社会上探子倾巢而出,跑遍天涯海角为剧作家们寻找这无法替代的、本身就是情节的第三者。
然而,剧作家们是生活在人群中的,这里的人群不是指那些“第三者”,而是指构成戏剧冲突的双方。关于这双方可说的内容无与伦比地丰富,但是直到今天却什么也未曾说出来,尽管这双方忍受着,活动着,不知道如何帮助自己。
真是可笑,现在我静坐斗室之中。我,布里格,已经二十八岁了,却没有人知道我。我坐在这儿,什么也不是。然而,什么也不是的我开始思索了,在这五层楼的小室里,在巴黎一个灰蒙蒙的下午,思索着以下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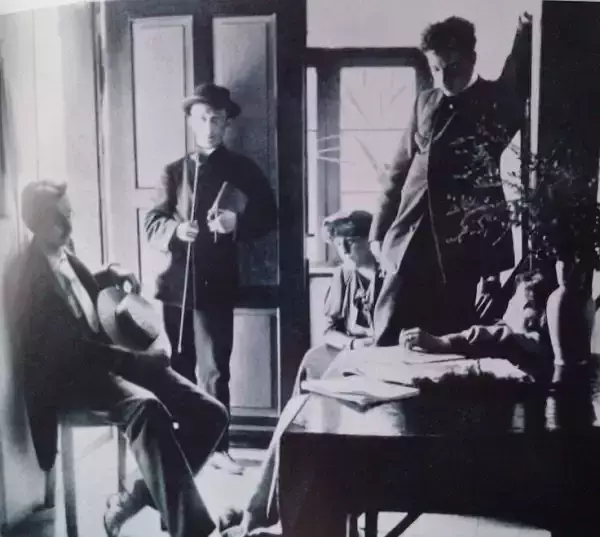
从未看见、认识和说出过任何真实和重要的东西,这可能吗?有难以计数的时间可以用来观察、思考和论述,却让这无数光阴像啃白脱面包和苹果的课间休息一样白白流逝过去,这可能吗?
对,这是可能的。
尽管有发明和进步,尽管有文化、宗教和人世智慧,却仍旧飘浮在生活的表面,这可能吗?甚至将这无论如何总还算得上什么的表面又罩上一层乏味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盖布,以致这表面看上去酷似暑期中沙龙里的家具,这可能吗?
对,这是可能的。
全部世界历史都被误解了,这可能吗?遗忘的历史都是虚假的,因为人们总是谈论大众,谈论汇聚在一起的众人,而不去注意个人(众人围拢在个人身旁,因为他是陌生的濒死者),这可能吗?
对,这是可能的。
坚信必须追补在自己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可能吗?必须回忆每一个生活在过去年代的先人,而且确实知道他们的情况,不使自己被持其他见解的人说服,这可能吗?
对,这是可能的。
所有这些人都对一种从未存在过的“以往”了如指掌,这可能吗?一切真实性对他们来说都等于零,他们的生活与一切无关,宛如空屋中的挂钟一样摆动着,这可能吗?
对,这是可能的。
对活着的少女一无所知,这可能吗?嘴里说着“妇女们”、“儿童们”、“男孩们”,却没有意识到(受过再多的教育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词早已不是复数了,而只是不计其数的一个个单数,这可能吗?
对,这是可能的。
有些人口诵“上帝”,视上帝为共有之物,这可能吗?举两个学童为例:一个买了一把刀,他的伙伴在同一天也买了一把一模一样的刀。一个星期之后,他俩各自拿出自己的刀来给对方看,结果是这两把刀的相似之处已所剩无几了,它们经过不同的手使用变得大不相同了(其中一个学童的母亲说,假如你们总是马上把每件东西都用坏……)。这样说吧:相信拥有一位上帝而又不去使用他,这可能吗?
对,这是可能的。
如果这一切是可能的,即使仅仅是看上去有可能,那么为了世上的一切,总该做些什么。不论是谁,既然有这令人不安的想法就必须着手补做耽误的事情,哪怕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非最适合的人选,因为除他之外,再没有其他人在这儿了。这个外国来的无名之辈布里格不得不坐在五层楼上的房间里写作,夜以继日地写作,是啊,他必须写作,坚持到最后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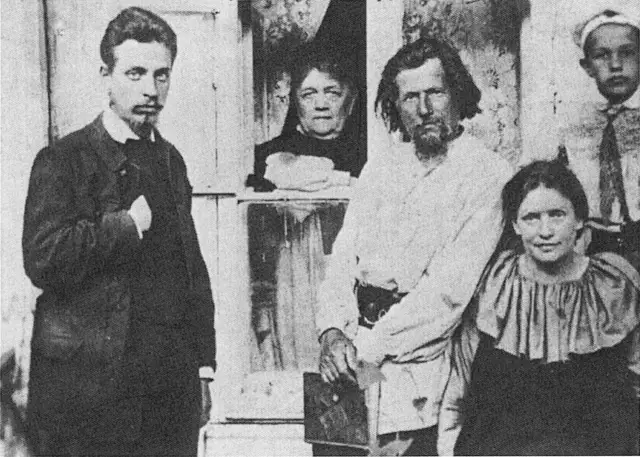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一位诗人”吗?魏尔兰……不知道?毫无印象?不。你们不能区别他和你们认识的那些人吗?你们不能区别,这我知道。但我读的是另一位诗人,完全不同的另一位。他不住在巴黎,他在群峦叠嶂中隐居。他的声音在清澄的空气里像钟声一样鸣响。他是一位幸福的诗人,吟咏着他的窗子和书橱的玻璃门如何眏射出一种可亲而孤寂的遥远。我一直向往成为这样的诗人,因为他像我一样对姑娘了如指掌。他了解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姑娘,她们早已香消玉殒,不过这没有什么,因为他了解她们的一切,了解才是最重要的。他念叨着她们的芳名,那些用纤柔细长的老式花体字母轻轻地写下的芳名,还有那些比她们年长几岁的女友成熟的芳名,而这些名字里已经有少许命运,少许死亡,而死亡在曼声长吟了。在他红木书桌的抽屉里,可能收藏着她们褪色的书信和日记散页,那上面记载着生日、夏季舞会的情形。或许,他卧室背面墙边那架装得满满登登的五斗柜里有一只抽屉,里面保存着她们春季用的服装,复活节时第一次穿的浅白衣裙,本来是夏装,但她们等不及提前上身的缀着薄纱花饰的布拉吉。啊,这命运是多么幸福:坐在祖传邸宅的一间静室里,周围的东西显得宁静安谧,漫步屋外,在铺青叠翠、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里聆听刚来此地的山雀的学唱和远处村落的钟声。坐着,凝视午后太阳铺下的一条温暖的光带,知道那么多已逝少女的往事,俨然一位诗人。我想,假如我能住在某个地方,大千世界的某个地方,远离尘嚣无人打扰的一座乡村别墅,我也会成为一位这样的诗人的。我只要一个房间(靠山墙光线明亮的房间)就够了。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的旧物、和家庭肖像、和书生活在一起了。此外我还要有一把扶手椅,几束鲜花,几条狗和一根走石子路用的粗手杖。再不需要其他什么了,除了一本用淡黄的象牙色皮面装订的、衬页上画有古老花纹的本子:我要在这本子上写作,写很多很多,因为我有很多想法和回忆。
译 | 魏育青
本文选自《词与文化》,199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