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德勒兹(1925年—1995年)在他的著作《反俄狄浦斯》中提出了“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将“有机组织”与“身体”对立起来,但他所反对的并不是器官,而是大写的有机体系,即使身体的连接成为一种由多个器官组织而成的等级化的和谐整体。德勒兹坚持欲望没有客体,欲望并不意味着任何匮乏和不可能,它在其自身之中、在其内在性中得到自我满足,而任何的快乐都是对自由的欲望之流的再辖域化。在反抗的意义上,德勒兹对一切实体的“去辖域化”运动最终指向了自由与解放。齐泽克在《无身体的器官》中,致力于重建一个更“真实”的德勒兹。他将德勒兹的作品与俄狄浦斯和黑格尔相连接,通过对德勒兹主义概念的颠覆,进一步探索电影作品中“无身体的器官”。
本文节选自《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转载自公众号“安斯本文化”,特此感谢!


齐泽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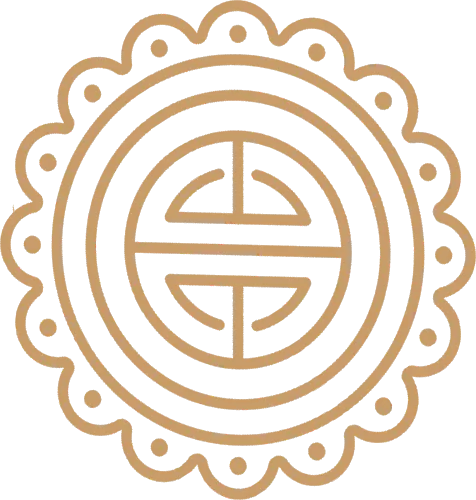
无身体的器官
——论德勒兹
文/齐泽克
译/吴静
一、黑格尔、拉康、德勒兹
对德勒兹后期哲学最精炼的定义是:它是“费希特化的斯宾诺莎主义”。而首先我们应当牢记的是,费希特是(或者把他自己描绘为)一个绝对的反斯宾诺莎主义者。纯粹虚拟的自参考创造可以达到无限大的速度,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外在,在其中或通过其来中介自己的自我设定的运动。
“因此无限大的速度描述的是一种不再与实际运动相关的速度,它是一种纯粹虚拟的‘运动’,总是可以达及自己的目标,或者说它的运动本身就是它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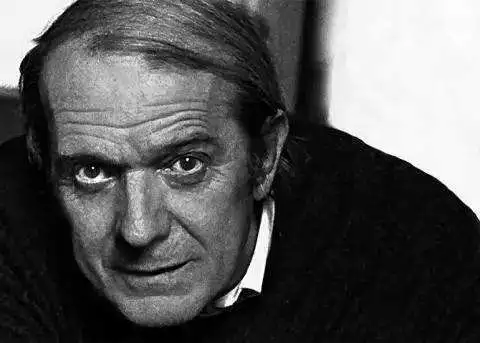
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1925年—1995年)
这正是德勒兹坚持欲望没有客体(客体的缺乏将引发并维持欲望的运动)的原因:欲望正是这样“一种纯粹虚拟的‘运动’,总是可以达及自己的目标,或者说它的运动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这也是德勒兹从受虐狂和骑士之爱中领会出来的主旨——在这两种情形中,所被尊奉的并不是牺牲的逻辑,而是如何维持欲望……根据对受虐狂的标准解读,受虐者和常人一样,也寻求快乐;其问题在于,由于被内在化的超我的存在,他不得不通过经历痛苦的方式来达到快乐,以抚慰被压抑的能动性,后者深信快乐是不可饶恕的。相反,德勒兹认为,受虐者之所以选择痛苦是为了消解欲望与作为其外在衡量标准的快乐之间的虚伪联系。快乐绝不是只有通过痛苦才能迂回得到的东西,但是只有延迟能使快乐达到极大值,正在于它中断了肯定性欲望的连续过程。这是欲望的一种固有的愉悦,就仿佛欲望本身是自我满足的,并不意味着任何匮乏以及不可能。
骑士之爱也同样如此:它对于满足的永恒延迟并不符合匮乏的原则或超然的理想:在这里,它也同样意味着一种没有缺乏的欲望,因为它在其自身之中、在其自己的内在性中得到满足;相反,任何的快乐都已经是对自由的欲望之流的一种再辖域化。在这一点上蕴含了对德勒兹的黑格尔批判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当德勒兹反对黑格尔的时候,他声称创造行为“本身就具有即时的原创性;并不存在一个进行创造的先验主体或否定性的主体,他可能需要花点时间才能意识到或明白自己正在创造”。因此,德勒兹将黑格尔的错误归咎于并不存在的实质化具体化,并以这样的方式消除了黑格尔思想中最接近于德勒兹本人的维度。黑格尔不厌其烦地坚称精神是“其自身的产物”:这并不是一个逻辑先在的主体对于客观性的干涉和扬弃中介,而是其自我运动的结果,即,一种纯粹的过程性。因此,它并不需要花时间“明白自己”,而是生成自己。
德勒兹的第二个指责就是对黑格尔的这种误读的反面:“鉴于在黑格尔那里,任何的既定‘物都有别于其自身,因为它首先有别于其所不是的东西’,即有别于一切与它相联系的客体,而德勒兹笔下的柏格森则认为由于物本身所具有的‘内爆力’的存在,‘物首先、即时地与自身相异’。”如果真有过一个稻草人的话,那就是德勒兹笔下的黑格尔:黑格尔最基本的理论难道不正是所有的外在对立都源于物内在的自我对立——或者说所有的外在差异都暗示了自身差异吗?一个有限物有别于其他的(有限)物,因为它与自身已经不是同一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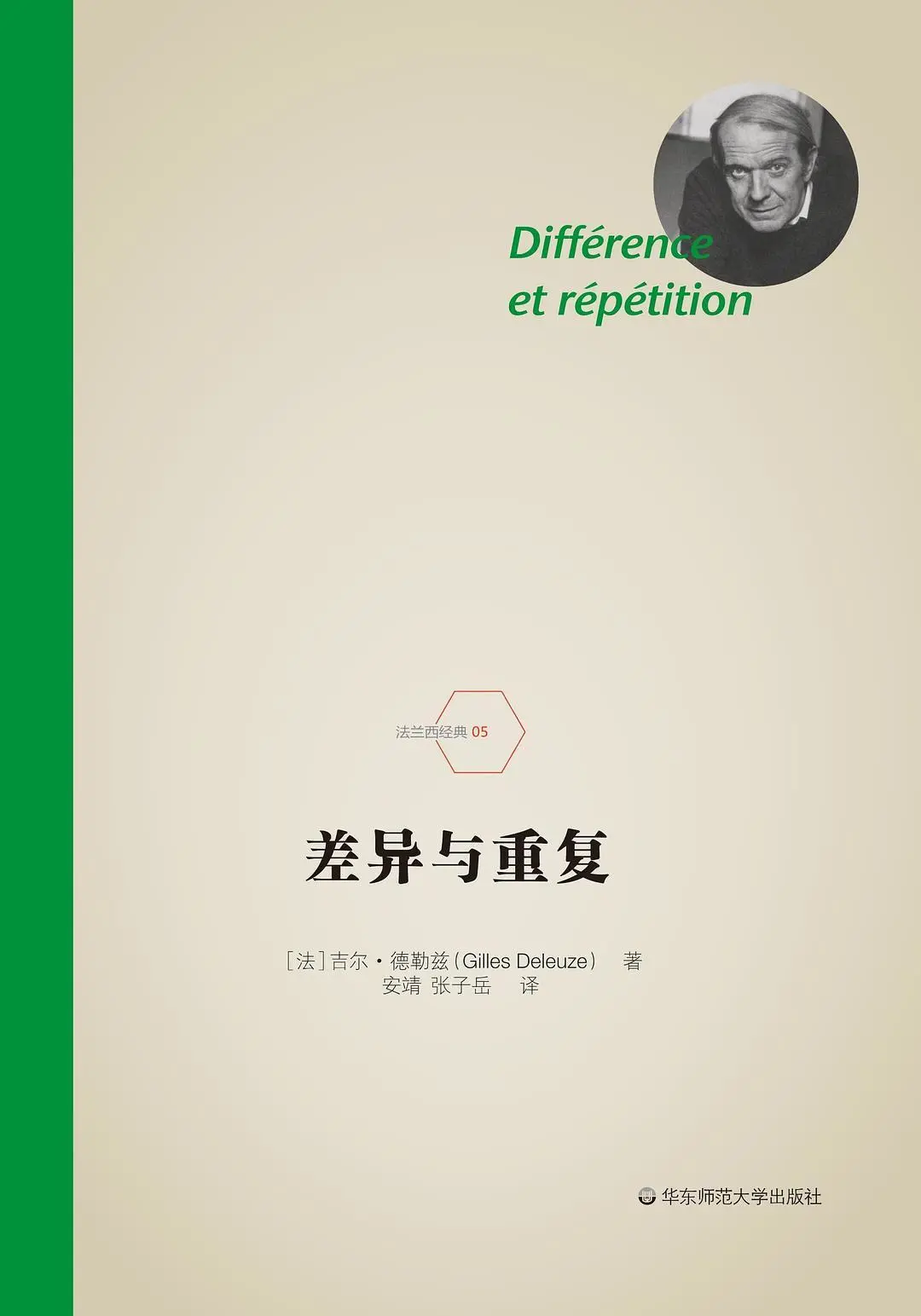
《差异与重复》,吉尔·德勒兹著,
安靖 / 张子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当德勒兹言说在一个单独的运动中进行创造和观照的过程时,他随即自觉地想起了理智直观的公式,即上帝独一的特权。德勒兹进行的是一种前批判的议程,他满腔热情地称赞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直接洞穿了自在之物的核心),反驳了康德为我们的知识对于现象表征所设立的“批判性”界限。然而,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是:万一再现的距离,即物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镌刻在物自体的核心之处的,那么我们与物(包含了我们与物的关系)之间的鸿沟——就在这一方面成了黑格尔基督教神学的中心,因此我们与上帝的分离和上帝与其自身的分离就是一致的。德勒兹声称,这些命题并没有描述物,却是对物的口头实现,即以言语方式存在的物自体——那么同样的,黑格尔是不是也会抱怨说,我们对上帝的再现是以表征方式存在的上帝本身,而我们对上帝的错误观念是以错误观念方式存在的上帝本身呢?
这种创造性过程的典型例子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允许一种绝对的、真正具有变革性解放的表达,恰恰因为被解放的只是解放本身,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化或去物质化的运动”:最终必须要被解放的就是解放本身,这是对一切实体的“去辖域化”运动。这种自联系的运动是关键性的——并且,沿着同样的脉络,欲望所欲望的不是一个确定的客体,而是对欲望本身无条件的肯定(或者,正如尼采所言,意志就其最根本而言,是对意志本身的意志)。这一过程也可被称之为“个体化”,“这是一种被设想为纯粹或绝对地在其间的关系,它被理解为完全独立或外在于它的所有项——因此这种在其间也可以被描述为在无有‘之间’”。
顺着这样的脉络,我们应该去阅读一下基督形象所具有的(常常非常明显的)奇怪的平静,即他的“默然”:如果基督是德勒兹意义上的一个事件——一个不具有正当的因果能力的个体性的出现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会忍受痛苦,却选择一种彻底地默然的方式的原因。基督是德勒兹意义上的一个“个体”:他是一个纯粹的个体,并不需要证明自己拥有比常人“多”的肯定性属性,也就是说,基督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是完全虚拟的——回到舒曼,基督在现实性的意义上与常人无异,他所多出来的只是关于他的口口相传的“虚拟旋律”。在圣灵中,我们可以领会这种“虚拟的旋律”:圣灵是一种纯粹虚拟性的集体场域,它并不具有自己的因果能力。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是一个实体之人的死亡,它使我们直接面对复活的虚拟场域,而这一虚拟场域又是支撑受死的基础。基督教把这种虚拟性的力量称之为“爱”:当基督在死后对忧心不已的追随者们说“若你们二人中有爱,我必在那里”的时候,他也就是在肯定自己的虚拟状态。
支撑现实性的这一虚拟维度是否允许我们将德勒兹和拉康联系在一起呢?对德勒兹进行拉康式解读的出发点应当是一个粗暴的、简单的替换:任何时候德勒兹和加塔利说到“欲望机器”,我们都应该把它替换成驱力。拉康的驱力,是“无身体器官”(这一概念出现在德勒兹谈论俄狄浦斯三角化及其所具有的禁忌和僭越的辩证法之前)以沉默和长期的方式坚持重复,其实完全符合试图为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欲望的游牧机器所做的限定:拉康的讲座十一中有一章是献给自己的驱力概念,他强调了驱力的“机器”特征,也就是它作为一个人工复合物/不同部分的合成所具有的反系统本质。——然而,言之至此,不过是开始而已。使这个问题即刻变得复杂化的事实在于:在这种替换作用中,某种东西不见了,即冲动与欲望之间不可归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本质性区别使得既不可能从一者推断出另一者,也不可能从一者产生出另一者。换句话说,德勒兹的“欲望”是一个反表征主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可以自我创造出表征/压抑情景的原始的流。而这一概念与拉康毫不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总是会谈论欲望的解放,以及将解放了的欲望从其表征主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话题。而这一切,在拉康的界限范围内是毫无意义的:对德勒兹而言,最纯正的欲望就是力比多的自由流动;而拉康的冲动则是被一种基本性的、无法解决的僵局构成性地标注出来——冲动是一种僵局,一个绝境,它在这一绝境的不断重复中发现了(过去的——原文为法语)满足。
黑格尔
(1770年——183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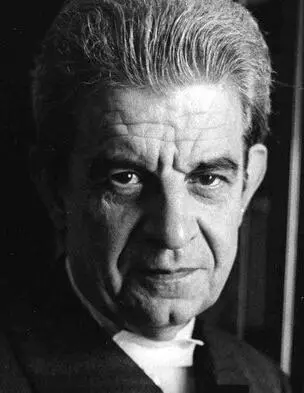
雅克·拉康
(1901年——1981年)
或者,用德勒兹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欲望流就是BwO,无器官身体,而拉康的冲动则是OwB,无身体器官。欲望不是部分客体,而冲动却是。德勒兹特别强调,他所反对的不是器官,而是大写的有机体系,即使身体的连接成为一种由多个器官组织而成的等级化的和谐整体。其中,每一个器官“各在其位”,承担特定的功能:“无器官身体绝不是器官的对立面。它的敌人不是器官,而是有机体系。”德勒兹试图以此来表明他要斗争的对象正是组合主义/有机体系。在他看来,斯宾诺莎的实体是一种终极的无器官身体:在这个非等级化的空间中存在着一种(器官的?)无序的多样性,每一种器官都是平等的,流动的……但是,这里其实存在着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为什么是无器官身体?为什么不能(也)是无身体器官?为什么不是身体——这个自主性的器官可以自由流动的空间呢?难道是因为“器官”所唤起的是在某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为特定目的而服务的功能吗?但是这样一个事实不正好成就了它们的自主化?无身体器官,不是更加具有颠覆性吗?
德勒兹对身体的喜爱明显超过器官,而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以清楚地在他对莱布尼茨的单子等级理论的接受中看到:单子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而言是数量化的。换言之,每个单子从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它表达了整个无限的世界,但是每个单子却又具有不同的,并且总是特定量的强度和能力,就最低的一级而言,所谓的“黑暗单子”只有一个清晰感知:对上帝的憎恶;而在最高的一级,“合理单子”却能开放自身,映射出整个宇宙。而单子之所以不能充分地表达上帝的原因正在于它过分执着于自己作为被造物(译者按:这里之所以这样译,是creature作为其所表现的上帝creator身份的对立)的错觉,过分执着于其特殊的(从根本上而言也是物性的)身份。人类在这里是最高形式矛盾的体现:一方面,人类比其他的生物种类更深陷于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固执地关注于如何保存自我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德勒兹而言,哲学的最高使命是将人提升到他的人性条件之上,即将其提升到“超人”[overman]的“非人”层面);而另外一方面,德勒兹同意柏格森所说的,人体现了生命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突破,一个至高点——因为人具有意识,而这正使得一个生命体最终能够避开自己的物性(机体)界限,上升到具有神圣完满状态的纯粹精神的统一体。
从黑格尔的立场来看,人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德勒兹所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问题,谢林却看得更加清楚,即最低级和最高级这两方面特征其实具有一个终极的同一性,即正是通过对独特的自我的执着,人类个体才能将其自身从真实生命的特殊轮回(繁衍与腐朽的不断循环运动)中提炼出来,与潜在的永恒建立起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在此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执迷有了另一个名字:恶)恶恰恰是善的兴起的一个形式上的条件:它的确为善创造了空间。那么,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不正好是一个本质性连接的实例吗:为了保持其连贯性,善的场域必须以恶的独一性(singularity)来进行缝合?
二、纯粹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讲清楚“纯粹差异”这个核心概念,让我们求助一下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人物:简·西贝柳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差异(不仅是在音乐上)的一个方面就在于现代性围绕着禁止与/或限制的逻辑:难道十二音体系不正是一个自我设定的、和声的限制与禁止的集合吗?阿多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悖论,即摆脱连续的音调表现为一个自我设定的、有着严格规则的限制与禁止的集合。相反,后现代性则表现为向“怎么样都可以”立场的大规模回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物自体”已经销声匿迹了,不可能再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联系。而这一认知实行的是一种戏谑的态度,认为古老的形式可以以仿品的形式被规定,而无关乎它们的真实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能自由演奏所有流传下来风格的斯特拉文斯基(与勋伯格相反)不正是第一位后现代作曲家吗?

简·西贝柳斯(1865年—1957年)
如果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这一对宿敌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立,那么,哪一个人物可以象征已经消失的第三选择,即持续存在的传统主义呢?这就是第三个S(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名字都是以S开头——译者注):西贝柳斯,即被阿多诺极度鄙视的西贝柳斯。这指的并不是所有时候的西贝柳斯,而是消除了柴可夫斯基影响之后的西贝柳斯,是写第四交响曲时期的西贝柳斯。在西贝柳斯那里,人们真正与最彻底的“实体”概念相遇——这是一个人的存在得以浸润其中的[文化性的]民族实体——而不是晚近其他所有廉价的浪漫的民族[国家]主义。人们在这里应该反对西贝柳斯和马勒,当然我是说,他们的交响曲中的两个相似的乐章: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中恶名昭著的小柔板,以及极具争议性的西贝柳斯的杰出作品,即他的第四交响曲中的第三乐章(缓板)。且不去说它们之间令人震惊的相似性,人们在这里能够简明地感受到一种分歧,这种分歧正是在马勒造访赫尔辛基期间、两位作曲家一起在公园散步时那段著名的对话所体现出来的:马勒强调一首交响曲怎样才能包含整个世界,而西贝柳斯则辩称要保持克制和矜持。
对于西贝柳斯艺术上的正直以及他并非公开地故作保守的最好的证据恰恰就是他最终的失败:他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长达三十年的静默,在这期间,他在音乐创作上一无所为(所有伟大的作曲家最终都失败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失败了,瓦格纳的《帕西法尔》失败了,莫扎特的《女人心》的终曲也失败了——失败是一种标志,它意味着作曲家正以真诚面对着音乐素材。只有“轻浮”庸俗的作曲家才会顺利地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此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是:在西贝柳斯发展过程中的哪一个精确点上,他陷入了静默?答案是,当原本给他的作品提供了基本张力的视差崩溃了,当两种音乐旋律——交响乐和叙事曲——之间的距离消失了的时候。他最后两部重要的作品是第七交响曲和交响诗《塔皮奥拉》(正如人们经常评论的那样,人们在这首交响诗中所感受到的森林与在德彪西的《海》中所看到的大海异曲同工),其最关键性的特征是它们的相似性(两者长度几乎相同,一个长乐章的内部分节,却从更深的意义上相互衔接)——似乎西贝柳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行到了同一个相遇点:不可能/理想之点。西贝柳斯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不可能/理想,它“扬弃”了“绝对音乐”(交响曲)和“标题音乐”(交响诗)之间的张力,扬弃了作为表现(刻画、唤起……)特定“内容”的音乐和直接借助于形式连接而赋予其精神内容的音乐之间的张力,扬弃了个人性(自然)经验的丰富与主体性的空虚之间的张力。(《塔皮奥拉》将在森林中的经历内化为一种纯粹精神性的、“抽象的”内在旅程,而第七交响曲则逐步地接近于交响诗。)这种综合从推理上而言当然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失败必然是结构上的。而西贝柳斯,如果他仍要坚持他在艺术上的正直的话,则不得不保持沉默……当然,正是因为这种出奇的接近与相似,绝对音乐与标题音乐,交响曲与交响诗之间的差异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最后这首交响曲给出了一种内在的平静与满足,一场最终凯旋的战役,一种对生命的肯定,(难怪它常常与第五交响曲有相似之处)。而《塔皮奥拉》——它并没有陷入以自然来获得治愈的浪漫主义的圈套——则展现了自然的原生力量的不安和可怕,以及人们在对抗自然力量时的徒劳和最终的失败。交响曲回旋的最后结果当然是肯定与和解,而交响诗的终曲则是失败和惆怅,这两极之间毫无调和的可能性。西贝柳斯的第四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提供了一个例证,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同音乐问题/素材之间的紧张关系:与音乐的这种情形类似的是罗丹(或者晚期的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形体费力地、奋发地试图从石材的惰性中挣扎出来,而并没有完全消除物质惰性的压迫性沉重——这一乐章的伟大努力成就了中心的乐旨节奏(主题旋律),直到乐章的结束,它也只出现几次而已。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过程与维也纳的古典主义相对照。在古典主义中,乐旨,即主旋律是被直接给出和表现的(在莫扎特著名的《木管小夜曲》的第三乐章中,旋律直接“从天”“而降”,获得了肉身的沉重)。——如果在时间的回溯中能走得更远一些,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就术语的严格意义而言还不存在旋律的时期。让我们来看一下巴洛克时期流行的和谐,如巴哈贝尔的“卡农”:今天,最先出现的音符会自动地被当作伴奏,因此我们会悄然等待旋律乐章出现的时刻;但我们没等到旋律,只是前调伴奏越来越趋于复杂的复调变化,我们多少会感到有些“上当受骗”。那么这种期望值,即认为旋律乐章缺失的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呢?旋律的诞生当然是维也纳古典主义的事情;简单地说,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前面已经提过的《木管小夜曲》的第三乐章:最开始出现了一些身份不明的音符(今天,我们把它当作是为旋律乐章而准备的伴奏,但是就当时而言,它的身份极有可能是不确定的。比如,它完全有可能被认为已经是主旋律了),然后旋律乐章仿佛“从天而降”……接下来,旋律乐章会在哪里结束呢?答案也很清楚:在晚期贝多芬那里(尤其是他最后的钢琴奏鸣曲)。浪漫主义乐章的真正突破正在于它赋予了旋律乐章以“不可能”,以一种不可能性对其进行了标注(“优美的浪漫旋律”的兴盛不过是何种根本的不可能性的浅薄而娴熟的反面罢了)。因此,我们所拥有的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旋律),实质上却是受到限制的,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具有表现主义的晚期浪漫主义的最终成果可能就是旋律的概念,主题乐旨的概念,必须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将它们从声音素材的惰性中“锤炼成型”,刻画并萃取出来:它们并不是构成乐章主体的一系列变化的起点,而是来源于对音乐素材的艰苦不懈的精心制作,从而形成了作品的主体部分。这种与素材/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正是将西贝柳斯和柴可夫斯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对于后者而言,土地,这种惰性的、潮湿的材料,不但不与灵性相对立,反而是达及它的媒介。
在这个方面,西贝柳斯第四交响乐的第三乐章必须要被拿来与作为尾曲的第四乐章进行对照,两者体现了不同的失败模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三乐章显示了试图提炼出主旋律的痛苦努力,这种努力两次走到成功的边缘,然而最终却失败了:“那些意在成为主题的/……/当乐章两次试图发展成为成熟的旋律时,两次都后退了,第一次被开场主题的重返所阻挡,第二次被铜管乐所挤压。”这种失败,这种阻碍了对旋律的最终肯定的内在阻滞,对于西贝柳斯而言是格外难以承受的。他广为人知的见长之处在于能缓慢地建立起张力,然后以最后出现的完整的主题旋律来释放张力——关于这一点,想一下他第二和第五交响乐大获成功的终曲就足够了。而第四乐章以一种更加令人不安的方式失败了:
“终曲的第一部分出现在释放节奏和冲动的丰富性的地方,似乎更长的铺陈原则,以及伴随主题核心的更柔美的乐句就要兑现了。但接下来的并不在意料之中:很快地,一种令人不安的消解过程就开始了,到结束时,它已经完成并不可调和。最后几页逐渐消退为一种放弃的空无,一段双簧管独奏出现了三次,仿佛某种神秘的生物,正在冰雪覆盖的灵性荒漠中,发出无限孤独的喊叫……”

电影《十三度凶间》, 约瑟夫·鲁斯纳克导演,1999年
这段音乐的最后一部分不仅是拙劣的伪诗歌,而且从狭义上来讲是错误的:在西贝柳斯的第四交响乐终曲的最后一部分实际发生的,比起对在空虚的荒漠中无人听见的孤独者的喊叫的普遍表现来,更令人觉得古怪。我们宁愿目睹一种音乐的肿瘤或病毒,开始逐渐瓦解某个音乐结构——仿佛(音乐)现实的基础、“素材”正在慢慢丧失它的连贯性;如果用另一种充满诗意的比喻来说,仿佛我们所栖居的世界正在逐渐丧失其色彩、深度、特定的形状以及其最根本的本体论上的一致性。在西贝柳斯第四交响乐的最后一个乐章中所发生的,类似于约瑟夫·鲁斯纳克的《十三度凶间》结束前的场景,当霍尔,电影的主角,驾车去往一个他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时;在旅途中的某一特定地点,他停下车来查看为什么这个地区以及当中所有的一切都被线框图模型所代替。他到达了我们世界的尽头,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密集的现实溶解成了抽象的数字坐标,而他最终获得了真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洛杉矶——他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拟像……因此,正如第三乐章致力于努力扭转旋律一样,第四乐章反而有了一个和谐的开始,仿佛一切都很不错,仿佛城堡已经被攻占,它似乎昭示着其潜能将会得到全面而彻底的展开。然而接下来发生的却是,素材经不起我们想将它塑造成型的努力(正如在第三乐章中那样)——它直接瓦解了,消失,逐渐丧失了它的物质实体,变成了虚空。我们可以对它为所欲为,但问题在于,我们所作用于的素材本身渐渐内爆了,崩塌了,并最终消逝了……那么,在电影的历史中,第三交响乐中的第三、四乐章之间的这种张力与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和《惊魂记》之间的张力是不是同样的呢?第三、四乐章之间的差异正是人和非人,更准确地说是后人类之间的差异:当第三乐章赋予了人类维度最浓重的犹豫时,第四乐章却变换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在此一种非人的、疯狂的戏谑与主体性的贫乏不谋而合。
本文节选自《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
《无身体的器官:
论德勒兹及其推论》
作者: 斯拉沃热·齐泽克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8
页数: 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