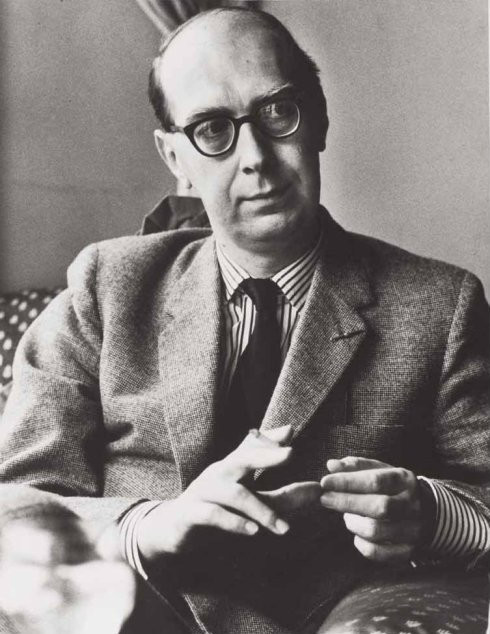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20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1922年出生于英格兰考文垂。1943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于各大学图书馆,其中任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达三十年之久。著有诗集《北方船》(1945)、《少受欺骗者》(1955)、《降灵节婚礼》(1965)、《高窗》(1974)及小说、评论等,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主流文学“运动派”主将。1965年获英国女王诗歌金质奖章,被评论界誉为“英格兰现有最优秀诗人”。1974年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术院洛安尼斯奖。1976年获德国莎士比亚——普瑞斯奖。1984年,因拒绝受聘桂冠诗人,被称为“非官方的桂冠诗人”。1985年因喉癌在赫尔去世。终生未婚。拉金被公认为继艾略特之后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
菲利普·拉金诗五首(舒丹丹译)
别处的意义
在爱尔兰是孤独的,因为它不是家,
保持疏远颇为明智。风趣而冷漠的言语,
如此与众不同,使我受到欢迎: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开始了联系。
他们的街道穿堂风盛行,尽头连着小山,隐约
而陈腐的码头的气息,如一座马厩,
鲱鱼小贩的叫卖声,渐渐微弱,
证明了我的隔离,并非不切实际。
生活在英格兰不会有这样的借口:
这些是我的风俗和规矩
拒绝它们可严重得多。
除了这里,再没有别处支撑我的存在。
去教堂
确信里面没什么动静,
我走了进去,让门砰然关闭。
又一座教堂:草垫,座椅,石地,
和小本的书;蔓生的花束,为礼拜日
而摘,现在已近枯黄;一些铜器物什
在圣堂上方;灵巧的小风琴;
一种浓重、陈腐、不容忽视的沉寂,
上帝知道酝酿了多久。无帽可脱,我笨拙地
摘下自行车夹子聊表敬意,
走上前,伸手摸了一圈洗礼盆。
从我站立的地方,屋顶看起来几乎是新的——
刷扫过,或被修复?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我。
登上读经台,我细读了几首
煞有介事的大字体的赞美诗,并且念出
“到此结束”,比我预料的大声得多。
回声短暂地吃吃窃笑。回到门边
我在书上签了名,捐出一枚爱尔兰六便士,
心想这地方不值得停留。
然而我停留了:事实上常常如此,
总是像这样在困惑中结束,
不知道想寻找什么;也不知道
当教堂完全沦为无用
我们会把它们变成什么,如果我们愿意
长期开放几座大教堂,在上锁的陈列柜里
展出它们的羊皮纸文稿,捐款盘,和圣饼盒,
其余的免费交给雨水和羊群。
我们是否会把它们当作不祥之地加以回避?
或许,天黑后,疑惑的女人们会来
让她们的孩子们摸一摸某块特别的石头;
采摘治疗癌症的草药;或在某个
约定的夜里看见幽灵散步?
总会有某种力量将继续
存在于游戏,或谜语中,像是随意;
但是迷信,如同信仰,必将消亡,
当不信仰已经离去,还有什么能够存留?
野草,荒径,刺藤,扶壁,天空,
日益难辨的形状,
日益模糊的用途。我不知道
谁将是最后,那最后的一个,前来寻访
这个地方,只为它往日的样子;是那轻轻敲打
并记录、知道十字架楼厢为何物的某个工作人员?
某个贪爱古董的,废墟中的酒鬼,
或某个迷恋圣诞节的家伙,指望吸一口
长袍饰带以及管风琴和没药混合的气味?
或者他将成为我的代表,
厌倦,孤陋,明知灵魂的泥沙
已溃散,却仍穿过郊区的灌丛,
来到这十字架之地,只因它让那些
后来只在分离中才能发现的事物保持未被分割,
如此长久而稳定——婚姻,出生,
和死亡,以及对这些的思考——这特殊的壳
正是为它而建?尽管我不知道
这装配齐全的霉臭的谷仓价值几何,
但在沉默中站在这里令我愉悦;
这是肃穆的大地上一座肃穆的房子,
在它混合的空气里我们所有的冲动汇合,
获得认可,披上命运的长袍。
而这一切永不能废弃,
既然永远会有人惊奇地发觉
他体内有一种想变得更为严肃的饥渴,
并因它而被这片土地吸引,
他曾听说,在这里,人会变得智慧,
只要周围还躺着那么多死去的人。
关于读书习惯的研究
我把鼻子埋进书里
治好大部分上学不够的毛病,
毁掉眼睛也值得
知道我仍能保持冷静,
熟练地抡起右钩拳
痛打大我两倍的癞皮狗。
后来,戴上一吋厚的眼镜,
罪恶就是我的云雀:
我和我的大衣以及牙齿
在黑暗中快活得要命。
我用性狠揍女人!
像捏碎蛋白烘饼。
现在读得不多了:那个
在英雄赶来之前
按倒女孩的花花公子,和那
守着零售店的黄脸老兄,
看起来都太过熟悉。见鬼:
书就是一堆废物。
广播
盛大的耳语和咳嗽声来自
星期天人满为患、令管风琴皱眉的广阔空间,
突然一阵疾促的鼓点,
女王驾临?然后是落座的轰鸣。
接着,小提琴的抽泣开始了:
在所有的脸中,我念想你的脸
美丽而虔诚,
在一片浩瀚的音乐的滑翔前,
你的一只手套悄悄掉在地上
落在崭新的,稍稍过时的鞋子旁。
天很快黑下来了。我失去了
一切,除了安静而枯萎的
树叶映在那微微寂寥的树上的轮廓。
在热烈的波段后面,遥远而疯狂的
和弦风暴更加无耻地
抑制我的头脑,他们碎裂的尖叫
留下我绝望地搜寻
你的手,在那样的空气里微弱的,鼓掌。
一座阿伦德尔墓
肩并着肩,面目模糊,
伯爵和夫人躺在石墓,
他们体面的气度隐隐可见,
自接合的盔甲,僵硬的褶皱,
还有那微弱的荒诞的暗示——
他们脚下的小狗。
这种前巴洛克风格的朴素
几乎不能留住视线,直到
看见他左手的护手套,仍旧
空空地攥在另一边;然后
发现,带着锋利而温柔的震撼,
他的手抽回,握住她的手。
他们想不到会躺这么久。
雕像中的这种忠诚
正是朋友们看到的细处:
雕刻者摆脱受人托付的
腻味的优美,为了环绕底座的
拉丁姓氏能流传更久。
他们猜不出,从多早开始
在他们仰卧静止的旅程
空气将变成无声的伤害,
赶走墓穴衰老的住民;
也猜不出,后来者的眼睛多久以后
开始打望,不再细品。他们僵硬地
坚持,牵手,跨过时间的
弧度。雪,不期而落。阳光
在每个夏天挤进草丛。明亮
而杂乱的鸟鸣撒落在同样
撒满尸骨的大地。而路上
无尽的变幻的人流涌来,
冲刷掉他们的身份。
而今,无助地躺在
一个非纹章年代的坟墓,一个烟雾的
低谷,在缓慢漂浮的混乱里,
在历史的碎片上,
只有一种姿势保留:
时间已使他们变得
不真实。无意而为的
岩石的忠贞,已慢慢变成
最后的徽盾,为了印证
我们的一丝直觉几近真实:
爱,将使我们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