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的“求经之路”,起起伏伏(上)
迟子建 经典短篇小说选读 2018-10-11
近日,著名作家迟子建的最新小说《候鸟的勇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既写了东北的落寞,也写了东北的生机。这些人事、情事、心事融汇到东北莽林荒野中,汇聚成迟子建的文字力量。
迟子建说:“写过《群山之巅》之后,我又回到了这样一片故土,我依然情钟于这片土地,依然能在这片土地里面发现当下生活我们所面临的焦虑、矛盾、不公、欢笑、坚忍、眼泪等等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谁也逃避不了,我们五味杂陈的生活、我们酸甜苦辣的遭遇等等,我们人生的遭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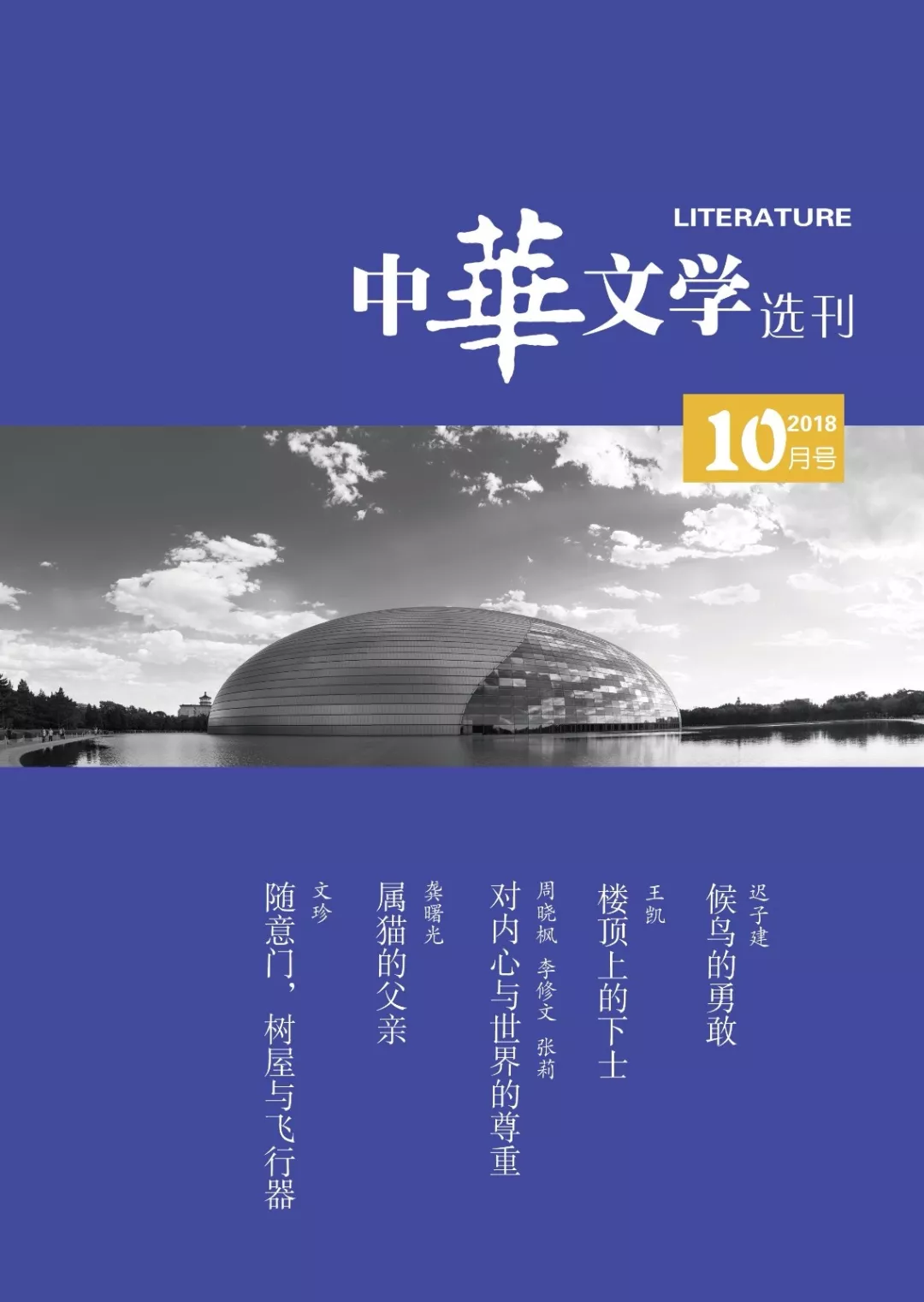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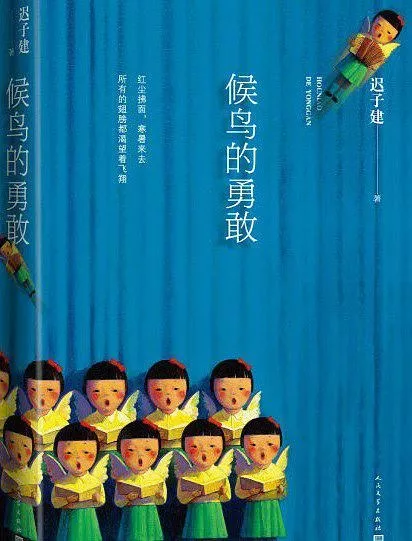

《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10期“主编阅读”栏目选载《候鸟的勇敢》。
今天的文章,是迟子建2016年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迟子建回顾了自己的写作之路,可以说,这篇长文是深入了解迟子建创作资源与文学理念的入口。
文学的“求经之路”
迟子建
长假期间,我在家里看了一部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大唐玄奘》,玄奘走过的路是一条宗教的“取经之路”;当时我就想,其实文学跟宗教差不多,也是一条“取经之路”,尤其对于我这样写了30多年的作家来说。每个作家走过的路都是个人的经验,我曾说过,文学经验有点像一次性消费的纸巾,可能我的经验不会对别人有用,但如果我的文学的求经路上的一些心得,可以给学子们哪怕是点滴的启示,我都觉得愉快。那么今天我就尝试着讲一下,文学的“一人一经”。我将从六个方面来阐述,简要回顾我的写作之路,或者说我的文学的“求经之路”。

△电影《大唐玄奘》
1民间神话与原始宗教
我的故乡是大兴安岭,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飘雪,到十一月,那里已披上冰雪的铠甲了。冬天时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讲故事。烧着炉子,喝着花茶,有时我们围在火炉旁,从地窖里拿出几个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茶,围炉听老人们讲鬼神故事。我还记得土豆片儿被烤后,因为淀粉沉积,就像给炉盖做了一次美容,在炉盖留下一圈一圈的白白的淀粉。我那时候很小,在外婆家,我就在大人堆里听鬼神故事。他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因为故事是小说的核。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些小说不要这样的核,但那样的小说大多成了软柿子,虽然甜,但很寡淡,没有嚼头。我听的故事多半都是民间神话传说,为什么呢?东北人很多是闯关东过去的,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是闯关东时来到大兴安岭的。齐鲁之地,大家知道《聊斋志异》,那里面的鬼神故事实在是影响深远;这些老一辈的人,很自然地把神话故事带到了边地。我是1964年生人,大概我都十来岁了,北极村还没通电,也不像现在有什么电视之类的,只有一个我姥爷称之为“戏匣子”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姥爷那时候整天守着“戏匣子”找京剧来听,那时候那就是“一大件”。你想在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在大兴安岭生活的还有这样两个少数民族,一个就是我作品里常常写的鄂伦春,他们是游牧民族,骑马,在山上生活、狩猎,住在桦皮围子里,也有的是兽皮围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鄂温克部落。鄂伦春和鄂温克都是狩猎民族,住着同样的“房子”(其实就是林间的“撮罗子”和“西愣柱”,叫法不同而已),宗教崇拜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骑在马上,一个是骑在驯鹿上。这两个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在他们眼里,花、石头、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

△鄂温克的冬季
我小的时候,一个是外婆他们讲的神话故事,一个是当地少数民族原始的宗教,对我影响很深。直到如今,我觉得这些朴素的宗教观和自然观还在影响着我。举一个例子,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我去当地采访了,在这之前也听说了那一带很多神异的故事。下面我要说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在香港的一所大学驻校时也讲过的:一个猎人,比如说他叫张三,前提是他是无儿无女的一个人,常年在山中打猎。有一天他打猎时,看见一只怀孕的狐狸,他举起枪就要打,因为狐狸的皮毛是很值钱的。可是这个时候这只狐狸忽然抬起了两只前爪 ,像人一样立起来,叫着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张三,求求你——”因为它是只怀孕的母狐狸嘛。当这个狐狸说出人话,向他求饶的时候,猎人特别害怕,他就放下猎枪给这个狐狸磕了一个头,从此再不打猎了。奇异的事情在后面,猎人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可等他终老,村人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葬礼上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一身素服,说是他的干女儿,来为他送葬,一直把猎人送到墓地,然后这两个女儿就消失了。像这种故事,在当地是广为流传的。
我作品里面的一些原始宗教的气息哪里来?就是这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老一辈人从齐鲁之地带来、流传下来的鬼神故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少数民族带给我的原始宗教崇拜。
2大自然与命运感
你们学地理的应该知道,整个大兴安岭相当于一个奥地利国土的面积,据说如果按新加坡的面积计算,有135个新加坡大。这么大的面积,大自然真是太壮阔了,现在全境也不过50万人口,人在那里太渺小了。所以小的时候在小镇上遇到生人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感。因为人在那里是少数族类,而动植物是多数族类,像林木等等。
我是冬天出生的,冬天有一项活儿,我是特别恐惧的,就是一到放了寒假,就得去拉烧柴。因为冬天很冷,需要大量烧柴取暖。那时没有燃煤,我们烧的柴禾就来自山上。那时拉烧柴的工具有两种,一个是手推车,一个是雪爬犁。一到放寒假,每天的第一要务,不管刮风还是下雪——零下四十度你也要进山,就是父亲带着我们去拉烧柴。我前一段给一家评论刊物写一个创作谈,标题叫《小说的丛林》,其中谈到这个细节。那个时候小,十一二岁上山跟着去拉烧柴的时候,有一种风干的树木,由于被雷击或者是病虫害,时间久了它就站着枯死了,我们叫它“站干”。那时也是要保护树木的,鲜树是不允许采伐作为烧柴的,“站干”就是我们的主要采伐对象。经常我父亲放倒了这些“站干”,十来岁的我们就要从密林深处,扛着“站干”往雪路上走,因为那是手推车停放的地方,你要把烧柴集中在那儿。从家里去山上要走很远的路,很多次我就看见一条“狗”,我说:“这是谁家的狗啊?”我到里面去扛“站干”出来的时候,这“狗”老是看我,还挺肥大的,我也不认识它。我跟爸爸说扛站干时遇见“狗”了,它老是跟在我身后,我爸就不再让我一个人往里面走,后来回去才告诉我:“那哪里是狗,那是狼!”——它尾巴拖着,耳朵是尖尖的。所以狼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并不是一个凶残的动物。我想可能那时食物链比较好,狼可吃的太多了,它看见一个毛头小孩儿,心想吃了有什么劲呢!所以没有胃口。但也可能是它吃得很饱,正在悠闲地散步。
这样的冬天,我们还去哪儿呢?进城,买年画。我们是在一个小山村生活,那时过年都要买杨柳青年画、朱仙镇年画等等,各县城的新华书店都有卖的。从我们小山村到城里大概20里路,一般家长给我个三两块钱去买年画的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你去城里书店的路上,沿着雪路走着走着,就得跑起来,因为天实在是太冷了,尤其是腊月天,基本都是零下三四十度这样的天气;腊月天的大兴安岭要是零下20度,那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了。我穿着棉猴,穿着厚厚的胶皮鞋,我们叫“棉靰鞡”。当你觉得脚一瞬间有“嗖”的一下凉的感觉,那就是你把脚趾冻着了,麻了,那时候要飞快地脱下鞋,抓一把雪搓两下脚,这样就不会生冻疮。你在寒风当中再穿上鞋,要飞快地跑一段再走,不然你的脚就冻坏了。我小时候生过冻疮,是因为拉烧柴,天太冷了,回到家里生了冻疮。我不觉得痛苦,反倒觉得无限幸福,因为我免除了苦役,不用再跟着我父亲上山拉烧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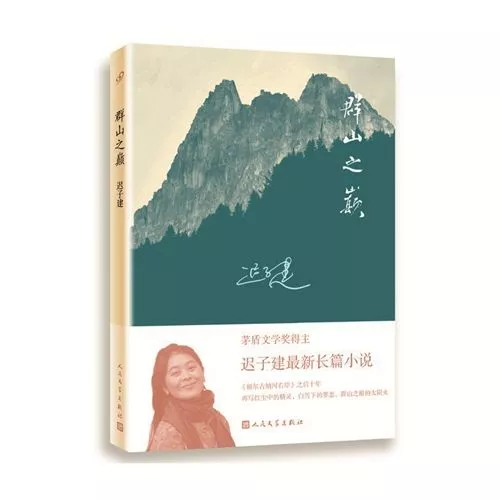
△迟子建《群山之巅》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样的生活对我的文学确实是有影响的。大自然漫长的冬天,你们在南方真是体验不到的。所以很自然地盼春,因为春天太美好了。春天一到,风暖了,不用穿厚衣服了,女孩子可以穿薄薄的花衣裳了。可是这样的日子特别短。那里的春天真是一闪即逝,大概只有半个多月,满山遍野的达子香花,就是映山红,全开了。那时候我们常去山上采达子香花。我曾在新作《群山之巅》里写到这样一个细节,这也是真实的。我们采了满抱的达子香花后,哪有那么多花瓶啊,没有地方栽,放哪儿呢?我父亲喝酒的酒瓶插几枝,猪肉罐头瓶子也插几枝,最后杯盘碗盏都派上了。最有趣的器皿,那真不是虚构的,家家不是都要养猪吗,猪食槽子那口比较深,所以废弃的猪食槽子,也被我们用来栽映山红花了。在那个年代,生活是那么的朴素,又那么的美好。当然因为我贪吃,所以我最喜欢那些能坐果的花,比如说蓝莓,我们叫“都柿”。
都柿开花了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山村小学的后面就是一片树林,一般是第二节课后的课间操,要做广播体操时,我基本上就会溜掉,从我的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纸,叠一个三角小喇叭,飞快地溜进树林,奔向各种果子。不管青的还是熟的,都摘。然后上第三节课,老师讲课时,我就在下面往嘴里塞,偷着吃点,什么马林果、水葡萄等等。大家知道花里边的忘忧草,其实就是黄花菜,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它能吃。我妈妈喜欢百合花、芍药花,经常命令我“你去给我采点百合芍药回来栽”,而我采这些花的时候,都会采一把黄花菜回来——用黄花菜做炸酱面太好吃了!
春天和夏天,也许因为太美好了,一闪即逝。我们几乎不敢种香瓜和西瓜,往往它们还在旺盛的生长期时,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它们没有熟的机会了。有时候9月份就要下雪了,霜来了,然后满山的绿叶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五花山那是绚丽之极,美得醉人。到了这时候,没有成熟的果实,自然也就结束了生命。可能我受前面讲的第一个话题的影响,感觉什么都是有灵魂的,我觉得这些没有成熟的果实,都有一颗心,这么多颗心寂灭了,特别伤感。我很小的时候就爱伤感,骨子有一种天然的忧伤,可能与此相关。没熟的果子死了,冬天突然就来了,大自然是那么多变。而人的命运呢,其实也是如此。
那时都是土葬,过了六十岁的人,在当时就算高寿了,当地的风俗,就要准备一下寿材,打上个棺材,刷上红色的油漆摆在家门口,阴森森的。晚上的时候出去串门,经过棺材的时候,真是害怕。这种棺材摆在那儿,让你时刻知道人是有终点的。但也有不该到终点的人,却在人生的列车上出了故障,下车了,夭亡了。死有时候真是突然而至的。童年的时候,我们是四家住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有三个属龙的女孩,都是1964年生人。有一个女孩生了痢疾,在卫生院打错针了,然后就死了。一个常和我一起玩的女孩,因为一针命就没了,她的母亲哭得抢天呼地,让我觉得特别恐怖,每天在观察自己是不是有痢疾,生怕也被打错了针,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还有一个对我刺激很深的,同一栋房的另外一个属龙的女孩,她叫小平。杀猪那天,她家的炕烧得特别热,不能睡人,她就来我家,和我睡在一铺炕上,她还把一块猪肉拿过来给我吃。我有一篇散文谈到这个细节。当天晚上她就发病了。第二天大人们用生产队的马车,把她送到了城里的医院,检查为结核性脑膜炎,一周后她死了。这些跟我整天蹦跶在一起的一栋房子里的同龄女孩,突然地死去,对我刺激太深了。命运是如此残忍,如此难测。我妈妈比较迷信,她跟我爸爸说:“咱们最好是搬家吧,你看这栋房子好像养不住属龙的女孩子。”那时我们家也没地方可搬呀,就一直住在那里。可能我命比较硬吧,安然无恙,逐渐长大。
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还有一些朋友、邻居命运的变故,包括我个人经历的父亲和爱人的早逝等等,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人生真是非常的苍凉。
一些批评家谈到我作品的死亡情结哪里来的,我想就是在我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看了生,看了死;看到了春天,也看到了冬天;同时看到了死去的植物,在第二年春天复生。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
3苍凉与温暖
冬天给予了我们极北之地人漫长的风雪,也给了我们对温暖的渴望,以及不屈、倔强的性格。所以我作品的底色是苍凉的,我笔下的北方人也是隐忍的、坚强的,就像冬天的河流。大家知道黑龙江是中俄界河,冬天的这个时候已经封江了,到了12月、1月的时候,冰会越来越厚,可是我们冬天时还会在江上捕鱼。我从小跟着大人去江上捕过鱼。你用冰钎凿开厚厚的冰后,能看到江水像生命的春水一样在涌流,我们从水里还能捕上鱼来——即使那样的严寒,也没能真正把一条江冻僵,因为春天又会来。

△黑龙江的冬季
这样的气象就像人生,不管现实多么严酷,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这就是我作品中的“暖”吧。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也是一种宗教情怀。我也知道恶在人性的丛林中像荆棘一样密布,悲凉之雾在我们人生之河中,从来就不曾远离我们。但我就想在这样的地方,在迷雾当中寻一丝丝的亮光,在这无边的寒冷当中寻找这种丝丝缕缕的暖。实际上,我作品的“暖”也没那么强悍,有时批评家把它夸大了。过于“暖”,大家都知道火炉烧得太暖了,烧过头了,就引起火灾了。我们老家的炕是用油纸糊的,要是烧得过热,它就会糊了,冒出焦糊的味道,炕面落下伤口结痂似的疤痕。所以说作品的温暖,要恰到好处。在这样一个苍凉的背景下,“暖”要水到渠成地呈现,不要一味地去给它一种“暖”,强加所谓“高大上”的东西。在“文革”时期,一些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就是“高大全”式的人物,那是小说人物的悲剧。
大家知道我有一个短篇叫《白雪的墓园》,有人读了,说我写得挺温暖,我说这个小说其实多凄切啊。1986年1月,我父亲去世了,他是在凌晨去世的,那天白天他看上去情况挺好,所以晚上我和姐夫在医院的抢救室守着他,让我妈妈去姐姐家休息了。凌晨时我看父亲不行了,赶紧让姐夫回家叫我妈。妈妈一进来看到我父亲停止呼吸了,她就哭;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哭不像一般的人大放悲声,她是忍着的那种哭。她哭着哭着,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里瞬间有了一颗红豆,红红的,很大的一粒;我就想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妈妈的眼睛就不好使了,所以害怕极了。举行完我父亲的葬礼,葬礼三天后要去圆坟,我们怕她伤心,不让她去。爸爸是腊月去世的,接着就是过年,过年前按风俗还要上坟——《白雪的墓园》写的都是真实的情节。我爸爸去世后的那段时日,我妈妈眼睛里那颗圆圆的红豆一直在,我们以为它永远就伴随着她了。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姐弟三人都好好地干活,哄我母亲,怕她伤心难过。挑水、劈柴、蒸年干粮等等,不想让她提起父亲的话题。腊月二十七,她要跟我们一起去上坟,我们坚决不肯,飞快地跑出家,七拐八绕,把她甩开了。我们回来后,发现她哭过。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突然发现她失踪了,我们特别害怕她想不开去自杀了,到处找,可哪儿都找不到她。最后她终于回家了,外面在下雪,她落了一身的雪,进来后拍打身上的雪花。那时我父亲的坟还没立碑,一般来说要转年清明才立碑,所以坟前是没有名字的,再说那是当时做白事的几个人给选的一块墓地,所以她并不知道父亲埋在哪里。但是她进来说:“我去看你爸爸去了。”我们立刻问:“你找到了吗?”她说:“我找到了,我一上山,经过一座新坟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和见到别的坟不一样,我就知道那是你爸。”那一瞬间我们特别难过,然后看她的眼睛,发现特别清亮,原来她眼里的红豆没了!她上了坟回来,眼里这颗一直带着多少天的、早晨时还在的红豆,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我写《白雪的墓园》的时候说,我父亲去世的一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耍赖,不忍离开,他就化作一颗红豆藏在我母亲的眼睛里,直到我母亲亲自把他送过去,他才真正安心待在另一世了。
你们现在听的这个故事,小说里面的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批评家也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温暖”,我不敢苟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它是多么的残缺,多么的忧伤!所以我一直说,我作品的“暖”,是苍凉当中的温暖。
我写作的“求经之路”(下)
迟子建 经典短篇小说选读 2018-10-11
4现实与超验
也许是童年所听的鬼怪故事对我的影响比较深吧,我一直觉得在人间之外,有另外的生命存在。那些离去的人,也许去了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空间,他们在以另外的方式与我们沟通,谁敢说不是这样呢?因为死去的人,也会托梦给你,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一直在想,人没了以后,是不是真在另外的空间存在呢?所以每当有消息称发现了第几空间,或者说灵魂有重量的时候,我总是无限好奇;我想如果能经过科学的证明,真有人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灵魂真的有极其微弱的重量的话,那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的小说偏于现实主义的很多,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些读者比较喜欢的作品,像我刚才谈到的《白雪的墓园》《亲亲土豆》《伪满洲国》《白银那》等等。但我也写了一些超验的作品,我这里想到的有《向着白夜旅行》。还有就是《逆行精灵》《朋友们来看雪吧》《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旅人》等。我在这里以一篇小说为例,来谈我为什么会写超验的东西。
2000年的时候,我们经由爱尔兰去挪威访问,当时是王蒙作为团长,也曾来你们这儿驻校的王安忆女士也同行,还有冯骥才、刘恒等一批作家。我们到挪威去了卑尔根。卑尔根大家都知道,这是挪威最著名的作曲家格里格的故乡,格里格改编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组曲中比较著名的是《晨景》。我们去格里格的故居访问,他的故居面朝大海。接待方给我们代表团请来了一个钢琴演奏者,演奏类似于《培尔·金特》组曲里一些比较经典的《晨景》《索尔维格之歌》等曲子。钢琴演奏是在厅里进行的,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台,这个露台面朝大海。露台是没人的,那天又没很大的风,可是在演奏的时候,我看到厅里通向露台的那个门,一会儿就“吱吱”地在响,然后就开了。门开了我就很好奇,我悄悄过去看,唉,并没有人啊。我就把门关上,可是关上以后,不一会儿它又慢慢地开了,好像背后有个重要人物要出场一样。我对冯骥才说,我怎么觉得是格里格想听他自己的曲子,所以他才从露台推门而入呢。门开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我相信他来了。这种感觉真是很奇妙,我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冯骥才也鼓励我,所以回来后我就写了《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格里格故居
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现实的作品,但这里面也有超验的东西。比如说我写到了那个萨满,她每救别人一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玄妙?这是不是超验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这情节是真实的。我还记得《百年孤独》里写的有些情节也是超验的,在一个部落,那些没见过磁铁的人们,突然有一天发现谁拖着一块磁铁在走——马尔克斯描写得太精彩了,他写磁铁所经之处,家里的锅呀什么的铁器,都跟在后面“嗖嗖”地走,平时那些针之类的找不到的可以被磁铁吸引的东西,突然全都现身了。这些东西在跟着一块磁铁走。你能相信这样的细节吗?它在科学上是对的,但也运用了超验的艺术手法。对于文学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超验,这都是一个作家真实心灵的写照,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谁能说现实生活就一定是日升月落,而没有灵魂出窍的时刻呢?它一定在静悄悄笼罩着我们。
5女作家与女性形象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我作品的研讨会,有一些批评家到场,其中有批评家在谈我作品的时候说,迟子建的作品虽然好,但是女性色彩不足,写个人化的东西太少。我是尊重所有善意的批评的,因为好的批评,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及时的提醒,是一种有力的鞭策。但是对这个批评,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十七八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女性观》,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未变。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光明,各自照耀不同的天空,不可能谁取代谁,也别指望谁打倒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大多数的女性是会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不管现实多么严酷,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这就是我作品中的“暖”吧。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也是一种宗教情怀。
对于文学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超验,这都是一个作家真实心灵的写照,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谁能说现实生活就一定是日升月落,而没有灵魂出窍的时刻呢?
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而任何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男作家的写作难道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吗? 你说曹雪芹、蒲松龄、冯梦龙的写作,哪一个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呢? 来过你们这里驻校的男作家,韩少功、张炜、阿来、苏童、格非、毕飞宇,他们的写作太不一样了,是不是?苏童和毕飞宇还同在南京,可是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各具风采?也正是这些差异,他们才成就了自己。还有,为什么批评家喜欢在“女”字上做文章? 强调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强调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其实还是有封建的那些东西,似乎女性就是被“看”的。所以我是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比如说王安忆、铁凝、方方,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你能看出它们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
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也有精彩之作。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如果为迎合潮流,有意为之,那就是看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牢笼。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有精神上真正的独立。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
从自然属性来说,女性有善良、隐忍的性别特征,而且热爱大自然,对充满灵性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所以女性成为作家———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但我也承认,女性成为作家,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女巫多,男巫少。而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巫气”的。
这些年的文艺作品,尤其是看到一些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我有时真是失望,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当然这里有社会拜金主义之风愈演愈烈的因素,让这样的女性形象大行其道。前天我给本科生上课谈到了元曲,关汉卿的戏剧,比如说《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汉宫秋》,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位置。她们尽管在生活当中受到了爱情的压迫,她们最后的选择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生活,而没有那么物质地屈从于这些剧里的官吏。再比如说像《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尤三姐、晴雯,甚至黛玉———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虽然不排除有封建的因素,但一种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绎的那部著名的电影《苏菲的选择》,苏菲面临的选择是什么? 在纳粹集中营中,让她交出两个孩子,只能存活一个。苏菲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情节大家都知道,她后来把女孩送出去了,让她赴死,把男孩留下了;战后她特别地痛苦,剧里写到她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痛苦的情感纠葛。现在很多人把它分析为“苏菲要把女孩儿献出去,是因为男尊女卑”。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苏菲身为女性,她把女儿献出去,更主要的是她知道,女性是真正富有牺牲精神的,她很自然地把女儿献出去了,而不是觉得女性是低贱的。我认为是苏菲天性里的牺牲精神,让她认为她的女儿应该也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这种女性人物形象太伟大了。

△电影《苏菲的选择》
关于对女性的认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前不久我发了一条微博,记得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时,有个奥地利作家在讨论会上说,他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写爱情诗,因为女性喜欢爱情诗,后来他说真正有了女人之后,他就写死亡了。还有一个尼泊尔女作家,她在谴责他们国家议会里面都是长胡子的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占的席位太少了。我觉得政治呢,可能这是我的偏见,我觉得这真就是一场游戏,是男人之间的一个游戏;女性更接近大自然和天性当中的美好,不太适宜加入这样的游戏。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我很喜欢她的一些批评文章。她有两部著作,我觉得做批评的人,尤其是对女性文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可以去读一下,一个是《狂欢的女神》,一个是《彷徨的娜拉》,娜拉就是易 卜生的名剧里出走的那个。《狂欢的女神》里面,她就写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女艺术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一个那么不屈的女性,我去墨西哥的时候参观过弗里达·卡洛的画室,就是蓝屋。刘剑梅教授认为在当代,当代女性的物质化会妨碍她们精神上的成长,影响她们的高度。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作家和女性文学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小天地,一定要视野开阔一点。
回到这个问题开头的话题,我当时特别想跟提出问题的批评家说,我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的萨满,明知道救别人一个孩子,要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不断地救,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孩子,这种女性像圣母一样,这不是女性意识吗?我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逝川》,写一个接生婆,一个老女人,孤苦一生守着一条江,也是那么坚强的一个女性。我还有一个短篇《亲亲土豆》,写丈夫得了癌症以后,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最后她给丈夫搭了一个土豆坟,她离开那座坟的时候,一个土豆骨碌碌地滚下来,这个寡妇往前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一句:“还跟我的脚呀?”当然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的伤痛,这种自尊,难道不是女性意识吗?一个作家的心扉和她笔下的人物共融了,只不过她不歇斯底里,就缺乏女性意识吗? 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狭隘地定义女性的形象不好。但我同时也要强调,文学史上确实也有女作家写“私小说”,完全写个人经历和情怀的,也有写得很棒的,但它的比例是极少的。
6“走出去”与“走回来”
“走出去”是中国文学向外走,我们知道莫言走得最好也最远,走到了斯德哥尔摩的荣誉殿堂。当然“走出去”特别重要,但是“走回来”也很重要。
我以一个小故事开始吧。2012年的时候举办伦敦书展,那年的春天,我从老家坐火车回哈尔滨。插个话吧,我挺爱写火车的,因为我的故乡偏僻,火车一直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我经常在路上折腾一两天,才能到家。那天我在火车上遇见一对老夫妻,老头是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他老伴跟我聊了一些他发病时的细节,比如他晚上时喜欢卷起行李,说他要出发了,还有的时候他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的,觉得自己特别美,有些被我写到《群山之巅》 中那个患了阿尔兹海默病的安玉顺身上了。我在火车上遇见的这个老头特别能吃鸡蛋,一会儿吃一个,他老伴就给他剥一个。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她说我们要去按手印,从大兴安岭经由哈尔滨,去老头原来的工作单位,好像是哪个地方的一个粮库,去按手印;你要是今年不按手印,你的退休金就会停发了。我说这个太不人性了。她说:“你不按手印,公家认为你这个人有可能死亡了。”我说:“那一定要见到活生生的?如果是瘫痪了或者其他情况,那怎么按?”她说:“那没办法,你就得领着他去。”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就在同年,因为要去参加伦敦书展,我去驻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按手印。只为按一个签证的手印,我从哈尔滨至北京,来去两天,非常辛苦。而没有手印作为证据,就无法签证,也让我心情沉重。可是到了书展开幕的时候,我在进入伦敦境内的时候,我们代表团的人都进去了,我却被拦住了。我英文不好,海关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比比画画对我说,我明白了大概,就是我入境的手印和我当年留在北京的手印不符,难道我是女巫,“我”居然不是我了。你说我怎么办?好在我们代表团是参加伦敦书展的,照片什么的都对上了,尽管僵持了很久,最后还是放我入境。看来这样的手印制造的麻烦,不要以为只有在中国存在,在世界上依然存在。
我今年8月在长春参加国际汉学家大会,见到了一些汉学家、翻译家,也见到了瑞典的陈安娜,她刚好要翻译我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她翻译作品也要采风,会后她和丈夫万之先生去了内蒙古我描写的这个部落,做了实地采访。她真是很敬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有一个发言叫《樊篱外的青草》,我说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樊篱一直存在。消除文化上的樊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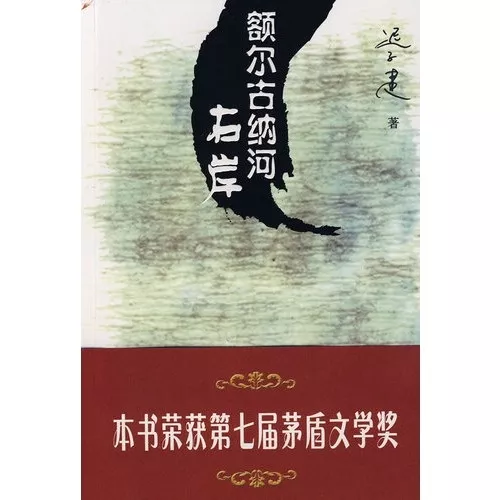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这种“走出去”有时也容易跟风。李安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导演,大家知道他拍了著名的《断背山》,它是根据美国女作家安妮·普鲁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那一时期这样的电影太多了,2005年我和刘恒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时,看过几部类似片子。爱荷华大学有一个免费放映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放映各个国家的电影,作为资料片。刘恒是搞电影的,他给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都做过编剧。我不会说英语,但电影打的英文字幕,我还能看懂一些,所以我和刘恒去看电影的时候,偶尔兼做他的翻译,讲讲剧情。我们俩那时期看的片子,我后来查了一下日记,澳大利亚的、法国的都是同性恋题材的,基本刘恒一看开头又是这样的,他就呼呼大睡。有时候醒来的一瞬,他会看看银幕嘟囔一句,又是这个呀。商业和文学在融合的时候,一个作品成功了,它能带来好的一面,当然也可以带来不好的一面。盲目跟风是对艺术最大的不敬和伤害。所以任何一种艺术的发展与创新,需要艺术实践者有开放的视野、包容的心态、独辟蹊径的勇气,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走回来”,也就是珍视我们的内心生活,珍视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珍视我们脚踏土地的丰饶与贫瘠,阳光与阴影,我们才不至于堕入虚浮的泥潭。

△电影《断背山》
过于追随国际风,文学可能失去自我,而一味地展览黑暗与丑陋,无视我们民间存在的善良与美,也是一种投机和不自信的表现。同样,无视于我们所体味到的寒凉,生硬地把五味杂陈的生活兑成一锅甜粥,也是脆弱的表现。所以我说,无论“走出去”还是“走回来”,都要警惕文化极端现象的出现。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作家都要警醒,你一定要脚踏实地,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一定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跟风,这样我们的艺术才能立得住。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民间神话与原始宗教,大自然与命运感,苍凉与温暖,现实与超验,女作家与女性形象,“走出去”与“走回来”,我简要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写作之路,当然也是我文学的“求经之路”。其中有我对自己作品的回顾,也有我的一些文学观,在理解上可能比较粗浅,不够深入。我也想引出这些话题,由大家去丰富和完善这些话题的讨论。
再回到 《大唐玄奘》 这部电影,玄奘翻译的《心经》流传于世,对佛教的贡献巨大。他走了两条路,一条是现实的路,玄奘走过的路往返数万里,在他那个年代走了几年。他还有一条精神之路,那就是佛学之路,也就是求经之路。他求来的经,至今万人传诵。可是文学的取经却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每个作家,各念各的经。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经”,会不会对你们有一点点的启发。对于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我走过的现实的取经路,就是我刚才回顾的,我是从大兴安岭开始到哈尔滨,又到了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不管经历了多少山川河流,最爱的还是故乡的山水;但我写作的“求经之路”,起起伏伏的。因为在我眼里,没有完美的写作,写作也是没有尽头的。这也就意味着,写作的求经之路无限漫长,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壮阔所在。这样的路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性,是艰难之路,同时也是灿烂之路。对于一个生长在极北之地的人,一个在雪地里打滚,经历了几十年严寒摧打的人,一个开始不断生长白发的50多岁的人,筋骨还算强健吧! 我愿意在这样的路上倾听风雨,迎接未知的暴风雪,继续我文学的“求经之路”。
原载《文学报》2017年3月17日
本文系迟子建2016年11月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