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雪窗帘
迟子建 经典短篇小说选读 2017-03-14



作家简介
迟子建,女,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主席团成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一级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四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逝川》《雾月牛栏》《清水洗尘》,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的《迟子建作品精华》。
所获荣誉:《雾月牛栏》曾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清水洗尘》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迟子建是当今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她是唯一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两次获得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在所有这些奖项中,包括了散文奖、中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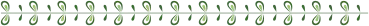

雪 窗 帘

迟子建


有一幅窗帘,是由霜雪凝结而成的,这些年来一直掩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每到年味渐浓的时候,它就耸动着,浮现在我眼前。我曾几次提起笔来,想把这幅雪窗帘挂出来,然而它最终还是融化在世俗生活的浊流中了。
我以为它就此消失了,谁知这两年它又悄悄地现出形影了。它孤寂地待在我心中的一角,发出明亮而又冰冷的寒光,让我警醒。我这才明白,真正的霜雪如果不用心去暖化它,是送不走的。
一进腊月,火车站就像要上演一部最叫座的故事片似的,拥挤得要爆棚。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面色焦灼的购票者,站台上是黑压压的等候上车的人。广播里一会儿传来某列新增列车的开车时刻,一会儿又传出某一列车的晚点通知。大多数的旅客都是为了赶着回家过年的。于是,候车厅的卫生间由于被人频繁地使用而散发出刺鼻的尿骚气,每一条长椅上都坐满了面色疲惫的旅人。过道上遗弃着烟蒂、果皮和纸屑,清扫员对着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着小孩撒尿的妇女和随便把烟灰磕在地上的男人常常发出斥责声。火车站在这时节比农贸市场的早市还要庸碌和零乱。它就像一棵被千千万万人觊觎着的圣诞树,所有的人都想在它身上挂上一件礼物,结果使它不堪重负,呈现着倾颓的趋势,发出沉重的喘息声。
那个时候的火车票还不像今天这么好买。如果你不能起大早去排队的话,要想购得一张卧铺票,除了从票贩子手中买高价票外,就只有托铁路的熟人了。好在我有一个这方面的朋友,就免除了购票的劳苦。
我回家过年,大抵是在小年前后。因为腊月二十五是给父亲上坟的日子,我必须在此前赶回家中。
我记得那一年是过小年的那天动身的。走前我把家门贴上了“福”字。我不希望除夕时别人家的门前要春联有春联,要灯笼有灯笼,而我的门前却毫无喜气,所以总是提前张贴含有吉祥意味的“福”字。
火车站的乱自不用说了,当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提着沉重的旅行包从蜂拥的人丛中艰难地挤上火车时,对年不由生起了一种怨恨。我觉得年是个让人劳神费力的东西,是头捉弄人的怪兽,是个只能让人围着它转的自私鬼。
安顿好行李,气也喘得均匀了,火车缓缓离开了站台。天已黑了,列车的玻璃窗上蒙着霜花。有淘气的小孩子为了看窗外的风景,就不停地用手指甲刮着霜花,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给鱼剐鳞的声音。
一个烫了满头鬈发的女列车员捧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召唤旅客换卧铺票。大家把一张张客票交到她手中,换来一枚枚长方形的铁牌。她把票依次插在黑皮包中,那些相挨着的车票看上去就像竖立在公墓里的一排格式化的白色墓碑。她带着一股守墓人惯有的漠然神情,离开了车厢。
大约半小时后,列车员又来了,她在车厢的过道里一遍一遍地吆喝:“还有没有没换票的?!”见没有旅客回答,她就夹着皮包走了。
我吃了一个橘子,打算到盥洗室刷刷牙,就到铺位休息。然而盥洗室已经被无座的乘客给占领了,只好悻悻地回来,把牙具塞回旅行袋里,爬到中铺去休息。我讨厌乘火车时睡下铺,旅客把它当作自家的炕头理直气壮地坐着且不说,有的人还坐在那里就着油腻的烧鸡和猪手喝着小酒,油污会弄到床单上。还有的女人喜欢吃瓜子,将瓜子皮嗑得四处飞扬。更有甚者,将喝得黏糊糊的果汁撒在了上面。你躺在被形形色色的人坐过而被弄得污渍斑斑的铺位上,就有一种睡在猪窝的感觉。
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翻开一本杂志。才看了一会儿,就听对面的下铺传来了一阵争吵声。我连忙探出头去望。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我上车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看上去六十左右,穿灰棉袄,扎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带着一只篮子。先前那篮子是放在茶桌上的,后来陆续到来的其他乘客要往上面放水果和茶杯,嫌其碍事,就把那篮子放到茶桌下面。她似乎怕别人不小心踢着那篮子,时常地往下望上几眼。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她的自言自语声曾引得我忍不住想笑。比如她轻声嘀咕:“这荒郊野外的还亮着灯,这不是给鬼照亮的嘛”;还有:“哦,这电线杆子可真多啊,隔不远就一个,隔不远就一个。这电是从哪里走的呢?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到它们闪光?”
与这老女人吵嘴的,是一个穿着皮夹克的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他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
老女人说:“这是我的铺,你咋让我走呢?”
胖男人说:“什么你的铺,这是我的铺,我刚刚补的铺!”
老女人恍然大悟地说:“敢情这是快过年了人太多,火车上让两个人睡一个铺啊?”围观的人发出阵阵笑声。
胖男人不耐烦地说:“谁跟你个老太太睡一个铺?你是哪张铺的,就快回哪儿去!”
可老女人认定了这男人要跟她睡一个铺,她问:“你这是要睡上半宿了?”
那男人没有好气地说:“我上半宿下半宿都睡!”
老女人“哎呀哎呀”地叫着,似乎在懊恼自己怎么碰上这么一个合铺者。
这时一个吸着烟的男人提醒老女人:“你再看看你的票,是不是这个铺的?火车是不可能卖重铺的啊!”
还有的人说:“你是不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假票啊?”
老女人很委屈地说:“这票不能有假,我闺女早晨四点钟上火车站排队给我买的。”说着,她起了一下身,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千真万确,可是,她没有跟列车员换票,所以她的铺被当做空铺卖给了别人!
大家把她犯的过失说给她听时,她几乎要急哭了。她说:“我以前坐火车时都是自己拿着票,乘警查票时就把它掏出来。哪能买了票又交给人家呢!”
酒气熏天的胖男人用轻蔑的语气说:“连火车都不会坐,出的什么门呢!”
她申辩道:“谁说我不会坐火车?我这辈子坐了有十来回了呢!”她的话又引来一串笑声。
那个吸烟的男人对新来的铺位主人说:“哎,跟老太太说话客气点,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出趟门容易吗?”
“你想当雷锋是不是?那行啊,你把自己的铺让给老太婆睡不就行了么!”胖男人咄咄逼人地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吸烟者掐灭了烟,跃跃欲试地朝胖男人挥舞了一下胳膊。
“怎么着?是不是过年回家没什么带的,想挂点彩回去呀?!”胖男人脱下皮夹克,将它甩在铺上,挑衅说:“过来呀,老子成全你!”
“你们可别因为我打架啊,这大过年的,把谁打了都不好。”老女人起身拉住胖男人的毛衣袖口说。
吸烟者大约也不想无端惹麻烦,说着“我找列车员来给评评理”,转身朝乘务员室走去。
很快,那个满头鬈发的列车员过来了。
她听明了事情原委后,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我一遍又一遍地喊让乘客换票,嗓子都要喊破了,大家都能证明吧?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属于人家的了。”她指了指胖男人。
老女人可怜巴巴地说:“我以前没有坐过能睡人的火车,我坐的都是座儿,哪知道还得换票呢。”她说:“那我这票就等于作废了?”
“作废倒不至于,不过现在卧铺都满员了,你只能坐着了。”
“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
“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老女人落下了眼泪,她独自嘟囔着,埋怨女儿刚才送她上车时,没有告诉她换票的事。她说早知如此,还不如坐硬座呢!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懊恼万分地提着篮子来到边座上。她看了一眼那贴着车厢壁立着的座儿,说:“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七仙女的屁股也坐不稳它呀!”她的话又引来一片笑声。
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要是一起身,它就自动立起来了!”
老女人把篮子放到窄窄的桌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用手护着那只篮子。那篮子有三分之一探出桌面,很容易被过往的行人给刮到地上。有人就劝她说:“你把篮子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吧,那里宽绰。”
她没有作声,而是满怀忧伤地看着胖男人展开被子,他脱下鞋子和棉裤,一头钻进了被窝。人们都对他投以鄙夷的目光,不过再没有人说什么。
当列车员要离开的时候,老女人问她:“我这票是能睡人的,现在成了不睡人的了,能不能把钱给我找回来呀?我闺女不是等于白白花了冤枉钱么,那可不是小钱,得好几十块呢!要是买一袋米的话,够我吃多半年的了!”
列车员似有些不耐烦地说:“行行,一会儿我给你问问车长去!”
“什么事都得当官的做主呀?”她嘟囔了一句。
列车员不再理睬她,她对着那些意犹未尽的围观者说:“有什么好看的,都回自己的铺位上吧。我告诉你们,九点一过就熄灯了,你们提前把被子铺好了,别到时候抓瞎!”说完,她昂头挺胸地带着一种解决了棘手问题的自豪感走了。
胖男人已经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先前与胖男人险些大打出手的那个男人,用嘴努了一下那像死猪一样沉睡着的胖男人说:“哎,就是不愿意和他一般见识吧!这要是放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不把他打成豁牙才怪呢!喝点狗尿,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发完牢骚,很同情地看了老女人一眼,问她:“大娘,你要水喝吗?”
老女人说:“我坐火车怕上厕所,火车晃悠着,我怎么也撒不出尿来,我就忍着,一口水也不喝。”
那男人叹了一口气,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去睡得了。”
老女人说:“不用,你们年轻人觉大,你去睡吧。”
这时从靠近门口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穿驼色毛衣的男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左右了,戴一副老花镜,手中提着一份报纸。他对那个让铺的年轻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那年轻人听了老人的话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万一磕着碰着可怎么办?”
“我天天早晨都打太极拳,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别说爬个上铺了,就是让我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保证着。
“哎,那可不行,万一你有个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他急忙说自己拉肚子,得赶快上厕所,逃之夭夭。
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不诚心让铺,还装什么好心人啊。”说完,他提着报纸回自己的铺位了。
让铺的事情就此结束了。
火车“咣──嚓──咣──嚓──”地行驶着,随着夜色加深,寒冷愈浓,车窗上的霜花面积越来越大,几乎要满窗了。老女人坐在那里,就像镶在白色镜框里的一幅肖像画,陈旧、暗淡,弥漫着一股哀愁的气息。有个抱小孩的妇女走过来和她搭话,她对着怀中吃着虾条的小女孩说:“给奶奶吃个虾条吧?”小女孩耸着身子蹬着腿,发出要被人给抢了东西的那种尖叫声。妇女觉得脸上很没面子,她斥责小女孩说:“现在就吃独食,将来还能是个孝顺孩子?我可真是白白养了你!”小女孩受了奚落,愈发地任性了,她挣扎着,腿扫着了老女人的篮子。
老女人声音嘶哑地说:“小祖宗,你可不能踢着这篮子,这里面可是装着我老头爱吃的东西!他这个人干净,脏了的东西他可是不碰!”
只一会儿的工夫,老女人的嗓子就哑了。仿佛车厢里的烟气和尘埃全都拥进了她的口腔。妇女气恼地把小女孩放到地上,说:“你不听妈的话,我可把你扔到火车下边去了,外面荒郊野岭的,到处都是狼,我让狼把你给吃了!”
小女孩吓得呜呜地哭了。她大约觉得让狼吃了自己,不如让老女人吃虾条合算,就把虾条递给老女人,抽抽噎噎地说:“奶奶──吃──奶奶──吃──”,妇女这才仿佛又把丢了的面子捡了回来似的,面上现出温和的笑容。
老女人对小女孩说:“奶奶不吃虾条,你自己吃吧,啊?”她又转而对妇女说:“小孩子胆小,可别吓唬她。你给她吓丢了魂,还得给她叫魂。”
火车放慢了速度,大约前方有车站要停了。
妇女问老女人:“你这是去哪里啊?”
“到小闺女家过年去。”她说:“我年年都在大闺女家过年,小的说想我,写了好几封信催我去。我一想都好几年没有在小闺女家过年了,再说我老头埋在那里,我也想看看他去。”
“那这篮子里装的都是上坟的东西啊?”妇女吃惊地问,并且下意识地把小女孩揽到怀中,仿佛那篮子里藏着鬼,会突如其来地蹦出来伤害人似的。
“哦,我打城里给他买了松仁小肚和皮蛋,还给他蒸了块我腌的咸肉,带了两瓶高粱小烧酒,这些都是他最得意的。”她的话音刚落,火车就“咣当”地剧烈抖动了一下,停在一个站台上。老女人也抖动了一下,她死死地护着那只篮子,生怕它被晃到地上。站台上的灯光把玻璃窗映得一片橘黄色,老女人的脸也跟着有了几分光彩。
有两个上车的人来到卧铺车厢。他们的身上落着星星点点的还没有来得及融化的雪花。老女人望了一眼新乘客,叹了口气说:“这里原来下着雪啊。”
大约五分钟后,火车又喘了一口粗气,颤着身子向前走了。玻璃窗忽明忽暗的,很快,它又恢复以前的模样了,是那种被车厢的灯光所笼罩着的灰白。
妇女抱起小女孩,对老女人同情地说:“我带着孩子睡在下铺,可是小孩子离不开我,不认别人,我要是在家,她奶奶搂着她睡都不行。你说她要是像别的小孩子不认生的话,我就让你和她睡一个铺了。”
小女孩一听说妈妈有让她和老女人睡的打算,就像让她和狼外婆睡似的,又开始闹了。她揪着妈妈的头发,使劲地蹬腿。妇女呵斥她道:“怎么这么没礼貌?今年过年是不是不想要新衣裳穿了?”
小女孩委屈地哇哇哭了。妇女只能抱着她回到铺位上。
到了快闭灯的时刻,过道的行人就多了起来,人们大都是上厕所的,想解个手后,睡一夜的安稳觉。厕所外面就排了不少人。人们经过老女人身边时,总要同情地看她一眼。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找车长去,说是她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就是再有过错的话,他们也应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给她再安排一个铺位。老女人听不懂“人道主义”这个词,她张口结舌地问:“让我找'人道'给出主意?'人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呀?”她的话又激荡起一片笑声。她显然意识到自己说了可笑的话,她的脸微微红了。这时正赶上列车员来拉车窗帘,她就转而问列车员:“闺女,你跟当官的说了么?我的票钱能不能给我找回来呀?”
列车员打了一个呵欠,说:“我给您说了,车长说不行。”
“怎么就不行啊?”老女人说,“我花的是躺着的钱,可我现在是坐着!还弄这么个窄巴座让我坐,真板身子呀。”
“您那票又不是在我们火车上买的,您是在车站买的,我们把钱找给您,我们不是有损失么?”列车员说。
“敢情你们和车站不是一家的啊?”老女人很失望地说。
“现在除了钱和钱是一家的,谁跟谁还是一家啊。”列车员笑着说。
老女人不再说什么。不过列车员把她身边的那面窗户拉上窗帘时,老女人又把它打开了。她说:“我坐着没意思,让我看看风景还不行么?”
“外面黑糊糊的,有什么看头啊?再说了,一窗的霜雪,你能看清什么呀!”列车员嘟囔着,不过她尊重了老女人的意愿,没有再动那块窗帘。
老女人护着的那只篮子,上面蒙了一块蓝布,它就像剧场垂着的幕布似的,让人觉得它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戏剧。我想她不像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不然她不会呈现如此天真、愚钝的情态。一问,果然如此。她说她大闺女家住在农村,女儿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大城市换车,特意送她来的。她们住在旅馆的地下室里,女儿为了给她买票,几乎一夜都没睡好。
她很沮丧地对我说:“早知道这样,真不应该买躺铺呀!闺女买时遭着罪,我在车上也遭着罪。遭罪倒也罢了,还花了冤枉钱!”
我犹豫了一下,轻声对她说:“要不你和我睡一个铺,你睡前半宿?”
“姑娘,不用你费心了,我能坐着,不就是一宿吗?”
先前我还有些紧张,她的话竟使我一阵轻松。我说:“要不我睡前半宿,后半宿你睡?”
老女人说:“我年纪大了,觉少多了,睡不睡都那么回事。我早年在生产队干活时,要是赶上秋收时天气不好,为了往回抢收庄稼,我三天三夜都没合过眼呢!”她叹息了一声,说:“不过收庄稼时在野外,有风,人能四处走动,不觉得憋屈。我宁肯在庄稼地里熬十宿,也不愿意在这里熬一宿!”
我还想和她说些什么,车厢突然暗了下来。是九点钟了。顶棚的大灯熄灭之后,只有过道上的几盏壁灯散发着微弱的光晕。先前还有人关注的老女人,如今就像闭店后无人再看的商场橱窗里的摆设一样,再无人理睬了。不久,各个铺位传来高低起伏的鼾声。我睡不着,不时地翻身探头看一眼老女人,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样子就像一个用心听讲的规规矩矩的学生。她的双手依然放到篮子上,仿佛那就是她的护身符一样。渐渐地,我疲倦了,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梦乡。然而我睡得并不塌实,时睡时醒。睡着的一刻又总是被噩梦缠绕着,一会梦见火车出轨了,车厢里血肉横飞,一片惨叫声;一会又梦见父亲站在我的铺位前用皮鞭抽打我,骂我是不肖之人;一会又梦见一条狗把我追到一条死胡同,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我在惊醒的一刻,总要惯例地看一眼老女人,她已经不胜疲倦地把头伏在篮子上了。她伏在篮子上的姿态很像一只南瓜卧在丰盈的叶片上,我很想下去看看她,但终于是自私和疲倦占了上风,尽管心存挂碍,还是躺在铺上,复又迷迷糊糊地睡去。
我终于在黎明前连续睡了三四个小时。当我醒来的时候,能听见有人在放屁,有人在磨牙。对面下铺那个补了老女人铺位的男人,他的呼噜简直可以用山呼海啸来形容。老女人已经醒了,她依然把手搭在篮子上,端正地坐着。我想起梦中父亲对我的鞭打,不由得心生羞愧。我跳下中铺,对她说:“大娘,你到我的铺上休息一会儿吧,篮子我帮您看着。”
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快到站了,不麻烦你了。”她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喉咙那里热辣辣的,仿佛着了火,就打开一瓶矿泉水,“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一瓶水喝光,依然觉得火烧火燎的。
天色逐渐地亮了。有三三两两早起的旅客晃晃悠悠地去厕所了。车窗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积满了厚厚的霜雪,所以即使它没有挂窗帘,却仿佛挂了似的,那是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老女人又开始像她上车时一样用指甲去刮霜花了,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刀在割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阵阵疼痛。终于,她划开了一道明亮的玻璃本色,它微微弯曲着,就像一尾鱼苗。橘黄的晨光就透过它闪现在我面前。它那么的活泼生动,那么的凄艳动人!它像被秋风吹黄的一片柳叶,带给我对韶华易逝的伤感;它又像一把要割掉杂草的镰刀,使满心芜杂的我伏下头来。
乘务员睡眼惺忪地出现在车厢了。她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地吆喝:“起来了,起来了,还睡的旅客起来了!”尽管离终点站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多数的乘客还在睡梦中,但她要提前整理床铺,打扫卫生。我最厌烦的就是这个时刻了。人们被迫给驱赶到过道上,乘务员无所顾忌地把每一个铺位的床单抖来抖去的,弄得灰尘飞扬。老女人原本端正地坐着,后来听见乘务员在发牢骚,就侧过身抬头去望。原来,有人不慎把茶水洒在了床单上,她气急败坏地说:“这要是你们自己家的床单,你们能这么不在乎吗?敢情公家的床单就是你们揩屁股的纸呀!”那个弄污了床单的乘客怕罚款,赶紧溜到厕所去了。当乘务员气鼓鼓地从铺上跳下来时,老女人对她说:“姑娘,床单弄上茶能洗净,你把那块地方洇湿了,从锅底抓把灰敷上,隔个十分八分钟地去揉搓,保准能洗透亮!”乘务员瞟了一眼老女人,没有好气地说:“啊,我洗个床单还得拿到你们农村去用锅底灰,我傻不傻呀!”老女人遭到奚落后抽了一下嘴角,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她转回身,把目光放到窗外了。
那个占了老女人铺的胖男人已经起来了。他穿戴好后见许多人无声地望着自己,把他当个贼看待,觉得有些不自在,就起身去车厢连接处抽烟去了。为老女人打抱不平的那个睡在上铺的男人也起来了,他从旅行袋里掏出一个橘子给老女人,说:“吃个橘子解解渴吧。”老女人谢绝了,她说自己吃橘子生口疮。那人只得把橘子讪讪地收回去。抱小孩的妇女也过来了,她对老女人满怀歉意地说:“原想着和孩子早点起来让你去躺躺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唉,人一坐火车就乏得很。”说完,她还真的打了一个呵欠。这时,又有两三个旅客来对她表示关心,他们都说愿意让她去自己的铺位躺一会。老女人回答大家的话总是一个内容:“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要到站了,不用了。"
火车走得慢慢吞吞的,前方就要到青杨树车站了,那是老女人下车的地方。当车身摇晃着逐渐停稳,她起身的一瞬,那座位自动弹了起来,把她吓得“哎哟哎哟”地连叫了几声,这也是她给旅客带来的最后一次欢笑。
人们笑着送她下车。她大约由于坐了一夜腿已经麻木了,走得很迟钝,踉跄着,像是拼尽全力在拖着两条腿走。她胳膊挎着的那只篮子,也跟着她踉跄着。她离开火车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幸亏昨夜我没起身,要是那座儿一离屁股立了起来,我又不会把它落下来,还不得站一宿呀。”
我坐在老女人坐过的边座上,透过她刮开的那道明净的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站台。她终于下了火车,她把蓝围巾系到头上了,看起来外面很冷。她缩着身子在站台上张望着,终于有个年轻女人朝她跑来。我想看看她见了亲人是否会因为委屈而哭泣,可是火车启动了,我们向终点站驶去了,她的身影很快就被甩在车后,甩在一片苍茫的白雪中,模糊了,不见了。而我所坐的座位,还残存着她的体温,那么的热,可我却觉得周身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照例在每年的腊月乘火车回家过年。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刻。兴许是对那老女人所欠下的愧疚之情未得偿还的缘故吧,这两年我登上火车,她的身影就会悄然浮现在脑海中。我仿佛又看见她悄无声息地坐在边座上,她的头嵌在弥漫着霜雪的车窗里,看上去就像悬挂在列车上的一幅永恒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