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星期天
迟子建 经典短篇小说选读 2017-1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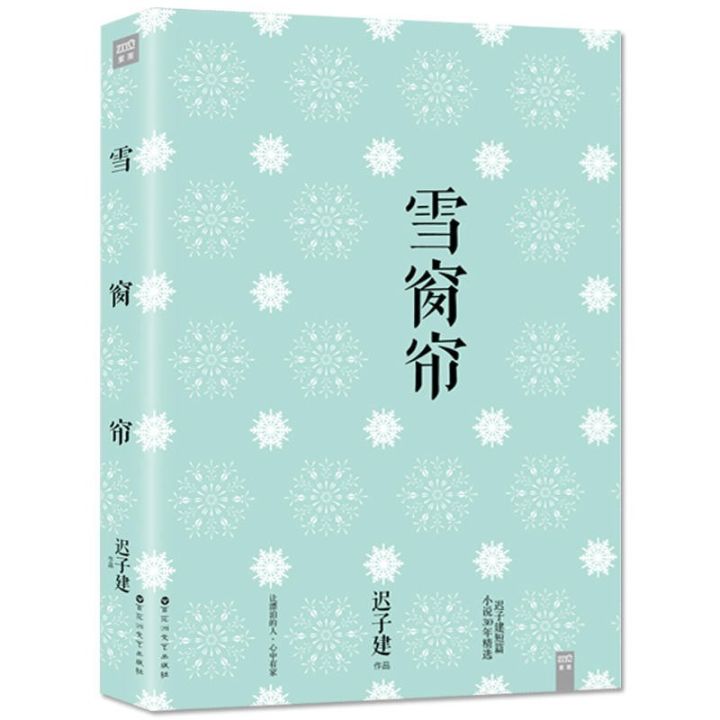
这简直是太美太妙的一个春天。风象少女的脸一样滑腻,蹭得人心里暖洋洋的。毛毛狗喷出了黄灿灿的花儿,绒球一样,毛嘟嘟的;这时,松树才羞羞答答地咕哝出淡绿的叶子,文文静静地看着先它而开的、满山满坡红红火火的达子香花。
今天是星期天,又逢上了这么个好天气,当然要尽兴地玩了。
“你穿上那件红夹克,别天天总是鹅黄的。”
“我不喜欢。”我毫不客气地将韦佳给我买的红夹克衫甩到一边。
“女为悦已者容嘛!”他有些不高兴了,然而还是扮出一副洒脱不俗的样子,开了句自以为雅的玩笑。
“十分抱歉。我不是你的时装模特儿。”
“你这人怎么……”
“怎么?我跟你说过了,这个星期天,少劳尊驾,我自己出去玩——自己!懂吗?”
我几乎要哭了。和韦佳相爱一年了,不知为什么,有时总觉得自己成了他的附属品。我想做什么,他都要插手,而且,一定要按他的意愿去行事。连买发夹,也要由他来选择颜色、式样、这真叫人受不了。
“又耍小孩子脾气了。”他软了,把胳膊搭在我肩上,抚弄着我的头发,轻轻地说,“穿鹅黄就鹅黄吧。”
我不知如何是好地望他一会儿,喝了杯奶粉,嚼了几块饼干,竟自收拾自己的东西。
“你应该背黑皮包。白色的春天用太淡。”
真是十恶不赦,不可救药了。我把白色皮包往肩上一搭:“对不起,我们今天就分手吧。”
“分手就分手呗,我再找个比你温柔美丽的。”
“我再找个心胸豁达,不干涉我自由的。”
我动了真气,没有理他,一个人推开门跑了。韦佳在后面柔声细语的喊声,在我听来比猫叫都难听。我不愿意回头望他那张比我还要白净的脸。
公共汽车救了我的驾。刚跳上去,车就开了。扔下韦佳一人怪模怪样的干着急,我心底禁不住一阵快活。
绝对不能让他再跟着我。在龙津市场那站,我下了车。
新开张的市场挺气派。大门两侧的饮食亭,全都是白铁皮筑成的。我被烤肉的香味所诱惑着,就折身进了一家小店。
已经坐满了人,生意够兴隆的。星期天嘛!
“同志,您请坐。”热情周到的服务员把我让到里面,她与我一样年轻。
“要点什么?“
“两个肉饼,一碗鸡蛋汤。”
“好的。”
好的是好的,然而左右一寻,似乎是没有我的位置。学孔乙己嘛,把汤当做酒,把肉饼当做茴香豆,很快地吃完,很快地走掉。我自以为得到什么妙处,端着碗笑了。
有一个小伙子在打量我。看得出,他是个长得短小精悍的、很机敏聪明的人。这点,从他的眼睛便可看得出来。他的脸是属于北方土地的那种颜色,健康而粗犷。
“你请坐吧。”由于小店的座位是长条凳,所以,凭他的勇气和魄力足以挤出一块能容下我的地方。既然有位置了,我也绝不想学孔乙己。我礼貌地谢谢他,客客气气地坐在那里。真够挤的,他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的身体,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冲进心扉。我想起了韦佳,如果他在这儿,看见我和一个陌生的男人紧紧地坐在一起,一定会故作轻松地冲我讪笑的。
汤和肉饼放在桌上。我的食欲上来了,端起来汤,咕滋咕滋地喝起来。肉饼挺烫,一咬,冒出一汪油,沾得满手皆是。那男青年低低地笑着说:
“你几天没吃东西了?”
“半小时前还在吃。”我侧过头也笑了,望着他棱角分明的脸,“我一见着好吃的,胃就瘪了。”
“好家伙,该把所有的食杂店都装到你肚子里。”
他已经吃完了,正掏出手绢擦嘴和手。不知为什么,我加快了吃的速度,嘴就跟卷扬机一样,嗖嗖嗖几下就吃进另一个饼,而且将碗内的汤底一饮而尽。
“够实惠的。”他又说。
“那当然,挣钱是件太辛苦的事。”我掏出手绢擦嘴。唉,韦佳,又是你换了我的手绢。我喜欢白色的,可你偏偏偷着换上了这块火红的,真让人头痛。刚刚吃饭的兴致彻底给破坏了,我沮丧透了。
“怎么,胃不好受?”
“有点儿。”我想韦佳若在身边,一定会得胜地打个口哨,哼一曲:
我爱你至死不渝,
哪怕海枯石烂;
我爱你天长地久,
千年万载共蝉娟。
我想起了,跟韦佳一起去看电影,每当我旁边坐的是个男的,他一定要与我调换位置。如果他的邻座和我的邻座都是男性,不可调和时,他一定要在电影一开始就把我揽在怀里,生怕谁碰我一指头。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神经质,他回答道:
“世界上好女人可以找到,好男人可就难寻了。你不知道,男人的心呀,都挺野的。”
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男人。可是现在,我跟一个陌生男人这般近于老相识地交往,韦佳若知道不知会怎样嘲弄呢。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觉到了自由,好象刚刚从寂寞的天上跳下来,蹬碎了围住我不撒手的云彩,有一种接近土地的踏实感。
我跟他一起走了,肩并肩的。在别人看来,也许我们就是一对和谐的恋人。这一刻,我忘掉了韦佳。
市场里有一家书摊,我们进去,浏览一番。我买了两本畅销书——《一夜天堂》和《白梦》;他呢,则买了一套连环画册。
我在心里揣摩,他一定是小学文化程度,不然,怎么会买这种画册看呢?他似乎是猜中了我的心思,很莫名其妙地笑了。
人熙熙攘攘的,叫卖声和录音机播放的《阿里巴巴》、《成吉思汗》、《春夜小雨》搅在一块,彼此不相谦让地冲进我的耳膜。有一家音乐茶座吸引了我们。
“想进去吗?“我问。
“可以可以,星期天不就是消遣消遣嘛。“
门票五毛。他掏出一元钱,买来两张,带我进去。五毛钱,包括一碗值五分钱的清茶,以润喉舌。另外的四毛五呢,不过是买来眼福吧,一会儿有京剧清唱,或《红灯记》或《沙家浜》,老旦和青衣的服装扮相不分彼此,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又有自称严凤英徒弟者大唱特唱《女驸马》;一会儿又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子的录音。真是广采博闻,令人应接不暇。他时时扶颏微笑,我亦然。
茶也吃得淡淡,看也看得淡淡,我们都有些兴味索然了。彼此心照不宣地摇头一笑,几乎是同时站起走出这家音乐茶厅,也是同时在走出之后大大地呼吸了一口户外含有阳光的清爽空气。
“真有趣。“他感慨。
“的确有趣。”我答。
又向前走,有个叫卖袜子的拦住我们:
“你们看看,这袜子质量多好,颜色多好,穿着多舒服,买两双吧,穿袜子是不分男女的。”
我哑然失笑。他摆摆手,表示拒绝。那人悻悻然地掉转身边走连嘟哝:
“这小两口够抠的。”
是中午了,我又感觉到饿,肚子在咕咕叫食。于是又进了一家小店,喝了碗大馇子粥。出来时,觉得天分外地白,鼻尖上也沁了一层细汗。
他提议去看电影,并且掏出了两张票。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甚至都没有问电影的片名,更没有问他为什么事先买了两张票——是另有他约,还是早料到我会同他一起去?
电影院里阴凉凉的,刚坐下不到两分钟,就开演了。我第一次坐在两个男人的中间看电影,所以感觉特别不舒服。一会儿看看左边,一会儿又望望右边,银幕上映些啥,根本没有收进眼底。我想起了韦佳,如果他在身边,会俯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些什么,我呢,也会温顺而默默地听着。
他在大笑着,所有的观众都大笑着。原来,银幕上的妻子有了外遇,正在家里寻欢作乐,丈夫回来了。她把情人按到床底下,若无其事地扑向丈夫,煞有介事地喃喃细语:
“亲爱的,你回来了。”
我却笑不出来。这是件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有什么值得笑的呢?韦佳若在,也会笑吗?
我极其失望地走出电影院。他没有跟出来,因为他正笑得前仰后合,所有的观众都笑得不知所措。
我出了影院,直奔汽车站。坐上车,一心想着去见韦佳。
到了一站,上来一位年逾六旬的白发老翁。售票员颇有所指地瞅着我说:
“哪位给这位老人让个座。”
我直视着售票员的眼睛,毫无惧色。我干嘛要让座?说不定这老头是个罪犯,越狱潜逃,**机关正下令通辑他呢。也说不定这老头子是个精神病患者,专好挤车坐着玩。你瞧瞧他吧,哼,还豁着一口漏风的牙贱笑,老不正经!
在许多人责备的眼神中,我下了车。啊,是下午了,春天的下午是恋人说情话的时刻呀。那个在电影院的他,还会想起我吗?
这个下午,我是和韦佳一起度过的。我们一起骑自行车郊游,采了好多好多达子香花。他还给我拍了好多照片,当然都是按照他要求的姿势拍的。我感觉到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气息。我不懂,问韦佳。他说:
“春天才这样好闻。”
于是,我感动了,并且毫不保留地讲了自己一个上午的奇遇,讲了自己如何与一个陌生男子逛市场,听音乐,看电影,尤其讲了自己迫不及待要见到韦佳时的心情:
“我一心只想见你,我没有给那老头子让座,我猜测他是个囚犯。”
我嘻嘻地笑了。韦佳的嘴角抽搐了几下,我不知他是痛苦,还是笑。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吻我一下,一点也不热烈,就象一个大活人向亲人遗体告别时的那种吻,凉嗖嗖的。
郊游结束后,我们一起吃了晚餐,一起跳了一会迪斯科。后来,我们又一起出去看月亮。
“你对老人那么刻薄,连座都不让,我真是看错了你。你将来怎么会好好待我的老父亲呢?我们还是分手吧。”
他这样说,的确是这样说的。他只字未提我与陌生男子的事,他只是怕我将来对他父亲不好,所以……我倒真心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孝子。
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分手了。
我没哭。月光也淡淡如水,而我则又想起音乐茶座中的淡淡清茶,真想再喝它一杯。
哝,下个星期天,我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