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的百年孤独
臧棣 九叶窗台 3 days ago

穆旦的百年孤独
文/臧棣
一百年过去,新诗的大水已依然激荡不已。都说水落干净了,石头才会凸显出来,但这话用于诗歌史视野中的穆旦,就不太合适。尽管离世已有40多年,在穆旦周围,激烈的诗歌浪花从未停止过溅射,正如针对他的诗歌地位的种种争议从未消停过片刻一样;而穆旦作为杰出的现代诗歌之石,却已赫然耸立在并未有丝毫退意的潮涌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或许,这一充满争议的现象本身,对穆旦而言,已堪称是一个奇迹。对中国新诗而言,更是堪称一个心灵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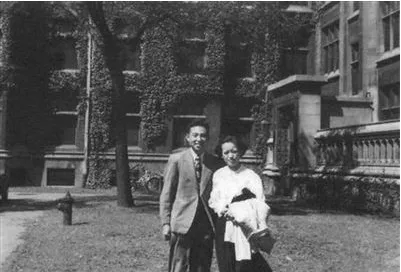
穆旦、周与良夫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复杂的天真
我阅读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差不多也有40年了。我从不掩饰我对穆旦的偏爱,这种偏爱甚至发展成一种激烈的文学情感:我无法想象没有穆旦的中国新诗历史。也许,对有些人而言,穆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座高峰,他们更愿意看到穆旦辉煌的这一面。但另有一些人,特别是来自诗歌内部的人,他们审慎于穆旦和他的诗歌师傅奥登的关系中显露的种种疑窦之处,觉得穆旦更像是现代主义的国际传播中的一个传声筒:遮羞布还来不及彻底剥除呢,哪里还当得起一座诗歌高峰?围绕穆旦的此类争议,也许永远都不会消除。所以,要表态的话,在我看来,穆旦当然算是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这既然涉及私人的文学态度,也牵涉基于文学良知的审美判断。至于高峰究竟高到什么程度?比如和穆旦曾心仪过的奥登相比,奥登的文学高度显然要高耸得多。但这样的比较,更像是机械性抬杠。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从30岁以后,迫于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的历史原因,穆旦的诗歌进程突然崩断了。所以,穆旦的诗歌地位,穆旦在百年新诗中的文学位置,穆旦的诗人形象,我们不仅要从诗歌历史的角度看,也从文学奇迹的角度来看。
从文学奇迹的角度看,我甚至觉得把穆旦仅仅说成是新诗历史上的一座高峰,都有草率之嫌。诗歌高峰,作为一个文学风景,多半只适用于远观。即便是躬身前往攀登,留下的也多半是停留在外部的观赏性的赞叹。所以,仅仅把穆旦看成是一座诗歌高峰,是远远不够的。那样做的结果,有可能忽略了穆旦和诗歌内部的更细致的更富于启示性的关系。在我看来,穆旦更像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有着绝对分量的压舱石。我更偏爱的是,作为一块诗歌的石头,穆旦更可感的更能用文学的指纹触及的那一面。

1934年7月10日,穆旦在天津法国花园亭留影
描述现代诗人的成长轨迹,最常用的套路不外乎是说,诗人的成熟经历了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的精神蜕变。表面上看,穆旦的诗人生涯也没有脱离这一窠臼。初习现代诗歌,穆旦确实深受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他的诗歌基调洋溢着浓郁的“天真之歌”的回音。但作为诗人,穆旦的禀赋也异于常人。即使在他的早期诗歌中,他的“天真之歌”也混杂有音质优异的“经验之歌”。比如他的早期名作《春》,既可看作是“天真之歌”,也可读作“经验之歌”: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从感受的角度看,《春》是一首近乎完美的“天真之歌”。尽管掺杂有青春的迷惘,这首诗还是将青春和春天叠合在诗的隐喻中,把充满活力的青春作为一种生命机遇来加以颂扬。另一方面,《春》也是一首写作手法老练的“经验之歌”。通过悖论的使用,它有着自己的语言意志。对生存的危险,对命运的晦暗,诗人都有自己异常敏锐的预判。
更令人着迷的是,穆旦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位真正深刻于天真的现代诗人。其深刻的程度在于,在穆旦的诗歌态度中,“经验之歌”并不是用来告别“天真之歌”的。这两种诗歌想象力一直融汇在他的写作中,尽管他本人有可能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经验之歌”和“天真之歌”就像一对缠绕的复调,交错出现在他的诗歌视野中。在他发挥的最好的诗歌中,“经验之歌”中回荡着“天真之歌”,“天真之歌”中也潜含着“经验之歌”。譬如,可称得上用现代汉语写出的最优秀的情诗《诗八首》,就是最好的范例。
在这方面,穆旦和其他的现代诗人有着本质的差别。可以说,穆旦是唯一不以诗的天真为缺陷的诗人。面对现代历史中的社会世相,穆旦的观察力并不短视;相反,他的社会洞察力是非常敏锐的,甚至敏锐到了有点强悍的地步。作为一个自觉地锤炼现代意识的诗人,穆旦对个体生命在现代历史中所可能遭遇的生存际遇,一直有着清醒的判断。他的诗人心智,至少在1940年代是非常复杂的;更难能可贵的,它还并未因复杂而失去行动的能力。很多现代诗人,心智复杂到一定程度,会丧失介入存在的兴趣,转而将冥想作为唯一的工作方式。比如,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冯至,就将冥想视为诗人最有效的工作范式;不仅如此,冯至甚至将冥想视为衡量诗人是否成熟的一个决定性的标识。而穆旦从来就不是这样的诗人;诗人的冥想,与穆旦身上的文学气质格格不入。冯至的感受也许是对的,一个诗人是否有能力将冥想发展成一种现代的工作方式,确实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但对穆旦而言,最有效的诗人的工作方式,就是语言的戏剧性。冥想,作为一种诗歌想象力,它太偏向提纯,会过滤掉鲜活的生活经验;而穆旦向往的是,在诗歌的感觉中保留足够多的“丰富的痛苦”。他更偏爱在诗歌中包容相互矛盾的原质经验。完全可以这么看,穆旦实际上是以纯粹的方式,对“诗的不纯”显示出强烈兴趣的现代诗人。
诗的力量
迈出这一步,就那个年代的诗歌观念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在穆旦这一代诗人之前,追求纯粹,纯诗的观念,在新诗场域里已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否认同诗的纯粹,被看作是维护诗的审美独立性的基石。这种诗学动向,从新月派的诗歌主张里,可以明显感到;从现代派的的诗歌实践里,也可以明显感到。事实上,直到1940年代后期,创办《诗领土》杂志的新诗的另一代表人物纪弦,也还在坚称要捍卫诗的纯粹,并用“诗的纯粹”来对抗同时期要求诗歌更积极地参与时代的呼吁。换句话说,在穆旦这代诗人步入诗坛之前,从穆木天对“诗的纯粹”的追求开始,新诗的审美驱动力便把“诗的纯粹”作为提升新诗现代性的突破口来推进的。这中间,有过多次的观念摇摆,直到穆旦出现,直到穆旦拿出令人惊艳的诗歌成品,在新诗的现代化的审美构想中,诗的包容力高于诗的纯粹,才真正进入到新诗的观念自觉中。可以说,这是新诗审美历史中的一次非常关键的裂变。在1940年代之前,新诗的现代性的构想中,诗的纯粹被视为诗的力量的主要来源。在1940年代之后,诗的不纯(有包容力的诗)被看成是诗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事实上,穆旦提出的新诗必须重塑“新的抒情”的呼吁中,诗的力量一直是作为主要对象来关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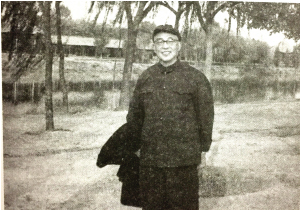
1975年,穆旦在天津水上公园留影
何为诗的力量?简单地说,就是诗歌的想象力必须包含强悍回应现实的复杂性的能力。诗歌的文体应该反映现代智识的进展,尽量涵容吸纳更广泛的社会经验;诗歌的风格应该更粗朴有力,措辞果断。穆旦的老师,当年任教于西南联大的朱自清甚至更明确地指出,新诗的现代化的主要媒介就是新诗的散文化。这和西方现代派诗歌大师庞德的主张近乎惊人的一致:诗必须从现代散文的进展中获得自身的文体启迪(“诗必须写得和散文一样好”)。下面的引文出自穆旦的代表作《赞美》,这首诗展示的文体意识和节奏感,在我看来,颇能代表上面谈到的穆旦诗歌中对语言的力量的追求: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里,诗人为自己设定的位置也和穆旦的前辈诗人有很大的不同。要发出这样的音质,诗人实际上已把自己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央。也就是说,穆旦所主张的“新的抒情”,要求诗人既是时代的观察者,又是历史的代言人,同时诗人必须对更深邃的生存意识有着积极的自我省察。这一节诗中包含着突出的描述性,这是新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有争议的标记;但在穆旦的诗歌中,这种描述性从来不是静止的,也永远不趋向冥想,相反它会激起更强烈的感情节奏。而新的激发的节奏又会将这种诗的描述性带向更丰富的更富于戏剧性的诗歌思辨。
叶芝曾给诗歌下过一个现代的定义:诗是和自我争辩。穆旦的诗歌可以说很好地践行了叶芝的信念。对穆旦来说,一首诗就是一部戏剧。穆旦最好的诗歌都带有诗剧的影子,比如《森林之魅》《诗八首》。也许可以辨认,诗歌中的对话是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的最突出的标记。从想象力的角度看,他的诗歌力量也主要来自这深深嵌入诗歌内部的对话。哪怕只是触及很小的素材,穆旦都要在他的诗歌中展开各种各样的对话:和历史对话,和时代对话,和命运对话,和自我对话,甚至和生活之恶本身对话。而为了有效进行这样的对话,穆旦也积极更新他的诗歌句法。正如他的好友王佐良指认的,穆旦的诗歌句法已新异到了全然摆脱掉古典趣味的地步。也许有争议,但穆旦的确展示了用现代汉语写出新的抒情的可能性。一句话,穆旦写出了新诗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