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付出毕生努力,建构一个杜拉斯传奇
华夏出版社 经典与解释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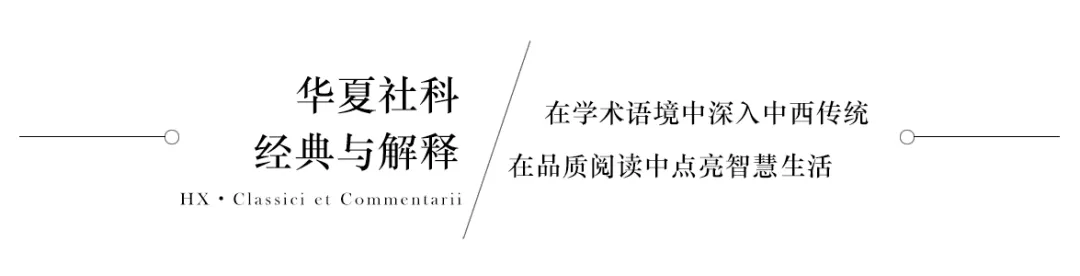

玛格丽特·杜拉斯
吴雅凌 撰
我至少有十年没读杜拉斯的书。
那天,我在书架上翻找半天,我很快找到伽利玛口袋丛书系列的《写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街心花园》《塔尔奎尼亚的小马》,等等,多数是在巴黎拉丁区的旧书店里几欧元买回的旧书。扉页用心地记下购书时间,2002年9月,2003年8月……但我怎么也找不到《情人》。
过了很久,我才想起,《情人》是没有简装本的。依据杜拉斯本人的意愿,只出过子夜出版社的版本。那套丛书的封面有一种简单而权威的美,素白的底,书名用蓝字。我找到了同一丛书里的好几本,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2年版,素白的封面沉淀成耐看的暗黄色调。但我怎么也找不到《情人》。
在翻遍书架的那几个小时里,各种消失在我记忆深处的细节,如积聚在长久没有触碰的那些书上的尘灰,在我眼前悄然飞扬起。
我首先想起那个孤零零站在甲板上的少女,戴着一顶古怪的男人的帽子,臂肘支在船舷上。在前一个画面里,她还在西贡的渡船上。湄公河上雾蒙蒙的阳光,泥泞的河水闪着耀人眼的光。河两岸,周围的喧哗,少女的身影,全隐没在那闪光里。后一个画面转到回法国的邮船。她在甲板上的长椅里睡了一觉,醒来只见汪洋无边的公海,陆地是望也望不到了。她哭了。

这两个画面重叠在一起,在我模糊的记忆里,起初几乎没有差别。仿佛是同一个画面,仿佛少女是同一个少女。她“才十五岁半,胸部平得和小孩一样,涂着口红和脂粉”。但渐渐地,我记起了在这两个画面之间隔着无边的距离,无法逾越,记起了发生在这两个画面之间的那些事。它们被反复地记录。文字。电影。杜拉斯如有强迫症似的,在无数个版本的自传性作品里,反复记录那些生离死别,反复记录一个少女在瞬息之间被摧毁容颜的事实。
与此同时,我还记起了阅读杜拉斯的那些日子里的我自己。一个在外乡求学的孩子,在陌生的世界寻求实在的生存感,仿佛也乘坐一艘远行的船,原乡渐行渐远,而对岸还看不到。那些日子,阅读杜拉斯的简单的法语句子,简单到极致,简单到挑战法语写作传统,我确实从中感到难以言说的震撼和力量。无论是那个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异邦长大的贫穷的白人少女,还是那个回到法国反复不断谈论从前和从前的自己的作家,我确实从她们的错位挣扎的生存感里获得共鸣。
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辗转迁徙,生存的感觉始终脆弱,杜拉斯却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中。2006年是作家去世十周年,国内外学界掀起新一轮“杜拉斯热”。我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们从世界各地赶赴日本,参加杜拉斯学会主办的研讨会。作家出版社和译文出版社纷纷推出新作品集。我买了王道乾先生的《情人》旧译本,新版装帧很精致。十年间,这大约是唯一的交集。
她付出毕生努力,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建构一个杜拉斯传奇。特别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情人》的巨大成功以后,她不停地谈论那个叫做杜拉斯的人。批评她的人,批评最多的莫过于此。那个不得不回去读自己从前写的作品的作家。那些“洋洋自得的圣徒传记式作品”(语出杜拉斯的传记作者阿莱德尔)。那种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吞噬自己的爱。那样无法自拔的水仙花少年般的自恋。1992年,她不满意让-雅克·阿诺导演的《情人》,赶在电影发行前出版新书《中国北方的情人》,分解镜头一般,把故事重新又说了一遍。她不能忍受第二个人书写杜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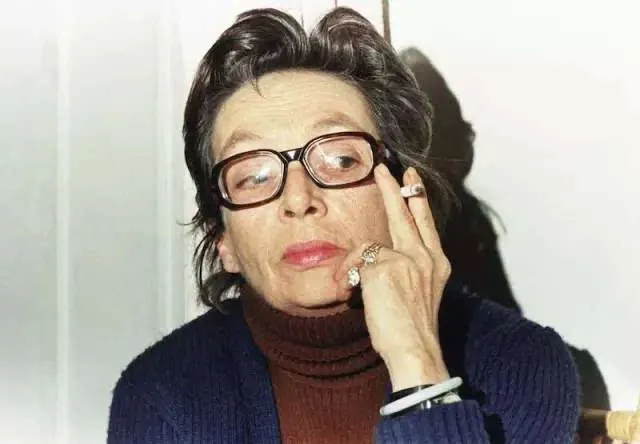
看见是挥之不去的主题,和谈论自己一样强迫着她。归根到底,看见和谈论自己是一回事。《情人》里的少女想必也有古怪的眼神,没有人能捕捉的目光,虹一般却褪色的眼睛,和《劳儿之劫》中的劳儿一样,和杜拉斯所有小说里的人物一样。这样的眼睛却经常是没有能力看的,经常不得不闭上。在与情人最后离别的那天,她在人海中不朝他看一眼,她闭了眼睛,睁开眼时,他已不在那儿,他也不在别处,他走了。
没有能力在当下看见的人物。没有能力在当下直面的存在感。在杜拉斯那些才华横溢的电影里,这被处理成摇曳不休的黑暗镜头,黑夜的黑,闭上眼睛的黑,蛮横无遮拦的黑。仿佛要走过这如死的黑暗地带,才有重生,才能真正的看见。好比汪洋大海中,直等到看不见陆地,人们才会长久站在甲板上,痴痴望着再也望不见的风景。
少女孤零零站在甲板上。在前一个画面里,她还在西贡的渡船上,还没有遇见她的中国情人,后一个画面转到回法国的邮轮,她已然结束十五岁半的初恋。发生在这两个画面之间的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黑暗镜头,她闭了眼睛,不去看那最后一眼,睁开眼时,他不在了,而她不复原来的少女。她成了作家,成了老去的杜拉斯。

十年后,我带着仅存的一点《情人》的模糊记忆,第一次读《中国北方的情人》,并重新被震撼。这一回,我看到的是一个生者对逝去的时光,坦坦然的难以释怀,一边无法抑制地为难以治愈的有所欠缺的过往哭泣,一边又拼命超越去看见从前错过的风景。因为这样,那些强迫症般的重复自我叙事被赋予某种意义。“必须讲述一切,为了以后有人反复讲述这一切,不管是谁,为了全部故事不被遗忘……必须痛苦地理解这些故事。没有痛苦,一切就被遗忘。”必须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国北方的情人》里的这些话。
神话里,少年纳喀索斯不肯停地看水中的自己。直至某个无法预期的瞬间,他闭了眼,经历瞬息的黑暗。水中的影像发生质的变化。从前看见的是少年自恋的美颜。从此以后,水中只有水仙的踪影,只有意义的纯粹,只有美本身。
杜拉斯的秘密也许就在于此。在那个黑暗瞬间,所谓的杜拉斯传奇在世人的欣赏或非议中灰飞烟灭。她凭靠在字里行间赴死一般的坚持和挣扎,终究化身成了一则古典语境的肃剧:有死者面对存在的苦难和悲哀,坦坦然的难以释怀。不是传奇,而是肃剧。即便在这里,tragedy也回归古典的用意,不是悲怆、哀伤的,而是肃穆、沉重的。犹如索福克勒斯的人物,她的黑暗镜头戳瞎了她自己的眼,以便更分明地看见存在的真相。
二十世纪文学用解构苦难的方式去述说和应对有死人生的必然。在这一点上,二十世纪终究还是古典的孩子,哪怕是一个逆子。杜拉斯的例子既是独特的,也是典型的,不自知地留下痕迹。
直到写完这篇短文,我始终没有找到那本子夜版的《情人》。我想象它潜伏在书架的某个角落,窥伺着重新出场的最佳时机。
(节选自《黑暗中的女人》)
▼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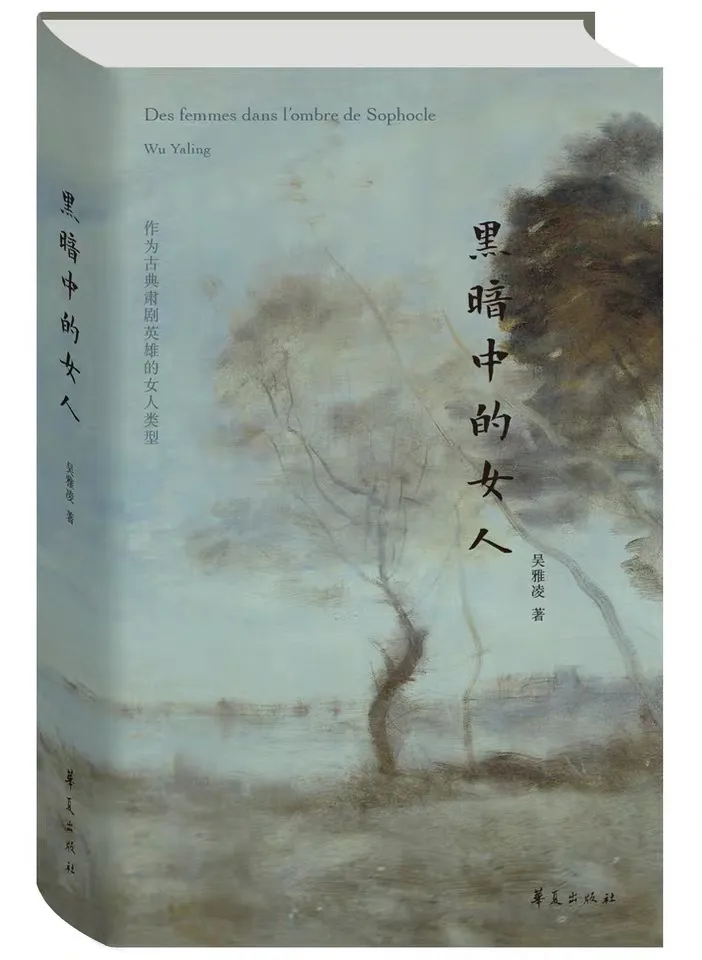
黑暗中的女人
吴雅凌 著
华夏出版社
本书以古典肃剧世界作为思考的参照点,实际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女性类型在西方文明史中不同时代所呈现出的形形色色的样貌。她们名叫潘多拉,安提戈涅或阿佛洛狄特。她们从古希腊神话诗和肃剧世界中走出来,摇身变成二战期间在巴黎舞台上演出的女主角,或二十一世纪女性当代艺术展的女创作者。她们是中世纪晚期的神话诗书写者,是欧洲文明史上最早以写作谋生的职业女作者。她们是十九世纪末成就现代雕塑的转变因而也导致自身毁灭的女雕塑家。她们是二十世纪的女思想者、女智识人和女小说家。克里斯蒂娜·德·匹桑、卡米耶·克洛代尔、西蒙娜·薇依、玛格丽特·杜拉斯。她们的目光触及哲学、诗歌、戏剧、小说、艺术、电影等等不同创作领域。她们的生命轨迹离不开创作这一据说是让人类最有可能与神接近的动作。创作是她们实现自我完成的过程。与此同时,女人身份与创作者身份在她们身上的撕裂似乎也比其他人明显。

吴雅凌,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目前从事比较古典学研究,著译有《神谱笺释》《劳作与时日笺释》《柏拉图对话中的神》《黑暗中的女人:作为古典肃剧英雄的女人类型》(201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