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幻想,及其坚硬
Original 张秋子 经典与解释 2017-11-02
本文发表于豆瓣,经作者授权后转载。张秋子,南开大学文学博士。

一个人如何在自身糅合“智性”与“女性”?我们见惯了那些法式女知识分子的优雅与声势,回头一看西蒙娜·薇依,她正在自作自受、自讨苦吃地踽踽独行,无党派、无教会、无团体,那路径因而如此古怪、坚硬、且充满梦幻色彩。她的梦幻色彩,往往被解读成一种“圣徒气质”,这其中,既能觉察到中世纪修女才有的狂热激情,又分明洋溢着二十世纪一个推己及人、从“我”不断走向“你”的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这两者奇妙的结合,构成了米沃什对薇依的一个观察:“不合时宜”。
阅读薇依是不易的。薇依的书写呈现出一种貌似分裂的状态,一方面,她走进最世俗的政治经验与革命沉思;另一方面,她又不断在超验世界中努力弥合着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缝隙。也许,对于政治经验的诉说早已浸透了沉沉的情感经验,而在表现与体悟常人乃至贫人求生的经历中,她也早已安静地发出了自己的“旷野呼告”。同时,薇依的人生负重感明显不同于其他“流行”的知识分子,因而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文字上,她都有着强烈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使得她所勾勒的许多梦幻学说显得坚硬无比。想来,这种明显向内的写作本来也不惜求被理解,只不过当人们更愿意谈论薇依的传奇生平时,她不得不在写给贝兰的最后一封信中,请他以后更多关注她的思想,而不是她本人。毕竟,谈八卦的门槛向来最低,连西蒙娜·波伏娃在论及薇依时,也不免以一种庸常的眼光打量着着她:长得并不出众,身材也不出众。
薇依为古希腊文学的书写构建了一座肉身的巴别塔。她的目的很清晰:在古希腊诗歌与哲学世界中发掘上帝的荣光,通过对神的无限顺从反证古希腊的生死爱欲。然而,最有趣且悖谬的是,作为最愿意接近上帝的人,薇依不曾受洗,而作为柏拉图的信徒,她却始终将脸沉浸在基督的光辉中。两种文化记忆与文化语境都成为她扎根的所在,我们眼看她脚下的两块本已疏离的土地渐渐松动,互相进入,其上的树木也枝叶相拥。这种“或此或彼”的状态,颇让人想起克尔凯郭尔钟爱的句子:“那内在的就是那外在的,那外在的就是那内在的。”对克尔凯郭尔来说,“那内在的”与“那外在的”已经预设对方为自己不可分割的条件,分别走向对方时,自我的身体里就有“他者”,在相互之中完成了自己并被他者充满。
对两种古典文明融合的渴望,使得薇依身上飘散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虽然她明确提到厌弃那种“虚假的文艺复兴”带来的所谓的“人文精神”:“起初,它还具备某种平衡点,让人几乎可以预感到两种精神的统一。但很快地,它创造了人文精神,把古希腊继承给我们的桥梁当成永久的据说。”(《奥克文明启示何在?》)在薇依看来,缺乏了对于基督精神的理解就贸然回归古希腊,无异于自取灭亡。显然,薇依是一个“反人文精神”的人文主义者。
当我们像卡夫卡笔下那位K走近这座巴别塔时,同样看到了无数飞翔在那城堡上方的鸟群,轮廓清晰有力,它们是“必然性”“力量”“调和”“度”“中介”……这些独属于薇依的神秘语汇构成其诗化哲学的核心。然而,大多数人依然摆脱不了K的命运:无法走进其中。波伏娃早就抛下了冷酷的预言: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薇依,除非,我们将生活看得与神圣一样重。至于那些缭绕于城堡顶端的神秘的玄学元素,一来是我们如今对其知之甚少,古典世界中的密教与秘仪因其隐私性和对泄露的恐惧,流传到如今只剩厄琉西斯秘仪、俄耳甫斯秘仪、狄俄尼索斯秘仪等名字与它们影影绰绰的回响;二来,大概也如薇依在与哥哥的信中坦白:“话说回来,‘神秘主义’一词(我采用它的现代词义的)含糊性真是到了极点,它无所不包,从精神狂迷状态到特雷莎修女、再到苏菲派教徒和某些印度教派的规矩……”(《兄妹通信》)总之,那些神秘元素是无法拨开的密云。因而,纠结薇依到底是柏拉图的传人还是在曲解柏拉图,都是大可不必的,甚至不用把薇依描述成“女思想家”,她其实更近似于佩索阿笔下那个一辈子都不曾离开拉多雷斯大街的小职员索雷阿斯,此人坚信“写下就是永恒”,而蛰居于马赛多明我会修道院的薇依,想来也与小职员有着同样的信仰:用个人的神秘语汇写下经验世界,铸就某种永恒。
然而,当带着无法全然实现的理解走近时,我还是感受到薇依对于古典世界及其在当下世界之投射的深深依恋。这种依恋以精纯的阅读以及阐释功夫展现在与神的不断对话中。不止一次被薇依的解读所震动,那是来自精确(是的,薇依念兹在兹的度量标准)的科学家之眼,而不是迷狂的信徒之心。《圣经》文句与古希腊文句之间的无缝切换达到了一种“天然”的地步:仿佛两种文献在最原始的状态里果真就是一体的,而在日后又不断彼此呼唤。在充满审慎的狂想色彩的《论毕达哥拉斯定理》中,薇依大胆地将毕达哥拉斯派中的数学观与现代的数学概念等同起来,在这个几何学的视野中,她看到福音书中对于门徒与耶稣的关系与《泰阿泰德》中正义与神的关系的相似,这是一种符合数学正比公式的存在。从这里出发,我们大概就能理解但丁在《神曲》中对于几何、数字、数学的迷恋了,《神曲》与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作品一样,都在不断“调和”(这又是一个薇依酷爱的词汇)基督神学与古希腊资源的关系。通过薇依的努力,我们对于这种调和之努力的理解又往前迈了一大步,直接进入了两种文明草创时期的宏阔画卷之中。在这一点上,薇依是但丁的继承人,也是他的解谜人——她也确实在行文中乐于引用但丁。

而在《柏拉图对话中的神》中,薇依以毫无反驳可能性的方式证明了柏拉图与基督教中神秘学说的关系,洞穴比喻与密教传统丝毫不爽地吻合了,细节的相似性简直令人惊诧。其实,对洞穴隐喻的密教式解读指向一个更为宏大的对象:对文艺复兴之后十八世纪诞生的“启蒙”的疑窦。因为,在启蒙的观念里,人从黑暗中走出后,只选择了天平这一端的“真理、美、自由”,而轻视了天平那一头的“恩典”。(《奥克文明启示何在?》)受十字若望影响极深的薇依又怎能容忍这种“度”的失衡。由此,也可以推测,薇依对于“秩序”之坚持、对于“精确”之迷恋、对于《会饮》中将爱若丝比喻成芥菜籽的比例感的认同,无不有着深深的圣十字若望神学色彩——“即使是最轻微的执着,包括心灵的执着在内,都会阻止一个人达到与天主结合。”
《<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这是薇依论述古希腊文化时最核心、最纯净灿烂的文章。丝毫不用怀疑这篇文章受到了她所钟爱的文字风格的浸淫有多深——当她谈起荷马史诗那“没有什么珍贵之物遭到轻视,无论它注定毁灭与否;所有人的不幸一一曝光,既无掩饰也无轻蔑;人人处在人类的共同生存环境,不会更高也不会更低;一切遭到毁灭的东西均获得哀悼”之时,难道不会令人回想起她乐于引用的《会饮》中那风格一致的句子——“《会饮》中的爱若思,既不施行力量,也不承受力量,既不对他者施暴,也不忍受他者施暴”——这还是那个或此或彼的句式、还是那种或此或彼的姿态。
力量诗学,则是其中充满天才感的创见。开篇就谈到:“《伊利亚特》的真正主角、真正主题和中心是力量。”这种力量具有某种灰色调,它是面向死亡——或者说肉化——的躯体的凝视。它具有两面性,漠然平静地石化两种人的灵魂,承受力量的人和操纵力量的人——至于前者,他们有可能是在遭遇力量(战争之暴力)时变成死物,有可能是待死之物,比如与安德洛玛克告别的赫克托耳,披上阿克琉斯铠甲的帕克罗克洛斯。在1937年的《新札记》中,薇依甚至把马克思认为的决定历史的“阶级”也换成了“力量”,此时,她正在读《伊利亚特》。荷马的战场上,灰色调的力量将灵魂挤出躯体,而在柏拉图看来,灵魂不能寄寓在物中,躯体由此彻底物化、彻底尸体化。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描写少女的脊背是“荒芜”的、安部公房在《砂女》里面写口渴极了的人听到别人的小便声音,觉得“可惜”,这些,都是物,都是一种尸体化的身体描写,它们不同程度地遭受着力量的扼杀。至于薇依笔下力量的来源,则是人对于神所授予的力量的失调之滥用,它与后文中薇依频繁提及的“必然性”构成了微妙的关系,这一投向力量的沉重凝视进一步从古典的视野之中穿越到二战的现场,希特勒的力量巨兽扼杀文明的一刻。(《从一部史诗看一种文明的终结》),薇依对人类困境之用心,可见一斑!
同时,再也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描绘“力量”的对立面:日常感。“整部《伊利亚特》均在远离热水澡。人类的全部生命几乎总在远离热水澡之中度过”。这简直是令人汗毛倒竖的观察。薇依进而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阿克琉斯安慰失去孩子的普里阿摩斯,“死了十二个孩子的尼奥柏也得吃饭啊”——洗澡、吃饭、放屁、瘙痒,这些日常感有时带有沉重的下坠意味,将生活拖入泥潭,有时却轻盈地成为了抹杀和嘲笑力量的存在。“过日子”的常态化与生命相关的需求达成一致,抵抗着力量向内的抹杀。乔治·斯坦纳一定是仔细读过薇依的,因而他也才会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注意到尼奥柏这个情节,并且评论了薇依的“力量诗歌”。
必然性的力量有其“必然”要摧毁的东西,但“你看看吧,星星依然闪烁”。当斯坦纳相信生命和星光天长日久且一定能超越人世间短暂的苦难之时,薇依也认同于面向神的“联合、友爱、秩序、节制和正义。( 《高尔吉亚》)”她所期待的,是不应成为“我”,而应成为“你”,是在虚空之中扎根,是在流放中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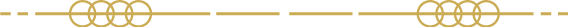

神造物
不是说他造出自身之外的什么东西
而是他抽身引退
使某部分存在得以在神之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