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一颗钉向灵魂深处的钉子
Original 华夏出版社 经典与解释 2019-02-25
爱是灵魂追求的方向,
当灵魂被钉子穿透,钉在宇宙中心时,
它仍朝向上帝。
在西方神秘主义思想史上,西蒙娜·薇依的思想占有独特的地位,既表达出西方神秘主义的诸种基本共性,亦表达出她自己独具的个性。

关于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20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思想大师。薇依一生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薇依拥有特立独行、自甘苦行、永远站在穷苦人民一边的“圣女”人格和感人生平,她的思想充满智慧。
她的思想、著述经历可分为四个阶段:
1926年到1931年,薇依进入巴黎高师从事哲学学习、研究。这个阶段她深受著名哲学家阿兰(Alain,1868—1951)的影响,对古希腊思想、笛卡儿哲学、康德哲学等都有深入广泛的研究。

阿兰
薇依早期的一篇名为《美与善》的文章表现了她一些独特观点:薇依认为善是“为摆脱物进行的精神运动”,这种摆脱则成为感知美的条件。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与工团主义对薇依的影响也很大,她对社会问题、对劳苦工农及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苦难有着天生的深切感受。
1931年到1934年,薇依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她在希特勒上台后发表长篇调查,深入分析德国形势。1934年,薇依完成题为《关于自由与压迫之原因的思考》的论文。
1934年到1940年,薇依开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出发思考她的时代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为对世上的苦难有切实的体验,1935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这段经历使薇依体味到自己就是受苦大众中的一个,而基督教就是受苦人的宗教。正是出于对卑贱者的爱,薇依趋向基督教。她感到必须超越政治才能真正得以自救。
1937年春,薇依在阿西兹第一次跪在十字架下,感受到了上帝的恩惠。1938年在索莱斯姆修道院,她听到基督经受尘世的痛苦直至喊出:“上帝,你为何遗弃我?”从此,宗教在薇依的思想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从1940年到1943年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最为重要的几年。薇依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直至1943年因饥饿、重病死于伦敦郊区的修道院……
薇依的思想
薇依的神秘主义“超出善与恶对立的范围之外,而这是通过灵魂和绝对的善的统一实现的”。薇依的神秘主义信仰的神秘合一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上帝。这是真实的爱的结合,灵魂在这之后“总是变成他者”。灵魂为了这种变化应该赞同上帝。
薇依的神秘主义在基督信仰的神秘主义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薇依始终坚持理智精神指引下的基督信仰,她把基督信仰与宗教信仰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基督精神不等同于基督宗教。虽然她一直拒绝受洗和参与圣事,置身于教会、基督团体之外,但她的实践和思考却证明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薇依的唯基督论与泛基督论会合于她的基督信仰之中。她认信上帝,认为唯有基督的上帝才是真实的上帝。这种信仰的确立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激烈甚至痛苦的思考。
最初,薇依对上帝还只是感情上的认同,在理智上还有抵触:“我仍有一半在拒绝,这不是我的爱,而是我的理智……一个人绝不会纯粹为了理智去虔心祈祷上帝。”理智的深厚根底和科学知识的较高素养使薇依怀疑超自然的存在。
但是,她通过理智上的努力,找到了理智与上帝接触的点,这就是理智的注意力。感情与上帝的接触方式是祈祷,而理智与上帝接触的方式是注意力。这种注意力并不是要证明上帝,推论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把自身的注意力引向上帝,使心智趋向和接受上帝成为可能,而不能相遇的上帝永远在期待之中。
薇依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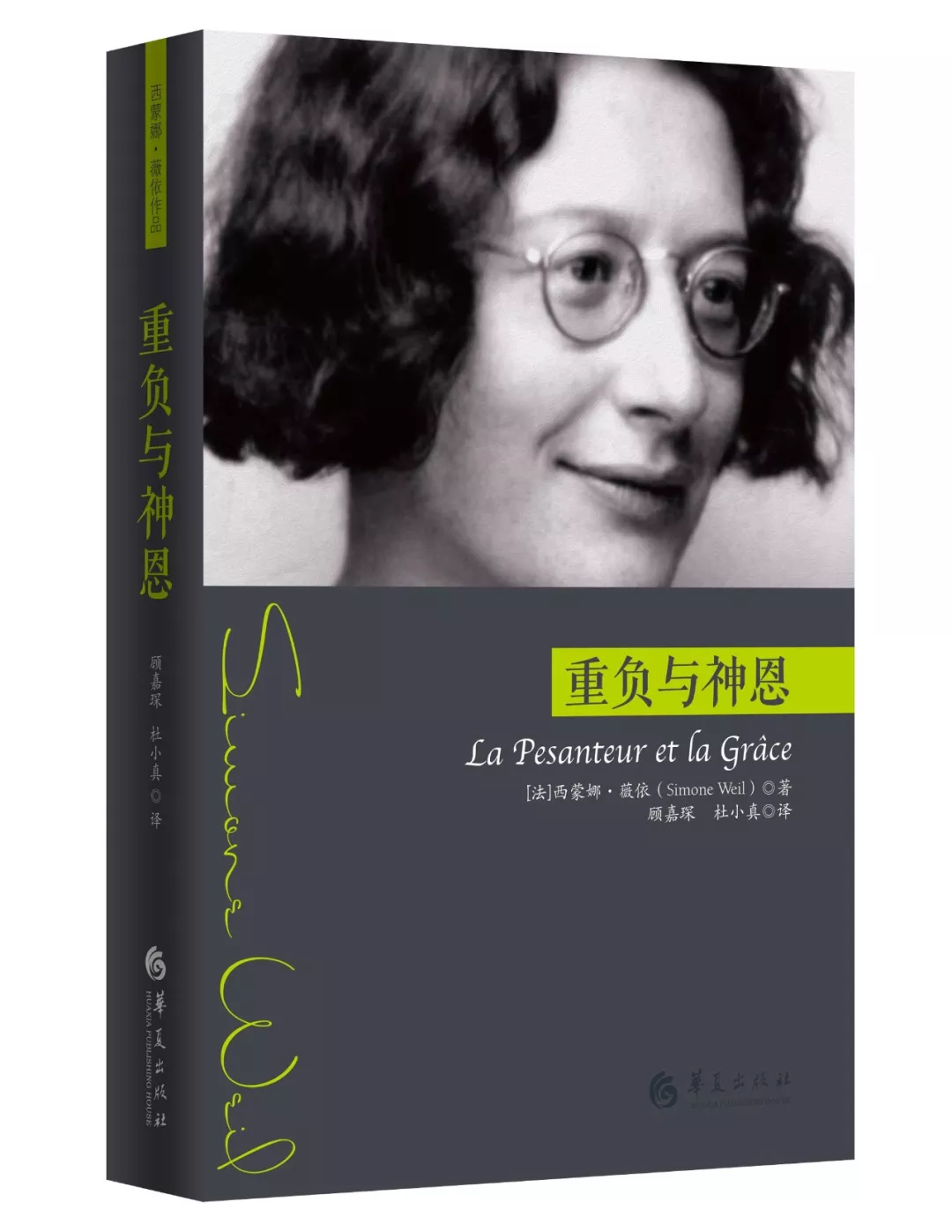
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
而是艰难的、绝非轻松的重负。
《重负与神恩》
顾嘉琛、杜小真 译
华夏出版社
2019年3月
《重负与神恩》不是系统的专门论著,而是薇依的朋友、著名宗教学家梯蓬在薇依去世后从她大量的手稿、言谈记录中整理成书的。这些闪烁着精神之光的篇章渗透着薇依的深邃思考,显示了薇依的伟大心灵和崇高的信仰,是20世纪神秘主义思想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
有人把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提并论,并称薇依为“当代的帕斯卡尔”。这位法国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沿循的是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