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丨吴雅凌 x李宏伟:力量之诗——西蒙娜·薇依阅读分享记录
经典与解释 2019-11-2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青年文学杂志社 Author 吴雅凌 李宏伟

青年文学杂志社
《青年文学》官方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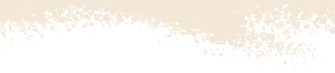
吴雅凌:译者、学者,供职于上海社科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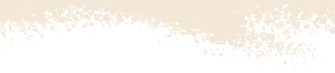
李宏伟:诗人、小说家,供职于作家出版社。
▶ 编者按:
今年五月,雅凌译作新成,这就是西蒙娜•薇依平生所写的唯一一部戏剧:《被拯救的威尼斯》。这部剧作很奇特,因为它是半成品。你可以想象一幅情景:画家猝然离世,画室里画布上的油彩还是湿的,盘中的颜料已经调好,只是未及使用。《被拯救的威尼斯》就是这样一幅画,薇依在稿纸边上留下的大量文字则是调好的颜料。这些文字记录着她的整个运思,包括角色安排、情节编织、对白设计等。其中有的构思在剧中实现,有的则永远作为构思在那里定格。我们从中看到薇依如何理解救赎、理解公义、理解城邦政治以及理解人性。
为了纪念《被拯救的威尼斯》中译本面世,2019年5月11日,华夏出版社请来雅凌以及她的作家好友李宏伟,在北京外文书店,二人围绕《被拯救的威尼斯》举行了一场对谈。谈话当然也兼及薇依其他作品,如《柏拉图对话中的神》《重负与神恩》《在期待之中》等。我们将两位嘉宾的对谈整理成文,后经谈话者本人修订,先发表于《青年文学》2019年第11期,又于2019年11月21日在该刊公号“青年文学杂志社”推出。感谢《青年文学》及其公号的刊发!为答谢读者的热忱,我们在此再做推送。
力量之诗
——西蒙娜·薇依阅读分享记录
文/吴雅凌 李宏伟
小标题为小编所加
01
开场
李宏伟:我对薇依最初的了解是从诗人韩东的一首诗里,他写过一首诗叫《西蒙娜·薇依》。作为开场,我先念一下这首诗:
要长成一棵没有叶子的树
为了向上,不浪费精力
为了最后的果实而不开花
为了开花不要结被动物吃掉的果子
不要强壮,要向上长
弯曲和枝杈都是毫无必要的
这是一棵多么可怕的树啊
没有鸟儿筑巢,也没有虫蚁
它否定了树
却长成了一根不朽之木。
我是先读这首诗才看薇依的作品。这棵“没有叶子”“却长成了一根不朽之木”的树,这个意象太让人印象深刻了。这首诗强大的感染力让人乍一听,会相信薇依确实如此,但实际上,读了薇依的作品,我们知道,那个意象只是韩东的意象,薇依是有果实有花朵的,她从来都不否认树。
吴雅凌:谈薇依,对我来说是挺困难的事。很期待可以和一位诗人谈薇依。宏伟选了一首诗开场,树的意象,听上去挺准确。薇依不止一次提到树,在《人格与神圣》中说,深深扎根大地的树,是从天空持续投射的光照中汲取能量,某种程度上,这棵树扎根在天上。她也说过,最美的树长在我们身上,不是通常看到的大树,是十字架。
李宏伟:我和雅凌商量,我们尽量集中在一两部作品上来聊薇依,最后选定《被拯救的威尼斯》和《力量之诗》,特别是新出版的《被拯救的威尼斯》,“它一以贯之地围绕薇依始终关注的人类基本问题”。作品后面附了雅凌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我想先问雅凌,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把它译成中文的?
吴雅凌:其实译《柏拉图对话中的神》的时候考虑过要不要把这篇放进去。它的题材特殊,算是薇依唯一的戏剧,未完成稿,就像大多数笔记一样。《被拯救的威尼斯》是我很多次读过又放下的篇目。当时觉得没有准备好。又等了几年,生活里经历一些变数,有了一点沉淀,才又拿出来,感觉可以译了。进入这个文本要求一种特别的状态。感觉它经得起反复讨论。不太好懂。所以我挺期待。
02
作为理想城邦的威尼斯
在对美的确信中得到拯救
李宏伟:介绍一下《被拯救的威尼斯》内容。十七世纪,西班牙人策划了一场占领威尼斯的叛乱,行动指挥加斐尔出于怜悯,得到承诺后,向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告密。行动败露,十人委员会违背誓言,处死了包括加斐尔要求保证安全的所有人,只留下加斐尔,他们给了他一笔钱,要将他驱逐出威尼斯。这部剧有四个人物认领或者说代表了四种面对世界的方式,我们一个一个说。第一个是法国领主何诺,何诺是这次谋反行动的实际策划者,他是精明的政治动物,有段很有蛊惑力的演讲,说明为什么占领威尼斯后,要留出几天时间,容忍士兵进行发泄欲望和展示力量的屠城。叛乱之后,需要迅速摧毁威尼斯人的尊严和信心,这样才不会引发更大的反抗,才能迅速稳定形势,避免更大的牺牲。薇依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巨兽或者动物性的,她非常反对。但从现实操作而言,何诺的思路似乎有其合理性。十人委员会书记官后来也是用类似何诺的方式,让加斐尔平静下来,以免他自寻短见。雅凌对此怎么看?
吴雅凌:谈这个可能先要有些铺陈。在这出三幕戏里,主人公有一个认知的转变过程。故事发生在圣灵降临节,这个日子对威尼斯有特殊意味,威尼斯长官在节日这天将一枚金戒丢进亚德里亚海,象征威尼斯与大海联姻,意思是与自然缔造相亲相爱的关系。谋反者的行动就是要破坏这种秩序。薇依的笔记提到,何诺如何对付威尼斯人的告诫,与事败后威尼斯书记官如何对付谋反者的话,完全一致。这是一场没有爆发的战争,双方遵循柏拉图的巨兽理论,无论谋反者的政治理念,还是威尼斯人的社会常态,唯一的例外发生在主人公身上,这个例外带来标题的拯救之说。我想,这出戏讨论的重点不是常态,而是这个例外。
李宏伟:在薇依的笔记中,也充满对常态的理解,尽管这个理解是出于深度或反衬的需要。薇依提到这些叛乱者,说“要让他们最大限度地给人好感。要让观众期盼这次行动能够成功”。叛乱者有怨恨需要发泄。但我关心的是何诺提出的屠城,或者说以屠城为象征的统治手段,如果谋反成功了,这个手段是否存在合理性?
吴雅凌:何诺的话,以及威尼斯长官的话,都是柏拉图所说的驯养巨兽的人的言论,这些手段对于巨兽的驯养有效。至于合理性,薇依本人译过《理想国》里的话,大概是,这些手段观念究竟是美是丑,是善是恶,是否正义,驯养巨兽的人一无所知,因为他运用这些字眼只是迎合巨兽的喜好罢了。以荷马诗中的特洛亚战争为例,无论胜者败者,无论力量的施者还是受者,都同等地受到力量的必然控制。我们看到,薇依笔记中区分了所谓帝国和城邦的概念,一种是没有灵性扎根的一味崇拜力量的帝国,比如谋反者的集体,比如常被她批评的罗马帝国或旧约的希伯来人。相应的,威尼斯代表一种城邦的理想。
李宏伟:但这个剧本中的威尼斯也不是一个可以扎根的城邦,它的城邦的特点体现在一个纯洁甚至无知的叫维奥莱塔的女孩身上。
吴雅凌:是的,像你说的,现实和理想的威尼斯并非同一个。理想的威尼斯扎根在维奥莱塔的信中,与其他威尼斯人无关。这个女孩天性美好,她爱她的城邦,相信威尼斯因为自身的美不会被伤害,它是蒙福的。这种信没有道理可讲,是属灵性的。故事的结尾恰恰是这一信念得到落实。但对整件事的发生经过,包括背后各种暴力牺牲,她一无所知。她也不需要知道。
李宏伟:维奥莱塔像威尼斯的象征,她对危险一无所知,相信威尼斯凭借它的美就可以避免灾难。在这部剧里,威尼斯避免灾难的背后是加斐尔巨大的牺牲。此处有个疑问,维奥莱塔的相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得威尼斯享有豁免权?毕竟,加斐尔得到的是十人委员会的背弃誓言。假设将来还有人面临加斐尔的选择,他已得到警示:不要怜悯这座城市。
吴雅凌:你的假设恰恰反映了威尼斯人和谋反者遵从同样的逻辑。我的理解是,威尼斯被拯救,不是通过一次可歌可颂的英雄行为,而是凭靠一种微乎其微的信,一次不被理解、没有名分的行为。甚至可以直接理解成一场神迹。
李宏伟:这场神迹来自维奥莱塔的信。她认为威尼斯是美的存在。她的感受传递给了加斐尔,加斐尔在她的身上确证了威尼斯之美。
03
重拾古代悲剧
探究群己关系的冲突
吴雅凌:她带有薇依说的无限微末的属灵的东西。薇依在别的地方说过:“这无限微末之处就是神,就是比万物无限多之处。”可以发生在一个民族、一个人的身上。时机到了可能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不过宏伟,你刚才是不是想讨论这一事件对我们当下的有效性?
李宏伟:我想知道如何理解加斐尔,如何理解威尼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一个很现实的处境,包括现在和美国这么大的摩擦,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国家理性?我们要在怎样的层面上理解国家理性?薇依提供了一个纯粹的、给我们个人很大感召力的精神示范,但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集体中。薇依很厌恶作为复数的“我们”,但这个是很现实的存在。如果我设想我是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其实也很难不去处死所有背叛的人。
吴雅凌:如何理解加斐尔,也是我在这出戏中遇到的主要困难。笔记中有句话给了我启发。重拾古希腊悲剧中完美英雄的传统,古代悲剧探究群己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的表现。读这出戏,我们可能是加斐尔或维奥莱塔,当然我们更可能是威尼斯人,或谋反者,或威尼斯政府。每个人在事件发生时的言和行都是符合自身逻辑的。读者能找到不同程度的映照。但这出戏关注的人物是加斐尔,关注最不可能的那一种言行逻辑。我想恰恰是由此建构的思想框架的深远度足以给不同时代的现实处境提供某种光照。
李宏伟:薇依的意思肯定不是仅仅设置人物以代表不同立场,薇依有着清楚的价值序列。比如何诺和加斐尔,他们在薇依价值序列里,孰高孰低是很清楚的。
吴雅凌:一开始你提到何诺的言辞是否有可取之处,包括威尼斯政府,他们的言辞确乎表现了某种程度的逻辑。但事实上,在戏中,何诺及其他同伴在谋反前自信狂喜,在事败后绝望求饶,说明他们从头到尾是力量的囚徒。戏中强调他们先前遭遇很多不幸,似乎有一个翻身的机会,但希望落空了。他们遭受暴力,也对别人施暴,在薇依看来,他们不光事败后才沦为囚徒,从头到尾他们都不自由。她说过,真正的自由不是通过欲求和满足的关系得到定义,而是通过思想和行动的关系得到定义。
04
“准备”与“行动”
李宏伟:我们中午的时候讨论过,你说薇依讨论这种精神典范是以未来为目的。
吴雅凌:原话是为未来做准备。我把原话找出来读给大家听。这是薇依二十五岁写的论文,与她去世前的《扎根》互相呼应,从“自由和社会压迫的起因”到“对人类的责任的宣言”,我总觉得有点像卢梭从“不平等”到“社会契约”。薇依的政治哲学框架是相当坚实的。这一段在结尾部分:
“我们转而通过盘点当前文明而有方法地为未来做准备,还有比此更高贵的任务吗?确切说来,这一任务远远超乎人类生活的极其有限的可能性。一个人朝这条路走,就意味着他自我判处以道德的孤独,无论现有秩序的敌人还是仆人都不理解他并仇视他。至于未来世代,我们更无理由假设,他们会在偶然中穿越使之与我们隔绝开的各种灾难,在必要的时候抓住那些在我们今天造就若干孤独精神的思想的片鳞半爪。但抱怨这类事是愚蠢的。人与神意的契约从来不曾保证人付出的努力必定有效,即便最高贵的努力也是如此……在清楚地看到有事可为,并且独有此事可为时,坚定的灵魂不会为了这类原因而放任自己改变方向。”
李宏伟:对,就是这段话。薇依会给人错觉,即总是在做准备。现实中的薇依是很有行动性的,包括她从纽约想回到法国。薇依在准备和行动两方面做了很好的平衡。
吴雅凌:其实并行不悖。她的意思是为真正的生活做准备。准备不光是为未来,是直指当下的思想和行动。她说过,我们今天会把文化当成单纯的消遣,通常还借此寻求逃避现实生活的手段,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为真正的生活做准备。思行合一才自由。所以我们会发现,她直接地写作,直接地行动,两者浑然合一。没有多余的修辞。让人惊叹。
李宏伟:薇依的感召其实不只是她的思想,她的行为是很好的示范。我们在讨论题目的时候,雅凌问我说到薇依会想到什么画面。我说记得她曾经到工厂去帮忙,因为眼睛的高度近视,一脚踩到锅里,被严重烫伤。
吴雅凌:我们当时还说,这也是一首“力量之诗”。这是她参加西班牙战争的时候,她的近视眼没看清地上挖的烧火做饭的坑,一脚踩进油锅,要不是当医生的父亲抢救及时,很可能感染被截肢。我们一开始想到用“力量之诗”作为对谈活动的标题,就是感觉也许可以从诗的角度谈谈我们今天为什么依然读薇依。她的书写是一种“笨拙”的书写,像她一脚踩进热锅。笔记,未完成稿,写得气喘吁吁,来不及。有一种更常见的书写会钻研如何把思想从容舒服地表达出来,读的人和写的人都能享受其中的愉悦。她相反。她的行文过程是一片狼藉的战场。她的所有作品是正在进行时。读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跟上她。
05
论“沉默”
李宏伟:对薇依来说,写完不是最重要的,写的过程和修改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被拯救的威尼斯》中只有第三幕和后面几节是完成了的。特别有魅力的是,前面有着几十条笔记,这是对薇依思想的概括。我们回到戏剧中,在最后,加斐尔面临十人委员会的毁约时,他开始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愤怒,继而哀求,他希望同伴能被释放,但他最后陷入了彻底的沉默。这个转变其实有点像耶稣会问“你为什么会离弃我”。
吴雅凌:这出戏严格遵循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规则,正文都为诗体形式。但它是未完成的作品,有些部分诗行已成形,有些地方还是笔记。薇依把最要紧的写出来了,剩下的没时间很可能也觉得没必要写出来。已经完成的诗体多与加斐尔有关。我们读一段吧(略,见书第61-63页)……
李宏伟:这是加斐尔的独白。这时候是要采取行动了,也就是加斐尔要去告密了。“这城这人这海即将属于我……我焉不能学天地的无情?”——这句“我焉能不学天地的无情”,会让人想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吴雅凌:属天的公正往往以无情冷漠的方式得到表现。不是天地无情,而是人单靠理性无法理解天地的仁慈。
李宏伟:这里是不是暗示,他可能已经知道告密会带来什么?
吴雅凌:很难说。笔记里说,这一幕里加斐尔语带双关,在他的灵魂深处究竟发生过什么始终是个谜。我们对加斐尔身上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李宏伟:薇依对此有所知吗?
吴雅凌:我觉得她是有所感悟的,至少她尝试去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为神秘主义精神体验的东西。一种思想主动向灵性开启可能。一种思想有没有真正和宇宙立约,这是重点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她那么在意不同古代文明里的“密”的部分。在薇依的表述里,这是一种超自然的认知。黑暗中有一种珍贵无比的人的可能性。她关心这个。她的书写和生命都是要尝试接近这个神秘经验。从现实的技术层面看,戏剧舞台上可能很难实现,主人公沦为一头兽、一件物品,静滞不动,沉默不语。
李宏伟:说到“沉默”,远藤周作著名的小说就叫《沉默》,可以拿来类比。一个葡萄牙教父到日本传教,当时日本在大规模镇压天主教,当地教徒秘密接待了这个教父。后来日本的掌权者抓住包括这些教徒在内的很多信徒,施以严重而残酷的处罚。释放的条件,是神父要做出叛教的行为,踩在圣母像上。“沉默”这个题目指神的沉默,也指神父意识到在他在这些教徒被如此对待时,神只有沉默——这是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处理的主题。小说最后,神父踩在了圣母像上,叛教而出。我不太满意的是,他对此进行辩解,说这是耶稣让他做的,这也是爱上帝的表现。以我对薇依的理解,可能更好的处理方式是,神父可以这么做,但他不该那样为自己辩解,找理由。就像加斐尔,他只能沉默,他的沉默传达的东西对于每个读者来说可能都不太一样。
吴雅凌:我赞同你的说法。这是不可言说的。除非神父做了一场苏格拉底式的申辩,否则“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默而识之。
李宏伟:加斐尔的结局应该是被威尼斯市民们杀掉了,虽然十人委员会有保证他个人安全的处置,但这个处置没有得到执行。从思想深度来说,如果加斐尔不被处死,而是也以沉默的方式在世间流浪,这样的形象的说服力是否会更强大?
吴雅凌:在剧中,天亮的时候,所有囚徒被处死。只剩他一人,背负恶名。他是背叛者。威尼斯人醒来,正是节日当天,他们看到加斐尔,不但不感激,反而遗憾他们的城邦竟然是在叛徒的手中得救的。他们讥笑他,侮辱他,送他去赴死。所有种种,很难不会想到受难的耶稣。像你刚才说的,有这层影射的用意。
李宏伟:这里还有一个难题——不管加斐尔是被处死还是被流放,都有先例。被流放的话,很像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的处境稍微好一些,他至少得到了世人的理解。加斐尔在各种方面都没有被理解,他背负着双重的背叛。
吴雅凌:是的,困难在于,加斐尔身为英雄没有英雄的光环。甚至连俄狄浦斯这样公认被神诅咒的英雄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尊严荣誉,特别是他死的时候。加斐尔遭遇了人间最彻底的不幸。像你说的,以沉默的方式在世间流浪,是俄狄浦斯的自我审判,也是俄狄浦斯的光环。加斐尔让人想到耶稣,薇依说过,基督的光环乃是教会和基督宗教史的作品,耶稣受难时丧失了全部声誉,连门徒也不认他。
李宏伟:皮埃尔被处死,加斐尔的自我审判就已经开始了。
吴雅凌:从这个角度来说,故事的高潮是他在不幸中进入神秘境界,也就是这出戏尝试说那难以言说的。其他的不太重要。
李宏伟: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加斐尔说,“死神来带走我,耻辱也离开我”,对于他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
吴雅凌:是。他最后说:“死亡带我走,耻辱也离开我。//我即将看不见,眼前的城多么美!//我要远离活人的住所,永不返归。//无人知晓我去向的黎明和城邦。”——重点还是他去向无人知的黎明和城邦?这是他最后的话。第三幕的漫长沉默里只有这段台词,让我们稍微可能知道他的灵魂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
06
通往幸福的路径:
必然与偶然
李宏伟:提到皮埃尔,我岔开一下。我觉得,薇依对皮埃尔存在某种程度的怜悯。加斐尔告密之后,他最好的朋友皮埃尔被逮捕了。皮埃尔的光辉在于,一直不知道更不相信加斐尔背叛了他,他以为加斐尔早已被处死,痛悔自己把加斐尔拖到叛乱里来。薇依对皮埃尔的怜悯在于,她没有向皮埃尔揭露真相。皮埃尔直到被处死,都不知道实情。以皮埃尔对加斐尔的信任,除非加斐尔来到他面前,亲自坦白,他才会相信加斐尔的背叛。我相信,如果加斐尔来到皮埃尔面前,他只能告诉皮埃尔实情。这让我忍不住猜想,如果加斐尔告诉皮埃尔自己告密了,皮埃尔会怎么反应?
吴雅凌:你的忍不住是小说家的思维和想象。我则是努力想要了解她为什么这么讲故事。相信一定有她的道理。那么道理是什么?《力量之诗》里提到过,荷马诗中有一个人是力量控制的例外,恰恰因为他的友爱,懂得对所有人温柔。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罗克罗斯。就像所有值得反复阅读的作者,薇依的作品也是连在一起的。讨论皮埃尔的友爱,我会想到《在期待之中》的“不幸与爱上帝”,内心爱上帝的一种形式是友爱,爱他人。因为友爱,皮埃尔有别于其他谋反者,有别于前面说到的“思想的囚徒”。我没有特别注意他们的结局多么悲惨,而是在意他们在困境中表现出人的尊严。在不幸的深处,与世界、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无愧于人的尊严的关系。
李宏伟:是,皮埃尔身上确实有这种东西。这时你会发现皮埃尔与维奥莱塔身上似乎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个薇依认定的光辉,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真相,都因为不知道真相而保持了目前的精神状态。在薇依的写作中,他们不需要知道真相,有加斐尔作为知道真相的路径。
吴雅凌:确实是,薇依笔记中说,维奥莱塔代表一种“幸福的无知,无比珍贵的东西”,但这是“偶然的幸福”,“这种幸福不与无知相连”。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并没有一条凭靠无知的信德通往幸福的路径。我们只能努力去知道,知自己,知命,然后走自己该走的路。
李宏伟:薇依为什么让维奥莱塔处于这样的状态,什么都不知道,完全处在幸福中?对此我有两个感受,一个感受是,薇依的读者不是维奥莱塔,而是我们。从客观结果来说,故事对我们形成感召,我们所有人都会把自己代入加斐尔,我们清楚维奥莱塔代表什么,也清楚我们做出加斐尔的选择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这两方面我们都知道,但我们还是有可能做出加斐尔这样的选择,这是薇依作品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感召作用。第二个感受是,我不是基督徒,无法体会,只能猜想。所有的事情都有审判者,你在文章的结尾也说,维奥莱塔或威尼斯的美,有加斐尔看见,或者说有一个人看见了,就足够了。这个足够,在薇依的语境中,是因为有一个最终的裁判者在那儿。
吴雅凌:悲剧里只有一个人发生了经验认知的转变。不论维奥莱塔还是皮埃尔,不论何诺还是威尼斯人,他们从头到尾没有变化,戏里只有加斐尔的转变。维奥莱塔或皮埃尔更像发生在加斐尔的苦路上的象征性设定。关键是加斐尔,这个完美英雄的受难经过。笔记里说,受难就是独立承受世间的恶,英雄的美德在于“把正在承受的恶保留在自己身上”,不让周遭的人遭受不幸。按照这个思路,维奥莱塔等人确实不该知道真相。当然我们可以跳开来假设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会怎么做,那会是另一个悲剧英雄故事。第二个感受是?
李宏伟:第二个问题是确信。你写的那篇解读文章里面,当你写下“有一个人看见就足够”的时候,你的确信的基础是什么?
吴雅凌:薇依从某个被遗忘的十七世纪的作者的书里“看见”了。思想史上有这样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这就是确信吧。发生在加斐尔身上的是一种终极经验,对我们常人而言肯定是有困难的。好比苏格拉底的经验,或耶稣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每个时代的人有什么光照作用?有人说薇依给了相当极端的示范,但为什么我们感觉亲近?不妨回到这问题上来。
李宏伟:示范的作用。拿这部剧来说,薇依是非常清醒的,她看穿了这件事的结果,还是做了这样的选择。加斐尔可能不知道告密后会面临什么,但薇依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她写下加斐尔去做这件事。我的理解,她不是把他作为操控的工具——说情感代入也好,说思想实验也好——薇依写了这样的人和他的选择,对我的意义就是一个感召。我不敢肯定,因为我没有面临加斐尔这样的境遇,但至少,读了这部戏,面临这样的选择时,我可能会想到加斐尔。这就是薇依给人力量的地方。
07
尾声
吴雅凌:加斐尔的形象与薇依谈柏拉图洞穴神话是相通的。洞穴之说关乎人的认知,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进一步说,我们都知道,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启示的和理性的,恰恰是两个传统的有益冲突不断迸发让人赞叹的东西。薇依就是一例,她理解宗教的方式很哲学,同时她也清楚哲学不够,需要有神,需要她说的超自然认知。
李宏伟:薇依理解宗教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她的一个词“顺服”来概括?作为一个人,在薇依看来,“顺服”终究是一种幸福?
吴雅凌:这和她谈不幸有关。不幸不等同为苦难。不幸是一种恶,把人去人性化的恶,侮辱、贬低、破坏属人的尊严。《在期待之中》却说,不幸是人世的杰作,是灵魂向上的通道。她在这个场合说顺服。就像《门》那首诗。处在不幸的尽头,放弃愤怒哀求抗争等等,知命,可能就有一种特别的光照。
李宏伟:时间差不多了,最后问一个私人化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喜欢一个作家,经常面临时间节点,就是当我们的年龄超过他/她之后。薇依三十四岁去世,而你已经活过了薇依的年龄,对你来说,现在薇依意味着什么?
吴雅凌:(笑)我有幸译过不同年代的作者作品,好像与薇依特别亲近。好些读者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她关注的问题似乎就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她就像那个我们无法成为的自己。我对薇依的认识其实也在变化,归根到底是自我认识在时光里的不断偏移。她只活了三十四岁。三十四岁之后,我们还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