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小说都是在写历史”——访霍达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29日09:46 来源: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霍达
记者手记:
25年前的9月1日凌晨,霍达完成《穆斯林的葬礼》,在后记中写道:“请接住他,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当年的“婴儿”如今已长大成人。在《穆斯林的葬礼》25岁生日庆典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透露说,25年来,《穆斯林的葬礼》正版销量已突破200万册。
有人说,《穆斯林的葬礼》是中国当代最有人缘、最纯净的书。25年来,这部作品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所做的听众最喜欢的小说民意调查显示,《穆斯林的葬礼》和《平凡的世界》并列第一。而在当当网上,关于《穆斯林的葬礼》的读者评论达3万多条。
然而,这部作品的光芒,也掩盖了霍达的其他作品,她为此感到“委屈”,和读者见面的时候,忍不住说:“我写了800万字,不止这一本书,其他作品也希望你们有空看一看,那也是我的儿女。”
是的,自青年时代步入文坛,霍达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著作等身,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蜚声海内外。其中,198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1988年出版),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1年);1985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红尘》于1988年获第四届(1985—1986)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创作的报告文学《万家忧乐》于1988年获第四届(1985—1986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4年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霍达深入香港,历时三载创作的长篇小说《补天裂》,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北京和香港两地同时出版,影响巨大,1999年被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电影总局评为建国五十周年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图书和优秀电视剧两个奖项,并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由作者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剧本《红尘》同年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
霍达的作品,读来大气磅礴,具有史诗般的厚重。这大概与其“亦文亦史,以史为文”的创作理念分不开。 她平生最佩服的作家是司马迁,最推崇的著作是《史记》。霍达说,“我愿做太史公的小学生”。
屋里飘着袅袅的茶香。采访之前,霍达先放了一段《穆斯林的葬礼》的小说连播的录音。一段穆斯林做礼拜时的阿拉伯语吟唱,立刻把我带入神秘而肃穆的氛围,一时沉浸在《穆斯林的葬礼》中,许多年前手捧此书边读边落泪的情景依晰如昨。
当时只是想把“爱和死”写到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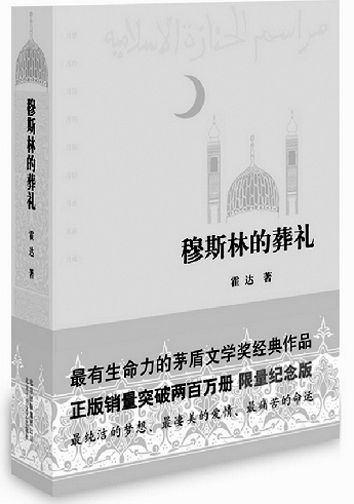
《穆斯林的葬礼》问世25周年纪念版
读书报:25年前,您创作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冰心老人称这部作品是“奇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
霍达:已经经历了岁月的沧桑、生活的磨炼、学养的积淀、技巧的操演,为创作长篇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穆斯林的葬礼》真正执笔写作的时间只有四个半月,而前面的准备工作已经有几十年,可以说动用了我前半生所有的积累。鲁迅先生说过,“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我从不逼着自己“硬写”,作品酝酿成熟之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分泌出来,流淌出来,欲罢不能。《穆斯林的葬礼》的创作非常顺畅,酝酿胸中许久的话要一吐为快,直到“吐”完为止。
读书报:能讲一讲创作的情况吗?在写作过程中,您是怎样的心态?
霍达: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用手写稿。我写字又认真,字字清晰,连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每天早上不到八点就开始,一直写到深夜,有时几千字,有时一万字,写得很辛苦,手指都磨破了。家务事由保姆操持,我一概不管,把心完全沉浸在创作的规定情景中,这是一种“穿越”般的生活体验。第二天早晨,先把昨天写的梳理一遍,常常有改动,甚至推倒重来。钱锺书谓,“寻诗争似诗寻我”,此言极是。一件作品在构思阶段,仿佛冥冥之中就已经“完成”,已经“存在”,正等待着你去寻找,去发掘,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寻寻觅觅的过程。这个过程很辛苦,也很有趣。当作品完成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是作者最陶醉的时候,但前面“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寻找过程也很享受,而且是只有经历过创作甘苦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的。在北京出版社出书之前,这部作品分两期在《长篇小说》季刊连载,前一半发稿的时候,就已在卷首刊出全书每一章节的标题,就是你看到的“玉”和“月”的那些篇章,整个框架摆在那儿了,可是后一半还没写呢,编辑看了前一半,相信作者驾驭全局的能力。
读书报:这部小说在25年里拥有那么多读者,为一代代人所喜欢,您觉得,小说凭什么打动读者,成为经典?
霍达:古代有一首民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海誓山盟,惊心动魄,堪称我国先民咏叹爱情的绝唱。如此坚贞、果决、永恒的爱情,今天还找得到吗?《穆斯林的葬礼》中写了上世纪60年代初韩新月和楚雁潮生死不渝的纯真爱情,在那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假冒伪劣泛滥成灾,连阳澄湖大闸蟹都山寨版满地爬,上哪儿找纯真的爱情去?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内心深处才感到对“真情”的饥渴。缺什么就向往什么。
读书报:您料到这部作品会获得巨大成功吗?
霍达:当初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奢望得奖,没有奢望成为“经典”,也没有奢望25年后还能够畅销,当时只是想把爱和死写到极致,把这个“活儿”做绝。一件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作者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是岁月的淘洗,读者的检验。
读书报:1991年,《穆斯林的葬礼》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请您讲一讲获奖的情况。
霍达:当时我正生病,和外界很隔膜。人家说“你获奖了”,我也笑不起来。颁奖那天,都没有力气去,是我先生陪着我去的,很勉强地上台去领奖,让记者拍照、录像。至于当时都有什么人出席,什么人讲话,都不记得了。
读书报:读《穆斯林的葬礼》,有如身临其境,真实得令人不容置疑,其中有没有自传的成分?
霍达:韩新月去世50年了,而我还活着,怎么可能是“自传”呢?我也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询问书中的人物的“原型”,甚至委托我“向韩子奇一家问好”。文学作品来自生活,我当然会从生活中汲取素材,但不会是生活的实录,小说的基本技巧是虚构,就看你虚构得好不好。送给你和其他读者朋友两句话,一句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无论他写的是古人今人、男人女人、老人幼童,也无论是英雄豪杰、奸雄佞臣、凡夫俗子,都是他自己的化身,只有潜入这个人物的内心,才能写好。我经常在写作过程中“扮演”各种人物,又哭又笑,家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其实是“入戏”了。另一句是:“作家无所不能。”作品中的人和事不必确曾发生和存在,也不必作者亲历亲为,凭借的是作家观察生活、把握生活、表现生活的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读书报:《穆斯林的葬礼》获奖后,多家拍摄单位都曾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并且不惜付出天价片酬,听说被您婉言谢绝。为什么?您对改编影视剧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霍达:没有期待。一部文学作品转换成影视形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已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读者已经通过阅读原著先入为主,每个读者的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韩新月、楚雁潮,你想做到人人满意,是根本不可能的。《穆斯林的葬礼》曾经拍成电影,看过原著的人都说没拍好,所以我对于拍电视剧就更慎重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电视剧就是商品,投资商要拿它赚钱,无视艺术规律,我对这种操作方式没有信心,宁可不拍,也不愿意把它糟践了。
读书报:您的这个主张,现在似乎有点儿松动?
霍达:总是有各种制作单位找到我,有人跟我说,如果现在不拍,等我去世了还是会被拍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现在还活着,还能控制他们,如果我死了,就控制不了了。如果在世时没有看到电视剧版的《穆斯林的葬礼》,也将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的态度是,不要一概拒绝,而是从中选择有诚意、有实力、有艺术追求的拍摄单位,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为此作作努力,也未尝不可吧?
庆幸今生,亦文亦史
读书报:您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史学家马非百研究中国历史,但后来并未走专门治史的路,而是迈进了文学之门,这是不是一个误会?
霍达:不,作家首先应该是史学家、思想家,我至今感谢历史老人非百先生把我引上了正路,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读书报:是谁激发了您在文学上的努力?
霍达:是太史公司马迁,他以无与伦比的文学笔致,书写了彪炳千秋的历史。翻开《史记》,随便找一篇《项羽本纪》,随便找一段“鸿门宴”,写得剑拔弩张,绘声绘色,完全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这就是我的文学生涯所宗:“亦文亦史”。没有史家的心胸难以为文,没有文人的才情难以为史。
读书报:您的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霍达:青少年时代从写作散文开始,说不上哪一篇算是“处女作”了,真正具备一定篇幅和一定质量的,是上世纪70年代先后创作的两部剧本。一部是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写是的儿童和动物题材,很有趣味,茅盾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得了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奖;另一部是历史剧本《公子扶苏》,也就是后来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的《秦皇父子》,这就走上“亦文亦史”的道路了。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这种意识清晰吗?
霍达: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是阴历七月七,我穿着白裙子,披着月光,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桌上,等啊等啊,就想听听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有没有哭。夜里12点了,我真的听见了牛郞织女在窃窃私语——现在想想,这可能是我的幻觉,就凭着那种感觉,把它写出来了,那算不算“处女作”呢?当然,那时候并不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职业作家。一个人以什么为业?也许是当教师,也许是卖豆腐,也许是炸油条,职业是挣钱吃饭、养家糊口的工具,未必就是你的兴趣所在,大部分人就是这么生活的,但从少年时代起,我心里就有一个世界——文学世界,将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这个爱好是改变不了的。我庆幸,今生今世以写作为业,爱好和职业完全一致,一生的心血都付与文学。
读书报:童年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您小时候肯定也阅读了大量的作品。谁的作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霍达:小时候,找到什么看什么,有的书残破不堪,前后都没有封面、封底,从半截儿看下去,也饶有兴致。长大一点儿,就喜欢读《史记》了,百读不厌。但我不是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性格,从小喜欢学着写作,注意观察生活。比如,我在小学的时候,听奶妈说起陈年往事,某某人穿着五花格大衣,她是顺口说的,我就记住了,那个时代的人,穿“五花格”大衣,后来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信手拈来,于细节处显出时代感、历史感。
读书报:读您的作品,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感,我想,这就是“亦文亦史”的魅力。请问,作家应该如何把握历史、表现历史?
霍达: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辨。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因此,广义地说,一切小说都是在写历史,差别只是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深度和广度,肤浅的作品只记录下浮光掠影,而深刻的作品则写出了时代精神、历史本质。
读书报:您的《补天裂》当时在大陆、香港两地引起很大反响。您曾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创作这部作品据说特别艰难,最大的艰难在何处?
霍达:前面说过,写历史小说需要具有“穿越”历史的功力。一百年前的香港,不要说我,连香港人也不熟悉,我只有下最大的功夫钻进去,用两只脚踏遍港岛、九龙、新界,采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查阅中外文献上千万字,凡是相关的书籍、资料,片言只字也要搞到手。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创作,就是在历史框架的严格限制中发挥创作自由,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很难,但很过瘾。创作就是要挑战难度,没有难度也就没有高度。
一生能留下片言只语,足矣
读书报:《海棠胡同》之后,您又有什么新作问世?
霍达:这两年身体不好,以休养为主,只发表了一些散文。文学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一部作品的诞生要经过孕育、分娩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很快,一首诗的灵感袭来,如电光石火,刹那之间就诞生了;也许很慢,一部长篇花费作者几年、几十年的功夫,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要以数量来计算作家的劳动,他不是机器,一按电钮就吐出产品。其实早在《海棠胡同》之前,我已经在酝酿一个长篇,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写得很累,很痛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放在那儿,也不急于完成,更不急于发表。
读书报: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累?
霍达:书名暂定为《悟》,写一组女性的命运,写人生的醒悟。解剖人生是很残酷的,手里握着笔,就像拿着手术刀,不忍下手啊!感情收不住,太脆弱了!
读书报:“五十而知天命”,您现在应该什么都看得开了,承受能力更强了吧?
霍达:如果你什么都看开了,就不写了。好比登山,你费时费力地爬上去,干什么?不就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山上的风景吗?如果上山之前就看开了:咳,哪儿的风景都差不多,有什么看头儿?如果这样,你就根本不用上山了。写作就是一个上山的过程,寻访风景的过程,探求未知数的过程。
读书报:您对自己如何评价?
霍达:没有评价,说好说歹是别人的事儿,我只是力求做好自己的本分。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但大浪淘沙,历史无情,这由不得自己。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深情地吟咏明月?可是每逢中秋,人们首先想起的、反复传诵的只有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和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取代,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张九龄一生写了很多诗,但真正流传下来的,深入人心的,只有这么两句,这也就很不错了,别人还默默无闻呢!想到这些,自然心平气和,让岁月去淘汰吧,让历史去选择吧,一个作家的一生,如果能有一篇文章,一首诗词,甚或片言只语流传下来,足矣!
读书报:您现在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霍达:养病,看书,思考。虽然足不出户,但仍然关注着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今天走到什么地步,下一步将怎么走。关于创作,一些构思正在酝酿,将会再写几个剧本,还没有成型的作品不愿意炒作,不说也罢。日常所做的,就是赋诗填词,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发表,是自己在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