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罗兰的家乡情
2017-12-13 00:15
红遍中国的台湾女作家罗兰日前辞世,享年96岁。很多人知道她都是从她那著名的《罗兰小语》开始的,现在看来这本书似乎就是中国最早的心灵鸡汤。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罗兰的籍贯其实是天津,这期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位长在天津,红在台湾的女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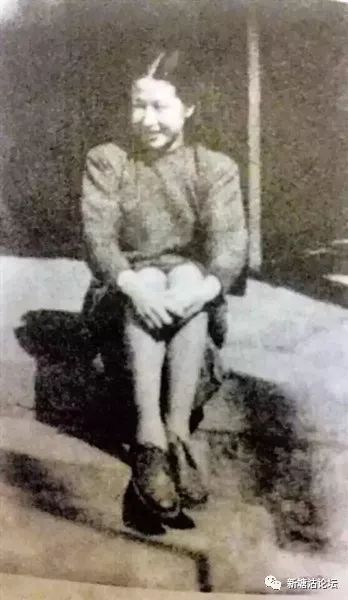
出身于豪门大户 上学却囊中羞涩
1948年5月1日,台北的“台湾广播电台”传来了一个女生的声音,她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显得格外悦耳,这个声音一播就是十五年,那些充满哲理和感情的人生物语,应该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心灵鸡汤。当女生响应了听众的要求,把她的广播文字结集出版,取名叫做《罗兰小语》,立刻洛阳纸贵而风靡一时。从此,出版了《罗兰小语》五集、《罗兰散文》七集,还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书信杂文集和论文集,在上世纪整个60-80年代罗兰红遍全台。1988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罗兰小语》,在广州,在上海,在京津也接连出版,在全国范围引起了空前热度的“罗兰热”。那么,罗兰到底是谁?
罗兰其实是笔名,本名叫靳佩芬,生于1919年,天津宁河芦台人。她的家是当地大户人家,高祖最先开创家业,逐渐成为芦台首富。靳家的大院子有多大呢?它的大门在芦台北街上,四进的大院子,东西两边的跨院,第五进是横跨东西跨院的大花园,直抵蓟运河畔。后来靳佩芬下乡教书的时候,带着她五年级的学生到她家玩,一个女生说你们家好像一座大庙啊,另一个说房子那么高,站在院子里好像要晕倒。没见过祖父的靳佩芬对于这个深宅大院充满了喜爱,她在自传中写道:我极爱蓟运河畔的这片住宅。
然而靳佩芬出生的时候,这个大家庭早已经家道中落了,她父亲因交不起学费几乎辍学,是同学集资挽救了他,毕业以后,她父亲来到塘沽久大精盐公司上班,于是她和母亲一同随着父亲搬到塘沽的职工宿舍去住了。从带花园的深宅大院,到连路和路灯都没有的泥泞狭小的平房,靳佩芬心理上并没有落差,反而觉得小家更温馨。
1925年久大精盐公司成立职工子弟小学(明星小学)的时候,小靳佩芬正好达到学龄,第一次上课就遭到一个打击,她的芦台口音引起了同学的哄笑。她哭着回家,说什么也不要再去上学了。她父亲安慰说:“塘沽话在我们听来一样可笑,以后你听班上哪一位同学说话好听,跟他学就是了。”靳佩芬觉得她的邻桌冯以玉说话的口音最好听,她马上决定就向这个同学学习。这个决定几乎影响了她一生的命运。那时候政府正在推行国语,这位冯同学说的正是国语,这使小靳佩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习国语,使她得以在天津广播电台、台湾广播电台讨生活,“说话”居然成为她受用一生的技艺。
小学毕业了,多数同学都要上南开中学,当大家听到靳佩芬要上师范学校的时候,都很吃惊。她为什么要上师范学校呢?因为她要为父亲分忧。大家庭败落了,小家庭只靠父亲一个人的薪资养活全家,关键是父母给她生下了六个弟弟妹妹,所以父亲的意见是让她上河北女师。河北女师,原址就是现在的天津美院,这里留下了靳佩芬太多美好的回忆,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久大、永利两厂是抗日企业,面对日军的进攻,不为利诱,毅然迁厂,人员全部南下,只剩靳佩芬的父亲一人留守。她则被父亲送去乡下做了一名乡村教师,学师范派上用场了。
四十年重归故里 遥望海河泪婆娑
后来靳佩芬误打误撞乘着招商局“和顺号”客轮,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凭借她在塘沽明星小学学的国语,河北女师培养的能力,天津广播电台的历练,第二天就找到了工作,依然是广播电台,然后是恋爱结婚生子,与家乡这一别就是40年。当她受了40年思乡之苦,1988年终于踏上这片土地那一刻,她的心情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聆听广播电台主播那沁人肺腑的声音吧。
“我没有去看北京城里的大杂院,我急于去看的是天津。未曾重履天津以前,我一直是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人,我出生在芦台,长大在塘沽,这两个地方过去都属宁河县。我一直以为,天津只是我念书的地方,抗战期间受苦受难的地方,它写的只是12岁到29岁的我。而这次重履斯土,却发现,静海和塘沽都已划入了天津市。我也才发现,在心情上我是如此地属于天津。当我在与它阔别四十年之后,在此坐火车由北京抵达天津北站——我少年时,每个春假、暑假和寒假,都从这里回家与回来,记录着父亲的慈爱和我成长的车站,它竟然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小巧精致又方便,使我立刻投入时光隧道回到从前。出站时,当我就在一拐弯的地方叫到了一部出租车,听到那司机一口天津话:‘上哪儿去?大姑’的时候,我就立刻找回了四十年前的自己,找回了那个名叫靳佩芬的,从父亲塘沽久大精盐工厂的办公室出发,来到这里上学的那个得宠的女孩。天津记录着我最繁华的青春。”
她是如此熟悉这个地方。出租车路过律纬路、黄纬路时,她说:“啊,先别去找旅馆,前面往右转,我的母校在天纬路!我四十年没回来了!我要去看看!”她怀着激动的心情踏进校园,尽管大门牌匾上写的已经不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师范部中学部”的字样,但这些字样已经镶嵌在她心里,眼前的一切都与她心中的记忆模糊地重合了。她兴奋地在校园里穿行,这里是食堂,诱人的地方;这里是音乐馆,已经变成了招待所,这与她记忆貌不合而神合的飘忽错位,更加让她享受了梦一般的美好。
到了酒店,她的房间正对着海河,这个当年搭乘“和顺号”轮船启程,独自飘离大陆去到台湾的起点,四十年后的今天,她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