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 又见叶嘉莹老师
玉茗堂前 2019-09-12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光明日报 Author 郑培凯

光明日报
思想品格 人文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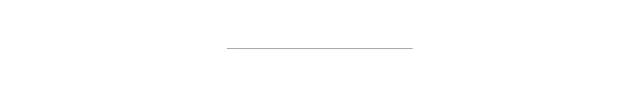
每一个字从她口中说出,就像天使在云端摇着铃铛,散发美妙的天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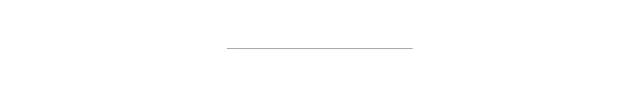
将近十年没见到叶嘉莹老师了,心中时常挂念,偶尔从电视及报章看到她的消息,虽然只是零星片段的新闻,但总还是吉光片羽,带来令人高兴的佳音。她精神奕奕,依旧和往日一样,充满着生命的激情解说诗词之美,以甜润丰美的北京口音吟诵优美的古典诗篇,这让我感到无限温馨,并在心底为她祝福,希望老师长此以往,像50年前在台湾大学给我们讲课那样,一直讲到地久天长。
然而,还是怀念跟老师在一起的日子。那时的我们沐浴在谈诗论词的春风里,聆听每一个字从她口中说出,就像天使在云端摇着铃铛,散发美妙的天籁。怀念美好的往事是容易上瘾的,就像听一段喜爱的乐曲,来来回回,永远不嫌重复。

从1970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几乎每年暑假,我们都会在波士顿相聚,朝夕相处,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数据,翻阅馆内富赡的图书收藏。经常几个人一道,在不同院校的餐厅用点简餐,谈论超然世外的诗文乐事。周末的时候,老同学会安排聚会,每人烹煮自己拿手的菜肴,童子请观音,和叶老师共度美好的时光,品尝各人的家乡菜,互道背井离乡之后的漂泊,谈说个人风风雨雨的经历,好像我们都来自一个家庭,可以在古典诗词的熏陶中相濡以沫。回想起来,往事像漂浮在云烟里的织锦,记忆的阳光偶尔投射过来,一片璀璨。
去年有南开大学师生来香港访问,特别要求和我相见,说带来了叶老师的问候。我就跟他们说起,十多年前曾邀请叶老师来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授了一个学期的古典诗词,后来还帮着出版了演讲录,题作《风景旧曾谙》,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繁体版,内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简体版,这是叶老师等身著作中最为深入浅出的一本诗词通论,极受欢迎。南开师生回去之后,居然通过微信,辗转让我听到了老师的谆谆教诲:“郑培凯啊,你好不好啊?我一切都好,这些年就在南开住下来了。同学让我说几句话,说可以传给你,听得到。我今年93岁了,还站着讲课。我们都好多年没见了,很想念你们。有空来天津,来我这里看看。他们给我建了迦陵学舍,读书、写作、教学,是很宜人的环境。”

听到老师清朗的声音,有似慈母的召唤,不禁联想到陶渊明《归鸟》诗中的一段:“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探望老师的心念便日益强烈。终于在春暖花开之时,我专程北上天津,到南开大学去问候十年没见的老师。
见到叶老师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很难形容,高兴是不必说了,还有着无限的欣慰与惭愧。老师神采奕奕,风神依旧,她伸出双手和我对握,像年轻人那么坚定有力,笑靥如春花盛放,哪里像93岁的人?她兴奋地向我抱怨,现在比以前还忙,得看许多人寄来的著作,整理文稿,还得给不同时期的老学生上课。

我写了两幅字,都是老师的诗词,裱好镜框,带来作为贽见之礼。一幅是她上世纪60年代在哈佛听张充和与李卉演唱昆曲所写的诗,另一幅则是她写晚年心境的一阕《鹧鸪天》:“似水年光去不停,长河如听逝波声。梧桐已分经霜死,幺凤谁传浴火生。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老师看着我的字,笑说,凤凰浴火重生,只是神话,不是人间现实,幺凤已是人间老凤了。我说,神话就是现实经历写成的诗,您来南开二十年,柔蚕依旧吐丝不断,天孙不是已经织成了一匹灿烂辉煌的锦缎吗?老师笑了,笑得如此开怀。
本文作于2017年

鄭培凱教授,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台灣大學等校。1998年於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並擔任中心主任。現任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2016年獲頒香港政府榮譽勛章。
著作所涉學術範圍以文化意識史、文化審美、經典翻譯及文化變遷與交流為主。著有《湯顯祖:戲夢人生與文化求索》、《賞心樂事誰家院》(《多元文化與審美情趣》《歷史人物與文化變遷》《文化審美與藝術鑒賞》全三冊)、《在紐約看電影:電影與中國文化變遷》、《茶道的開始——茶經》、《茶餘酒後金瓶梅》、《雅言與俗語》等三十餘種。主編《近代海外漢學名著譯叢(百種)》、《史景遷作品系列》、《春心無處不飛懸——張繼青傳藝記錄》、《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