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故土”与“超越故乡”:贾平凹与莫言小说文化母本与叙事空间营建之比较
王西强 莫言研究 Yester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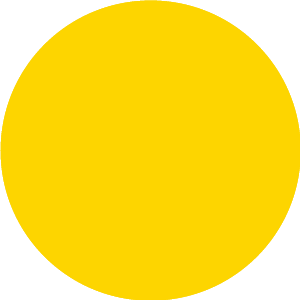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回归故土”与“超越故乡”:贾平凹与莫言小说文化母本与叙事空间营建之比较王西强
摘要:莫言和贾平凹同为“从乡村到城市”的“文化迁移者”,都以生养自己的“故乡”及其文化深蕴作为其文学叙事的文化底本和空间蓝本。莫言深受古齐国兵家“诡/诈”文化基因、志异志怪文学传统和开放、大气、奇伟、神秘、想像力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影响,以齐地文化为其文学创作的文化母本和审美“血地”;贾平凹在文化精神、审美气质和语言风格上深度体验、细致书写其长期生长浸淫其间的“商州山地文化”和“商山隐逸文化”,以其作为文学创作的“文化母本”。莫言和贾平凹都在学习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地调动其故乡故土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使用“高密东北乡”和“商州山地”作为其叙述故乡故事的叙事空间。所不同的是,在其“故乡书写”中,莫言不断对“高密东北乡”的时空外延进行拓展,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涵盖一切事件、包罗所有人物、容纳各种情绪的叙事场,“高密东北乡”是莫言通过“想象”“再造”的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故乡”;贾平凹笔下的故乡“商州”的时空外延基本上没有得到拓展,“商州”一直都是其实在的“故乡”商州,其间的人事,在文化外形和精神内质上都具有典型的商州特色,是贾平凹通过文学描写“再现”出来的一个属于全体商州人的“实在的”“文学化的故乡”。
关键词:莫言;贾平凹;“高密东北乡”;“商州山地”;文化母本;叙事空间营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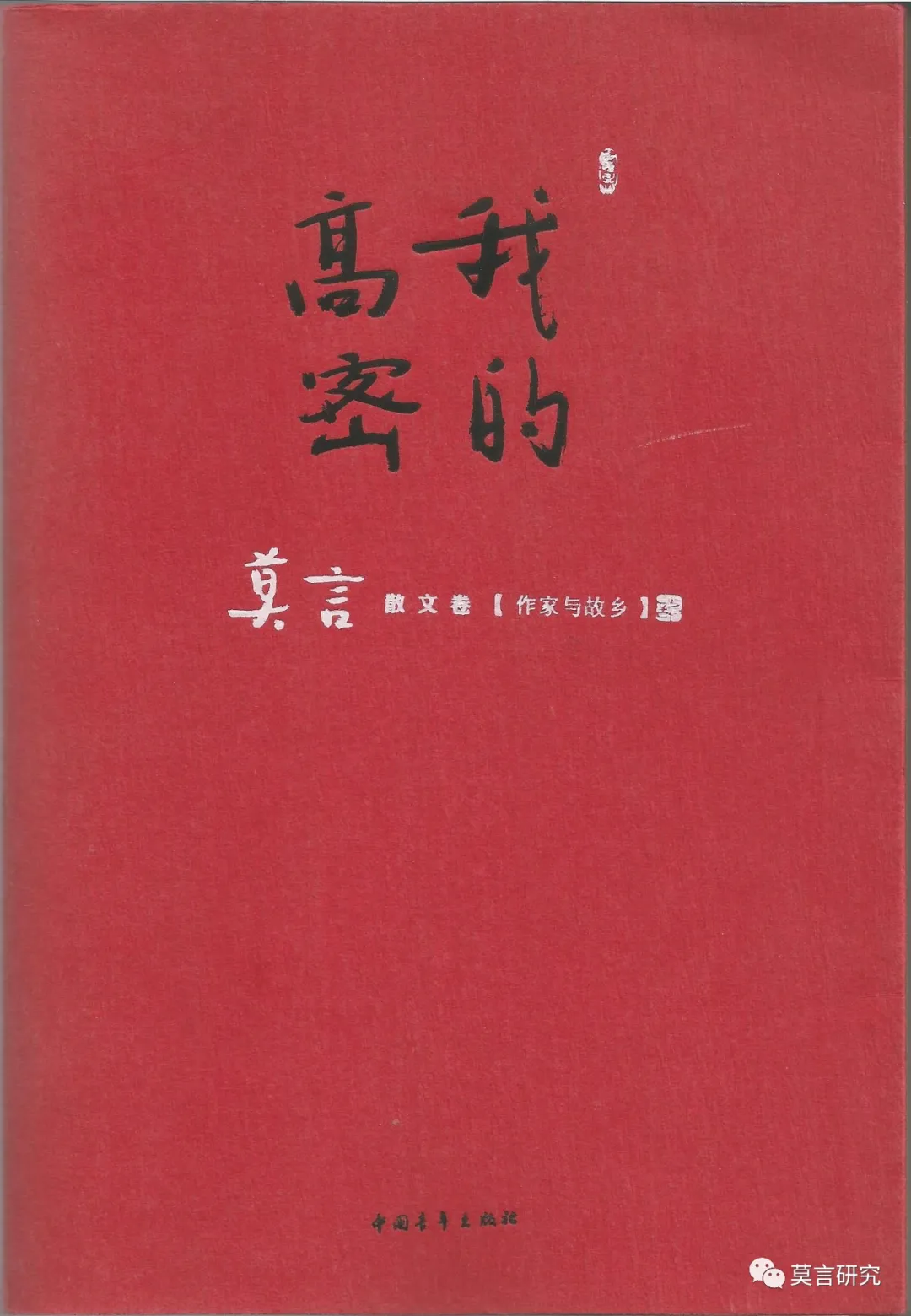

同是“出身乡村、客居城市”的作家,莫言和贾平凹的文学活动轨迹和文学思想的变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们是同代人,经历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变革和历史变迁,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迁移;他们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并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呈现并批判了当代中国社会、人文的“病”与“变”;他们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参与开创并代表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两个地域文化作家群——“鲁军”和“陕军”;他们笔耕不辍,求新不断,均有大量作品出版,并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作品的叙事艺术和审美风格,多次引起批评热潮;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间,他们通过众多精彩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有深度的反思与批判,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他们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个性思考和民族性时代印象,记录了大变革时代的民生、民风、民情、民瘼,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变革的审美记录者。
莫言和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高产、高质作家,均多次以其作品引起文坛评论热潮,均多次获得国内外诸多文学大奖,均有作品被国外翻译家译成外文,获得世界文学声誉,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很强的叙事创新自觉,均不断通过叙事探索和创新为读者奉献了深具地域色彩和中国气派却又个性鲜明的文学精品。我们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向西方文学阅读期待展现了中国作家在叙事艺术和现实关怀层面上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通过独特的“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与历史”,“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1];而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也具有同样的艺术特质:在叙事上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立足自己熟悉的“商州山地”和“西京城”,不遗余力地表现着山民与市民的喜怒哀乐和时代变迁。
作为“从乡村到城市”的“文化迁移者”,莫言和贾平凹都以生养自己的“故乡”及其文化深蕴作为其文学叙事的空间蓝本和文化底本,不断结撰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和鲜明个人气质的“乡村/城市故事”,分别营造出了具有中国气派、享誉世界文坛的“高密东北乡”和“商州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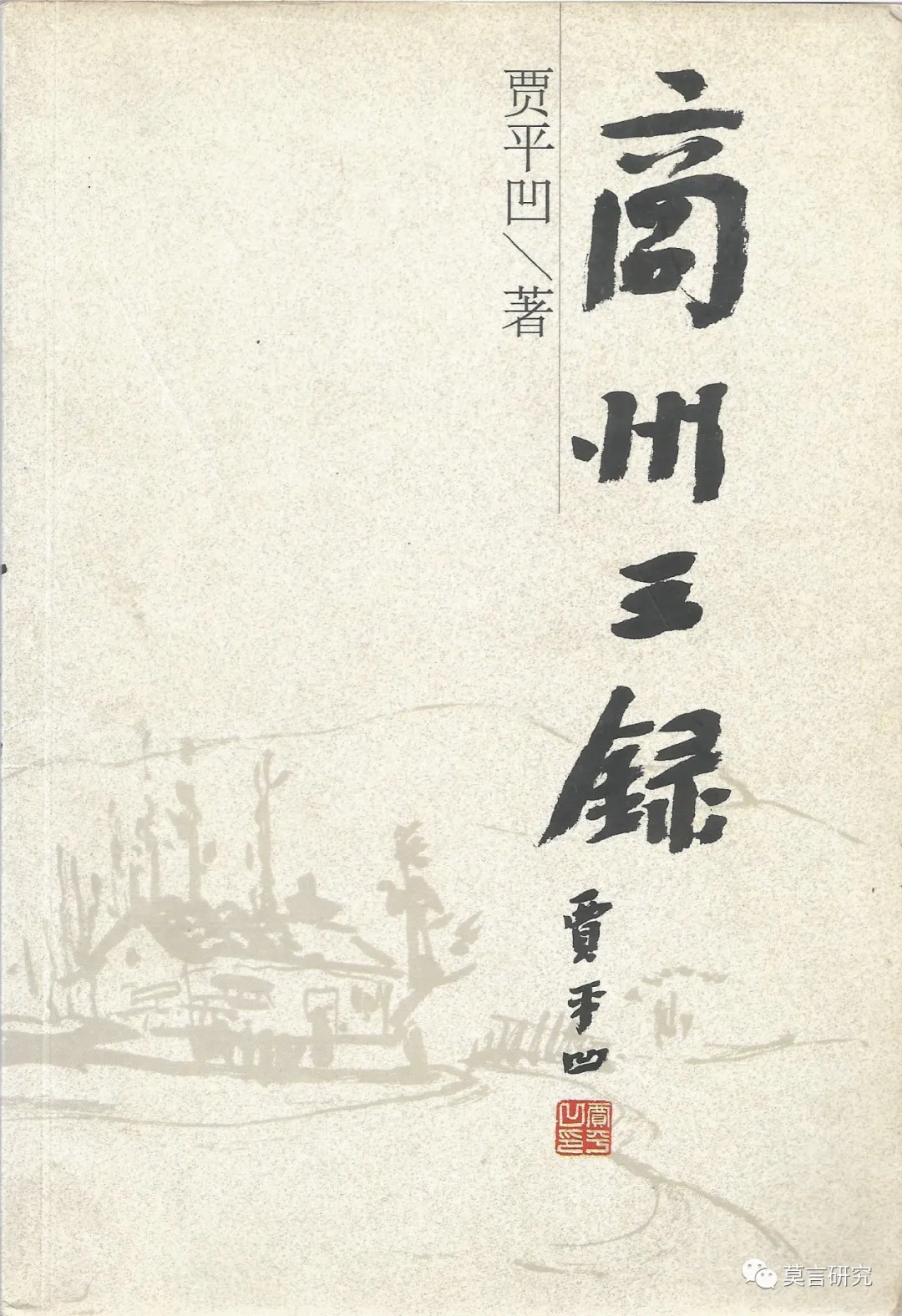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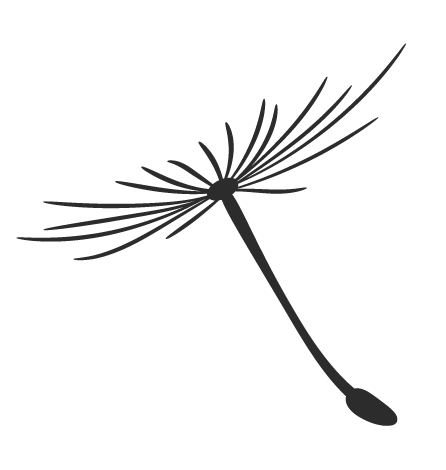
一、莫言与贾平凹小说叙事的文化母本与审美“血地”
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丹纳指出了影响艺术家产生及其艺术风格形成的三种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在比较分析莫言与贾平凹小说艺术风格的过程中,因其所属种族与所处时代一致,我们重点关注“环境”——物质生存环境和故乡文化母本对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影响。
从两位作家出生地的地理位置和所属的文化样态来看,莫言出生长大的高密县境属古齐国故地,齐地近海,齐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大气、奇伟、神秘的海洋文明的特点。古齐国是兵家文化的发祥地,兵家文化大开大合、神秘“诡诈”、有大气魄。因此,在民俗上,齐地的民俗和民间文艺充满“奇思怪想,天马行空,取材随意,情趣盎然”[2];在民风上,齐人“刚健不屈,侠肝义胆,豪放旷达”[3];在文学上,齐地民间文学资源丰富,民间故事多涉神鬼狐怪,想象丰富大胆,寓民间正义于奇谭怪事之中,产生了《聊斋志异》这样志异志怪、神秘奇幻、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巨著。新中国成立之后,董均伦和江源收集整理山东民间故事,结集为《聊斋汊子》和《聊斋汊子续集》,其中的故事多流传于齐地,是齐地志异文化的遗存,其中有多个故事和人物都被莫言化用,成为其小说的故事母本和人物原型。莫言有一本颇具志异色彩的短篇小说集,题为《学习蒲松龄》,其中的《学习蒲松龄》、《奇遇》、《夜渔》、《良医》、《翱翔》、《嗅味族》、《草鞋窨子》等篇什无疑是其追忆童年“耳朵阅读”经历和向故乡文学大师蒲松龄学习、致敬的作品。在提及幼年在故乡听到的故事时,莫言说:“这些故事一类是妖魔鬼怪,一类是奇人奇事。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故乡最丰厚的馈赠。故乡的传说和故事,应该属于文化的范畴,这种非典籍文化,正是民族的独特气质和禀赋的摇篮,也是作家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4]可以说,受故乡古齐文化影响的莫言一身灵气和“匪气”,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聊斋志异》等志异志怪小说和明清笔记小说的叙事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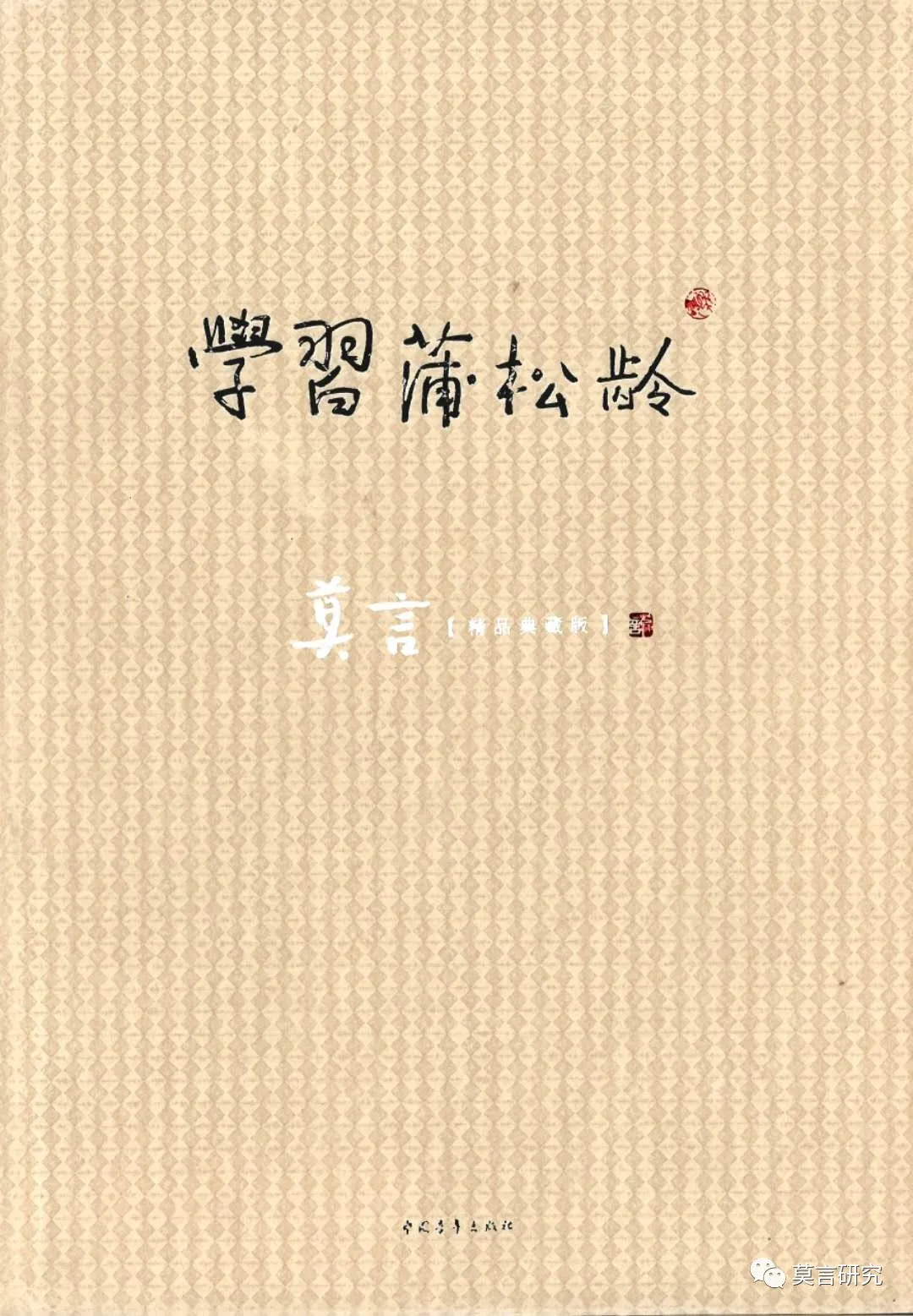
故乡的风土人情、故人故事,无疑是作家进行创作所要依凭的一种重要文化资源。关于故乡对其创作的影响,莫言曾说过:“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5]莫言在农村生活期间,乡村娱乐项目少,讲故事是农村人闲时尤其是夜晚打发时间、对孩童进行道德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对于作家莫言来说,这恰恰是一种有效的文学教育方式,是一种“耳朵的阅读”。莫言自述幼年爱读书,其教育经历也基本上是自学,但正是这种自由的文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可以免受正规教育中某些程式化的意识形态性规范和认知限制,从而使他的文学天才得以自由舒张和发展;莫言后来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的学习,则引导他对其既有的创作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正是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超越故乡》中,莫言认真而自觉地思考和总结了“小说家与故乡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小说家创造的小说与小说家的故乡的关系”[6],指出“故乡是‘血地’”[7],认真思考、总结并坚定了坚持以“高密东北乡”作为其整个文学世界核心叙事空间的信念。
凡此种种,都是莫言生长、浸淫其间的文化和文学教育环境,敏感多思的莫言长期受这种具有海洋文明特征、具有想象力启发作用的文化资源的影响,加上他童年少年时代聪慧敏感却又内心孤独,在长兄的引导下,在写作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文学氛围里,莫言在学习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地调动其故乡故土的文化资源,将其变成了个人文学创作的“文化母本”,并以其作为审美精神依托,创造性地使用“高密东北乡”作为其叙述故乡故事的叙事空间。
就莫言小说已经表现出的审美气质和文化样态来看,开放大气的海洋性齐地齐风齐文化赋予了莫言小说以下几种独特的文学气质和美学特征:众声喧哗的杂语交响、虚实相生的叙事结构、煞有介事的叙事腔调、天马行空的意象交织、泥沙俱下的语言浊流、深沉刻薄的思想能力、亲切真诚的民间立场和模糊朦胧的文本表意等。莫言小说中的种种创新与陌生化追求,贯穿其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不管是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关系的设置、故事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的身份、语言风格还是意象的营造,都具有明显的多变性和复合性。不管评论界将其定义为作家有意识的锐意创新、努力求变,还是将其评价为借鉴模仿、先锋作怪,甚至是将其贬斥为乱耍花枪、故弄玄虚,但是大家都无法否认莫言作品本身的生气、灵气、大气和鬼气,而这“四气”恰就是齐文化的精气所在。
贾平凹出生在秦巴山腹地的古商地——商洛市丹凤县,这里地处陕西省东南部的秦岭南坡,西邻西安,东通鄂豫,山岭交错、千沟万壑,沟大、沟多、沟深、石多、土薄;这里是秦时卫鞅的封地,商山四皓[8]的隐居地。北有百里秦岭苍茫大山使之与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西安)相阻隔,四围皆山,在地理上处于南北交界处,却是偏南方的气候,山水灵秀。地理上的闭塞,在客观上造成了经济的落后和思想的保守,造就了商州的“美丽与神秘”,使之适合隐逸。这里是典型的内陆山地,不便农耕,商业也不发达,因而民风淳朴。同时,关中、长安(西安)地区是中国古代佛道文化的核心地带,佛道文化对当地民风和文化思想影响最为深远,而中国古代隐逸文化正是佛道文化中“出世”思想的重要一脉。受此影响,商州山地中形成了相对封闭又自成一体的“商州山地文化”和“商山隐逸文化”,这种文化样态具有中国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即在中心城市的左近山区,常常会有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或出世的知识分子隐避山林、晴耕雨读,使得中国古典文学中长有田园文学和山林文学两脉。隐于山水或生长于山地的知识分子,其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上都是偏于出世的,因而文风、格调也偏于清淡、静穆、平和,追求节奏的舒缓和审美的雅致。
与莫言的父辈世代务农不同,贾平凹出生在农村读书人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对我是寄了很大的希望的,只说我会上完初中,再上高中,然后去省城上大学,成为贾家荣宗耀祖的人物”[9]。贾平凹接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恢复之初就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接受了正规系统的文学教育。同样是早年敏慧,莫言多语,贾平凹少言。早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对两人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贾、莫两位都多次自报,在《我是农民》和《变》中各有详述。在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文学成长过程中,都有多次“还乡”经历,他们出身乡村,客居城市,“精神还乡”。正是在一次次的“还乡”之中,他们不断对比着“城”与“乡”的差别,尤其是在新时期的文学变革大潮中,他们都在认真思考、寻找着文学创作的突破口和叙事展开的“文化场”,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生养其间的“故乡”“故土”。在试笔成功之后,他们都不断加大对“故乡”的书写力度和挖掘深度,不断开疆拓土,但是两位作家努力的方向和效果却又大不相同,此处按下,下文详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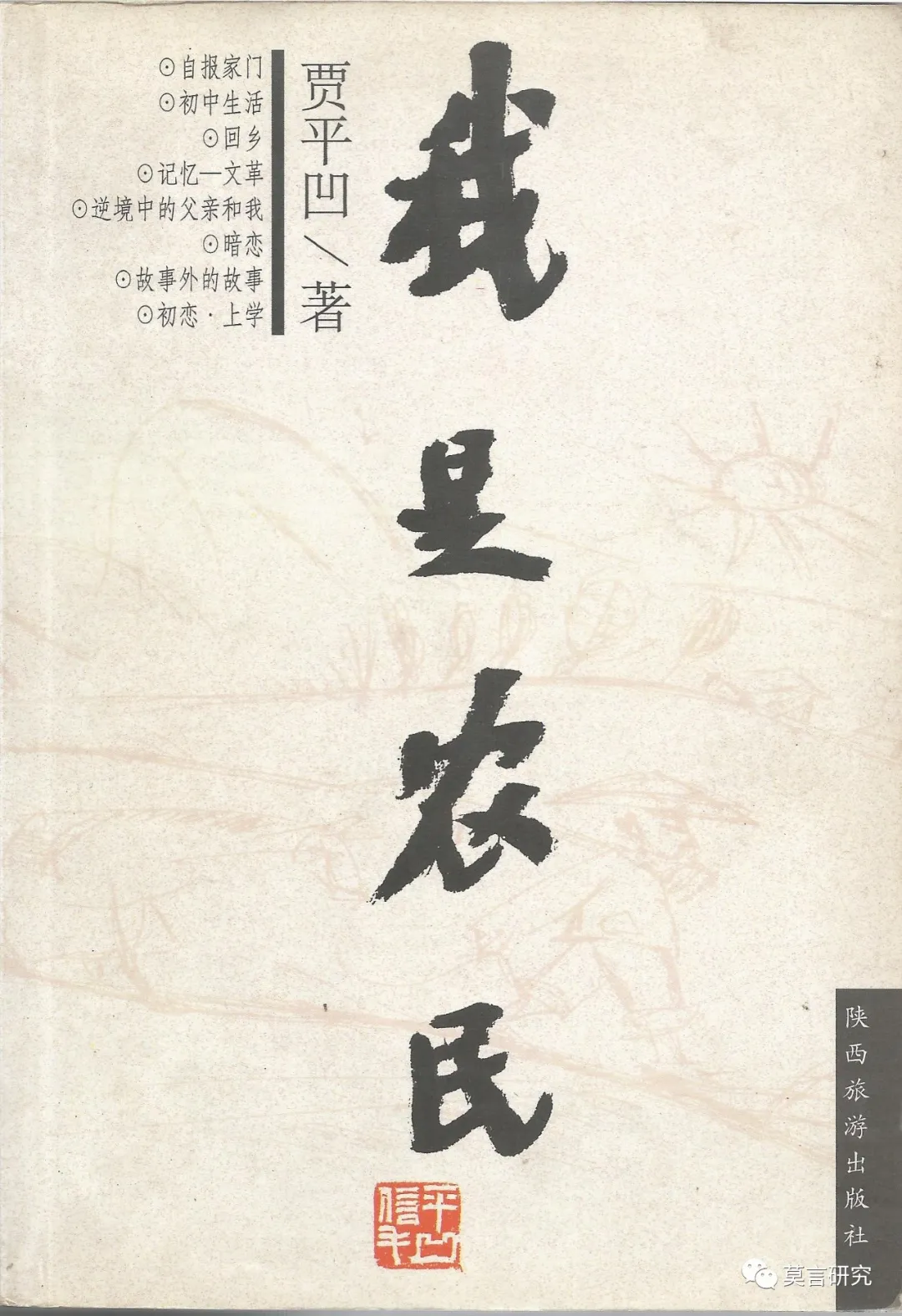
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有一个“回归商州和创作质变”的转折,“1983年初,贾平凹在遇到创作的大苦闷时,产生了一个大行动,一过春节,他就重返商洛。......思想上经过苦闷之后的深刻反省,行动上领略商州的大山大河,感受时代迁转流动的风云,使贾平凹创作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越。......他不但更深入地认识了商州,也吃惊地发现了自己;不但找寻到自己最适宜的描写地域,也从商州民俗向中国文化系连,摸出了同商州世界相应合的美学精神。”[10]此时贾平凹在创作上已经初有成就,这次“回归商州”其实是一次文学审美精神上的回归,是在有了城市生活经验之后反观“故乡”“故土”,是一种“还乡书写”,这与莫言在《白沟秋千架》中首次使用“高密东北乡”作为其叙事空间来铺陈故事是一样的,是与当时的“寻根文学”主潮合拍的。而这也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等的“还乡书写”是一脉相承的。贾平凹在这次回归之后创作的《商州三录》、《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商州》等篇什,都明显着力于展现商州山地文化的魅力,在文风和格调上也明显倾向于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中散文和笔记小说的笔法,追求简洁、雅致,尚白描,而这种文风的变化也是与贾平凹的阅读经验紧密相关的,“在此之前他阅读过各方面的杂书,熟悉了中国古籍中洒脱简括富于神韵的叙写文字,这次他每到一县,先阅读县志,县志是一种地域史,对该县辖区的地理、历史、民俗、人物都进行纵的和横的大扫描。这种方志文体的全局眼光,质实而又通脱自由的描述,给贾平凹创造新文体以极大的启发,正应合了他俯瞰地、历史化地表现商州的形式需要。”[11]我们不难推断,阅读这些由商州历代士人编撰的地方史志,无疑会让贾平凹在文化精神、审美气质和语言风格上更深刻地体认“商州山地文化”和“商山隐逸文化”的精髓,以其作为文学创作的“文化母本”,并以这种自己携带的地域性文化基因去对接、“系连”中国文化,从而可以“较多地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承的古典艺术美学精神。”[12]因此可以说,费秉勋先生所谓的贾平凹“摸出了同商州世界相应合的美学精神”,无疑是指贾平凹对于“商州山地文化”与“商山隐逸文化”的发现与继承发扬,这倒是与上文论及的“商山隐逸文化”的特点颇有渊源。而贾平凹对“商州”的发现,其实就是对其个人审美气质的发现和再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审美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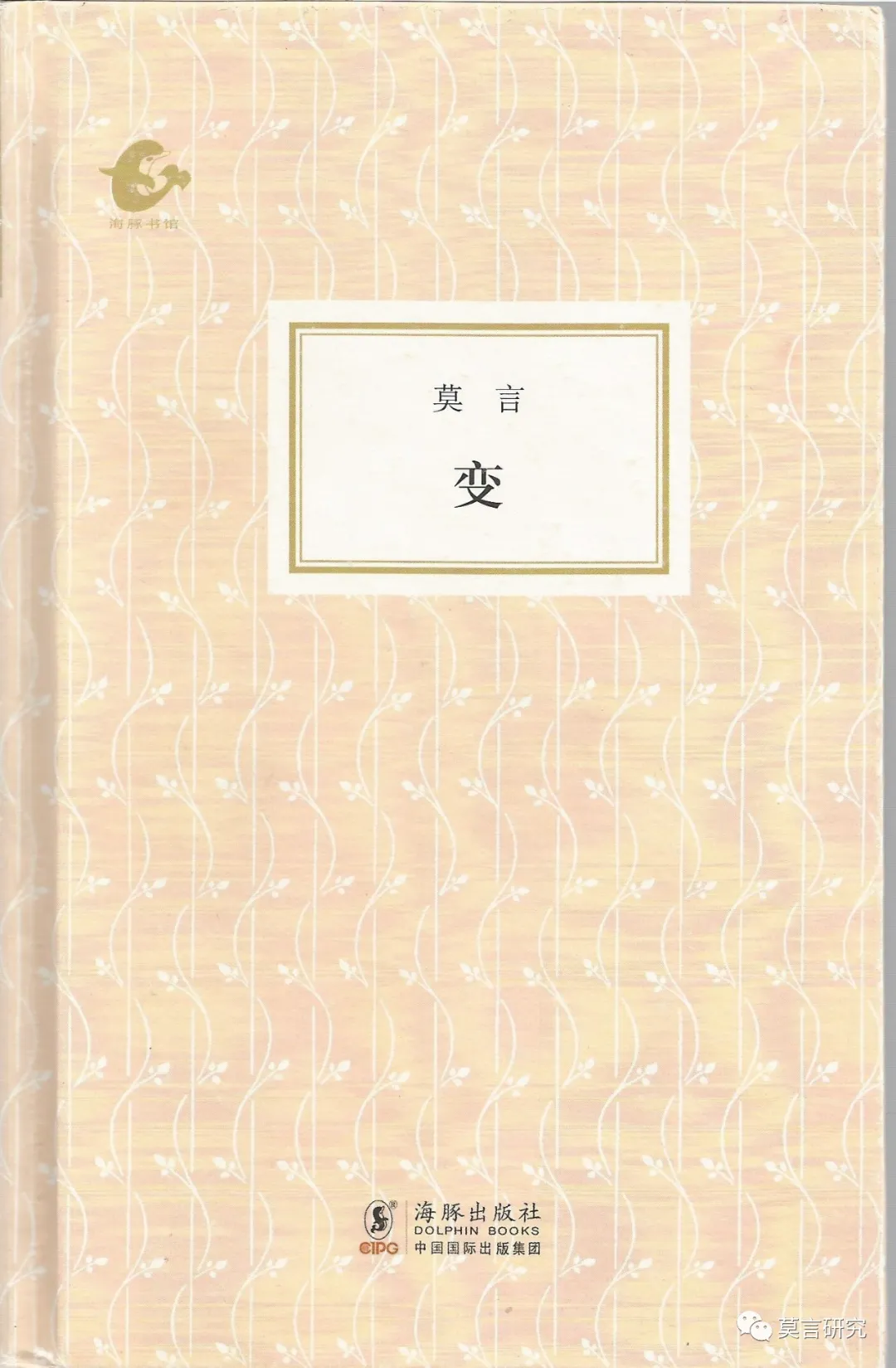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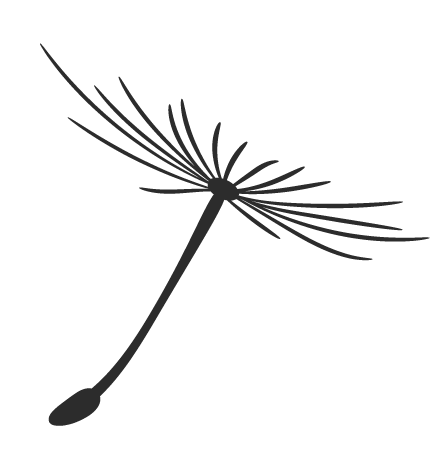
二、“文学故乡”与“文学化的故乡”:作为叙事场的“高密东北乡”和“商州山地”
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关于“故乡”,莫言更多地强调其早年农村生活的苦难、孤独与饥饿,在对待“故乡”的态度上,是爱恨交织的。因此,在其“故乡书写”中,莫言并没有对“高密东北乡”表现出太多的温情和回望时的怀念与向往,他没有固守“高密东北乡”的实在地域,而是不断对其时空外延进行拓展,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涵盖一切事件、包罗所有人物、容纳各种情绪的叙事场。贾平凹对待“故乡”的态度则是前后变化的,早期多以温婉唯美的笔调摹写故乡人事、民风民俗和自然山水,有空灵高蹈的庄禅味,是学习孙犁《白洋淀纪事》风格而对故乡山水田园牧歌般赞美式的回望;后期则反思改革和现代文明给乡土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书写被现代文明熏染了的乡村和自然的种种不美好和无奈。作为叙事场的故乡“商州”的时空外延基本上没有得到拓展,故乡故人故事都还是作家“还乡”时的观察所得,“商州”一直都是贾平凹的实在“故乡”商州,其间的人事,在文化外形和精神内质上都具有典型的商州特色,而不像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的人物和故事,多是挪移而来,包罗万象。“莫言地理建构的历史跨度很大,自清末以来至今天一百多年历史的重大事件、细枝末节、野史狐禅尽收笔底,这与鲁迅、沈从文他们从一己经验出发的、对于故乡的现时进行描写是不一样的,也因此他的作品多长江大河式的长篇巨卷,这反映出作家想以自己建构的一小块地理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缩影、历史寓言的野心。”[13]
关于“高密东北乡”这一叙事空间,莫言自己曾做过这样的表述:“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14]我们不妨对这段话语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解读:其一,莫言清醒地认识到了“地理故乡”与“文学故乡”的差异,“地理故乡”是父母之邦,个人的“血地”,而“文学故乡”则是对“地理故乡”的诗意想象与审美扩张,是开放的,可以不断生成新的时空意义,其目的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历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15],是一种展开审美想象的“故乡文化酵母”;其二,这种审美想象的深层次目的是表现中国生活,讲述中国故事,并使小说成为“人类情绪的容器”和“人类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的古老的雄心”[16];其三,因其阅读西方文学经典的经验所致,莫言也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设定了高层次的、与世界文学对话接轨的目标,期待其创作可以获得国外读者的认同和共鸣。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对他这种叙事空间营建努力的最高奖励和认可。
贾平凹书写“商州山地”的目的,却不像莫言那样试图将其营造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叙事场,而只是出于对故乡故土人文的亲近和讲述故事的情感便利,尽管“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的笔下也有同样的功用。贾平凹书写“商州山地”,有着文学和审美之外的现实目的:“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极需要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17]简言之,在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是作为文学想象的“故事”的发生地,是作为叙事的背景和空间场域而被书写的,并非是莫言小说创作的最高目的和最终指向;而在贾平凹的笔下,尤其在其散文和数量众多的“商州小说”里,“商州”就是作者书写的对象和目的,是其文学世界的中心意象。也正因为如此,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在“实在”地理区域基础上的想象性审美生成,是一个被作家想象出来的、美学意义上的“故乡”——“文学故乡”;而贾平凹的“商州”则更多地是作者对“商州”现实世界审美过滤后的艺术呈现,是一个经过作家艺术加工过的现实“故乡”的审美翻版,是一个“文学化的故乡”。
两位作家关于“故乡”的定位有很大差异,莫言“再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再现”了一个属于全体商州人的“商州山地”,并因此导致他们在这两个性质和时空外延均不相同的叙事场里演绎“故乡”“故事”时的叙事身份、情感认同和对待城乡关系态度上的差异。
在莫言的小说中,总有一个显在的、作为故事人物或叙事者的“我”或“莫言”存在着,这是与其“想象故乡”或“故乡想象”的叙事方式有关的。莫言在其小说文本世界里结撰了很多“虚构家族传奇”故事,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和“类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复合人称视角)来讲述故事。作者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无疑是放置这一类故事和叙事人称的最佳场域。这类叙事人称视角的大量使用,是莫言为了增强“故乡叙事”的“我在”感和现场感,是为了获得叙事语境和情感上的参与感和亲近感,是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事空间的紧密而完美的结合。值得一提的是,在莫言小说积极而有效的叙事探索中,叙事视角的变化所带来的叙事美学上的创新是最具有文本试验意义的,这种叙事上的“耍花枪”无疑是与作者所长期浸淫其间的齐文化“志异志怪”的陌生化审美追求传统和兵家文化“诡/诈”的言行方式有莫大关联的。在贾平凹的“故乡书写”或“书写故乡”叙事中总有一个隐在的“我”,这个“我”藏而不露、秘不示人,这与其小说叙事多采用全能叙事视角有关。因其是全能叙事视角,作者不便以第一人称“我”去参与故事或叙述故事,而只能以全知全能的叙事手法来讲述“故乡”“故事”,但因其所叙述的这个“故乡”“故事”只能是作者的“故乡”“故事”,那么这个隐在的叙事者便与作者高度重合了。贾平凹对故事叙述节奏的把控力是超强的,贾平凹的叙事不尚渲染与铺排,而是高度的收放自如和大开大合,而这恰恰又是全能叙事的优点。作者“隐在”却又无处不在,故乡、故人、故事、故情都在其笔下自然地、原生态地呈现,这无疑与贾平凹深受“商州山地文化”自闭内敛和“商山隐逸文化”“隐”与“藏”的精神追求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贾氏对明清小说叙事传统——全能叙事、全面掌控、舒缓自如——的继承与发扬。
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情感态度基本上保持着“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那种爱恨交织的情怀,在叙事的情感维度上是连贯的、完整的;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赋形完全因时因地制宜,“高密东北乡”时而是一个村子,时而是一个县城,时而是城市边缘的郊区,时而是外族入侵时的“难所”,时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屠宰村”。而贾平凹文学世界的叙事空间则是分立的“商州山地”与“废都西京”并存,贾平凹对城市与乡土的情感也是自我矛盾、前后冲突的。贾平凹早期的文学书写歌咏乡野之美,却也真心礼赞乡村与农民的现代化进步,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而在其中后期的城市叙事中,则又表现出对城市与市民的厌弃,以及对乡村现代化给植根于农耕文明的道德传统带来的冲击和乡民精神世界失序的焦虑与担忧。因此可以说,在贾平凹的“城”与“乡”的二纬叙事空间里,他的叙事情感是矛盾的、对立的。此外,关于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传统)文明之间的关系,贾平凹基本上将其处理为对立的、对峙的关系,而莫言基本上将其处理为对话、融合的关系。
我们不妨再把两位作家对于“故乡”的书写放置到整个“乡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观照。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关于“乡土”,莫不是“田园”、“山林”和“怀乡”,我们可以称之为“乡土叙事/乡野抒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乡土”,夹杂在近现代化大潮中的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代知识分子,在回望故乡时,多怀着对故乡故土的思念与怀想,进行着“乡土文学”的书写,或对故乡进行田园牧歌式的礼赞,或痛苦地批判着故乡的落后愚昧,或哀伤地咏叹着旧乡村的凋败,我们可以称之为“还乡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于“乡土”,寻根作家们进行着文化自拯式的文化寻根书写,知青作家们感念着农村对自己的接纳或痛恨着下乡带给自己的伤害,我们可以称之为“下乡叙事”和“乡下叙事”。在这诸种关于“乡土”的叙事之中,“故乡”都是那个自然的、实在的故乡。在鲁迅、沈从文、许杰、废名等作家笔下,“故乡”是一个令人哀伤的字眼,是近现代化进程中“老中国”的凄凉背影。在这样的中国“乡土文学”背景下,我们可以见出莫言和贾平凹在“故乡叙事”叙事空间营建上的异同: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莫言和贾平凹的小说在叙事空间的营建上具有一致性,都在“故乡”找到了叙事场域和叙事激情,其叙事精神都深深植根于、汲力于故乡的文学精神传统,浸淫其间,深受地域历史文化影响,并以天纵之才将其发扬,自成其惊泣鬼神的巨匠神气,在文学创新的同时,不断感受着时代的脉动,书写着自己的“家国情怀”。不同之处在于,莫言和贾平凹小说“故乡叙事”场域的时空外延不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想象的故乡”——一个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故乡”,贾平凹的“商州”是一个“实在的故乡”——一个“文学化的故乡”,尽管二者都是作家的文学世界中的“故乡”,但它们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所占的权重不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作家精心营建的一个叙事场域,但却不是作家书写的重点和中心。贾平凹的“商州”则先是作家倾力表现的对象,后来才又变成其“商州故事”的叙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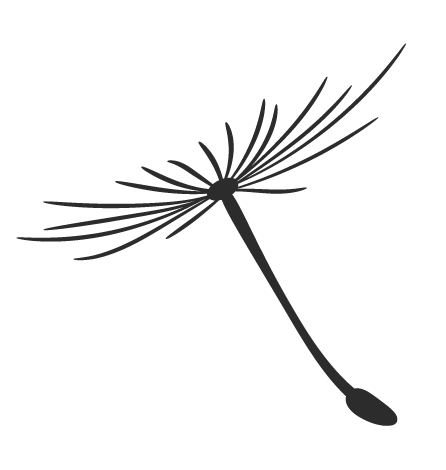
结语
从地域文化和“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莫言和贾平凹分别营造出了“高密东北乡”和“商州山地”,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坛奉献了独具艺术魅力的“高密东北乡”故事和“商州系列”散文、小说。虽然限于论题,我们在上文中没有论及外国文学对两位作家“故乡”叙事空间营建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在两位作家的文学教育和文学阅读经验中,外国文学的某些作品的确触发了他们营建“故乡”叙事空间、进行“故乡叙事”的灵感,从文学叙事的方式和场域上给他们以启迪。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莫言和贾平凹都是天才的作家,其对外国文学叙事精神的学习和借鉴是深深扎根于其实在“故乡”的地域性文化资源和文化母本中的。“为什么这么多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他们的纸上故乡,外来的文学影响固然是一个诱因,更深刻的诱因却在本土文化历史语境中,它使得‘地理的’在此时不仅仅是‘地理的’,不仅仅是某种美学风格上的偏锋,而是一种被挖掘的文化力量,用来补充主流政治文化,修复和抗衡已经十分单调的民族主流文化的文化建设行为。”[18]与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等文学叙事场域一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贾平凹的“商州山地”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叙事场域中的重要板块,代表着一方独特的风土和人情,在文学叙事空间和文化指代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这种文学叙事空间的营建赋予了作家空前的叙述权力和想象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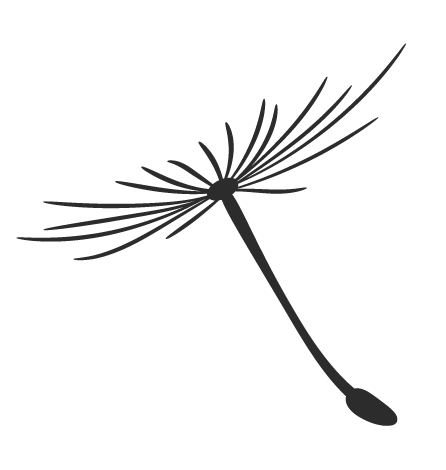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佩尔• 瓦斯特伯格《莫言诺奖授奖词英文全文》(The Nobel Prizein Literature 2012 Award Ceremony Speech,Presentation Speech by Per Wästberg,Writer,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Chairman of the Nobel Committee, 10December 2012.),谭五昌:《见证莫言——莫言获诺奖现在进行时》,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2]杨守森:《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莫言研究会:《莫言与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7页。
[3]杨守森:《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莫言研究会:《莫言与高密》,第6页。
[4]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
[5]莫言:《故乡往事》,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6]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我的高密》,第253页。
[7]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我的高密》,第257页。
[8]商山四皓,秦时隐士,汉代逸民。是居住在陕西商山深处的四位白发皓须、德高望重、品行高洁的老者。他们四位分别是苏州太湖甪里先生周术,河南商丘东园公唐秉,湖北通城绮里季吴实,浙江宁波夏黄公崔广。
[9]贾平凹:《我是农民》,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10]费秉勋:《贾平凹与商州》,《唐都学刊》1993年第1期。
[11]费秉勋:《贾平凹与商州》,《唐都学刊》1993年第1期。
[12]李星:《序》,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页。
[13]李俏梅:《“文学地理”建构背后的宏大文化理念》,《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14]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演讲》,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213-214页。
[15]莫言:《神秘的日本文学与我的文学历程——在日本驹泽大学的即席演讲》,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16]莫言:《超越故乡》,第251页。
[17]贾平凹:《商州三录》,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8]李俏梅:《“文学地理”建构背后的宏大文化理念》,《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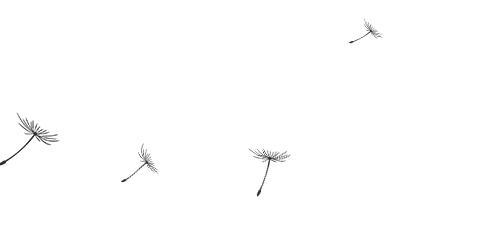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王西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在英语国家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1949—2013)”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BZW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