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921年10月的日记:谴责剥削,鼓动百姓揭竿而起
Original 百无一 文学文化研究 Yester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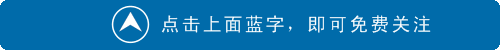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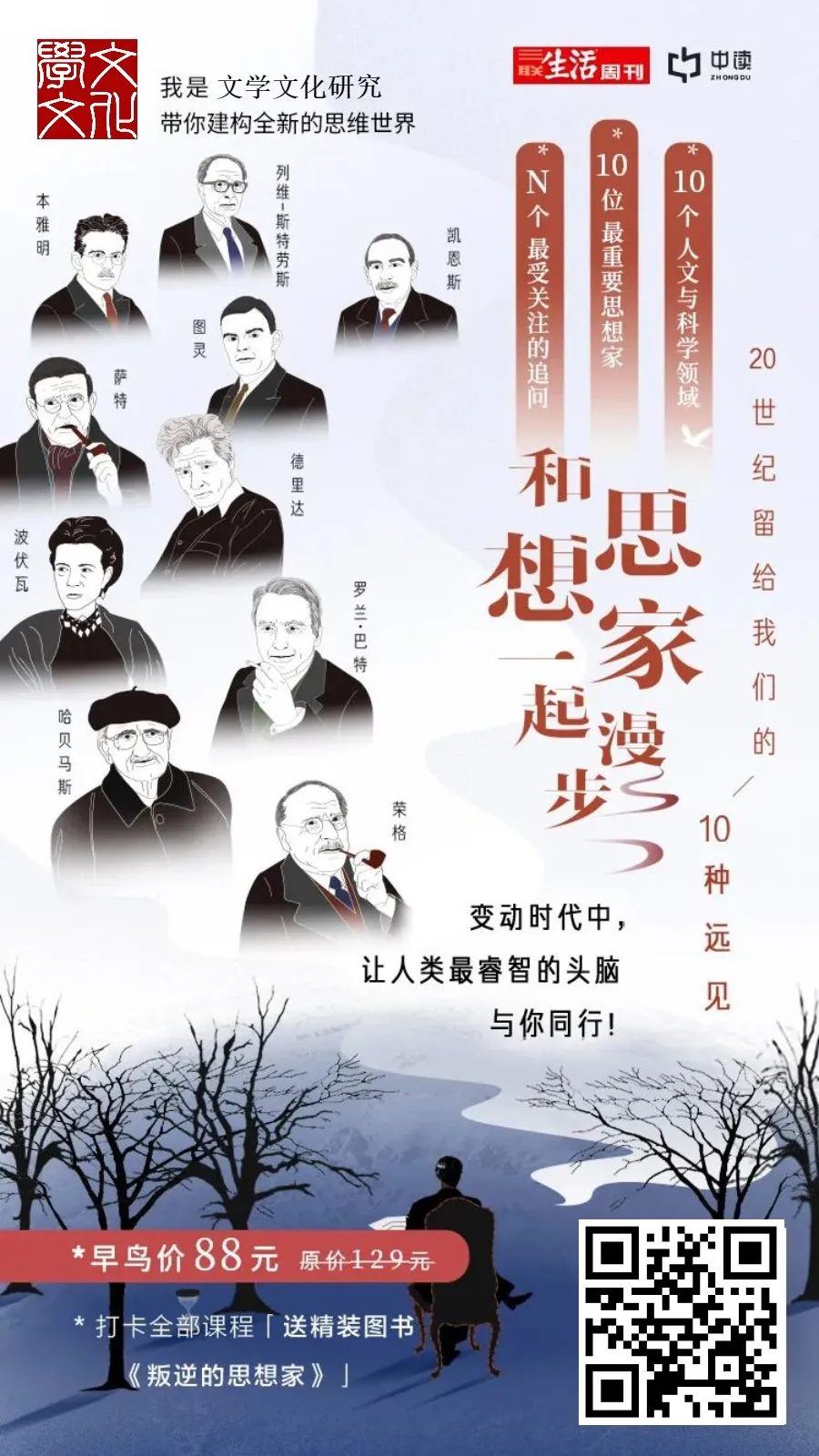
20世纪西方思想家
From 文学文化研究
00:0015:47
打卡全部章节,赠送价值
68
元的精美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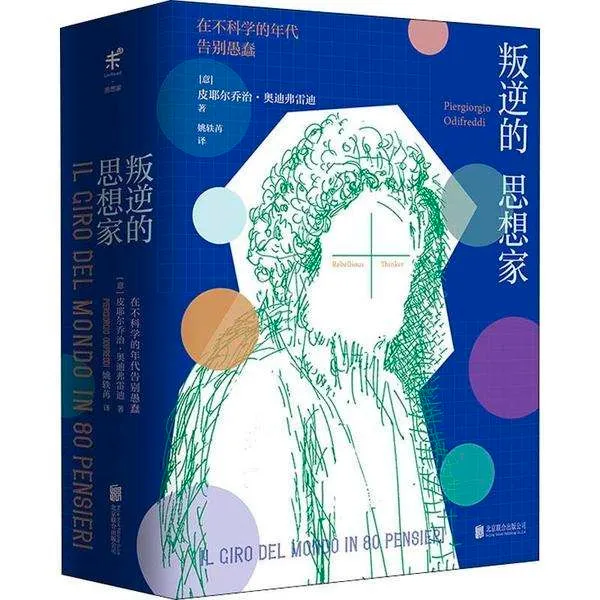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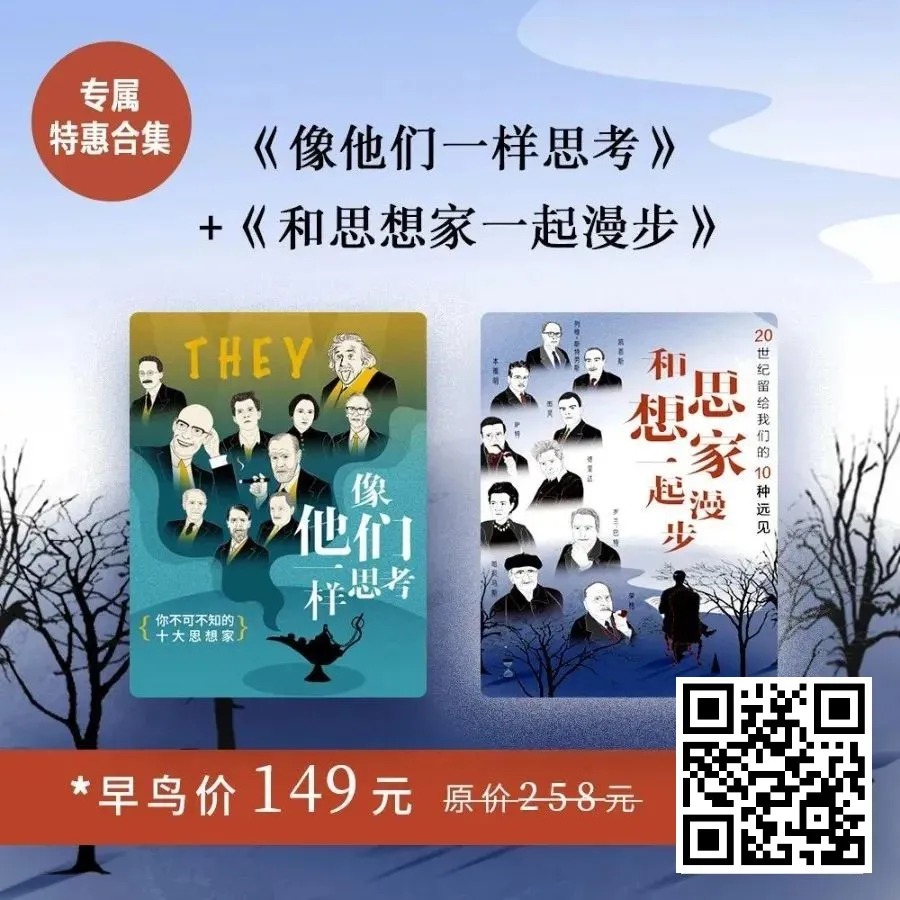
21岁留日期间的郁达夫:倘为国死,予之愿也

抗战中与抗战后,文化人的升沉遭遇,是反映了整个民族在如何惨痛的蜕变。郁达夫与闻一多之死,不仅是“千古伤心文化人”的问题,而是证明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要在广泛的血洗过程中茁长起来!同时文化人如周知堂,张资平,樊仲云,汪馥泉……等,又如何像沉渣一般的被捡起与马粪搅和着,为侵略者压迫者当燃料在使用。这是多么清楚,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两个侧面。
--- 潘汉年,1946年10月2日《联合日报晚刊》

经郭沫若举荐,1921年10月开始,郁达夫从上海赶赴到安庆的法科大学教书。东京而上海而安庆,从其繁华程度而言自然是一个不如一个。抵达安庆的第一晚,郁达夫是在一家条件很差的荒店里度过的。“人疏地僻,我好像是从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被放逐到了罗马黑暗时代的样子。“在10月2日的日记里,他引陶潜、阮籍及英国十八世纪的诗人詹姆斯.汤姆森为同志。认为”像我这样的人,大约在人生的战斗场里,不得不居劣败的地位。由康德的严肃主义来看,我却是一个不必要的人。“ 郁达夫天生是一个不喜欢被束缚的浪漫派,他习惯的是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和说走就走的旅行。因此高校的教书职业也并不适合于他。从到达安庆的第二天起,他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到了学校里,见了些同事,同新媳妇见了小姑一样,可怜我的“狂奴故态”没有放出来的余地了。此后的生活,我好像是看得到的样子,大约到解约的时候止,每天的生活,总不出《创世纪》里的几句话的: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and second ……day. (有晚有早,就是一,二,…… 日。)
在10月4日的日记里,郁达夫再次提到自己因接受的教职而不能外出游玩的懊丧之情:“又是晴快的天气!像这样秋高气爽的时候,不到山野去游行,且待何时?我弄错了,我不该来这里就缚的。…… 这些传统的陋俗不得不打破,破坏破坏!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由我的自在就好了。”
在10月5日的日记里,郁达夫由前一段时间发生在长江一带的水灾联想到安庆一带农民的疾苦,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同胞呀,可怜的农民呀!你们经了这许多兵灾、旱灾、水灾、怎么还不自觉,怎么还不起来同那些带兵的,做总统总长及一切虐民的官和有钱的人拼一拼命呀!你们坐而待毙,倒还不如起来试一试的好呢。不管他是南是北是第三,不问他是马贼是强盗,你们但能拼命的前进,就有希望了。这事用不着代表的,因为代表都是吸血鬼……
在10月6日的日记里,郁达夫再次结合自己教书和备课的艰辛,谈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认为自己和其他劳苦大众都是被剥削的对象,应该杀光那些不劳而获、专靠剥削别人的劳作而得以享乐度日的社会阶层:
我倦极了。单是四点钟的讲义,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四点钟讲义之外,又不得不加以八点钟的预备。一天十二点钟的劳动,血肉做的身体,谁经得起这过度的苦工呢!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者,都因为有一部分人不劳而食的缘故。世界的劳动本来是一定的,有一部分人不做工,专在那里贪逸乐,所以我们不得不于自己应作之工而外,更替他们做他们应作的工。这一部分人是什么人呢?第一就是做官的,带兵的,作各团体的代表的,妇人之专事淫奢的,和那些整日在游戏场里过日子的人。把这些人杀尽了,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至于苦到这步田地。大同世界,就可以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