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佩索阿来了:该群嘲的是我们的“真实世界”
Original 赵俊 深港书评 2 days ago

《晶报·深港书评》
这几年,佩索阿正在超越洛尔迦,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在汉语世界最被重视的20世纪诗人。这从他的出版著作的密度就可以看出,他在读者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前几天,在诗人晴朗李寒的朋友圈,他晒出了佩索阿最近几年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可谓琳琅满目。这里面有《阿尔伯特卡埃罗》《自决之书》《坐在你身边看云》《不安之书》等等,仅《惶然录》就有三个版式。
也许,在汉语世界,佩索阿出现得并不是那么早,而这种后发式的发现,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布朗肖说,写作是为了永生。福柯进一步阐释说,“也许,甚至,说话也是为了永生。无疑,这是一项同词语一样古老的任务。”佩索阿,不过是一个小职员,在生前籍籍无名,暗恋着一个叫做奥菲利亚的姑娘。对于他而言,写作的目的性,也许就着眼在了永恒的意义之上。他并不追求名利。但对于他而言,写作已经是他最大的嗜好,他几乎每天都在写。当他去世的时候,抽屉里的著作让人惊叹,这是一个未被充分发觉的金矿。

关于自己的写作,佩索阿在《惶然录》里已经谈了很多。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自我治疗。“从今以后,我会碰到一些事情。当这些事情照常突如其来的时候,生活将一种极度的烦闷强加给我的情感,对这一种如此剧烈的烦闷,任何疗救都于事无补。自杀看来是过于不当和过时了,即便有人假定这种办法可以确保遗忘,但也没有什么意义……我用写作来除掉这一魔影,做到这一点的力量,不仅仅来自纯粹的情感,也来自知识。没有一种真正深藏着的苦恼,不可以在讽刺性的相应书写之下得到救治。在少有的情况下,这也许就是文学的用处之一,而且可以假定,这种写作也不会有其他用途。”
他仅仅为了治病,却造就了现代文学中一个辉煌的镜像。众所周知,佩索阿可以在作品中分裂出各种形象。在他的笔下,假托的作者有《惶然录》中的贝尔纳多·索阿雷斯,还有《守羊人》中的阿尔伯特·卡埃罗,以及《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中的阿尔瓦罗·德·冈波斯。那么,谁才是真正的佩索阿呢?或许,他们都是,又或许他们都不是。文学本身就寄生于生活,通过想象塑造更多的空间。本雅明说,“一件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与他所处于的那种传统的联系是一致的。当然,这传统把本身是绝对富有生气的东西,它具有极大的可变性。”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他假托的形象,借助于某种传统,在佩索阿的作品中完成了“独一性”和“可变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带给了更多的生命,使永生成为了一种可能性。比如,纪念张国荣的一本书叫《与他共渡61世》,因为他拍了61部电影,每看一部电影,就和他过了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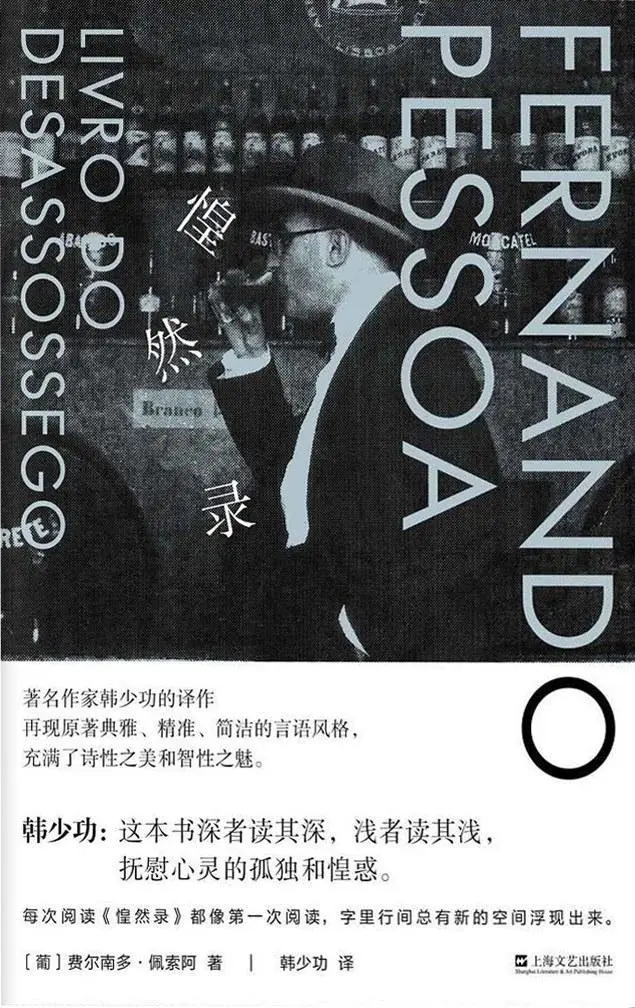
《惶然录》2019年版
以前,“双重人格”是众多文艺作品喜欢探讨的问题。比如,张国荣的电影遗作《异度空间》就讲述了一个具有精神分裂的精神病医生的故事。但对于佩索阿而言,“双重人格”是远远不够的,他甚至可以幻化出多重的人格。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接近了佛学的某些要义。按照普遍的佛学观点,佛的化身主要可分为三种,即殊胜化身、种种化身、工巧化身。就“种种化身”而言,《华严经》中经常讲,佛陀会随应因缘而化现为沙门、婆罗门、国王、大臣、乞丐等人的形象以及飞禽走兽等其他形态,所以说我们要懂得观清净心,因为一些看起来很可怜的动物说不定就是诸佛菩萨的化现,甚至在植物界中也有(显宗里面一般说,认为植物有生命是外道的观点,但《时轮金刚》中提到,植物中有些也有生命,它们实际上应该属于旁生之列)。佛学(而并非佛教)是一种普遍的东方思维,贯穿于印度、中国及日本等几大主要国家,佩索阿的化身,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和东方的思想、审美产生了某种共鸣。诗歌在这个程度上而言是神秘的。比如,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诗歌时,很多西方的大诗人也从中国的古典诗歌中汲取着营养,并对我们进行着响应。我们无从得知,佩索阿是不是也曾经研读过佛学著作,但从精神内核上而言,这也是一种“遥远的回应”。
一些评论家认为,佩索阿是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称:他的虚构作品超过了拉美文学的代表人物博尔赫斯的所有作品。有评论认为,“佩索阿为自己杜撰了一百多个异名,对他来说,异名与笔名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笔名是作者自身的介入和投射,是写作者的附庸,而异名是以全新的姿态、经验、哲思参与文学创作的不同身份,他们并非佩索阿不同性格侧面的夸大和碎化,而是和他本人完全不一致的独立的人,每一个异名表现出鲜活的生命,他们有具体的出生和职业,也有不同的思想和个性……异名写作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所谓的作家的局限:即作家的文字与作家本人的声音密不可分。阅读常规文本时,叙事者的声音和写作者的声音相互纠缠,渗透进每一个语言结构里。”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异名写作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他是接近于后现代主义的。埃及裔美国文学评论家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样,一个多元的宇宙可以支撑我们丰饶多样的信仰,那些能够对行为作为回答并构成意义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可以说,佩索阿的众多异名的交织,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的多元宇宙”,从后现代的另外意义上而言,他也符合消解和拼贴的含义,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的佩索阿。如果说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用几个小故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地图,那么,佩索阿为文学提供新可能显得更加狂飙突进。
佩索阿有那么多的分身,即使一个分身,也让我们在阅读中受益匪浅。基于此,雅众文化出版的《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显得颇为及时。此前,雅歌诗丛曾经在2016年出版过《佩索阿诗选》,但并没有在业界引起特别大的反响。所以,翻译佩索阿的诗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他的众多分身,会让整本诗集的翻译难度成倍增加。是以,杨铁军选择了冈波斯,这个据说最近于佩索阿本人的化身。对此,杨铁军是这样说的:“从表面上看,冈波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花花公子,留学苏格兰海军工程学,周游世界,性格豪放恣肆,和佩索阿本人的生活毫无相像之处。但冈波斯应该是佩索阿想要成为,却没有成为的那个人。冈波斯回到葡萄牙后,陷入绝对的悲观,对现实,甚至对自己采取轻蔑嘲讽的态度。这也应该是佩索阿本人的态度。”
该书的译者杨铁军近年翻译过希尼的《电灯光》和弗罗斯特的《林间空地》,尤其让人敬佩的是,他通过非凡的勇气翻译了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代表作《奥麦罗斯》。这本八千多行的鸿篇巨制对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19年9月20日,杨铁军凭《奥麦罗斯》获第4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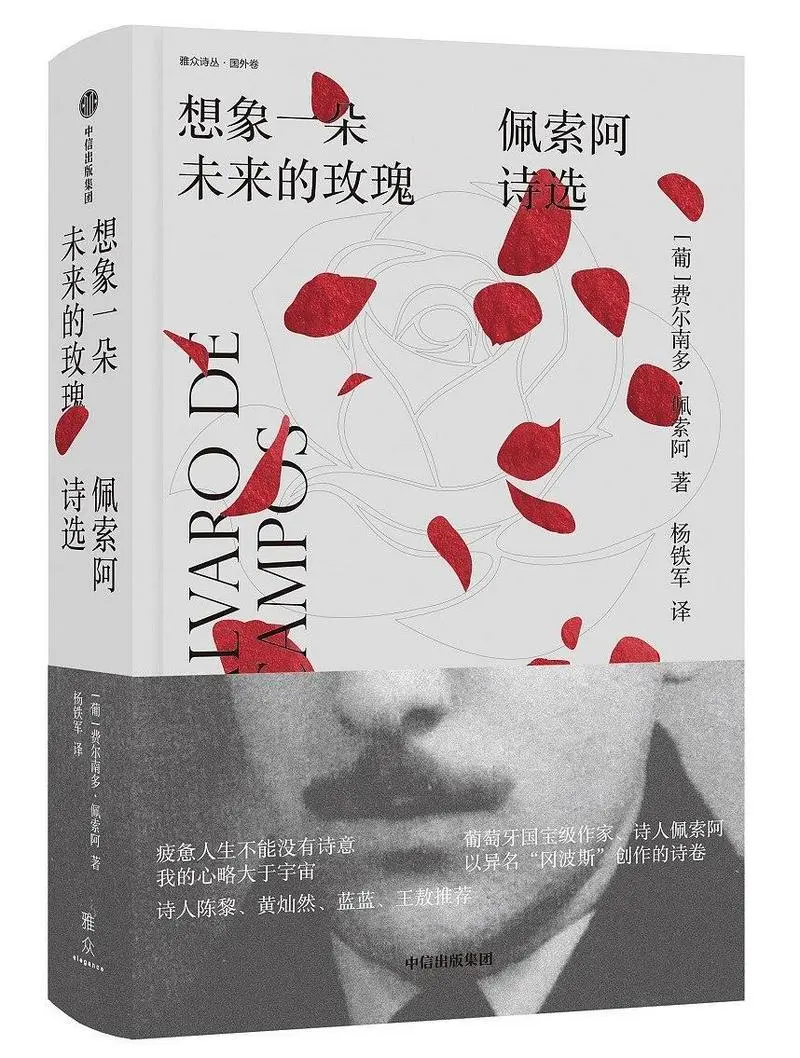
《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
[葡] 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雅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杨铁军 译
2019年5月
在《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一书中,很多诗歌倾向于口语写作。《是的,我知道这很自然》就是一首典型的口语诗:
婴儿死了,但一千块还在。
是的,一千块。
一千块可以干很多事(可怜的孩子)。
一千块可以付
多少债务(可怜的小宝贝)。
一千块可以买
多少东西(死去的漂亮的婴儿)。
译者杨铁军认为,“冈波斯只信任感觉,所以想要用尽所有可能的方法去感觉,因为那才是生活的真实。现实对于他来说是不真实的,所以他在现实中永远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冈波斯在想象中曾无数次是恺撒,甚至比基督更‘人性’,比康德更能写,但在现实中,却在旅行的前夜收拾不好‘行李’,永远无法成行,处于一种绝对的“矛盾”之中。当然,这种‘永远无法出发’的旅行不可避免令人联想到死亡。”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感觉主义”的存在,才让杨铁军的翻译文本呈现出这种语言状态。
当然,冈波斯是丰饶的,《鸦片吸食者》这首小长诗就代入了佩索阿自己的生活,因为副标题是“致马里奥·德·扎—卡尔内罗”,这中间,虚构的身份和佩索阿的自身产生了某种神秘的交集。因为卡尔内罗是葡萄牙现代主义诗人,也是佩索阿的朋友,他们一起创办《奥尔菲》杂志。后来,卡尔内罗在巴黎自杀,对佩索阿的影响甚大。该诗的落款是“1914年3月于苏伊士运河船上”。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所以我吸食鸦片。就当它是药。
我一口鸦片吸下,就在那一刻
得到康复。我住在思想的底楼,
看生活慢慢逝去是一种折磨。
看过陈凯歌电影《风月》的观众一定对一句台词记忆犹新:“什么是鸦片?鸦片,那是人世间的钟灵毓秀啊!”《鸦片吸食者》整首诗都沉浸在对鸦片的病态迷恋之中。在诗中,“我”不断地游历,这种游历和布罗茨基的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后来人,我们必须让流亡变得轻松一点(如果我们不能令它安全一点的话)。而唯一能使流亡变得轻松、使后来者对流亡的恐惧有所减少的办法,便是指给他看流亡的全部限度——也即,我们自己曾经担当下来的全部。”众所周知,布罗茨基几乎是被赶出祖国的,虽然他带着这样的信念——“宁做自由世界的普通人,不做独裁社会的大文豪。”而这里的“鸦片吸食者”却是一种自我流亡,最后,他说:“让我待在这里吧,坐在椅子上,/直到他们过来把我塞进一口木棺。”整首诗沉浸在一种钟灵毓秀的颓废中,这区别于《是的,我知道这很自然》,让人得到了最大的阅读快感。
杨铁军认为,“阿点出诗人是个造假者,而这又是一种真诚的造假,一种关于生活的造假,他借由摆脱、消解自己来获得一种突破局限的方式,拓展了一个诗人个体可获得的空间与自由,佩索阿真正实现了写作上的零度,抹去写作者的声音。”在《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一书中,却给人一种艺术意义上的“灵魂写真”。我想,真正应该被群嘲的反而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无趣的真实世界。

赵俊/文
独家原创内容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编辑 | 邓晓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