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已经熟悉这种黑夜
Original 陈小星 诗歌颂 1/13

图片出自 ▏one
熟悉黑夜
[美]弗罗斯特
译/赵毅衡
我早就已经熟悉这种黑夜。
我冒雨出去——又冒雨归来,
我已经越出街灯照亮的边界。
我看到这城里最惨的小巷。
我经过敲钟的守夜人身边,
我低垂下眼睛,不愿多讲。
我站定,我的脚步再听不见,
打另一条街翻过屋顶传来
远处一声被人打断的叫喊,
但那不是叫我回去,也不是再见,
在更远处,在远离人间的高处.
有一樽发光的钟悬在天边。
它宣称时间既不错误又不正确,
但我早就已经熟悉这种黑夜。
Acquainted with the Night
I have been one acquainted with the night.
I have walked out in rain—and back in rain.
I have outwalked the furthest city light.
I have looked down the saddest city lane.
I have passed by the watchman on his beat
And dropped my eyes, unwilling to explain.
I have stood still and stopped the sound of feet
When far away an interrupted cry
Came over houses from another street,
But not to call me back or say good-bye;
And further still at an unearthly height,
One luminary clock against the sky
Proclaimed the time was neither wrong nor right.
I have been one acquainted with the night.
-关于作者-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之一。他曾赢得4次普利策奖和许多其他的奖励及荣誉,被称之为"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代表作品:《诗歌选集》《一棵作证的树》《山间》《新罕布什尔》《西去的溪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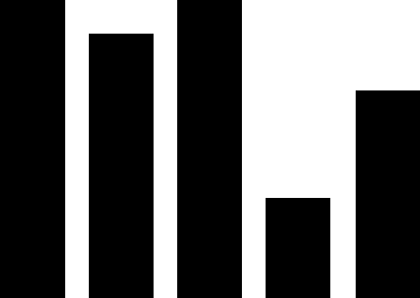
关上门,不是为了幽禁快乐,
而是为了解放悲伤。
——阿多尼斯
孤独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黑夜是孤独最贴切的载体。
这首诗歌中的“我”,经常在黑夜中逗留,在雨夜前行,出去又折返,“越出街灯照亮的边界”,从繁华明亮的都市中出走,又回到冷冷清清的黑暗中,经过凄清冷寂的小巷,“我”和困顿的守夜人一样,独自穿梭在黑暗的夜晚中,这样的夜晚是无言的,寂静的。
脚步停下,骤然无声,黑夜像一个巨大的罩子,将“我”隔绝在一处天地间。远处,在屋脊的另一边,传来“一声被人打断的叫喊”,这一声叫喊打破了黑夜的静谧,“我”似乎感到期待,然而,这兴许代表某种突破或者希望的呼唤,却与“我”无关——“那不是叫我回去,也不是再见”。“我”终究还是只身在黑暗中,无处可去,唯有高悬在天边的钟发出冷淡的微光,推动着时间向前流逝。
时间始终向前,它是没有对错的,它只是冷漠地向前,穿越人类的历史,指向未来的无垠。“我”所站立的这一寸黑夜,也只是漫长岁月中的一瞬息。这样的黑夜,不仅是同为人类的我们,身处繁华都市而心灵却无家可归的时刻,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无所依、无所留存的悲哀处境——既不能依赖过去,也无法把握未来,只有孤独是永恒的。
这首诗读来,是一种深层的孤独感,是生命无所适从的孤独感。我们需要承认,即使是身处灯火明亮的小家、人群之中,内心无家可归的感触依旧鲜明,这样的时候有很多。然而,敢于直视并承认孤独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多的时刻我们都在极力回避孤独,我们说服自己融入,说服自己妥协,说服自己忽略,唯有在黑夜的掩饰下,我们才敢透露出那么点内心的孤寂,和对人群的蔑视。
尽管作为普通人,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常态,仅仅作为某些内心脆弱时刻的写照,但你必须承认,某些夜晚是要一个人度过的。比如那些躲在房间里的,静默抽泣的时刻。
承认吧,有些话,你无人想要诉说,
有些时刻,你无需任何陪伴,
唯有黑夜,给你安定和放纵。
黑夜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拥抱了我。
文/陈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