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 | 作为策略的文本
Original 伊格尔顿 上河卓远文化 2019-06-17

Terry Eagleton
文学作品的悖论之一在于,在不可改变性与自我完成方面,它是“结构”,然而它必须在永恒运动中进行自我完成,并且只能在阅读行动中实现自己,就此而言它又是“事件”。作品的每个字都不可改动,可是在变化无常的回应中,没有哪一个词语可以固守原来的位置。本文节选自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第五章《策略》。微信标题为编辑自拟。
作为策略的文本
【英】特里·伊格尔顿 文
阴志科 译
陈晓菲 校译
一旦将对象/事件的区分纳入考量,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又会是什么样子?有一派符号学理论把文本当成对象来分析,正如我们在尤里·洛特曼、米歇尔·里法泰尔的作品里所看到的那样。但是另外一些符号学流派——比如翁伯托·艾柯——更接近我们之前了解的接受理论,对他们来说阐释符号是一种复杂的策略性实践。艾柯称之为“符号—生产”的活动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运用推论(假设)、诱导、推理、过度编码(overcoding)、编码不足(undercoding)等策略破译文本中的“信息”,后者是一种“可以被赋予任意意义的空洞形式”。文本不再是一个固化的结构,而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花园”,充满解读的幽径和可能。如此一来,阅读更像在海德公园里闲逛,而不是横穿威斯敏斯特大桥。这些纵横作品的路径或“推理散步”邀请读者参与进来,对作者的编码或接纳,或否拒,或者有时候因为不知道“信息发出者”的规则是什么,只能尽力从支离破碎的信息碎片中推算出这类解读指南,或者为了弄清楚作品中难解的部分,尝试提出自己的编码规则,如此等等。文本信息不仅仅是有待从符码中读取的对象,它们是一组事件或者符号行为,不能简化为产生它们的符码。也许有人会联想到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人类应用规则的巨大创造力。正如查尔斯·奥尔提耶里指出的那样,表演行为不能简化为语言构造物。由于符码自身可能会被读者的生产活动修改或者变形,甚至可能面目全非。
对艾柯来说,文本符号并非稳定的构件(unit),而是编码规则的临时结果;编码本身不是固定的结构,而是应急的工具,或者是读者为了解读一条“信息”而提出的工作假设。如此一来,它们只会在阅读行为中成形,通过将文本片段临时组织起来,帮助我们理解文本的意义建构模式。文本中的“信息”不是既定的,而是某种“约束的网络”,允许读者作出“丰富的推论”,以及容忍“生产性的偏差”。一部作品并非含义的依序排列,而是一组指导意义生产的、有时候几乎难以辨识的指令;不独于此,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解释单个符号,它们不是索绪尔认为的那样是离散化、自我同一的单元,更像是一个包含着多重语义可能性的“微文本”(microtexts)。
在符号和文本双重层面上,符号指代过程最终消弥于无限之中。是符号、文本、信息的生产和接收都是拜占庭式的复杂工程。并且,由于指代过程没有终点,某一个符号的意义只能来自于另一个符号,对于劳苦的读者大众来说并不存在天然的安息所。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稳定结构,而是一个结构化过程。正如艾柯指出的,“美学的文本持续不断地将它的外延转换成新的内涵,没有一个成分会止步于最初的解释,内容不可直译,而是指向其他事物的符号载体。”
在此过程当中,作品的每一个特征都必须通过读者来实现,作为结果又激励读者参与到全新的解释活动当中。读者通过应用某种临时编码具实了文本结构,正如他所回应的文本结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一样。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艾柯对詹姆逊模型的符号学仿写。这种读者与文本互动的观点——读者投射出某些意义又对此作出回应——和詹姆逊有关文本和潜文本之间相互交通的观点如出一辙。艾柯理解的文学作品既是结构也是事件,既是事实也是行动,彼此相互定义。文本的符码和读者的符码无休止的相互穿透。和名为图书的实物对象相反,没有读者的“具实化”行动就没有文学作品,但这种行动并不是自我决定的。尽管它不受文本结构左右,但依然在后者中有迹可寻,并受其引导和约束。(有人可能注意到,这正是艾柯和某个斯坦利·费什厚脸皮的唯心主义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关键差异。)在解读作品时,读者会在它身上施加某种一般化的能力;但是这种被规制的能力通过实际的阅读行为最终以某种独特、个性化的方式实现出来的,能力和行为表现变得难以区分。这并不是说读者拥有一套固定的能力装备,只待落实即可,就好比在温布尔顿夺冠的网球选手不可能只是在更衣室里突击了一把竞赛技巧就现学现卖,上阵迎敌。
正如符号学在强调策略性方面有强弱之别,这种区别同样适用于结构主义。沃尔夫冈·伊瑟尔写道:“(一部作品)所有元素的(结构主义式)项目表生成秩序,它的技巧总和负责把元素衔接起来,在此之上形成的语义维度构成这个文本的最终产品——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产品为何诞生,文本如何发挥作用,谁在利用文本。”在完成这番异常贫乏的思维操练之后,他又摆出一副维特根斯坦的架势作出回应,引用某个德国同行的妙语:“人只有不止乎语言才能理解语言。”只有理解了这种文本化结构的功能——也就是说掌握它和语境之间的联系,并将其看作表演——结构本身才能昭然若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结构并不是决定性的参考基准。从广义来说也一样,因为只有当某个结构是自明的或者自我诠释的,它才有可能构成基准。只要它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必然存在逻辑上先于它的事物,换言之就是解释所用的语言。
伊瑟尔写道:“文学文本的结构只有借助文本的功能才有意义。”这相当于说,文本最好视为某种策略。策略恰恰就是一种广义上由目的决定的结构。事实上,伊瑟尔的主张不仅适用于文学作品,对意义来说同样适用。正如结构主义者急于强调的那样,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结构问题;但是符号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是意义产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仅仅知道“不动产(realty)”不同于“现实(reality)”并不能使我掌握“不动产”的用法,而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意义和现实恰好相反。我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生活形式中掌握它的功能。
从历史上看,文学作品的功能是高度多变的。正如我们先前讨论的那样,作品的功用几乎涵盖所有领域,从鼓舞你的战士冲向战场到让你的银行存款增加四倍。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文学文本的内部有其特殊语境,文本与语境之间包含某种内部联系;从广义上说,这里也是功能决定结构。正是作品处理其语境的方式决定了它所选择的技巧以及展开方式。伊瑟尔发现:“如果文学文本体现了朝向特定世界的意向行为,那么文本所趋近的世界不会原样照搬进文本,它将经历各种调整和纠正……在澄清文本与文本外现实之间关系的同时,(功能的概念)也阐明了文本试图解决的各种问题。”“各种调整和纠正”之类慎重的官样文字不足以描述世界进入文本时惊心动魄的转化过程。但伊瑟尔正确地指出:功能的观念与将作品视为“问答模式”的观念息息相关。
有一派结构主义试图确定究竟何种规则导致离散的元素组合为意义单元,而这正是客体论的金科玉律。其典型有热奈特和格雷马斯的叙事学。也许还可以算上N.弗莱的文学分类学,尽管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有时候他似乎致力于为了分类而分类。这正是德里达曾经批判过的一类分析,“仅仅由机械学,而非热力学”(energetics)推动。这种观点最失策的地方在于未能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修辞,即它往往别有所图。这大概是Zog星人眼中的文学。不过,有一类结构主义更接近我之前所提出的文本观念,它的支持者之一是列维–斯特劳斯:“神话思维通常从意识到二元对立发展为解决二元对立。”他写道:“神话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克服对立的逻辑模型。”有鉴于此,神话就是“有助于思考”的策略,是一种处理悖论和矛盾的前现代思维机制。尽管无须无条件赞同这种神话理论,但是它对文学分析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和伊瑟尔的接受理论或艾柯的符号学理论一样,神话完成该任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作为一个策略性过程:一组对立式转化为另一组,旧的矛盾得到化解,只为产生新的矛盾,一个元素取代另一个元素,以此递推,不一而足。此外由于无休止的“文本间性”的作用,神话文本戕食同类后又成俎下肉。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神话的无意识目的就是解决问题,为此它调用了诸如形象、情节和叙事之类有意识的机制。然而,我们被警告,意识和无意识、情节和问题之间并非镜像或同源关系,而是彼此的变形或转化。这和詹姆逊模型中文本策略与其潜文本之间的关系不谋而合。
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神话是关于“具体之物的科学”,它预言了未来成为启蒙审美学核心的关于具体事物的科学。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自成一体,这些精巧奥妙的神话是人类心智结构运作于其上的象征形式。在此意义上,神话相当于象征主义诗歌的前现代版本或者(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确,神话以一种貌似写实的方式揭示人类的思维活动;但是,对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来说,神话自命描述的世界同时也是它一手建构的。反而正因为如此,借助局部精细度堪比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分类范畴,神话使男人和女人自在地栖居于世界,并得以发挥各自的实践功能。它们既是理论反思、美学游戏的范例,同时也是认知地图。正是在这些方面,结构主义者所理解的神话同文学虚构具有明显的可比性。
列维-斯特劳斯下文中的表述可以印证上述内容,我把自己的按语放在括号里:
萨满巫师的神话是否对应客观现实(指作者的虚构作品并没有直接参照物)并不重要。生病的女子(指读者)相信这个神话(指虚构作品),她归属于一个信仰该神话的社会(指文学制度)。守护灵和恶灵,超自然的妖怪和有魔力的动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序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上构筑了某种天然的宇宙观(指意识形态)。生病的女人(指读者)接受了这些神话式的存在(将怀疑搁置一旁),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压根就没有质疑过这些存在是否真实。她所不能忍受的是那种孤立、没有来由的痛苦(指社会压迫与冲突),也就是她所处的体系中的异质成分,但是萨满巫师通过召唤神话(指虚构作品),成功地将这些成分重新统合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当中每个组成部分都是有意义的。一旦病人(指读者)理解了这个逻辑,她不止听任摆布;她还恢复了健康(重新投入到社会生活的实际角色当中去)。
诚然,把神话与文学直接对应起来不免有简化之虞。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是这样一种直白的意识形态工具。实际上,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还会故意和它们所处时代的统治意识形态唱反调,反之也有许多通俗或者非经典作品意识形态其亦步亦趋。我们不应当将经典等同于保守,将通俗视作进步。即便如此,上文示范的粗糙对应依然不乏启发意义。由此看来,神话并不仅仅是一种思考工具,也是一种象征行为。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我们遭遇的问题和矛盾才有了解释,否则将是不可忍受的。
西蒙·克拉克指出,早期的列维-斯特劳斯将神话视为问题–解决式的工具,而晚期的作品更倾向于唯理主义,把它们看作不涉私利的认知操作。剔除了实用性目的,神话不过是按平行、对立、倒置、同源之类的逻辑组织世界的方式罢了,这种痴迷于细枝末节的秩序安排并不需要自身之外的理由。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观念中神话从意识形态转向了理论——从通过想象性的冲突解决从而使社会秩序合法化,转向一种纯粹的认知形式。
然而,只要这种认知方式满足了某种对秩序的狂热,它在意识形态上和阿尔都塞所谓的理论一样并不清白无辜。在克拉克看来,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里所做的是一种纯粹从内部出发的分析,照这种分析方式,神话就是人们对头脑中宇宙法则的编码化表达,它不涉及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在此意义上,仿佛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并不仅仅从意识形态转移到理论,同时从现实主义转到了现代主义。和许多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文本一样,神话是自我指涉的。实际上,我们可以将结构主义本身视为某种由法国式极端唯理主义与同样属于高卢血统的象征主义不能自洽的结合。唯理主义体现在对普遍心智结构的信念上;而象征主义牢牢立足于一个事实,即这些结构是终极的自在之物。相比之下,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有一种更“现实主义”或曰实用主义的倾向,将神话视为对自然与社会施加的策略性操作,是阐释性的虚构,具有建构、调停、转化冲突的功用。在此过程中,神话试图解决一些难解之谜,诸如人类如何同时从属于自然又脱离自然,或者为何既是泥塑又是胎生之类的难题。
由此看来,部落传说采用具体有形的方式去处理抽象问题,这是神话和文学的另一个共同点。这里所说的神话制造者被称为“修补匠”——为了完成某个象征性任务,这位手艺人会把手边的破铜烂铁(比如事件的残骸瓦砾、回收再利用的符号以及其他神话的碎片等等)敲打成一块。(此处又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不谋而合,无意识必须汇聚各种现成的边角碎料,把它们编织成我们称之为梦的文本。)相比之下,《神话学》里的神话制造者在智慧和品味上更胜一筹,他用不偏不倚的目光凝视着人类世界,仅仅是为了在茫茫世界中找到一种法则,由于该法则同时支配着他自己的思维,故而也主宰着他的凝视。当列维–斯特劳斯在其《野性的思维》当中写到澳洲人显示出对博学、沉思的爱好甚至学问上的骚首弄姿时,他想到的不是邦迪海滩的冲浪者,而是当地土著。
这一类象征性思维方式力图把被自然和文化撕裂的世界重新缝合起来。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因为被用来恢复整体性的手段——思想、语言、符号——恰恰是这种断裂的产物。它们正是自己竭力修复的分裂的后果。人类文化的强势崛起对世界的完整性造成了威胁,但是在神话的调解下,通过披上一件象征的外衣得以化解。不仅仅通过内容,甚至通过形式本身,将事物和思维、具体现象与普遍概念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神话和文学一样具有一种隐密的乌托邦面向。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学作品这种魔法式的或曰乌托邦式的属性似乎起到了调和语言和现实的作用,但这仅仅是因为现实本身是语言的秘密产物罢了。于是,文学作品就在其形式中实现了它们在内容中常常无法实现的愿望,沉湎于思索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罅隙,以及人类自我意识与其境遇之间可笑又悲怆的背离。而文学艺术的最大心愿就是以形式的乌托邦属性来补偿其注定悲情的内容。
神话可以是由事件的碎片拼贴成的结构,然而对某些思想家来说,它们也是抵抗事件的力量。保罗·利科评论道:“神话历史站在结构一方对抗事件,并代表人类社会努力终止历史因素带来的混乱,可以看作撤销历史、消除事件效应的一种战术。”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结构与事件之间的另一种关系主宰着艺术。在《野性的思维》当中,他评论道,艺术包含某种“结构与事件之间的平衡”。他指的是艺术作品的总体设计或者内部逻辑和显然毫无关联的意外事件之间的平衡,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小说里或者放进绘画里会让人觉得它们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正如我们所知,现实主义作品虽然有既定的设计,但是谁也不能迫使作品中所有的特征受制于任何严苛的法则,也不能为其注入绝对化的必然性色彩。
这种古典的观念,即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包含但不支配内容,在启发性上略逊于结构化概念。结构化的作用方式和策略一样,在结构和事件之间居中调停。它是结构,这点毫无疑问——但它是一种行动的结构,根据自己订立的目标不断重构,在此过程中目标本身也在不断刷新,因此是事件性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它与索绪尔的语言观念和早期形式对诗歌的理解截然对立。为了理解这个词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逻辑。
有人可能会说,纯粹或者完整的结构——保罗·利科称之为“绝对形式主义”结构——只是一具空壳。这种结构将自身范围内的一切都简化为一个不可动摇的逻辑,这么做的风险是将所有一切都变成随机的、可替换的事件,并且惟有当它们能够例示内部法则时才有意义。事件是结构的例证,不能和它唱对台戏。相比之下,纯粹的事件是盲目的:其存在不能还原到任何解释性结构当中,就像达达主义的偶发艺术那样,它不可言说,神秘莫测。(因此也说明事件理论似乎是一种矛盾修辞法,而这是这位在世最伟大法国哲学家的核心思想。)
然而,策略或者结构化概念从字面意义上“解构”了结构与事件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取消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是展示了这个概念在不断的自我撤消行为中保持着某种不容否认的力量。策略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的形成是基于依据目标功能实时进行自我统合。它的动力来自一个意图——不过,这个意图不是某种幽灵般的外力,而是一个或一组内置于其中的特定设计。此外,文学作品的结构所创造出的事件可以反作用于结构本身,并改变它的条件;就此而言,这样的作品拥有人类行动的自由。因为这种双向过程同样适用于所谓的日常语言,文学作品就是日常言说更戏剧化、更自有皮肤感觉的呈现。
保罗·利科认为词语位于结构与事件的接榫处,“是既定规则与具体行动之间的中介商”,它是“结晶点,将所有发生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交换行为统合起来”。一方面,词语从它所属的语言系统当中提取价值;另一方面,它在“语义学上的现实”等价于“言说行为上的现实”,后者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事件。但是,“word suivies the sentence”既可以理解为“语句消逝,词语留存”,也可以理解为“词语逃出法网”。词语并非注定伴随言语行为的消亡而消亡,相反,它的可重复性(iterability)允许它取回它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并且时刻准备接受不可预知的新用法。但不是原封不动地返回到它被分配好的位置上。如今语词“负载着全新的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在重新加入语言系统时,该词语改变了自身的历史进程,尽管这种改变是微乎其微的。诗歌只是将这种辩证性放大了而已。
文学作品的悖论之一在于,在不可改变性与自我完成方面,它是“结构”,然而它必须在永恒运动中进行自我完成,并且只能在阅读行动中实现自己,就此而言它又是“事件”。作品的每个字都不可改动,可是在变化无常的回应中,没有哪一个词语可以固守原来的位置。穆卡洛夫斯基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留存下来的只是结构本身,而它的内部构成——各成分之间的关联——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些相互关系当中,单个成分不断试图去支配其他成分,通过损抑他者来主张自身。等级制——换言之就是各成分之间的从属与支配……永远处在某种不停重组的状态当中。”或许穆卡洛夫斯基让文学作品听起来像华尔街,但是其内蕴的真理不会被隐喻的外壳所遮没。
选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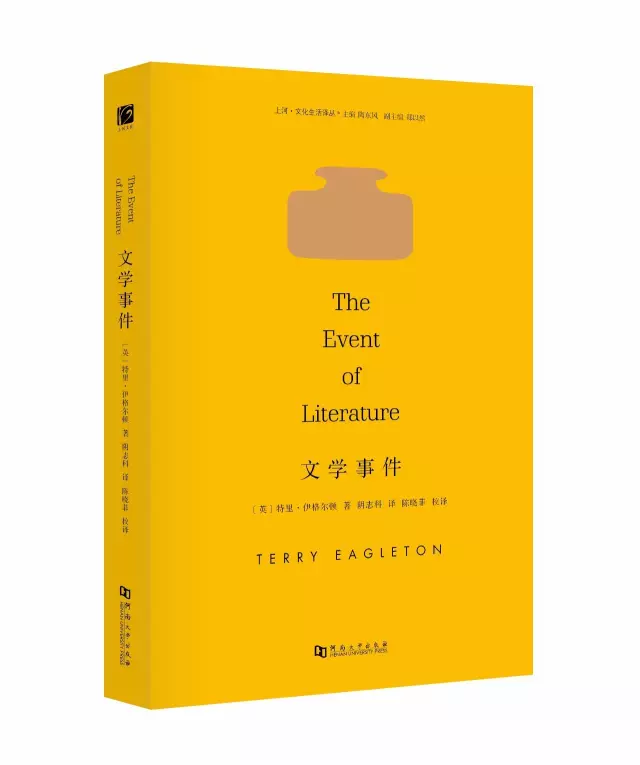
《文学事件》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阴志科 译
陈晓菲 校译
ISBN:978-7-5649-29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