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钱翰:“中性”作为罗兰·巴尔特的风格
文艺批评 2019-04-0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艺研究 Author 文艺研究编辑部

文艺研究
《文艺研究》创办于1979年5月,是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月刊。邮发代号:2-25。国外代号:M163。ISSN 0257-5876CN11-1672/J。本账号负责本杂志信息发布与交流。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
罗兰·巴尔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事业就是对意义和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启发之下,其质疑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意义观念,而是质疑产生意义的结构:聚合关系。人在聚合关系中的选择形成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偏于一边,破除这种聚合关系,才能破除价值的偏执和幻觉。巴尔特从早年的《写作的零度》到晚期的《中性》,对意识形态祛魅的方法不断演进,深刻影响了其文学风格和生存风格。然而巴尔特自己也并不能在对“中性”的欲望中保持中性的状态,“中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以巴尔特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可以梳理和发掘“中性”这个关键词在巴尔特整体思想和风格学中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巴尔特的文学历程及其思想。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2期,感谢“文艺研究”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吁真的批评家

钱翰
“中性”作为罗兰·巴尔特的风格
罗兰·巴尔特从1977年到1980年3月6日去世之前,在法兰西学院以“文学符号学”为主题讲授了三次课程,“中性”是第二年的课程(1978年2月至6月)。围绕“中性”,国内学界已经有一些文章,但是讨论尚不够深入,尤其是不少法国文学研究者把巴尔特的“中性”视为一个理论概念,主要探讨其思想内涵,而没有把这个词置于巴尔特的整体风格之中。这个巴尔特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使用的重要词汇,贯穿了他一生的思考,今天,我们重新从整体语境中深入研究巴尔特所说的“中性”,有助于理解法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表现出的独特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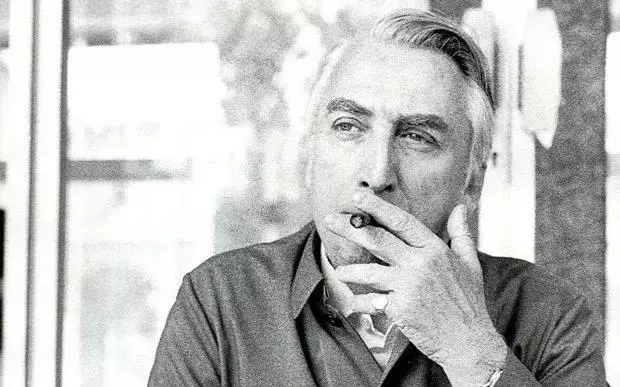
在中国,巴尔特普遍被视为一位重要的法国理论家,但是在法国学界看来,巴尔特则显得更加复杂。他确实有不少重要的理论著述,也有《作者之死》[1]这样的文章,然而他与当时主要理论家的风格大不一样。今天,理论的风潮渐行渐远之时,回头再来看巴尔特和那个如火如荼的法国理论时代,无论相比其好友格雷马斯,还是更年轻一些的德里达,甚至相比他的学生克里斯特瓦,其在理论体系上的建树也许略逊一筹,醉心于理论建构的时间也并不很长,只有十年左右。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巴尔特作为文学家或者说作家的一面却越来越凸显[2],尤其是在他70年代以后的晚期工作之中。虽然这位“二战”后法国最优秀的文体家,没有写过小说或诗歌这样的“标准”文学体裁作品,但是苏珊·桑塔格以“拒绝阐释”来形容巴尔特的时候,极为敏锐地抓住了巴尔特风格的实质[3]。理论的作用就在于提出一种阐释的方式和方法,以一种特殊的视角和观念来把握对象。巴尔特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过一个理论期,相信科学精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写作过《服饰体系》来阐释和批评流行杂志的语言符号,不过,其“拒绝阐释”的特质也提醒我们,要想看清真正的巴尔特,就不能把他简单看成一位理论家。我们对他使用的概念应该格外小心,不能以概念和命题的推演为依据来看待其写作和话语实践,而应当把他看做是一位特殊的运用理论写作的作家,因为他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是科学的,他已经不相信科学可以解决文学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中性”这个词,我们首先就不应把它看成是一个具有严密内涵和外延的概念,不能赋予它明确的定义,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巴尔特用来表达其文学和生活美学风格的理论工具。这样才能理解他在使用这个词语(我们避免使用“概念”)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内在的矛盾;同时也能把这个词语与巴尔特的其他写作结合起来,看清其语言观、生活观念和美学风格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风格演变的过程。
一、“中性”:
从零度的乌托邦向“真”出发
1964年,巴尔特在接受杜马耶(Pierre Dumayet)的电视采访时说:“我一直在思考的根本问题:文学是什么?”[4]虽然巴尔特并没有如萨特那样写作一本《什么是文学?》,而且出于其反本质主义,他最终很可能会说: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但这个纠缠他一生的问题是理解巴尔特整体文学思想和文学感觉的切入口,也是我们理解其“中性”的基本语境。他在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中提到了“中性”:“任何写作的痕迹都沉淀于一种初见是透明、单纯与中性的化学成分中,(写作的)简单持续逐渐在一种悬停状态中,揭示出越来越厚重的整个过去,就如同一部密码。”[5]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名为“零度”的书中,“零度”(zéro)这个词只出现了九次,而“中性”(neutre)却出现了十七次,成为比“零度”更加重要的关键词。实际上这本书中的“中性”与“零度”,完全可以看成是同义的。另外,“单纯”(innocent)出现了八次,“白色”(blanc)则出现了七次。当一种新的思想出现的时候,新概念常常不是孤单地走上词语的舞台,而是以概念群的方式涌现:“零度”“中性”“单纯”“白色”,构成了一个语义场,它们都指向一个文学的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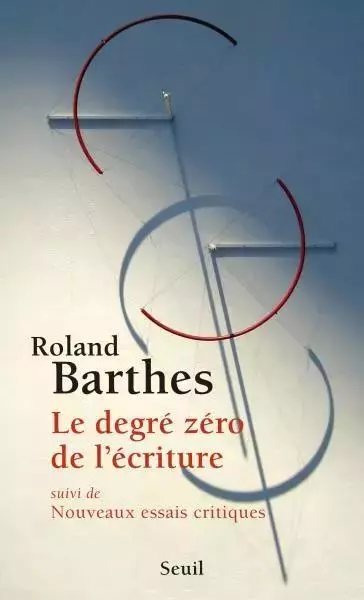
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写作的零度》
巴尔特在这本书中以一针见血的方式总结了历史上政治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遗产:过去的文学使文字染上了色彩(décor des mots),当代文学只有清除掉各式各样浓重的颜色,拒绝历史遗产的印记,才能走向其本原。理想的文学是中性的,中性是一种纯净、没有被污染的状态,是零度,也是“白色的写作”(écriture blanche),就像他在那个时期格外赞赏的加缪和罗伯—格里耶的风格。“在这些中性的写作中(此处被称为写作的零度),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一种否定的运动……就像文学从一个世纪以来就试图把它的表面改变为没有遗产的形式,文学只能在没有符号的情况下找到其纯洁性,最终他提出了成为孤儿的梦想:没有文学的作家。”[6]
我们如何理解“没有文学的作家”这样一个奇特的表述?无独有偶,罗伯—格里耶在《为了一种新的小说》中所提出的意见与《写作的零度》很类似,他认为我们的文学遗产已经使这个世界“符号化”和拟人化了,充塞的意义使我们看不见真实的世界,只有清除掉这些意义,我们才能达到现实。诗歌、小说和散文等等文学作品在生活经验的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文学的世界,在我们把眼光投向客观世界之前,一种有关世界的意识已经通过文学的经验形成了。隐喻是“自然”的:大海是平静的或者愤怒的,玫瑰意味着爱情,阴天表达的是忧郁。这些附加在事物之上的意义给它们赋予了一种“深度”,成为文学的关键。事物变得多情善感,也富有道德色彩,是人的某种象征,这也许就是“艺术之为何”,也是人们孜孜不倦描绘玫瑰、大海与清晨的原因。词、物和人同时被纳入到这个象征领域:文学。罗伯—格里耶对此提出质疑:
最少受到局限的观察者也已经无法用自由的眼睛看周围的世界。我们要立即明确一点,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对客观性的天真的想法,即遭到心灵(主观的心灵)分析家们耻笑的那种客观性……我们会记得,一片风景很“肃穆”或很“宁静”,却不能说出它的任何一个线条,任何一个基本的部分。我们甚至会立即想到:“这是文学”,我们却想不到去反叛。我们习惯于这一文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的作用,就像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组成的窗子,把我们的感觉场分解,并纳入一个个小小的格子。[7]
对于罗伯—格里耶来说,文学传统加之于事物的“增值”意义不过是人类的幻觉,是扭曲了事物本相和本色的窗户,以前的人们透过这扇窗户看东西的时候,陶醉在那些缤纷的漂亮色彩之中,其实它不过是遮蔽事物本然的哈哈镜或者有色眼镜。而我们使用语言对事物进行切分[8],就像是窗户上的格栅标志在外界的物上,它们不是自然的分界,反而是对我们目光的限制。对于这种幻觉,有人意识不到,以为窗户是透明的,把这些色彩当作真实;另一些人明白这是幻觉,然而却不以为意,或者如尼采[9]和苏珊·朗格[10]歌颂美的幻觉。
让我们重审巴尔特提出的那个根本问题:文学是什么?他不像萨特那样,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把这个问题事实上巧妙地转换成“文学应当是什么”[11],而是始终在追寻一个真相。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理论给了他追索这个答案的可能性,从《符号学原理》《神话学》《批评与真理》到《服饰体系》,巴尔特始终以祛魅的方式突破神话的遗产,他努力剥离文学历史在文字上留下的浓墨重彩,寻找那个零度的、白色的、单纯的、中性的文字乌托邦。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在《神话学》中那些机智的文章,虽然是以所谓小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主要批判对象,但是他在1971年《今日的神话学》中总结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一切“意义”都纳入到批判和祛魅的范畴:“第一时间,我们要摧毁所指(意识形态);接下来,要摧毁符号:从‘神话破坏学’在另一个层面上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一种符号破坏学(sémioclastie)。”[12]其意在揭示一个物或者现象如何变成象征的符号和意识形态价值的表征,而大写的“文学”毫无疑问也属于要被破坏的符号,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那个没有污染的乌托邦。
文学批评在19世纪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断裂,批评家的问题从“文学如何才能写得更美”转向“文学的真理是什么”。这次提问方式的嬗变确立了19世纪以后文学元语言、尤其是学院的文学元语言的根本方向。从此,文学批评的基础就不再是品味和教养,而是“求真之志”(volontéde savoir)。在与皮卡尔那场著名的关于《新批评还是新骗局》[13]的辩论中,巴尔特写道:“人的智性通向了另一个逻辑,它开启的是一个‘内部经验’的空白领域,人们追寻的是一个唯一的同质的真理……”[14]在这场通向“真理”的征途中,人类的文学史不断层叠堆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就不再是美的遗产,反而变成妨碍人们达到那个纯粹的“真”的障碍,所以巴尔特试图发掘五颜六色的图画底下最初的白色织物(texte,“文本”最初的含义就是纺织物),重新归于中性的零度,开辟文字和书写的纯洁的乌托邦。巴尔特的符号破坏学和法国人20世纪60年代建构科学理论的激情,必须放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当然,在这场破坏大战中,巴尔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转换:从“作品”到“文本”[15]。“这个术语转换的背后隐藏着文学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是对文学制度的质疑。在传统观念中,文本是与作品相互关联和对立的观念,文本要走向作品,后者是前者的归宿。”[16]“文本”概念走上前台,动摇了传统的文学价值体系和等级。相比“作品”,“文本”这个概念显得更加中性、单纯、白色,靠近零度。

罗兰·巴尔特

二、“中性”:从零度到差异和多样性
巴尔特始终坚持这个破坏学,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中性》。不过,同样都是破坏,巴尔特在早期和晚期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写作的零度》中,“零度”“白色”与“中性”是同义词,常常混用,然而到晚期,“零度”和“白色”逐渐从他的词汇表中消失了。巴尔特早期的文章中,常常对“一边,另一边”“左和右”“资本主义和革命”矛盾双方都做出批判,试图开辟出一片可以容纳真相的清白之地。然而,他似乎渐渐认识到这一乌托邦是没有可能的,就像他在《今日神话》中所说的:“他对集体的语言进行的解构对他而言是绝对的,要彻底摧毁其自身的工作:他义无反顾,无法回头……乌托邦对他来说是无法承担的奢侈……”[17]在1964年出版的《批评文集》的序言中,他说:“这个最初的话本来可以表达我的痛苦,这纯洁的话本来只是纯粹要说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是这最初的话也是一个乌托邦;他人的语言活动把这个话传递给我的时候就已经被装饰了无数我不想有的信息:索绪尔的真理在语言学之外,就在此处产生了效果;仅仅只是写一封表达哀悼的信,我的同情就变成了无动于衷,词语使我显得只是冷淡地遵从了一种习惯……”[18]
巴尔特经历了理论时期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写作上来说,巴尔特最大的特点是从早期的“两边否定”,转向了“多重肯定”。“中性”不再是寻找一片没有被符号和神话污染之地的努力,不再是对回归零度和白色的想象,而是对现实更广阔的容纳与混同。也许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转变:透明的光分为两种,一种是本身就无色透明的纯洁的光(例如激光),另一种则是如太阳光一样,七种色彩的光混合一起,形成了透明的光。这个翻转使巴尔特从“唯一的同质的真理”,转向了差异和杂多。

Roland Barthes, 《S/Z》
在《S/Z》中,巴尔特首先否定了自己此前寄予厚望的科学:“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得以在一粒芥子之内见到须弥。这是早期的叙事分析家想达到的目标……这是桩苦差事,需要殚精竭虑(真是‘耐心的科学,实在的苦刑’),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并不令人欢喜,因为文本由此而失掉了它的差异性。”[19]从这里出发,巴尔特转向了差异的诗学,这个转向常常被看成从结构主义到所谓解构主义的标志,同时也被看成是巴尔特放弃科学主义的转折点。不过,这里需要强调,巴尔特放弃科学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真”的追寻,而只是不再相信那个唯一的科学化的真理。蒂凡娜·萨摩约(Tiphaine Samoyault)在《巴尔特传》中对此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巴尔特把整体打成碎片,让事物走向碎片化,更加接近真相。……拒绝了超验的文本模型,《S/Z》的主导方法就是把每个文本看成是它自己独有的模型,并在其差异性中对待每个文本,最小的变化也构成了它自己特殊的事件。”[20]在这里,对“物”(choses)的直接体验,并不像《神话学》或者《写作的零度》一样,代表了某种纯净的无污染的诗学乌托邦,而是差异的、杂多的、与符号意指混为一体之物。在同一年出版的《符号帝国》中,那个激烈嘲讽一切“神话性”(也就是符号性)的巴尔特变成了对日本符号或者说神话充满热情的巴尔特,当然这是与西方文化不一样的符号与风格。他谈到了日本城市的“空”:
基于很多原因(历史的、经济的、宗教的、军事的),西方几乎过分地遵循了这样的规律:所有的城市都是同心圆结构的(contentriques);而且与西方形而上学的运动一致,所有的中心都是安放真理之处(lieu de vérité),我们的城市中心总是满满的:一个显眼的地方,文明社会的价值在这里凝结和聚集:精神性(与教堂在一起),权力(办公大楼),金钱(银行),商业(大型商场),语言(人群集合之处:咖啡馆和散步的场所):进入中心,就是与社会的“真理”相遇,就是参与到了不起的丰富的现实。
而我要谈到的城市(东京)则体现出珍贵的反面:她也有一个中心,但是这个中心是空的。整个城市围绕这一个地方,它既是无法进入的,也是无所谓的(indifférent)。这个处所被绿荫掩蔽、护城河保卫着,居住着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皇帝,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谁。[21]
表面上指向日本东京的这段描写,如实反映了巴尔特的文学趣味和他的文本观:去中心和去价值,他在为“Universalis”百科全书写作的著名辞条“文本”(texte)中写道:“判定文本的标准,至少就某个独立的方面来看,取决于它是否被高贵的、人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的规范是在学校、批评和文学史中确立的)所拒斥和贬低……”[22]文本理论的核心是对价值体系的颠覆,而这种颠覆不是以新的价值观取代旧的价值观,而是被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实践,并且在这种绝对的反叛中感受到高潮(jouissance)[23]。空的东京如同空的文本,没有本质,是一片没有中心的星云。众所周知,正如巴尔特自己认可的,他的文本理论受到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的重大影响,而互文性恰恰与传统的文学史批评常用的汇聚文本(con-texte)[24]相对立。文本理论和互文性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提出了文本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其实,无论是西方解释学还是中国的训诂学,都很早就意识到并研究这种关系。传统批评和阅读中,以考据的方式探寻围绕中心文本的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最终确定构建这些文本之间关系的意义的真理(vérité)是什么,这是一种太阳系一般的向心力,如西方的城市一样是同心圆结构;而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则是消灭中心,废除文本之起点和终点,他与克里斯特瓦喜爱的“inter-”是离心力,如星云一般,没有中心,也没有作者(作者已死)。巴尔特在为东京配的地图上写了一行批语:“城市就像一个象形文字(idéogramme),文本继续。”[25]也就是说,在他眼里,文本就像星云般展开的东京,是一个无中心、无边界的纺织物。东京表面上有一个具体的位置和边界,然而,这个城市在每时每刻呈现的区别中,永无停歇,而文本也一样,最后的句号并不是它的终结之处,而是继续的标记,是真正的阅读或者说“重读”开始的地方,通过重读,文本变成复数和差异:“我们还需要最后一个自由度:阅读这个文本的时候犹如曾经已读过。……然而就我们想确立复数性而言,不可将这种阅读阻挡在门外,因为阅读方式本身也是复数的,多样的……我们一开始就在此提出重读,因为只有它可以把文本从重复中拯救出来……重读质疑如下说法:初次阅读是原形、素朴和现象性的……我们所要获得的,并非文本的真实,而是文本的复数性:既是相同,又是全新。”[26]
对比法国现代派象征主义的旗手马拉美的诗学,我们也许能够更准确地看清巴尔特的差异美学观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马拉美的诗歌形而上学观念接续柏拉图的哲学,认为现象世界背后隐藏着更真实的世界,在相对的和复杂多变的世界背后有一个绝对的世界,而诗歌就是通过象征的方法探索这个纯粹之物,每一个诗句都对应着整体的诗歌:“诗歌是通过人类的语言来表现多样存在的神秘意义,这个语言有其本质的韵律:诗歌就这样独特地展示了我们的生活并完成了它唯一的精神任务。”[27]在《诗句的危机》中他写道:
我说:一朵花!我的声音中遗忘了真实的花的任何轮廓,在遗忘之中音乐般升起某种东西,与人们熟悉的花萼无关,只是花本身的甜美概念,使它远离一切现实的花束。[28]
在马拉美那里,诗歌的语言是纯粹的概念,而不是它所指的现实事物,诗句中“花朵”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仅仅意味着“概念的效果”,而不是现实花朵的效果,诗歌并不是用来描绘世界的,诗句仅仅展现了它们自身的联系,马拉美追寻那个纯粹的语言。巴尔特则对语言和概念不那么信任,表意(signification)总是不那么纯粹,偏离真相,也许只有在非语言、非概念和非表意中才能发现真相。在对照片和图像的评论中,他写道:
不管怎样,我们看到,内涵能够走得很远。能否说,一种纯粹的外延,即一种停留于此岸的言语活动(en deçà du langage),是可能的呢?如果这种外延是存在的,那么,它也许并不是在日常的言语活动称之为无意指活动性特征、中性、客观性的层次上,而是相反在真正创伤性的图像层次上:所谓创伤,恰恰是中止了言语活动、阻碍了意指的东西。[29]
巴尔特所谓“创伤性的”,指的就是在我们的语言体系中无法被分类,无法确定其内涵(connotation),最终使我们无法命名,让我们无法言说。因为“人是喜爱符号的,喜欢让它们清晰”[30]。符号的功能是让人给对象加以分类,使人把含混的世界区分开来,就像盘古开天辟地,阴阳分开,万物获得命名,并被认识,这使人感到安心,因为通过命名和知识,我们得以把握这个世界。然而,无法言说之创伤却使我们从这个稳定、固化的世界中被抛出来,无法再“定义”(définir)这个无穷的世界。“définir”这个法语词由两部分构成,“dé”是强调,而“finir”是达到终点,有一个结束。这意味着:在确定内涵(定义)的过程中,人们把杂多的世界结束于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定义之中。当我们把对象纳入到这个依据于同一性(identité)而规定的概念(词语)体系中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精神上的创伤和冲击。“冲击性照片(photo-choc)从结构上讲是无意义的(insignifiante):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知识,极言之,在意指的构成过程中没有形成任何的语言的范畴化。我们似乎可以想象一种规律:创伤越是直接,内涵就越是困难:或者说,一幅照片的‘神话学’效果(effet mythologique),是与其创伤性效果成反比的。”[31]换句话说,要想颠覆和超越神话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就要冲击已有的意义和价值习惯,感受这种因为无法言说造成的创伤。这样,我们才能像巴尔特一样感受他所谓的文本体验:“当我在摩洛哥干涸的河谷中,突然维吉尔般美妙的立体声音迎面而来——鸟鸣、远处儿童的哭喊、抽水机的马达声,此时我身上产生了文本和文本性强烈的意识;乡村、文本,这就是了:田园诗般的地方穿越某种机器:一些色彩、一些寂静、一些微风,这些古老的浪漫的文化价值构成的锦缎,被摩托车的喧嚣割断。”[32]这里的文本不是语言书写的产物,它恰恰是反符号、反文字和反言说的。当这个世界从符号、言说和文化逃离之时,摩托车的喧嚣隔断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文化命名和控制,一切归于本来的自然中性状态,这就是巴尔特的精神桃花源。从这里,我们也就能明白他对老庄的兴趣。
三、“中性”:无法言说
巴尔特“中性”这门课程一开始引用两个著名的场景。一个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德烈公爵受伤倒地,睁开眼看到了天空:“他在遐想,‘这跟我们在呐喊和炮击当中狂奔的样子多么不同啊!’……我怎么就一直没见过这天空呢?我最终还是发现了它,真是幸福啊!除了这无边无涯的天空以外,一切的一切都是虚荣,都是欺骗。除了它,一切都不存在……或许这是一个诱饵,除了寂静和安息之外,什么都不存在。感谢上帝!……”[33]另一个是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他散步时被一条大狗撞倒,晕厥受伤:“我发现自己躺在三四个年轻人的臂弯里。他们讲了事故的经过……夜色渐深。我看到了天空,寥落的星辰和花草的一丁点儿绿色……我在这一刻重新获得了生命,感到我似乎在用看到的一切充实我那卑微的存在。这个时刻我仍然回忆不起来任何事情;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全然不晓,不知道我是谁,身在何处;既没有感觉疼痛,也没有感觉害怕和不安。我看到自己的血在流淌,小溪似的流淌,根本没有想到这血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在整个生命里感到一种令人欣悦的平静;每次回想起来,我都感到这种平静是我所体验过的任何乐趣都无法比拟的。”[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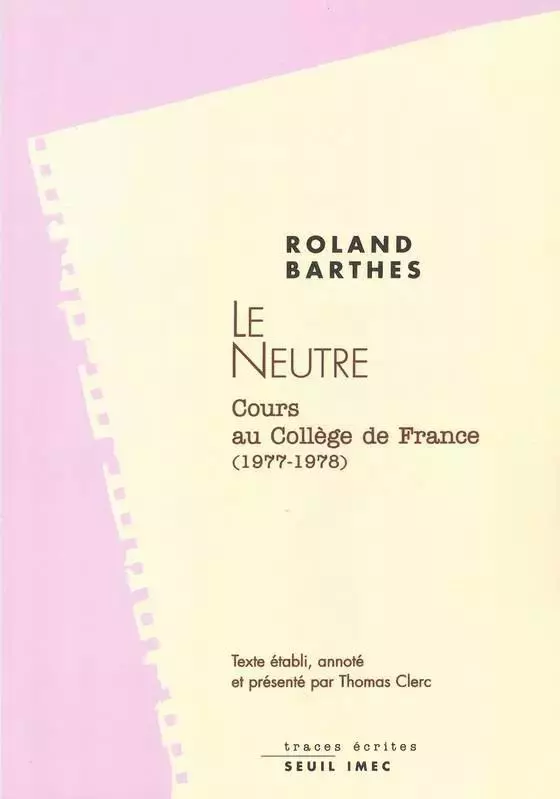
Le Neutr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中性》
研究《中性》的文章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巴尔特对“中性”的理论说明上,很少讨论作者引用的这两个文本。这些场景与之前巴尔特在摩洛哥的河谷中听到摩托车响声的感觉类似,都是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冲击(choc),刹那间截断日常的观念、文化和思想。“中性”最大的秘密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断裂和冲击,使人进入某种难以言说的状态。人脑日常的范畴化和概念的工作停止,日常的价值观和命名遇到困难,这时我们迎头撞上了尚未被划分的世界本身,如同我们头脑中的曾经被盘古用斧子劈开的、清清楚楚的世界,重新又回到了阴阳不分的混沌天地,或者回到了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果之前的那个懵懂的乐园。
巴尔特从理论上把“中性定义为破除聚合关系(paradigmes),或者凡是破除聚合关系之物即为中性”[35]。现代语言学从索绪尔开始,认为语言表意的基础是建立在区分和对立之上的结构:“凡是有意义的地方,就有聚合关系;凡是有聚合关系(对立)的地方,就有意义。简略地说,意义的基础是冲突(取此舍彼),而一切冲突都产生意义:取一个,舍另一个,意味着是对意义的献祭,生产意义,让人们使用意义。”[36]因此,意义的生产总是在选取一边的时候牺牲另外一边,这就是所谓意义和价值的生产机制。人在聚合关系中的选择形成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且执于一边,只有破除这种聚合关系,才能破除价值的偏执,祛魅意识形态,进而获得自由。
我们思考的总体场域将是:伦理学是有关“好的选择”……或者“不选择”,或者“从旁选择”:即在选择之外,在聚合关系的冲突之外……
让我补充一句:就我来说,对中性的思考是(自由地)寻找一种在时代的斗争中,我自己如何自处和面对的风格(mon propre style de présence aux luttes de mon temps)。[37]
这一段的中文翻译“寻找在时代抗争中的自身风格”[38],似乎与原文差不多,但“风格”却大不相同,中译文的意思似乎是巴尔特要以自己的风格参与到时代的斗争中,而巴尔特的原意则是自处和面对。
巴尔特一般被当作左派知识分子,然而他的行事风格又与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们不同:一方面他与左派的“如是小组”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他也常常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却基本不直接介入政治,不参与当时知识分子热衷的请愿和签名活动,没有走上街头与愤怒的群众携手示威。1968年运动中学生批评“结构不上街”的时候虽然并不专指巴尔特,但是巴尔特“不上街”却是事实[39]。他在提到“愤怒”一词的时候说道:“在神话里,中性总是与软弱、不强烈的‘状态’(感性诉求)相联系。它疏远并摆脱强烈的、显著的、激烈的状态(后者因此属于阳刚之气)。→我们讨论强烈感情的时候,可以‘愤怒’为例:它的作用正是反中性。”[40]
然而,据此认为巴尔特所说的“中性”的风格就是温和、平静,恐怕也是一种容易出现的误解。翻译过不少巴尔特著作的张智庭说:“以‘平和’这一相同义素联系起来的具有同位素性的关联文本……而且这种‘平和’赋予了‘中性’以基调。”[41]吊诡的是,巴尔特的思想与他喜爱的老庄思想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是:一方面反对意志强烈的争斗,认为人世间的种种冲突没有什么意义,尤其不愿掺和现实的政治斗争;但是另一方面却惊世骇俗,始终产生着“冲击”,构成现实世界的创伤。巴尔特对此有一个非常敏锐的总结:“中性就是丑闻。”[42]老子也自嘲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於人,而贵食母。”[43]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所有的贪欲(vouloir-saisir)造成的,但是当有人跳离出来说,“你们的算计都太聪明,我是愚蠢的”,那么他在使自己成为丑闻的同时,也使一味执著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人变成丑闻。因此,这个退出冲突的行动和姿态并不必然显得“平和”与“和谐”:众人的喧嚣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巴尔特的“中性”和道家思想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切价值观的基础。知识分子们发表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观点,固然是人类文明史永恒的争议主题,但是“善之与恶,相去若何”[44]取消善恶的对立,恐怕比对立的善恶观构成更为强烈的冲击。因此以“中庸”为最高典范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常常不忘严厉批评老子蛊惑人心,甚至“猖狂自恣”[45]。
然而“中性”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思辨,甚至不是以思想方法推倒现存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而在于人的生活自身。巴尔特在讨论“无为”的时候,敏锐地首先提到生存意志(vouloir-vivre),因为所谓“无为”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生存意志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基于不同的生存意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种不同如何解决?“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意志,因此,既然我们都有朋友,我们接受某些生存意志,反过来,别人也接受我的生存意志。”[46]这是人生于世的根本处境,儒家的行为方案是以“无不敬”的自我要求来尊重众人之生存意志,确立明确的是非观念,从而构建和谐的社会,这与西方的传统道德差别不是太大。而按照巴尔特所理解的道家的方案“无为”,则是放下选择:“道家无为的深层态度=不作取舍。……非常困难,因为这与定见冲突,损害形象(imago)→因此必须承受→道家充分意识到这个困难。”[47]
困难之处在于,人的生存与意义和价值观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实在的“物”,无法得到也无法摧毁,却又无处不在,从不停歇,是人之生存意志的外显。同样,“中性”也不是一个物,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到“中性”。认识“中性”是容易的,思辨也未必困难。然而既然价值构成了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对于中性的欲望”[48]就总是会遇到困难。暂且不论“对于中性的欲望”或者老子所说的“欲不欲”在逻辑层面上的悖论,就意义作为人的根本生存处境而言,打破构成意义的聚合关系,就不是一件说得通的事情。因为“说得通”本身就需要一个意义体系的承载,巴尔特说:“认识中性容易:既认识又谈论中性难。”[49]他又提到禅宗要摆脱“语言的扰动”[50]。我们也许会惊讶巴尔特在这里没有引用老子最著名的那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过,巴尔特、道家和禅宗的修行者,在他们的实践中,恐怕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体认“中性”。这并非类似解答一道数学题,或者写作一篇论文,可以得到结果。“中性”是一个语言问题,同时又不仅仅是用语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语言及其聚合关系同时构成人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除非彻底更新或者消灭这个结构,否则“中性”的颠覆永远只能处在一个“尝试去颠覆”的状态。判断的悬置(suspension du jugement)也还是会走向判断。巴尔特最终还是会难免接受自己处于一种“中性”和“非中性”两边游离的状态。事实上,巴尔特一方面始终质疑和批判价值和本质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不断显露自己的价值观。他在后期不但放弃从作品到文本的观念,提出重新回到“作品”[51],同时还对当代文学价值的沦落倍加伤感:“书籍,本来是神圣之地,已经不再神圣,变得平庸:当然还有人买书,有点像超市里的冰冻披萨,但是已经失去往日的荣光。”[52]贡巴尼翁把巴尔特当作在现代和反现代之间撕扯的典型代表[53],而巴尔特在《自述》中也自嘲有点“精神分裂的风格”[54]。被人看做是先锋派的他,甚至激烈地批评当代文学,维护传统经典作家:“今天的小说,也就是如尘土一般铺天盖地的小说,而不再有伟大的小说,它们身上已经没有价值的意图,也没有任何伦理的理想或激情,就我来判断,这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境况,私人的牢骚:是真实伦理的衰退或中断→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历史的倒退……”[55]巴尔特在这里表现出的对伦理和美学的激情与《中性》看上去似乎格格不入,但是又合情合理。
巴尔特并不自诩真如老庄所说的已臻齐物之境的“至人”或者佛家所言“见平等相”的菩萨。对“中性”的欲望并不能真正获得。就像他自己所言,保持这个状态是极难的,甚至于不可能。难言的“中性”也并没有让他彻底消解意义的聚合关系,只是试图在思考和行为之时,在人们深陷于其中的意义生产关系里,他尽可能保持一种“中性化”(neutralisation)的可能性,始终保持对“中性”的欲望。在现存的聚合关系的另一个层次上,引入新的聚合体消解现存的意义结构。“中性”本身没有“本质”(nature),不能获得,不是一个可以占有的状态,只能在生命中不断得到欲望,并体认这个欲望。无论在个人的思想中,还是在社会意识的冲突中,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斗争。如他的一生所表明的那样,“‘破除聚合关系’是一场热情洋溢、激情似火的行动”[56]。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2期
注释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1] Roland Barthes, “La Mort de l’auteur”, Manteia, 4e trimestre, 1968, Œuvres complètes, édition établie et présentée par Eric Marty, t. II, Paris: Seuil, 1993, pp. 491-495.
[2] 黄晞耘:《罗兰·巴特:业余主义的三个内涵》,载《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3]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苏珊·桑塔格文集》,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4] 1964年3月25日的电视采访节目(http://www.ina.fr/video/I05265306/roland-barthes-sur-son-livre-essais-critiquesvideo.html)。
[5][6] 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Paris: Seuil, 1953,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 p. 148, pp. 140-141.
[7] Alain Robbe-Grillet, Pour un nouveau roman, Paris: Minuit, 1961, pp. 17-18.
[8] 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分类命名所隐含的语言观是:语言是给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事物贴标签的产物。然而,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符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没有必然性。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因此,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这一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声音”就隐含着区分,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区分是语言得以成立的条件,同时也只有通过语言,人类才得以完成对世界的区分。就像中国神话中所说的盘古开天辟地,从象征的意义来说,他用以砍开天地的斧头就是语言。而语言是人造之物,并不是“自然的”。这一理论也是整个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论基础,语言与自然世界之分裂都是基于这一思想。
[9]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阐发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其实质都是制造幻觉的艺术,不过在尼采看来,这种幻觉恰恰使人类有了超越悲剧命运的勇气(参见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10] 参见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 Jean-Paul Sartre,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Paris: Gallimard, 1948.
[12] Roland Barthes,“La Mythologie aujourd’hui”, Esprit, avril, 1971,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p. 1481.
[13] Raymond Picard, 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 Paris: Jean-Jacques Pauvert, 1965.
[14] Roland Barthes, Critique et vérité,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p. 36.
[15] Roland Barthes, “De l’œuvre au texte”, Revue d’esthétique, 1971, 3e trimestre,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pp. 1211-1217.
[16] 钱翰:《从作品到文本——对“文本”概念的梳理》,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7]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Paris: Seuil, 1957,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 p. 718.
[18] Roland Barthes,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1964,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p. 1172.
[19][26] Roland Barthes, S/Z, Paris: Seuil, 1970,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p. 557, pp. 564-565.
[20] Tiphaine Samoyault, Roland Barthes, Paris: Seuil, 2015, p. 464.
[21][25] Roland Barthes, L’Empire des signes, Paris: Seuil, 1970,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p. 767, p. 768.
[22] Roland Barthes, “(Théorie du) Texte”,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Paris: Universalis, 1996.
[23] “jouissance”这个词在中文常常译为“狂喜”,也有人译为“绝爽”,笔者认为译为“高潮”也许更接近原义。该词本身在法语中只是一个普通生活词汇,只是巴尔特等人用它来表达一种文学思想。汉语中“高潮”亦为普通生活词汇,也有多种隐喻和引申义。
[24] “contexte”,英语为“context”,一般翻译为“语境”,但是在这里主要为了强调“inter-”与“con-”的对立,因此,此处译为“汇聚文本”。
[27][28] Mallarmé,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98, p. 657, p. 213.
[29][30][31] Roland Barthes, “Le Message photographique”, Communications, 4e trimestre, 1961,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 p. 948, p. 947, p. 948.
[32] Roland Barthes, “Sollers écrivain”,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p. 962.
[33][34][35][36][37][40][42][46][47][48][49][50] Roland Barthes, Le Neutr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annoté et présenté par Thomas Clerc, Paris: Seuil, 2002, p. 29, p. 30, p. 31, p. 3, p. 131, p. 107, p. 106, p. 222, p. 223, p. 25, p. 232, p. 233.
[38] 罗兰·巴尔特:《中性》,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39] François Dosse,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2, t. II, pp. 159-172.
[41] 张智庭:《罗兰·巴特的“中性”思想与中国》,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3期。
[43][44]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48页,第46页。
[4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1页。
[51][54] Roland Barthes,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Paris: Seuil, 1975, repri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I, p. 199, p. 173.
[52][55][56] Roland Barthes,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Cours et séminaire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et 1979-1980), texte établi, annoté et présenté par Nathalie Léger, Paris: Seuil, 2003, p. 243, p. 363, p. 32.
[53] Antoine Compagnon, Les Andimodernes, Paris: Gallimard, 2005, pp. 404-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