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 现代诗歌文化艺术 2019-10-04
凡本刊发表的文章阅读量满1000,评论10条即有15元稿费,阅读量满2000评论20条即有30元稿费。领取方式:直接截图发总编即可领取!以上以初发时间6天内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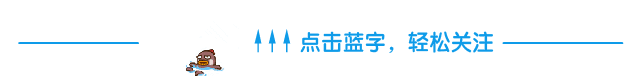
天地有大美巫娜 - 风月无古今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诗人何为?
·
艾略特说过:“我们必须记着,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认定,但是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认定。”(《宗教与文学》)
每位诗人都渴望写出伟大的诗篇。但是什么样的诗篇才称得上是伟大,艾略特的说法很能给我们以启发。在我看来,能够写出伟大诗篇的诗人,不仅仅是掌握了诗歌技能、技法的诗人,而且应该是有自由的心灵,有高洁的品格,有博大的爱情,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承担的诗人。他的灵魂中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一个层面是向下的,要执着地固守着大地,这二者力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诗歌中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概括起来,那便是仰望天空与扎根大地的统一。
当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的时候,也许低俗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所有人都去低俗,而应当有中流砥柱来抵制低俗。也就是说,有陷落红尘的人,就应有仰望天空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毫无疑问,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固然,天空是美的,如哥白尼所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跟天空相媲美,能够比无美不臻的天空更美呢!”不过,我们这里说的对天空的关注,不单是迷醉于天空的美,而是指天空所能给我们的启发与想象。实际上,对天空的关注,更是对把个人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的那样一种人生境界的关注。
人生是一个过程,寄居于天地之间,追求不同,境界也就存在着高低的差别。诗人郑敏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念书时,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哲学”课。冯友兰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说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生物学的本能和社会的习俗,对于他所做的事情的性质,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处于混沌的状态。功利境界,是说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增进自己的荣誉。他所做的事,其后果可以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是说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他为社会的利益去做各种事,不是以“占有”,而是以“奉献”为目的。天地境界,是指在此境界中的人,知道人不但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且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在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却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这样的人,就其形体而言,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就其精神而言,却超越了有限的自我,进入浑然与天地融合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天地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一个人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的“顶峰体验”,便是一种主客观交融的生命体验。此时,审美主体从拘囿自己的现实环境、从“烦恼人生”中解脱出来,与审美对象契合在一起,进入一种物我两忘、自我与世界交融的状态,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管子》上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天即宇宙,宇宙是人所生活的大环境,人只有和宇宙这个大环境保持一致,才能领略到人生之美、宇宙之美,抵达人类生存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的澄明之境。
仰望天空便是基于人与宇宙、与自然交汇中最深层次的领悟,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内心的无限自由对外在的有限自由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从而高扬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认识宇宙,也就是认识人类自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种种的限制,生命的有限和残缺使得人类本能地幻想自由的生存状态,寻求从现实的羁绊中超脱出来。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伟大的诗篇都是基于天地境界的。曹操的《观沧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就是因为它们传达了宇宙人生的空漠之感,那种对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有限的深沉喟叹,那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成为诗学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优秀诗人的身上也不难寻觅出这种超然与旷达。宗白华曾这样描述自已的创作心境:“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我和诗》)宗白华结合他切身体验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自我与天地交融的审美心境。在这种心境下写出的诗,才能“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梁宗岱:《谈诗》)。
基于天地境界的诗歌写作即是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
仰望天空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超越,但这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这是由于审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是指向抽象的理念世界或超验的彼岸世界,而是高度肯定和善待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与自由。因此,终极关怀脱离不开现实关怀。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扎根大地,重视日常经验写作。把诗歌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在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更需要诗人有独特的眼光,要以宏阔的、远大的整体视点观察现实的生存环境,要在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经过诗人的处理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
这里要特别提及新世纪以来的关注弱势群体的诗歌写作,这不仅牵涉到诗人的伦理取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历史并非滋生幸福的土壤。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出动人的诗篇。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苦难意识,这里不单有对社会生活的苦难体验,更有诗人在精神上去主动承受苦难的一种人生态度。夏济安说过:“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耶稣基督在荒野里对魔鬼说:‘撒旦,走开!’这些都是两位教主生命中的大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悟到了‘道’,他们有了自信。这种内心的动作,应该和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风病人这种外界的动作一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如果没有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风病人那样身历苦难,如果没有他们那颗博大的爱心,也就不会有他们得道时的“悟”,对诗歌之“悟”,亦可作如是观。
当然,作为诗歌,关注弱势群体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关注弱势群体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
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俗的红尘遮蔽了人性的诗意本质的时代,不能不让人思考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有名的命题:“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诗·语言·思》)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芸芸众生。他不仅要忠实地抒写自己真实的心灵,还要透过自己所创造的扎根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世界,展开自觉的人性探求,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召唤自由的心灵,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诗探索》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