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在中国流传最广诗歌《礼物》的8个译本,译者均为当今名家
多人 诗想者HIPOEM 2019-0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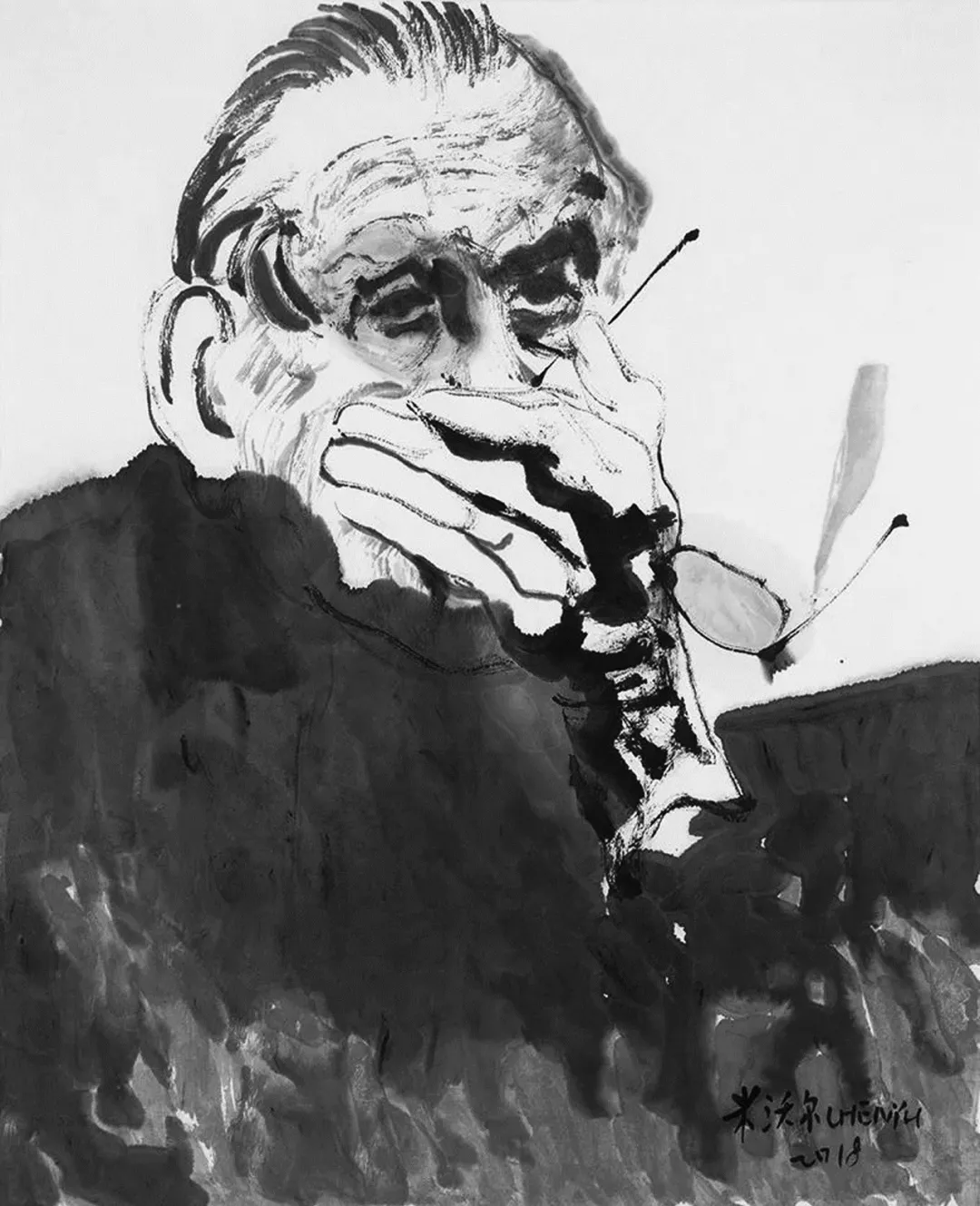
(塔社阿非工作室)陈雨 / 绘
《礼物》(Dar)也许是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流传最广的诗作。以下是米沃什《礼物》的8个译本。
1 西川 / 译
礼物
诗/〔波兰〕 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
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2 李以亮 / 译
礼物
诗/〔波兰〕 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早早散了,我漫步花园。
蜂鸟歇息在忍冬花。
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我遭受过的一切邪恶,我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使我难堪。
在我体内,我没有感到痛苦。
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蔚蓝的大海和叶叶船帆。
3 杜国清 / 译
礼物
诗/〔波兰〕 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拥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我曾遭受的任何恶祸,我都忘了。
认为我曾是同样的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我没感到痛苦。
当挺起身来,我看见蓝色的海和帆。
4 韩逸 / 译
天赋
诗/〔波兰〕 米沃什
日子过得多么舒畅。
晨雾早早消散,我在院中劳动。
成群蜂鸟流连在金银花丛。
人世间我再也不需要别的事物。
没有任何人值得我羡慕。
遇到什么逆运,我都把它忘在一边。
想到往昔的日子,也不觉得羞惭。
我一身轻快,毫无痛苦。
昂首远望,唯见湛蓝大海上点点白帆
5 沈睿 / 译
礼物
诗/〔波兰〕 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劳作。
歌唱着的鸟儿正落在忍冬花上。
在这世界上我不想占有任何东西。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不管我曾遭受过什么样的苦难,我都忘了。
想到我曾是那同样的人并不使我难受。
我身体上没感到疼。
挺起身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
6 张曙光 / 译
礼物
诗/〔波兰〕 米沃什
多么快乐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中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的上面。
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
无论遭受了怎样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是同的人并不使我窘迫。
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
直起腰,我看见蓝色的海和白帆。
7 马永波 / 译
天赋
诗/〔波兰〕 米沃什
一天如此幸福
雾气早早消散,
我在园中劳动。
蜂鸟落在忍冬花上。
在世上我不想拥有任何事物。
也没有任何人值得我羡慕。
曾经遭受的不幸,我都忘在一边。
想起过去也没有困窘不安。
我的身体感觉不到痛苦。
当我直起身,看见
蔚蓝的大海上白帆点点。
8 胡桑 / 译
礼物
诗/〔波兰〕 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园中劳作。
蜂鸟们停在忍冬花上。
尘世间的事物,没有一样我想去占有。
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羡妒。
遭受过的任何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曾经我是同一个人,并不使我羞愧。
在我身上,我感觉不到任何痛苦。
直起腰,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
《礼物》这首诗写于1971年。米沃什在1960年结束了在法国的十年流亡生涯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在1980年,米沃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以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
描述人在激烈冲突世界中的暴露状态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米沃什成了他诗中所说的“失踪的人”——离开祖国,成为内在和外在意义上的双重流放者,只有在记忆中回到故乡的市镇和乡村。“失踪”意味着另一种“出现”,意味着告别虚假,追求真实,意味着清醒地写作,在一个黑暗世纪中表达对和平与正义之国的向往,为人类理想和尊严发言。
1968年,米沃什写过一本自传——《另一个欧洲》。他认为存在两个欧洲,自己是“另一个欧洲”(东欧)的孩子,命定要坠入20世纪的“黑暗中心”。他出生于“另一个欧洲”——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立陶宛。由于当时立陶宛归入波兰版图,米沃什又一直用波兰语写作,因此他是一个波兰诗人,而非立陶宛诗人。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诺(犹太人称它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接受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学生时代,他读到了一套波兰出版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丛书”,其中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一书对他启发很大,直接影响了他的诗歌观念。主人公尼尔斯骑鹅在天空飞翔,时高时低,既俯视地球又仔细地观察它。这一双重眼界成为诗人职业的隐喻。后来,米沃什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距离是美的灵魂,但也要对现实进行热情追踪并了解全部的现实。
1933年,21岁的米沃什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冰封的日子》,随后去巴黎留学。在巴黎,米沃什结识了一位亲戚——立陶宛裔法籍诗人奥斯卡·米沃什(1877—1939),这是一位巴黎的隐士、幻想家和先知。老米沃什将小米沃什视作亲儿子,以他强有力的人格力量教诲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在心智活动方面要追求一种严谨的、律己的体系,同时,当旧爱已被怜悯、寂寞和愤怒销蚀殆尽的时候,要向一个滑向灾难的疯狂世界发出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波兰被德军占领,米沃什留在华沙参加了抵抗运动。除了秘密写作,还选编了一部抗德诗集《无敌之歌》。战后社会主义波兰成立,米沃什成为外交官,先后在华盛顿和巴黎的波兰使馆任文化参赞和一等秘书。随着斯大林主义盛行,他于1951年离开祖国,自我放逐到西方。旅居巴黎十年后移居美国伯克利,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并于1970年加入美国国籍。

从米沃什的生活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创作历程和思想脉络。在“另一个欧洲”,历史已成为一个“嗜血的神祇”,充塞一个国家的是畸形的幽默、荒唐的罪恶、可怕的德行、现实梦魇般的不合理以及罗宾逊·杰弗斯所说的“非人主义”,人们过的是被迫接受的生活,而不是自己选择的生活。诗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普遍的灾难:“变化的毁灭过程——在个人身上,在国家身上,以及在体系身上。”(《青年人和神秘事物》)“不论你到哪儿,都会碰上同一堵移动的墙。”(《野兽的肖像》)“每分钟世界的惨状使我惊讶。……每分钟一摸就在肉里感到创痛。”(《一个诗的国家》)米沃什还谈到自己反复做过的一个梦:一道致命的光线追逐着他,等他到达安全的岸边,终于将他穿透了。
既然岁月已经改变了我的血,
而成千的行星系统在我肉体中生生死死,
我坐着,一个灵巧而愤怒的诗人,
眼睛斜视,满怀恶意。
手中,掂量着笔,
我密谋复仇。
——《可怜的诗人》
这幅精神肖像表明,米沃什首先是一位警惕、愤怒和抗议的诗人。正如他在诗中呼唤的:“哦,黑色的背叛,黑色的背叛——雷霆!”(《阿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在《康波·代·菲奥里》一诗中,米沃什写到了诗人的愤怒是怎样被点燃的。康波·代·菲奥里是罗马的一个广场,天文学家乔丹诺·布鲁诺因宣传哥白尼“太阳中心学说”在此被宗教法庭处死。米沃什认为,处死布鲁诺的火刑柴堆至今还没有熄灭,人们在烈士的火刑堆旁争吵、大笑,觉得合乎道德,人性事物已经消逝,而死去的人已为世界所忘却。米沃什将华沙比作一个新康波·代·菲奥里广场,他写道:“许多岁月过去了,/在一个新康波·代·菲奥里/愤怒点燃了一个诗人的话。”
愤怒将命令诗人说出怎样的话呢?当然是说出真话——“在一间屋子里,人们一致保持一种共谋的沉默,说一句真话就像一声霹雳。天哪,要把真话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痒,变成一种不让人想别的什么的强迫观念。”(《授奖演说》)也要说出光——“就是不同意无意义,要寻求意义……”(《作家的自白》)
然而,从更本质上来说,世界虽然荒诞,却既不好也不坏,“大地,既不慈悲也不邪恶,既不美丽也不残暴,天真地坚持向痛苦和欲望开放”(《没有名字的城》)。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米沃什认为想象力必须容纳痛苦、贬值、暴力、贫困、信仰和道德的滑坡,诗人应该有更大的承担。如果我们多愁善感,同时又无能为力,那么我们会生活在一种绝望的夸张状态中。
愤怒的诗人不愿像荒诞派那样去扮鬼脸,他需要的是健康、秩序、古典的纯朴,他要做一个肯定者:一边说“不”,一边将“是”扶起。
愤怒的诗人走向了怜悯与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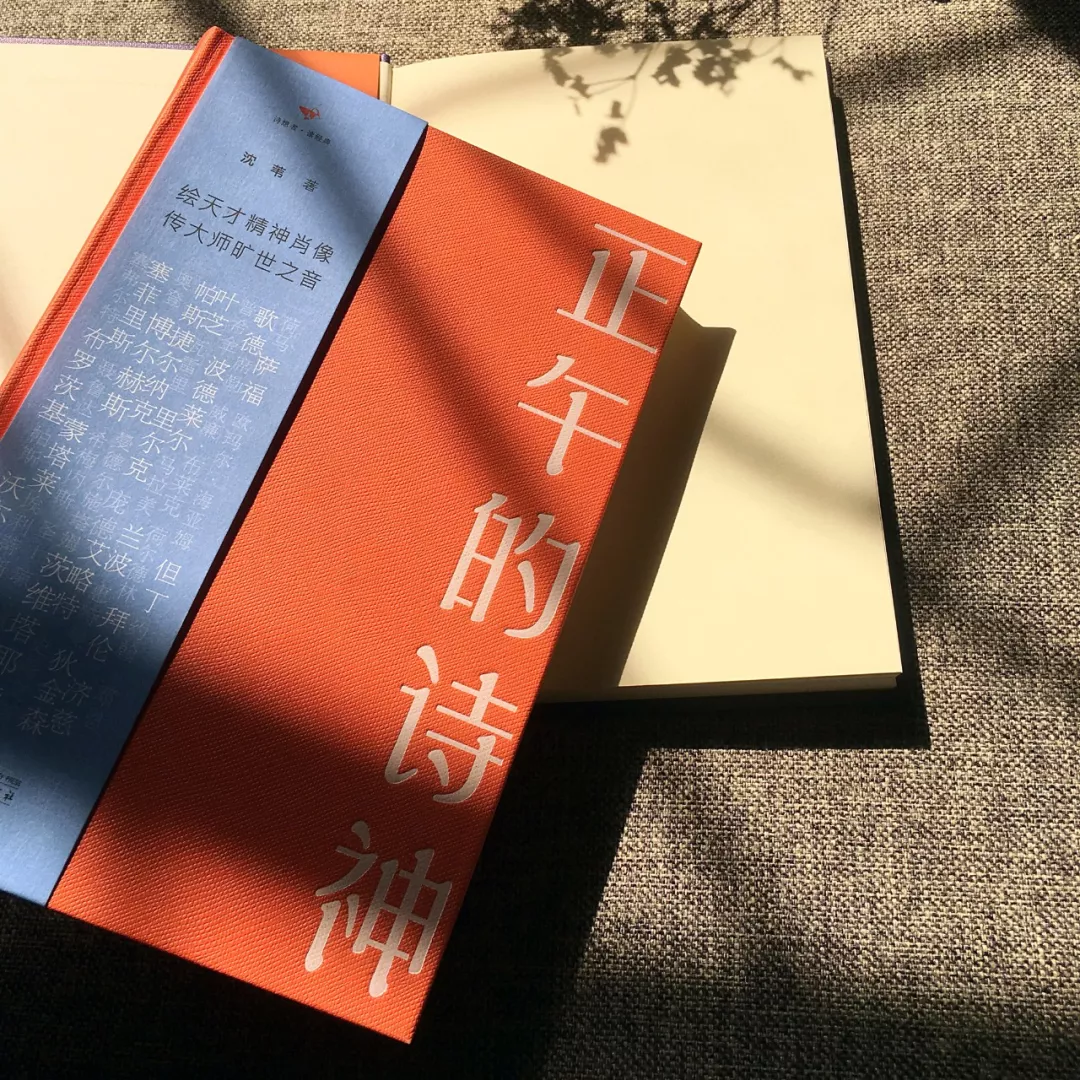
1987年,米沃什在接受法国《文学杂志》的提问“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时回答说:“在我的作品中,我首先试图叙述引起我怜悯的事物的重要性;当然,这是从尊敬、虔诚、热爱的意义上谈论怜悯的。我非常看重这一点。比如说,确定一片面包、一把刀子的存在同样是一种怜悯。我所谈论的怜悯,是对于存在的事物的怜悯。”
关于怜悯,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也有过精彩的论述:“世上的一切,包括人、动物和石头,都应该得到同情,‘犯人值得怜悯,铁门更值得怜悯’(雨果)。要为恶心的癞蛤蟆,为肮脏的蜘蛛,为蠕动的虫子而哭泣。他们都在向上帝赎罪,最终也都会被上帝宽恕。”
怜悯之心使米沃什既没有像金斯伯格一样嚎叫,又没有像蒙塔莱那样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更没有滑入虚无、荒诞和梦魇的泥淖。这并不意味着诗人的妥协,不再发出愤怒和抗议之声,而是——声音中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对“现实”表示尊重,将这个充满恐惧和危险的时代视作人类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之前经历阵痛的一个必要阶段,追寻意义和真理,以明朗而克制的心态迎向可能的曙光。这就是米沃什的“希望诗学”,与赫伯特的“反讽诗学”构成了波兰当代诗歌的两大维度。
经由怜悯,诗人要在世界的灾祸中建立“一点点秩序和美”,要活过多年到达“移动的边境”。在那儿,色彩和声音成为真实,世界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同时,一个新的、勇猛的种族必须诞生,米沃什请求一把火剑为我们劈开大地。
当这位忧愤的诗人掂量着笔,密谋复仇的时候,时常也会被世界明朗的一面打动,心怀感激——
当月亮升起来,穿花衣的妇女漫步时
我被她们的眼睛、睫毛和世界的整个安排打动了。
依我看来,从这样一种强烈的相互吸引里
终归会流出最后的真理。
——《当月亮》
米沃什十分喜欢19世纪初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凝望着花朵。”
他正是这样一位在地狱凝望花朵的诗人。
摘自沈苇《正午的诗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