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的智性抒情诗 | 臧棣诗系问世(赠书)
中国诗歌网 2019-08-15
▲
关注
中国诗歌网
,让诗歌点亮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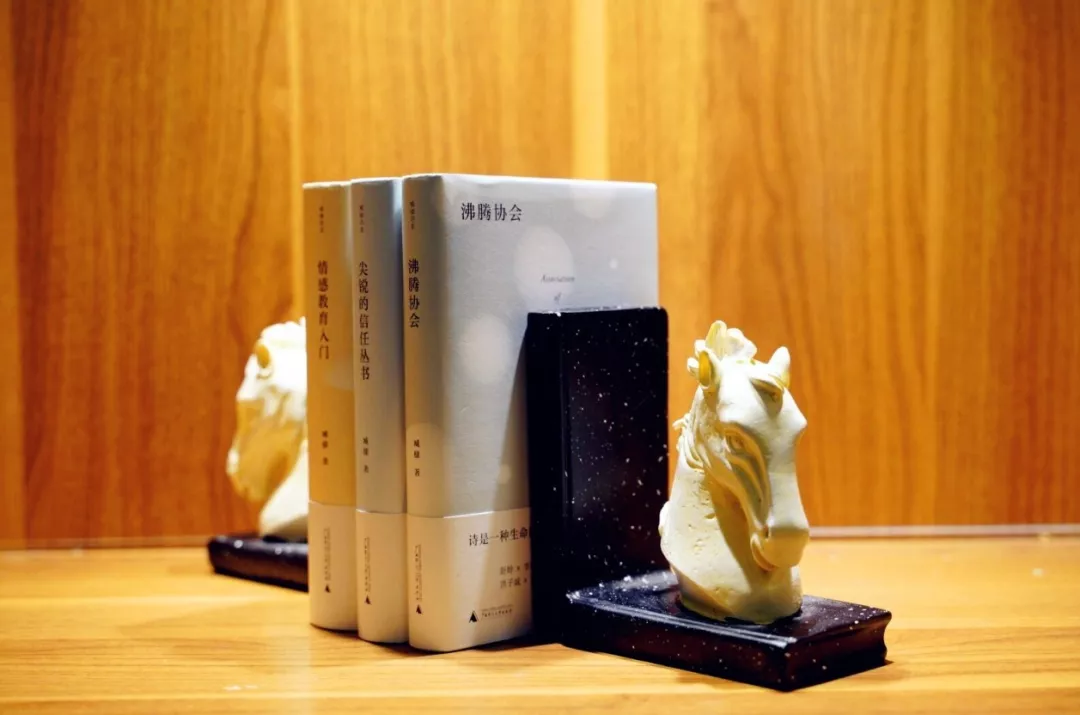
诗的最根本的力量在于它能激发生命的觉醒
诗开启的是一个人对生命自身的美妙的体验
近年来,臧棣写了一系列协会诗、丛书诗和入门诗
他运用想象力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勘测
或许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知识
帮助我们重新感受世界
这系列诗歌坚持了诗人一贯的诗学主张:
对语言的追寻以及对认识的追寻
同时也反映出臧棣近年来诗歌创作的新变:
一种具有浓郁后现代特征的、互文性的探索,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自然书写的再造与化用,由此形成一种辨识度极高的“咏物的智性抒情诗”风格,对现代汉语诗歌文体建构做出了有益的开拓。

01
协会诗
◣
绝对审美协会
我蹲下来,我在等细得像鞋带的蚯蚓说话。 我的四周是没膝高的油菜地,自行车放倒一边,我像是已无路可迷。 成年后,每个人都声言他们没见过会说话的蚯蚓。 这世界已足够小了,但我们还是找不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蚯蚓先生,你知道你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吗?你身上的线 看上去太短小,就像是主动邀请我们把你当成一个诱饵。 而你的身材细长,很适合在地下跳探戈。这也是我尊敬你的地方。 我为你准备的耐心甚至超过了我为我的生活准备的耐心。 我不介意你的性别,假如我邀请你做我的诗神,你会在意这首诗里干净得没有一点土吗? 2005年8月
◣
喜剧演员协会
我带着我的猴子散步,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听任它选择它想走的路。很奇怪,它喜欢向西延伸的路——它身体里像是装有一个探测香蕉和水蜜桃的定位系统。 我几乎总是跟在它的身后。它对我们的世界还很不习惯。它经常会把我当成树干搂得紧紧的。它很容易受惊,它的两只眼睛频繁地眨动,像滚落在地上的水银珠。 我当然是它的主人,这一点几乎不用证明。而一旦走出屋门,我很快就会感到一丝难堪——很多时候,我更像是它的跟班。在散步途中,但凡有一点自然的迹象,它就会挣脱我,像一团撒出去的灰。 我并不嫉妒它比我更善于和自然打交道。它很敏感,就仿佛我和你的生活确实与它有关。它会做很多可笑的事。有一次,它竟然把我给你写的信翻出来,放在炖锅里。 那似乎是它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给它取名字,颇费了我一番工夫。它看不上以往那些为猴子准备的名字。它就像一个公诉人盯着我,直到最后我给他起名叫天鹅,他才回应我。所以,也不妨说,每天,我是带着我的天鹅在散步。 2005年8月
02
丛书诗
◣
落日丛书
又红又大,它比从前更想做你在树上的邻居。 凭着这妥协的美,它几乎做到了,就好像这树枝正从宇宙深处伸来。 它把金色翅膀借给了你,以此表明它不会再对别的凤凰感兴趣。 它只想熔尽它身上的金子,赶在黑暗伸出大舌头之前。 凭着这最后的浑圆,这意味深长的禁果,熔掉全部的金子,然后它融入我们身上的黑暗。 2012年
◣
新观察丛书
从舷窗上俯瞰下去,灯火像发亮的海藻漂浮在黑暗的潮水中。广大的灯火正慢慢加热你以为再也看不到的东西。巨变难移沧桑。心灵的代价怎么就不朴素了呢。本性从来就可耻,但是天性就不一样了,可以琢磨的地方有很多。这里拧拧,那里还应再紧紧。精神的螺丝钉可是比精神更幽默,你最好能早点波及这一点。没错,久违的温暖也许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而人间的黑暗就在这样的高度之下。 2007年
◣
走出洞穴丛书
你走出洞穴。半小时前,在幽暗中你有着一头成年棕熊的体重。每个脚印,都是对大地的无知的肯定。十分钟后,一个极限在洞口欢迎你。阳光打在你的脸上,你的毛发像斑斓的呼吸。你蜕变成一只崭新的豹子。变形记很尽职,将你还原成一道野性的彩虹。世界隐藏在肉中,于是你奔跑,冲向一只小羚羊。你扑上去狠狠咬住它的喉咙,将它掀翻在草甸上。它的喉咙里回响着真理的哨音。你不再需要洞穴。你需要大地的启示。我觉得你的路线选得很有意思——沿着你留下的踪迹,我也尝试着走出我们的洞穴。我用羚羊的骨头炖了一锅汤。放入沙枣后,果然很滋补。不过,我的进展很慢,到目前为止,只能说,与迷宫打了一个平手。 2011年
◣
挖掘丛书
—— 题记:雅安,一个巨大的倾听 第一锹,像我挖你一样,挖我。第二锹,也是第十万锹,清晰得像 请把我从瓦砾中挖走。第三锹,请把我从语言中挖走。 再没有比语言更深的坑中 才会有一次最深的飞翔。第四锹,请把我从新闻中挖走—— 我不是你的兄弟,也不是你的姐妹, 但是,挖,会改变我们。第五锹,比第六锹更像一个闷雷, 请把我从真相中挖走。第七锹,咔嚓,短促而精准, 巨大的悲痛中一个回音的切片。第八锹,不是很深,却结束了每个人 都曾有过的一个巨大的渺小。第九锹,事情始于挖,但不会终于挖。第十锹,请继续挖我身上的你, 直到挖出你身上的我们—— 一个巨大的倾听始终会在那里。 2008年5月
03
入门诗
◣
菊芋入门
美好的一天,无需借助喜鹊的翅膀,仅凭你的豹子胆就能将它从掀翻的地狱基座下狠狠抽出,并直接将时间的蔚蓝口型对得像人生的暗号一样充满漂亮的刚毛。为它驻足不如将没有打完的气都用在鼓吹它的花瓣像细长的舌头。或者与其膜拜它的美丽一点也不羞涩,不如用它小小的盘花减去叔本华的烦恼:这生命的加法就像天真的积木,令流逝的时光紧凑于你的确用小塑料桶给我拎过世界上最干净的水。清洗它时,我是你骑在我脖子上尖叫的黑熊,也是你的花心的营养大师;多么奇妙的茎块,将它剁碎后,我能洞见郊区的文火令大米生动到你的胃也是宇宙的胃。假如我绝口不提它也叫鬼子姜,你会同意将它的名次提前到比蝴蝶更化身吗? 2018年10月4日
◣
人在科尔沁草原,或胡枝子入门
十年前,它叫过随军茶;几只滩羊做过示范后,你随即将它的嫩叶放进干燥的口腔中,用舌根翻弄它的苦香。有点冒失,但诸如此类的试探也可能把你从生活的边缘拽回到宇宙的起点。没错,它甚至连替代品都算不上,但它并不担心它的美丽会在你广博的见识中被小小的粗心所吞没。它自信你不同于其他的过客——你会从它的朴素和忍耐中找到别样的线索。四年前,贺兰山下,它也叫过鹿鸡花;不起眼的蜜源植物,它殷勤你在蜜蜂和黑熊之间做过正确的美学选择。如今,辨认的场景换成科尔沁草原,但那秘密的选择还在延续——在朱日和辽阔的黎明中,你为它弯过一次腰;在大青沟清幽的溪流边,你为它弯过两次腰;在双合尔山洒满余晖的半坡,你为它弯过三次腰,在苍狼峰瑰美的黄昏里,你为它弯过四次腰;表面上,它用它的矮小,降低了你的高度;但更有可能,每一次弯下身,都意味着你在它的高度上重新看清了我是谁。 2018年 9月 2日
◣
敬亭山入门
最好的旅行仿佛总和逆水的感觉相关。无形的码头逼真于鸟鸣越来越密集。车门打开时,我们像是从摇晃的船舱里跳出来的。密封的时间刹那间充满了蜜蜂的叮咛。这一跳,一千年的时光制造的隔阂柔软成清晰的鞋印;这一跳,也跳出了人心和诗心,其实从来就差别不大;自然的环抱绝不只是贴切于自然很母亲;一旦进展到两不厌,密林的友谊依然显得很年轻。这一跳,也区分了悠悠和幽幽哪一个更偏方:一旦入眼,任何时候,翠绿都比缥缈更守时。回首很随意,但水面的平静却源于存在的真相从来就不比竹林的倒影更复杂。要么就是,比水更深的生活是对世界的一种误导。拾级而上,凤凰才不悬念呢。因为杜鹃如此醒目,所以我猜想山不在高的本意是:假如从未有过神仙,我们怎么会流出这么多的汗。 ——赠吴少东 2018年9月19日

关于系列诗写作的若干解释
——为什么要写作“协会诗”或“丛书诗

臧 棣
/ 命运的含义 /
协会诗和丛书诗的写作,到今年为止,差不多也写了有十五年。最早开始写协会诗,应是1999年。当时的想法很模糊,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坚持写这么久,写得这么规模庞大。当初,只是想用一种集约式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写作中的片断性。组诗的方式,可以解决某种片断性,但“组诗”在方法上太依赖文学的主题性。所以,我就想到了“系列诗”的概念。这很可能是借鉴了现代绘画的系列性。“系列性”的概念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它可以不要求风格的同一,不挑剔主题的连续,而只在意语言的感受力的内在的关联性。当然,写了这么久,我对协会诗和丛书诗的想法,也在不断深化。我曾做过这样的解释,我偏爱对差异的观察,对世界的细节的捕捉,我认为这种对生活的细节的捕捉和描绘,是我们抵抗意识形态对生活的绑架,以及它对存在的遮蔽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协会”和“丛书”这样指向宏大和同一性的概念,可称得上是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的自我命名的色彩。这里,将世界的细节和宏大的现代性的自我命名强力黏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带有反讽色彩的反差。“协会”和“丛书”在命名方式上都偏向于实体和实物,要么热衷于机构的权威性,要么沉迷于知识的权力感。所以,我故意将它们用在它们通常的对立面上——对那些瞬间的、偶然的、细小的、孤独的,奇异的、纯体验性的事物进行无限的呼唤,意在从细节、差异和尊严这几个角度肯定生存的可能性。而生活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对细节的尊严充满差异的观察和想象之上的。长诗的写作,更依赖于文学传统,以及孕育在这文学传统中的诗歌文化。从汉诗的传统看,我们没有写长诗的传统。这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语言上,汉语在古诗的范式里,组织起来的语言呼应——对偶与平仄,不太能容忍太长的语言结构。或者说,在太长的语言结构中,基于汉字本身之美的语言对应,就没有施展出来。这样,转入到风格层面,古诗的语言推重的是记忆与情景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依赖词语的延展,而是强调语言的凝缩。这些,都不利于长诗的写作。换句话说,古典诗学的结构观不支持长诗的写作。更诡异的,古代汉语的语言质感,以及从这种语言质感中酝酿出来的诗歌文化,也天然地排斥长诗的写作。我们的汉语在语言质感上对诗句的长度有着苛刻的要求,这确实令我困惑。但也必须意识到,这种要求是基于古诗的实践,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新诗的状况。让我困惑的还有一点:即古诗的语言在结构上对短小体式的偏爱、对长诗体式的抵触,很可能反映出了汉语独有的语言秘密。不过,即便如此,我依然反对我们过度地僵死地拘泥于这个秘密。我依然相信,汉语诗歌的出路在于积极强化和信任语言的延展性。第二,在诗学观念上,我们的传统审美推重诗的境界。但在古典的汉语实践中,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假如在审美观念上,推重境界,那么,诗就写不长,也没法写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赵野讲的是对的。第三,我们的汉诗传统,在世界观上,喜欢把语言道德化。比如庄子讲“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已埋下将讲语言的主体心智化的伏笔,这或多或少会助长了将语言工具化的倾向。到了唐宋以后,比如司空图主张诗贵“性情”,这实际上在诗的观念上强化了语言人格化。这样,在崇尚心器的诗歌传统里,古人虽然也会提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总体而言,和心器之高贵相比,语言便显得外在而次要了。因为按境界的要求,语言属于被遗忘的对象。这种语言观,肯定不鼓励写长诗。回到当代诗的实践,我觉得,写不写长诗,没必要太拘泥传统的尺度。说到底,这也许和个人的写作意志有关,和个人的语言运气有关。所以,不妨率性一点,感觉需要写长诗了,就写吧。
/ 重新认识诗的即兴性 /
一开始时,我也不甚明确在斟酌一首诗的题目时,我为什么会对“协会”这个词忽然产生了类似着魔的兴致。一种极其顽固的仿佛是出于抒写本身的乐趣。协会,这个词,在当代的文化情境中,有非常特殊的含义。比如,对个人而言,它是一个单位,是一个很制度化的机构。我们本来觉得协会是一种非官方的组织,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但令人吃惊的是,现实生活的“协会”,往往带有很深的衙门的印记。事实上也是如此。按现代文化的逻辑,协会本身其实带有很浓厚的威权色彩的专业机构。另一些,又远离生活体验,太专业。比如,天体物理学协会,闻一多协会,又仿佛有很深奥的门槛,一般人不得入内。但是,很奇怪,在诗歌中成立的协会,却是一个充满悖论性的组织。我开始写“协会诗”时,只是觉得感到被某种新的东西所吸引。比如,在人和世界的交往中,有很多无名的,无法被规训的,偶然的印迹和情境,它们很少得到连续性的展现。基本上出于无名状态。这种无名状态,一方面呈现了生活的私人时刻,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对它们的有意无意的遗忘。某种意义上,我想结束这种情形。至少是在我的人生回忆里,有意识地终止这种对个人生活中的无名状态的漠视。从我自己的体会而言,我觉得这些东西,才真正构成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基础。就经历的最深的含义而言,它们无名地属于我们,我们也真实地属于它们。所以,在我写协会诗时,我的确有意为普通事物立名,将我和它们之间的交往看成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遭际的种种缩影。我想以协会的名义为它们翻身,意在让它们扬眉吐气,每一朵花都可能是协会的会员,每一只狐狸,也可能是协会的会员。某种意义上,这种命名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将个人和世界的相遇中最隐秘的体会组织化,将相关的记忆戏剧化。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虚构的专属机构——不存在协会组织,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协会体制的一种反讽。旧的协会体系已经僵化,那么,不妨让新的协会来参与对我们的生活的构建。所以,假如说协会诗的写作包含有一种文学政治的意图的话,我觉得,我的确在写作意识上,要求这些协会诗,至少在诗歌动机上,应积极地参与改造我们的生存面目。哪怕这样的意图很难实现。哪怕是,一首诗只能做到微小的改变。在写作这些协会诗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愉悦:这些协会诗或许可以让“沉默的大多数”有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家园。也就是说,协会是一个家的概念,或者一个新的故乡的概念。比如,在《石榴协会》里,通过对人与石榴之间的关系的编织与揭示,我们或许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些美丽的植物的认识。更进一步的,甚至有可能改变我们对部分自然存在的认知。语言是我们的家园,而我想做得更具体一点,我想让我擅自成立这些众多的诗歌协会,为我们身边的普通事物找到它们自身的归属。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存在也依赖这样的归属感。从家园到协会,对我来说,也意味着一种对事物的想象方式的变化。家园,或故乡,包含了强烈的空间想象。“家园”或“故乡”,也是这些协会在形象上的原型。这样,在我的意识中,协会诗中呈现的“协会”,不仅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且也容纳了事物之间诸多隐秘而又有趣的联系。从根本上说,这些“协会”也许意味着我对我们如何度过此生的一种积极的想象,或者说私人的建议。说到诗学上的意图,我确实这样想,假如我们认同诗的公共性,那么,依据我们对生存的体验,对诗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私人的建议”,恰恰是诗最应该做的事情。冠名“丛书”的一个初衷是,每首诗歌要处理的一个题材,但就文学的意图而言,其实用一首诗根本写不完一首诗的内容。这似乎是诗歌写作中一个古老的难题。再小的题材,哪怕是写一只萤火虫,全世界有那么多诗人写,这就说明,一个题材和人的意识之间的关联是无限的。总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处理方式。一个题材背后所包含的意图,或意义,实际上是一首诗在体式上没法处理完的。我的“丛书诗”,有些是对非常具体的事物的命名。在这背后,包含着我的一个想法:“丛书”是很重的东西,大部头的,体系性的,预设性,有很强的规划性。而我们对待细小的事物时,恰恰要放下点身段来;这意味着,诗人可以用体系性的东西,很重的东西,去关注卑微事物所处的境况。不要以为那种很细小的东西,很卑微的东西,就跟“丛书”这种宏大的格局不匹配。一旦放下姿态,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以前都没有细心地去关怀过。所以,要说“丛书”有一个诗歌的含义的话,那就是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对我们的人生境况。
/ 命名的乐趣 /
一开始也没有特别的想法。写着写着,慢慢就形成了强大的冲动。这种冲动又在写作中形成了内资的惯性。总体性的考虑是在写了两三年之后,才开始酝酿形成的。但我又有意识地抵抗体系性的东西。开始时,只是想发明一种我称之为系列诗的东西,来缓解长诗写作对我的诱惑。我们这代人写诗,信奉的是现代诗不能超过60行。作为诗人,有本事的话,就在60行内解决诗的战斗。按年轻时的理解,长诗写作脱胎于史诗,而史诗写作又布满神话写作的阴影,根本就不符合现代的认识。而且,现代生活的节奏飞快,除了特别有闲的人,谁还有精力有耐心去读长诗。更深层的审美疑惑是,我觉得,长诗的认知冲动已无法跟现代小说竞争。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过类似的自述,和《日瓦戈医生》相比,他的那些抒情诗缺乏分量。这里面,还有一个新诗史的插曲。
新诗史上,曾有过一种论调,认为我们的抒情性和西方的史诗比,缺少一种文学上的伟大。当然,现在这样的比较已是笑话。但从视觉上讲,金字塔和坟堆相比,哪个更有视觉冲击力还是会经常造成某种困惑。长诗和短诗的争论,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质疑:一首短诗可能很美妙,妙到无可言说,但,妙还是一个瞬间的悟性认知。在很多方面,它可能无法与长诗完成的认知抗衡。所以,长诗完成的是对世界的复杂认知,它展现的审美空间不仅深邃,而且具有规模,它孕育的心理能量非常充沛,它包含的生命视野也非常深广,无形中会形成一种魅力,带给人一种审美敬畏。所以,1990年代中期,我一边写长诗,一边又抵抗这个东西。诗歌史的惯性是,一个诗人要想在其中立足,必须写出有分量的长诗。我们可以反思,这是一种很反动的标准。但它仍会不时冒出来,诱惑我们。所以,尽管信赖短诗,但潜意识里,我也渴望写长诗。传统意义上长诗,很难吸引我。所以,我想用系列诗来取代长诗的写作。我相信,系列诗,可以形成一种独特的类型长度,从而形成足够的总体意义上的风格力量。
中国的抒情诗传统非常伟大。但也自身的问题。首先是诗歌语言的问题。传统上,中国诗歌语言强调对偶,平仄呼应,加上汉字本身的原因,它的形式感偏于短制,阉割了写长诗的可能性。我们古代的诗歌文化,总体说来,不支撑长诗的写作。像白居易的《长恨歌》那种长度,已经是罕见的例外。古典诗学的核心观念是,得意忘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写得太长,在审美上,就是一种忌讳。我有一个观点,按古体和汉语的文字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诗,除非特例,超过一定的行数的话,会在视觉上造成一种疲劳。同时,也会在阅读期待上引起厌烦,甚至是嫌恶。新诗的出现,以解放语言为名,释放了汉语的可能性。在体例和语感上,解决了长诗写作的形式前提。新诗历史上,写作长诗构成一种暧昧的文学情结。我也有这个情结。但另一方面,我又想破除这个情结。90年代,我也写了几首长诗。但都不太满意。1999年开始写协会诗。丛书诗的写作稍晚几年。我觉得找到了一种新的写长诗的路径。
对我来说,像协会诗这样的系列,就是长诗的一种变体。或者说,一种变奏。系列诗,在结构,连续性,主题方面,不像传统的长诗那样依赖同一性,和长时间的构思。系列诗,在语言组织上,在诗的体制上,不需要严密的结构安排,只要诗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对世界的观察,具有一致的出发点,比如审美的好奇,就可以了。诗人可以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态度,来挖掘世界的秘密,从而展现犀利的审美认知。对世界的态度,在系列诗的写作起着主线的作用。诗的写作中,揭示经验固然重要,但发明看待世界的态度,也很根本。有了诗歌的态度,我们就有机会锤炼出一种诗歌的方法。这时候,再去看待我们置身的世界,眼光和感受也会大有不同。另外,系列诗不同于长诗之处,还在于它释放了更多的写作的即兴性。我可以写得既放松,又在放松中保持一种强度。
写协会诗或丛书诗,还有一个感受也很深。诗的写作可以彻底地颠覆小大之辩。正如布莱克说的,一粒沙子里有一个宇宙。在诗歌中,看起来很小的素材,只要细心洞察,都会触及很大的主题。哪怕是一个杯子,一片树叶,一只蚂蚁,都能协调我们对存在的根本观感。我将自己的诗命名为“丛书”时,确实有一个自觉的意图:一首诗就是一本书。而一首诗触及的内容的深邃,即使动用“丛书”的规模,也无法将它的含义穷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一首诗加上“丛书”这一后缀的缘由。一首诗触及的题材和主题,今天写,是这个样子,明天写又会是那个样子。这也反映出我对诗的主题的开放式的理解。一首诗触及的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主题,而是复合的主题。丛书的命名,也包含这样的想法:一首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生成性的,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正如诗的素材和诗人的眼光之间的关系的不断更新。从意图上讲,丛书的意思就是,一首诗,是写不完的。每一首诗,都是处于一种丛书状态。
诗的写作中,如何命名,如何给游弋的素材起个好名字,激活感受和经验之间的关联,是件很神秘的事情。
我写协会诗时,还有过一个想法,就是用貌似官方的、体制化的、正式的、权力化的“协会”,为我们的存在中那些细小的、瞬间的、偶然的、易逝的、平凡的、备受忽视的、频繁遭受剥夺的事物,伸张它们的生命主权。我写的协会诗都很小,有些可能是一个词组,当时内心的一个句子,我把它叫协会。几乎每首协会诗,都闪烁着一个隐含的抵抗线索。我经常感到,现代世界有很多偏见,这些偏见把我们对世界的观感,对存在的体会都固化在一个偏狭的认知范式里。而我想用协会诗触及更丰富的诗意态度,从而突破那些偏见。现代体制中,作为一个机构,协会展现了科学理性的权力面孔,专业,高级,行会性,高高在上,外人难以涉足。比如现代物理学协会,天文学家协会。它们预示了一种垄断的权力。所以,我有意反其道而行。我去命名蚂蚁协会,蝴蝶协会,晚霞协会,微光协会,有意用“协会”这一高度权力化的命名,来彰显我们的生存境遇里那些微弱的、不断被忽略的审美领域。通过这样的命名,形成一种新的目光,让我们尽量慢下来,以便重新打量生存的细节。


臧棣, 1964年4月生在北京。1997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性诗集有《燕园纪事》(1998),),《宇宙是扁的》(2008)、《小挽歌丛书》(2012),《骑手和豆浆》(2015),《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2017),《情感教育入门》(2019),《沸腾协会》(2019),《尖锐的信任丛书》(2019)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年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2005),“1979-2005中国十大先锋诗人”(2006),“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2007)。《星星》2015年度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2017)。2016年5月应邀参加德国不来梅诗歌节。2017年10月应邀参加美国普林斯顿诗歌节。
推荐阅读

作者:臧棣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本套诗集包含《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情感教育入门》,严选自臧棣在2000年至2018年间写作的系列诗。
“
一位卓越的诗人,臧棣的作品展现了对诗歌本质的独特理解,示范了想象力和生命、道德、文明根本的相关性。
——奚密(美国加州大学杰出教授)
臧棣的诗歌写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将智性的伦理视野与具有挑战性的幽默感结合起来,不断探索自我及其存在的深度,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柯雷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臧棣的诗意锋利而开阔,辞语精粹且优雅,其神髓兼得先锋与学院之妙……最终,一种诗的高度自觉和成熟,赢得了当之无愧的世界性意义。
——杨炼(诗人)
臧棣的汉语诗歌写作在意识、技艺、主题和题材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为当代诗歌的更新贡献了源源不尽的活水……堪称当代诗歌的一个奇观。
——西渡(诗人,清华大学教授)
用乔装成体系化的知识,书写其对存在的情感与觉识,臧棣的驳杂与精纯、设计感与随意性都趋于两极,为当代中国诗学确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范型。
——江弱水(浙江大学教授)
臧棣的写作一直是当代诗歌在创新维度上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标识之一。
—— 唐晓渡(批评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