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诗人
冯川 译 燃读 2019-0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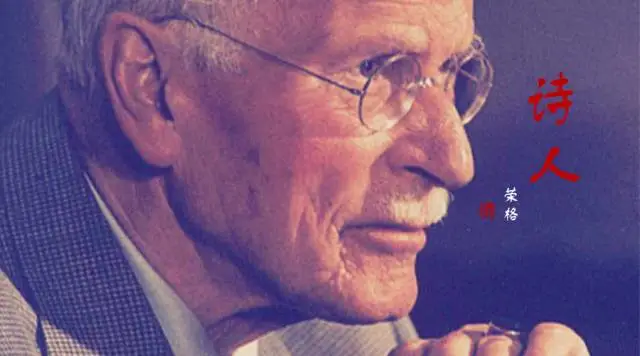
诗人
文|荣格
译|冯川
如同意志自由一样,创造也包含着一种奥秘。心理学家可以描述这两种表现的过程,却不能解答它们提出的哲学问题。富于创造性的人是一个谜,我们尽管力图予以解答,到头来却总是徒劳无益。尽管如此,这一事实却不能阻止现代心理学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艺术家及其艺术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在他由艺术家的个人经历推论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他已找到一把开启神秘的钥匙。不错,在这一方向上的确存在着某些可能性。因为可以想象, 艺术作品也正如神经症一样,可以追溯到精神生活被我们称之为情结的那些环节。神经症在精神领域里存在着发病的根源,它们来源于种种情绪状态以及真实的和想象的童年经历,这是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他的某些追随者如兰克和斯泰克尔,担负起了有关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无可否认,诗人的精神气质渗透了他的全部作品。即使说个人因素极大地影响着诗人对素材的选择和运用,那也并没有什么新意。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学派证明了这种影响是何等深远,它的表现形式又是何等出奇,这终究还是值得称道的。
弗洛伊德将神经症视为直接满足方式的一种替代。他因此认为神经症是某种不正常的东西:一种错误,躲闪、借口或自愿的盲目。对他说来,神经症本质上是一种不应该发生的缺陷。由于神经症显然是一种精神失调,而且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也就很少有人敢于为它说几句好话。而当艺术作品被看作某种可以从诗人的精神压抑角度进行分析的东西的时候,它也就同神经症有了一种可疑的相似。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为自己找到了更好的同伴,因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把宗教和哲学也看作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承认这种方法仅仅解释了一部艺术作品舍弃了它们就不可想象的那些个人因素,那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但如果声称这种分析解释了艺术作品本身,那就必须加以绝对否定。渗透到艺术作品中的个人癖性,并不能说明艺术的本质;事实上,作品中个人的东西越多,也就越不成其为艺术。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个人色彩在艺术中是一种局限甚至是一种罪孽。仅仅属于或主要属于个人的“艺术”,的确只应该被当作神经症看待。弗洛伊德学派认为:艺术家无一例外地都是自恋倾向者,也就是说是一些发育不全的、具有童年和自恋品质的人。这一观点或许有几分道理。然而也只有当涉及作为个人的艺术家时,这种说法才能成立;对于作为艺术家的个人,这种说法则毫不相干。在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中,他既不自恋,也不恋他,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爱欲。他是客观的、无个性的(甚至是非人的),因为作为艺术家,他就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这个个人。
每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人,都是两种或多种矛两倾向的统一体。一方面,他是一个过着个人生活的人类成员,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无个性的创作过程。因此作为一个人,他可能是健全的或病态的,我们必须注意他的心理结构,以便发现其人格的决定因素。但是我们只有通过注意他的创作成就,才能理解他的艺术才能。如果我们试图依据个人因素来解释一个英国绅士,一个普鲁士官员或一个红衣主教的生活模式,我们必然会犯一种可悲的错误。绅士、官员和教士都是作为无个性的角色进行活动的,他们的心理结构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客观性,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家并不行使官吏的职能——以这种极端的对立为例更便于说明真相,然而他在某一方面又类似于我所列举的这几种类型。因为某种特殊的艺术气质负载着一种对于个人的、集体精神生活的重荷。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成为它的工具。艺术家不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找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实现艺术目的的人。他作为个人可能有喜怒哀乐、个人意志和个人目的,然而作为艺术家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即“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类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为了行使这一艰难的使命,他有时牺牲个人幸福,牺牲普通人认为使生活值得一过的一切事物。
既然如此,艺术家成为心理学家运用分析法加以研究的有趣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艺术家的生活不可能不充满矛盾冲突,因为他身上有两种力量在相互斗争:一方面是普通人对于幸福、满足和安定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发展到践踏一切个人欲望的创作激情。艺术家的生活即便不说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是高度不幸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幸的天命,而是因为他们在个人生活方面的低能。一个人必须为创作激情的神圣天赋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规律几乎很少有任何例外。这就好象我们每个人生来就被赋予一定的心理能量,而我们心理结构中最强大的势力将会夺取甚至垄断这种能量,使它不可能再去生产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创造力象这样汲取一个人的全部冲动,以致一个人的自我为了维持生命的火花不被全部耗尽,就不得不形成各种各样的不良品行——残忍、自私和虚荣(即所谓“自恋”)——甚至于各种罪恶。艺术家的自恋,类似于私生和缺少爱抚的孩子一样,这些孩子从年幼娇弱的年代起就必须保护自己,免遭那些对他们毫无爱恋的人的作践蹂躏;他们因此而发展出各种不良品行,后来则保持一种不可克服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者终生幼稚无能,或者肆无忌惮地冒犯道德准则和法规。我们怎能怀疑,可以用来解释说明艺术家的,不是他个人生活中的冲突和缺陷,而只能是他的艺术呢?个人生活中的冲突和缺陷,不过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结局而已,事实则是:他是一个艺术家,也就是说,从出生那一天起,他就被召唤着去完成一种较之普通人更其伟大的使命。特殊的才能需要在特殊的方向上耗费巨大精力,其结果也就是生命在另一方面的相应枯竭。
诗人是否意识到他的作品与他一起出生,生长和成熟,他是否以为他的作品是他通过构思从虚无乌有中创造出来的,这无关紧要。他的看法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作品超越了他,就象孩子超越了母亲一样。创作过程具有女性的特征,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来源于无意识深处,或者不如说来源于母性的王国。每当创造力占据优势,人的生命就受无意识的统治和影响而违背主观愿望,意识到的自我就被一股内心的潜流所席卷,成为正在发生的心理事件的束手无策的旁观者。创作过程中的活动于是成为诗人的命运并决定其精神的发展。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浮士德》除了作为一种象征,还能是什么呢?我所谓象征,不是一种寓言,其所指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是一种表现。它所代表的东西尚未认识清楚,然而却根深蒂固地存在。这里有某种东西,它活在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而歌德则促成了它的诞生。我们除了把他们视力写作了《浮士德》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德国人外,还能把他们想成是什么人呢?这两部作品都接触到某种在德国人灵魂中发出回响的东西,也就是一度被雅可布•布尔克哈特称为“原始意象”的人类导师和医生的形象。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蛰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一旦时代发生动乱,人类社会陷入严重的谬误,它就被重新唤醒。每当人们误入歧途,他们总感到需要一个向导、导师甚至医生。这类原型意象举不胜举,然而除非由于普遍观念的动摇,它们绝不可能被召唤出来,显现在人们的梦和艺术作品中。每当意识生活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某种虚伪倾向的时候,它们就被激活——甚至不妨说是“本能地”被激活——并显现于人们的梦境和艺术家先知者们的幻觉中,这样也就恢复了这一时代的心理平衡。
诗人的作品以这种方式,迎合了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精神需要。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就比他个人的命运更具有意义,而不管他本人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既然诗人本质上是他的作品的工具,他也就不能不从属于他的作品,而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期待他对我们作出解释。诗人通过赋予作品以形式,已经最大限度地发挥厂他个人的才能,他必须把解释留给别人,留给未来。伟大的艺术作品就象梦一样: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明明白白,然而它却从来不对自己作出解释,从来都是模糊暖昧的。梦绝不会对我们说:“你应该’,或“这就是真理”。它就象大自然赋予植物以生命一样地表现出一种意象,我们对此只能自己作出结论。如果一个人做了恶梦,那就意味着他不是过份恐惧,就是太无恐惧;如果一个人梦见了智慧的长者,那就可能说明他需要一个导师来指点,或者他自己太好为人师了。两种意义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表现为同一事物,就象我们欣赏艺术作品并真正领会到艺术家本人的感受时那样。要把握艺术作品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让它象感染艺术家本人那样地感染我们。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理解艺术家的体验的性质。我们看到:他从集体精神中召唤出治疗和拯救的力量,这种集体精神隐藏在处于孤独和痛苦的谬误中的意识之下;我们看到:他深入到那个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生命模式中,这种生命模式赋予人类生存以共同的节律,保证了个人能够将其感情和努力传达给整个人类。
艺术创作和艺术效用的奥秘,只有回归到“神秘共享”的状态中才能发现,即回归到经验的这样一种高度,在这一高度上,人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整体生活着,个人的祸福无关紧要,只有整个人类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客观的和非个人性质的,但同时又丝毫不影响它深深地感染我们每一个人。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人的个人生活对于他的艺术是非本质的,它至多只是帮助或阻碍他的艺术使命而已。艺术家在个人生活中也许是市侩、循规蹈矩的公民、精神病患者、傻瓜或罪犯。他的个人生活可能索然无味或十分有趣,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作为诗人的他。
(译自《荣格文集》英文版15,苏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