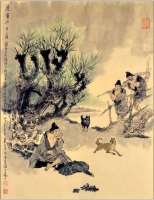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赏析】 中宗神龙二年(706),宋之问奉恩旨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北归,经过汉江(也就是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了这首诗。宋之问的家在巩县,汉水离巩县,虽然还有不少路,但较之岭外的泷州,毕竟要近得多,所以诗里说“近乡”。诗的语言,极为浅近通俗,但乍一读,仍不免会有疑惑。一个离开家乡已逾半年的游子,能踏上归途,自当心情欢悦,而且这种欣喜之情,也会随着家乡的越来越近而越来越强烈。宋之问却偏说“近乡情更怯”,乃至不敢向碰到的人询问家人的消息,这岂非有点不合情理?
要解开这一疑团,必须重视诗的前两句,它们提供了必要的线索。诗人在到达贬所后,即与家人断绝了联系,且已持续了半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心境如何呢?诗中似未明言,其实不然。“近乡情更怯”,说明诗人早巳“情怯”。对家中情况的一无所知,使诗人的思虑中,增加了不安和疑惧:亲人们是否遭遇到什么不幸呢?空间的阻隔,时间的推移,使这种不安和疑惧,日趋沉重地郁结在诗人的心头。渡过汉水,离乡日近,但心中的恐惧也越来越沉重,因为不祥的猜测,有可能即将被证实。“不敢问”,不是“不想问”,诗人也想能尽早知道家人的消息。不过,假如能听到好消息,固然会无限欣喜,但万一相反呢?那么,期待着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岂不将被这无情的消息一下子所粉碎?与其如此,不如听任这模糊不明再持续下去,因为毕竟还存在着一切皆好的希望啊。这种想问而又不敢问的矛盾心理,反映了诗人焦虑痛苦的心情。大诗人杜甫在战乱中与亲人分离,又音信不通,在《述怀》一诗中,写了这样几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尽管诗人的身份不同,造成音书惭绝的原因不同,但矛盾痛苦的心情却完全相同。当然,这种独特的生活体验,不会人人都有;但这种特殊微妙的心理状态。却是大家都能理解,真实可信的。看似不合情理,其实只是情况特殊而已。
以上这一思索,理解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对这首诗巧妙的抒情艺术,有更深刻的体会。诗人在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鉴赏]
这是宋之问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的一首诗。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作者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作者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宋之问的家乡一说在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一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离诗中的“汉江”都比较远。所谓“近乡”,只是从心理习惯而言,正象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过了黄河就感到“近乡”一样(宋之问这次也并未逃归家乡,而是匿居洛阳)。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作者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作者贬居岭外,又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向两极发展,形成既切盼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由贬所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透过“情更怯”与“不敢问”,读者可以强烈感触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抒写,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分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人们爱拿杜甫《述怀》中的诗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和这首诗作类比,这正说明性质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时可以用类似方式来表现,而它们所概括的客观生活内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刘学锴)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Here turn back, this very month....
Shall my own southward journey
Ever be retraced, I wonder?
...The river is pausing at ebb-tide,
And the woods are thick with clinging mist –
But tomorrow morning, over the mountain,
Dawn will be white with the plum-trees of home.
【白话文】 阴历十月的时候,大雁就开始南飞,据说飞到大庾岭,它们就全部折回。
鸟儿不进,我却行程未止远涉岭南,真不知何日何时,我才能遇赦归来?
潮水退落了,江面静静地泛着涟漪,深山老林昏暗暗,瘴气浓重散不开。
来日我登上高山顶,向北遥望故乡,抑或能看到:那山头上初放的红梅。
【注释】 ①大庾岭:在江西、广东交界处,为五岭之一。北驿:大庾岭北面的驿站。
②殊:还。"我行"句意谓自己要去的贬谪之地还远,所以自己还不能停下。
③瘴:南方湿热天气山林间对人有害的毒气。
④望乡处:远望故乡的地方,指站在大庾岭处。陇头梅:大庾岭地处南方,十月即开梅花。
【赏析】 大庚岭为五岭之一,古人以此为南北分界,有北雁南飞至此不过岭南之传说。诗是作者流放钦州途经大庚岭时所作。 全诗写贬谪岭南的伤感,于旅途中抒发情怀。开头以比兴入手,写望雁思乡,再写岭南境恶,更衬怀乡情切。最后两句由写景转为抒情,暗祈能见到红梅采寄亲眷,以表衷情。 诗旨在写“愁”,却未着“愁”字,情致凄婉,愁绪满怀,以情布景,以景托情,情真意切,柔婉动人。
这是诗人流放时途经大庾岭之作。全诗通过描写途中所见景物,借景抒情,抒发了诗人对官场坎坷的慨叹和思念家乡的感情。诗先写诗人见雁南飞,触景生情,传说中雁南飞至大庾岭而北回,而自己却行程无尽头,不知何日能归。人雁相比,人不如雁,深切表现了诗人忧伤哀怨的复杂的内心感情。后四句写大庾岭黄昏的凄迷景色,江潮初落,水面平静,瘴气缭绕,故乡何在?明晨踏上岭头时,再望一望故乡吧!虽然见不到她的踪影,但岭上盛开的梅花该是可以见到的!悲苦和乡思在此一露无遗。全诗写的是“愁”,却未着一“愁”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愁绪满怀,凄恻缠绵。诗人以情布景,又以景衬情,使情景融合,传情达意,因而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鉴赏]
这是宋之问流放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途经大庾岭时,写在岭北驿的一首五律。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庾,岭上多生梅花,又名梅岭。古人认为此岭是南北的分界线,因有十月北雁南归至此,不再过岭的传说。
本来,在武后、中宗两朝,宋之问颇得宠幸,睿宗执政后,却成了谪罪之人,发配岭南,其心中的痛苦哀伤自是可知。所以当他到达大庾岭北驿时,眼望那苍茫山色、长天雁群,想到明日就要过岭,一岭之隔,与中原便咫尺天涯,顿时迁谪失意的痛苦,怀土思乡的忧伤一起涌上心头。悲切之音脱口而出:“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阳月(即农历十月)雁南飞至此而北回,而我呢,却象“孤雁独南翔”(曹丕《杂诗》),非但不能滞留,还要翻山越岭,到那荒远的瘴疠之乡;群雁北归有定期,而我呢,何时才能重来大庾岭,再返故乡和亲人团聚!由雁而后及人,诗人用的是比兴手法。两两相形,沉郁、幽怨,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蕴其中。这一鲜明对照,把诗人那忧伤、哀怨、思念、向往等等痛苦复杂的内心情感表现得含蓄委婉而又深切感人。
人雁比较以后,五六两句,诗人又点缀了眼前景色:“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黄昏到来了,江潮初落,水面平静得令人寂寞,林间瘴气缭绕,一片迷蒙。这景象又给诗人平添了一段忧伤。因为江潮落去,江水尚有平静的时候,而诗人心潮起伏,却无一刻安宁。丛林迷瞑,瘴气如烟,故乡何在?望眼难寻;前路如何,又难以卜知。失意的痛苦,乡思的烦恼,面对此景就更使他不堪忍受。
恼人的景象,愁杀了这位落魄南去的逐臣,昏暗的境界,又恰似他内心的迷离惝恍。因此,这二句写景接上二句的抒情,转承得实在好,以景衬情,渲染了凄凉孤寂的气氛,烘托出悲苦的心情,使抒情又推进一层,更加深刻细腻,更加强烈具体了。
最后二句,诗人又从写景转为抒情。他在心中暗暗祈愿:“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明晨踏上岭头的时候,再望一望故乡吧!虽然见不到她的踪影,但岭上盛开的梅花该是可以见到的!《荆州记》载,南朝梁时诗人陆凯有这样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显然,诗人暗用了这一典故。虽然家不可归,但他多么希望也能寄一枝梅,安慰家乡的亲人啊!
情致凄婉,绵长不断,诗人怀乡之情已经升发到最高点,然而却收得含吐不露。宋人沈义父说:“以景结情最好”,“含有余不尽之意”。(《乐府指迷》)这一联恰好如此,诗人没有接续上文去写实景,而是拓开一笔,写了想象,虚拟一段情景来关合全诗。这样不但深化了主题,而且情韵醇厚,含悠然不尽之意,令人神驰遐想。
全诗写的是“愁”,却未着一“愁”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愁绪满怀,凄恻缠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艺术魅力呢?因为“善道景者,绝去形容,略加点缀”,“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陆时雍《诗镜总论》)。这首诗正是在道景言情上别具匠心。诗人以情布景,又以景衬情,使情景融合,写出了真实的感受,因而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张秉戍)
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
寒露衰北阜,夕阳破东山。浩歌步榛樾,栖鸟随我还。
暗芳足幽气,惊栖多众音。高兴南山曲,长谣横素琴。
啼鸟弄花疏,游蜂饮香遍。叹息春风起,飘零君不见。
与君共时物,尽此盈樽酒。始愿今不从,春风恋携手。
中有乔松树,使我长叹息。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
尔寻北京路,予卧南山阿。泉晚更幽咽,云秋尚嵯峨。
药栏听蝉噪,书幌见禽过。愁至愿甘寝,其如乡梦何。
山薮半潜匿,苎萝更蒙遮。一行霸句践,再笑倾夫差。
艳色夺人目,斅嚬亦相夸。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
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始觉冶容妄,方悟群心邪。
钦子秉幽意,世人共称嗟。愿言托君怀,倘类蓬生麻。
家住雷门曲,高阁凌飞霞。淋漓翠羽帐,旖旎采云车。
春风艳楚舞,秋月缠胡笳。自昔专娇爱,袭玩唯矜奢。
达本知空寂,弃彼犹泥沙。永割偏执性,自长薰修芽。
携妾不障道,来止妾西家。
此时客精庐,幸蒙真僧顾。深入清净理,妙断往来趣。
意得两契如,言尽共忘喻。观花寂不动,闻鸟悬可悟。
向夕闻天香,淹留不能去。
锦缋织苔藓,丹青画松石。水禽泛容与,岩花飞的砾。
微路从此深,我来限于役。惆怅情未已,群峰暗将夕。
赤岸杂云霞,绿竹缘溪涧。向背群山转,应接良景晏。
沓障连夜猿,平沙覆阳雁。纷吾望阙客,归桡速已惯。
中道方溯洄,迟念自兹撰。赖欣衡阳美,持以蠲忧患。
人远草木秀,山深云景鲜。余负海峤情,自昔微尚然。
弥旷十馀载,今来宛仍前。未窥仙源极,独进野人船。
时攀乳窦憩,屡薄天窗眠。夜弦响松月,朝楫弄苔泉。
因冥象外理,永谢区中缘。碧潭可遗老,丹砂堪学仙。
莫使驰光暮,空令归鹤怜。
晶耀目何在,滢荧心欲无。灵光晏海若,游气耿天吴。
张乐轩皇至,征苗夏禹徂。楚臣悲落叶,尧女泣苍梧。
野积九江润,山通五岳图。风恬鱼自跃,云夕雁相呼。
独此临泛漾,浩将人代殊。永言洗氛浊,卒岁为清娱。
要使功成退,徒劳越大夫。
地阔八荒近,天回百川澍。筵端接空曲,目外唯雰雾。
暖气物象来,周游晦明互。致牲匪玄享,禋涤期灵煦。
的的波际禽,沄沄岛间树。安期今何在,方丈蔑寻路。
仙事与世隔,冥搜徒已屡。四明背群山,遗老莫辨处。
抚中良自慨,弱龄忝恩遇。三入文史林,两拜神仙署。
虽叹出关远,始知临海趣。赏来空自多,理胜孰能喻。
留楫竟何待,徙倚忽云暮。
兹山栖灵异,朝夜翳云族。是日濛雨晴,返景入岩谷。
幂幂涧畔草,青青山下木。此意方无穷,环顾怅林麓。
伊洛何悠漫,川原信重复。夏馀鸟兽蕃,秋末禾黍熟。
秉愿守樊圃,归闲欣艺牧。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
风泉度丝管,苔藓铺茵席。传闻颍阳人,霞外漱灵液。
忽枉岩中翰,吟望朝复夕。何当遂远游,物色候逋客。
猿啼山馆晓,虹饮江皋霁。湘岸竹泉幽,衡峰石囷闭。
岭嶂穷攀越,风涛极沿济。吾师在韶阳,欣此得躬诣。
洗虑宾空寂,焚香结精誓。愿以有漏躯,聿薰无生慧。
物用益冲旷,心源日闲细。伊我获此途,游道回晚计。
宗师信舍法,摈落文史艺。坐禅罗浮中,寻异穷海裔。
何辞御魑魅,自可乘炎疠。回首望旧乡,云林浩亏蔽。
不作离别苦,归期多年岁。
徒郁仲举思,讵回道林辙。孤兴欲待谁,待此湖上月。
松露洗心眷,象筵敷念诚。薄云界青嶂,皎日鶱朱甍。
苔涧深不测,竹房闲且清。感真六象见,垂兆二鸟鸣。
古今信灵迹,中州莫与京。林巘永栖业,岂伊佐一生。
浮悟虽已久,事试去来成。观念幸相续,庶几最后明。
天香众壑满,夜梵前山空。漾漾潭际月,飗飗杉上风。
兹焉多嘉遁,数子今莫同。凤归慨处士,鹿化闻仙公。
樵路郑州北,举井阿岩东。永夜岂云寐,曙华忽葱茏。
谷鸟啭尚涩,源桃惊未红。再来期春暮,当造林端穷。
庶几踪谢客,开山投剡中。
含情不得语,转盼知所属。惆怅未可归,宁关须采箓。
太和亦崔嵬,石扇横闪倏。细岑互攒倚,浮巘竞奔蹙。
白云遥入怀,青霭近可掬。徒寻灵异迹,周顾惬心目。
晨拂鸟路行,暮投人烟宿。粳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
石髓非一岩,药苗乃万族。间关踏云雨,缭绕缘水木。
西见商山芝,南到楚乡竹。楚竹幽且深,半杂枫香林。
浩歌清潭曲,寄尔桃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