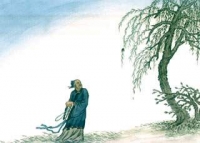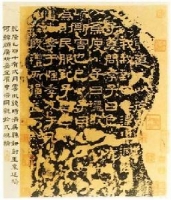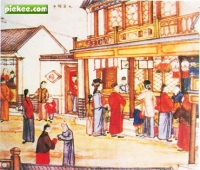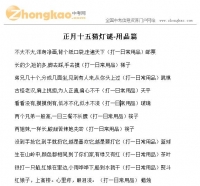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And spring comes green again to trees and grasses
Where petals have been shed like tears
And lonely birds have sung their grief.
...After the war-fires of three months,
One message from home is worth a ton of gold.
...I stroke my white hair. It has grown too thin
To hold the hairpins any more.
Another version:
Advent of Spring
The city has fallen: only the hills and rivers remain.
In Spring the streets were green with grass and trees.
Sorrowing over the times, the flowers are weeping.
The birds startled my heart in fear of departing.
The beacon fires were burning for three months,
A letter from home was worth ten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I scratch the scant hairs on my white head,
And vainly attempt to secure them with a hairpin.
【白话文】 长安沦陷国家破碎,只有山河依旧,春天来了城空人稀,草木茂密深沉。
感伤国事面对繁花,难禁涕泪四溅,亲人离散鸟鸣惊心,反觉增加离恨。
立春以来战火频连,已经蔓延三月,家在州音讯难得,一信抵值万金。
愁绪缠绕搔头思考,白发越搔越短,头发脱落既短又少,简直不能插簪。
又一:
国都残破,山河依旧不改。城郭春景,遍地树长草深。
感伤时势,花儿也都落泪;怅恨别离,鸟儿也会惊心。
春来三月,战火仍然未断;消息阻隔,家信价值万金。
发愁搔头,白发越搔越短。稀疏寥落,簪子都难别紧。
【注释】 1.国破山河在:言山河依旧,而人事已非,国家残破。春到京城,而宫苑和民宅却荒芜不堪,杂草丛生。
2.这两句有两种解说:一说是诗人因感伤时事,牵挂亲人,所以见花开而落泪(或曰泪溅于花),闻鸟鸣也感到心惊。另说是以花鸟拟人,因感时伤乱,花也流泪,鸟也惊心。二说皆可通。
3.连三月:是说战争从去年直到现在,已经两个春天过去了。抵万金:极言家信之难得。
4.浑欲:简直要。不胜簪:头发少得连发簪也插不住了。
【赏析】 此诗表现了诗人爱国念家的深厚感情,是唐诗中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篇。春望:春天所望之所见。国破:指安史乱军攻下唐都长安。惊心:心神为之震撼。烽火:战争中的警报信号。家书:家信。白头:头上白发。浑:简直。不胜:禁不起。簪:即簪子,古人用来束发或作装饰。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在投奔灵武途中,被叛军俘至长安,次年(至德二年)写此诗。 诗人目睹沦陷后的长安之箫条零落,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不免感慨万端。诗的一、二两联,写春城败象,饱含感叹;三、四两联写心念亲人境况,充溢离情。 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眷怀家人的感情。今人徐应佩、周溶泉等评此诗曰:“意脉贯通而平直,情景兼备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此论颇为妥帖。 “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诗人杜甫知道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后,不顾安危投奔唐肃宗而来,想要再有一番作为,结果被安禄山叛军拘留在长安。春天又来了,诗人登高远望,山河依旧然而国家却四分五裂,人民流离失所,长安城一片残破景象。诗人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感时恨别、忧国忧民的五言律诗《春望》。
全篇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诗人以写长安城里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来衬托国家残破。起首一“国破山河在”,触目惊心,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句以物拟人,将花鸟人格化,有感于国家的分裂、国事的艰难,长安的花鸟都为之落泪惊心。诗人由登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地感叹忧愤。国家动乱不安,战火经年不息,人民妻离子散,音书不通,这时候收到家书尤为难能可贵。诗人从侧面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人民在动乱时期想知道亲人平安与否的迫切心情。同时也以家书的不易得来表现诗人对国家深深地忧虑。结尾两句,写诗人那愈来愈稀疏的白发,连簪子都插不住了,以动作来写诗人忧愤之深广。全篇诗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多,充分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公元756年六月叛军攻下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只身投奔肃宗,途中被叛军俘获,带到长安,但因官职卑微而未被囚禁,次年三月写下此诗。
春望所见何物?大好河山未改而国破家离,都城残败、遍地乱草、树木空自凄青。首联寄情于物、托感于景,诗情曲折、工巧自然,出手不凡。次联进一步把感时恨别而堕泪惊心的感情寄托于本来是喜心悦目的花鸟身上,更显出作者心中情感之强烈。战争连续到次年三月,造成音信不通、消息断绝,此情人人能解,因此“家书抵万金”极易引起读者共鸣,宜其成为千古名句,流传至今。心中愁闷便频频搔首,乃至发落稀疏、新发短浅,连簪子都几乎要别不住了,足见忧愁之深长不断。且于家国之恨外,又见白发衰落、老之将至,更增一层垂暮之哀。
杜甫留下的诗作中,为后人推崇、传诵的有许多是感时伤乱的作品,特别是那些表现作者仁爱之心和真挚之情的名篇。仁爱与真情永远是产生优秀诗歌的源泉,也是历史用以造就圣贤和明哲的两大元素。
[鉴赏]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下唐都长安。七月,杜甫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的羌村,去投奔肃宗。途中为叛军俘获,带到长安。因他官卑职微,未被囚禁。《春望》写于次年三月。
诗的前四句写春城败象,饱含感叹;后四句写心念亲人境况,充溢离情。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开篇即写春望所见:国都沦陷,城池残破,虽然山河依旧,可是乱草遍地,林木苍苍。一个“破”字,使人怵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令人满目凄然。司马光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温公续诗话》)诗人在此明为写景,实为抒感,寄情于物,托感于景,为全诗创造了气氛。此联对仗工巧,圆熟自然,诗意翻跌。“国破”对“城春”,两意相反。“国破”的颓垣残壁同富有生意的“城春”对举,对照强烈。“国破”之下继以“山河在”,意思相反,出人意表;“城春”原当为明媚之景,而后缀以“草木深”则叙荒芜之状,先后相悖,又是一翻。明代胡震亨极赞此联说:“对偶未尝不精,而纵横变幻,尽越陈规,浓淡浅深,动夺天巧。”(《唐音癸签》卷九)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一般解释是,花鸟本为娱人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诗人见了反而堕泪惊心。另一种解释为,以花鸟拟人,感时伤别,花也溅泪,鸟亦惊心。两说虽则有别,其精神却能相通,一则触景生情,一则移情于物,正见好诗含蕴之丰富。
诗的这前四句,都统在“望”字中。诗人俯仰瞻视,视线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视野从城到山河,再由满城到花鸟。感情则由隐而显,由弱而强,步步推进。在景与情的变化中,仿佛可见诗人由翘首望景,逐步地转入了低头沉思,自然地过渡到后半部分──想望亲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安史叛乱以来,“烽火苦教乡信断”,直到如今春深三月,战火仍连续不断。多么盼望家中亲人的消息,这时的一封家信真是胜过“万金”啊!“家书抵万金”,写出了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这是人人心中所有的想法,很自然地使人共鸣,因而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烽火遍地,家信不通,想念远方的惨戚之象,眼望面前的颓败之景,不觉于极无聊赖之际,搔首踌躇,顿觉稀疏短发,几不胜簪。“白发”为愁所致,“搔”为想要解愁的动作,“更短”可见愁的程度。这样,在国破家亡,离乱伤痛之外,又叹息衰老,则更增一层悲哀。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热爱国家、眷念家人的美好情操,意脉贯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具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得铿然作响,气度浑灏,因而一千二百余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
(徐应佩 周溶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Bid me to be resolute here in my cell,
Yet it needed the song of those black wings
To break a white-haired prisoner's heart....
His flight is heavy through the fog,
His pure voice drowns in the windy world.
Who knows if he be singing still? - -
Who listens any more to me?
2) On Hearing Cicadas in Prison
Tr. Liu Yiqing
The year is sinking west, cicadas sing,
Their songs stir up the prisoner's grief.
I cannot bear the sight of their dark wing,
Their hymn to innocence gives me no relief.
Wings heavy with dew, hard becomes the flight,
Drowned in strong wind, their voice cannot be heard.
None would believe their songs are pure and bright,
Who could express my feeling deep in word?
French version:
En prison,
le poète entend chanter la cigale
La voix de la cigale a résonné, du c?té de la route occidentale;
Elle jette dans une rêverie profonde l'h?te qui porte un bonnet du midi.
Comment supporterais-je patiemment la vue de ce frêle insecte,
Qui vient, tout près de ma tête blanche, répéter son chant douloureux!
La rosée, trop lourde pour ses ailes, appesantit sa marche, et l'empêche de prendre son vol;
Le vent, qui souffle avec violence, emporte ses cris étouffés.
Les hommes ne veulent pas croire à ce qu'il y a de pur et d'élevé (dans le secret de son existence).
Puis-je espérer qu'il s'en trouve un, pour faire conna?tre à tous ce que renferme mon c?ur?
【白话文】 囚禁我的牢房的西墙外,是受案听讼的公堂,那里有数株古槐树。虽然能看出它们的勃勃生机,与东晋殷仲文所见到的槐树一样;但听讼公堂在此,象周代召伯巡行在棠树下断案一般。每到傍晚太阳光倾斜, 秋蝉鸣唱, 发出轻幽的声息, 凄切悲凉超过先前所闻。难道是心情不同往昔?抑或是虫响比以前听到的更悲?唉呀,蝉声足以感动人,蝉的德行足以象征贤能。所以,它的清廉俭信,可说是禀承君子达人的崇高品德,它蜕皮之后,有羽化登上仙境的美妙身姿。等待时令而来,遵循自然规律;适应季节变化,洞察隐居和活动的时机。有眼就瞪得大大的,不因道路昏暗而不明其视;有翼能高飞却自甘澹泊,不因世俗浑浊而改变自己本质。在高树上临风吟唱,那姿态声韵真是天赐之美,饮用深秋天宇下的露水,洁身自好深怕为人所知。我的处境困忧,遭难被囚,即使不哀伤,也时时自怨,象树叶未曾凋零已经衰败。听到蝉鸣的声音,想到昭雪平反的奏章已经上报;但看到螳螂欲捕鸣蝉的影子,我又担心自身危险尚未解除。触景生情,感受很深,写成一诗,赠送给各位知己。希望我的情景能应鸣蝉征兆,同情我象微小秋蝉般飘零境遇,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怜悯我最后悲鸣的寂寞心情。这不算为正式文章,只不过聊以解忧而已。
深秋季节西墙外寒蝉不停地鸣唱,蝉声把我这囚徒的愁绪带到远方。
怎堪忍受正当玄鬓盛年的好时光,独自吟诵白头吟这么哀怨的诗行。
露重翅薄欲飞不能世态多么炎凉,风多风大声响易沉难保自身芬芳。
无人知道我象秋蝉般的清廉高洁,有谁能为我表白冰晶玉洁的心肠?
【注释】 ①西陆:指秋天。南冠:指囚犯。
②玄鬓:即蝉鬓。古代妇女的鬓发梳得薄如蝉翼,看上去像蝉翼的影子,故玄鬓即指蝉。
③高洁:指蝉,其实是自喻。
【赏析】 这首咏物诗,名为咏蝉,实为自表心迹。诗人抒写了因无罪被诬,无人相信自己的高洁而为之辩白的忧愤。但忧愤之中又有着超然的心态,不愿与俗流为伍。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屈居下僚十八年,刚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被捕入狱。其罪因,一说是上疏论事触忤了武则天,一说是“坐赃”。这两种说法,后者无甚根据。前者也觉偏颇。从诗的尾联“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来看,显然是受了他人诬陷。闻一多先生说,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宫体诗的自赎》)。这几句话,道出了骆宾王下狱的根本原因。他敢抗上司、敢动刀笔,被抨击者当然要以“贪赃”、“触忤武后”将他收系了。也正因为如此,骆宾王才在狱中写下这首诗。
诗题又作《咏蝉》。同前人咏蝉之作,如陆云的《寒蝉赋》、曹植的《蝉赋》、曹大家的《蝉赋》、虞世南的《咏蝉》诗仿佛,骆宾王的这首五律旨在以蝉之餐风饮露表示自身的高洁,求得世人的同情。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首联承題而来,正切主旨。“西陆”,秋天。《隋书·天文志》释“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南冠”,又称獬豸冠.本指楚冠,此处作囚犯解,用楚国钟仪被囚的典故。《左传·成公九年》记,晋景公到军府检查,看见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被囚系着。成公便问:“那个被捆着的戴着楚冠的人是谁?”有司回答说:“是郑国献来的楚国囚犯钟仪。后世遂称絷囚为“南冠”。此处的南冠是作者自指。“南冠”后的“客”字不作通常的“客人”或“旅居外地”解,而指“坐牢”,称坐牢为“客”,可见冤愤殊深。首联两句十字用工整的对仗描绘了这样一副图景:深秋里,寒蝉发出了阵阵凄楚的叫声,这声音打动了囚絷在牢的骆宾王的心弦,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虑。此联中,应特别注意“思深”二字,它是作者的苦心所在,是全诗之“源”。诗的名句诸事如“玄鬓”、“白头”、“露重”、“风多”及种种联想,皆由此遣发派生。
由于作者在首联中即以南冠自切痛处,又以“思深”二字为诗旨的表达作了铺垫,故颔联即被顺势推出:“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玄鬓”,黑色鬓发,这里指蝉的双翼。“白头吟”,汉魏乐府名篇,写一女子被负心汉始爱终弃的悲郁心情,表达了她对专一爱情的追求。据说此诗为西汉卓文君作。卓文君慕司马相如之才,私奔并与司马相如结成伉俪。但司马相如爱情不专,入京后,要娶茂陵一女为妾。文君闻知,作《白头吟》以自伤。相如见诗悔悟,不再纳妾。宾王此句的写作,其意有表里二层。表层的意思是说,蝉掮动着乌黑的双翼来对着满头白发的作者悲吟,使他无法忍受。里层的含意则更为深刻,作者意在通过香草美人的传统文学手法,抒发自己失去朝廷宠信,受贬遭困的怨愤。作者“蝉”人对举,“玄”“白”并用,睹蝉翼而起悲,闻蝉鸣而不堪,是因为他也有过鬓发玄黑的豆蔻年华。早在公元669年,他就跻入仕途,以图报效:“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宿温城望军营》)。为逞壮志,他文官任过府属、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武官任过四川,燕北掌书记,然奔波三十载,却始终沉沦下僚,刚升为侍御史,便被捕入狱。报国之想,终成泡影,何堪忍受。
若说首联见景生情,托物起兴,颔联蝉人并举,叙中生议,那么颈联的重心则转在感慨议论的抒发上。“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说蝉因露重而难以前飞,因风大而鸣声不能远传。这既是描写深秋寒蝉的艰难处境,也是对自身遭遇的慨叹。作者在诗前的序中写道:“仆失路艰虞,遭时徽墨。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意即是时代的“徽墨”(绳索之意)将其捆绑,使他不能驰骋壮志。序文还说他“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看到螳螂抱紧螳斧,欲扑捉被食之虫,立即想到自己仍处在深深的危机中。朝廷内外奸邪势力的浓露重霜不但冻僵了他的翅膀,锁住了他的声音,而且会将他的生命推向“末日”。序文的这些话说明了颈联虽宇宇写蝉,然意不在蝉。这两句诗,写得蝉人相融,抒情忘蝉,达到了出神入化地步。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试读卢照邻的《古从军行》,杜甫《蜀相》诸诗,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犖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官体艳诗之上。
[鉴赏]
这首诗作于高宗仪凤三年(678)。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起二句在句法上用对偶句,在作法上则用起兴的手法,以蝉声来逗起客思。诗一开始即点出秋蝉高唱,触耳惊心。接下来就点出诗人在狱中深深怀想家园。三、四两句,一句说蝉,一句说自己,用“不堪”和“来对”构成流水对,把物我联系在一起。诗人几次讽谏武则天,以至下狱。大好的青春,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折磨已经消逝,头上增添了星星白发。在狱中看到这高唱的秋蝉,还是两鬓乌玄,两两对照,不禁自伤老大,同时更因此回想到自己少年时代,也何尝不如秋蝉的高唱,而今一事无成,甚至入狱。就在这十个字中,诗人运用比兴的方法,把这份凄恻的感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同时,白头吟又是乐府曲名。相传西汉时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爱情不专后,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伤。其诗云:“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见《西京杂记》)这里,诗人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典故,进一步比喻执政者辜负了诗人对国家一片忠爱之忱。“白头吟”三字于此起了双关的作用,比原意更深入一层。十字之中,什么悲呀愁呀这一类明点的字眼一个不用,意在言外,充分显示了诗的含蓄之美。
接下来五六两句,纯用“比”体。两句中无一字不在说蝉,也无一字不在说自己。“露重”“风多”比喻环境的压力,“飞难进”比喻政治上的不得意,“响易沉”比喻言论上的受压制。蝉如此,我也如此,物我在这里打成一片,融混而不可分了。咏物诗写到如此境界,才算是“寄托遥深”。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有谁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呢?这句诗人自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有那一个来替诗人雪冤呢?“卿须怜我我怜卿”,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这首诗作于患难之中,感情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多双关,于咏物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由人及物,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沈熙乾)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注释】 铁锁开:唐朝都城有宵禁,此夜消禁,铁锁开启,任人通行。
秾李:《诗经·召南·何彼秾矣》:“何彼秾矣,华如桃李”,形容艳妆。
落梅:古曲调名
金吾:京城禁卫军
玉漏:漏,古代计时器具。玉是形容质料的精致华美。
游妓: 一作游伎
【赏析】 本诗描写长安城热闹非凡的元宵夜景。首二句写灯火。用“火树银花”形容全城的灯火,一个“合”字从诗人视觉产生出来,无论朝着哪个方向看都是灯火繁盛,道路两旁、游乐场所、家家户户皆无所例外,大有灯火合围之势。“铁锁开”表明四面城门是敞开的,就连护城河上的桥也张灯结彩,故有“星桥”之说。节日的环境和气氛是相当浓烈的了。中四句写游人。人流一波接一波,官宦子弟骑马带起“暗尘”、浓重的尘土,万名百姓无论在何处观灯而明月都一视同仁照耀着,歌伎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边赏灯边唱着乐府歌曲《梅花落》,人们欢乐之情得到充分表达。末二句写人心。金吾,京城禁卫军。玉漏,质地精美的计时漏壶。既然官方禁卫破例取消禁夜,那就祈求计时壶莫要催促而败兴,让欢乐的人群通宵达旦地欢度节日吧!由渲染气氛引出游人,再由人的狂欢到不愿中途散去的心理历程,使节日显得极不平常而让人兴奋不已、情不自禁。从结构上看,大层次套小层次,自然和谐,符合诗的内容需要,也是本诗写法的突出点。
[鉴赏]
这首诗是描写长安城里元宵之夜的景色。据《大唐新语》和《唐两京新记》记载:每年这天晚上,长安城里都要大放花灯;前后三天,夜间照例不戒严,看灯的真是人山人海。豪门贵族的车马喧阗,市民们的歌声笑语,汇成一片,通宵都在热闹的气氛中度过。
春天刚刚才透露一点消息,还不是万紫千红的世界,可是明灯错落,在大路两旁、园林深处映射出灿烂的辉光,简直象明艳的花朵一样。从“火树银花”的形容,我们不难想象,这是多么奇丽的夜景!说“火树银花合”,因为四望如一的缘故。王维《终南山》“白云回望合”,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的“合”,用意相同,措语之妙,可能是从这里得到启发的。由于到处任人通行,所以城门也开了铁锁。崔液《上元夜》诗有句云:“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可与此相印证。城关外面是城河,这里的桥,即指城河上的桥。这桥平日是黑沈沈的,今天换上了节日的新装,点缀着无数的明灯。灯影照耀,城河望去有如天上的星河,所以也就把桥说成“星桥”了。“火树”“银花”“星桥”都写灯光,诗人的鸟瞰,首先从这儿着笔,总摄全篇;同时,在“星桥铁锁开”这句话里说出游人之盛,这样,下面就很自然地过渡到节日风光的具体描绘。
人潮一阵阵地涌着,马蹄下飞扬的尘土也看不清;月光照到人们活动的每一个角落,哪儿都能看到明月当头。原来这灯火辉煌的佳节,正是风清月白的良宵。在灯影月光的映照下,花枝招展的歌妓们打扮得分外美丽,她们一面走,一面唱着《梅花落》的曲调。长安城里的元宵,真是观赏不尽的。所谓“欢娱苦日短”,不知不觉便到了深更时分,然而人们却仍然怀着无限留恋的心情,希望这一年一度的元宵之夜不要匆匆地过去。“金吾不禁”二句,用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心理描绘,来结束全篇,言尽而意不尽,读之使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这诗于镂金错采之中,显得韵致流溢,也在于此。 (马茂元)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Watching it alone from the window of her chamber-
For our boy and girl, poor little babes,
Are too young to know where the Capital is.
Her cloudy hair is sweet with mist,
Her jade-white shoulder is cold in the moon.
...When shall we lie again, with no more tears,
Watching this bright light on our screen?
【白话文】 今晚圆圆的秋月多么皎洁美好,
你在鄜州闺中却只能一人独看。
我遥想那些可爱的小儿幼女们,
还不理解你望月怀人思念长安!
夜深露重你乌云似的头发湿了?月光如水你如玉的臂膀可受寒?
何时能依偎共赏轻纱般的月华?让月华照干我俩满是泪痕的脸!
【注释】 鄜(fū )州:地名,今陕西富县。当时杜甫的家属在鄜州的羌村,杜甫在长安。这两句设想妻子在鄜州独自对月怀人的情景。
闺中:指妻子
清辉:指月光
怜:爱。未解:尚不懂得
夜雾本无香,香从妻子的云鬟中散出;凄清的月光照在妻子的玉臂上,显得寒凉。湿、寒二字,写出夜已深而人未寐的情景。
虚幌:悬挂起的帷幔,透明的窗帷。双照:与上面的"独看"对应,表示对未来团聚的期望。
鬟huán:妇女的梳成环形的发卷
【赏析】 这首诗作于至德元年(756)。是年八月,杜甫携家逃难州,自己投奔灵武的肃宗行在,被叛军掳至长安。诗是秋天月夜的怀妻之作。 望月怀思,自古皆然。但诗人不写自己望月怀妻,却设想妻子望月怀念自己,又以儿女(因为年幼)“ 未解母亲忆长安”之意,衬出妻之“孤独”凄然,进而盼望聚首相倚,双照团圆。反映了乱离时代人民的痛苦之情。词旨婉切,章法紧密,写离情别绪,感人肺腑。
天宝十五年(756)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杜甫只得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身陷贼营的杜甫八月在长安所作。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祸,便没有诗人的这番家人离散,身陷绝境的悲惨经历。而如果没有这番特殊的经历,要产生诗中的哀惋凄切、深挚缠绵的离情也是不可想象的。此诗的重要价值,确乎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一点上。
不过使得这首诗在众多的抒写乱世之离情的作品中高标独秀的,却无疑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新奇角度与抒写章法。在这里,老杜并不一般地就景敷情、缘情述事,而是别出心裁从思念对象一边落笔,从头至尾细致熨帖地描摹自己想象中的对方的景况。无限的深情、痴情都从这一系列想象描写中流泻而出,达到了抒情的极致。首联二句,绝不说自己望月而忆妻,偏说妻子见月而思己,比起一般的直诉自己的情感的忆内之作,一开篇意思就深了一层。前人写过“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和“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一类的名句,那都是兼及“忆”与“被忆”双方的,这里却偏偏只提被忆的一方,抒写角度的转换,使得辞旨婉切,更显出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身边,是时时尾随着可爱的小儿女的。诗人月夜思妻,必然密不可分地念及孩子。可是颔联二句不正面说自己望月忆儿女,偏说儿女随母望月,又想象儿女幼小,尚不解望月而思念身陷长安的慈父。真是此情此景,将何以堪!诗人刻骨铭心的忆内之情,又在这痛苦的想象中更深入一层。第三联,想象愈加具体化,虚拟妻子在这个夜晚望月怀夫、久久不眠的情景,是整首诗中意境最优美,辞采最清丽的抒情句子。鬟湿而臂寒,状看月之久与怀人之痴。月色愈好而痛苦愈增,夜深天寒都浑然不觉。这位闺中娘子是如此多情而执着,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诗人深切思念吗?王嗣奭《杜臆》认为此联“语丽情悲”。实为中肯。诗的末联,方才将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摆进去,仍以想象之笔结情。这是盼望相思之愿能偿,有朝一日伉俪重逢,双双对此明月舒愁,抹掉战乱带来的伤痛痕迹。这里对前文的承接照应十分细密周到,表现出诗人情感之深婉沉绵,如“双”承“独”,“照”承“月”,“泪痕干”反衬双方各自“独看”时的泪流不止,这些都真切地传达出诗人憎恨乱离,盼望团圆的迫切心情。
[赏析]
天宝十五载(756)春,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白水(今陕西白水县)的舅父处。六月,长安陷落,玄宗逃蜀,叛军入白水,杜甫携家逃往鄜州羌村。七月,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位,杜甫获悉即从鄜州只身奔向灵武,不料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回长安。这首诗即是困居长安时所作,表达了对离乱中的妻子家小的深切挂念。情深意真,明白如话,丝毫不见为律诗束缚的痕迹。诗的构思采用从对方设想的方式,"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读杜心解》)。后世诗人常常学此法度。
题为《月夜》,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如果从自己方面落墨,一入手应该写“今夜长安月,客中只独看”。但他更焦心的不是自己失掉自由、生死未卜的处境,而是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如何焦心。所以悄焉动容,神驰千里,直写“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这已经透过一层。自己只身在外,当然是独自看月。妻子尚有儿女在旁,为什么也“独看”呢?“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一联作了回答。妻子看月,并不是欣赏自然风光,而是“忆长安”,而小儿女未谙世事,还不懂得“忆长安”啊!用小儿女的“不解忆”反衬妻子的“忆”,突出了那个“独”字,又进一层。
在一二两联中,“怜”字,“忆”字,都不宜轻易滑过。而这,又应该和“今夜”、“独看”联系起来加以吟味。明月当空,月月都能看到。特指“今夜”的“独看”,则心目中自然有往日的“同看”和未来的“同看”。未来的“同看”,留待结句点明。往日的“同看”,则暗含于一二两联之中。“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这不是分明透露出他和妻子有过“同看”鄜州月而共“忆长安”的往事吗?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其中有一段时间,是与妻子在一起度过的。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这自然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到了羌村的时候,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而共“忆长安”,已不胜其辛酸!如今自己身陷乱军之中,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那“忆”就不仅充满了辛酸,而且交织着忧虑与惊恐。这个“忆”字,是含意深广,耐人寻思的。往日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虽然百感交集,但尚有自己为妻子分忧;如今呢,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她的负担,哪能为她分忧啊!这个“怜”字,也是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的。
第三联通过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描写,进一步表现“忆长安”。雾湿云鬟,月寒玉臂。望月愈久而忆念愈深,甚至会担心她的丈夫是否还活着,怎能不热泪盈眶?而这,又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这就不能不激起结束这种痛苦生活的希望;于是以表现希望的诗句作结:“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也就意在言外了。
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但所抒发的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夫妇离别之情。作者在半年以后所写的《述怀》诗中说:“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寄书问三川(鄜州的属县,羌村所在),不知家在否”;“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两诗参照,就不难看出“独看”的泪痕里浸透着天下乱离的悲哀,“双照”的清辉中闪耀着四海升平的理想。字里行间,时代的脉搏是清晰可辨的。
题为《月夜》,字字都从月色中照出,而以“独看”、“双照”为一诗之眼。“独看”是现实,却从对面着想,只写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而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鄜州,已包含其中。“双照”兼包回忆与希望:感伤“今夜”的“独看”,回忆往日的同看,而把并倚“虚幌”(薄帷)、对月舒愁的希望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词旨婉切,章法紧密。如黄生所说:“五律至此,无忝诗圣矣!”
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
城中曲江水,江上江陵城。
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
【注释】 【按】元九,元稹。诗中多次用到重复字,大约是有意打破成规。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Soon you will be with people in the south,
Where the mountains end and the plains begin
And the river winds through wilderness....
The moon is lifted like a mirror,
Sea-clouds gleam like palaces,
And the water has brought you a touch of home
To draw your boat three hundred miles.
【白话文】 远道而来渡过荆门之外,来到楚地游览。
山随着低平的原野地出现逐渐消失。
江水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奔流。
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像天上飞下来的一面天镜,云彩升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
我还是怜爱故乡的水,流过万里送我行舟远行。
又一:
自剑门之外的西蜀沿江东下,来到了楚国境内作一次旅游。
崇山随着荒野出现渐渐逝尽,长江进入了莽原也缓缓而流。
月影倒映江中象是飞来天镜,云层缔构城郭幻出海市蜃楼。
我依然怜爱这来自故乡之水,行程万里继续漂送我的行舟。
【注释】 远:远自。
江:长江。
下:移下。
海楼:海市蜃楼。
仍:频频。
1. 荆门:即荆门山,位于今湖北宜都县西北,长江南岸,与北岸虎牙山隔江对峙,形势险要,自古即有楚蜀咽喉之称。
2. 楚国:古楚国之地,泛指今湖北、湖南一带。
3. 海楼:现在所说的海市蜃楼。
4. 怜:爱。
5. 故乡水:指长江,李白早年住在四川,故有此言。
【赏析】 唐开元十四年(726),诗人怀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情,出蜀东下,此诗即在旅游途中所作。从诗意看,诗人与送行者同舟共发,是在舟中吟送的。清朝沈德潜认为,诗中无“送别”意,题中“送别”二字可删,是不确的。这首诗虽意在描绘山水,然而仔细揣摩, “送别”之意犹在,足见椽笔功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与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可比功力。或认为李是行舟流览,杜则停舟细看。此说颇是在理。
诗人远渡荆门,眼望一派壮丽的大好河山,心生豪放。抒发了自己的胸怀与进取精神,生气勃勃,意气风发。诗的前三联描写的是渡过荆门山时诗人所看到的奇妙美景。最后一联写的是诗人在欣赏荆门一带的风光时,面对那流经故乡的滔滔江水,所产生的思乡之情。诗人没有直接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我远行,从对面写来,愈发显出自己对故乡的思念。
全诗想像瑰丽,意境高远,充满了生活的光彩。
这首诗风格雄健,形象奇伟,想象瑰丽。“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写得逼真如画,有如一幅长江出峡渡荆门长轴山水图,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果说优秀的山水画“咫尺应须论万里”,那么,这首形象壮美瑰玮的五律也可以说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并且容量丰富:诗人选取日、月、江、天,包涵长江中游数万里山势与水流的景色这样瑰丽大气的意象,显得大气磅礴,风格雄健有力;而描写又逼真如画,意境高远,具有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力。故此诗成为李白描绘祖国壮丽河山著名的诗篇之一。
李白这次出蜀,由水路乘船远行,经巴渝,出三峡,直向荆门山之外驶去,目的是到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游览。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指的就是这一壮游。这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情观赏巫山两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过荆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域顿然开阔,别是一番景色。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前句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渡过荆门山后长江两岸的特有景色:山逐渐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的原野。它好比用电影镜头摄下的一组活动画面,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将静止的山岭摹状出活动的趋向来。“江入大荒流”,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从荆门往远处望去,仿佛流入荒漠辽远的原野,显得天空寥廓,境界高远。后句著一“入”字,力透纸背,用语贴切。景中蕴藏着诗人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的蓬勃朝气。
写完山势与流水,诗人又以移步换景手法,从不同角度描绘长江的近景与远景:“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长江流过荆门以下,河道迂曲,流速减缓。晚上,江面平静时,俯视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象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似的;日间,仰望天空,云彩兴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奇景。
这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中和平静的江面上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夏水襄陵,江面水流湍急汹涌,那就很难有机会看到“月下飞天镜”的水中影像;在隐天蔽日的三峡空间,也无从望见“云生结海楼”的奇景。这一联以水中月明如圆镜反衬江水的平静,以天上云彩构成海市蜃楼衬托江岸的辽阔,天空的高远,艺术效果十分强烈。颔颈两联,把生活在蜀中的人,初次出峡,见到广大平原时的新鲜感受极其真切地写了出来。
李白在欣赏荆门一带风光的时候,面对那流经故乡的滔滔江水,不禁起了思乡之情:“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而又初次离别的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出自己思乡深情。诗以浓重的怀念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情无穷。
[鉴赏]
这首诗是李白出蜀时所作。荆门,即荆门山,位于今湖北宜都县西北,长江南岸,与北岸虎牙山隔江对峙,形势险要,自古即有楚蜀咽喉之称。
李白这次出蜀,由水路乘船远行,经巴渝,出三峡,直向荆门山之外驶去,目的是到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游览。“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指的就是这一壮游。这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情观赏巫山两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过荆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域顿然开阔,别是一番景色: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前句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渡过荆门山后长江两岸的特有景色:山逐渐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的原野。它好比用电影镜头摄下的一组活动画面,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将静止的山岭摹状出活动的趋向来。
“江入大荒流”,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从荆门往远处望去,仿佛流入荒漠辽远的原野,显得天空寥廓,境界高远。后句著一“入”字,力透纸背,用语贴切。景中蕴藏着诗人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的蓬勃朝气。
写完山势与流水,诗人又以移步换景手法,从不同角度描绘长江的近景与远景: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长江流过荆门以下,河道迂曲,流速减缓。晚上,江面平静时,俯视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象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似的;日间,仰望天空,云彩兴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奇景。这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中和平静的江面上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夏水襄陵,江面水流湍急汹涌,那就很难有机会看到“月下飞天镜”的水中影像;在隐天蔽日的三峡空间,也无从望见“云生结海楼”的奇景。这一联以水中月明如圆镜反衬江水的平静,以天上云彩构成海市蜃楼衬托江岸的辽阔,天空的高远,艺术效果十分强烈。颔颈两联,把生活在蜀中的人,初次出峡,见到广大平原时的新鲜感受极其真切地写了出来。李白在欣赏荆门一带风光的时候,面对那流经故乡的滔滔江水,不禁起了思乡之情: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五岁诵六甲”起,直至二十五岁远渡荆门,一向在四川生活,读书于戴天山上,游览峨眉,隐居青城,对蜀中的山山水水怀有深挚的感情,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出自己思乡深情。诗以浓重的怀念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情无穷。诗题中的“送别”应是告别故乡而不是送别朋友,诗中并无送别朋友的离情别绪。清沈德潜认为“诗中无送别意,题中二字可删”(《唐诗别裁》),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首诗意境高远,风格雄健,形象奇伟,想象瑰丽。“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写得逼真如画,有如一幅长江出峡渡荆门长轴山水图,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果说优秀的山水画“咫尺应须论万里”,那么,这首形象壮美瑰玮的五律也可以说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容量丰富,包涵长江中游数万里山势与水流的景色,具有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力。
(何国治)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With gentle Spring aye born in fitting hour.
Along the Wind with cloaking Night it goes.
Enmoistening, fine, inaudible it flows.
The clouds the mountain paths in darkness hide.
And lonely bright the vessels’ lanterns glower.
Dawn shows how damp the blushing buds divide,
And flowers droop head-heavy in each bower.
【赏析】 这是描绘春夜雨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
一开头就用一个“好”字赞美“雨”。在生活里,“好”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做好事的人。如今用“好”赞美雨,已经会唤起关于做好事的人的联想。接下去,就把雨拟人化,说它“知时节”,懂得满足客观需要。不是吗?春天是万物萌芽生长的季节,正需要下雨,雨就下起来了。你看它多么“好”!
第二联,进一步表现雨的“好”。雨之所以“好”,就好在适时,好在“润物”。春天的雨,一般是伴随着和风细细地滋润万物的。然而也有例外。有时候,它会伴随着冷风,由雨变成雪。有时候,它会伴随着狂风,下得很凶暴。这样的雨尽管下在春天,但不是典型的春雨,只会损物而不会“润物”,自然不会使人“喜”,也不可能得到“好”评。所以,光有首联的“知时节”,还不足以完全表现雨的“好”。等到第二联写出了典型的春雨伴随着和风的细雨,那个“好”字才落实了。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仍然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潜入夜”和“细无声”相配合,不仅表明那雨是伴随和风而来的细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润物”,无意讨“好”。如果有意讨“好”,它就会在白天来,就会造一点声势,让人们看得见,听得清。惟其有意“润物”,无意讨“好”,它才选择了一个不妨碍人们工作和劳动的时间悄悄地来,在人们酣睡的夜晚无声地、细细地下。
雨这样“好”,就希望它下多下够,下个通宵。倘若只下一会儿,就云散天晴,那“润物”就很不彻底。诗人抓住这一点,写了第三联。在不太阴沉的夜间,小路比田野容易看得见,江面也比岸上容易辨得清。如今呢?放眼四望,“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只有船上的灯火是明的。此外,连江面也看不见,小路也辨不清,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云,地上也象云一样黑。好呀!看起来,准会下到天亮。
尾联写的是想象中的情景。如此“好雨”下上一夜,万物就都得到润泽,发荣滋长起来了。万物之一的花,最能代表春色的花,也就带雨开放,红艳欲滴。等到明天清早去看看吧!整个锦官城(成都)杂花生树,一片“红湿”,一朵朵红艳艳、沉甸甸,汇成花的海洋。那么,田里的禾苗呢?山上的树林呢?一切的一切呢?
浦起龙说:“写雨切夜易,切春难。”这首《春夜喜雨》诗,不仅切夜、切春,而且写出了典型春雨的、也就是“好雨”的高尚品格,表现了诗人的、也是一切“好人”的高尚人格。
诗人盼望这样的“好雨”,喜爱这样的“好雨”。所以题目中的那个“喜”字在诗里虽然没有露面,但“‘喜’意都从罅缝里迸透”(浦起龙《读杜心解》)。诗人正在盼望春雨“润物”的时候,雨下起来了,于是一上来就满心欢喜地叫“好”。第二联所写,显然是听出来的。诗人倾耳细听,听出那雨在春夜里绵绵密密地下,只为“润物”,不求人知,自然“喜”得睡不着觉。由于那雨“润物细无声”,听不真切,生怕它停止了,所以出门去看。第三联所写,分明是看见的。看见雨意正浓,就情不自禁地想象天明以后春色满城的美景。其无限喜悦的心情,又表现得多么生动!
中唐诗人李约有一首《观祈雨》:“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和那些朱门里看歌舞的人相比,杜甫对春雨“润物”的喜悦之情难道不是一种很崇高的感情吗?
(霍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