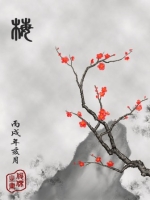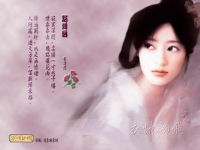起来慵整纤纤手。
露浓花瘦,
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
袜铲金钗溜,
和羞走。
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
【赏析】 靖康之乱前,词人李清照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她这时期的词,主要是抒写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对自由的渴望。风格基本上是明快的。《点绛唇》(“蹴罢秋千”)很可能就是这一时期中的早期作品。
这首词的上片用“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给读者描绘出一个身躯娇小、额间鬓角挂着汗珠、轻衣透出香汗刚下秋千的如花少女天真活泼、憨态可掬的娇美形象。紧接着,词人转过笔锋,使静谧的词境风吹浪起,写少女忽然发现有人来了,她自然而然地、匆匆忙忙地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光着袜子,害羞地朝屋里就跑,头上的金钗也滑落了。这把封建社会深闺少女的另一种心理和行动,也就是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遵守所谓“礼”的心理和行动,逼真地摹写出来了。但是,她害羞地跑到门边,却没有照常理立刻躲进屋里去,而是“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李清照这两个短句和李煜《一斛珠》中的“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样,成功地写出了少女的情态。同时,李清照这两个短句还生动地表露了少女的内心世界。她嗅青梅,不是真的嗅,而是用以表现其若无其事来遮掩她的紧张。这和欧阳炯《贺明朝》中的:“石榴裙带,故将纤纤玉指,偷捻双凤金线。”晃冲之《传言玉女·上元》中的“娇波溜人,手捻玉梅低说”,都有类似之处。这和今天现实生活中,年轻的姑娘以摆弄辫梢、手绢等,来掩饰她的害羞、紧张也是类似的。至于“回首”,那也和欧阳炯《南乡子》中“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的“回顾”,李珣《南乡子》中“玉纤遥指花深处,争回顾,孔雀双双迎日舞”的“回顾”一样,虽然它们所表现的内容、表达的感情,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都是以简单的回头看的动作,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心活动的。李清照这两个短句中的“回首”是少女对来人打搅了她自由玩乐的不愉快,她要看看打搅她的来人是谁,她要看看把他弄得那么狼狈的是谁,是什么样的人。这表现了她的天真、勇敢,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束缚轻视的一面。这种思想感情,就其内容来说,远远超过了这一生活侧面的描写。
在李清照之前,虽然绝大多数词都是写妇女,但是,能够描绘出妇女的形象,并写出妇女的内心世界,而且有一定意义的却不多。李清照这首《点绛唇》语言质朴,形象生动逼真,不但有心理描写,而且有一定的深意,的确是一首写封建社会的少女(词人的自我写照)的好作品。它和李清照的著名词作《一翦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完全可以媲美。(马兴荣)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
今何许?
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注释】 丁未: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
吴松:即今吴江。本年春,姜夔曾由杨万里介绍到苏州去见范成大。
①燕雁:北来之雁。北国燕赵之地。
②商略:商量,筹划,酝酿。此处指遥望山峰,雨意很浓。
③第四桥:指吴江城外的甘泉桥。郑文焯《绝妙好词校录》:“宋词凡用四桥,大半皆谓吴江城外之甘泉桥……。《苏州志》:甘泉桥旧名第四桥。”
④天随:唐诗人陆龟蒙字鲁望,号天随子,隐居吴江松江甫里,曾乘扁舟渔樵于太湖。
拟共天随住:晚唐诗人陆龟蒙号天随子,住松江,近苏州。当时杨万里等人要用陆的天然情趣,来救江西诗派的瘦硬之风。白石虽是江西人,论诗却是膺服陆龟蒙的。陆龟蒙不羡权贵,恬淡江湖的性格,也很合白石的脾胃。白石曾赋诗,「三生定是陆天随,又向吴松作客归。」
【赏析】 本篇为淳熙十四年(1187)冬,作者前往苏州拜访范成大,途经吴松时所作。先写景。大雁南飞,山峰矗立,显得落寞荒凉,既有着超然出世的淡泊,又有着客子飘流的孤独凄凉。
接下来明言欲像陆龟蒙一样隐居。晚唐诗人陆龟蒙号天随子,住松江,近苏州。当时杨万里等人要用陆的天然情趣,来救江西诗派的瘦硬之风。白石虽是江西人,论诗却是膺服陆龟蒙的。陆龟蒙不羡权贵,恬淡江湖的性格,也很合白石的脾胃。白石曾赋诗,“三生定是陆天随,又向吴松作客归。”
“今何许”突作陡转,“凭阑怀古”承上启下,“残柳参差舞”又陷入一片迷茫萧瑟之中。
【评解】
此词为作者自湖州往苏州,道经吴松所作。乃小令中之名篇。虽只41字,却深刻地
传出了姜夔“过吴松”时“凭栏怀古”的心情。上片写景。“燕雁”、“数峰”,不仅
写景状物出色,且用拟人化手法,使静物飞动,向为读者称赞。下片因地怀古。“残柳
参差舞”,使无情物,着有情色,道出了无限沧桑之感。全词委婉含蓄,引人遐想。
【集评】
卓人月《词统》:“商略”二字诞妙。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白石长调之妙,冠绝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点绛
唇》一阕,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云:“今何许?
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倡,“凭阑怀古”下,
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
绝调。
陈思《白石道人年谱》:案此阕为诚斋以诗送谒石湖,归途所作。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欲雨而待“商略”,“商略”而在“清苦”之“数
峰”,乃词人幽渺之思。白石泛舟吴江,见太湖西畔诸峰,阴沉欲雨,以此二句状之。
“凭阑”二句其言往事烟消,仅余残柳耶?抑谓古今多少感慨,而垂杨无情,犹是临风
学舞耶?清虚秀逸,悠然骚雅遗音。
[鉴赏]
白石论诗有四素:气象、体面、血脉、韵度。对四者的要求且是“气象欲其浑厚”、“体面欲其宏大”、“血脉欲其贯通”、“韵度欲其飘逸”。虽是论诗之语,移之于词,也甚贴切。读此词,知其所言非虚。南宋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之冬,白石往返于湖州苏州之间,经过吴松(今江苏吴江县)时,乃作此词。为何过吴松而作此词?因为白石平时最心仪于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龟蒙生前隐居之地,正是吴松。
上片之境,乃词人俯仰天地之境 。“燕雁无心”。燕念平声(y ān 烟),北地也。燕雁即北来之雁。时值冬天,正是燕雁南飞的时节。陆龟蒙咏北雁之诗甚多,如《孤雁》 :“我生天地间,独作南宾雁。”《归雁》:“北走南征象我曹,天涯迢递翼应劳。”《京口》:“雁频辞蓟北。”《金陵道》:“北雁行行直。”《雁》:“南北路何长。”白石诗词亦多咏雁,诗如《雁图》、《除夜》,词如《浣溪沙》及本词。可能与他多年居无定所,浪迹江湖的感受及对龟蒙的万分心仪有关。劈头写入空中之燕雁,正是暗喻飘泊之人生。无心即无机心,犹言纯任天然。点出燕雁随季节而飞之无心,则又喻示自己性情之纯任天然。此亦化用龟蒙诗意。龟蒙《秋赋有期因寄袭美(皮日休)》 :“ 云似无心水似闲。”《和袭美新秋即事》:“心似孤云任所之,世尘中更有谁知 。”下句紧接无心写出:“太湖西畔随云去。”燕雁随着淡淡白云,沿着太湖西畔悠悠飞去。燕雁之远去,暗喻自己飘泊江湖之感。随云而无心,则喻示自己纯任天然之意。宋陈郁《藏一话腴》云:白石“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语到意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张羽《白石道人传》亦曰其“体貌轻盈,望之若神仙中人 。”但白石与晋宋名士实有不同,晋宋所谓名士实为优游卒岁的贵族,而白石一生布衣,又值南宋衰微之际,家国恨、身世愁实非晋宋名士可比。故下文写出忧国伤时之念。太湖西畔一语,意境阔大遥远。太湖包孕吴越,“天水合为一”(龟蒙《初入太湖》)。本词意境实与天地同大也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商略一语,本有商量之义,又有酝酿义。湖上数峰清寂愁苦,黄昏时分,正酝酿着一番雨意。此句的数峰之清苦无可奈何反衬人亡万千愁苦 。从来拟人写山,鲜此奇绝之笔。比之辛稼轩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又是何种不同的况味。卓人月《词统》评云:“商略二字,诞妙。”
下片之境 ,乃词人俯仰今古之境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第四桥即“吴江城外之甘泉桥”(郑文焯《绝妙好词校录》),“以泉品居第四 ”故名(乾隆《苏州府志》)。这是陆龟蒙的故乡。《吴郡图经续志》云 :“陆龟蒙宅在松江上甫里 。”松江即吴江。天随者,天随子也,龟蒙之自号。天随语出《庄子·在宥》“神动而天随 ”,意即精神之动静皆随顺天然。龟蒙本有胸怀济世之志,其《村夜二首》云 :“岂无致君术,尧舜不上下。岂无活国力 ,颇牧齐教化。”可是他身处晚唐末世,举进士又不第,只好隐逸江湖。白石平生亦非无壮志,《昔游》诗云:“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永遇乐》:“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 。”但他亦举进士而不第 ,飘泊江湖一生。此陆 、姜二人相似之一也。龟蒙精于《春秋》 ,其《甫里先生传》自述 :“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探大籍识大义”,“贞元中,韩晋公尝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 ”,“而颠倒漫漶翳塞,无一通者,殆将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误后学,乃著书摭而辨之。”白石则精于礼乐,曾于庆元三年(1197)“进《 大乐议》于朝”,时南渡已六七十载,乐典久已亡灭,白石对当时乐制包括乐器乐曲歌辞,提出全面批评与建树之构想,“书奏,诏付太常。”(《宋史·乐志六 》)以布衣而对传统文化负有高度责任感,此二人又一相同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上的认同感,使白石有了“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三高祠 》诗),及“三生定是陆天随”(《除夜》诗)之语。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即是这种认同感的体现。第四桥边,其地仍在,天随子,其人则往矣。中间下拟共二字,便将仍在之故地与已往之古人与自己连结起来,泯没了古今时间之界限。这是词人为打破古今局限寻求与古人的精神句诵而采取的特殊笔法。再如刘过《沁园春》之与东坡、乐天、林和靖交游,亦是此一笔法。以上写了自然、人生、历史,笔笔翻出新意结笔更写出现时代,笔力无限 。“ 今何许”三字,语意丰富,涵盖深广。何许有何时、何处、为何、如何等多重含义。故今何许包含今是何世、世运至于何处、为何至此我又如何面对等意。此是囊括宇宙、人生、历史、时代之一大反诘,是充满哲学反思意味一大反诘 。而其中重点,主要在今之一字。凭栏怀古,笔力雄劲 ,气象阔大 。古与今上下映照成文,补足“今何许”一大反诘之历史意蕴。应知此地古属吴越,吴越兴亡之殷鉴,曾引起晚唐龟蒙之无限感慨 :“香径长洲尽棘丛 ,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吴宫怀古》)亦不能不引起南宋白石之无限感慨 :“美人台上昔欢娱,今日空台望五湖。残雪未融青草死,苦无麋鹿过姑苏。”(《除夜》)怀古正是伤今 。“残柳参差舞 ,”柳本纤弱,那堪又残,故其舞也参差不齐,然而仍舞之不已。舞之一字执著有力,苍凉中寓含悲壮,悲壮中透露苍凉 。“残柳参差舞”这一自然意象,实际上是南宋衰世的象征,隐然包含着虽已残破仍不甘灭亡的意味。这与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象征唐朝国运的不可挽回有同工之妙。而其作为自然意象之本身,则又补足“今何许”一大反诘之自然意蕴。结笔之意境,实为南宋国运之写照 。返观数峰清苦二句,其意蕴正为结尾之伏笔 。在此九年之前 ,辛稼轩作《摸鱼儿》,结云:“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乃是同一意境。白石本词用舞字结穴,蕴含无限苍凉悲壮。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一阕,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云‘今何许 ,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凭栏怀古下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绝调 。”善于提空描写,从虚处着笔,正是白石词的一大特点 。此词将身世之感、家国之恨融为一片,乃南宋爱国词中无价瑰宝。而身世家国皆以自然意象出之,自然意象在词中占优势,又将自然、人生、历史(尚友天随与怀古)、时代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尤其“今何许”之一大反诘,其意义虽着重于今,但其意味实远远超越之,乃是词人面对自然、人生、历史、时代所提出之一哲学反思。全词意境遂亦提升至于哲理高度。“今何许”,真可媲美于《桃花源记》“问今是何世 ”,《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首词无限感慨,全在虚处,正是“意愈切而词愈微 ”,这种写法,易形成自我抒写之形象与所写之意象间接开距离,造成朦胧之美感。此词声情之配合亦极精妙。上片首句首二字燕雁为叠韵,末句三四字黄昏为双声,下片同位句同位字第四又为叠韵,参差又为双声。分毫不爽,自然天成。双声叠韵之回环,妙用在于为此一尺幅短章增添了声情绵绵无尽之致。
柔肠一寸愁。
千缕惜春春去,
几点催花雨。
倚遍栏干,
只是无情绪!
人何处?
连天衰草,
望断归来路。
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
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
【注释】 点绛唇:杨慎《词品》:“《点绛唇》取梁江淹诗‘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以为名。”
【赏析】 此词吟咏归隐。上阕写冬末初春景:寒江夜月,梅横影瘦。心境的落寞与凄清在这些景物描写中得到表现。下阕前两句写霜寒无酒可饮,处境十分困窘,听到乱鸦聒噪,更增退隐之思。“归兴浓于酒”,形象具体表现有力。
梦云烟树。
依约江南路。
碧水黄沙,梦到寻梅处。
花无数。
问花无语。
明月随人去。
【赏析】 此为怀人念远之词。
全词以行云流水般的空灵笔调,从闻歌入乎,转入梦境,又由梦中寻觅转入对月怀人。整首词回旋往复,句琢字炼,清空醇雅。
上片首句以一个“清”字为全词感情上定下了幽清的基调。“水流歌断春风暮”,断,终了,这句是说那流水般的一曲清歌,春风吹拂的暮霭中结束了。
“春风暮”,景语,一字一景,词中以下诸景,皆缘此三字而来;这里也同时点出了这首词的特定节候,这正是一个怀人的季节,怀人的天气,怀人的时刻。
“水流”,字面上自然是写“清歌”的缠绵婉转,实际上,这里“水流”即流水,暗寓知音,典出《列子思。由此,作者的笔触转入怀人。作者写怀人,非用泛泛之笔,而是借助于一个梦境,把怀人念远的思想情绪写得深刻入微。“梦云烟树,依约江南路”以及下片的“碧水黄沙”云云,皆是梦境,用笔上又极见层次。 “梦云”、“依约”两句是入梦之境。“云”,是“梦云”,“树”是“树”是“烟树”,“江南路”是“依约”(隐约)朦胧的,极是迷离惝恍的梦境。由“云” 而“树”而“路”,由飘忽而实,梦中寻找知音的足迹甚明。
下片写梦中寻觅和对月怀人。“碧水黄沙”,紧承上片结句之意,进一步写对知音的寻觅。如果说上片“依约江南路”是朦胧中辨认知音去路的话,那么,“碧水黄沙”所表现的则是到处寻觅,水中陆上,无所不至,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了,且四字属对工稳,色彩鲜明,为本词的唯一亮色,这正是作者用笔变幻处。“梦到寻梅处”是穷尽“碧水黄沙”辗转寻找的结果,笔法由面到点,然后由“寻梅处”引出“花无数”,再由花而人,向花打听知音之所。这几句,用笔如剥茭,一步一层,层层转深,转愈深而情愈切,及至问花无语,寻觅无着,顿挫之下,不禁怅然若失,愁绪茫茫,不知所之,转见明月,也好象已随那人运去,而失去了它那固有的光辉。“明月随人去”一句所展示的空间既大且空,读之令人如置身于一个广漠而暗淡的世界,进而想到作者于此所寄寓的感情必然是悲凉而空虚的。此时的作者,是醒是梦,已难分难辨之际,这真是以景传情的神来之笔。不过,作者的情调显然是过于低沉了,同样是写对月怀人,却不如苏轼“千里共婵娟”来得旷达。
此词作者是一位以清丽素雅著称的词人。他的作品,善写烟雨和月色,具有一种素淡、朦胧的美。本篇即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艺术风格。
眼波微注。
将谓牵牛渡。
见了还非,重理霓裳舞。
都无误。
几年一遇。
莫讶周郎顾。
【注释】 “霓裳”,
《霓裳羽衣曲》,唐代乐曲名,相传为唐玄宗所制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唐?白居易《琵琶行(并序)》
一雨落桐花,掩斜晖、心事顿成秋院。易急采菱歌,青嶂晚、云湧暝潮初转。啼鹃犹唤,江山未觉风流远。回首池塘青遍处,一夜离情都满。春草池在旧中山书院,即今校舍也。
何时社燕还逢,说赚人词赋,长卿应倦。鸥讯堕鱼天,梦痕在、旧谱薲洲东畔。鼓鼙不管,鹿车安顿眉颦暖。只恐明朝桃李艳,又惹看花肠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