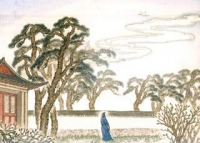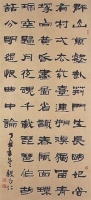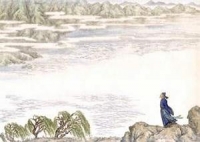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In the year of his demise, too, he was in the Palace of Eternal Peace.
The blue-green banners can be imagined on the empty mountain,
The jade palace is a void in the deserted temple.
In the pines of the ancient shrine aquatic cranes nest;
At summer and winter festivals the comers are village elders.
The Martial Marquis's memorial shrine is ever nearby;
In union, sovereign and minister share the sacrifices together.
【白话文】 当年刘备谋攻东吴曾到达三峡;他驾崩时也在白帝城的永安宫。
想象里仪仗旌旗仍在空山飘扬;白玉殿在荒郊野寺中难寻影踪。
古庙的松杉树上水鹤筑巢栖息;每年三伏腊月跑来祭祀的村翁。
诸葛武侯祠庙长年在附近为邻;生前君臣一体死后的祭祀相同。
【注释】 蜀主征吴:指刘备当年起兵伐吴事。
幸:旧称皇帝踪迹所至曰"幸"。
翠华:皇帝仪仗中用翠鸟羽毛作装饰的旗帜。
玉殿:句下原注:“殿今为卧龙寺,庙在宫东。”
巢水鹤:水鹤在杉松上做巢。
岁时伏腊:代指年节之日。
武侯句:诸葛亮曾封武乡侯,其祠在先主庙西。常:一作"长"。
一体句:正因他们君臣一体,情分特密,故也一同祭祀。顾宸所谓"平日抱一体之诚,千秋享一体之报。"
【赏析】 (一)
这首诗是推崇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关系。作者借村翁野老对他们的祭祀,烘托其遗迹之流泽。但是对于玉殿的虚无缥缈,松杉栖息水鹤,诗人发抒了无限感慨。
(二)
此诗咏叹蜀先主刘备,有世事沧桑之感,也有寓有君臣遇合月得之慨。清浦起龙说:”因庙而咏蜀主,悲不祀也。结以武侯伴说,波澜近便,鱼水君臣,殁犹邻近,由废斥飘零之人对之,有深感焉。“(《读杜心解》卷四之三)
首联从永安宫写起,追思当年刘备伐吴并驾崩于此的史事。颔联想象当时这里的繁华景象,如今已满目凄凉,只有空山野寺而已,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感。颈联继续描写古庙的荒凉萧条。”巢水鹤“似有寓意,与君臣遇合有关,当是反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曹操《短歌行》)的句意。死后之庙可”巢水鹤“,生前之礼贤下士亦可想而知也。”走村翁“写当地百姓还在怀念着这位曾叱诧风云的一代英主,按照节令而前来祭祀。尾联的”一体君臣“有双关意,用两庙邻近同受祭祀来暗寓君臣遇合,心心相印的胜事。
刘备以仁德之主而著称于史,但使他获得更高声誉的则是”三顾茅庐“及以后的识贤、礼贤、尊贤、用贤的明智之举,故他的名字常和诸葛亮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为君臣遇合的典范。而这一点正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绝大部分士人所梦寐以求的,因为只有遇到明君才能有机会一展胸襟怀抱,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这便是刘备深受后人推崇的主要原因。
(毕宝魁)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
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荜兴,得兼梁甫吟。
独在阴崖结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常风寒。
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知君此计成长往,
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
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注释】 为云: 作云
【赏析】 此诗约作于天宝中作者献赋后。由于困守京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者饱谙世态炎凉、人情反复的滋味,故愤而为此诗。
诗何以用“贫交”命题?这恰如一首古歌所谓:“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贫贱方能见真交,而富贵时的交游则未必可靠。诗的开篇“翻手为云覆手雨”,就给人一种势利之交“诚可畏也”的感觉。得意时便如云之趋合,失意时便如雨之纷散,翻手覆手之间,忽云忽雨,其变化迅速无常。“只起一语,尽千古世态。”(浦起龙《读杜心解》)“翻云覆雨”的成语,就出在这里。所以首句不但凝炼、生动,统摄全篇,而且在语言上是极富创造性的。
虽然世风浇薄如此,但人们还纷纷恬然侈谈交道,“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轲湛(沉)七族”,“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刘峻《广绝交论》),说穿了,不过是“贿交”、“势交”而已。次句斥之为“纷纷轻薄”,谓之“何须数”,轻蔑之极,愤慨之极。寥寥数字,强有力地表现出作者对假、恶、丑的东西极度憎恶的态度。
这黑暗冷酷的现实不免使人绝望,于是诗人记起一桩古人的交谊。《史记》载,管仲早年与鲍叔牙游,鲍知其贤。管仲贫困,曾欺鲍叔牙,而鲍终善遇之。后来鲍事齐公子小白(即后来齐桓公),又荐举之。管仲遂佐齐桓成霸业,他感喟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鲍叔牙待管仲的这种贫富不移的交道,岂不感人肺腑。“君不见管鲍贫时交”,当头一喝,将古道与现实作一对比,给这首抨击黑暗的诗篇添了一点理想光辉。但其主要目的,还在于鞭挞现实。古人以友情为重,重于磐石,相形之下,“今人”之“轻薄”益显。“此道今人弃如土”,末三字极形象,古人的美德被“今人”象土块一样抛弃了,抛弃得多么彻底呵。这话略带夸张意味。尤其是将“今人”一以概之,未免过情。但惟其过情,才把世上真交绝少这个意思表达得更加充分。
此诗“作‘行’,止此四句,语短而恨长,亦唐人所绝少者”(见《杜诗镜铨》引王嗣奭语)。其所以能做到“语短恨长”,是由于它发唱惊挺,造形生动,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
(周啸天)
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
交河几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
何由却出横门道。
是何意态雄且杰,骏尾萧梢朔风起。毛为绿缥两耳黄,
眼有紫焰双瞳方。矫矫龙性合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
伊昔太仆张景顺,监牧攻驹阅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
别养骥子怜神俊。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尽下。
故独写真传世人,见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
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
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
万草千花动凝碧。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
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春天衣著为君舞,
蛱蝶飞来黄鹂语。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照日宜轻举。
香汗轻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许。君不见才士汲引难,
恐惧弃捐忍羁旅。
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
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
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
稚子无忧走风雨。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
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
残花烂熳开何益。篱边野外多众芳,采撷细琐升中堂。
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轗轲,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赏析】 根据诗人的自注,这首诗是写给好友郑虔的。郑虔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的诗、书、画被玄宗评为“三绝”。天宝初,被人密告“私修国史”,远谪十年。回长安后,任广文馆博士。性旷放绝俗,又喜喝酒。杜甫很敬爱他。两人尽管年龄相差很远(杜甫初遇郑虔,年三十九岁,郑虔估计已近六十),但过从很密。虔既抑塞,甫亦沉沦,更有知己之感。从此诗既可以感到他们肝胆相照的情谊,又可以感到那种抱负远大而又沉沦不遇的焦灼苦闷和感慨愤懑。今天读来,还使人感到“字向纸上皆轩昂”,生气满纸。
全诗可分为四段,前两段各八句,后两段各六句。从开头到“名垂万古知何用”这八句是第一段。
第一段前四句用“诸公”的显达地位和奢靡生活来和郑虔的位卑穷窘对比。“袞袞”,相继不绝之意。“台省”,指中枢显要之职。“诸公”未必都是英才吧,却一个个相继飞黄腾达,而广文先生呢,“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那此侯门显贵之家,精粮美肉已觉厌腻了,而广文先生连饭也吃不饱。这四句,一正一衬,排对鲜明而强烈,突出了“官独冷”和“饭不足”。后四句诗人以无限惋惜的心情为广文先生鸣不平。论道德,广文先生远出羲皇。论才学,广文先生抗行屈宋。然而,道德被举世推尊,仕途却总是坎;辞采虽能流芳百世,亦何补于生前的饥寒啊!
第二段从“广文先生”转到“杜陵野客”,写诗人和郑广文的忘年之交,二人象涸泉的鱼,相濡以沫,交往频繁。“时赴郑老同襟期”和“得钱即相觅 ”,仇兆鳌注说,前句是杜往,后句是郑来。他们推心置腹、共叙怀抱,开怀畅饮,聊以解愁。
第三段六句是这首诗的高潮,前四句樽前放歌,悲慨突起,乃为神来之笔。后二句似宽慰,实愤激。司马相如可谓一代逸才,却曾亲自卖酒涤器;才气横溢的杨雄就更倒霉了,因刘棻得罪被株连,逼得跳楼自杀。诗人似乎是用才士薄命的事例来安慰朋友,然而只要把才士的蹭蹬饥寒和首句“诸公袞袞登台省”连起来看,就可以感到诗笔的针砭力量。
末段六句,愤激中含有无可奈何之情。既然仕路坎坷,怀才不遇,那么儒术又有何用?孔丘盗跖也可等量齐观了!这样说,既评儒术,暗讽时政,又似在茫茫世路中的自解自慰,一笔而两面俱到。末联以“痛饮”作结,孔丘非师,聊依杜康,以旷达为愤激。
诸家评本篇,或说悲壮,或曰豪宕,其实悲慨与豪放兼而有之,而以悲慨为主。普通的诗,豪放易尽(一滚而下,无含蓄),悲慨不广(流于偏激)。杜诗豪放不失蕴藉,悲慨无伤雅正,本诗可为一例。
首段以对比起,不但挠直为曲,而且造成排句气势,运笔如风。后四句两句一转,愈转感情愈烈,真是“浩歌弥激烈”。第二段接以缓调。前四句七言,后四句突转五言,免去板滞之感。且短句促调,渐变轩昂,把诗情推向高潮。第三段先用四句描写痛饮情状,韵脚换为促、沉的入声字,所谓“弦急知柱促”,“慷慨有余哀”也。而语杂豪放,故无衰飒气味。无怪诗评家推崇备至,说“清夜以下,神来气来,千古独绝。”“清夜四句,惊天动地。”(见《唐宋诗举要》引)但他们忽略了“相如逸才”、“子云识字”一联的警策、广大。此联妙在以对句锁住奔流之势,而承上启下,连环双绾,过到下段使人不觉。此联要与首段联起来看,便会觉得“袞袞诸公”可耻。岂不是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吗?由此便见得这篇赠诗不是一般的叹老嗟卑、牢骚怨谤,而是伤时钦贤之作。激烈的郁结而出之以蕴藉,尤为难能。
末段又换平声韵,除“不须”句外,句句用韵,慷慨高歌,显示放逸傲岸的风度,使人读起来,涵泳无已,而精神振荡。
(曹慕樊)
世上儿子徒纷纷。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
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只今年才十六七,
射策君门期第一。旧穿杨叶真自知,暂蹶霜蹄未为失。
偶然擢秀非难取,会是排风有毛质。汝身已见唾成珠,
汝伯何由发如漆。春光澹沱秦东亭,渚蒲牙白水荇青。
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搅离思花冥冥。酒尽沙头双玉瓶,
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
所思碍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浐路,迢迢天汉东。
愿腾六尺马,背若孤征鸿。划见公子面,超然欢笑同。
奋飞既胡越,局促伤樊笼。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
嘉蔬没混浊,时菊碎榛丛。鹰隼亦屈猛,乌鸢何所蒙。
式瞻北邻居,取适南巷翁。挂席钓川涨,焉知清兴终。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赏析】 (一)
这首诗,是杜甫在天宝十一载(752)秋天登慈恩寺塔写的。慈恩寺是唐高宗作太子时为他母亲而建,故称“慈恩”,建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塔是玄奘在永徽三年(652)建的,称大雁塔,共有六层。大足元年(701)改建,增高为七层,在今西安市东南。这首诗有个自注:“时高適、薛据先有此作。”此外,岑参、储光羲也写了诗。杜甫的这首是同题诸诗中的压卷之作。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诗一开头就出语奇突,气概不凡。不说高塔而说高标,使人想起左思《蜀都赋》中“阳鸟回翼乎高标”句所描绘的直插天穹的树梢,又想起李白《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句所形容的高耸入云的峰顶。这里借“高标”极言塔高。不说苍天而说“苍穹”,即勾画出天象穹窿形。用一“跨”字,正和“苍穹”紧联。天是穹窿形的,所以就可“跨”在上面。这样夸张地写高还嫌不够,又引出“烈风”来衬托。风“烈”而且“无时休”,更见塔之极高。“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二句委婉言怀,不无愤世之慨。诗人不说受不了烈风的狂吹而引起百忧,而是推开一步,说自己不如旷达之士那么清逸风雅,登塔俯视神州,百感交集,心中翻滚起无穷无尽的忧虑。当时唐王朝表面上还是歌舞升平,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对烈风而生百忧,正是感触到这种政治危机所在。忧深虑远,为其他诸公之作所不能企及。
接下去四句,抛开“百忧”,另起波澜,转而对寺塔建筑进行描绘。“方知”承“登兹”,细针密线,衔接紧凑。象教即佛教,佛教用形象来教人,故称“象教”。“冥搜”,意谓在高远幽深中探索,这里有冥思和想象的意思。“追”即“追攀”。由于塔是崇拜佛教的产物,这里塔便成了佛教力量的象征。“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极赞寺塔建筑的奇伟宏雄,极言其巧夺天工,尽人间想象之妙。写到这里,又用惊人之笔,点明登塔,突出塔之奇险。“仰穿龙蛇窟”,沿着狭窄、曲折而幽深的阶梯向上攀登,如同穿过龙蛇的洞穴;“始出枝撑幽”,绕过塔内犬牙交错的幽暗梁栏,攀到塔的顶层,方才豁然开朗。此二句既照应“高标”,又引出塔顶远眺,行文自然而严谨。
站在塔的最高层,宛如置身天宫仙阙。“七星在北户”,眼前仿佛看到北斗七星在北窗外闪烁;“河汉声西流”,耳边似乎响着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银河既无水又无声,这里把它比作人间的河,引出水声,曲喻奇妙。二句写的是想象中的夜景。接着转过来写登临时的黄昏景色。“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交代时间是黄昏,时令是秋季。羲和是驾驶日车的神,相传他赶着六条龙拉着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跑。作者在这里驰骋想象,把这个神话改造了一下,不是六条龙拉着太阳跑,而是羲和赶着太阳跑,他嫌太阳跑得慢,还用鞭子鞭打太阳,催它快跑。少昊,传说是黄帝的儿子,是主管秋天的神,他正在推行秋令,掌管着人间秋色。这两句点出登临正值清秋日暮的特定时分,为下面触景抒情酝酿了气氛。
接下去写俯视所见,从而引起感慨,是全篇重点。“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诗人结合登塔所见来写,在写景中有所寄托。秦山指终南山和秦岭,在平地上望过去,只看到青苍的一片,而在塔上远眺,则群山大小相杂,高低起伏,大地好象被切成许多碎块。泾水浊,渭水清,然而从塔上望去分不清哪是泾水,哪是渭水,清浊混淆了。再看皇州(即首都长安),只看到朦胧一片。这四句写黄昏景象,却又另有含意,道出了山河破碎,清浊不分,京都朦胧,政治昏暗。这正和“百忧”呼应。《通鉴》:“(天宝十一载)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杜甫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有百忧的感慨。
以下八句是感事。正由于朝廷政治黑暗,危机四伏,所以追思唐太宗时代。“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塔在长安东南区,上文俯视长安是面向西北,现在南望苍梧,所以要“回首”。唐高祖号神尧皇帝,太宗受内禅,所以称虞舜。舜葬苍梧,比太宗的昭陵。云正愁,写昭陵上空的云仿佛也在为唐朝的政治昏乱发愁。一个“叫”字,正写出杜甫对太宗政治清明时代的深切怀念。下二句追昔,引出抚今:“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瑶池饮,《穆天子传》卷四,记周穆王“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列子·周穆王》称周穆王“升昆仑之丘”,“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乃观日之所入”。这里借指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饮宴,过着荒淫的生活。日晏结合日落,比喻唐朝将陷入危乱。这就同秦山破碎四句呼应,申述所怀百忧。正由于玄宗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李排抑贤能,所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贤能的人才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排斥,只好离开朝廷,象黄鹄那样哀叫而无处可以投奔。最后,诗人愤慨地写道:“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指斥那样趋炎附势的人,就象随着太阳温暖转徙的候鸟,只顾自我谋生,追逐私利。
全诗有景有情,寓意深远。钱谦益说:“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漂摇崩析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这就说明了全篇旨意。正因为如此,这首诗成为诗人前期创作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作者:周振甫
(二)
杜甫也写现实的情事,在现实的情事之中如何看杜甫的象喻性?下面我们再讲他的一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诸公”,是杜甫一些朋友。“慈恩寺塔”就是西安市的大雁塔,据说是唐高宗为纪念他的母亲而建造,所以取名“慈恩”。这首诗有一个原注说,“时高适、薛据先有作”。其实,当时登塔而且写过诗的除了高适、薛据,还有岑参和储光羲。岑参的“参”字,有不同的读音。由于孔子的学生曾参的“参”读作“深”,所以西方很多人在翻译的时候都把岑参的“参”也拼成“深”的读音。可是根据考证,这个字不应该读作“深”而应该读作“餐”。因为岑参曾写文章说他的祖先有很多人都参与公卿之位,他们家里希望他也能够参与公卿之位,所以取名岑参。这是我们顺便提到的。岑参、高适都是唐代有名的诗人,他们每个人都写了登塔的诗,所以你就要比较了。同样写山,王维写什么样的山,杜甫写什么样的山,更妙的是陶渊明写什么样的山。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诗》),于是后来辛弃疾就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的词说,“岁岁有黄菊,千载一东篱。悠然政须两字,长笑退之诗”。唐朝的韩愈韩退之写了一首《南山诗》,共两百多句,押的是上声“有”韵,用的都是希奇古怪的字,全诗都在描写都在堆砌。可人家陶渊明也是写南山却根本就没有那一大片的描写,人家就是抓住了“悠然”两个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得多么好!每一年都有黄菊花开,但千载之中把黄菊和南山写得如此悠然的,不是只有一个陶渊明吗?陶渊明的诗真的是好,你看他写春天:“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那种生命,那种自然,不像杜甫这样逞气使力,而自有一种精神上非常高妙的境界。所以这诗人与诗人之间真的是大不相同的。那我们现在说的是杜甫的诗,我们说他在写实之中有“象喻”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诗不像那“鱼跃练川抛玉尺”只写耳目的知觉,他的诗里边有他的志意和理念,是他整个儿的人格、心灵的涌现,因此就有了那更高一层的“象喻”的性质。《杜诗详注》在这首诗的后边引了清朝钱谦益的评论说:“同时诸公登塔,各有题咏。薛据诗已失传;岑、储两作,风秀熨贴,不愧名家;高达夫出之简净,品格亦自清坚。少陵则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矣。”其实就登慈恩寺塔而言,岑参的诗写得也是不错的,比如他的开头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他说这慈恩寺塔从平地涌出来,孤立直耸,好像一直插入了天宫。他说我登上慈恩寺塔向下观望,就像是在尘世之外临望尘世;循着塔的阶梯一层一层向上走,觉得似乎走在虚空之中。他说这座高塔压在大地上,那种峥嵘的样子简直是鬼斧神工,人怎么有力量造出这样的塔来!他说这塔四面的四角,好像把太阳都可以阻止住;这塔七层的塔顶已经接近了天空的苍穹。我们在地面上要仰视那高飞的鸟,可是到了慈恩寺塔上一看,那些高飞的鸟都在你脚底下。我们低下头来,就可以听见高空中大风的声音。总而言之,岑参这首诗写得也很有气象,但他通篇所写的,只不过是夸说这塔的高大神奇而已。那么杜甫和他有什么不同呢?好,我们现在就看杜甫这首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尧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高标”,是一个地方的很高的一个标识,你老远就看见它了。像世贸大楼本来在纽约是一个标识,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杜甫说,这慈恩寺塔高得一直插到天上去,而在这高塔之上,永远在刮着猛烈的大风,没有一个时辰是停止的。这个开头就跟别人不一样。像岑参的“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空”就只是写塔的高,而杜甫的“烈风无时休”有一种不平静的感觉。因此才引出下边的“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我不是那种对尘世漠不关心的怀有出世襟怀的高士,所以我登到这高塔上,感觉那大风的强烈,就引起了我心中很多的忧虑。“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的“象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宗教常常是以形象来吸引和感动人的,像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十字架、圣像,像佛教的佛像和壁画,所以他称象教。塔是佛教的塔,杜甫说我现在看到这个塔才知道佛教的力量,它竟可以一直插入上天,直通冥冥之中的那些不可知的东西——也就是说通向天地鬼神等超乎现实的事物。“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龙蛇窟”是指这个塔的里面,因为在塔里面一层层向上爬,总是要盘旋地像龙蛇似地旋转。“枝撑”,指塔的下边几层那些交错支撑的柱子,他说我向上爬了好久才爬过没有窗子的黑暗的底层,可以从塔的窗子里面探出头来看一看。看见了什么?看见“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北斗七星就在窗外,好像都听见天上的银河流动的声音了。——这也是写塔的高。“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羲和”是给太阳赶车的神,他用鞭子赶着太阳的车走得那么快,马上就要到日暮了。“少昊”是秋天的神,现在他已经在行使行他秋天的节令。这是说什么?“羲和鞭白日”是太阳的下沉,“少昊行清秋”是一年的将尽,这都是从他的“登兹翻百忧”引出来的。那么他忧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已近日暮?是什么东西已到了秋天?这他都没有说。他说他看到“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这本来也是登塔下望的写实。秦地多山,你在平地上看都是整体的大山,可是你在高塔上面向下看,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许多山头,所以是“秦山忽破碎”。“泾渭”是泾水和渭水,这两条水清浊分明。可是你登在高塔上看,这清水和浊水就分不出来了。在玄宗天宝的时代,战乱已经快要起来了。当大家都还没有看到这危险,都还沉醉于盛世游乐的时候,杜甫以他诗人的敏感已经预见到了乱离之将至。唐玄宗任用杨国忠,任用李林甫,朝廷里边连善恶贤愚都不能够分辨了,而朝廷外边的战乱也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写的都是现实景物,但现实景物里面已经让我们联想到当时那个时代的政局。“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仍是从塔上下望。他说我低头看一看,整个大地一片烟雾茫茫,什么地方是长安城的所在已经分辨不出来了。这很像《长恨歌》上所说的,“回头下望尘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于是下面他说,“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虞舜”,指的是唐太宗。舜是受了尧的禅让,而唐太宗是受了他父亲李渊的禅让,所以以“虞舜”喻之。太宗时代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然而“苍梧”是舜所葬的地方,在这里是暗指唐太宗的昭陵。其实,这也是写登塔远望所见。他说在高塔上遥望昭陵的方向,只能看见一片一片的惨淡的白云。但这景物的描写令人联想到:唐太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美好的往事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用了周穆王在西王母的瑶池饮宴的典故,而他所要反映的,其实是玄宗的求神仙和宠爱杨贵妃。“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是说,高飞的黄鹄都飞走了,它们哀鸣着飞到那里去?这也是塔上所见,可是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不接受高飞远举的黄鹄鸟,现在的世界接受的是什么?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你看一看眼下一般的这些个人,他们就像追随太阳的鸿雁,哪里温暖就到哪里去,哪里有粮食就到哪里去。所有的人都是短视的,都是追求现实功利的,哪一个人有黄鹄那样高远的追求?“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大家都只谋求自家的温饱,可是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我们的理想怎么办呢?这就是杜甫的诗跟一般人的诗之不同。他的志意和他的理念都融入了他所写的景物之中,所以虽然是写实,但很多地方都有他的象喻性。
作者:叶嘉莹
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
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
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可论。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
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
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
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
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
钓竿欲拂珊瑚树。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
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
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
蔡侯静者意有馀,清夜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
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赏析】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奭《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琎之。他于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开宝五载適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琎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琎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琎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知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情绪欢乐。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样而又统一,构成一个整体,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何国治)
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
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
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昳荡荡,
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
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波涛万顷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
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主人锦帆相为开,
舟子喜甚无氛埃。凫鹥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
沈竿续蔓深莫测,菱叶荷花静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
下归无极终南黑。半陂已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
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此时骊龙亦吐珠,
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少壮几时奈老何,
向来哀乐何其多。
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仿像识鲛人,空蒙辨鱼艇。
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崷崒增光辉,乘陵惜俄顷。
劳生愧严郑,外物慕张邴。世复轻骅骝,吾甘杂蛙黾。
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
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迥。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