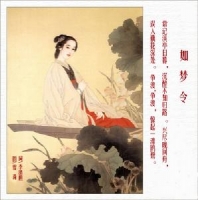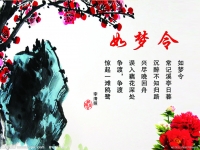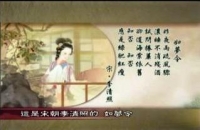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注释】 消:去除。
【赏析】 李清照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其词流传至今的只不过四五十首,但却“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这首《如梦令》,便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小词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令人玩味不已。
起首两句,如何理解颇有争议。盖推以事理逻辑:既然是“浓睡不消残酒”,又何以知道“昨夜雨疏风骤”,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其实对这两句词,是不能用生活中的简单事理去体会理解的,因为词人的本意实不在此,而是通过这两句词表达无限的惜花之情。大凡惜花的诗词都言及风雨。白居易《惜牡丹二首》诗:“明朝风起花应尽,夜惜衰红把火看。”冯延巳《长相思》词:“红满枝,绿满枝,宿雨厌厌睡起迟。”周邦彦《少年游》词:“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花在风雨中零落,这层意思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说“浓睡不消残酒”也是写惜花之情,恐怕就不太容易理解了。不过只要多读些前人写的惜花诗词,也就不难体会了。杜甫《三绝句》诗:“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韦庄《又玄集》卷下录鲍征君(文姬)《惜花吟》诗:“枝上花,花下人,可怜颜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尽此花下饮,莫待春风总吹却。”这些诗句正可用来作为“浓睡不消残酒”的注脚。易安在其咏红梅的《玉楼春》词中所云:“红酥肯放琼苞碎,探著南枝开遍未。……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亦可视为对“浓睡”一句的自注。这句词的辞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翌日晨起宿酲尚未尽消,但在这个辞面的背后还潜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酒醉是因为惜花。这位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漱玉词》中曾多处写到饮酒,可见易安居士是善饮的。善饮尚且酒醉而致浓睡,一夜浓睡之后酒力还未全消,这就不是一般的过量了。我们只要思索一下词人为什么要写“浓睡不消残酒”这句词,得到的回答只能是“惜花”。就这句词的立意而言,与上引杜甫和鲍文姬的诗句都是同一机杼,并无二致。但易安的高处正在于不落窠臼,独辟蹊径。一旦领悟了潜藏在“浓睡不消残酒”背后的这层“惜花”之意,那么对以下数句的理解也就“水到渠成”了。
接下去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理的必然反映。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晓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海棠。词人情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揉损,窗外定是残红狼藉,落花满眼,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试”字,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落花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相比之下,周邦彦《少年游》:“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便显得粗俗不堪,味同嚼蜡了。“试问”的结果如何呢?──“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之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一个“却”字,既表明侍女对女主人委曲的心事毫无觉察,对窗外发生的变化无动于衷,也表明词人听到答话后感到疑惑不解。是啊,“雨疏风骤”之后,“海棠”怎会“依旧”呢?这就非常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两句。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诘,也象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应是”,表明词人对窗外景象的推测与判断,口吻极当。因为她毕竟尚未亲眼目睹,所以说话时要留有余地。同时,这一词语中也暗含着“必然是”和“不得不是”之意。海棠虽好,风雨无情,它是不可能长开不谢的。一语之中,含有不尽的无可奈何的惜花情在,可谓语浅意深。而这一层惜花的殷殷情意,自然是“卷帘人”所不能体察也无须更多理会的,她毕竟不能象她的女主人那样感情细腻,那样对自然和人生有着更深的感悟。这也许是她所以作出上面的回答的原因。末了的“绿肥红瘦”一语,更是全词的精绝之笔,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绿”代替叶,“红”代替花,是两种颜色的对比;“肥”形容雨后的叶子因水份充足而茂盛肥大,“瘦”形容雨后的花朵因不堪雨打而凋谢稀少,是两种状态的对比。本来平平常常的四个字,经词人的搭配组合,竟显得如此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这实在是语言运用上的一个创造。由这四个字生发联想,那“红瘦”不正表明春天的渐渐消逝,而“绿肥”象征着绿叶成荫的盛夏的即将来临吗?这种极富概括性的语言,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此语甚新。”《草堂诗余别录》评:“结句尤为委曲精工,含蓄无穷意焉。”看来皆非虚誉。
这首小词,只有短短六句三十三言,却写得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表达得摇曳多姿。《蓼园词选》云:“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可谓的评。(李汉超刘耀业)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五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一九三零年一月
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
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注释】 沉沉:又作沈沈
①遥夜:长夜。沉沉:深沉,寂静。
②驿亭:古代旅途供过往官员差役休息、换马处。
③梦破:梦醒:鼠窥灯:老鼠胆怯地望着灯盏,想偷吃灯油。
④侵被:透进被窝。
【赏析】 秦观一生,因涉党祸屡遭贬谪。宋哲宗赵煦绍圣三年(1096),词人自处州再贬郴州。这首小令,作于是年冬季赴郴州途中。词借描写夜宿驿亭苦况诉行旅艰辛。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夜色苍茫,沉沉如水,寒风阵阵紧吹,吹过这古道的驿亭和暂歇驿亭的行人。“如水”、“风紧”,以其重量感造就出一种强烈的空间的挤压感。似一股无形的力在肆意捏挤,取境也随之由远拉近,凸出一个特写:驿亭紧闭的大门。那般突兀,那么引人注目,空间的闷压至最大限度。作为一个审美对像,“驿亭深闭”既是现实的意象,也是心灵的象征啊!在新旧党争的政局变幻中,词人无辜受害,如今身坐党籍,艰难跋涉在贬途中,身心憔悴,纵有满肚的不平又怎敢铺展?词人的心情从这纯粹的景语中已暗示出几分。
“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驿亭的深闭阻隔了外界的喧嚣,寂寥之中劳累的词人也开始悄然入梦。诗人梦到了什么?渺然不可追考,也无须乎落实。描写梦境,寄寓悲思之作,几乎贯串了词人的一生。这是由他一生沉郁,特别是政治上遭打击后远谪蛮荒,痛感人生无望的独特心境所决定的。如“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梦扬州》)、“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阮郎归》)、“一觉相思梦回处,连宵雨,更那堪,闻杜宇”(《夜游宫》)等等。“古之伤心人也”惟有希冀一个个好梦消释现实中无法消释的无限悲慨!然而“梦破”二字,又流露出多少烦恼意绪。它推动着词意的递进:心魂从梦中归来,往事在梦中幻灭,萦怀往复,给全词带来了更为浓重的悲剧气氛。接着,作者通过醒后之所见、所感再加渲染。“梦破”大约与鼠有关。老鼠半夜出来偷油吃,不免就弄出些声响来了,鼠惊人梦,人醒鼠也当惊,可它并未立即逃藏起来,还垂涎于那盏灯油吧!又不免惶恐地窥觑着这盏昏暗的油灯和惊梦初醒之人。一个“窥”字,用得十分传神。“鼠”之敢对人“窥灯”,可见驿亭之荒凉破败。唐代杜甫《北征》中写旅途所见:“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野鼠见人时不惊不藏,竟交其前足如人之拱手,自立于乱穴中间。见出荒山之无人、战争的创伤。诗心词境,传神而妙。再说梦回之后的词人。孤灯照壁,再也无法成眠,只觉得薄薄的衾被已挡不住寒意侵身,一定是外面下了霜,才送来这寒气逼人吧!这两句写所见、所感,驿亭之简陋,词人之孤独冷寂,不言而喻。王国维说秦观晚期词境变而为“凄厉”,此其一斑。
“无寐,无寐”两次的重复,是词中唯一直抒作者感叹之笔。二词叠用,除了协律,还突出了词人多少烦闷、无奈、凄苦的心绪……是啊!如果不是心中那水一样浩茫梦一般绵邈的愁情的折磨,哪里会如此夜难再成眠?身心都极需休憩的词人又何苦要这般和自己过不去呢?
好梦既无从续起,不起来又怎么样呢?这自然是第二天早晨的事了,时光总算暗暗在流转。“被冷香销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李清照《念奴娇》)。门外,马儿嘶鸣,是在催人上路啊。从听觉感受中暗示黎明的到来。熬过了大半夜不眠的词人,又该怀着一般什么样的心情,拖着疲累的身躯,开始又一天的旅途奔劳?
细味全词,词人高明之处在于善用极省净的笔墨(共33字),描绘了一个典型环境──古代简陋的驿馆。鼠之扰闹,霜之送寒,风声阵阵,马嘶人起,如耳闻目睹,俱以白描手法出之。毫无缘饰,不用替代,只坦直说出,却别有一番感人的力量。这是由于词人下笔精到,所写驿馆种种景况,无不蕴含着天涯飘泊的旅思况味,婉曲地传出了郁积于心的人生不平──遭谗受害,屡遭贬谪,岁暮飘零如是!可见白描手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描写之逼真,尤重在情味之活现,使人读之有一目了然之快意,味之而作深长之联想。读秦观此词,读者或当获得吟赏之回味之快意?(林家英、陈桥生)
【赏析2】
本篇是词人贬谪途中,夜宿寒冷荒僻的驿舍所作。借写夜宿驿舍的况味,诉说旅途的艰辛。写的是在漫漫的长夜里,霜风紧吹,饥鼠窥灯,弄得无法安睡。等到天刚破晓,门外驿马长鸣,人声嘈杂,艰苦的长途跋涉又将开始。通过环境的描写和景物的烘托,寓情于景,把旅人的艰辛和谪贬者的失意表达得真切感人。词作短小而精练,也很有生活气息。
多点金釭红蜡。
取酒拥丝簧,迎取轻盈桃叶。
桃叶。
桃叶。
唱我新歌白雪。
心似丁香百结。
不见谪仙人,孤负梅花时节。
愁绝,愁绝,
江上落英如雪。
和我影儿两个。
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
无那。无那。
好个恓惶的我。
【赏析】 《全宋词》收录了向滈作品四十三首。这些词除个别篇章之外,全都是叙写别情和孤独处境的。由此可见作者长期为离愁所缠绕的生活与心理,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首《如梦令》中的情绪绝非无病呻吟或故作多情者可以比拟的。
羁旅当然是愁苦、寂寥的。不过向滈的孤独似乎在离家别亲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向滈出生时正当南宋初期,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小朝廷采承妥协退让的国策;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受到创伤而更加强烈,因而,要求驱逐金、收复失地的呼声高涨。为了给投降路线扫平障碍,统治阶级于是大规模地镇压抗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那时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眼看国力日衰,痛感空有报国之志而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为个人渺茫的前途所烦愁,因此多半处在矛盾与伤感之中。向滈在一首《临江仙》中说:“治国无谋归去好,衡门犹可栖迟”,透露的正是爱国被冷落后的凄凉。心情据此,我们认为这阕《如梦令》抒写的恓惶情绪中也包含有对时代苦闷的色彩。
李白《月下独酌》中有一首也写作者的孤独,全诗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作者、影子、月亮在一起,又歌、又舞、又饮,颇有一点热闹气氛。向滈此词写灯、影、人相伴,大半是受了李诗的影响,但两者的情调却是不一样的。李白遇上的是唐帝国最强烈的时,他的个性既旷达不羁又积极向上,因而他的诗总是进取的,活泼的。向滈则不然,生活在那个令人空闷的时代里,加上自己又长年同亲人隔绝,所以他不可能象李白那样即使在孤独之中也充满着希望与活力。比如在这首词中就只有“灯、”我“和”影儿“,无月,无酒,自然也无歌,无舞。同样是写孤独,但向滈笔下却处处是绝望的影子。
这首词构思新颖,作者把“影儿”写入作品,用以反衬自己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这既避免了纯说愁苦的单调,又使词篇更具形象性,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词篇用“谁伴”二字开头,一上来就突出了作者在窗前灯下为孤独而久久苦恼的情态,由“谁”字发问,便把读者引向对形象搜索与寻求。果然在问了千万声“谁伴”之后,作者终芋发现了只有“影儿”相伴。虽有“影儿”相伴。可是,就是这无言的、难以发现的影儿,况且也并不能“伴”得持久:“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找到影儿作伴,为的是给自己寻求安慰,谁料灯灭后连“影儿”不复存在了,加倍衬出了自己的孤单,于是便喊出:“无那,无那,好个栖惶的我”(无那,即无奈的意思)。影儿的恰妙运用,使抽象的愁思更为具体,行文也更生动。与晏几道《阮郎归》词中“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之句,可以先后媲美。
自然,这阕词的新颖构思,还可以从结构的安排上看出来。词作从独坐开始,用唯影相伴表现作者的孤单,这可以算是诗文中的佳境。接着说“影儿把人抛躲”,则将旧境翻新,感情也被深化到了顶点。
向滈词以通俗、自然取胜。这首《如梦令》语言平易,即使是今天的读者读他的诗,也很少有难解的词句。从构思方面讲,它虽然有新颖的一面,但同时又不存在着做作的痕迹。自个儿静静地坐在窗下,相伴的当然只有影儿了。到了“灯烬欲眠时”,当然影儿也就不见了。到了结尾的地方,实际上是照直说出了问题的原委。新颖与自然本是两种难以调和的风格,向滈却能把它们统一在一首小词中,这是很不容易的。
赏析2.
词人静夜独坐,顾影自盼,颇觉寂寞孤独,终至感到“凄惶”。开头两句,明白如话,述说自己临窗独坐,只有自己的影儿相伴。在宋词中写夜晚独处的作品不胜枚举,著名的如秦观有一首《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通篇以白描手法写景,以气氛烘托来衬托人物的寂寞。本词与秦观的《如梦令》题材相同,但在写法上另辟新径,分明是一个人在万籁俱寂时临窗独坐,却偏说是“两个”。夜晚百无聊赖剩吹阶约旱挠岸呛茏匀坏氖拢哟巳氪剩倚吹泌缎秤腥ぃ萑凰挡簧厦钍峙嫉茫部晌焦顾计嫣兀朴诓蹲揭帐跣蜗蟆?o:p>
“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烬”,火余下的灰,“灯烬”即灯灰,这儿作动词,就是“灯灭”。灯灭了,要睡觉了,影儿也不见了;“抛躲”二字,把影儿的自然消失说成了主动行为,与首二句贯通一气,“影”也就更加人格化了。以下连用两个“无那”,进一步把词人孤独寂寞无法排解的情绪表达出来。“好个凄惶的我”,尾句直抒胸臆,自叹“凄惶”,全词的气氛也由冷清、寂廖转为哀惋、悲凉了。
本词虽无深远的意境,但通篇以质直的口语,状绘自我,于平淡中见新奇,读之饶有兴味,称得起一首独具特色的小令。
向滈的《如梦令》共有八首,这一首曾误传为大词人李清照的作品(见《续选草堂诗余》卷上),这也多少可以从侧面说明这首小令的艺术成就。(王方俊)
谁信一筹一画。
相送到矾园,赢得泪珠如泻。
挥洒。挥洒。
将底江州司马。
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
曾记。
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
【白话文】 说是梨花,但不是
说是杏花,也不是
颜色红白相间,此花的风韵别具一格,超凡脱俗!
还记得吗?在武陵的那一醉?(这就是《桃花源记》武陵源的桃花阿!)
【注释】 “白白与红红”,一树花分红、白两色,高标逸韵,独特别致,作者正是以这“别是东风情味”的红白桃花自况。这首词还用了映衬对比写法,以梨花之白、杏花之红既映衬又对比,赞美红白桃花独标一格,超拔于春天群芳之上
“人在武陵微醉”一句用了“武陵人”的典故,出自晋代文学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由此可知这首宋词写的是桃花。
燕尾点波绿皱。
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
依旧,依旧,
人与绿杨俱瘦。
【赏析】 这首词诸本题作“春景”。乃因伤春而作怀人之思。
首二句直笔写春。莺歌燕舞,花红水绿,旨在突出自然春光之美好。三、四句却转作悲苦语。化用李璟《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春光明媚,本应产生舒适欢畅之感受,而女主人公何以有这般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是为点题之笔。柳絮杨花,标志着春色渐老,春光即逝。同时也是作为别情相思的艺术载体。飞絮蒙蒙,是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念人之情。因为有那刻骨深情的相思,所以忧思约带、腰肢瘦损。“人与绿杨俱瘦。”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感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含意自在其中。直让人想象到一幅花落絮飞,佳人对花兴叹、怜花自怜的图画。
词人之心,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展示流转在节序交替中的伤春念远之情。词从愉快之景象叙起,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愈为悲苦。然而词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衬的效果,甚而不惜极尽雕琢气力状物写景,终不免落于攻琢之痕。“溜”字本写花红之鲜艳欲滴,“皱”则欲状摹水波漾漪之态,亦不可谓不巧矣!然味之终觉神韵欠焉!究其原委,就在于它显得雕琢、吃力。正如其“天连芳草”句,如换“连”为“粘”,则失于穿凿矣!故《吹剑录》谓“莺嘴”二句:“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很多词评家们都恰切地指出了这一点:《草堂诗余》批曰:“琢句奇峭。”《弇州山人词评》评曰“险丽。”《古今词话词品》亦云:“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如此雕炼奇峭,有《粹编》本要以为此词乃黄庭坚所作,实在也是事出有因。
“诗缘情”,贵其感发之力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重其内在之情味意境。而由于诗、词体裁的限制,其用字造句,又特别讲究锤炼洗净。但是这种锤炼不是刻意地雕章琢句。其用心尽管良苦而出之必须自然,浑成无迹,顺手拈来,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秦观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程垓“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摊破江城子》)新鲜奇特,形象生动,各具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得其失,均当以审慎公允态度待之,不隐其得,不讳其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有益的。(陈桥生)
专下死功夫,悟得长生活计。
长生活计,收得精光神气。
【注释】 《鸣鹤余音》无名氏
睡起不胜情,行到碧梧金井。
人静,人静,风弄一枝花影。
【注释】 ①曾慥《乐府雅词》及黄升《花庵词选》以为曹组作。
②金井:雕饰华丽的井栏。
【赏析】 这首小令题为“春景”,情因景生。“风弄一枝花影”,以动写静,妙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