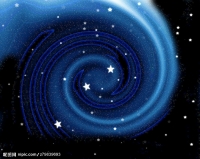很典型的日本现代派作品,颓废、堕落、幻觉、性爱、毒品、犯罪、同性恋,基本上人性的欲望都集合在了其中,被无止境的夸张放大,昏暗变态的描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恶心和压抑。女主角在分裂的人格中,和自己意识深处的多个自我进行对话,既是一种对自我心灵的不断探求,又形成一股死亡的力量将她引至毁灭。疯狂放纵的生活内容,在作者冷静理智的文字叙述下,变成一种奇特的冰火混合体,使读者在晕眩的阅读之后,还留有一点点清醒的意识,这是小说的最赞之处。自毁性的内容,没有毁灭文字,带着浓重毁灭色彩的文字,也没有毁灭读者,却是把现代都市里种种的毁灭基因,显性的或隐性的,赤裸裸的呈现于读者之前,并在毁灭中寻找生存下去的可能和意义。
我头一次看见那女孩时,她一边吃着沙拉一边在哭。那是一家在东京都内很有名的意大利餐厅,我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在这里打工做服务员。我在这里打工还不到三个月,就觉得有点厌烦。当初本想去俱乐部打工,可是父亲不准我去,他说如果要增加人生修行经验的话,还是去餐厅打工好。我打工并不是为了赚学费,而是想多赚点钱享乐一下。人生哪需要什么修行?因为我觉得人生很无聊。一听到“修行”两个字,我就会想起在瀑布下被水冲得嘴唇冻成紫色的小笨和尚,我脑子虽然不是很好,但我还不至于笨到去瀑布冲水。那样的修行根本就毫无意义。
我打工的这家餐厅位于青山,老板偶尔会在给青年人看的杂志上登广告,不过年轻客人好像并不多。我至今还没见过老板,听说他搞电脑软件进口生意赚了很多钱,为了少纳税才开了这家餐厅,他对意大利料理根本就是外行。主厨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在米兰住过三年,在芬兰住过五年,但做的都是些洗碗扫地的工作。我每次偷瞧厨房时,总看见他红着眼在煮通心面,也许做事认真的人很适合当意大利料理的厨师吧!
这家餐厅虽然大不受年轻人欢迎,而且价位很高,但每天晚上总是高朋满座。我想就算我赚了钱也不会来这么贵的餐厅吃饭。我一直梦想的是存些钱出国玩玩。那个女人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上,她边吃沙拉边安静地在哭。我以前很少看见客人哭。人们不是通常在分手时才哭吗?在这么高级的意大利餐厅谈分手的事,分手的悲伤就能减少一半吗?因分手而哭的人当中男女都有,但边哭边吃饭的只有女人,哭泣着的男人连场都不会喝。我们这些服务员都已被训练得面对这些客人时可以视而不见了。
她被一块儿用餐的中年男人欺负了。那女人看起来年龄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穿着绿色的套装,围了一条高级丝巾。虽然算不上是美女,但打扮得很优雅得体,是个上班族。虽然我也被训练得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耳朵就例外了,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那男人很过分。他大概有四十岁,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职员,从他的长相到穿着,能给的评价就是“平淡无奇”。他一进来我就觉得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当客人打开门进来时,我们都要用意大利语对客人说“欢迎光临!”就连面对日本客人也要讲意大利话。餐厅有些常客,可我觉得那些常客都像些白痴。
他们两人喝完白酒后,一切还好。后来男人说了些可恶的话。那种人三杯黄汤下肚后就是那个德性。我装作没看见,但耳朵却使劲地在听。他们两个人都在旅行社上班,同是春天新旅游计划方案的计划组成员。这个女的好像是小主管,男的似乎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
“一开始我就不愿意,可是科长都那么说了,我也没办法,总不能跟科长说不愿意吧!他说:‘组员全都是女孩子,会让你更年轻些。’被比我小两岁的上司那么说,真是太过分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和你这位组长一起吃饭,我就是要告诉你,对人不要太傲慢无理,知道吗?”
餐厅里很安静,那男人的声音显得很突出。他穿的西装看起来比别人差,我真的担心自己也像他一样,到了四十岁生活水平却这么差。
男人接着说;“我还是要恭贺你的亚洲之旅计划成功,可是早先是我提议举办澳洲、新西兰之旅的,然而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却没有列入我的名字,这也就算了,但是‘到澳洲去拖抱无尾能’可是我的点子,竟然被人盗用了,这算什么嘛?你们只是在利用我、使唤我罢了。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一个男人四十岁了还只是个小主任。虽然我是以顾问的名义加入你的小组,可当部长时,却没有我的份儿,不错,也许在你们眼里我是多余的,因为已经四十岁了,名片上的职务还只是个主任而已,但是我所说的那些事情并不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人本来就该分工合作,不是吗?这是你的第一次成功,工作能让你生存,所以就无视我的工作,反正我已经习惯人家这样对我了。计划中没有列上我的名字也无所谓,我可以不去想它。像你们这些女企划人员,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你是第一次,而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从头到尾就被人小瞧。我并不是无能,我的办公桌大小不也跟你一样吗!可是给科长作四十多分钟的报告时,却没听到你提我的名字。我知道,我了解科长的顾虑,还有你的心情,但我还是感到不平,我还是要跟你说。”
真是个无礼的家伙!男人一直在说,女人就一直哭。那种具男人一开始就打算把人骂哭的。女人很后悔似地点着头,她哭可能是因为情不自禁,觉得不好意思吧!那男人说话的口气很粗,虽然我们餐厅的常客中并没有上等人,但也从来没有像他那样的人。真想走过去摸他几拳。
“好了,我还是预祝你的计划成功,牢骚就到此为止,现在好好享受这一顿吧!”
男人看到女人哭了好像很高兴,然后这样说。接着那男人又说了很多恭维的话,女人面无表情只是“嗯”“啊”地回答。
当我把主莱烤羊肉串送到他们面前时,男人问女人:“你休假想去哪里旅行?黑木?还是瑞典?”
女人的回答叫人吃惊。
“我想去古巴!”
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
“幄?”男人显然也感到很惊讶,反问道。
“古巴?那里现在的情况不是有危险吗?”
女孩不回答,只是吃着肉,脸上的表情好像说:“如果是你的话,可能会死吧!”这下子我很难再装作若无其事了。当我收拾他们的碗盘时,手都有些抖了,其实我一直想去的国家正是古巴。
我跟同事打了声招呼,就马上奔出去追他们两人。他们正站在路口说话。
“要不要去喝一杯,半小时就行,我还有话想跟你说。”男人对女人说。
“不了,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只要半小时就行,你是不是怕我对你怎么样?”
“怎么会呢?”
“俄知道这里有一家小店的鸡尾酒很好喝,我前天就订好了位子了,走吧广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就半小时,我觉得对你过意不去,想赔罪。”
女人先注意到了我。我一直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可我穿的是白衬衫红领结的招待,所以显得很醒目。当我与女人四目相对时,我向她行了个礼说:
“谢谢你们到本店来用餐!”
男人用一副讨厌的表情看着我。
“你要干什么?”
在这时候出现,又站在这么冷的街头,我想那男人下一次肯定不会再到我们店里来了。我才不管他呢,他天生就是那种可以被小视的人。
“我是在刚才那个餐厅打工的学生。我也很想去古巴,现在打工就是为了赚旅费,可是因为我太忙,没时间找资料,如果你有空,可不可以告诉一些古巴的事?”
女人听我这么一说,显得有些疑惑的样子。我想至少也要拿到她的名片吧!正好前面来了辆出租车,我招手要它停下,“请上车!”我打开车门。女人一脸得救的表情,向身边的那个男人说了几句话便坐进出租车。
“请你给我一张名片可以吗?”
我来了个九十度鞠躬。
“你喜欢古巴的什么呢?”
女人坐进车后问我。
“有一位名叫菲比尔的歌手,我有他的CD,我实在太喜欢他了。”
“是吗?我不认识这个歌手。”
“我送你一盘他的录音带,他比唱爵士的值得贝克棒一万倍呢!”
女人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对着离去的出租车背影又行个大礼。我可不是要听她作旅游介绍的,我是想跟她一起去古巴。
“喂,你想干什么?”
那男人抓着我的肩膀。我贴近他的耳朵说:
“我讨厌你,地球上每个人都讨厌你!”
我甩开他的手,一口气跑回店里。
那个女人叫赤川美枝子。晚上回到家后,我边看着她的名片边听菲比尔的CD。我的老家在千叶县北方,爸爸是一家中药公司的老板,妈妈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哥哥是医生,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在国立大学读原子能专业。我的脑子并不差,可就是不爱读书。我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满二十岁的男人。很少有人知道我从小学起就有点自闭症倾向,我不知道怎样与人沟通,应该说是不会。上了高中后生活也没什么改变,但自闭症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上中学之前,我是个让学校头痛的学生,逃学、部车、交女朋友,只要是不会致死的坏事都干过。虽然这样,但我也读了不少书,所有刘!欧郎的书我都看过,可是从书中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直到上了高中后,认识了一个朋友叫纯一,他是个很开朗的人,但他也有和我一样的问题。和他交谈过后,我才知道并非只有我才有这种想法。我能知道这么多爵士歌手,也是他教我的。他的爸爸是建筑师,还是位欧美音乐唱片的收藏家。正因为这样,纯一才能懂得十六岁少年所不知道的很多知识。除了我和纯一以外,高中很少有人会欣赏欧美音乐。能认识纯一我感到很高兴,他教会了我许多事情,是他教我什么叫作“丰富的心”、“温柔体贴”、“生命的意义”、“充实感’、‘撼动”。这些东西就算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也都很缺乏吧!虽然现在高楼大厦已经取代了老式建筑,但是从前就缺乏的这些特质,至今依然欠缺。当人们不满越多、压力越多时,就更难体会这些境界。绝不要相信年长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直不能自觉的人更不能相信。
半年前逛唱片商店时,我发现了一张卖得只剩下最后一张的CD,封面上的画面吸引着我,那个人有股柔柔的自闭气质。这就是我和菲比尔的初次相遇。我从没听过古巴音乐,但菲比尔的声音深深地感动了我。听了第一首歌从个爱情故事》,不知不觉我党哭了出来,当时我就想,拥有如此美妙歌喉的歌手居住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那周的星期六和赤川美枝子通了电话,我和她约好到咖啡店见面。她头发梳得很整齐,还是穿着套装,系着那条丝巾。有一股莫名的寂寞写在她的脸上,当时我竟然有种想占有她身体的想法。
“你常在这里等人吗?”
她点了维也纳咖啡后,突然这样问我。
“不,这是第一次。”
我回答。这四天来我已经作好充分心理准备接受她的任何盘问,这大概是属于自闭症少年的一种习惯吧?但这是个让人感到悲伤的习惯。
“像赤川小姐这样的人很习惯这种地方吧?”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问题我早料到了。
“在我不懂的世界中拥有一份好工作,而且经常出国去玩…真是这样。”
“你看见我在餐厅里哭了?”
这也是我早就料到的问题。
“是!”
“没有客人会那样吧?”
“偶尔也会有人在餐厅里哭。”
“真的?”
“但没有人哭得像你那样。”
说完,赤川小姐笑了出来,然后叹了口气,表情又变得很沉静。
“那次是你救了我。”
我想现在有必要换话题了。
“对了,我可以向你请教一些古巴的事吗?”
当我说出古巴这两个字时,赤川美枝子的表情变得很复杂。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当她听到古巴时,应该是很高兴的表情,但她却没有,反而有点忧伤的样子。
“古巴……”她忧伤般地喃喃自语。我感觉到她很不想说,也不想听到古巴这两个字。我一直等她开口。我喝了一杯一千元的咖啡,虽然很贵,但确实是我喝过的咖啡中最好的。
“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她终于开口了。
“古巴嘉年华会期间在全国各地都有舞蹈公演,那都是强劲有力且美妙绝伦的舞蹈,有伦巴、芭蕾,还有现代舞,真的很叫人激动,于是我就追着表演团体到处跑。我喜欢上了一位舞蹈家。回到日本后,我邀请他到日本来玩,因为古巴人生活很苦,所以我买了很多东西给他。我很想跟他结婚,但我知道他只把我当成朋友而已。”
原来如此。我想那个舞蹈家一定是个黑人。
“我虽然一直想去古巴,但又很害怕再去,你懂我的心情吗?没有人能像我一样了解古巴舞蹈的美妙,也没有人像我一样愿意帮助他们。生长在富裕环境下的日本人是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贫困,就连我也不是很清楚。古巴和美国的关系闹僵后,经济遭到封锁,但古巴始终不肯向美国人低头道歉。说真的,就是到现在我还是很怕去古巴,你知道吗?”
她说了一些不在我设想之内的话题,叫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对她有股奇妙的好感。我们坐在豪华饭店的咖啡厅里,空间很宽敞,整体设计甚至服务员的都显得很优雅,服务员对客人的应对也很得体,客人的穿着品味也很高。为了不破坏这里的高雅气氛,出门前我还冲个澡,刮了胡子,头发也梳得很利索。可是,在我眼前的这位职业妇女还有我,幸福离我们还好远。在这看似令人满足的咖啡厅里却充满了一股寂寞感。
“我知道,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她忘了喝咖啡。也不看着我,只是冲着窗外说话。春日的夕阳似乎特别适合她,那地平线是橙色的,上面的天空一片粉红,好美的景色!但却总有点模糊不清。
“我真的很害怕再去古巴,那个舞蹈家好像有很多女朋友,因为他常常要到世界各地演出,所以可以认识许多女人,他现在好像和一个追到古巴的瑞士女人同居。一定是这样,我很害怕去面对这个事实。”
夕阳真美,我想。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她正将她最重要的秘密告诉我,可是我无法阻止她不说。
“不过古巴舞蹈真的很新鲜。我每年都会到纽约一次,去欣赏新舞蹈发布会上的演出。一看到古巴舞蹈,心中就会有股说不出的快乐感,它让我有新的生命刺激,每次都有奇妙的相会。我真的迷上了古巴舞蹈,不管是杂志还是电视,只要有关于古巴舞蹈的报道,我一定要看。真的很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中还是有股恐惧感。我很期待与新的古巴舞蹈相会的时刻,但又怕失去了它。失去他和失去古巴舞蹈是两码事,但我现在好像把它们混在一起了。”
我能理解她的心清,能让人真正沉迷的事情并不多。其实我也一样。
“赤川小姐!”我开口了,赤川小姐忧郁的脸从窗边转向了我。在夕阳的斜照下,那面容变得比平常还美。
“你要不要听听菲比尔的歌?”
我取出随身听。曲子当然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将耳机递给她,调整好音量。“歌声很富有感情、很柔和吧?”我问。她直点头。那确实是天籁之音。虽然我不懂西班牙文,但我知道那是首悲哀的恋歌。
虽然我喜欢你,
但我们的恋情已结束。
每次旅行都有结束之日,每段恋情也都有终了之时。
她稍懂点西班牙语,我问她听了有何感想?每次我听菲比尔的歌都会哭。听完《一个爱情故事》后,好一段时间里我俩都沉默不语,只是看着窗外即将落山的夕阳。
听了《一个爱情故事》后,事情的发展竟是那么不可思议。
我和赤川小姐到她常去的那家酒吧,喝着古巴产的兰姆酒,欣赏其他古巴歌手的CD。在酒精和陶醉的气氛的作用下,他约我到她家,于是我们就一起上床了。
我要出发到古巴前,和她见了好多次面,也在她家过了很多夜。
一个月后,我们决定利用黄金周的假期结伴去古巴。我在成田机场的出境通道口前喝着速溶咖啡等她。
成田机场人很多。
然而她没有来。
我当然打了电话给她,但她只是不断地对我说对不起。
我的眼前一片黑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还是决定打起精神上飞机。说真的,我是第一次出国。
我的心中有股惶恐的感觉。我在墨西哥机场边的饭店住了一晚,只身到了哈瓦那。
我漫步在街头,哈瓦那的上空骄阳似火。
从饭店房间可以眺望到令人心跳的蓝天和大海。
我向服务员打听菲比尔的事,但他们却都不认识他,看来他在古巴好像并不是很有名。
通过雷姆录音室,我知道了那位令我痴迷的歌手就住在哈瓦那郊区。
我带了两瓶兰姆酒去探望他。他住的是一间古老狭窄却很干净房子。他爸爸是一个有名的乐团主唱,但他说的西班牙话我一点也听不懂。他让我看菲比尔的CD。
古巴不卖CD,所以没有CD的音响设备。
过了一会儿,菲比尔带着一名年轻女孩回来了。他穿了件旧T恤和短裤,外表一点也不像歌手。那个年轻女孩并不是他的女朋友,是他爸爸的。喝完兰姆酒后,菲比尔唱了一些古巴民谣给我听。
那声音和CD里一模一样,这让我想起了和赤川小姐的那些事,不禁哭了出来。
我在古巴住了三个星期,也见了许多其他的古巴歌手。这期间我只打过一次电话给赤川。
“我现在就在哈瓦那。”
“是吗?”
“这房间里可以看到海。”
“那一定很美,拍些照片回来让我看看。”
可能是因为国际电话的关系,我觉得那声音距离很遥远。赤J;;确实是在很遥远的一方。
“我很喜欢这里。”
我说完后她沉默不语。我很想跟她说下一次我们俩一起来,但只说了一些日本太远了,哈瓦那的天空和大海很蓝等无聊的话题。
“回去再给你打电话。”
说完我便挂了电话。通完话后,我就到阳台上晒日光浴。
突然被这么强烈的阳光照射,感觉就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我好像稍稍了解菲比尔歌声中的秘密了。
古巴是不容人们过分安逸的。
我打工的这家餐厅位于青山,老板偶尔会在给青年人看的杂志上登广告,不过年轻客人好像并不多。我至今还没见过老板,听说他搞电脑软件进口生意赚了很多钱,为了少纳税才开了这家餐厅,他对意大利料理根本就是外行。主厨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在米兰住过三年,在芬兰住过五年,但做的都是些洗碗扫地的工作。我每次偷瞧厨房时,总看见他红着眼在煮通心面,也许做事认真的人很适合当意大利料理的厨师吧!
这家餐厅虽然大不受年轻人欢迎,而且价位很高,但每天晚上总是高朋满座。我想就算我赚了钱也不会来这么贵的餐厅吃饭。我一直梦想的是存些钱出国玩玩。那个女人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上,她边吃沙拉边安静地在哭。我以前很少看见客人哭。人们不是通常在分手时才哭吗?在这么高级的意大利餐厅谈分手的事,分手的悲伤就能减少一半吗?因分手而哭的人当中男女都有,但边哭边吃饭的只有女人,哭泣着的男人连场都不会喝。我们这些服务员都已被训练得面对这些客人时可以视而不见了。
她被一块儿用餐的中年男人欺负了。那女人看起来年龄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穿着绿色的套装,围了一条高级丝巾。虽然算不上是美女,但打扮得很优雅得体,是个上班族。虽然我也被训练得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耳朵就例外了,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那男人很过分。他大概有四十岁,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职员,从他的长相到穿着,能给的评价就是“平淡无奇”。他一进来我就觉得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当客人打开门进来时,我们都要用意大利语对客人说“欢迎光临!”就连面对日本客人也要讲意大利话。餐厅有些常客,可我觉得那些常客都像些白痴。
他们两人喝完白酒后,一切还好。后来男人说了些可恶的话。那种人三杯黄汤下肚后就是那个德性。我装作没看见,但耳朵却使劲地在听。他们两个人都在旅行社上班,同是春天新旅游计划方案的计划组成员。这个女的好像是小主管,男的似乎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
“一开始我就不愿意,可是科长都那么说了,我也没办法,总不能跟科长说不愿意吧!他说:‘组员全都是女孩子,会让你更年轻些。’被比我小两岁的上司那么说,真是太过分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和你这位组长一起吃饭,我就是要告诉你,对人不要太傲慢无理,知道吗?”
餐厅里很安静,那男人的声音显得很突出。他穿的西装看起来比别人差,我真的担心自己也像他一样,到了四十岁生活水平却这么差。
男人接着说;“我还是要恭贺你的亚洲之旅计划成功,可是早先是我提议举办澳洲、新西兰之旅的,然而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却没有列入我的名字,这也就算了,但是‘到澳洲去拖抱无尾能’可是我的点子,竟然被人盗用了,这算什么嘛?你们只是在利用我、使唤我罢了。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一个男人四十岁了还只是个小主任。虽然我是以顾问的名义加入你的小组,可当部长时,却没有我的份儿,不错,也许在你们眼里我是多余的,因为已经四十岁了,名片上的职务还只是个主任而已,但是我所说的那些事情并不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人本来就该分工合作,不是吗?这是你的第一次成功,工作能让你生存,所以就无视我的工作,反正我已经习惯人家这样对我了。计划中没有列上我的名字也无所谓,我可以不去想它。像你们这些女企划人员,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你是第一次,而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从头到尾就被人小瞧。我并不是无能,我的办公桌大小不也跟你一样吗!可是给科长作四十多分钟的报告时,却没听到你提我的名字。我知道,我了解科长的顾虑,还有你的心情,但我还是感到不平,我还是要跟你说。”
真是个无礼的家伙!男人一直在说,女人就一直哭。那种具男人一开始就打算把人骂哭的。女人很后悔似地点着头,她哭可能是因为情不自禁,觉得不好意思吧!那男人说话的口气很粗,虽然我们餐厅的常客中并没有上等人,但也从来没有像他那样的人。真想走过去摸他几拳。
“好了,我还是预祝你的计划成功,牢骚就到此为止,现在好好享受这一顿吧!”
男人看到女人哭了好像很高兴,然后这样说。接着那男人又说了很多恭维的话,女人面无表情只是“嗯”“啊”地回答。
当我把主莱烤羊肉串送到他们面前时,男人问女人:“你休假想去哪里旅行?黑木?还是瑞典?”
女人的回答叫人吃惊。
“我想去古巴!”
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
“幄?”男人显然也感到很惊讶,反问道。
“古巴?那里现在的情况不是有危险吗?”
女孩不回答,只是吃着肉,脸上的表情好像说:“如果是你的话,可能会死吧!”这下子我很难再装作若无其事了。当我收拾他们的碗盘时,手都有些抖了,其实我一直想去的国家正是古巴。
我跟同事打了声招呼,就马上奔出去追他们两人。他们正站在路口说话。
“要不要去喝一杯,半小时就行,我还有话想跟你说。”男人对女人说。
“不了,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只要半小时就行,你是不是怕我对你怎么样?”
“怎么会呢?”
“俄知道这里有一家小店的鸡尾酒很好喝,我前天就订好了位子了,走吧广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就半小时,我觉得对你过意不去,想赔罪。”
女人先注意到了我。我一直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可我穿的是白衬衫红领结的招待,所以显得很醒目。当我与女人四目相对时,我向她行了个礼说:
“谢谢你们到本店来用餐!”
男人用一副讨厌的表情看着我。
“你要干什么?”
在这时候出现,又站在这么冷的街头,我想那男人下一次肯定不会再到我们店里来了。我才不管他呢,他天生就是那种可以被小视的人。
“我是在刚才那个餐厅打工的学生。我也很想去古巴,现在打工就是为了赚旅费,可是因为我太忙,没时间找资料,如果你有空,可不可以告诉一些古巴的事?”
女人听我这么一说,显得有些疑惑的样子。我想至少也要拿到她的名片吧!正好前面来了辆出租车,我招手要它停下,“请上车!”我打开车门。女人一脸得救的表情,向身边的那个男人说了几句话便坐进出租车。
“请你给我一张名片可以吗?”
我来了个九十度鞠躬。
“你喜欢古巴的什么呢?”
女人坐进车后问我。
“有一位名叫菲比尔的歌手,我有他的CD,我实在太喜欢他了。”
“是吗?我不认识这个歌手。”
“我送你一盘他的录音带,他比唱爵士的值得贝克棒一万倍呢!”
女人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对着离去的出租车背影又行个大礼。我可不是要听她作旅游介绍的,我是想跟她一起去古巴。
“喂,你想干什么?”
那男人抓着我的肩膀。我贴近他的耳朵说:
“我讨厌你,地球上每个人都讨厌你!”
我甩开他的手,一口气跑回店里。
那个女人叫赤川美枝子。晚上回到家后,我边看着她的名片边听菲比尔的CD。我的老家在千叶县北方,爸爸是一家中药公司的老板,妈妈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哥哥是医生,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在国立大学读原子能专业。我的脑子并不差,可就是不爱读书。我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满二十岁的男人。很少有人知道我从小学起就有点自闭症倾向,我不知道怎样与人沟通,应该说是不会。上了高中后生活也没什么改变,但自闭症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上中学之前,我是个让学校头痛的学生,逃学、部车、交女朋友,只要是不会致死的坏事都干过。虽然这样,但我也读了不少书,所有刘!欧郎的书我都看过,可是从书中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直到上了高中后,认识了一个朋友叫纯一,他是个很开朗的人,但他也有和我一样的问题。和他交谈过后,我才知道并非只有我才有这种想法。我能知道这么多爵士歌手,也是他教我的。他的爸爸是建筑师,还是位欧美音乐唱片的收藏家。正因为这样,纯一才能懂得十六岁少年所不知道的很多知识。除了我和纯一以外,高中很少有人会欣赏欧美音乐。能认识纯一我感到很高兴,他教会了我许多事情,是他教我什么叫作“丰富的心”、“温柔体贴”、“生命的意义”、“充实感’、‘撼动”。这些东西就算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也都很缺乏吧!虽然现在高楼大厦已经取代了老式建筑,但是从前就缺乏的这些特质,至今依然欠缺。当人们不满越多、压力越多时,就更难体会这些境界。绝不要相信年长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直不能自觉的人更不能相信。
半年前逛唱片商店时,我发现了一张卖得只剩下最后一张的CD,封面上的画面吸引着我,那个人有股柔柔的自闭气质。这就是我和菲比尔的初次相遇。我从没听过古巴音乐,但菲比尔的声音深深地感动了我。听了第一首歌从个爱情故事》,不知不觉我党哭了出来,当时我就想,拥有如此美妙歌喉的歌手居住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那周的星期六和赤川美枝子通了电话,我和她约好到咖啡店见面。她头发梳得很整齐,还是穿着套装,系着那条丝巾。有一股莫名的寂寞写在她的脸上,当时我竟然有种想占有她身体的想法。
“你常在这里等人吗?”
她点了维也纳咖啡后,突然这样问我。
“不,这是第一次。”
我回答。这四天来我已经作好充分心理准备接受她的任何盘问,这大概是属于自闭症少年的一种习惯吧?但这是个让人感到悲伤的习惯。
“像赤川小姐这样的人很习惯这种地方吧?”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问题我早料到了。
“在我不懂的世界中拥有一份好工作,而且经常出国去玩…真是这样。”
“你看见我在餐厅里哭了?”
这也是我早就料到的问题。
“是!”
“没有客人会那样吧?”
“偶尔也会有人在餐厅里哭。”
“真的?”
“但没有人哭得像你那样。”
说完,赤川小姐笑了出来,然后叹了口气,表情又变得很沉静。
“那次是你救了我。”
我想现在有必要换话题了。
“对了,我可以向你请教一些古巴的事吗?”
当我说出古巴这两个字时,赤川美枝子的表情变得很复杂。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当她听到古巴时,应该是很高兴的表情,但她却没有,反而有点忧伤的样子。
“古巴……”她忧伤般地喃喃自语。我感觉到她很不想说,也不想听到古巴这两个字。我一直等她开口。我喝了一杯一千元的咖啡,虽然很贵,但确实是我喝过的咖啡中最好的。
“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她终于开口了。
“古巴嘉年华会期间在全国各地都有舞蹈公演,那都是强劲有力且美妙绝伦的舞蹈,有伦巴、芭蕾,还有现代舞,真的很叫人激动,于是我就追着表演团体到处跑。我喜欢上了一位舞蹈家。回到日本后,我邀请他到日本来玩,因为古巴人生活很苦,所以我买了很多东西给他。我很想跟他结婚,但我知道他只把我当成朋友而已。”
原来如此。我想那个舞蹈家一定是个黑人。
“我虽然一直想去古巴,但又很害怕再去,你懂我的心情吗?没有人能像我一样了解古巴舞蹈的美妙,也没有人像我一样愿意帮助他们。生长在富裕环境下的日本人是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贫困,就连我也不是很清楚。古巴和美国的关系闹僵后,经济遭到封锁,但古巴始终不肯向美国人低头道歉。说真的,就是到现在我还是很怕去古巴,你知道吗?”
她说了一些不在我设想之内的话题,叫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对她有股奇妙的好感。我们坐在豪华饭店的咖啡厅里,空间很宽敞,整体设计甚至服务员的都显得很优雅,服务员对客人的应对也很得体,客人的穿着品味也很高。为了不破坏这里的高雅气氛,出门前我还冲个澡,刮了胡子,头发也梳得很利索。可是,在我眼前的这位职业妇女还有我,幸福离我们还好远。在这看似令人满足的咖啡厅里却充满了一股寂寞感。
“我知道,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她忘了喝咖啡。也不看着我,只是冲着窗外说话。春日的夕阳似乎特别适合她,那地平线是橙色的,上面的天空一片粉红,好美的景色!但却总有点模糊不清。
“我真的很害怕再去古巴,那个舞蹈家好像有很多女朋友,因为他常常要到世界各地演出,所以可以认识许多女人,他现在好像和一个追到古巴的瑞士女人同居。一定是这样,我很害怕去面对这个事实。”
夕阳真美,我想。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她正将她最重要的秘密告诉我,可是我无法阻止她不说。
“不过古巴舞蹈真的很新鲜。我每年都会到纽约一次,去欣赏新舞蹈发布会上的演出。一看到古巴舞蹈,心中就会有股说不出的快乐感,它让我有新的生命刺激,每次都有奇妙的相会。我真的迷上了古巴舞蹈,不管是杂志还是电视,只要有关于古巴舞蹈的报道,我一定要看。真的很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中还是有股恐惧感。我很期待与新的古巴舞蹈相会的时刻,但又怕失去了它。失去他和失去古巴舞蹈是两码事,但我现在好像把它们混在一起了。”
我能理解她的心清,能让人真正沉迷的事情并不多。其实我也一样。
“赤川小姐!”我开口了,赤川小姐忧郁的脸从窗边转向了我。在夕阳的斜照下,那面容变得比平常还美。
“你要不要听听菲比尔的歌?”
我取出随身听。曲子当然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将耳机递给她,调整好音量。“歌声很富有感情、很柔和吧?”我问。她直点头。那确实是天籁之音。虽然我不懂西班牙文,但我知道那是首悲哀的恋歌。
虽然我喜欢你,
但我们的恋情已结束。
每次旅行都有结束之日,每段恋情也都有终了之时。
她稍懂点西班牙语,我问她听了有何感想?每次我听菲比尔的歌都会哭。听完《一个爱情故事》后,好一段时间里我俩都沉默不语,只是看着窗外即将落山的夕阳。
听了《一个爱情故事》后,事情的发展竟是那么不可思议。
我和赤川小姐到她常去的那家酒吧,喝着古巴产的兰姆酒,欣赏其他古巴歌手的CD。在酒精和陶醉的气氛的作用下,他约我到她家,于是我们就一起上床了。
我要出发到古巴前,和她见了好多次面,也在她家过了很多夜。
一个月后,我们决定利用黄金周的假期结伴去古巴。我在成田机场的出境通道口前喝着速溶咖啡等她。
成田机场人很多。
然而她没有来。
我当然打了电话给她,但她只是不断地对我说对不起。
我的眼前一片黑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还是决定打起精神上飞机。说真的,我是第一次出国。
我的心中有股惶恐的感觉。我在墨西哥机场边的饭店住了一晚,只身到了哈瓦那。
我漫步在街头,哈瓦那的上空骄阳似火。
从饭店房间可以眺望到令人心跳的蓝天和大海。
我向服务员打听菲比尔的事,但他们却都不认识他,看来他在古巴好像并不是很有名。
通过雷姆录音室,我知道了那位令我痴迷的歌手就住在哈瓦那郊区。
我带了两瓶兰姆酒去探望他。他住的是一间古老狭窄却很干净房子。他爸爸是一个有名的乐团主唱,但他说的西班牙话我一点也听不懂。他让我看菲比尔的CD。
古巴不卖CD,所以没有CD的音响设备。
过了一会儿,菲比尔带着一名年轻女孩回来了。他穿了件旧T恤和短裤,外表一点也不像歌手。那个年轻女孩并不是他的女朋友,是他爸爸的。喝完兰姆酒后,菲比尔唱了一些古巴民谣给我听。
那声音和CD里一模一样,这让我想起了和赤川小姐的那些事,不禁哭了出来。
我在古巴住了三个星期,也见了许多其他的古巴歌手。这期间我只打过一次电话给赤川。
“我现在就在哈瓦那。”
“是吗?”
“这房间里可以看到海。”
“那一定很美,拍些照片回来让我看看。”
可能是因为国际电话的关系,我觉得那声音距离很遥远。赤J;;确实是在很遥远的一方。
“我很喜欢这里。”
我说完后她沉默不语。我很想跟她说下一次我们俩一起来,但只说了一些日本太远了,哈瓦那的天空和大海很蓝等无聊的话题。
“回去再给你打电话。”
说完我便挂了电话。通完话后,我就到阳台上晒日光浴。
突然被这么强烈的阳光照射,感觉就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我好像稍稍了解菲比尔歌声中的秘密了。
古巴是不容人们过分安逸的。
这是坐落在西新宿区高层建筑群中的一家饭店,游泳池在它的最顶层。
我是画家。因为要给这家饭店的宣传册上画插图,还要替饭店购买钢板画装饰22间大套房,所以有机会每周在游泳池游上两三次。
游泳池大约15米长。面积虽不大,但是因为门票很贵,每张八千元,所以来游泳的人很少。在这里可以一边游泳,一边从距离地面33层的高处眺望整个市中心,真是惬意极了。
我喜欢在星期天的中午过后来游泳,因为这个时候客人最少。在这里偶尔也能看到一些欧美的白人男子,他们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机组人员自然不用说了,可是这些意大利人在一起却相互用蛮正规的英语交谈。我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上过床。他的性格有些腼腆,这在意大利人中很少见。他教我游蝶泳,我们饭店的自助餐厅吃意大里面条,他说这么难吃的细面条在意大利连狗都不稀罕。他的笑真像约翰·波轮奇。我喜欢上了他笑的样子,于是就走进了这个意大利人的房间。
那是个下雪天。在游泳池旁边的低温桑拿浴室里,一个矮个子的男人在说话,“日本也成富翁了!”他坐在桑拿浴室的一角,双手抱着膝盖。我含糊地回应他。
“你常来这里吗?”
桑拿浴室里充满了亲切感。虽然穿着泳装,但在桑拿浴室里汗还是不停地从皮肤里冒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警惕心会减弱吧!“一周能来两三次。”我一边拢着头发一边回答。
“我还以为人会很多呢,简直像空的一样!”
我对他说我来这里游泳已经有一年了,这个季节人最少。因为是室内游泳池,所以外面不能游泳时照理这里会很拥挤,但是情况正好相反,还是夏天来的人多。男人的皮肤很滑润。看上去不像一般的职员。他的年龄大概有三十多岁,好像比我小两三岁。
“这样空荡荡的可真不错,以后就到这儿来游泳。”
“你平常在其它地方游泳吗?”我问。男人点点头。
“我在想象这里有很多年轻的女孩。”
“啊!为什么?”
“听说的。”
“谁说的?”
“一个年轻女孩。”
男人肩膀冒出水珠般的汗滴。落下的水滴和身上的汗珠混杂在一起。
从桑拿浴室里出来,男人没休息就下池游泳了,他游的是自由式。他的泳姿算不上美,但看上去很有力,简直就是在海上的感觉!
“太棒了!”
在泳池旁的柜台前,我们坐在一起喝着椰汁。男人让扎蝴碟结的女招待将兰姆酒和椰汁兑在一起,但是被拒绝了,因为这里没有准备含酒精的饮料。
“晦,你是在海边出生的吗?”
我把浴巾搭在肚子上。我的腹部比起同龄女人来还是蛮紧绷的,但毕竟不能和少女的身材相比了。年轻女孩,男人说的这个词还停留在我的耳朵里。
“是在四国。”
男人身上的肌肉很发达,但下腹部却有赘肉。我想这不是肉体的衰老,而是他放荡的证据。
“我是画家,版画家。”
“我家里有卢奥的石版画。”
“您也喜欢画?”
“一般吧,卢奥的画是我老婆买的。”
“那夫人一定也很喜欢画了!”
“好像比较喜欢卢奥的画。”
这时,有两对一起来到游泳池。两位母亲和两个孩子以及孩子的欢叫声,同浓浓的椰汁和厚玻璃窗外的白雪极不相称,让人感到刺耳。
“我想你是单身吧?”
“正在分居。”
“让你听讨厌的话了吧?”
“没有的事。”
5岁左右的小男孩在母亲稍不留神的空儿溺水了。游泳池的监督员像教练一样飞身跃入池中。我们两人也注视着这一场面。我是第一次看到溺水的小孩。小孩被救出,他一边大声地哭,一边吐着水。
男人面无表情地看着这情景。最后他请我一起吃饭。
“是单纯的虫牙吗?”
一瓶洋酒快喝完的时候,男人开始讲开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概两年前吧,正在嚼口香糖时,一直塞着的像胶皮似的东西掉了下来。我想这和牙医说的情况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感觉疼。吃饭的时候食物塞牙,那滋味很难受吧?”
我们在酒店的地下餐厅里,吃着和这雪夜的格调很相称的野禽料理,我吃的是小竹鸡,男人吃的是班鸦。
“用舌尖去找塞在牙上的东西,舌头可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家伙,用它去掏牙洞时,它会在你的脑子里制作影像。你是艺术家,对影像你一定了解的很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舌头?制作影像?等一下,我都有点糊涂了!”
因为洋酒喝得太多了,我的头有些发昏,这时候男人还讲什么叫人不可思议的舌头和牙洞的关系,我可理解不了。
“那好吧,从另一个角度给你讲讲。自从有了那次的舌头体验后,我做了点调查。记忆就是影像吧?不对吗?”
“是吗?”
“对了,你还记得大约在十年前有一首令人怀念的流行歌曲吧?是什么了的?比如伊格尔斯的《加利福尼亚的旅店》,听到那吉它弹奏的序曲,一股怀念之情就会涌出来吧?”
“《加利福尼亚的旅店》流行的时候,我和丈夫分开的。”
“就是这样的。如果只是声音的话,那只不过是单纯令人怀念的东西,但声音必定会浮现影像。一听到十年前那令人难忘的乐曲,就会想起当时的事情了。那么气味又怎样呢?我一闻到令人愉快的气味,眼前就一定浮现某个女人的影像。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有过的。”
的确如此。我讨厌阿拉米兹的气味,因为那是伤过我自尊心的男人擦的法国科隆香水。不过,很遗憾他是第一个让我身体起反应的男人。以后我再没见过那个男人。所以,阿拉米兹的香味让我想起那个男人,并且告诉我眼前的这个男人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听说在美国已经完成实验,进入开发阶段了,那是一种能体验各种事情的装置。简单点说,影像、声音、气味。温度、包括全部的记忆,这些都作为物质安眠在大脑的某个位置。实验就是从发掘这些物质开始的。对大脑进行电刺激,这样,记忆就像电影一样在眼前展开。也就是说,首先找到记忆安眠的地方。那样的话,后面就有意思了,接受实验的人们全都看到了他们以前从没有体验过的影像。”
“可是,现在有电影和电视,还有书呀!”
“所以,实验组挑选的都是住在西北部保留地的印地安人,或者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还有墨西哥高原的印地安人。他们从出生起就没离开过保留地,不用说电影、电视,就连字也不会念。那些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自身绝对没有过的记忆,比如埃及、亚马逊河以及冰河期以前的事情,或者株罗纪的恐龙,中世纪的日本等等。”
“为什么呢?好可怕!”
“不可思议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因还不太清楚。”
“也许是前世的记忆吧?”
“后面还有呢,这个话题你没兴趣吧?”
“很有意思呀!”
也许是因为听了男人的话,吃着香喷喷的海龟场,一个性的影像突然浮现,怎么也消不去。
“刺激大脑的某个地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像呢?据说把资料集中,用电脑分析它们,就能够随心所欲地体验到任何事情。”
“例如一个残疾人,他生下来就因为脊椎病变而只能躺着。这种人哪儿也不能去。可是,只要用电刺激大脑,他就能体验到所有一切。即使植物人也说不准是可能的。因为已经观测到某些植物人肯定在做梦的脑电波。所以,也许能够让植物人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影像,好像还可以体验声音和气味。”
“舌头?我是说你的舌头。”
“我的舌头和能做有声音、气味、温度的梦的装置有相同的作用呢。所以,在知道美国的那种实验之前还曾经感到很不安,我想自己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了。”
“舌头怎么了?”
“用舌头去碰牙上的洞,就出现了影像。塞在牙洞里的东西不同,出现的影像就不一样。”
“见过女人吗?”
“如果是鸡蛋的话,就出现女人,当然,要是鱼子酱和鱼子的话就不同了。听起来可能有点离谱,我真的有过的事呢。”
烤制的小竹鸡肉和褐色的寿司散发着野兽的血和肝脏的香气。
“稍等一下!舌头怎么了?我还是不太明白。”
“那么,我说说最近的体验,没关系吧?”
“什么?”
“是些无聊的话。”
我回答说没关系。两瓶洋酒几乎都见底了。从开胃菜洋蓟和椰子螃蟹到我的眼睛和肚子之间,一种奇妙的东西开始堆积。椰子螃蟹的柔软的内脏、滑溜溜黄色的生殖腺那刺激舌头的苦味和口中的洋酒搅一起,不仅没有溶解,反而好像再生成另一种生物。它吐着粘汁,伸着长满毛的触手,变成了几万根肢节攀缠的生物。我被这个生物控制着。
“那是吃海狗时候的事。我和同行的朋友们到我办公室附近的寿司店吃饭,我吃的是海狗。听说是从北海道的西海岸抓的,是个壮实的真货。”
“这种东西可塞牙呢?”
“没错。感觉很不舒服,想用舌头弄出来,于是把舌头对着牙洞掏起来。忽然,我先是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大风吹动大树的叶子的声音,又像是几百万只小虫一起爬行时的声音,或者是上百万人压低了的可怕的笑声。就是这样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使我的视野出现了裂缝。我慌忙擦拭眼睛,可感觉左眼和右眼看到的好像是不同的东西。这个裂缝逐渐地扩大,我感到自己正被吸进当中。这同游泳时被潮汐吸进去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发出了惊恐的声音。后来听朋友们说,当时我叫喊起来了。最后,视野中出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房屋栉比的地方。汗味、太阳蒸发动物粪便的气味。狭窄的路上蠕动的人群,我很快明白了这里是东南亚的贫民窟。我正走在那里。我想这是印度的南部。当然,我以前没去过。一群粘满污泥光着身子的孩子们伸着手,磨刀师拿着半月刀正在割猪脚,耍蛇的女人让青蛇从嘴里进去,然后又从鼻子里钻出来,好几千个妓女从格子屋里伸手打着招呼。
闷热的天气和人的热气使我发晕。铺着石头的小路让人感觉很凉爽。阴凉处像孔雀模样的房子吸引了我,于是我走了进去。在门前有一座黄金做成的巨大的佛像。一个白人女人站在兰花丛中,我求她给我一杯水。女人让孔雀告诉我喷水的地方。”
“你和那个女人睡觉了吗?”
“是的。”
“别的还干了什么?”
“不光是性交,还一起滑雪、骑摩托车兜风、散步,总之有很多方式。”
“现在怎么样?”
“有洞的牙在左侧,所以今天是用右边咀嚼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现实比梦更美呀!”
男人说着,一口咬碎了班鹤的头。
在挂着我的版画的房间里,我们睡在了一起。男人正用牙洞和舌头进行一次旅游。我的和他的牙洞缠在一块儿。男人突然停止了动作,就像冻住了似的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姿势。只有脸上的表情在变化。他心荡神驰般地歪着嘴露出牙齿笑起来。我把手伸进他的两腿中间,用力握住那个变得坚硬的东西。这下男人的身体开始发抖,恐惧使他的脸部抽搐起来。
“到哪里了?”
“我不认识的城市。”
“是外国吗?”
“是的,好像是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是叫堪贝尔德的地方,那里的人多极了。”
“刚才你的表情变得很恐惧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记得了。”
“好像很可怕似的。”
“嗯,总的来说不是什么太好的梦。”
“我想听听,一个也好。如果里面不塞东西,你的梦就不会发生了吧?”
“不对。
“用舌头去碰什么也没有的空洞也会做梦吗?”
“当然。”
“是公园!”男人说。“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城市中的空无一人的公园。但是我感觉这里好像离我的家乡很近。”
黄昏十分,我正坐在地上。我的影子在我的身后伸长。这是一个小公园。我不知道自己在找谁,也不知道想回到哪里。我决不想一个人行动。沙滩上埋着被破坏了的人影。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冷音。是秋千摇摆的声音呢,还是谁在唱歌,或者是鸟鸣,我不知道。虽然是黄昏,但决不会变成黑夜。在那个梦里,我一定会哭出来的……
我是画家。因为要给这家饭店的宣传册上画插图,还要替饭店购买钢板画装饰22间大套房,所以有机会每周在游泳池游上两三次。
游泳池大约15米长。面积虽不大,但是因为门票很贵,每张八千元,所以来游泳的人很少。在这里可以一边游泳,一边从距离地面33层的高处眺望整个市中心,真是惬意极了。
我喜欢在星期天的中午过后来游泳,因为这个时候客人最少。在这里偶尔也能看到一些欧美的白人男子,他们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机组人员自然不用说了,可是这些意大利人在一起却相互用蛮正规的英语交谈。我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上过床。他的性格有些腼腆,这在意大利人中很少见。他教我游蝶泳,我们饭店的自助餐厅吃意大里面条,他说这么难吃的细面条在意大利连狗都不稀罕。他的笑真像约翰·波轮奇。我喜欢上了他笑的样子,于是就走进了这个意大利人的房间。
那是个下雪天。在游泳池旁边的低温桑拿浴室里,一个矮个子的男人在说话,“日本也成富翁了!”他坐在桑拿浴室的一角,双手抱着膝盖。我含糊地回应他。
“你常来这里吗?”
桑拿浴室里充满了亲切感。虽然穿着泳装,但在桑拿浴室里汗还是不停地从皮肤里冒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警惕心会减弱吧!“一周能来两三次。”我一边拢着头发一边回答。
“我还以为人会很多呢,简直像空的一样!”
我对他说我来这里游泳已经有一年了,这个季节人最少。因为是室内游泳池,所以外面不能游泳时照理这里会很拥挤,但是情况正好相反,还是夏天来的人多。男人的皮肤很滑润。看上去不像一般的职员。他的年龄大概有三十多岁,好像比我小两三岁。
“这样空荡荡的可真不错,以后就到这儿来游泳。”
“你平常在其它地方游泳吗?”我问。男人点点头。
“我在想象这里有很多年轻的女孩。”
“啊!为什么?”
“听说的。”
“谁说的?”
“一个年轻女孩。”
男人肩膀冒出水珠般的汗滴。落下的水滴和身上的汗珠混杂在一起。
从桑拿浴室里出来,男人没休息就下池游泳了,他游的是自由式。他的泳姿算不上美,但看上去很有力,简直就是在海上的感觉!
“太棒了!”
在泳池旁的柜台前,我们坐在一起喝着椰汁。男人让扎蝴碟结的女招待将兰姆酒和椰汁兑在一起,但是被拒绝了,因为这里没有准备含酒精的饮料。
“晦,你是在海边出生的吗?”
我把浴巾搭在肚子上。我的腹部比起同龄女人来还是蛮紧绷的,但毕竟不能和少女的身材相比了。年轻女孩,男人说的这个词还停留在我的耳朵里。
“是在四国。”
男人身上的肌肉很发达,但下腹部却有赘肉。我想这不是肉体的衰老,而是他放荡的证据。
“我是画家,版画家。”
“我家里有卢奥的石版画。”
“您也喜欢画?”
“一般吧,卢奥的画是我老婆买的。”
“那夫人一定也很喜欢画了!”
“好像比较喜欢卢奥的画。”
这时,有两对一起来到游泳池。两位母亲和两个孩子以及孩子的欢叫声,同浓浓的椰汁和厚玻璃窗外的白雪极不相称,让人感到刺耳。
“我想你是单身吧?”
“正在分居。”
“让你听讨厌的话了吧?”
“没有的事。”
5岁左右的小男孩在母亲稍不留神的空儿溺水了。游泳池的监督员像教练一样飞身跃入池中。我们两人也注视着这一场面。我是第一次看到溺水的小孩。小孩被救出,他一边大声地哭,一边吐着水。
男人面无表情地看着这情景。最后他请我一起吃饭。
“是单纯的虫牙吗?”
一瓶洋酒快喝完的时候,男人开始讲开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概两年前吧,正在嚼口香糖时,一直塞着的像胶皮似的东西掉了下来。我想这和牙医说的情况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感觉疼。吃饭的时候食物塞牙,那滋味很难受吧?”
我们在酒店的地下餐厅里,吃着和这雪夜的格调很相称的野禽料理,我吃的是小竹鸡,男人吃的是班鸦。
“用舌尖去找塞在牙上的东西,舌头可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家伙,用它去掏牙洞时,它会在你的脑子里制作影像。你是艺术家,对影像你一定了解的很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舌头?制作影像?等一下,我都有点糊涂了!”
因为洋酒喝得太多了,我的头有些发昏,这时候男人还讲什么叫人不可思议的舌头和牙洞的关系,我可理解不了。
“那好吧,从另一个角度给你讲讲。自从有了那次的舌头体验后,我做了点调查。记忆就是影像吧?不对吗?”
“是吗?”
“对了,你还记得大约在十年前有一首令人怀念的流行歌曲吧?是什么了的?比如伊格尔斯的《加利福尼亚的旅店》,听到那吉它弹奏的序曲,一股怀念之情就会涌出来吧?”
“《加利福尼亚的旅店》流行的时候,我和丈夫分开的。”
“就是这样的。如果只是声音的话,那只不过是单纯令人怀念的东西,但声音必定会浮现影像。一听到十年前那令人难忘的乐曲,就会想起当时的事情了。那么气味又怎样呢?我一闻到令人愉快的气味,眼前就一定浮现某个女人的影像。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有过的。”
的确如此。我讨厌阿拉米兹的气味,因为那是伤过我自尊心的男人擦的法国科隆香水。不过,很遗憾他是第一个让我身体起反应的男人。以后我再没见过那个男人。所以,阿拉米兹的香味让我想起那个男人,并且告诉我眼前的这个男人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听说在美国已经完成实验,进入开发阶段了,那是一种能体验各种事情的装置。简单点说,影像、声音、气味。温度、包括全部的记忆,这些都作为物质安眠在大脑的某个位置。实验就是从发掘这些物质开始的。对大脑进行电刺激,这样,记忆就像电影一样在眼前展开。也就是说,首先找到记忆安眠的地方。那样的话,后面就有意思了,接受实验的人们全都看到了他们以前从没有体验过的影像。”
“可是,现在有电影和电视,还有书呀!”
“所以,实验组挑选的都是住在西北部保留地的印地安人,或者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还有墨西哥高原的印地安人。他们从出生起就没离开过保留地,不用说电影、电视,就连字也不会念。那些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自身绝对没有过的记忆,比如埃及、亚马逊河以及冰河期以前的事情,或者株罗纪的恐龙,中世纪的日本等等。”
“为什么呢?好可怕!”
“不可思议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因还不太清楚。”
“也许是前世的记忆吧?”
“后面还有呢,这个话题你没兴趣吧?”
“很有意思呀!”
也许是因为听了男人的话,吃着香喷喷的海龟场,一个性的影像突然浮现,怎么也消不去。
“刺激大脑的某个地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像呢?据说把资料集中,用电脑分析它们,就能够随心所欲地体验到任何事情。”
“例如一个残疾人,他生下来就因为脊椎病变而只能躺着。这种人哪儿也不能去。可是,只要用电刺激大脑,他就能体验到所有一切。即使植物人也说不准是可能的。因为已经观测到某些植物人肯定在做梦的脑电波。所以,也许能够让植物人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影像,好像还可以体验声音和气味。”
“舌头?我是说你的舌头。”
“我的舌头和能做有声音、气味、温度的梦的装置有相同的作用呢。所以,在知道美国的那种实验之前还曾经感到很不安,我想自己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了。”
“舌头怎么了?”
“用舌头去碰牙上的洞,就出现了影像。塞在牙洞里的东西不同,出现的影像就不一样。”
“见过女人吗?”
“如果是鸡蛋的话,就出现女人,当然,要是鱼子酱和鱼子的话就不同了。听起来可能有点离谱,我真的有过的事呢。”
烤制的小竹鸡肉和褐色的寿司散发着野兽的血和肝脏的香气。
“稍等一下!舌头怎么了?我还是不太明白。”
“那么,我说说最近的体验,没关系吧?”
“什么?”
“是些无聊的话。”
我回答说没关系。两瓶洋酒几乎都见底了。从开胃菜洋蓟和椰子螃蟹到我的眼睛和肚子之间,一种奇妙的东西开始堆积。椰子螃蟹的柔软的内脏、滑溜溜黄色的生殖腺那刺激舌头的苦味和口中的洋酒搅一起,不仅没有溶解,反而好像再生成另一种生物。它吐着粘汁,伸着长满毛的触手,变成了几万根肢节攀缠的生物。我被这个生物控制着。
“那是吃海狗时候的事。我和同行的朋友们到我办公室附近的寿司店吃饭,我吃的是海狗。听说是从北海道的西海岸抓的,是个壮实的真货。”
“这种东西可塞牙呢?”
“没错。感觉很不舒服,想用舌头弄出来,于是把舌头对着牙洞掏起来。忽然,我先是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大风吹动大树的叶子的声音,又像是几百万只小虫一起爬行时的声音,或者是上百万人压低了的可怕的笑声。就是这样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使我的视野出现了裂缝。我慌忙擦拭眼睛,可感觉左眼和右眼看到的好像是不同的东西。这个裂缝逐渐地扩大,我感到自己正被吸进当中。这同游泳时被潮汐吸进去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发出了惊恐的声音。后来听朋友们说,当时我叫喊起来了。最后,视野中出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房屋栉比的地方。汗味、太阳蒸发动物粪便的气味。狭窄的路上蠕动的人群,我很快明白了这里是东南亚的贫民窟。我正走在那里。我想这是印度的南部。当然,我以前没去过。一群粘满污泥光着身子的孩子们伸着手,磨刀师拿着半月刀正在割猪脚,耍蛇的女人让青蛇从嘴里进去,然后又从鼻子里钻出来,好几千个妓女从格子屋里伸手打着招呼。
闷热的天气和人的热气使我发晕。铺着石头的小路让人感觉很凉爽。阴凉处像孔雀模样的房子吸引了我,于是我走了进去。在门前有一座黄金做成的巨大的佛像。一个白人女人站在兰花丛中,我求她给我一杯水。女人让孔雀告诉我喷水的地方。”
“你和那个女人睡觉了吗?”
“是的。”
“别的还干了什么?”
“不光是性交,还一起滑雪、骑摩托车兜风、散步,总之有很多方式。”
“现在怎么样?”
“有洞的牙在左侧,所以今天是用右边咀嚼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现实比梦更美呀!”
男人说着,一口咬碎了班鹤的头。
在挂着我的版画的房间里,我们睡在了一起。男人正用牙洞和舌头进行一次旅游。我的和他的牙洞缠在一块儿。男人突然停止了动作,就像冻住了似的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姿势。只有脸上的表情在变化。他心荡神驰般地歪着嘴露出牙齿笑起来。我把手伸进他的两腿中间,用力握住那个变得坚硬的东西。这下男人的身体开始发抖,恐惧使他的脸部抽搐起来。
“到哪里了?”
“我不认识的城市。”
“是外国吗?”
“是的,好像是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是叫堪贝尔德的地方,那里的人多极了。”
“刚才你的表情变得很恐惧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记得了。”
“好像很可怕似的。”
“嗯,总的来说不是什么太好的梦。”
“我想听听,一个也好。如果里面不塞东西,你的梦就不会发生了吧?”
“不对。
“用舌头去碰什么也没有的空洞也会做梦吗?”
“当然。”
“是公园!”男人说。“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城市中的空无一人的公园。但是我感觉这里好像离我的家乡很近。”
黄昏十分,我正坐在地上。我的影子在我的身后伸长。这是一个小公园。我不知道自己在找谁,也不知道想回到哪里。我决不想一个人行动。沙滩上埋着被破坏了的人影。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冷音。是秋千摇摆的声音呢,还是谁在唱歌,或者是鸟鸣,我不知道。虽然是黄昏,但决不会变成黑夜。在那个梦里,我一定会哭出来的……
等电话的时候,我在想纽约按摩中心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起那里的事。按摩中心在纽约城郊十七巷的七号街和八号街之间,那儿没什么招牌,也没有菲律宾人和韩国人,全都是些越南难民,经营方式并不是会员制,但一定要有熟客介绍才知道这个地方。这家店没有张贴任何色情海报,就算路过也不会知道那是家按摩中心。在专用电梯前有个黑人警卫,他会说法语和阿拉伯语,身高一米九十,从前是足球运动员。
他会向你行个礼,问你要去哪儿,如果你说“塞可利克寺院”的话,他就会让你进电梯,和你一起来到四楼。这栋楼的外表和内部陈设以及警卫人员,都和一般郊区的高级住宅区一样。这裹住着各种行业的人,有按摩中心并不是个秘密。到了四楼,警卫指指门牌,然后他又搭电梯下去。
入口处铺着地毯。先向右走,最后再向左转。
厚重的木板门开了。
门的那一边站了一排只穿着薄衣的女人,里面有蒸气室、桑那浴室、全身美容室、淋浴室和水床。
我在纽约时,只去过那里两次。第一次是去洗桑拿浴,第二次是去按摩。一位有名的运动员请我吸可卡因,我对毒品没兴趣,但他说只是花钱抱抱女人不是很无聊吗?我并不是第一次吸可卡因,但是从没吸过这么纯的。将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的可卡因直接放在火上烧,吸它的气体,当然很过瘾。“并不是吸了可卡因就会性欲高涨,但是对于你所渴望的对象确实有作用,所以对那些小姐最合适了。”那位运动员说的报对。
有七、八个按摩女郎,她们并没有穿内衣或泳装,全都盛装出场。她们在这里面好像被看管着,但其实并没有被强制行动。她们中多数生于富裕之家,连个口红都没带,就干然一身地搭机或乘船来到美国。她们在这个寺院里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赚美金。只要一年时间,她们就能挣到足够的钱,说一口很流利的英语,走在曼哈顿街上又是另一个人。
据说这种事情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这是一位波兰裔的新西兰代理社长告诉我的。
2
我吸着可卡因,接着选了一位叫“安”的中法混血姑娘。我只记得她的名字,长相倒是忘记了。她的身材很好,够得上高级妓女的标准。那里的姑娘身材都很好,但是也有缺点。
她的牙齿长得不美,臀部下垂,脚踝过粗,背后有浓毛。其他部位长得都很匀称美丽。
当我回忆那些事时,突然想起美空云雀的歌。
我对音乐的兴趣很广泛,但是没有特别喜欢的,只要旋律好我就会买。
我走向唱盘架。想在两千多张CD中找出美空云雀的歌实在很难,我想该找个时间按名字顺序整理一下。
没有找到,我想找别的歌听听,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是从马德里打来的,打电话的我高中时的铁哥们儿。岩井打电话来说有三位马拉松选手答应签约。
“岩井,你喝醉了?”
“喝多了,对不起,但我还是拟好合同了。价码很便宜,是波多黎各的选手,只要一千五百美元,踢世界杯水平的足球选手一天才三十美金,很合适吧?”
“知道了,我现在不想和你谈公事。”
“喂,是不是嫌我醉了,我头脑很清醒,你记得美惠吗?”
“哪里的女人?”
“不是那个啦,四班的同学,我们一年级四班的同学,二年级时她转学到四国了。”
“是良原美惠吗?”
“是”
我和岩井都喜欢良原美惠。对正常的十六岁男孩来说,没有人会不喜欢那样的女孩的。家也好,又漂亮又聪明,爸爸是公司的大老板。
“我之所以会喝醉,全是为了美惠,你相信吗?”
“你见到她了吗?”
我和岩井都曾跟美惠约会过,是在植物园。不知道为什么模范生似的偶像人物美惠会跟我们这种常逃学的坏小子交往。那时美惠还从家里带过盒饭给我吃。我和岩井都认为,也许那样的人也有寂寞的时候吧!所以有人约她就会很高兴。
“应该算看见,不过只是见到她的脸而已。”
“她好像跟了一个傻乎乎的商社职员结婚,那家伙长得很矮,跟你差不多吧。哪天介绍你去一个好地方,拥里有个叫莉达的黑人女孩。”
“不是,我不是真放想见美惠钧。”
“露线地了吧!”
“她在演三级片。”
“你说什么?”
“以前流行的只是风情女郎,现在波多黎各最热门的就是日本的色情录像带。”
“我知道。”
“那里的人已经看腻了东南亚女人主演的色情片了,现在日本女郎是最受欢迎的。”
“你在哪里见到她的?”
“在马德里电视台运动部头头的办公室,她见到我只是笑笑,我也朝她一笑。你知道,我看见女人都会笑的。”
“会不会看错人了,美惠都三十二岁了,还演三级片?和外国人一起演吗?”
“她演一个关西人的太太,是和一个年轻的日本小伙子一起演。平常我看这些片子都觉得没什么,但是那次看过后,我真的胃都抽筋了。”
“知道片名吗?”
《再度重逢人妻的悲伤性态》
“人生真是痛苦。”
“你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看。”
“我不想看。”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醉吧?”
“还是好好工作吧!”
“知道了,我不打电话了,发传真给你。”
挂掉电话后,我又继续找CD。边听着歌,安的浓毛和美惠的脸一直在我的眼前交错出现。
那是马德里的深夜。岩井找了个女人来,把美惠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
3
我打电话给泽子,泽子是一家大建筑公司秘书科的职员,二十八岁,还没结婚。
“是我。”
“你今天起得真早。”
“朋友打来国际电话吵醒了我。中午时可不可以跟你见个面?”
“好啊!我的床变成了红色了。”
“月经来了吗?”
“铺床单时染到的,刚好在正中间。”
“当秘书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现在有没人在。”
“过来时带些三明治吧!”
“我今天带了盒饭,我有预感你会打电话来,所以做了两份儿盒饭。一起吃吧!”
打完电话后,我马上订好饭店房间,然后在上午十点出门。检查车子发动机时,来打扫的广美姐笑着跟我道早安,走进了家门。广美长得比我的前妻还丑几倍,所以每次看到广美时我就觉得前妻很美,心中难免有些后悔。
我先把车子停在饭店的停车场,然后搭出租车去新宿。听说在歌舞伎街的情趣用品商店中有《再度相逢人妻的悲伤性态》这部片子。那家店里没有,但主人说他会从别的连锁店调片子来,要我下午再来拿。我先付了一半的定金,请他在片子到后送到饭店的前台。
“好热!”
泽子擦着脖子上的汗水,走进房里,快步来到窗边,眺望着下面的公园好一会儿,然后拉上窗帘。
“我最讨厌看到小孩在阳光底下跑,把脸晒得通红的。”
说完她将一个纸袋放在桌上,纸袋中散发出令人怀念的味道。那是盒饭的味道。
“关掉空调吧!我想光着身出汗。”
“你不是一热就心烦吗?别逞能了。”我说。
“因为劳累出开才悲惨呢。我先去冲个澡好吗?还是你想先闻我的味儿?
泽子边说边脱掉衬衫。三年前我就认识她了,也许现在说来也没人会信,第一次见到泽子时,她还是个处女。二十五岁还是处女,真是稀罕的动物,我那时是这么想的。
一般来说,如果是丑女孩的话,过了二十岁还是处女,肯定会让人有种不利索的感觉。
泽子那个地方淡淡的毛是下垂的,它让我想起在纽约的安。泽子一丝不挂地将床单盖在身上。
我并不是因为泽子才和前妻离婚的,而是因为我经常出国的缘故。我太太喜欢夫妻二十四小时都能在一起,共同享受酸甜苦辣,丈夫汗流侠背地修理桌椅,太太在厨房里烤着饼干或蛋糕,吃饭的时间到了就敲个钟,大家一起陶醉在天伦之乐中。
前妻和我离婚后就回到她的家乡,和一个从事建材业的男人结婚,生了两个小孩。不知道她变胖了没有,她每年都会寄明信片给我。
不知她是不是在向我炫耀她的幸福生活。
泽子吻着我。她抬起眼看着我,用她那擦着鲜红指甲油的双手轻柔地抚摸着我的下腹,用舌头舔着。
“你抽烟吧!“
她说,继续将脸埋在我身上。看着我抽烟最能令她感到兴奋,我记得她以前这么说过。
“可以再来一次吗?”
“相反顺序的话还可以。”
“先来我的,接着是用嘴吗?”
“是”
“为什么?哪一个才是主菜?用嘴不是开胃菜吗?”
“开胃菜吃饱了,主菜会吃不下。”
泽子喜欢这样,但是我不太喜欢。如果彼此间有爱情存在的话,就算是为对方做什么也心甘情愿,但是我不喜欢太过火。
好像很多女孩都在学习这种方式。泽子虽然,但她不是那种只要是男人就行的女人。虽然也有那种只要有男人就行的女人,但我觉得那种女人真的很可怜,那种女人通常容易遭受自己亲身父亲的性侵害。
我不知道泽子还有没有其他男人。也许这是个很天真的谎话,她说没有别的男人能像我给她这么多快乐。
泽子把她的脸贴在我的大腿上。
“喂,你记得京都旅馆吗?”
我的腿被打开,我问她。泽子点点头,她的头发刺激着我的腹部和大腿。
“让我们像在京都那样再来一次。”
我刚说完,泽子直摇头说不要。今年冬天我们去了京都。那是在一个小山上的旅馆。我们品尝了最美味的京都怀石料理,喝着辣辣的冷酒,喝醉倒在茶室了。在天花板很低的茶室里有很糜烂的东西,打开衣橱,里面藏了好几百幅春宫画。泽子提议模仿这些画的动作。我们真的汗水淋漓地做了,在狭窄的茶室中,我第一次尝到了泽子那里的味道。
“不要,会很痛的。”
泽子摇着头,但她知道我一说出口就是一定要做的。我在下面垫个枕头,双脚打开高高抬起。
“你真是够劲儿。”
我感觉刺激到了极点,对泽子这么说。
泽子的脚在颤抖着。
“马上就行了,通常一定要开到手指宽才行吧?”
“你的那个不是很小吗?”
“也许吧,可总比指头宽吧!你老是这么说我,如果遇见比较内向自卑的男人,你可不要这么说。”
“这样臀部会变大,我不要。”
“可是我喜欢!”
“你喜欢就好,喂,好痛!快点啦!”
因为没有时间吃盒饭,泽子留下盒饭袋,便回公司去了。
我下午两点去公司,和广告公司、电视台和排球协会的人见面,签了三份文件,给十一个地方发去电报,晚上和肯尼亚大使馆的人在浅草吃饭,然后带他们去吉原,最后打电话给泽子问她的身体要不要紧,她用很可爱的声音回答我说,还很痛。我回到饭店,打电话到俱乐部去找了女人来。来的是一个名叫京子、懂得各种床上游戏的女人。
桌子放着录象带,我等不及回家看,就叫服务台帮我拿个录放机来。
“我看过了。”
我打电话给在马德里的岩井。
“怎么样?”
“没错!”
“我说的是真的吧?”
片里的情节是良原美惠在午后的公园里喂鸽子,遇见了来慢跑的年轻的大学生,她很笨拙地问他,要不要去宾馆呢?于是镜头就移到宾馆的床上,我先看到她的镜头,接着是吸吮年轻大学生的身体十几分钟,然后开始压在他身上……
“她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怎样?”
“可能是被黑道控制,也可能是因为老公负债才需要做这行吧!”
“这好像是色情片的故事情节!”
“你有何感想?”
“觉得有点垂头丧气的,对了,岩井,你昨天看了带子以后找女人了吧?”
“嗯!”
听声音岩井好像没什么精神。
“我是找了,可是那个女人也像美惠一样,遭遇很多事后,不得已才去当妓女。她也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做了这一行,真是不可思议。”
“什么?”
“我看见美惠时也觉得很失望,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悲伤而失望,总之就是失望得浑身没劲儿,是不是这样?”
“不错。
“为什么会这样呢?”
总之我们对女人还不太了解,我下了个含糊的结论后就挂了电话。京子很快就来了。门刚打开,她就紧抱着我狂吻起来。
趁着京子洗澡,我又看一次录像带。感觉肚子饿了,我便打开泽子带来的盒饭吃。
虽然我没跟岩井说,但是我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因为良原美惠去演三级片而觉得悲伤,而是看见别的男人也能让美惠感到快乐,才知道自己是多余的,因此觉得沮丧。
我和岩井,恐怕所有的男人都会喜欢所有的女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给女人幸福。也许是美惠自己不求上进,但我并不觉得她是不幸的人。
京子洗完澡出来。
“啊,你在看色情片?“
我告诉她那女主角是我高中同学,我高中时还跟她约会过,她也做盒饭给我吃。
京子比屏幕上的良原美惠。也比泽子年轻多了。
我点着了香烟,京子发光的还滴着水珠,看着正在做爱的美惠,我说了一声好没劲。
“一个半老徐娘能有这样的身材就算不错了。
京子说。
他会向你行个礼,问你要去哪儿,如果你说“塞可利克寺院”的话,他就会让你进电梯,和你一起来到四楼。这栋楼的外表和内部陈设以及警卫人员,都和一般郊区的高级住宅区一样。这裹住着各种行业的人,有按摩中心并不是个秘密。到了四楼,警卫指指门牌,然后他又搭电梯下去。
入口处铺着地毯。先向右走,最后再向左转。
厚重的木板门开了。
门的那一边站了一排只穿着薄衣的女人,里面有蒸气室、桑那浴室、全身美容室、淋浴室和水床。
我在纽约时,只去过那里两次。第一次是去洗桑拿浴,第二次是去按摩。一位有名的运动员请我吸可卡因,我对毒品没兴趣,但他说只是花钱抱抱女人不是很无聊吗?我并不是第一次吸可卡因,但是从没吸过这么纯的。将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的可卡因直接放在火上烧,吸它的气体,当然很过瘾。“并不是吸了可卡因就会性欲高涨,但是对于你所渴望的对象确实有作用,所以对那些小姐最合适了。”那位运动员说的报对。
有七、八个按摩女郎,她们并没有穿内衣或泳装,全都盛装出场。她们在这里面好像被看管着,但其实并没有被强制行动。她们中多数生于富裕之家,连个口红都没带,就干然一身地搭机或乘船来到美国。她们在这个寺院里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赚美金。只要一年时间,她们就能挣到足够的钱,说一口很流利的英语,走在曼哈顿街上又是另一个人。
据说这种事情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这是一位波兰裔的新西兰代理社长告诉我的。
2
我吸着可卡因,接着选了一位叫“安”的中法混血姑娘。我只记得她的名字,长相倒是忘记了。她的身材很好,够得上高级妓女的标准。那里的姑娘身材都很好,但是也有缺点。
她的牙齿长得不美,臀部下垂,脚踝过粗,背后有浓毛。其他部位长得都很匀称美丽。
当我回忆那些事时,突然想起美空云雀的歌。
我对音乐的兴趣很广泛,但是没有特别喜欢的,只要旋律好我就会买。
我走向唱盘架。想在两千多张CD中找出美空云雀的歌实在很难,我想该找个时间按名字顺序整理一下。
没有找到,我想找别的歌听听,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是从马德里打来的,打电话的我高中时的铁哥们儿。岩井打电话来说有三位马拉松选手答应签约。
“岩井,你喝醉了?”
“喝多了,对不起,但我还是拟好合同了。价码很便宜,是波多黎各的选手,只要一千五百美元,踢世界杯水平的足球选手一天才三十美金,很合适吧?”
“知道了,我现在不想和你谈公事。”
“喂,是不是嫌我醉了,我头脑很清醒,你记得美惠吗?”
“哪里的女人?”
“不是那个啦,四班的同学,我们一年级四班的同学,二年级时她转学到四国了。”
“是良原美惠吗?”
“是”
我和岩井都喜欢良原美惠。对正常的十六岁男孩来说,没有人会不喜欢那样的女孩的。家也好,又漂亮又聪明,爸爸是公司的大老板。
“我之所以会喝醉,全是为了美惠,你相信吗?”
“你见到她了吗?”
我和岩井都曾跟美惠约会过,是在植物园。不知道为什么模范生似的偶像人物美惠会跟我们这种常逃学的坏小子交往。那时美惠还从家里带过盒饭给我吃。我和岩井都认为,也许那样的人也有寂寞的时候吧!所以有人约她就会很高兴。
“应该算看见,不过只是见到她的脸而已。”
“她好像跟了一个傻乎乎的商社职员结婚,那家伙长得很矮,跟你差不多吧。哪天介绍你去一个好地方,拥里有个叫莉达的黑人女孩。”
“不是,我不是真放想见美惠钧。”
“露线地了吧!”
“她在演三级片。”
“你说什么?”
“以前流行的只是风情女郎,现在波多黎各最热门的就是日本的色情录像带。”
“我知道。”
“那里的人已经看腻了东南亚女人主演的色情片了,现在日本女郎是最受欢迎的。”
“你在哪里见到她的?”
“在马德里电视台运动部头头的办公室,她见到我只是笑笑,我也朝她一笑。你知道,我看见女人都会笑的。”
“会不会看错人了,美惠都三十二岁了,还演三级片?和外国人一起演吗?”
“她演一个关西人的太太,是和一个年轻的日本小伙子一起演。平常我看这些片子都觉得没什么,但是那次看过后,我真的胃都抽筋了。”
“知道片名吗?”
《再度重逢人妻的悲伤性态》
“人生真是痛苦。”
“你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看。”
“我不想看。”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醉吧?”
“还是好好工作吧!”
“知道了,我不打电话了,发传真给你。”
挂掉电话后,我又继续找CD。边听着歌,安的浓毛和美惠的脸一直在我的眼前交错出现。
那是马德里的深夜。岩井找了个女人来,把美惠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
3
我打电话给泽子,泽子是一家大建筑公司秘书科的职员,二十八岁,还没结婚。
“是我。”
“你今天起得真早。”
“朋友打来国际电话吵醒了我。中午时可不可以跟你见个面?”
“好啊!我的床变成了红色了。”
“月经来了吗?”
“铺床单时染到的,刚好在正中间。”
“当秘书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现在有没人在。”
“过来时带些三明治吧!”
“我今天带了盒饭,我有预感你会打电话来,所以做了两份儿盒饭。一起吃吧!”
打完电话后,我马上订好饭店房间,然后在上午十点出门。检查车子发动机时,来打扫的广美姐笑着跟我道早安,走进了家门。广美长得比我的前妻还丑几倍,所以每次看到广美时我就觉得前妻很美,心中难免有些后悔。
我先把车子停在饭店的停车场,然后搭出租车去新宿。听说在歌舞伎街的情趣用品商店中有《再度相逢人妻的悲伤性态》这部片子。那家店里没有,但主人说他会从别的连锁店调片子来,要我下午再来拿。我先付了一半的定金,请他在片子到后送到饭店的前台。
“好热!”
泽子擦着脖子上的汗水,走进房里,快步来到窗边,眺望着下面的公园好一会儿,然后拉上窗帘。
“我最讨厌看到小孩在阳光底下跑,把脸晒得通红的。”
说完她将一个纸袋放在桌上,纸袋中散发出令人怀念的味道。那是盒饭的味道。
“关掉空调吧!我想光着身出汗。”
“你不是一热就心烦吗?别逞能了。”我说。
“因为劳累出开才悲惨呢。我先去冲个澡好吗?还是你想先闻我的味儿?
泽子边说边脱掉衬衫。三年前我就认识她了,也许现在说来也没人会信,第一次见到泽子时,她还是个处女。二十五岁还是处女,真是稀罕的动物,我那时是这么想的。
一般来说,如果是丑女孩的话,过了二十岁还是处女,肯定会让人有种不利索的感觉。
泽子那个地方淡淡的毛是下垂的,它让我想起在纽约的安。泽子一丝不挂地将床单盖在身上。
我并不是因为泽子才和前妻离婚的,而是因为我经常出国的缘故。我太太喜欢夫妻二十四小时都能在一起,共同享受酸甜苦辣,丈夫汗流侠背地修理桌椅,太太在厨房里烤着饼干或蛋糕,吃饭的时间到了就敲个钟,大家一起陶醉在天伦之乐中。
前妻和我离婚后就回到她的家乡,和一个从事建材业的男人结婚,生了两个小孩。不知道她变胖了没有,她每年都会寄明信片给我。
不知她是不是在向我炫耀她的幸福生活。
泽子吻着我。她抬起眼看着我,用她那擦着鲜红指甲油的双手轻柔地抚摸着我的下腹,用舌头舔着。
“你抽烟吧!“
她说,继续将脸埋在我身上。看着我抽烟最能令她感到兴奋,我记得她以前这么说过。
“可以再来一次吗?”
“相反顺序的话还可以。”
“先来我的,接着是用嘴吗?”
“是”
“为什么?哪一个才是主菜?用嘴不是开胃菜吗?”
“开胃菜吃饱了,主菜会吃不下。”
泽子喜欢这样,但是我不太喜欢。如果彼此间有爱情存在的话,就算是为对方做什么也心甘情愿,但是我不喜欢太过火。
好像很多女孩都在学习这种方式。泽子虽然,但她不是那种只要是男人就行的女人。虽然也有那种只要有男人就行的女人,但我觉得那种女人真的很可怜,那种女人通常容易遭受自己亲身父亲的性侵害。
我不知道泽子还有没有其他男人。也许这是个很天真的谎话,她说没有别的男人能像我给她这么多快乐。
泽子把她的脸贴在我的大腿上。
“喂,你记得京都旅馆吗?”
我的腿被打开,我问她。泽子点点头,她的头发刺激着我的腹部和大腿。
“让我们像在京都那样再来一次。”
我刚说完,泽子直摇头说不要。今年冬天我们去了京都。那是在一个小山上的旅馆。我们品尝了最美味的京都怀石料理,喝着辣辣的冷酒,喝醉倒在茶室了。在天花板很低的茶室里有很糜烂的东西,打开衣橱,里面藏了好几百幅春宫画。泽子提议模仿这些画的动作。我们真的汗水淋漓地做了,在狭窄的茶室中,我第一次尝到了泽子那里的味道。
“不要,会很痛的。”
泽子摇着头,但她知道我一说出口就是一定要做的。我在下面垫个枕头,双脚打开高高抬起。
“你真是够劲儿。”
我感觉刺激到了极点,对泽子这么说。
泽子的脚在颤抖着。
“马上就行了,通常一定要开到手指宽才行吧?”
“你的那个不是很小吗?”
“也许吧,可总比指头宽吧!你老是这么说我,如果遇见比较内向自卑的男人,你可不要这么说。”
“这样臀部会变大,我不要。”
“可是我喜欢!”
“你喜欢就好,喂,好痛!快点啦!”
因为没有时间吃盒饭,泽子留下盒饭袋,便回公司去了。
我下午两点去公司,和广告公司、电视台和排球协会的人见面,签了三份文件,给十一个地方发去电报,晚上和肯尼亚大使馆的人在浅草吃饭,然后带他们去吉原,最后打电话给泽子问她的身体要不要紧,她用很可爱的声音回答我说,还很痛。我回到饭店,打电话到俱乐部去找了女人来。来的是一个名叫京子、懂得各种床上游戏的女人。
桌子放着录象带,我等不及回家看,就叫服务台帮我拿个录放机来。
“我看过了。”
我打电话给在马德里的岩井。
“怎么样?”
“没错!”
“我说的是真的吧?”
片里的情节是良原美惠在午后的公园里喂鸽子,遇见了来慢跑的年轻的大学生,她很笨拙地问他,要不要去宾馆呢?于是镜头就移到宾馆的床上,我先看到她的镜头,接着是吸吮年轻大学生的身体十几分钟,然后开始压在他身上……
“她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怎样?”
“可能是被黑道控制,也可能是因为老公负债才需要做这行吧!”
“这好像是色情片的故事情节!”
“你有何感想?”
“觉得有点垂头丧气的,对了,岩井,你昨天看了带子以后找女人了吧?”
“嗯!”
听声音岩井好像没什么精神。
“我是找了,可是那个女人也像美惠一样,遭遇很多事后,不得已才去当妓女。她也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做了这一行,真是不可思议。”
“什么?”
“我看见美惠时也觉得很失望,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悲伤而失望,总之就是失望得浑身没劲儿,是不是这样?”
“不错。
“为什么会这样呢?”
总之我们对女人还不太了解,我下了个含糊的结论后就挂了电话。京子很快就来了。门刚打开,她就紧抱着我狂吻起来。
趁着京子洗澡,我又看一次录像带。感觉肚子饿了,我便打开泽子带来的盒饭吃。
虽然我没跟岩井说,但是我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因为良原美惠去演三级片而觉得悲伤,而是看见别的男人也能让美惠感到快乐,才知道自己是多余的,因此觉得沮丧。
我和岩井,恐怕所有的男人都会喜欢所有的女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给女人幸福。也许是美惠自己不求上进,但我并不觉得她是不幸的人。
京子洗完澡出来。
“啊,你在看色情片?“
我告诉她那女主角是我高中同学,我高中时还跟她约会过,她也做盒饭给我吃。
京子比屏幕上的良原美惠。也比泽子年轻多了。
我点着了香烟,京子发光的还滴着水珠,看着正在做爱的美惠,我说了一声好没劲。
“一个半老徐娘能有这样的身材就算不错了。
京子说。
和她见面是在我常住的赤皈高层饭店。
当时她只有二十几岁,是一家旅游杂志社的编辑。在电话中她说是我的影迷,于是我接受了她的采访。
我叫樱井洋一,早先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广告片剪辑师,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拍了几部电影,也接了一些广告制作。凭着一张巴黎剧场的照片让我名利双收。日本女孩对巴黎有种近乎痴狂的迷恋。有了航空公司的赞助,我更可以到各地去拍电影,先是巴黎,接着是纽约、伦敦、罗马、香港,一年拍一部,大家都叫我国际导演。我赚了很多钱,但生活方式也因此而发生改变,结果老婆离我而去,原因是杂志上刊登了我和伦敦篇的那位女主角,后来我们正式离婚了。离婚后,和女演员谈恋爱又分手,我渐渐成了招人讨厌的角色。我拍戏全都是为了钱,有时我也很懒,但我的电影却是部部卖座,于是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尽管要支付前妻和孩子们的赡养费,但我还是有很多钱。因为我的知名度和财势,很容易就会有女人主动投入我的怀抱。我差不多两个月换一个女人,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四年。我跟各种女演员都交往过,也跟模特儿、女护士发生过关系。因为又抽烟又喝酒,生活没有规律,每天都是大鱼大肉,所以气色变得很差,肌肉也开始松弛,胃、肝和心脏都出现毛病。我不过才四十岁,身体状况却像年过半百的老男人。我和各种女人上过床,但也消耗了很多精力。
是她救了我,她叫赤川美枝子,我认识她时她才二十六岁。
“百忙之中您还是答应接受我的采访,非常感谢。可以谈谈有关您拍片的事吗?”
她长得很普通,但我对她很有好感。她说话的语气很温柔,有双漂亮的手,皮肤白嫩,不禁让我想起离婚的前妻。我前妻也有双漂亮的手。
“我想谈谈有关《进军南方》的事,樱井先生到过许多国家旅行,哪些国家或城市会让您有南国的印象呢?”
虽然已经是下午,但因前一天晚上的,还是让我觉得身体不大舒服。胃很痛,头也发沉。
她有双和我前妻一样的手,虽然使我有些伤感,但我对她的印象确实很好。我们开始了访谈。
“南国的城市中,您喜欢哪些地方呢?”
我的眼睛总是忍不住瞄她的手。真美。
“我心目中的南国,和南国的旅游胜地有不一样的风情。”
“是吗?可以具体讲讲吗?”
“我无法说得很具体。”
“那是否可以告诉我,您喜欢南国的哪些地方呢?”
“说起南国来,现在仍然存在着南北问题。如果说南国是指发展中国家,那么智利就不是南国,波多黎各就是吧!但如果照你的说法,希腊也是南国了?”
“希腊也好,波多黎各也好,我只是想知道樱井先生印象中的南国是什么样的。那寒冷和炎热地区,您喜欢哪一个?”
“炎热的!”
“为什么?”
“我心脏不好,所以不喜欢寒冷的地方。”
“那今后您是否会以热带都市为舞台背景?”
“比如说哪里?”
“什么?”
“哪个热带都市?”
“新加坡、牙买加、迈阿密,或是摩洛哥什么的。”
“我的工作本来就是要常往国外跑,新加坡是个充满绿色生机却很单调的国家,迈阿密住的全是些有钱的白痴,那里的犯罪率很高,海也一点都不美。至于摩洛哥也只是个观光胜地罢了。”
我不想隐瞒我的不耐烦。赤川美枝子的表情变了,摄影师停止了拍摄,问她怎么了。
她拼命地想找话题,但却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也是个讨厌的人,可是看到她的手更让我生气。于是我说:“对不起,我要回去了。”
赤川美枝子一脸的惊讶,但什么也没说,摄影师想劝阻我。她简直快要哭了,行个礼就走出去了。
两个小时后,杂志社的总编很慌张地打电话给我,他直向我道歉。她没错,失礼的人是我,但我却没有勇气认错,一想起那双手,我又把总编和她都臭骂了一顿。
我生气地挂了电话。我可没闲空儿去考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一个星期后,赤川美枝子寄了封短信来。
“前几天真是对不起,在此向您道歉。后来我辞职了。樱井先生是催化剂,其实我早就想转行。也许这封信是多余的,但我请您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找到了她家的电话。“我是樱井导演,冒昧打电话,真不好意思。”
“啊,不会!”
她有点紧张。
“我想见你,当面向你道歉,五分钟、十分钟就好。”
“对不起,我不想再当旅游杂志的编辑了,我想做旅游方案的企划工作。”
“我知道,我只是想向你道歉。”
“不用了,这样我会感到很尴尬。”
没错,是我一厢情愿要见人家的,但是我一定要再见她一面。她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我想向她表白,也许她会拒绝我。“我有事想问你,可以再讲两、三分钟吗?”
“我已经在听了。”
“与其说是要向你道歉,其实我是想救救自己,因为看见你时,让我想起了我的前妻。”
“幄?”
她好像很惊讶。
“我知道外面对我的评价很糟糕,我的生活问题很多,但是我不会乱说话。你的手和我太太的像极了。”
“手?”
“是的。”
“您想说什么呢?”
“我伤了她的心,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知道要见你的理由很无聊,但我真的想向你道歉,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带朋友一起来。求求你,只要五分钟就可以。”
我像个傻瓜一样不停地唠叨。最后她终于答应了。五天后我们饭店的咖啡厅里见面。这五天来我滴酒未沾。
她迟到了五分钟,还是穿着带有淡淡春天气息的绿色西装。
“我来迟了,您等了很久了吧?”
我尽量不看她的手,幸好她把手藏在桌下。
“不不,我也刚到。”
但这个谎言马上就被拆穿了,她看见烟灰缸里有七、八根烟蒂,微微一笑。
“还是谢谢你来了,虽然我的要求有点过分,但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见你一面。”
“我很高兴,上一次我不是说过吗?我是樱井先生的影迷呢?”
“让你这么一说,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前几天我在电话中说过的话,你大概不是很理解吧”
“您好像说我和您的太太很像。”
“是的,第一眼看见你时,我真的吓了一跳。”
赤川抽起放在桌下的手,用疑惑的神情看着。
“我的手很普通啊!”
说完后她很腼腆地笑着。我看着她的手和笑容,心情顿时平静下来。
“虽说你的手还没有漂亮到可以拍戒指广告,可我觉得长得很均匀,很让人心动。”
“您和太太……”
“四年前离婚了。”
“对不起,我问过了还问。”
“没关系。我太太只是个普通人,我也不是多有才华的人,只是不服输罢了。当我的太太就必须理解这一点,如果不理解的话,就会产生隔阂感,我的话题很无聊吧?”
“不,不是。”
“我和一个女演员来往。女演员都长得很漂亮,只要是男人就没有不动心的。于是我太太就离开了我。后来那个女演员知道自己不是我下部戏的主角时,竟然离我而去。我觉得好寂寞,于是就开始了放荡的生活。每当自己独处时就会想起我太太的手,我太太以前是我的同事,后来和我恋爱结婚。她真的只是个普通女人,跟她分手后,我只记得她的手。看到你的手就让我想起她,我的心开始乱了,所以才对你那么失利,我要向你道歉。”
说完我还是一直盯着她的手。一会儿她的手又放回桌下,她说了声:“我知道。”
从那后我们就经常联系,起初是两三个星期见一面,喝喝茶或吃顿饭,不过每次都在十二点前分手,我也没送她回过家。现在想想,大概是我们两人都想保持距离吧!
她喜欢喝红酒,但我们都避免喝醉,平常只喝一两杯。我们都想着进一步发展关系,但我们却都放不下戒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怕失去她,她也开始感到不安,不知该不该与我更深入地交往。
喝完茶、吃过饭或看完电影后,各自回家。这样的交往持续了半年后,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焦虑感,我们害怕两人的爱情因此而降温,虽然彼此有着特殊的情债,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变成更亲密的朋友。如果没有进展,那就要冷却了。
我逐渐不再跟其他女演员见面,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跟她们断绝关系。我筹备着新片的拍摄工作,我也考虑过要跟赤川美枝子结婚。我想自己要重新开始生活,先拍那些新类型的电影。
在一个吹着凉风的秋夜,我们终于突破了屏障。我送她给一付手套。吃完饭后我带她来到我住的饭店房间里。她很兴奋,一直看着手套,她说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手套。
“在房里戴手套热了些。”
我坐到她身旁,慢慢地帮她脱下手套。当她的手出现在眼前时,我心中激动不已,那是比看到裸体女人更兴奋的感觉。我吻了那双手,然后我们便发生关系了。
我们决定结婚,所有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
发生第一次关系后过了两个月,她来到广告拍摄现场。工作现场很少会有女人来,但因为那时我正患感冒,她送药来了。当时拍片背景是在热带旅游区的海边。画好的蓝天和海,搬来的白沙、椰子树。穿着泳装的女孩走向海边,我忙着取景。模特儿身上穿了件T恤,她的臀部正对镜头。我一直注意盯着模特儿的臀部,如果走路的姿势不好的话,拍出来的效果就不好看。模特儿下半身什么也没穿,我教她怎么走路,她好像有些紧张,我只好尽量放松她的心情。当模特儿放声大笑时,我想起美枝子就在现场,于是很不高兴地回头看看她,她也面无表情地直盯着我。
那一夜我意外地知道了她的另一面。周末时她都会来找我。
“你喜欢那样的屁股户
争吵就从这句话开始。
“不想生气不想嫉妒的话,就不要去我工作的地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在认识你以前,我就是跟那样身材的女人交往,现在因为工作关系,当然也得找这样的人啊!我说过你的手很美,可是每个人美的地方都不一样啊!你不要无理取闹,工作场合中难免会那样,大家都很高兴,难道你要一个人唱反调?我是为了缓解模特儿紧张的情绪才跟她有说有笑的。我想你应该能够体谅。”
在争执时,她一直用“你”字,以前她可都叫我洋一。听到她叫我“你”时,我变得很不安。我知道她真生气了,因为人一生气就会改变对人的称呼。我的前妻是个思想成熟的女人,离婚前后从未说过半句抱怨的话,只是默默地离开了家,但那种方式也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表现。
“不让我去拍片现场看你,可是你不在我就会胡思乱想,想你跟那些女人有说有笑的。我是长得不美,你也说我只是个普通女人,可是我很高兴你喜欢我。我今天才知道来这里见你,对我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
美技子已经陷入歇斯底状态了,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她的症状还算轻,当时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压力造成的,还是她天生就有这种倾向,我需要时间去判断。
“对不起,请你回去!”
我对她说。我想起和她初次见面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她很吃惊地看着我,不知是要哭着说抱歉还是生气,她好像很困惑。
“美技子,你应该知道我不是个坏人,我只是在工作,我并不想摸那模特儿的屁股。就算主角不是年轻女孩,是只猫或象,我还是要摸它们的屁股。现在你的心情不好,我们不要在一起,你快回去吧!”
这是一种测试,美技子脸上浮现出更惊恐的表情,突然间变得很可怕。没有必要跟她说“我知道”、“对不起”。如果她能客观看待自己,心情恢复平静,那我的测试就算成功了。我开口叫她回去,是为了让她冷静些。人要使自己恢复冷静是需要花费些精力的。
“你在说些什么?”
美枝子叫声更大。我的期望落空了。
“你说不喜欢摸屁股?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晚上就带那些法国女孩、意大利女孩去高级酒吧喝酒,这不就可以整晚摸个够吗?我知道,在认识我之前你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大家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不但不觉得自己不对,还自以为很了不起,是不是?”
发完牢骚后,她哭了。她还很有精神,只是无法接受打击。我真怕她会有更极端的表现。我走近她,抱着她的肩膀。她边哭边将我的手拨开,但还是接受了我,嘴里不知叨咕着什么,可能是“对不起”、“原谅我”之类的吧!
后来她又发作了好几次,但我不想离开她,每次争吵后我们就以做爱收场。我不愿和她分手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争吵后做爱真是件快乐刺激的事。另一个理由是她的手实在太吸引我了。我曾遇见过三位这样歇斯底里的人,但只有美枝子才能让我感到这么的刺激兴奋。我想我可能是为了有的性关系才放意让她那么激动。每当我骂完她后,她就又哭又叫,求我原谅,求我不要离开她。
我不想和她结婚了,跟这种女人结婚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每当她问我为什么不和她结婚,我就以时机未到为理由搪塞。我可以控制她的歇斯底里,然后享受无与伦比的快乐性关系。真的不想跟她结婚了。当然我也没有发觉我已经伤了她的心,分手的苦酒已经慢慢地酿就。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又发作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樱井先生了。”
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三年时间她不叫我樱井先生了,被她这么一叫,我倒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她看起来一本正经的。
“公司有事吗?”
她摇摇头。她现在在一家旅行社的企划部工作,平常不大跟我讲公司的事。
“不是因为公司。”
说完她笑了,表情怪怪的,我觉得那种笑很倒胃口。
“去年我跟你说我要带团去旅行,所以经常两个星期或一个月不来找你,这事你还记得吗?其实我不是去旅行,我是去看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布巴舞。最初我很高兴这件事只有我知道。我还想过找一天和你一起去看表演。但是我迷上了一名舞蹈家。”
“是古巴人吗?”
“当然是古巴人了,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比我小两岁。”
“和他上过床吗?”
“我不是说我们只是认识吗?我存了很多钱,很久以来都是樱井先生请我吃饭,还买衣服送我,所以我存了很多钱。我叫他来日本,我想和他结婚,所以我不再和你见面了。”
“等一下。
“我已经决定了。”
我颤抖地说:“我们现在就结婚好吗?”
她摇着头笑着说“再见了!”
然后她就走了。
此后我经历了痛苦的一年。刚开始的一个月,我天天打电话给她,但回答我的总是电话录音,她不接电话。我知道情况确实严重了,我和美技子再也不能恢复往日的关系了。我拼命工作,外界给我很高的评价,但是每当我看到新闻报道中出现“古巴”时,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撩拨着我的心,我的心情会低落好一阵子。每晚临睡前我都会想象美枝子和黑人男子做爱的情景,一想到别的男人抓着美枝子的手我就很难过。拍片时,她的手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搞得我无法顺利工作。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当我得知古巴舞蹈团来日本表演时,我便跑去看。我一边伸长脖子寻找美枝子,一边看着表演。
那舞蹈确实很棒,精彩极了,让我暂时忘却了美枝子的事。
以前我也听过古巴音乐。古巴音乐有疗伤的作用,当我听着古巴音乐时,会减少一些对美枝子的思念。
我们分手一年半左右,美枝子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想挂掉电话,但是我做不到。
“可以谈谈吗?”
她好像醉了,没什么精神。
“跟你分手后发生了很多事。”
我不说话,没什么话好说。
“为什么不说话?”
“我还没从你的事里恢复过来。”
“我好高兴。”
“什么事?”
“我和古巴人掰了。我们可以重新来一次吗?”
“别开玩笑了。”
“你讨厌我?”
“是的。”
“没错,我是很让人讨厌。我是喜欢那个古巴人,只是语言沟通有问题,而且古巴也太远了。”
她好像哭了。
“我被古巴人甩了。我认识一个男孩,他是个不错的孩子,我想和他一起去古巴,但我却因为害怕而半路退出。我现在才知道自己是个傻瓜、是个胆小鬼。他买了机票,和我约好在成田机场见面,可是我没有去。我真是太过分了,是不是,樱井先生?”
“为什么还找我?”
“请你教教我,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了。我每天都想见你,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不管是白天还是睡觉前,我都……”
她不说话了。
“怎么了?”
“我在擦手霜。”
听了她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是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她的手呀!
“不要笑我,这样是不是很傻?”
说完她又陷入沉默,我也不知说什么好。
“我在听古巴音乐。”
我说。她只是笑。
“真的很好听!”
“你知道菲比尔吗?”
“不知道,是歌手吗?”
“嗯,我也不认识,是那个男孩告诉我的。”
“那我就听听看好了。”
“他有一首《她走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手套。”
“手套?”
“你送我的手套啊!”
“啊,我想起来了。”
“我下一次想去古巴时再打电话给你,你要给我勇气啊!”
“好,我和你一起去古巴旅行,叫菲比尔唱那首《她走了》给我们听。”
“好”
我们挂了电话。
那次通话以后,好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接到美技子说要去古巴的电话。
菲比尔的那首《她走了》,我已经听了不下几十遍。那是一首很伤感的曲调优美的歌曲,听完后有种说不出的解脱感,那感觉的确很像那带刺绣的手套。脱掉手套后,就会露出一双世界上最美的手……
当时她只有二十几岁,是一家旅游杂志社的编辑。在电话中她说是我的影迷,于是我接受了她的采访。
我叫樱井洋一,早先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广告片剪辑师,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拍了几部电影,也接了一些广告制作。凭着一张巴黎剧场的照片让我名利双收。日本女孩对巴黎有种近乎痴狂的迷恋。有了航空公司的赞助,我更可以到各地去拍电影,先是巴黎,接着是纽约、伦敦、罗马、香港,一年拍一部,大家都叫我国际导演。我赚了很多钱,但生活方式也因此而发生改变,结果老婆离我而去,原因是杂志上刊登了我和伦敦篇的那位女主角,后来我们正式离婚了。离婚后,和女演员谈恋爱又分手,我渐渐成了招人讨厌的角色。我拍戏全都是为了钱,有时我也很懒,但我的电影却是部部卖座,于是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尽管要支付前妻和孩子们的赡养费,但我还是有很多钱。因为我的知名度和财势,很容易就会有女人主动投入我的怀抱。我差不多两个月换一个女人,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四年。我跟各种女演员都交往过,也跟模特儿、女护士发生过关系。因为又抽烟又喝酒,生活没有规律,每天都是大鱼大肉,所以气色变得很差,肌肉也开始松弛,胃、肝和心脏都出现毛病。我不过才四十岁,身体状况却像年过半百的老男人。我和各种女人上过床,但也消耗了很多精力。
是她救了我,她叫赤川美枝子,我认识她时她才二十六岁。
“百忙之中您还是答应接受我的采访,非常感谢。可以谈谈有关您拍片的事吗?”
她长得很普通,但我对她很有好感。她说话的语气很温柔,有双漂亮的手,皮肤白嫩,不禁让我想起离婚的前妻。我前妻也有双漂亮的手。
“我想谈谈有关《进军南方》的事,樱井先生到过许多国家旅行,哪些国家或城市会让您有南国的印象呢?”
虽然已经是下午,但因前一天晚上的,还是让我觉得身体不大舒服。胃很痛,头也发沉。
她有双和我前妻一样的手,虽然使我有些伤感,但我对她的印象确实很好。我们开始了访谈。
“南国的城市中,您喜欢哪些地方呢?”
我的眼睛总是忍不住瞄她的手。真美。
“我心目中的南国,和南国的旅游胜地有不一样的风情。”
“是吗?可以具体讲讲吗?”
“我无法说得很具体。”
“那是否可以告诉我,您喜欢南国的哪些地方呢?”
“说起南国来,现在仍然存在着南北问题。如果说南国是指发展中国家,那么智利就不是南国,波多黎各就是吧!但如果照你的说法,希腊也是南国了?”
“希腊也好,波多黎各也好,我只是想知道樱井先生印象中的南国是什么样的。那寒冷和炎热地区,您喜欢哪一个?”
“炎热的!”
“为什么?”
“我心脏不好,所以不喜欢寒冷的地方。”
“那今后您是否会以热带都市为舞台背景?”
“比如说哪里?”
“什么?”
“哪个热带都市?”
“新加坡、牙买加、迈阿密,或是摩洛哥什么的。”
“我的工作本来就是要常往国外跑,新加坡是个充满绿色生机却很单调的国家,迈阿密住的全是些有钱的白痴,那里的犯罪率很高,海也一点都不美。至于摩洛哥也只是个观光胜地罢了。”
我不想隐瞒我的不耐烦。赤川美枝子的表情变了,摄影师停止了拍摄,问她怎么了。
她拼命地想找话题,但却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也是个讨厌的人,可是看到她的手更让我生气。于是我说:“对不起,我要回去了。”
赤川美枝子一脸的惊讶,但什么也没说,摄影师想劝阻我。她简直快要哭了,行个礼就走出去了。
两个小时后,杂志社的总编很慌张地打电话给我,他直向我道歉。她没错,失礼的人是我,但我却没有勇气认错,一想起那双手,我又把总编和她都臭骂了一顿。
我生气地挂了电话。我可没闲空儿去考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一个星期后,赤川美枝子寄了封短信来。
“前几天真是对不起,在此向您道歉。后来我辞职了。樱井先生是催化剂,其实我早就想转行。也许这封信是多余的,但我请您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找到了她家的电话。“我是樱井导演,冒昧打电话,真不好意思。”
“啊,不会!”
她有点紧张。
“我想见你,当面向你道歉,五分钟、十分钟就好。”
“对不起,我不想再当旅游杂志的编辑了,我想做旅游方案的企划工作。”
“我知道,我只是想向你道歉。”
“不用了,这样我会感到很尴尬。”
没错,是我一厢情愿要见人家的,但是我一定要再见她一面。她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我想向她表白,也许她会拒绝我。“我有事想问你,可以再讲两、三分钟吗?”
“我已经在听了。”
“与其说是要向你道歉,其实我是想救救自己,因为看见你时,让我想起了我的前妻。”
“幄?”
她好像很惊讶。
“我知道外面对我的评价很糟糕,我的生活问题很多,但是我不会乱说话。你的手和我太太的像极了。”
“手?”
“是的。”
“您想说什么呢?”
“我伤了她的心,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知道要见你的理由很无聊,但我真的想向你道歉,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带朋友一起来。求求你,只要五分钟就可以。”
我像个傻瓜一样不停地唠叨。最后她终于答应了。五天后我们饭店的咖啡厅里见面。这五天来我滴酒未沾。
她迟到了五分钟,还是穿着带有淡淡春天气息的绿色西装。
“我来迟了,您等了很久了吧?”
我尽量不看她的手,幸好她把手藏在桌下。
“不不,我也刚到。”
但这个谎言马上就被拆穿了,她看见烟灰缸里有七、八根烟蒂,微微一笑。
“还是谢谢你来了,虽然我的要求有点过分,但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见你一面。”
“我很高兴,上一次我不是说过吗?我是樱井先生的影迷呢?”
“让你这么一说,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前几天我在电话中说过的话,你大概不是很理解吧”
“您好像说我和您的太太很像。”
“是的,第一眼看见你时,我真的吓了一跳。”
赤川抽起放在桌下的手,用疑惑的神情看着。
“我的手很普通啊!”
说完后她很腼腆地笑着。我看着她的手和笑容,心情顿时平静下来。
“虽说你的手还没有漂亮到可以拍戒指广告,可我觉得长得很均匀,很让人心动。”
“您和太太……”
“四年前离婚了。”
“对不起,我问过了还问。”
“没关系。我太太只是个普通人,我也不是多有才华的人,只是不服输罢了。当我的太太就必须理解这一点,如果不理解的话,就会产生隔阂感,我的话题很无聊吧?”
“不,不是。”
“我和一个女演员来往。女演员都长得很漂亮,只要是男人就没有不动心的。于是我太太就离开了我。后来那个女演员知道自己不是我下部戏的主角时,竟然离我而去。我觉得好寂寞,于是就开始了放荡的生活。每当自己独处时就会想起我太太的手,我太太以前是我的同事,后来和我恋爱结婚。她真的只是个普通女人,跟她分手后,我只记得她的手。看到你的手就让我想起她,我的心开始乱了,所以才对你那么失利,我要向你道歉。”
说完我还是一直盯着她的手。一会儿她的手又放回桌下,她说了声:“我知道。”
从那后我们就经常联系,起初是两三个星期见一面,喝喝茶或吃顿饭,不过每次都在十二点前分手,我也没送她回过家。现在想想,大概是我们两人都想保持距离吧!
她喜欢喝红酒,但我们都避免喝醉,平常只喝一两杯。我们都想着进一步发展关系,但我们却都放不下戒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怕失去她,她也开始感到不安,不知该不该与我更深入地交往。
喝完茶、吃过饭或看完电影后,各自回家。这样的交往持续了半年后,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焦虑感,我们害怕两人的爱情因此而降温,虽然彼此有着特殊的情债,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变成更亲密的朋友。如果没有进展,那就要冷却了。
我逐渐不再跟其他女演员见面,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跟她们断绝关系。我筹备着新片的拍摄工作,我也考虑过要跟赤川美枝子结婚。我想自己要重新开始生活,先拍那些新类型的电影。
在一个吹着凉风的秋夜,我们终于突破了屏障。我送她给一付手套。吃完饭后我带她来到我住的饭店房间里。她很兴奋,一直看着手套,她说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手套。
“在房里戴手套热了些。”
我坐到她身旁,慢慢地帮她脱下手套。当她的手出现在眼前时,我心中激动不已,那是比看到裸体女人更兴奋的感觉。我吻了那双手,然后我们便发生关系了。
我们决定结婚,所有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
发生第一次关系后过了两个月,她来到广告拍摄现场。工作现场很少会有女人来,但因为那时我正患感冒,她送药来了。当时拍片背景是在热带旅游区的海边。画好的蓝天和海,搬来的白沙、椰子树。穿着泳装的女孩走向海边,我忙着取景。模特儿身上穿了件T恤,她的臀部正对镜头。我一直注意盯着模特儿的臀部,如果走路的姿势不好的话,拍出来的效果就不好看。模特儿下半身什么也没穿,我教她怎么走路,她好像有些紧张,我只好尽量放松她的心情。当模特儿放声大笑时,我想起美枝子就在现场,于是很不高兴地回头看看她,她也面无表情地直盯着我。
那一夜我意外地知道了她的另一面。周末时她都会来找我。
“你喜欢那样的屁股户
争吵就从这句话开始。
“不想生气不想嫉妒的话,就不要去我工作的地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在认识你以前,我就是跟那样身材的女人交往,现在因为工作关系,当然也得找这样的人啊!我说过你的手很美,可是每个人美的地方都不一样啊!你不要无理取闹,工作场合中难免会那样,大家都很高兴,难道你要一个人唱反调?我是为了缓解模特儿紧张的情绪才跟她有说有笑的。我想你应该能够体谅。”
在争执时,她一直用“你”字,以前她可都叫我洋一。听到她叫我“你”时,我变得很不安。我知道她真生气了,因为人一生气就会改变对人的称呼。我的前妻是个思想成熟的女人,离婚前后从未说过半句抱怨的话,只是默默地离开了家,但那种方式也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表现。
“不让我去拍片现场看你,可是你不在我就会胡思乱想,想你跟那些女人有说有笑的。我是长得不美,你也说我只是个普通女人,可是我很高兴你喜欢我。我今天才知道来这里见你,对我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
美技子已经陷入歇斯底状态了,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她的症状还算轻,当时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压力造成的,还是她天生就有这种倾向,我需要时间去判断。
“对不起,请你回去!”
我对她说。我想起和她初次见面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她很吃惊地看着我,不知是要哭着说抱歉还是生气,她好像很困惑。
“美技子,你应该知道我不是个坏人,我只是在工作,我并不想摸那模特儿的屁股。就算主角不是年轻女孩,是只猫或象,我还是要摸它们的屁股。现在你的心情不好,我们不要在一起,你快回去吧!”
这是一种测试,美技子脸上浮现出更惊恐的表情,突然间变得很可怕。没有必要跟她说“我知道”、“对不起”。如果她能客观看待自己,心情恢复平静,那我的测试就算成功了。我开口叫她回去,是为了让她冷静些。人要使自己恢复冷静是需要花费些精力的。
“你在说些什么?”
美枝子叫声更大。我的期望落空了。
“你说不喜欢摸屁股?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晚上就带那些法国女孩、意大利女孩去高级酒吧喝酒,这不就可以整晚摸个够吗?我知道,在认识我之前你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大家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不但不觉得自己不对,还自以为很了不起,是不是?”
发完牢骚后,她哭了。她还很有精神,只是无法接受打击。我真怕她会有更极端的表现。我走近她,抱着她的肩膀。她边哭边将我的手拨开,但还是接受了我,嘴里不知叨咕着什么,可能是“对不起”、“原谅我”之类的吧!
后来她又发作了好几次,但我不想离开她,每次争吵后我们就以做爱收场。我不愿和她分手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争吵后做爱真是件快乐刺激的事。另一个理由是她的手实在太吸引我了。我曾遇见过三位这样歇斯底里的人,但只有美枝子才能让我感到这么的刺激兴奋。我想我可能是为了有的性关系才放意让她那么激动。每当我骂完她后,她就又哭又叫,求我原谅,求我不要离开她。
我不想和她结婚了,跟这种女人结婚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每当她问我为什么不和她结婚,我就以时机未到为理由搪塞。我可以控制她的歇斯底里,然后享受无与伦比的快乐性关系。真的不想跟她结婚了。当然我也没有发觉我已经伤了她的心,分手的苦酒已经慢慢地酿就。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又发作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樱井先生了。”
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三年时间她不叫我樱井先生了,被她这么一叫,我倒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她看起来一本正经的。
“公司有事吗?”
她摇摇头。她现在在一家旅行社的企划部工作,平常不大跟我讲公司的事。
“不是因为公司。”
说完她笑了,表情怪怪的,我觉得那种笑很倒胃口。
“去年我跟你说我要带团去旅行,所以经常两个星期或一个月不来找你,这事你还记得吗?其实我不是去旅行,我是去看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布巴舞。最初我很高兴这件事只有我知道。我还想过找一天和你一起去看表演。但是我迷上了一名舞蹈家。”
“是古巴人吗?”
“当然是古巴人了,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比我小两岁。”
“和他上过床吗?”
“我不是说我们只是认识吗?我存了很多钱,很久以来都是樱井先生请我吃饭,还买衣服送我,所以我存了很多钱。我叫他来日本,我想和他结婚,所以我不再和你见面了。”
“等一下。
“我已经决定了。”
我颤抖地说:“我们现在就结婚好吗?”
她摇着头笑着说“再见了!”
然后她就走了。
此后我经历了痛苦的一年。刚开始的一个月,我天天打电话给她,但回答我的总是电话录音,她不接电话。我知道情况确实严重了,我和美技子再也不能恢复往日的关系了。我拼命工作,外界给我很高的评价,但是每当我看到新闻报道中出现“古巴”时,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撩拨着我的心,我的心情会低落好一阵子。每晚临睡前我都会想象美枝子和黑人男子做爱的情景,一想到别的男人抓着美枝子的手我就很难过。拍片时,她的手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搞得我无法顺利工作。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当我得知古巴舞蹈团来日本表演时,我便跑去看。我一边伸长脖子寻找美枝子,一边看着表演。
那舞蹈确实很棒,精彩极了,让我暂时忘却了美枝子的事。
以前我也听过古巴音乐。古巴音乐有疗伤的作用,当我听着古巴音乐时,会减少一些对美枝子的思念。
我们分手一年半左右,美枝子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想挂掉电话,但是我做不到。
“可以谈谈吗?”
她好像醉了,没什么精神。
“跟你分手后发生了很多事。”
我不说话,没什么话好说。
“为什么不说话?”
“我还没从你的事里恢复过来。”
“我好高兴。”
“什么事?”
“我和古巴人掰了。我们可以重新来一次吗?”
“别开玩笑了。”
“你讨厌我?”
“是的。”
“没错,我是很让人讨厌。我是喜欢那个古巴人,只是语言沟通有问题,而且古巴也太远了。”
她好像哭了。
“我被古巴人甩了。我认识一个男孩,他是个不错的孩子,我想和他一起去古巴,但我却因为害怕而半路退出。我现在才知道自己是个傻瓜、是个胆小鬼。他买了机票,和我约好在成田机场见面,可是我没有去。我真是太过分了,是不是,樱井先生?”
“为什么还找我?”
“请你教教我,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了。我每天都想见你,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不管是白天还是睡觉前,我都……”
她不说话了。
“怎么了?”
“我在擦手霜。”
听了她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是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她的手呀!
“不要笑我,这样是不是很傻?”
说完她又陷入沉默,我也不知说什么好。
“我在听古巴音乐。”
我说。她只是笑。
“真的很好听!”
“你知道菲比尔吗?”
“不知道,是歌手吗?”
“嗯,我也不认识,是那个男孩告诉我的。”
“那我就听听看好了。”
“他有一首《她走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手套。”
“手套?”
“你送我的手套啊!”
“啊,我想起来了。”
“我下一次想去古巴时再打电话给你,你要给我勇气啊!”
“好,我和你一起去古巴旅行,叫菲比尔唱那首《她走了》给我们听。”
“好”
我们挂了电话。
那次通话以后,好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接到美技子说要去古巴的电话。
菲比尔的那首《她走了》,我已经听了不下几十遍。那是一首很伤感的曲调优美的歌曲,听完后有种说不出的解脱感,那感觉的确很像那带刺绣的手套。脱掉手套后,就会露出一双世界上最美的手……
“够了吧?我可不是你的朋友,只是你发泄的对象罢了,你好好想一想吧?”
站在我面前垂着头的女人姓赤川,长相很一般。她的名字叫美枝子。樱井洋一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我们大学念的也是同一所,现在我们又都是在广告公司谋职。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凭着实力进了日本第二大广告公司工作,我靠父亲的关系在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人做营业员。父亲四年前去世了,他生前是一个民营电台的重要人物。母亲是位传统保守的大家闺秀,一直很宠我,所以养成了我开放不拘的个性。
樱井洋一和我不一样,他是个做事认真,头脑聪明的人,很早就学会了自立,现在是个名导演,他的电影部部买座。但是他却常吃女人的亏。他以前交往过的那十几个女人我虽没全见过,但我了解她们全都长得不怎么样。他经常很骄傲地给我介绍说,她是个模特儿,会拉小提琴,也在进修戏剧课程,可我知道那些女人全都是他在便宜的酒馆儿里钩上的。他每次都很投入,其中还被一个三流的女演员欺骗过,结果他那称不上美人,但性格却很好的前妻因此离家而走。
“这我知道,可是想到要询问关于古巴的事,我就只想起村田先生您。”
以前我有几次遇见过樱井和这个姓赤川的女人在一起,他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是樱井被她甩了。这个姓赤川的女人喜欢上了一个古巴舞蹈家。赤川才离开的那一阵子,樱井很难过,每天都打电话给我,我很担心他会自杀。我的确很了解古巴,几年前我们公司举办夏季旅游时,我就负责古巴方向。后来我也去过几次古巴,虽然我的西班牙语说的不好,但结识了报多朋友,那些朋友几乎都是音乐家或是歌手,通过我的介绍有些乐团能由日本的唱片公司帮他们发行唱片。伤了男人的心后又说要回来,这种女人顶差劲了。我们三人一见面就要喝点酒,但从来不谈有关古巴的事。人们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酒席上不能谈论古巴的长处。古巴的音乐中最棒的要算古典乐和爵士乐,而这是不能用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
“实在对不起,也没事先打电话来,但我真的有话想问你。”
赤川长得很普通。如果你们到我的公司去看的话,就会觉得她实在不怎么样。她的表清楚楚可怜,可因为她是伤了我好朋友心的女人,所以我一点也不同情她。
“俄真的,你的所作所为对樱井实在是很不公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你只是想知道一些事情吧,对不对?”
“是的。”
赤川小声地回答。她脸上的表情让人无法得知她在想些什么。古巴舞蹈家的水平很高,当他们跳舞时会散发出一股奇特的性感魅力,所以日本女人被他们所吸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古巴人多数都很穷,就算舞蹈家也一样,这些日本女人给他们买衣服,请他们吃饭,这样就能满足她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可是不管是舞蹈家还是音乐家,古巴人的自尊心很强,头脑也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公事或私事,要跟他们交往都需要很充沛的精力和影响力,还要长相好,但赤川却不认为自己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我的好友被你搞得一塌糊涂,你还敢再来找我,要我向你提供有关他的事情,你不觉得自己很狡猾吗?”
“一塌糊涂?”
“你不懂?当然啦,分手这种事很难断定谁对谁错,但我绝对站在朋友这边。”
“樱井先生一定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女孩来取代我……”
“那不过是你的想法,你根本不了解他有多么痛苦,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讲樱井的事,你说有事要问我,我想你是为自己的事吧!”
赤1!I的反应令我感到惊讶,她竟然回答“你说得没错。”然后她开始掉下眼泪。一向被母亲宠爱的我,最讨厌看到长相一般的女人哭。我最受不了人哭了。我们现在可是在公司的会客室里,如果被同事或属下看到这样的场面,大家一定会议论纷纷。他们会说村田经理让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哭了。
“喂,你能不能不哭?”
“对不起,我该回去了。可我还有句话要说,樱井先生和岩井先生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我绝对不是在拍马尼,我是说真的。我的确就是村田先生所说的那种人,凡事只想到自己。因为我太软弱了,没有任何能力,也没多余的心情去考虑到别人。”
赤川嘴上说她要回去了,但却并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我刚才那番话并没有要苛责她的意思,只是说出实话罢了。无论是谁,看见他的好友为了一个女人变成那副模样,一定都会这么做的。但是在外人眼中,可能会以为是我在欺负她。赤川长相很普通,哭的时候又把双手捂在脸上,所以很容易被人误解我在欺负她。我想我还是赶快站起来的好,我的性格和母亲一样,所以我不能不管她。母亲是个极有爱心的人,每次看到电视剧中有弱者被欺负,她就会同情电视中的人物而哭得很伤心。我随了母亲的这种性格。
“好吧,你想问什么?”
听我这么一说,赤川擦着眼泪看着我。她的妆被泪水弄出斑迹,我无法正眼看她。看着她的脸,我心想,她不会有什么魔力吧,不然怎么让男人这么喜欢她!但我还是觉得樱井是个大笨蛋。
“是跟古巴人结婚的事。”
“结婚?”
“我要去古巴跟古巴人结婚,那样我还能保留日本国籍吗?”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这是政府的问题,我向来对法律不熟悉。”
“假如我在古巴生了小孩,再离婚的话,孩子可以带回日本吗?”
“这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有古巴音乐。”
她不再哭了,大概真的要回去了,她心里一定在想,这个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她临走时说她想去古巴。
我想我应该把赤川来找我的事告诉樱井,于是拨通他了电话。他们已经分手一年了,虽然樱井已经从最低谷中走出来了,但是如果他听道赤川这两个字心情还是不好吧!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隐瞒下来的话,对樱井来说太不公平了。告诉他赤川结婚的事可能会让他旧伤复发,但是说不定伤口也能因此恢复。
“喂,我是樱井。”
他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来的一般。虽然现在樱井的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开朗多了,但是我总觉得樱井的声音还和一年前一样。
“村田吗?我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了。”
这种气氛可不适合说赤川的事,因为他的声音像死了亲人或破产了一样。
“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是和赤川相关的事吗?”
“和美枝子有关,但还有另一件事,你和销售业的关系不错吧?”
“就算很熟,到底怎么啦?”
“你不是认识一个朋友,手中有百十张片子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些片子中是不是有的片子?”
“有,但都是拍些名人,大都是把摄影机输藏在爱情宾馆里拍的,最近好像不大听得到这方面的事了,以前是很多的。”
“有我和美枝子做爱的片子。”
“你是不是傻瓜,竟然跑去爱情宾馆!”
“不是爱情宾馆!”
“那是在哪里呢?”
“在饭店,你也知道,就是赤贩饭店的房间里。”
“到底是谁拍的?”
“我。
“你说什么?”
“是我拍的,我有台西德产的迷你型摄影机,我拍过好多次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有一阵子美枝子很歇斯底里吗?为了观察她态度的变化,我用摄影机把她这些行为都录下来了。”
“是赤川拿出去卖的吗?”
“不是她。我没有跟她说,她不知道。”
“我不懂你说什么,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些?”
“我正在给新戏的女主角试镜,突然公司的一个小职员把我叫了过去,他跟我说,有人看过老师您主演的片子,我想那是骗人的。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有种不妙的预感,我回到饭店房里一看,柜子里的录相带只剩下一盘。我原本有五盘,但丢了四盘。柜子的锁并没有被破坏,可是录像带真的被偷走了。”
“一定是赤川知道了偷偷溜进来拿走的。”
“不是,美枝子虽然很开放,但是她不可能把那种东西拿出来给人看。为了方便收藏,我曾经把录好的带子带回南青山的办公室,将带子转换成了VHS制式。我把带子放回饭店的时候,我已经跟美枝子分手一段时间了,所以绝不是她偷的,她从没来过南青山。”
“你为自己的性爱片剪辑?”
“我也知道自己不正常,可是现在不是讨论这种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那个职员是什么人看了带子?”
“我也不认识那个人,听人说他有时会到青山墓地入口处附近的面摊儿吃东西,晚上开出租车赚外快。”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差不多有三十岁,很瘦。”
“面摊儿的客人?”
“这下我要名誉扫地了。只有你会说西班牙话,我真的没有别人可以求了。”
我说我很忙。我真的很忙。其实就算自己的带子流到市面,主角看起来很像自己,但只要始终坚决否认,就不会有人再问。不过如果对方是有名的女演员,那又要另当别论了。我很想拒绝他,可是听他声音好像快要哭出来了。
“真的求你了,你也知道那些带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吧!如果被别人看到,一定以为我是神经病,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你的古巴CD。”
“那有什么关系?”
“那是我这一次电影里要用的。”
我的好心真是害了我。为了让古巴音乐家能够继续在贫困条件下制作高水平的音乐,我很想帮助他们。樱井的电影在日本非常有名,所以我希望他能用古巴音乐作电影配乐。这样一来他就要送一些著作权贸和使用费给这些古巴人。我愿意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快乐。
我带了一名部下驾车来到青山墓地入口处的面摊儿。他叫版木,今年二十六岁,靠我的关系进的公司,在高中和大学时是拳击队的主力。
“犯人的特征通常是戴着一项鸭舌帽,单凭这点要找人的话可能很难。”
皈木喜欢SWA队员所穿的黑色服装。他刚刚让我看了他的武器,有迷魂药、美工刀、装上沙子的细长皮带、金属拳套。
“黑色鸭舌帽是很特殊的象征,最近很少有人会以这种扮相作案。”
“你说他是犯人丁’
“请你不要再问了。”
从面摊儿开张我就一直盯着那里,但已经过了深夜十二点仍不见戴鸭舌帽的人。
“犯人真是出租车司机?”
“这种面摊儿上的客人十有都是出租车司机,但不一定是犯人。”
“上星期四他曾出现过,今天是星期三。”
“出租车公司的上班时间是固定的,可是个体的话就不一定了。但如果他是三十岁左右的人,那应该木是年轻的个体驾驶。”
面摊儿的生意很好。总是有七、八个客人在等着,从穿着看来,可以判断他们几乎全是出租车司机。他们穿着相同的衣服,低头静静地吃着饭。没有什么三十岁的人出现。面摊儿前停了近三十辆出租车,但并不是全为了吃面而停下来,有人边抽着烟边和同伴聊天休息,有人坐在出租车里闭目养神。从这里看不到睡在车内的司机的脸,这就是我叫版木来的原因,他有武器可以下车直看。
“我去仔细观察一下,如果发现可疑的人,我会给你个暗号。”
皈木在一群司机之中显得很突出。如果是平常,肯定会有人质问他“看什么看!”,但可能是因为他的穿着,大家不想惹他吧。他把武器藏在怀里,穿着黑色毛衣、黑色线帽。黑色野战裤、黑靴子,还有那奇特的走路姿式,任凭谁看了都会以为他精神不正常。
他走进停在路边的出租车,一辆一辆的窥探。因没有路灯,皈木整个人消失在黑暗中。
大约过了十分钟,皈木从黑暗中出现。他用双手招呼我,动作好像在跳舞,如果被看见一定会把他抓起来。我下了车朝他走去。
“人不在,但我发现了这个。”
我看见司机旁的位置上有样东西,那是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吃面的人群中没有三十岁模样的年轻人。“也许他到自动售货机那儿买饮料去了。”皈木说完,就听见背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
“你们在于什么?”
四周很暗,看不清他的脸,他的身材瘦瘦高高的。
“没什么,散步时发现车子里有顶鸭舌帽。”我说。
“我父亲是个画家,他以前常戴这顶帽子,真让人怀念。”
我不想被人识破身份就撒了个谎。
那男子打开车门,戴上帽子。饭木举起右手,他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可能是迷魂药吧。
“那这就送给你吧!你戴了它就会想起自己的父亲了。”
好奇怪的家伙!
“不,我不要!”
我很想这么说,但不知为什么却小声音说:“人都死了,再想起来是件痛苦的事。”
那男人说了句没错,就从我的手中接过帽子。这时候对面开来的车的车灯让我看清那人的长相。不是三十岁,应该更年轻一些,大概二十五岁左右吧。单眼皮,看起来比吸水更有女人缘。
“有件事想问你。”
我对坐进车里的那男人说。他戴上帽子回头看着我。
“我想知道关于樱井洋一导演的录像带的事。”
那人听到樱井洋一四个字时,反应很奇怪,好像听到死去的亲人或好友的名字一样。那表情好像这名字触到了他的伤心处。
“你们是?”
“不是。”
“那是这里的人?”
“不是,我们是樱井的朋友,想取回带子。如果你知道的话请告诉我们。”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用低低的声音说:“我有。”
男人带我到了一处狭窄的旧房子里,有个只穿着内衣裹着棉被的女人在睡觉。他说她是他女朋友。女人看见我和皈木,惊恐地用棉被盖着自己逃到角落。男人对她说别怕。
“是樱井洋一的朋友,我想还他们带子。”
男人这么说了,女人还是很害怕,她用惶恐不安的眼神看着我们,全身不停地抖动。我想她可能是哑巴。男人打开小厨房里的大冰箱,里面没什么东西,只有发蔫儿了的韩国泡菜和一瓶咖啡。
“我出去买饮料。”
男人一这么说,躲在房间一角的女人发出动物般的叫声,拼命地摇着头。我说我真的不想喝东西。
男人说要和我再看一次后就将带子还我。我叫皈木回车子里等我,因为没理由让皈木看那种东西。我也不想看。一般来说没有人会想看好友的那种东西。我很想跟他说,我不想看,可不可以马上还我,但是他很迟钝,没看出我的反应。
“我想赶快看完录像带,拿了回家。”
于是在没什么家具,只有一个暖炉的小房间里,我们看起录像带。真是难以置信,那盘带子的画质如此地清楚。床头灯开着,樱井和赤川在做爱。摄相机只有一台,有时将两人裸体全都收入镜头内,有时照着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樱井真不愧是导演,剪辑得绝对够专业。樱井在片头还写了宇:“将我的所有”。
现在不是笑的时候。在屋角一动不动的女人用一种受了伤的野犬般的眼神看着我。屋里好冷,喘气时呼出的是白色的气体。他们两人是怎么在这种地方过的呢?标题结束了,画面变成黑色,可以听到很清楚的声音。是樱井洋一和赤川美枝子的声音,赤I!D哭着喊叫。
“听不见。”
“对不起。”
“听不见。”
“对不起,请原谅我。”
“我不是说听不见吗?好了美枝子,你一定要大叫到门卫和清洁工都赶来才行。快大声地向我道歉、求我原谅。”
“糖原谅我,我不行了,不行了。”
“道歉!”
“对不起!”
“大声点!”
“对不起!”
“流着泪说对不起!”
“对不起!”
画面出现樱井和赤川的脸。赤川哭得脸上的妆都掉没了,头发散在脸上。樱井打了她好几巴掌,挨打时,赤川不停地说对不起。她的脸都红了,她真的哭了。
“知道为什么挨揍吗?”
“知道。”
“你说!”
“我”
“大声点,边哭边说!”
“我又发疯了。”
“发疯了要说什么?”
“最差劲的男人。”
“听不到。”
“最差劲的男人。”
赤川不光脸被打,而且全身都被打了。尤其是屁股上有好几十条青瘀。赤川的屁股挨打时,镜头就会对着她的屁股来个大特写。我觉得这情景太残酷,有些不敢看,那男人却边看边笑。后来樱井和赤川所始做爱了。在比利波蒂的“将我的所有”音乐声中,他们翻云覆水。
看完了,男人将带子取出放在盒子里交给我。带子背面贴了张纸签,写着“将我的所有”。
我说了声:“走了。”但男人要我等一下。
“她有点…”
男人说完看着躲在一边的女人,女人好像发现了什么一直摇着头。男人站起来走近她,将她的手放在肩上,很温柔地说:“不要怕/我从来未听过如此温柔,让人安心的语调。
“不要怕,他们不是也不是流氓,是樱井洋一的朋友。刚才在车上我问过他。他和樱井念的同一所高中,他们是朋友,所以我想跟他说一些关于你的事,拿这些带子,我和你都没有什么恶意吧?”
女人点了几下头。
“我绝对没有说谎,她叫美里子,美里子也不会说谎。她很神经质,所以不知道怎么和陌生人沟通。但是你们不要误解她,这世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要再说我和美里子的故事了,我们住在一起时就约定好要彼此真实,我们从不说谎,你们要相信我们。”
我说相信你们。
“我想当演员,我是樱井先生的影迷,我很尊敬他。所以美里子就在樱井先生的饭店当清洁工。后来怎样你也知道吧?”
我点点头。
美里子趁打扫房间时偷了录像带。
“有件事我想问你,可以吗?”
“你问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要让我看带子?”
“没什么理由。我想最后大家一起看嘛!虽说是私人带子,但场景很美,配乐也好听。”
“比利波蒂?”
“那是女歌手的名字?”
“是的。”
“她的声音并不好听,但曲子旋律很美。美里子也很喜欢那首曲子。只要是她喜欢的歌手,她就会想办法去收藏那歌手的所有CD。
“等一下。”我说。我问他可以让我听听那盘CD吗?男人显得很惊讶,但还是同意了。
我们就在小房间里听着“将我的所有”。真是很美。
古巴的音乐实在太棒了。那音乐使寒冷的屋内流动着丝丝暖意。
“我想再听一次。”
曲子结束时,美里子突然这么说。她还是很害怕地缩着身,脚却在打拍子。
“CD送你好了,喜欢就听个够。”
我走了出去。
我告诉皈木说,我们作战成功。当我坐进车子时,隐约听见从那屋里传来的“将我的所有”的歌声。
请带走我的所有,
我的唇,
想被你带走,
我的手腕,
想被你拥抱,
你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
没有你我能生存吗?
你不只带走了我的心
也想带走我的全部也将我的所有
带走
听着那歌声,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录像带里的画面。赤川美枝子擦着红指甲油的手在动着,不久就静止了。
站在我面前垂着头的女人姓赤川,长相很一般。她的名字叫美枝子。樱井洋一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我们大学念的也是同一所,现在我们又都是在广告公司谋职。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凭着实力进了日本第二大广告公司工作,我靠父亲的关系在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人做营业员。父亲四年前去世了,他生前是一个民营电台的重要人物。母亲是位传统保守的大家闺秀,一直很宠我,所以养成了我开放不拘的个性。
樱井洋一和我不一样,他是个做事认真,头脑聪明的人,很早就学会了自立,现在是个名导演,他的电影部部买座。但是他却常吃女人的亏。他以前交往过的那十几个女人我虽没全见过,但我了解她们全都长得不怎么样。他经常很骄傲地给我介绍说,她是个模特儿,会拉小提琴,也在进修戏剧课程,可我知道那些女人全都是他在便宜的酒馆儿里钩上的。他每次都很投入,其中还被一个三流的女演员欺骗过,结果他那称不上美人,但性格却很好的前妻因此离家而走。
“这我知道,可是想到要询问关于古巴的事,我就只想起村田先生您。”
以前我有几次遇见过樱井和这个姓赤川的女人在一起,他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是樱井被她甩了。这个姓赤川的女人喜欢上了一个古巴舞蹈家。赤川才离开的那一阵子,樱井很难过,每天都打电话给我,我很担心他会自杀。我的确很了解古巴,几年前我们公司举办夏季旅游时,我就负责古巴方向。后来我也去过几次古巴,虽然我的西班牙语说的不好,但结识了报多朋友,那些朋友几乎都是音乐家或是歌手,通过我的介绍有些乐团能由日本的唱片公司帮他们发行唱片。伤了男人的心后又说要回来,这种女人顶差劲了。我们三人一见面就要喝点酒,但从来不谈有关古巴的事。人们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酒席上不能谈论古巴的长处。古巴的音乐中最棒的要算古典乐和爵士乐,而这是不能用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
“实在对不起,也没事先打电话来,但我真的有话想问你。”
赤川长得很普通。如果你们到我的公司去看的话,就会觉得她实在不怎么样。她的表清楚楚可怜,可因为她是伤了我好朋友心的女人,所以我一点也不同情她。
“俄真的,你的所作所为对樱井实在是很不公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你只是想知道一些事情吧,对不对?”
“是的。”
赤川小声地回答。她脸上的表情让人无法得知她在想些什么。古巴舞蹈家的水平很高,当他们跳舞时会散发出一股奇特的性感魅力,所以日本女人被他们所吸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古巴人多数都很穷,就算舞蹈家也一样,这些日本女人给他们买衣服,请他们吃饭,这样就能满足她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可是不管是舞蹈家还是音乐家,古巴人的自尊心很强,头脑也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公事或私事,要跟他们交往都需要很充沛的精力和影响力,还要长相好,但赤川却不认为自己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我的好友被你搞得一塌糊涂,你还敢再来找我,要我向你提供有关他的事情,你不觉得自己很狡猾吗?”
“一塌糊涂?”
“你不懂?当然啦,分手这种事很难断定谁对谁错,但我绝对站在朋友这边。”
“樱井先生一定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女孩来取代我……”
“那不过是你的想法,你根本不了解他有多么痛苦,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讲樱井的事,你说有事要问我,我想你是为自己的事吧!”
赤1!I的反应令我感到惊讶,她竟然回答“你说得没错。”然后她开始掉下眼泪。一向被母亲宠爱的我,最讨厌看到长相一般的女人哭。我最受不了人哭了。我们现在可是在公司的会客室里,如果被同事或属下看到这样的场面,大家一定会议论纷纷。他们会说村田经理让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哭了。
“喂,你能不能不哭?”
“对不起,我该回去了。可我还有句话要说,樱井先生和岩井先生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我绝对不是在拍马尼,我是说真的。我的确就是村田先生所说的那种人,凡事只想到自己。因为我太软弱了,没有任何能力,也没多余的心情去考虑到别人。”
赤川嘴上说她要回去了,但却并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我刚才那番话并没有要苛责她的意思,只是说出实话罢了。无论是谁,看见他的好友为了一个女人变成那副模样,一定都会这么做的。但是在外人眼中,可能会以为是我在欺负她。赤川长相很普通,哭的时候又把双手捂在脸上,所以很容易被人误解我在欺负她。我想我还是赶快站起来的好,我的性格和母亲一样,所以我不能不管她。母亲是个极有爱心的人,每次看到电视剧中有弱者被欺负,她就会同情电视中的人物而哭得很伤心。我随了母亲的这种性格。
“好吧,你想问什么?”
听我这么一说,赤川擦着眼泪看着我。她的妆被泪水弄出斑迹,我无法正眼看她。看着她的脸,我心想,她不会有什么魔力吧,不然怎么让男人这么喜欢她!但我还是觉得樱井是个大笨蛋。
“是跟古巴人结婚的事。”
“结婚?”
“我要去古巴跟古巴人结婚,那样我还能保留日本国籍吗?”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这是政府的问题,我向来对法律不熟悉。”
“假如我在古巴生了小孩,再离婚的话,孩子可以带回日本吗?”
“这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有古巴音乐。”
她不再哭了,大概真的要回去了,她心里一定在想,这个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她临走时说她想去古巴。
我想我应该把赤川来找我的事告诉樱井,于是拨通他了电话。他们已经分手一年了,虽然樱井已经从最低谷中走出来了,但是如果他听道赤川这两个字心情还是不好吧!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隐瞒下来的话,对樱井来说太不公平了。告诉他赤川结婚的事可能会让他旧伤复发,但是说不定伤口也能因此恢复。
“喂,我是樱井。”
他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来的一般。虽然现在樱井的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开朗多了,但是我总觉得樱井的声音还和一年前一样。
“村田吗?我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了。”
这种气氛可不适合说赤川的事,因为他的声音像死了亲人或破产了一样。
“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是和赤川相关的事吗?”
“和美枝子有关,但还有另一件事,你和销售业的关系不错吧?”
“就算很熟,到底怎么啦?”
“你不是认识一个朋友,手中有百十张片子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些片子中是不是有的片子?”
“有,但都是拍些名人,大都是把摄影机输藏在爱情宾馆里拍的,最近好像不大听得到这方面的事了,以前是很多的。”
“有我和美枝子做爱的片子。”
“你是不是傻瓜,竟然跑去爱情宾馆!”
“不是爱情宾馆!”
“那是在哪里呢?”
“在饭店,你也知道,就是赤贩饭店的房间里。”
“到底是谁拍的?”
“我。
“你说什么?”
“是我拍的,我有台西德产的迷你型摄影机,我拍过好多次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有一阵子美枝子很歇斯底里吗?为了观察她态度的变化,我用摄影机把她这些行为都录下来了。”
“是赤川拿出去卖的吗?”
“不是她。我没有跟她说,她不知道。”
“我不懂你说什么,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些?”
“我正在给新戏的女主角试镜,突然公司的一个小职员把我叫了过去,他跟我说,有人看过老师您主演的片子,我想那是骗人的。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有种不妙的预感,我回到饭店房里一看,柜子里的录相带只剩下一盘。我原本有五盘,但丢了四盘。柜子的锁并没有被破坏,可是录像带真的被偷走了。”
“一定是赤川知道了偷偷溜进来拿走的。”
“不是,美枝子虽然很开放,但是她不可能把那种东西拿出来给人看。为了方便收藏,我曾经把录好的带子带回南青山的办公室,将带子转换成了VHS制式。我把带子放回饭店的时候,我已经跟美枝子分手一段时间了,所以绝不是她偷的,她从没来过南青山。”
“你为自己的性爱片剪辑?”
“我也知道自己不正常,可是现在不是讨论这种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那个职员是什么人看了带子?”
“我也不认识那个人,听人说他有时会到青山墓地入口处附近的面摊儿吃东西,晚上开出租车赚外快。”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差不多有三十岁,很瘦。”
“面摊儿的客人?”
“这下我要名誉扫地了。只有你会说西班牙话,我真的没有别人可以求了。”
我说我很忙。我真的很忙。其实就算自己的带子流到市面,主角看起来很像自己,但只要始终坚决否认,就不会有人再问。不过如果对方是有名的女演员,那又要另当别论了。我很想拒绝他,可是听他声音好像快要哭出来了。
“真的求你了,你也知道那些带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吧!如果被别人看到,一定以为我是神经病,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你的古巴CD。”
“那有什么关系?”
“那是我这一次电影里要用的。”
我的好心真是害了我。为了让古巴音乐家能够继续在贫困条件下制作高水平的音乐,我很想帮助他们。樱井的电影在日本非常有名,所以我希望他能用古巴音乐作电影配乐。这样一来他就要送一些著作权贸和使用费给这些古巴人。我愿意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快乐。
我带了一名部下驾车来到青山墓地入口处的面摊儿。他叫版木,今年二十六岁,靠我的关系进的公司,在高中和大学时是拳击队的主力。
“犯人的特征通常是戴着一项鸭舌帽,单凭这点要找人的话可能很难。”
皈木喜欢SWA队员所穿的黑色服装。他刚刚让我看了他的武器,有迷魂药、美工刀、装上沙子的细长皮带、金属拳套。
“黑色鸭舌帽是很特殊的象征,最近很少有人会以这种扮相作案。”
“你说他是犯人丁’
“请你不要再问了。”
从面摊儿开张我就一直盯着那里,但已经过了深夜十二点仍不见戴鸭舌帽的人。
“犯人真是出租车司机?”
“这种面摊儿上的客人十有都是出租车司机,但不一定是犯人。”
“上星期四他曾出现过,今天是星期三。”
“出租车公司的上班时间是固定的,可是个体的话就不一定了。但如果他是三十岁左右的人,那应该木是年轻的个体驾驶。”
面摊儿的生意很好。总是有七、八个客人在等着,从穿着看来,可以判断他们几乎全是出租车司机。他们穿着相同的衣服,低头静静地吃着饭。没有什么三十岁的人出现。面摊儿前停了近三十辆出租车,但并不是全为了吃面而停下来,有人边抽着烟边和同伴聊天休息,有人坐在出租车里闭目养神。从这里看不到睡在车内的司机的脸,这就是我叫版木来的原因,他有武器可以下车直看。
“我去仔细观察一下,如果发现可疑的人,我会给你个暗号。”
皈木在一群司机之中显得很突出。如果是平常,肯定会有人质问他“看什么看!”,但可能是因为他的穿着,大家不想惹他吧。他把武器藏在怀里,穿着黑色毛衣、黑色线帽。黑色野战裤、黑靴子,还有那奇特的走路姿式,任凭谁看了都会以为他精神不正常。
他走进停在路边的出租车,一辆一辆的窥探。因没有路灯,皈木整个人消失在黑暗中。
大约过了十分钟,皈木从黑暗中出现。他用双手招呼我,动作好像在跳舞,如果被看见一定会把他抓起来。我下了车朝他走去。
“人不在,但我发现了这个。”
我看见司机旁的位置上有样东西,那是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吃面的人群中没有三十岁模样的年轻人。“也许他到自动售货机那儿买饮料去了。”皈木说完,就听见背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
“你们在于什么?”
四周很暗,看不清他的脸,他的身材瘦瘦高高的。
“没什么,散步时发现车子里有顶鸭舌帽。”我说。
“我父亲是个画家,他以前常戴这顶帽子,真让人怀念。”
我不想被人识破身份就撒了个谎。
那男子打开车门,戴上帽子。饭木举起右手,他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可能是迷魂药吧。
“那这就送给你吧!你戴了它就会想起自己的父亲了。”
好奇怪的家伙!
“不,我不要!”
我很想这么说,但不知为什么却小声音说:“人都死了,再想起来是件痛苦的事。”
那男人说了句没错,就从我的手中接过帽子。这时候对面开来的车的车灯让我看清那人的长相。不是三十岁,应该更年轻一些,大概二十五岁左右吧。单眼皮,看起来比吸水更有女人缘。
“有件事想问你。”
我对坐进车里的那男人说。他戴上帽子回头看着我。
“我想知道关于樱井洋一导演的录像带的事。”
那人听到樱井洋一四个字时,反应很奇怪,好像听到死去的亲人或好友的名字一样。那表情好像这名字触到了他的伤心处。
“你们是?”
“不是。”
“那是这里的人?”
“不是,我们是樱井的朋友,想取回带子。如果你知道的话请告诉我们。”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用低低的声音说:“我有。”
男人带我到了一处狭窄的旧房子里,有个只穿着内衣裹着棉被的女人在睡觉。他说她是他女朋友。女人看见我和皈木,惊恐地用棉被盖着自己逃到角落。男人对她说别怕。
“是樱井洋一的朋友,我想还他们带子。”
男人这么说了,女人还是很害怕,她用惶恐不安的眼神看着我们,全身不停地抖动。我想她可能是哑巴。男人打开小厨房里的大冰箱,里面没什么东西,只有发蔫儿了的韩国泡菜和一瓶咖啡。
“我出去买饮料。”
男人一这么说,躲在房间一角的女人发出动物般的叫声,拼命地摇着头。我说我真的不想喝东西。
男人说要和我再看一次后就将带子还我。我叫皈木回车子里等我,因为没理由让皈木看那种东西。我也不想看。一般来说没有人会想看好友的那种东西。我很想跟他说,我不想看,可不可以马上还我,但是他很迟钝,没看出我的反应。
“我想赶快看完录像带,拿了回家。”
于是在没什么家具,只有一个暖炉的小房间里,我们看起录像带。真是难以置信,那盘带子的画质如此地清楚。床头灯开着,樱井和赤川在做爱。摄相机只有一台,有时将两人裸体全都收入镜头内,有时照着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樱井真不愧是导演,剪辑得绝对够专业。樱井在片头还写了宇:“将我的所有”。
现在不是笑的时候。在屋角一动不动的女人用一种受了伤的野犬般的眼神看着我。屋里好冷,喘气时呼出的是白色的气体。他们两人是怎么在这种地方过的呢?标题结束了,画面变成黑色,可以听到很清楚的声音。是樱井洋一和赤川美枝子的声音,赤I!D哭着喊叫。
“听不见。”
“对不起。”
“听不见。”
“对不起,请原谅我。”
“我不是说听不见吗?好了美枝子,你一定要大叫到门卫和清洁工都赶来才行。快大声地向我道歉、求我原谅。”
“糖原谅我,我不行了,不行了。”
“道歉!”
“对不起!”
“大声点!”
“对不起!”
“流着泪说对不起!”
“对不起!”
画面出现樱井和赤川的脸。赤川哭得脸上的妆都掉没了,头发散在脸上。樱井打了她好几巴掌,挨打时,赤川不停地说对不起。她的脸都红了,她真的哭了。
“知道为什么挨揍吗?”
“知道。”
“你说!”
“我”
“大声点,边哭边说!”
“我又发疯了。”
“发疯了要说什么?”
“最差劲的男人。”
“听不到。”
“最差劲的男人。”
赤川不光脸被打,而且全身都被打了。尤其是屁股上有好几十条青瘀。赤川的屁股挨打时,镜头就会对着她的屁股来个大特写。我觉得这情景太残酷,有些不敢看,那男人却边看边笑。后来樱井和赤川所始做爱了。在比利波蒂的“将我的所有”音乐声中,他们翻云覆水。
看完了,男人将带子取出放在盒子里交给我。带子背面贴了张纸签,写着“将我的所有”。
我说了声:“走了。”但男人要我等一下。
“她有点…”
男人说完看着躲在一边的女人,女人好像发现了什么一直摇着头。男人站起来走近她,将她的手放在肩上,很温柔地说:“不要怕/我从来未听过如此温柔,让人安心的语调。
“不要怕,他们不是也不是流氓,是樱井洋一的朋友。刚才在车上我问过他。他和樱井念的同一所高中,他们是朋友,所以我想跟他说一些关于你的事,拿这些带子,我和你都没有什么恶意吧?”
女人点了几下头。
“我绝对没有说谎,她叫美里子,美里子也不会说谎。她很神经质,所以不知道怎么和陌生人沟通。但是你们不要误解她,这世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要再说我和美里子的故事了,我们住在一起时就约定好要彼此真实,我们从不说谎,你们要相信我们。”
我说相信你们。
“我想当演员,我是樱井先生的影迷,我很尊敬他。所以美里子就在樱井先生的饭店当清洁工。后来怎样你也知道吧?”
我点点头。
美里子趁打扫房间时偷了录像带。
“有件事我想问你,可以吗?”
“你问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要让我看带子?”
“没什么理由。我想最后大家一起看嘛!虽说是私人带子,但场景很美,配乐也好听。”
“比利波蒂?”
“那是女歌手的名字?”
“是的。”
“她的声音并不好听,但曲子旋律很美。美里子也很喜欢那首曲子。只要是她喜欢的歌手,她就会想办法去收藏那歌手的所有CD。
“等一下。”我说。我问他可以让我听听那盘CD吗?男人显得很惊讶,但还是同意了。
我们就在小房间里听着“将我的所有”。真是很美。
古巴的音乐实在太棒了。那音乐使寒冷的屋内流动着丝丝暖意。
“我想再听一次。”
曲子结束时,美里子突然这么说。她还是很害怕地缩着身,脚却在打拍子。
“CD送你好了,喜欢就听个够。”
我走了出去。
我告诉皈木说,我们作战成功。当我坐进车子时,隐约听见从那屋里传来的“将我的所有”的歌声。
请带走我的所有,
我的唇,
想被你带走,
我的手腕,
想被你拥抱,
你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
没有你我能生存吗?
你不只带走了我的心
也想带走我的全部也将我的所有
带走
听着那歌声,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录像带里的画面。赤川美枝子擦着红指甲油的手在动着,不久就静止了。
醒来了,我发现自己正和一个陌生的女孩躺在床上。起初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梦里我为了给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的女孩买水果派,急匆匆地走在两旁有很多面包房和点心店的街上。我买了水果派,正要回家,我感觉现在好像还在梦境当中。
然而这不是梦。她的头枕在我的胳膊上,身体紧挨着我。女孩看上去有二十几岁,梦乡中的脸廓显得很娇美。呼吸时发出轻微的鼾声。我闻到了一股从她那里散发出的薄荷和尼古丁的气味。不知道该不该把她叫醒。
我已经习惯了房间里的昏暗,我努力地转动着脖子,慢慢地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并不是我熟悉的地方。墙壁纸的图案和颜色都与我的房间不一样,天花板要比我房间的高。窗户被纱帝和厚布挡着,好像要把光线都隔绝似的。我从窗帘缝隙钻进来的微弱光线判断,屋外现在应该是阴天,而且像是上午时分。虽然听不到什么声音但也许外面正下着雨吧。
枕头上罩着绿色的丝地儿枕套,我并没有这种枕套。女人穿件纯白的T恤衫,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项链。我轻轻地动了动被子里的脚,确定自己还穿着。
我怀疑自己可能出了什么意外丧失记忆了。说不定睡在我身边的女人是我的妻子或是同居的女朋友,也许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一起生活了。
我叫狄野广,在一家规模不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公司上班,我是销售部的职员,七年前离了婚,那以后就一直独身。
我的生活向来很有规律。二十八岁那年,我因为和妻子性格不合离婚了,女儿随了她妈妈。自从恢复单身生活后,我的生活更有规律了。我一般在七点左右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取出冰箱里的矿泉水喝一杯。我通常是买法国出的爱比昂牌矿泉水,有时换换样也会买富维可矿泉水。如果前一天晚上喝了酒的话,那就要喝菲露雅矿泉水。用来喝水的玻璃杯是我在百货公司大减价时买的,六个一套,原价三万元,我花一万八千元就买下来了。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喝完水后冲个澡,然后换好衣服出门。在车站旁的自助式咖啡店里解决早餐。这家店为了招揽顾客,给每天开店后进门的第二十位客人免费赠一杯橙汁,可是从这家店开张以来,我还从没喝过它的免费橙汁呢。不在家里做饭吃是因为我怕把厨房弄脏了。
刚离婚的那段时间,我会自己动手做早餐。咖啡、吐丝、荷包蛋、等等,但吃完后洗碗盘是件很麻烦的事,于是我决定不在家里吃饭。
我在上午八点五十分到达公司,我上班乘坐的电车的行驶方向刚好和塞车线路相反,所以电车总是很准时。
我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参加各部室会议,经常与宣传部或广告代理商打交道,有时也要外出拜访客户。中午就在公司附近的餐馆解决午餐。
一天的工作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就结束了。但我经常在公司里呆到六、七点才走。下班后有时和同事在车站附近喝两杯,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就在附近的芳邻餐馆吃份儿一千五百元的套餐。我还得负担前妻的赡养费,所以只能省吃俭用。节假日我常到多摩川散步,或是在家里听音乐。看书。
这就是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吧?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们,我的兴趣是写梦的日记。早上喝着矿泉水时,我会将前一天晚上的梦记录下来。四年前我就开始写日记,至今已经写了十一本。
开始时真是很辛苦。我的梦通常都很平凡,而且常常醒来就忘了刚才做了什么梦,所以开始后的半年里记录下来的梦很少。不过,坚持了一年后,我已经能够把梦里发生的一些奇景记录下来。
我说的奇景并不是什么影像,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最常出现在我梦里的人是我的女儿。找离婚时女儿才四岁,后来她就一直住在九州的姥姥家,所以我们很少见面。现在她该有十一岁了。但莫名其妙的是我常梦见她各种年龄的模样,有婴儿时的情形,也有她长大成人的样子。
梦境大概是这样……
成人模样的女儿就在我面前,我们在一家昏暗的咖啡店里见面。我问女儿过得好不好,她低头笑着说她现在的生活很糜烂,她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听到女儿的话我内心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那是一种嫉妒与不安,但又夹杂着的快感。没有父亲陪伴在身旁的女儿生活就是这样不检点。我还猜想过她交往的男孩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种身为父母的感叹,孩子已经长大了,不再管得住了。这样的念头常一个个地从我脑海中冒出来,我总是尽可能把它们如实地写在日记里。我偶尔也做一些不合常理的梦。比如我和长大后的女儿在森林公园里做爱,或者我把自己和女儿做爱的照片贴在房里当装饰;有时还会梦见我是个老鸨,把女儿卖到风月场所去。总之我的梦都是和性有关的。
我瞧着睡在我身旁的女孩的脸,她并不像是我认识的人,我认识的二十几岁的女孩并不多。咖啡店的服务员、公司的同事、电车站附近酒吧老板的女儿、芳邻餐厅的女招待,就这么多了,但是她们都没有和我上过床。离婚后我只去过两次风月场所,那种体验并不好受。我去过那种地方之后就决定一个人独居,我不想再乱搞关系。别人可能会觉得女人能带来快乐,殊不知那势必会浪费时间和精力。我可没有那么多工夫,我很珍惜自己的独处时间,可以散步、听音乐、看书、写梦的日记。正因为这样,我对女人的兴趣渐渐地淡薄了。
女人总觉得自己是最美的。我是第一次这样看着女人的睡相。今天是星期三,我要和一家广告代理商开会讨论有关推广新产品的事。我小心翼翼生怕吵醒她,抬头看看表,这样一来我的脸更接近女人的脸,这时我闻到以前从未注意过的头发气味。女人披散在床单上的长发味道,多么令人怀念啊!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儿闻过这样的气味。
女人的头发上散发着化妆品的淡淡香味。我想我现在才体味到女人的发香,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意识。我对女人几乎不了解,更没有过因为发香而引起强烈性欲的经验。脑中突然闪现一个念头:莫非这就是一直出现在我梦中的女人味儿?久远的梦中记忆该不会这样鲜明吧!除了昨晚外,已经一个月了,都没有女人走进我的梦中。
昨晚的梦是我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和陌生的女孩说话开始的。
“这里好窄!”
“那也没办法呀!”
“因为你的身份证掉到河里去了。”
“能不能别再提起那件事?从刚才就一直听你唠叨了。”
“我才说了一次!”
“才不是,我听了好几遍了!”
“什么也别说了,反正得住在这里了。”
“我也不知道那里有条河。”
“你喜欢鳗鱼吗?”
“没有日本人会讨厌鳗鱼吧?”
“要不要在这里吃?”
因为鳗鱼很贵,所以我觉得还是吃别的东西好,但又怕说出来会让她瞧不起我,何况吃一次鳗鱼也不至于把我吃穷。
“你知道鳗鱼店的电话号码吗?”女人问。
“干什么?”
“叫外卖呀!”
“这里没有电话。”
“是吗?对了,我们才搬进来。”
“搬家前我们也没有电话啊。”
女人的表情变得很难看。我把她留在屋内,出去找鳗鱼店。这里是位于郊区的住宅区,建了好多新房子。刚刚搬家,深怕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就算买了鳗鱼,可家里也没有炊具,而且就算找到鳗鱼店,送外卖的人也肯定不知道我家在哪儿。走了很久我来到一条商业街,路的两旁全是点心店。我想,买不到鳗鱼饭,买点水果派或其他东西也好。有一家点心店的伙计叫住了我。
“狄野先生,去年在顶楼吃的怪味儿果派好吃吗?”
我不记得自己在顶楼上吃过怪味儿果派,但我却回答说好吃。
“不对。”我小声响咕。这位头发飘出淡淡清香的女人不是昨晚我梦到的那个女人。我隐约想起昨晚睡觉前的事了。我下了班在电车站和同事道别后,在苦邻餐厅点了一千三百八十元的汉堡套餐吃。但我又觉得自己的记忆像平静的湖面掀起的波浪般模糊不清。我确实吃了汉堡套餐,但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的事。
女人睁开眼睛,一时间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快要停顿了。
“你醒了!”女人说。这不是我熟悉的声音。女人好像还很想睡。
“啊,你把我的胳膊当枕头,压得好痛!”我对女人说。
女人抬起脖子,我抽出手。我觉得喉咙很干,发不出声。
“喂!”女人轻轻地叫道。“让我再睡一会儿!”
她又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发出轻微的鼾声。那是很有节奏的呼吸,还散发出薄荷和尼古丁的香味。房间里寂静无声。从窗帘缝隙中透进来的微弱光线,让我觉得外面似乎在下雨,但听不到雨声。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热或冷,就算盖了棉被也不会热,不盖也不觉得冷。
我很想伸手去抚摸女人露在棉被外的圆润白皙的肩膀,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忍着喉咙的干渴,我照着女人刚刚说过的话,慢慢地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
然而这不是梦。她的头枕在我的胳膊上,身体紧挨着我。女孩看上去有二十几岁,梦乡中的脸廓显得很娇美。呼吸时发出轻微的鼾声。我闻到了一股从她那里散发出的薄荷和尼古丁的气味。不知道该不该把她叫醒。
我已经习惯了房间里的昏暗,我努力地转动着脖子,慢慢地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并不是我熟悉的地方。墙壁纸的图案和颜色都与我的房间不一样,天花板要比我房间的高。窗户被纱帝和厚布挡着,好像要把光线都隔绝似的。我从窗帘缝隙钻进来的微弱光线判断,屋外现在应该是阴天,而且像是上午时分。虽然听不到什么声音但也许外面正下着雨吧。
枕头上罩着绿色的丝地儿枕套,我并没有这种枕套。女人穿件纯白的T恤衫,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项链。我轻轻地动了动被子里的脚,确定自己还穿着。
我怀疑自己可能出了什么意外丧失记忆了。说不定睡在我身边的女人是我的妻子或是同居的女朋友,也许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一起生活了。
我叫狄野广,在一家规模不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公司上班,我是销售部的职员,七年前离了婚,那以后就一直独身。
我的生活向来很有规律。二十八岁那年,我因为和妻子性格不合离婚了,女儿随了她妈妈。自从恢复单身生活后,我的生活更有规律了。我一般在七点左右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取出冰箱里的矿泉水喝一杯。我通常是买法国出的爱比昂牌矿泉水,有时换换样也会买富维可矿泉水。如果前一天晚上喝了酒的话,那就要喝菲露雅矿泉水。用来喝水的玻璃杯是我在百货公司大减价时买的,六个一套,原价三万元,我花一万八千元就买下来了。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喝完水后冲个澡,然后换好衣服出门。在车站旁的自助式咖啡店里解决早餐。这家店为了招揽顾客,给每天开店后进门的第二十位客人免费赠一杯橙汁,可是从这家店开张以来,我还从没喝过它的免费橙汁呢。不在家里做饭吃是因为我怕把厨房弄脏了。
刚离婚的那段时间,我会自己动手做早餐。咖啡、吐丝、荷包蛋、等等,但吃完后洗碗盘是件很麻烦的事,于是我决定不在家里吃饭。
我在上午八点五十分到达公司,我上班乘坐的电车的行驶方向刚好和塞车线路相反,所以电车总是很准时。
我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参加各部室会议,经常与宣传部或广告代理商打交道,有时也要外出拜访客户。中午就在公司附近的餐馆解决午餐。
一天的工作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就结束了。但我经常在公司里呆到六、七点才走。下班后有时和同事在车站附近喝两杯,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就在附近的芳邻餐馆吃份儿一千五百元的套餐。我还得负担前妻的赡养费,所以只能省吃俭用。节假日我常到多摩川散步,或是在家里听音乐。看书。
这就是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吧?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们,我的兴趣是写梦的日记。早上喝着矿泉水时,我会将前一天晚上的梦记录下来。四年前我就开始写日记,至今已经写了十一本。
开始时真是很辛苦。我的梦通常都很平凡,而且常常醒来就忘了刚才做了什么梦,所以开始后的半年里记录下来的梦很少。不过,坚持了一年后,我已经能够把梦里发生的一些奇景记录下来。
我说的奇景并不是什么影像,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最常出现在我梦里的人是我的女儿。找离婚时女儿才四岁,后来她就一直住在九州的姥姥家,所以我们很少见面。现在她该有十一岁了。但莫名其妙的是我常梦见她各种年龄的模样,有婴儿时的情形,也有她长大成人的样子。
梦境大概是这样……
成人模样的女儿就在我面前,我们在一家昏暗的咖啡店里见面。我问女儿过得好不好,她低头笑着说她现在的生活很糜烂,她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听到女儿的话我内心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那是一种嫉妒与不安,但又夹杂着的快感。没有父亲陪伴在身旁的女儿生活就是这样不检点。我还猜想过她交往的男孩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种身为父母的感叹,孩子已经长大了,不再管得住了。这样的念头常一个个地从我脑海中冒出来,我总是尽可能把它们如实地写在日记里。我偶尔也做一些不合常理的梦。比如我和长大后的女儿在森林公园里做爱,或者我把自己和女儿做爱的照片贴在房里当装饰;有时还会梦见我是个老鸨,把女儿卖到风月场所去。总之我的梦都是和性有关的。
我瞧着睡在我身旁的女孩的脸,她并不像是我认识的人,我认识的二十几岁的女孩并不多。咖啡店的服务员、公司的同事、电车站附近酒吧老板的女儿、芳邻餐厅的女招待,就这么多了,但是她们都没有和我上过床。离婚后我只去过两次风月场所,那种体验并不好受。我去过那种地方之后就决定一个人独居,我不想再乱搞关系。别人可能会觉得女人能带来快乐,殊不知那势必会浪费时间和精力。我可没有那么多工夫,我很珍惜自己的独处时间,可以散步、听音乐、看书、写梦的日记。正因为这样,我对女人的兴趣渐渐地淡薄了。
女人总觉得自己是最美的。我是第一次这样看着女人的睡相。今天是星期三,我要和一家广告代理商开会讨论有关推广新产品的事。我小心翼翼生怕吵醒她,抬头看看表,这样一来我的脸更接近女人的脸,这时我闻到以前从未注意过的头发气味。女人披散在床单上的长发味道,多么令人怀念啊!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儿闻过这样的气味。
女人的头发上散发着化妆品的淡淡香味。我想我现在才体味到女人的发香,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意识。我对女人几乎不了解,更没有过因为发香而引起强烈性欲的经验。脑中突然闪现一个念头:莫非这就是一直出现在我梦中的女人味儿?久远的梦中记忆该不会这样鲜明吧!除了昨晚外,已经一个月了,都没有女人走进我的梦中。
昨晚的梦是我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和陌生的女孩说话开始的。
“这里好窄!”
“那也没办法呀!”
“因为你的身份证掉到河里去了。”
“能不能别再提起那件事?从刚才就一直听你唠叨了。”
“我才说了一次!”
“才不是,我听了好几遍了!”
“什么也别说了,反正得住在这里了。”
“我也不知道那里有条河。”
“你喜欢鳗鱼吗?”
“没有日本人会讨厌鳗鱼吧?”
“要不要在这里吃?”
因为鳗鱼很贵,所以我觉得还是吃别的东西好,但又怕说出来会让她瞧不起我,何况吃一次鳗鱼也不至于把我吃穷。
“你知道鳗鱼店的电话号码吗?”女人问。
“干什么?”
“叫外卖呀!”
“这里没有电话。”
“是吗?对了,我们才搬进来。”
“搬家前我们也没有电话啊。”
女人的表情变得很难看。我把她留在屋内,出去找鳗鱼店。这里是位于郊区的住宅区,建了好多新房子。刚刚搬家,深怕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就算买了鳗鱼,可家里也没有炊具,而且就算找到鳗鱼店,送外卖的人也肯定不知道我家在哪儿。走了很久我来到一条商业街,路的两旁全是点心店。我想,买不到鳗鱼饭,买点水果派或其他东西也好。有一家点心店的伙计叫住了我。
“狄野先生,去年在顶楼吃的怪味儿果派好吃吗?”
我不记得自己在顶楼上吃过怪味儿果派,但我却回答说好吃。
“不对。”我小声响咕。这位头发飘出淡淡清香的女人不是昨晚我梦到的那个女人。我隐约想起昨晚睡觉前的事了。我下了班在电车站和同事道别后,在苦邻餐厅点了一千三百八十元的汉堡套餐吃。但我又觉得自己的记忆像平静的湖面掀起的波浪般模糊不清。我确实吃了汉堡套餐,但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的事。
女人睁开眼睛,一时间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快要停顿了。
“你醒了!”女人说。这不是我熟悉的声音。女人好像还很想睡。
“啊,你把我的胳膊当枕头,压得好痛!”我对女人说。
女人抬起脖子,我抽出手。我觉得喉咙很干,发不出声。
“喂!”女人轻轻地叫道。“让我再睡一会儿!”
她又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发出轻微的鼾声。那是很有节奏的呼吸,还散发出薄荷和尼古丁的香味。房间里寂静无声。从窗帘缝隙中透进来的微弱光线,让我觉得外面似乎在下雨,但听不到雨声。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热或冷,就算盖了棉被也不会热,不盖也不觉得冷。
我很想伸手去抚摸女人露在棉被外的圆润白皙的肩膀,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忍着喉咙的干渴,我照着女人刚刚说过的话,慢慢地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
在出租车内看到那座塔时,一种不详的预感就像迪斯克舞厅里的镭射灯般地在心中闪烁跳动。
“到了!”一位穿着藏青色西装的圆脸男子喊着,我们来到了塔旁边的豪斯登堡。我们在入口处从圆脸男子手中接过火场券,走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个游乐场。夹杂着愉快、惊吓和刺激的叫声从四周传来,中间还有轰轰转动的机器声响,这里的气氛真够热闹的。这时,我突然想起第二次和高秋到迪斯克舞厅去的情景,脊背上不禁串出一股凉意。每次想到高秋就会有这样的反应。都已经半年没见到他了还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反常?朋友们拿话激我:“不跟着一块儿去吗?”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要跟去。今天晚上我是出来旅行的。就在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我满脑子还都是自杀的念头。
高秋比我大十二岁,现在在一个俱乐部里工作。他曾在伦敦当过音乐节目主持人,在墨西哥做过服装展示会的舞台设计师,也曾做过舞台剧演员,有太太和两个小孩。我认识他的那天便和他一起到饭店里过了夜。他的个头不高,戴副眼镜,额头有点窄,可我就是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和我以前认识的男人完全不同。第一夜我俩躺在饭店的床上,聊起了关于父亲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对其他男人说起过父亲的事。爸爸曾是浦和的一个公司职员,在我念高中时因为小小的失误而辞职了。详细情形连我妈妈也不清楚,好像只是文件登记出了点小错误,就被从东京调来的年轻上司痛斥了一番。虽然没有被炒鲸鱼,但爸爸却觉得面子挂不住,便辞职了。自从爸爸辞职后,就再没有踏出过家门一步。他整天精神恍惚,开始时妈妈叫他去看医生,爸爸还很生气地骂人,可后来他的精神越来越不好,也不和家人交谈。有时候我看见爸爸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我们家里的地现在有一半在与别人合盖公寓,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让出了部分产权。高中毕业后我马上离开了家,来到东京独自生活。在日本经济景气时,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内勤职员不用跑外务,一个月就可以赚好几万日元。那时我常和一些时髦的女同事在一起玩,就在那时我认识了高秋。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和高秋聊到父亲的事时,我们都赤身躺在饭店房间的床上,当时我哭了。高秋劝我不要那么憎恨父亲。他说:“我没有你那样的经历,所以无法了解你是多么的痛苦,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讨厌你的父亲,我并不是强迫你去喜欢他,只是你每次想起父亲,情绪是那样的低落。其实你真的不要那么讨厌他,有位FI赛车手,曾经也面临过和你现在一样的问题,可是有一次他参赛时,当他来到转弯跑道,眼前突然出现一幅车子模过弯道而撞得车毁人亡的画面,于是他马上打起精神专注地通过跑道,而就在那一瞬间,隐藏在他心中的怨恨突然消失了。人生苦短,何必为一点小事伤神呢。他这才发现,原来不去憎恨一个人是这么的容易。”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们交往大约有一年,后来我怀孕了,他不让我生下小孩,我们因此大吵了一架。虽然我对他感到失望,但还是相信他的话,因为那时候报纸上常常披露一些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内部丑闻,我担心出了绯闻对他不利。那时高秋的工作量开始减少,他的最后一笔生意是名古屋一家螃蟹料理连锁店的广告片。从那时起,我们就算见了面也不常交谈。提出分手的是我。听我说完,高秋并没有像他一贯的个性那样马上离开我,他一句话也不说,变得好可怕。我还以为当我提出分手那一刻,高秋一定会马上起身离去,但他却没有。
分手后高秋依旧每晚打电话来,我们还是会彼此说“喜欢你,爱你。”但是我们从此再没有见面。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两个月过后,就再也不来电话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要对自己说几遍:“他没有打电话来真是太好了。”这样才能安心入睡。其实我的内心很渴望接到他的电话。那段时间我整天魂不守舍,干什么事情都没劲。兼职的工作丢了,于是开始担心是否付得起房租和买衣服剧卡的钱。就连那时候是怎么将这份杂志的读者招募明信片寄出去的都不清楚。我连动都不想动,甚至觉得连吃饭都是件痛苦的事。嘴很干,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可是,想想自己总不能这样一直干坐着,一定要找点事情做,所以就将屋里所有的杂志都翻遍了,还填写了婚姻介绍所的调查问卷。后来我的脑子里开始出现自杀的念头,当我自己也察觉不妙时,杂志社寄来的一张旅游招待券救了我。
出发的当天,我很认真地化了妆,当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时,不禁吓了一跳。我身上穿的内衣是高秋最喜欢的黑色性感款式,外面穿着的仍是旧款式的西装,这样的搭配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看了其他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我真觉得自己比她们老多了。跟杂志社和旅行社的人还有女导游一起在豪斯登堡中转悠时,我眺望着风车和运河,心里在想,别人会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如果高秋现在在我的身边的话会怎样呢?想着想着,眼泪几乎要流出来了。其他的女孩都在寻找着自己中意的伙伴,兴致很高地互相交换相机拍照。
“请问你是今井小姐吗?”一个女孩跑过来问我。我回答:“是!”她大概是晚上要和我住的人吧。我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胸卡。她叫今村弓子,我叫今井由加利,因为导游安排房间是根据姓氏笔画,所以我们两个成了室友。她是福冈人,是个漂亮的女孩子,比我小一岁,说话轻声细语而且显得很害羞。
“我可能得了艾滋病!”
回到饭店,登记好房间后,在晚饭前的这段自由活动时间,和今村弓子在可以望见运河的咖啡厅里喝着奶茶时,她突然冒出这句话来。我情不自禁大声“啊”了一声,但马上察觉到自己失态了,赶紧向她道歉。
颇具欧洲格调的吊灯高挂在天花板上。望着眼前的豪华桌椅和器皿,我构筑了一个不受别人干扰的自我世界,在其中品着茶。“只要跟美丽相伴就会忘记烦恼。”这是高秋说过的话,我现在觉得这话说得对极了。假如今并弓子长得不漂亮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和她在一起喝茶聊天,当她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时,我也肯定会因此而疏远她。虽然她体态娇小,穿着打扮也极为一般,可她的确称得上是个美女。
“突然说出这么奇怪的话来,真是不好意思,可是我真的想告诉你。”
我说:“好吧!”于是她开始讲自己的事。她在福冈一家时装店做事,男朋友是专门承办演唱会的穴头,她和他已经有过好几次性关系,但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对性毫无节制的男人。
“他常出国,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就去找那里的女人,就是那种卖身的女人。”
弓子讲到这儿竟低头脸红了,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红了双颊的女孩子。我边笑边对她说:“你说的是妓女吧?”
“是的,听说在美国、墨西哥。欧洲,不管是什么地方,他都会去找这样的女人。”
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请了假到东京去找他,这之前跟他说过我会去找他的,结果他却装作不在家。于是我就去了他的公司,他公司的同事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的事情。”
坐在咖啡厅里的大都是日本人。这家饭店是想体现出欧式风格,可却没有将应有的欧洲气氛营造出来。日本客人和这家饭店的格调实在很不相称。有上着高尔夫球装、脚穿运动鞋、腰上扎着霹雳包的男人,也有打扮得像要赴晚宴的女人。服务员。行李员都彬彬有礼。训练有素,但可能是因为客人并不习惯这样的环境,因此所有人的行动都给人不协调的感觉。从铺着大理石板的大厅、豪华的旋转几插了好几百朵百合花的漂亮花瓶、壁毯、墙上挂的名画、地毯、椅子到烟灰缸,全都是真材实料,这些东西比人们更像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东西是有力量的。腰扎着霹雳包在吊灯下走动的男人们看起来似乎很没有安全感,就像是迷失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一群东方人。但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我也是不适合存在于这样的环境中,还有在我面前不知所云的弓子也是一样。
“他们会不会是在跟你开玩笑?”
“不会,其中有一位把我带到一个像是会客室的房里,他很平静地跟我说,绝对不要再跟那样的男人交往了。”
“他没有问你要不要跟他做男朋友吗?”
“他邀我同他一起吃饭。”
我并不觉得弓子笨,也许她是深度近视,也许他的双亲很晚才生下她,也许她总是碰到比我还不幸的问题吧!或者比起别的孩子来,她常容易迷失方向,还是她自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不管怎样,一定是其中某个原因造成她这样的个性。
“那你怎么知道他故意装作不在家呢?”
“你是说在他住的地方吗?”
“是的。
“因为我听到了从里面传出来的音乐的声音。”
我说:“那你可以用力敲门呀!”
“我好像听到有女人的声音,我很害怕所以没敢那么做。”
“那是什么音乐?”
“滚石会唱团唱的歌。”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春光碟,还去酒吧喝了好多酒。弓子还是不停地念叨艾滋病的事,她喝的酒比我多好几倍,整张脸都胀红了,连耳朵也变成了粉红色。
“今非小姐,以前你一定没想过万一得了艾滋病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吧?其实在我认识他之前交往的那个男人也不是个正经人,他是福冈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也常出国,也去找当地的妓女。所以每次和他发生关系后,我一定要去接受艾滋病检查,虽说我不知道今后会遇见多么好的对象,但总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嘛,今井小姐,你想过这样的问题吗?”
她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果未来遇见的理想对象也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话该怎么办?”我不想回答这种问题,所以保持沉默没有回应。在弓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大堆无聊的话题时,我的双眼一直盯着她那对粉红色的小耳朵。她戴了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
我说该回房间了。走在她身后望着她的背影,发觉其实她是个挺新潮的女孩儿。穿着粉红色的裙子,上身的白色衬衫外面罩着黄色羊毛衫,梳着时髦的发型,长筒袜是纯白色的。饭店走廊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她的皮鞋走过时发出很奇妙的声音。虽然还不到晚上十点,可周围异常的宁静,更感觉自己产生“是否已迷们于另一个世界”的错觉。
高秋常说人要自由,但是他自己却背叛了这句承诺,反倒是长久以来我始终谨守着这个诺言。望着弓子纤细的腰姿,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我想,身处另一个世界中的人都会注意自己周围的事物吧!突然弓子回过头,指着一个房间。我们喝多了酒,忘记了要搭电梯,就这样走在通道上,两旁全是套房。那房间的门半开着,灯是熄着的。我提议进去瞧瞧,弓子摇头说不行,可马上又笑着说愿意。我们确定四周元人就钻了进去,然后将门轻轻关上。刚过去的地方不是房间,是个大厅。弓子说房子好漂亮,光大厅就比我租的公寓大。我们虽然怕被人发现,但还是推开了半开的厅门走了进去,一线月光斜射进客厅里。我想,如果被人发现的话,就说走错房间道个欠就行了。可能房间里的入睡了,但又感觉不到有人在房间里。房间整理得很干净,烟灰缸是空的,玻璃杯好像也没人用过,连衣服、报纸杂志也没有。书桌和两个小茶几上也没有标着房客姓名的牌子。弓子很惊讶地说了句:“难道……”她的声音稍微大了些,我嘘了一声并用手轻轻压她的嘴唇,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女孩子的唇。有些冰冷,非常的柔软。她紧张地说“浴室里不会有尸体阳?”房间里暗得让人不禁产生这种联想。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紧张得心在砰砰的跳。我说:“没事儿,日本治安很好,何况这里又是九州的乡下。”透过薄丝窗帘可以看到不远处的运河,对面还有个闪着红色灯光的灯塔。黑暗中隐约可看见运河水面掀起淡淡的浪花,还有两个白点漂浮在水面。弓子双眸忽然一亮,指着前面说:“那是白鸟,你看见过吗?”我屏住呼吸点点头。朦胧的夜色中两只白鸟缠绵在一起,可以感觉到那羽毛的柔软温暖,它们的身影慢慢地在水面上滑动,仿佛是跳着水上芭蕾的公主。弓子双眸仍然闪着光。
我们走进卧房。床上罩着床套,洗手间的门开着,里面没人。吊着的衣架让人联想到尸体。弓子问我要不要躺下来休息一下。可能是喝得太多了,我感到浑身躁热,心脏跳得好像快要进出来一样。我渐渐适应了房间里的黑暗。弓子已经躺在床上,我将嘴贴近她的耳边对她说:“你休息一下吧,我去看看有没有尸体。”我正要从床上离开时,弓子轻声地说:“不要,请留下来陪我,我好怕。”我轻轻地打开卧室的窗帘,外面建筑物的灯光和月光射了进来,我看清了床上弓子的脚。我问她是木是不舒服,她皱着眉直点头,于是我解开她的衬衫纽扣和裙钩,帮她脱了鞋子。“好,就这样睡吧广说完我用手指轻轻压着她的唇,还是那么冰冷而柔软。我将她的长发拢到一边,脱下毛衣,轻轻地吻着她的唇。感觉到两个人的心跳在加速。我在想她的一定很柔软,也很大很圆,这是令我怀念而又残酷的念头。小时候,我在房里玩洋娃娃时,就很喜欢去碰娃娃的那个部位,那会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我脱下她的白色长筒袜,露出没有擦指甲油的脚趾,闻到了淡淡的皮革味,我吻着她的脚,只觉得快要窒息了。当我解开她的衬衫纽扣时,“纸、纸厂从她的冰冷的嘴唇中发出急促的声音。我想她可能要吐了,于是赶紧将她抱到浴室里。“不是!不是!”她小声说着,双手紧抱住我的后背,双眼紧闭,因为紧张,她的肩膀和脖子都僵硬了。忙乱中,她的裙子被掀起来,露出白白的双腿。她的双腿真是美极了,那曲线真是妙不可言。她又嚷着要纸,这时候我闻到一股浓烈的气味。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女人的那种气味,很像是血的味道。“喂!”弓子小声地说。“快用纸擦掉,不然的话可能会染上艾滋病的!”说完她的脚动了一下,那气味更浓烈了。我觉得我触到的不是皮肤,而是血或内脏之类的生物。我知道这个生物在呼吸。我松开她抱着我的手,解下她的裙子。“等一下。”我从口袋里拿出钱包中装安眠药的薄塑料袋。我先将安眠药倒掉,塑料袋大小和一张明信片差不多,我用唾液弄湿它,然后分开弓子的腿。我用塑料袋包住手指摩擦着她的。弓子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紧抓着床罩。她想把腿合起来,但我用力让她张开。弓子忍不住咬着自己的手,她的身上开始冒汗,气喘嘘嘘,好像渴望着什么。我感到那是一种很残酷很悲伤的蠕动。
过了一会儿,弓子平静了下来。
“也许你不会相信,但这真的是我的第一次。”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第一次和女人发生这种关系,但我却是第一次达到如此兴奋的状态,我又把唇贴上了她的耳边,抚弄着她的头发轻声说:“没关系的。”
“什么都不要想,不过,感觉上你真的不像是第一次。”
“我总觉得有点下流。”
弓子很害羞地笑着说。“但我觉得这种下流和男人的那种下流不一样。”
“我想我们还是赶快出去的好,回房间去洗个澡吧!”
我说“不必那么急。”又吻了她。
“想不想再看一下那两只白鸟?”我问她。她露出孩童般的表情说:“想。”于是我们来到窗前,彼此脸贴着脸,就这样一直凝视着窗外的运河。
“到了!”一位穿着藏青色西装的圆脸男子喊着,我们来到了塔旁边的豪斯登堡。我们在入口处从圆脸男子手中接过火场券,走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个游乐场。夹杂着愉快、惊吓和刺激的叫声从四周传来,中间还有轰轰转动的机器声响,这里的气氛真够热闹的。这时,我突然想起第二次和高秋到迪斯克舞厅去的情景,脊背上不禁串出一股凉意。每次想到高秋就会有这样的反应。都已经半年没见到他了还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反常?朋友们拿话激我:“不跟着一块儿去吗?”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要跟去。今天晚上我是出来旅行的。就在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我满脑子还都是自杀的念头。
高秋比我大十二岁,现在在一个俱乐部里工作。他曾在伦敦当过音乐节目主持人,在墨西哥做过服装展示会的舞台设计师,也曾做过舞台剧演员,有太太和两个小孩。我认识他的那天便和他一起到饭店里过了夜。他的个头不高,戴副眼镜,额头有点窄,可我就是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和我以前认识的男人完全不同。第一夜我俩躺在饭店的床上,聊起了关于父亲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对其他男人说起过父亲的事。爸爸曾是浦和的一个公司职员,在我念高中时因为小小的失误而辞职了。详细情形连我妈妈也不清楚,好像只是文件登记出了点小错误,就被从东京调来的年轻上司痛斥了一番。虽然没有被炒鲸鱼,但爸爸却觉得面子挂不住,便辞职了。自从爸爸辞职后,就再没有踏出过家门一步。他整天精神恍惚,开始时妈妈叫他去看医生,爸爸还很生气地骂人,可后来他的精神越来越不好,也不和家人交谈。有时候我看见爸爸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我们家里的地现在有一半在与别人合盖公寓,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让出了部分产权。高中毕业后我马上离开了家,来到东京独自生活。在日本经济景气时,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内勤职员不用跑外务,一个月就可以赚好几万日元。那时我常和一些时髦的女同事在一起玩,就在那时我认识了高秋。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和高秋聊到父亲的事时,我们都赤身躺在饭店房间的床上,当时我哭了。高秋劝我不要那么憎恨父亲。他说:“我没有你那样的经历,所以无法了解你是多么的痛苦,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讨厌你的父亲,我并不是强迫你去喜欢他,只是你每次想起父亲,情绪是那样的低落。其实你真的不要那么讨厌他,有位FI赛车手,曾经也面临过和你现在一样的问题,可是有一次他参赛时,当他来到转弯跑道,眼前突然出现一幅车子模过弯道而撞得车毁人亡的画面,于是他马上打起精神专注地通过跑道,而就在那一瞬间,隐藏在他心中的怨恨突然消失了。人生苦短,何必为一点小事伤神呢。他这才发现,原来不去憎恨一个人是这么的容易。”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们交往大约有一年,后来我怀孕了,他不让我生下小孩,我们因此大吵了一架。虽然我对他感到失望,但还是相信他的话,因为那时候报纸上常常披露一些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内部丑闻,我担心出了绯闻对他不利。那时高秋的工作量开始减少,他的最后一笔生意是名古屋一家螃蟹料理连锁店的广告片。从那时起,我们就算见了面也不常交谈。提出分手的是我。听我说完,高秋并没有像他一贯的个性那样马上离开我,他一句话也不说,变得好可怕。我还以为当我提出分手那一刻,高秋一定会马上起身离去,但他却没有。
分手后高秋依旧每晚打电话来,我们还是会彼此说“喜欢你,爱你。”但是我们从此再没有见面。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两个月过后,就再也不来电话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要对自己说几遍:“他没有打电话来真是太好了。”这样才能安心入睡。其实我的内心很渴望接到他的电话。那段时间我整天魂不守舍,干什么事情都没劲。兼职的工作丢了,于是开始担心是否付得起房租和买衣服剧卡的钱。就连那时候是怎么将这份杂志的读者招募明信片寄出去的都不清楚。我连动都不想动,甚至觉得连吃饭都是件痛苦的事。嘴很干,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可是,想想自己总不能这样一直干坐着,一定要找点事情做,所以就将屋里所有的杂志都翻遍了,还填写了婚姻介绍所的调查问卷。后来我的脑子里开始出现自杀的念头,当我自己也察觉不妙时,杂志社寄来的一张旅游招待券救了我。
出发的当天,我很认真地化了妆,当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时,不禁吓了一跳。我身上穿的内衣是高秋最喜欢的黑色性感款式,外面穿着的仍是旧款式的西装,这样的搭配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看了其他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我真觉得自己比她们老多了。跟杂志社和旅行社的人还有女导游一起在豪斯登堡中转悠时,我眺望着风车和运河,心里在想,别人会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如果高秋现在在我的身边的话会怎样呢?想着想着,眼泪几乎要流出来了。其他的女孩都在寻找着自己中意的伙伴,兴致很高地互相交换相机拍照。
“请问你是今井小姐吗?”一个女孩跑过来问我。我回答:“是!”她大概是晚上要和我住的人吧。我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胸卡。她叫今村弓子,我叫今井由加利,因为导游安排房间是根据姓氏笔画,所以我们两个成了室友。她是福冈人,是个漂亮的女孩子,比我小一岁,说话轻声细语而且显得很害羞。
“我可能得了艾滋病!”
回到饭店,登记好房间后,在晚饭前的这段自由活动时间,和今村弓子在可以望见运河的咖啡厅里喝着奶茶时,她突然冒出这句话来。我情不自禁大声“啊”了一声,但马上察觉到自己失态了,赶紧向她道歉。
颇具欧洲格调的吊灯高挂在天花板上。望着眼前的豪华桌椅和器皿,我构筑了一个不受别人干扰的自我世界,在其中品着茶。“只要跟美丽相伴就会忘记烦恼。”这是高秋说过的话,我现在觉得这话说得对极了。假如今并弓子长得不漂亮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和她在一起喝茶聊天,当她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时,我也肯定会因此而疏远她。虽然她体态娇小,穿着打扮也极为一般,可她的确称得上是个美女。
“突然说出这么奇怪的话来,真是不好意思,可是我真的想告诉你。”
我说:“好吧!”于是她开始讲自己的事。她在福冈一家时装店做事,男朋友是专门承办演唱会的穴头,她和他已经有过好几次性关系,但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对性毫无节制的男人。
“他常出国,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就去找那里的女人,就是那种卖身的女人。”
弓子讲到这儿竟低头脸红了,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红了双颊的女孩子。我边笑边对她说:“你说的是妓女吧?”
“是的,听说在美国、墨西哥。欧洲,不管是什么地方,他都会去找这样的女人。”
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请了假到东京去找他,这之前跟他说过我会去找他的,结果他却装作不在家。于是我就去了他的公司,他公司的同事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的事情。”
坐在咖啡厅里的大都是日本人。这家饭店是想体现出欧式风格,可却没有将应有的欧洲气氛营造出来。日本客人和这家饭店的格调实在很不相称。有上着高尔夫球装、脚穿运动鞋、腰上扎着霹雳包的男人,也有打扮得像要赴晚宴的女人。服务员。行李员都彬彬有礼。训练有素,但可能是因为客人并不习惯这样的环境,因此所有人的行动都给人不协调的感觉。从铺着大理石板的大厅、豪华的旋转几插了好几百朵百合花的漂亮花瓶、壁毯、墙上挂的名画、地毯、椅子到烟灰缸,全都是真材实料,这些东西比人们更像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东西是有力量的。腰扎着霹雳包在吊灯下走动的男人们看起来似乎很没有安全感,就像是迷失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一群东方人。但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我也是不适合存在于这样的环境中,还有在我面前不知所云的弓子也是一样。
“他们会不会是在跟你开玩笑?”
“不会,其中有一位把我带到一个像是会客室的房里,他很平静地跟我说,绝对不要再跟那样的男人交往了。”
“他没有问你要不要跟他做男朋友吗?”
“他邀我同他一起吃饭。”
我并不觉得弓子笨,也许她是深度近视,也许他的双亲很晚才生下她,也许她总是碰到比我还不幸的问题吧!或者比起别的孩子来,她常容易迷失方向,还是她自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不管怎样,一定是其中某个原因造成她这样的个性。
“那你怎么知道他故意装作不在家呢?”
“你是说在他住的地方吗?”
“是的。
“因为我听到了从里面传出来的音乐的声音。”
我说:“那你可以用力敲门呀!”
“我好像听到有女人的声音,我很害怕所以没敢那么做。”
“那是什么音乐?”
“滚石会唱团唱的歌。”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春光碟,还去酒吧喝了好多酒。弓子还是不停地念叨艾滋病的事,她喝的酒比我多好几倍,整张脸都胀红了,连耳朵也变成了粉红色。
“今非小姐,以前你一定没想过万一得了艾滋病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吧?其实在我认识他之前交往的那个男人也不是个正经人,他是福冈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也常出国,也去找当地的妓女。所以每次和他发生关系后,我一定要去接受艾滋病检查,虽说我不知道今后会遇见多么好的对象,但总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嘛,今井小姐,你想过这样的问题吗?”
她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果未来遇见的理想对象也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话该怎么办?”我不想回答这种问题,所以保持沉默没有回应。在弓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大堆无聊的话题时,我的双眼一直盯着她那对粉红色的小耳朵。她戴了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
我说该回房间了。走在她身后望着她的背影,发觉其实她是个挺新潮的女孩儿。穿着粉红色的裙子,上身的白色衬衫外面罩着黄色羊毛衫,梳着时髦的发型,长筒袜是纯白色的。饭店走廊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她的皮鞋走过时发出很奇妙的声音。虽然还不到晚上十点,可周围异常的宁静,更感觉自己产生“是否已迷们于另一个世界”的错觉。
高秋常说人要自由,但是他自己却背叛了这句承诺,反倒是长久以来我始终谨守着这个诺言。望着弓子纤细的腰姿,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我想,身处另一个世界中的人都会注意自己周围的事物吧!突然弓子回过头,指着一个房间。我们喝多了酒,忘记了要搭电梯,就这样走在通道上,两旁全是套房。那房间的门半开着,灯是熄着的。我提议进去瞧瞧,弓子摇头说不行,可马上又笑着说愿意。我们确定四周元人就钻了进去,然后将门轻轻关上。刚过去的地方不是房间,是个大厅。弓子说房子好漂亮,光大厅就比我租的公寓大。我们虽然怕被人发现,但还是推开了半开的厅门走了进去,一线月光斜射进客厅里。我想,如果被人发现的话,就说走错房间道个欠就行了。可能房间里的入睡了,但又感觉不到有人在房间里。房间整理得很干净,烟灰缸是空的,玻璃杯好像也没人用过,连衣服、报纸杂志也没有。书桌和两个小茶几上也没有标着房客姓名的牌子。弓子很惊讶地说了句:“难道……”她的声音稍微大了些,我嘘了一声并用手轻轻压她的嘴唇,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女孩子的唇。有些冰冷,非常的柔软。她紧张地说“浴室里不会有尸体阳?”房间里暗得让人不禁产生这种联想。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紧张得心在砰砰的跳。我说:“没事儿,日本治安很好,何况这里又是九州的乡下。”透过薄丝窗帘可以看到不远处的运河,对面还有个闪着红色灯光的灯塔。黑暗中隐约可看见运河水面掀起淡淡的浪花,还有两个白点漂浮在水面。弓子双眸忽然一亮,指着前面说:“那是白鸟,你看见过吗?”我屏住呼吸点点头。朦胧的夜色中两只白鸟缠绵在一起,可以感觉到那羽毛的柔软温暖,它们的身影慢慢地在水面上滑动,仿佛是跳着水上芭蕾的公主。弓子双眸仍然闪着光。
我们走进卧房。床上罩着床套,洗手间的门开着,里面没人。吊着的衣架让人联想到尸体。弓子问我要不要躺下来休息一下。可能是喝得太多了,我感到浑身躁热,心脏跳得好像快要进出来一样。我渐渐适应了房间里的黑暗。弓子已经躺在床上,我将嘴贴近她的耳边对她说:“你休息一下吧,我去看看有没有尸体。”我正要从床上离开时,弓子轻声地说:“不要,请留下来陪我,我好怕。”我轻轻地打开卧室的窗帘,外面建筑物的灯光和月光射了进来,我看清了床上弓子的脚。我问她是木是不舒服,她皱着眉直点头,于是我解开她的衬衫纽扣和裙钩,帮她脱了鞋子。“好,就这样睡吧广说完我用手指轻轻压着她的唇,还是那么冰冷而柔软。我将她的长发拢到一边,脱下毛衣,轻轻地吻着她的唇。感觉到两个人的心跳在加速。我在想她的一定很柔软,也很大很圆,这是令我怀念而又残酷的念头。小时候,我在房里玩洋娃娃时,就很喜欢去碰娃娃的那个部位,那会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我脱下她的白色长筒袜,露出没有擦指甲油的脚趾,闻到了淡淡的皮革味,我吻着她的脚,只觉得快要窒息了。当我解开她的衬衫纽扣时,“纸、纸厂从她的冰冷的嘴唇中发出急促的声音。我想她可能要吐了,于是赶紧将她抱到浴室里。“不是!不是!”她小声说着,双手紧抱住我的后背,双眼紧闭,因为紧张,她的肩膀和脖子都僵硬了。忙乱中,她的裙子被掀起来,露出白白的双腿。她的双腿真是美极了,那曲线真是妙不可言。她又嚷着要纸,这时候我闻到一股浓烈的气味。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女人的那种气味,很像是血的味道。“喂!”弓子小声地说。“快用纸擦掉,不然的话可能会染上艾滋病的!”说完她的脚动了一下,那气味更浓烈了。我觉得我触到的不是皮肤,而是血或内脏之类的生物。我知道这个生物在呼吸。我松开她抱着我的手,解下她的裙子。“等一下。”我从口袋里拿出钱包中装安眠药的薄塑料袋。我先将安眠药倒掉,塑料袋大小和一张明信片差不多,我用唾液弄湿它,然后分开弓子的腿。我用塑料袋包住手指摩擦着她的。弓子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紧抓着床罩。她想把腿合起来,但我用力让她张开。弓子忍不住咬着自己的手,她的身上开始冒汗,气喘嘘嘘,好像渴望着什么。我感到那是一种很残酷很悲伤的蠕动。
过了一会儿,弓子平静了下来。
“也许你不会相信,但这真的是我的第一次。”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第一次和女人发生这种关系,但我却是第一次达到如此兴奋的状态,我又把唇贴上了她的耳边,抚弄着她的头发轻声说:“没关系的。”
“什么都不要想,不过,感觉上你真的不像是第一次。”
“我总觉得有点下流。”
弓子很害羞地笑着说。“但我觉得这种下流和男人的那种下流不一样。”
“我想我们还是赶快出去的好,回房间去洗个澡吧!”
我说“不必那么急。”又吻了她。
“想不想再看一下那两只白鸟?”我问她。她露出孩童般的表情说:“想。”于是我们来到窗前,彼此脸贴着脸,就这样一直凝视着窗外的运河。
村上龙1977 年就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广播电台担任音乐主持人,从而涉足当代传媒界,后来也经常参加电视专题节目,在因特网发达后,他还个人发行免费网络杂志《Japan Mail Media》,分析当今日本的经济现象,这些都是他不同于大多数作家同行之处。村上龙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如上文提到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69 sixty nine》、《黄玉》、《最后的家族》,以及《京子》(1996)、《在酱汤里》 (1997,获读卖小说奖)、《昭和歌谣大全集》(2002)等。从1979 年至今,源自村上龙作品的电影已有十多部公映,有的还是他自编自导,其中《黄玉》为他在意大利电影节上赢得了导演奖。此外,他的《村上龙电影小说集》(1995)也写得非常出色,于1996年获得平林泰子文学奖。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村上龙与另一位流行作家村上春树经常被相提并论,并称为“W村上”。这两位同姓村上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表现现代化大都市为作品主题,两人私交也很好, 1981年7月曾举行座谈会,畅谈各自的文学志向(村上龙为 “自我解放”,村上春树为“自我变革”)、生活道路及婚姻等,之后发表了对谈录《Walk don't Run》(要走,不要跑)。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大都市已经从过去的人们聚集生活的空间,逐渐向工作谋生的场所、向孤独而枯燥乏味的象征性符号的集合体转化演变,生活空间日益狭小,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面对如此的状,村春树作品的特征是善于把玩孤独,善于从枯燥乏味中发掘乐趣,与生活真实保持距离感,格调也比较优雅而宁静,喜怒哀乐爱憎表现得并不强烈。相比之下,村上龙的作品虽然涉猎面非常广泛,但主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作品中对于血腥、污秽、放荡、暴力、噪音、力量的撞击等场面的逼真、露骨、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是通过深入社会亲自体验获得的,笔下大多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大量使用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他还注重向青年一代传达人生思想,认为年轻人没有既得权益,是最无私而且充满希望的一代,他要通过作品让青年人理解人生的苦难,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立并努力寻找未来。这些,都构成了村上龙作品的文学特点。如果将村上春树的小说比作爵士乐的话,那么村上龙的作品则是快节奏的表现反社会题材的摇滚乐。
综上所述,村上龙自 24岁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开创了新兴的文学流派“透明族”以后,一直是日本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通过村上龙的作品,读者在理解、透视、预测当代都市生活变化和所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将获得深刻的启发。
Plot
Narrated by the main character Ryū (possibly Ryū Murakami himself) the novel focuses on his small group of young friends in the mid-seventies. Living in a Japanese town with an American air force base, their lives revolve around sex, drugs and rock 'n roll. The near-plotless story weaves a vividly raw image intensive journey through the daily monotony of drug-induced hallucinations, vicious acts of violence, overdoses, suicide, and group sex.
Characters
* Ryū – Narrator. 19-year-old bisexual substance abuser.
* Lilly – Ryū's prostitute friend and casual sex partner.
* Reiko – From Okinawa, sexually promiscuous friend of Ryū and girlfriend of Okinawa.
* Okinawa – From Okinawa, drug addicted friend of Ryū and boyfriend of Reiko.
* Yoshiyama – Unemployed junkie friend of Ryū and abusive boyfriend of Kei.
* Kei – Friend of Ryū and sexually promiscuous girlfriend of Yoshiyama.
* Kazuo – Male friend of Ryū.
* Moko – Sexually promiscuous substance abuser friend of Ryū.
* Jackson – African American Airman at the local AFB, he arranges for group sex escapades with his base comrades and Ryū's group.
Awards and nominations
Murakami submitted the novel to the literary magazine Gunzo's debutant contest, in which it won the first prize. It also won the prestigious Akutagawa Prize the same year.
English-language editions
* Ryū Murakami, Almost Transparent Blue (Kagirinaku tōmei ni chikai burū), translated by Nancy Andrew, 1st hardback ed., Tokyo ; New York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Distributed by Kodansha International/USA through Harper & Row, 1977, 126 pages. Tokyo ; New York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Distributed by Kodansha International/USA through Harper & Row, 1977, 126 p. ISBN 0-87011-305-4
* Ryū Murakami, Almost Transparent Blue, translated by Nancy Andrew, 1st paperback ed., Tokyo; New York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1 (reissue, 1992), 126 p. ISBN 0-87011-469-7
* Ryū Murakami, Almost Transparent Blue, translated by Nancy Andrew, 1st trade paperback ed., New York : Kodansha America, 2003, 128 p. ISBN 4-7700-2904-7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村上龙与另一位流行作家村上春树经常被相提并论,并称为“W村上”。这两位同姓村上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表现现代化大都市为作品主题,两人私交也很好, 1981年7月曾举行座谈会,畅谈各自的文学志向(村上龙为 “自我解放”,村上春树为“自我变革”)、生活道路及婚姻等,之后发表了对谈录《Walk don't Run》(要走,不要跑)。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大都市已经从过去的人们聚集生活的空间,逐渐向工作谋生的场所、向孤独而枯燥乏味的象征性符号的集合体转化演变,生活空间日益狭小,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面对如此的状,村春树作品的特征是善于把玩孤独,善于从枯燥乏味中发掘乐趣,与生活真实保持距离感,格调也比较优雅而宁静,喜怒哀乐爱憎表现得并不强烈。相比之下,村上龙的作品虽然涉猎面非常广泛,但主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作品中对于血腥、污秽、放荡、暴力、噪音、力量的撞击等场面的逼真、露骨、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是通过深入社会亲自体验获得的,笔下大多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大量使用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他还注重向青年一代传达人生思想,认为年轻人没有既得权益,是最无私而且充满希望的一代,他要通过作品让青年人理解人生的苦难,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立并努力寻找未来。这些,都构成了村上龙作品的文学特点。如果将村上春树的小说比作爵士乐的话,那么村上龙的作品则是快节奏的表现反社会题材的摇滚乐。
综上所述,村上龙自 24岁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开创了新兴的文学流派“透明族”以后,一直是日本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通过村上龙的作品,读者在理解、透视、预测当代都市生活变化和所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将获得深刻的启发。
Plot
Narrated by the main character Ryū (possibly Ryū Murakami himself) the novel focuses on his small group of young friends in the mid-seventies. Living in a Japanese town with an American air force base, their lives revolve around sex, drugs and rock 'n roll. The near-plotless story weaves a vividly raw image intensive journey through the daily monotony of drug-induced hallucinations, vicious acts of violence, overdoses, suicide, and group sex.
Characters
* Ryū – Narrator. 19-year-old bisexual substance abuser.
* Lilly – Ryū's prostitute friend and casual sex partner.
* Reiko – From Okinawa, sexually promiscuous friend of Ryū and girlfriend of Okinawa.
* Okinawa – From Okinawa, drug addicted friend of Ryū and boyfriend of Reiko.
* Yoshiyama – Unemployed junkie friend of Ryū and abusive boyfriend of Kei.
* Kei – Friend of Ryū and sexually promiscuous girlfriend of Yoshiyama.
* Kazuo – Male friend of Ryū.
* Moko – Sexually promiscuous substance abuser friend of Ryū.
* Jackson – African American Airman at the local AFB, he arranges for group sex escapades with his base comrades and Ryū's group.
Awards and nominations
Murakami submitted the novel to the literary magazine Gunzo's debutant contest, in which it won the first prize. It also won the prestigious Akutagawa Prize the same year.
English-language editions
* Ryū Murakami, Almost Transparent Blue (Kagirinaku tōmei ni chikai burū), translated by Nancy Andrew, 1st hardback ed., Tokyo ; New York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Distributed by Kodansha International/USA through Harper & Row, 1977, 126 pages. Tokyo ; New York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Distributed by Kodansha International/USA through Harper & Row, 1977, 126 p. ISBN 0-87011-305-4
* Ryū Murakami, Almost Transparent Blue, translated by Nancy Andrew, 1st paperback ed., Tokyo; New York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1 (reissue, 1992), 126 p. ISBN 0-87011-469-7
* Ryū Murakami, Almost Transparent Blue, translated by Nancy Andrew, 1st trade paperback ed., New York : Kodansha America, 2003, 128 p. ISBN 4-7700-2904-7
我总是自称“男孩”。
我有名字,可是不经常用,朋友们也不叫我的名字。我的父母得了一种特殊的病同时住进医院,好像得的还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病。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所以别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在学校常被人欺负,也被不认识的人揍过,所以我经常逃学。我的双亲不只是失去了健康,也失去许多东西,但是因为他们经营的是贸易生意,所以赚的钱多得用不完。我已经有两年没见着他们了。在他们身上没长出紫红色斑点之前,他们曾谈到过我的将来。
“你是爸爸和妈妈有病前生的孩子,所以不会像爸爸妈妈一样,但是这个世界的人并不这么认为,所以他们会歧视你。爸爸和妈妈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健康了,只能慢慢地等死。你才十三岁,根本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下去。如果有爷爷奶奶或叔叔什么的就好了,遗憾的是我们连一个亲戚也没有。幸运的是,你脑子很聪明,电脑也懂得比爸爸多,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你知道怎么跟香港和瑞士银行上网通信吧?不必再去学校读书了,去读你想读的书吧!去读些新型电脑的使用手册,还要把英语学好,你一定要成为英语听说读写都很棒的人。一个人生活虽然很辛苦,但如果上面的那些事情都能做到,你肯定会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以后我便开始一个人生活。首先遇到的是三餐的问题,因为家里有女佣,所以这不成问题。安排学校的事最麻烦,但爸爸已经安排我在他好朋友的私立中学就读,我跟一位英籍老师学习我感兴趣的网络科学,当然还必须得上数学和物理课。基本课程就是英文。
女佣是个老太太,所以不能当我的朋友。我没有朋友,因为我不会通朋友做不喜欢的事,而且我和同年龄的人也没话可说。英国籍老师说他愿意做我的朋友,但他说起话来象个宗教家,十三岁的男孩怎么会听那一套。星期六和星期天英国老师放假。女佣说的话比较有人情味儿,可是她老是说些什么石头、瓷砖、地板之类的事,因此我也不愿意和她交谈。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只好上网和电脑说话,但这总让人有些不安和距离感,所以我只好利用上课以外的时间多和英国老师说话,好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昨天吃了什么?”
“海带沙拉和鱼。”
“女佣做的菜好吃吗?”
“嗯,好吃,这可是雇她的条件之一。”
“你喝牛奶吗?”
“人家叫我喝才喝。”
“不要那么被动嘛!”
“知道了。”
通过这样的谈话,我那漂浮在空中的大脑才能回到身体上。我知道这叫做自我确认。我还有另外一个确认自己的方法,就是叫自己男孩。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在房里敲着钥匙,低声叫着自己。
男孩很无聊……
可是男孩并不寂寞……
男孩想听歌,已经听了西洋乐曲……
我就这样自言自语着,大脑虽然仍在身体外,但我并不感到迷们。一段时间过后就歪着头,最后跟自己说,男孩就是我。
有时我躺在地上像失去知觉一般。我曾在书上看过,一个人独居是很危险的事,可是我别无选择。
过了一年,我已经对英国老师感到厌倦了,虽然他的思想很开放,对于我双亲的病情并不抱偏见,但是面对已经十五岁的我讲解原子能和丛林中的氧气时,他却仍红着脸。看他那样说话很痛苦,可是要找个新的家教也是件费劲的事,于是我只好忍着。忍耐是一种精神负担,这种负担只有男孩游戏才能消解。男孩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近,每次这样呼喊时,我都觉得需要很大的努力。
当进步派的英国人花了两个钟头对我解释,如果不停止丛林采伐的话,世界上最美的猛兽将会绝种,会降下酸雨时,我对他说:“我不舒服,请您回去吧*于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低声喊着:“男孩……”只见男孩站着的地毯是妈妈生病前出差去中国时买的。男孩站在地毯上不知所措。男孩和我一样,每当独处的时候就会陷入迷惘,所以我必须对他发号施令。“我”不见了,越叫男孩我越觉得可怕。妈妈曾对我说:“如果你害怕,就慢跑让身体动一动。这样恐惧就不会缠上你了。”我打开门跑出去,可是“我”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随意跑出去的人只是男孩而已。
外面的景象很奇怪,月光是橙色的,街灯仍像平常一样明亮,照得人影好长好长。出租车亮着“空车”的红灯。空气中夹杂着一种异样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时妈妈的身体还很健康,某个冬日我要到外面玩,妈妈说:“外面很冷,要穿外套。”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冷风吹得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对春天的感觉有点模糊,但是在冬天、秋天和夏天,就会感觉到温度与湿度混合的空气中有一种异样的东西。那是个男孩第一次到外面去的夜里,空气中有股酸奶油的味道。明明是从屋里打开门跑了出去,却觉得好像是走进另一间更大的屋子里。我想“男孩”是第一次一个人外出吧!男孩跑下楼梯,站在路上。“好舒服的夜晚。”男孩低声说着。就在男孩低语的瞬间,“我”完全消失不见了。
男孩想,一定要冲过这条街才行。这条街就在他身旁。男孩好像被什么指使着,他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你要到哪里?”司机问。司机似乎没有察觉到事态的严重。
“冲过这条街,你看可以吗?”男孩说。
“冲过去?是不是发生内战了?怎么新闻报道没说?”
“不冲去过的话就惨了。”
男孩说得挂钻有力,好像街道景色也变了。
“你看前面,有封锁线!”
前方路上排了好多圆锥型的塑胶红灯。四周站满,机动车停下来,一群穿皮衣的年轻人正大声。
“那是在取缔飙车族!”
司机好像还没有进入状态。
“不是,那是穿和飙车族服装的另一种动物。千万别停车,一停下来就会被袭击的。”
“可是不停下来会撞到人啊!”
接近现场时司机将车速放慢,和那些穿皮衣的男孩全往这里瞧,他们的眼神充满憎恶。
“不要放慢速度。不然就会被袭击!”
男孩还是这么说,但当挥挥手上的警棍,司机还是把车停了下来。头上是高架桥,两侧并排耸立着高大的树木,空气闷热,月光撒在地面上,生物的喘吸声像合唱般传入男孩的耳中。一个穿皮衣的男孩将摩托车停好,他手里的铁棒发出幄幄的声音,跑过来砸出租车的挡风玻璃。玻璃上出现裂痕,男孩知道,要是再敲一下就碎了。那个穿着皮衣的男孩还想再挥舞铁棒。“快跑,光倒车冲出封锁线。”男孩推摇着已被吓呆了的司机说。其他穿皮衣的男孩和也向这里走来了。“再不快跑就会被抓进拘留所,每天被严刑拷问呀!”男孩还是一个劲摇着司机的身体,让他快开车。好不容易司机才恢复了意识,赶紧倒车准备冲破防线。当车子倒退时,前面的挡风玻璃全都掉落了,男孩觉得脚很痛。有两名想阻止车子冲过防线。男孩一直叫着:“要是停下来就会被抓住。”司机这次不再放慢速度。一名赶紧跳起来躲避,另一名则被车子撞起来,像做体操运动似的飞起来掉到地上。司机冲过封锁线后,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车停下来,嘴里不知道嘟哝些什么,也没有开车门就走出去了。
男孩也下车向着寂静无人的路上走去。男孩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但他确定是在东京的街头。男孩很讨厌那些闪烁的霓虹灯,他朝没有灯光。两旁满是树木的黑暗的小巷里走去。男孩想象四周围一定有很多敌人。
避开人群,在树林间走着,一轮满月倒映在地面上,有个长椅,上面是一对正在拥吻的男女。他们说不定是敌人派来的间谍,为了小心起见,他沿着水池边俯身前进。
“你也逃到这里来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体型削瘦的女人突然叫住他问,女人站在池边的柳树旁。男孩想起三个月前曾和住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患酒精中毒症的老年人上网通信的事。那个男人问他:“听说日本的幽灵都现身在柳树下,是真的吗?”男孩对日本的传统知识一无所知。那个老男人还说:“还有,听说日本的幽灵都没有脚。”他确认那个站在柳树旁的女人有脚。
“你也逃到这里来了!”女人问。男孩点点头。
“你还是个孩子,真难为你了。”
女人说完就走近男孩身旁,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她要男孩也过来一起坐,坐在这里正好可以看见地中央的月影。那月光映照着地面,好美,像是红了脸的少女,让男孩感到很有安全感。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地面的月影。
不久,男孩先开了口。男孩觉得很不可思议,女佣人天天来做饭给他吃,还会站在旁边看着他吃饭,并且一直跟他说话,但是男孩就是懒得回答她。对英国老师也是一样,他从不会主动开口说话。
但是这个白衣女人不同,男孩好像被这个女人吸引住了,就算对他自己的双亲,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当男孩能说出些有道理的话时,双亲就已住院的缘故吧。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为什么这么问?”女人看着男孩。
“称呼人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或阿姨之类的词吧!叫奶奶也行,要是你不生气的话,不过你真的很像奶奶呢!”
男孩想女人可能不会说出她的名字,他觉得有点沮丧,但他还是想跟她说话。
“如果不会失礼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他鼓起勇气问。
“名字嘛,我有好多名字,有人叫我友代,也有人叫我春代,还有的叫我秋子或良子。”
“有这么多名字真好!”
男孩说着,不知为什么哭了出来。他好久以前就想这么哭了,这种声音多么令人怀念。“男孩没有名字……”他边哭边说。他说了很多,关于双亲、电脑的事,男孩和自己的关系,英国人老师,最近新买机子的系统、左脚烫伤的疤痕,许多有关他的事他都说了出来。说到最后,男孩喃喃自语着,身体开始往一边移动。当他说完时,女人抱住男孩的肩膀。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女人说。
“我是个跳芭蕾舞的,你知道什么是芭蕾舞吧?芭蕾舞对于人来讲可以说是最严格的训练。我已经到了极限,极限是说我的身体和年龄都已经到了跳芭蕾舞的极限,就是说我再也不能跳了。”
女人柔柔的声音像一股暖流流过男孩冰冷的心,抱着他的手和这声音让他不再想放弃自己。
“后来我的神经就出现了异常,我常对自己说,我会不会得了精神病?知道自己有这种症状却无能为力,你能体会那种感觉吗?”
男孩点着头,他问;“像你这么坚强的人怎么会变得异常呢?”
“这个嘛!”
女人撩起头发,露出她的耳环。
“是送给我这个的人感动了我、改变了我。在我筋骨变硬时遇见了那个人,我为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而感动,他是那么的博学多识。你知道曙光女神吗?”
男孩点点头。
“那个人在阿拉斯加最北端见过曙光女神,女神教他好多称呼自己的方法。他只要吹起口哨,曙光女神就会出现在他身旁。我看见他站在雪地上吹口哨,曙光女神就在他头上飞来飞去,好美啊!真的很美,美得让我情不自禁地颤抖。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过游世界各地,是他改变了我,他自己也改变了。我们俩人决定一起从地球上消失,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生存。”
女人指着耳环。
“这只是个塑胶耳环,不会褪色。这个耳环的四周是个小小世界,我现在还活在这个小世界中,就算变成老奶奶,我还是会一直戴着它。当那个人送我这对耳环时,我就已经这样决定了。”
那耳环的形状不像菱形,也不是方形,而是一种很奇特的形状,在月光的照射下发出淡淡的白光。它的四周确实像个小小世界。
女人让他摸了摸耳环,男孩问道:“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世界吗?”
女人说:“你还是个小孩子,不可以想这样的事情。”然后她指着池面上的月影。
“那就叫银河,每当我想起那个人或是曙光女神时,我就来到这裹着银河。”《银河》是一首很有名的世界民谣,作曲者叫赫里马斯尼,曲调美极了。歌词的作者就不知道是谁了。我也不知道今后你该怎么办才好,可是……”
女人说完“可是”后慢慢摘下一只耳环。
“虽然只有一个,送给你吧!”
男孩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不能要。
“我还留着一个,没关系。”女人微笑着说。
“在这公园外丑陋的舞台上,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很痛苦。所以为了共同对抗,我们就各拿一个吧!绝不要变成和其他人一样,说不定哪一天你也能看见曙光女神,然后再把这个故事说给别人听。”
女人说完站起身来,消失在黑暗的丛林中。
黎明到来了。银河从地面上消逝时,所有的东西都被手中那个耳环的白光吸引,男孩又回到了我身边。
手握耳环漫步的“我”对男孩说,“走了好远的路!”
我有名字,可是不经常用,朋友们也不叫我的名字。我的父母得了一种特殊的病同时住进医院,好像得的还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病。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所以别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在学校常被人欺负,也被不认识的人揍过,所以我经常逃学。我的双亲不只是失去了健康,也失去许多东西,但是因为他们经营的是贸易生意,所以赚的钱多得用不完。我已经有两年没见着他们了。在他们身上没长出紫红色斑点之前,他们曾谈到过我的将来。
“你是爸爸和妈妈有病前生的孩子,所以不会像爸爸妈妈一样,但是这个世界的人并不这么认为,所以他们会歧视你。爸爸和妈妈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健康了,只能慢慢地等死。你才十三岁,根本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下去。如果有爷爷奶奶或叔叔什么的就好了,遗憾的是我们连一个亲戚也没有。幸运的是,你脑子很聪明,电脑也懂得比爸爸多,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你知道怎么跟香港和瑞士银行上网通信吧?不必再去学校读书了,去读你想读的书吧!去读些新型电脑的使用手册,还要把英语学好,你一定要成为英语听说读写都很棒的人。一个人生活虽然很辛苦,但如果上面的那些事情都能做到,你肯定会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以后我便开始一个人生活。首先遇到的是三餐的问题,因为家里有女佣,所以这不成问题。安排学校的事最麻烦,但爸爸已经安排我在他好朋友的私立中学就读,我跟一位英籍老师学习我感兴趣的网络科学,当然还必须得上数学和物理课。基本课程就是英文。
女佣是个老太太,所以不能当我的朋友。我没有朋友,因为我不会通朋友做不喜欢的事,而且我和同年龄的人也没话可说。英国籍老师说他愿意做我的朋友,但他说起话来象个宗教家,十三岁的男孩怎么会听那一套。星期六和星期天英国老师放假。女佣说的话比较有人情味儿,可是她老是说些什么石头、瓷砖、地板之类的事,因此我也不愿意和她交谈。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只好上网和电脑说话,但这总让人有些不安和距离感,所以我只好利用上课以外的时间多和英国老师说话,好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昨天吃了什么?”
“海带沙拉和鱼。”
“女佣做的菜好吃吗?”
“嗯,好吃,这可是雇她的条件之一。”
“你喝牛奶吗?”
“人家叫我喝才喝。”
“不要那么被动嘛!”
“知道了。”
通过这样的谈话,我那漂浮在空中的大脑才能回到身体上。我知道这叫做自我确认。我还有另外一个确认自己的方法,就是叫自己男孩。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在房里敲着钥匙,低声叫着自己。
男孩很无聊……
可是男孩并不寂寞……
男孩想听歌,已经听了西洋乐曲……
我就这样自言自语着,大脑虽然仍在身体外,但我并不感到迷们。一段时间过后就歪着头,最后跟自己说,男孩就是我。
有时我躺在地上像失去知觉一般。我曾在书上看过,一个人独居是很危险的事,可是我别无选择。
过了一年,我已经对英国老师感到厌倦了,虽然他的思想很开放,对于我双亲的病情并不抱偏见,但是面对已经十五岁的我讲解原子能和丛林中的氧气时,他却仍红着脸。看他那样说话很痛苦,可是要找个新的家教也是件费劲的事,于是我只好忍着。忍耐是一种精神负担,这种负担只有男孩游戏才能消解。男孩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近,每次这样呼喊时,我都觉得需要很大的努力。
当进步派的英国人花了两个钟头对我解释,如果不停止丛林采伐的话,世界上最美的猛兽将会绝种,会降下酸雨时,我对他说:“我不舒服,请您回去吧*于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低声喊着:“男孩……”只见男孩站着的地毯是妈妈生病前出差去中国时买的。男孩站在地毯上不知所措。男孩和我一样,每当独处的时候就会陷入迷惘,所以我必须对他发号施令。“我”不见了,越叫男孩我越觉得可怕。妈妈曾对我说:“如果你害怕,就慢跑让身体动一动。这样恐惧就不会缠上你了。”我打开门跑出去,可是“我”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随意跑出去的人只是男孩而已。
外面的景象很奇怪,月光是橙色的,街灯仍像平常一样明亮,照得人影好长好长。出租车亮着“空车”的红灯。空气中夹杂着一种异样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时妈妈的身体还很健康,某个冬日我要到外面玩,妈妈说:“外面很冷,要穿外套。”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冷风吹得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对春天的感觉有点模糊,但是在冬天、秋天和夏天,就会感觉到温度与湿度混合的空气中有一种异样的东西。那是个男孩第一次到外面去的夜里,空气中有股酸奶油的味道。明明是从屋里打开门跑了出去,却觉得好像是走进另一间更大的屋子里。我想“男孩”是第一次一个人外出吧!男孩跑下楼梯,站在路上。“好舒服的夜晚。”男孩低声说着。就在男孩低语的瞬间,“我”完全消失不见了。
男孩想,一定要冲过这条街才行。这条街就在他身旁。男孩好像被什么指使着,他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你要到哪里?”司机问。司机似乎没有察觉到事态的严重。
“冲过这条街,你看可以吗?”男孩说。
“冲过去?是不是发生内战了?怎么新闻报道没说?”
“不冲去过的话就惨了。”
男孩说得挂钻有力,好像街道景色也变了。
“你看前面,有封锁线!”
前方路上排了好多圆锥型的塑胶红灯。四周站满,机动车停下来,一群穿皮衣的年轻人正大声。
“那是在取缔飙车族!”
司机好像还没有进入状态。
“不是,那是穿和飙车族服装的另一种动物。千万别停车,一停下来就会被袭击的。”
“可是不停下来会撞到人啊!”
接近现场时司机将车速放慢,和那些穿皮衣的男孩全往这里瞧,他们的眼神充满憎恶。
“不要放慢速度。不然就会被袭击!”
男孩还是这么说,但当挥挥手上的警棍,司机还是把车停了下来。头上是高架桥,两侧并排耸立着高大的树木,空气闷热,月光撒在地面上,生物的喘吸声像合唱般传入男孩的耳中。一个穿皮衣的男孩将摩托车停好,他手里的铁棒发出幄幄的声音,跑过来砸出租车的挡风玻璃。玻璃上出现裂痕,男孩知道,要是再敲一下就碎了。那个穿着皮衣的男孩还想再挥舞铁棒。“快跑,光倒车冲出封锁线。”男孩推摇着已被吓呆了的司机说。其他穿皮衣的男孩和也向这里走来了。“再不快跑就会被抓进拘留所,每天被严刑拷问呀!”男孩还是一个劲摇着司机的身体,让他快开车。好不容易司机才恢复了意识,赶紧倒车准备冲破防线。当车子倒退时,前面的挡风玻璃全都掉落了,男孩觉得脚很痛。有两名想阻止车子冲过防线。男孩一直叫着:“要是停下来就会被抓住。”司机这次不再放慢速度。一名赶紧跳起来躲避,另一名则被车子撞起来,像做体操运动似的飞起来掉到地上。司机冲过封锁线后,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车停下来,嘴里不知道嘟哝些什么,也没有开车门就走出去了。
男孩也下车向着寂静无人的路上走去。男孩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但他确定是在东京的街头。男孩很讨厌那些闪烁的霓虹灯,他朝没有灯光。两旁满是树木的黑暗的小巷里走去。男孩想象四周围一定有很多敌人。
避开人群,在树林间走着,一轮满月倒映在地面上,有个长椅,上面是一对正在拥吻的男女。他们说不定是敌人派来的间谍,为了小心起见,他沿着水池边俯身前进。
“你也逃到这里来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体型削瘦的女人突然叫住他问,女人站在池边的柳树旁。男孩想起三个月前曾和住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患酒精中毒症的老年人上网通信的事。那个男人问他:“听说日本的幽灵都现身在柳树下,是真的吗?”男孩对日本的传统知识一无所知。那个老男人还说:“还有,听说日本的幽灵都没有脚。”他确认那个站在柳树旁的女人有脚。
“你也逃到这里来了!”女人问。男孩点点头。
“你还是个孩子,真难为你了。”
女人说完就走近男孩身旁,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她要男孩也过来一起坐,坐在这里正好可以看见地中央的月影。那月光映照着地面,好美,像是红了脸的少女,让男孩感到很有安全感。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地面的月影。
不久,男孩先开了口。男孩觉得很不可思议,女佣人天天来做饭给他吃,还会站在旁边看着他吃饭,并且一直跟他说话,但是男孩就是懒得回答她。对英国老师也是一样,他从不会主动开口说话。
但是这个白衣女人不同,男孩好像被这个女人吸引住了,就算对他自己的双亲,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当男孩能说出些有道理的话时,双亲就已住院的缘故吧。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为什么这么问?”女人看着男孩。
“称呼人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或阿姨之类的词吧!叫奶奶也行,要是你不生气的话,不过你真的很像奶奶呢!”
男孩想女人可能不会说出她的名字,他觉得有点沮丧,但他还是想跟她说话。
“如果不会失礼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他鼓起勇气问。
“名字嘛,我有好多名字,有人叫我友代,也有人叫我春代,还有的叫我秋子或良子。”
“有这么多名字真好!”
男孩说着,不知为什么哭了出来。他好久以前就想这么哭了,这种声音多么令人怀念。“男孩没有名字……”他边哭边说。他说了很多,关于双亲、电脑的事,男孩和自己的关系,英国人老师,最近新买机子的系统、左脚烫伤的疤痕,许多有关他的事他都说了出来。说到最后,男孩喃喃自语着,身体开始往一边移动。当他说完时,女人抱住男孩的肩膀。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女人说。
“我是个跳芭蕾舞的,你知道什么是芭蕾舞吧?芭蕾舞对于人来讲可以说是最严格的训练。我已经到了极限,极限是说我的身体和年龄都已经到了跳芭蕾舞的极限,就是说我再也不能跳了。”
女人柔柔的声音像一股暖流流过男孩冰冷的心,抱着他的手和这声音让他不再想放弃自己。
“后来我的神经就出现了异常,我常对自己说,我会不会得了精神病?知道自己有这种症状却无能为力,你能体会那种感觉吗?”
男孩点着头,他问;“像你这么坚强的人怎么会变得异常呢?”
“这个嘛!”
女人撩起头发,露出她的耳环。
“是送给我这个的人感动了我、改变了我。在我筋骨变硬时遇见了那个人,我为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而感动,他是那么的博学多识。你知道曙光女神吗?”
男孩点点头。
“那个人在阿拉斯加最北端见过曙光女神,女神教他好多称呼自己的方法。他只要吹起口哨,曙光女神就会出现在他身旁。我看见他站在雪地上吹口哨,曙光女神就在他头上飞来飞去,好美啊!真的很美,美得让我情不自禁地颤抖。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过游世界各地,是他改变了我,他自己也改变了。我们俩人决定一起从地球上消失,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生存。”
女人指着耳环。
“这只是个塑胶耳环,不会褪色。这个耳环的四周是个小小世界,我现在还活在这个小世界中,就算变成老奶奶,我还是会一直戴着它。当那个人送我这对耳环时,我就已经这样决定了。”
那耳环的形状不像菱形,也不是方形,而是一种很奇特的形状,在月光的照射下发出淡淡的白光。它的四周确实像个小小世界。
女人让他摸了摸耳环,男孩问道:“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世界吗?”
女人说:“你还是个小孩子,不可以想这样的事情。”然后她指着池面上的月影。
“那就叫银河,每当我想起那个人或是曙光女神时,我就来到这裹着银河。”《银河》是一首很有名的世界民谣,作曲者叫赫里马斯尼,曲调美极了。歌词的作者就不知道是谁了。我也不知道今后你该怎么办才好,可是……”
女人说完“可是”后慢慢摘下一只耳环。
“虽然只有一个,送给你吧!”
男孩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不能要。
“我还留着一个,没关系。”女人微笑着说。
“在这公园外丑陋的舞台上,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很痛苦。所以为了共同对抗,我们就各拿一个吧!绝不要变成和其他人一样,说不定哪一天你也能看见曙光女神,然后再把这个故事说给别人听。”
女人说完站起身来,消失在黑暗的丛林中。
黎明到来了。银河从地面上消逝时,所有的东西都被手中那个耳环的白光吸引,男孩又回到了我身边。
手握耳环漫步的“我”对男孩说,“走了好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