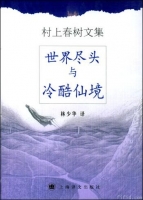這還是一個入口與出口的故事。就象那衹進入捕鼠器的小老鼠,因為出口已經關閉,第四天早上死掉了。小老鼠就是城市青年的例子,男主角也即是鼠,他在尋找出口。
詳盡的細節描寫,對彈子球機的迷戀,無不透出深深的寂寞和迷茫。曾在挪威森林出現的直子在這裏衹在第一節中提到,但感覺她的影子深深地籠罩住了全文。鼠忘不掉對直子的愛。他把自己封存在一個衹容自己容身的洞裏面,封存在彈子機遊戲裏面。持續不斷的彈子機遊戲把他與周圍的世界隔絶了。
《1973年的彈子球》為日本著名作傢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說,描述一青年為尋找少年時代的彈子機,又返回到無邊的孤獨之中的故事。這也是一部尋找的小說。一方面敘述者講述了“我”和“鼠”如何努力擺脫異化,尋求人生的出口;另一方面敘述者通過講述這段往事,也在為自己現在的生活尋找出口。小說藴涵着作者希望人類通過寫作獲得拯救的美好心願。
All three books in the Trilogy of the Rat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ut Pinball, 1973, and Hear The Wind Sing, the first two books in the trilogy, were only printed as English translations in Japan by Kodansha under their Kodansha English Library branding, and both only as A6-sized pocketbooks. Before being reprinted in 2009, these novels were difficult to locate and quite expensive, especially outside of Japan. Murakami is alleged to have said that he does not intend for these novels to be published outside of Japan. Whether or not this is true, both novels are much shorter than those that follow and make up the bulk of his work, and are less evolved stylistically. The title, 1973-nen no Pinbōru (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 reflects the title of the well-known Oe Kenzaburo novel, Man'en Gannen no Futtoboru (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
Plot introduction
Despite being an early work, Pinball shares many elements with Murakami's later novels. It describes itself in the text as "a novel about pinball," but also explores themes of loneliness and companionship, purposelessness, and destiny. As with the other books in the "Trilogy of the Rat" series, three of the characters include the protagonist, a nameless first-person narrator, his friend The Rat, and J, the owner of the bar where they often spend time.
Plot summary
The plot centers on the narrator's brief but intense obsession with pinball, his life as a freelance translator, and his later efforts to reunite with the old pinball machine that he used to play. Many familiar elements from Murakami's later novels are present. Wells, which are mentioned often in Murakami's novels and play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occur several times in Pinball. There is also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abuse of a cat, a plot element which recurs elsewhere in Murakami's fiction, especially Kafka on the Shore and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in which the search for a missing cat is an important plotline). Rain and the sea are also prominent motifs.
Major themes
Similar to many of Murakami's other novels, the narrator is a detached, unintentionally apathetic character whose deadpan demeanor stands either in union or, more often, starkly in contrast with the attitudes of other characters. The narrative, detached from the tangible world but highly introspective, sets a surreal tone for the novel, in which the narrator seems to find little unusual about such things as living with a pair of twins whom he cannot distinguish and whose names he does not know, or performing a funeral for a telephone circuit box. While the novel hints vaguely at supernatural occurrences (which often appear in Murakami's fiction), the plot is not intended to be interpreted allegorically.
詳盡的細節描寫,對彈子球機的迷戀,無不透出深深的寂寞和迷茫。曾在挪威森林出現的直子在這裏衹在第一節中提到,但感覺她的影子深深地籠罩住了全文。鼠忘不掉對直子的愛。他把自己封存在一個衹容自己容身的洞裏面,封存在彈子機遊戲裏面。持續不斷的彈子機遊戲把他與周圍的世界隔絶了。
《1973年的彈子球》為日本著名作傢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說,描述一青年為尋找少年時代的彈子機,又返回到無邊的孤獨之中的故事。這也是一部尋找的小說。一方面敘述者講述了“我”和“鼠”如何努力擺脫異化,尋求人生的出口;另一方面敘述者通過講述這段往事,也在為自己現在的生活尋找出口。小說藴涵着作者希望人類通過寫作獲得拯救的美好心願。
All three books in the Trilogy of the Rat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ut Pinball, 1973, and Hear The Wind Sing, the first two books in the trilogy, were only printed as English translations in Japan by Kodansha under their Kodansha English Library branding, and both only as A6-sized pocketbooks. Before being reprinted in 2009, these novels were difficult to locate and quite expensive, especially outside of Japan. Murakami is alleged to have said that he does not intend for these novels to be published outside of Japan. Whether or not this is true, both novels are much shorter than those that follow and make up the bulk of his work, and are less evolved stylistically. The title, 1973-nen no Pinbōru (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 reflects the title of the well-known Oe Kenzaburo novel, Man'en Gannen no Futtoboru (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
Plot introduction
Despite being an early work, Pinball shares many elements with Murakami's later novels. It describes itself in the text as "a novel about pinball," but also explores themes of loneliness and companionship, purposelessness, and destiny. As with the other books in the "Trilogy of the Rat" series, three of the characters include the protagonist, a nameless first-person narrator, his friend The Rat, and J, the owner of the bar where they often spend time.
Plot summary
The plot centers on the narrator's brief but intense obsession with pinball, his life as a freelance translator, and his later efforts to reunite with the old pinball machine that he used to play. Many familiar elements from Murakami's later novels are present. Wells, which are mentioned often in Murakami's novels and play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occur several times in Pinball. There is also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abuse of a cat, a plot element which recurs elsewhere in Murakami's fiction, especially Kafka on the Shore and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in which the search for a missing cat is an important plotline). Rain and the sea are also prominent motifs.
Major themes
Similar to many of Murakami's other novels, the narrator is a detached, unintentionally apathetic character whose deadpan demeanor stands either in union or, more often, starkly in contrast with the attitudes of other characters. The narrative, detached from the tangible world but highly introspective, sets a surreal tone for the novel, in which the narrator seems to find little unusual about such things as living with a pair of twins whom he cannot distinguish and whose names he does not know, or performing a funeral for a telephone circuit box. While the novel hints vaguely at supernatural occurrences (which often appear in Murakami's fiction), the plot is not intended to be interpreted allegorically.
村上春樹是以中篇《且聽風吟》開始文學創作的。《且聽風吟》的情節並不很復雜。“我”在酒吧喝酒,去衛生間時見一少女醉倒在地,遂就其護送回傢,翌日少女發現自己一絲不挂,斥責“我”侮辱了她,“我”有口難辯。但幾天後,兩人逐漸親密……不料“我”寒假回來,少女已無處可尋,衹好一個人坐在原來兩人坐過的地方悵悵地望着大海。
《且聽風吟》榮獲第二十二屆群像新人奬。有評委認為:“每一行都沒有多費筆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這是村上春樹的成名作,在日本已售出一百四十餘萬册。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絶望。“ -村上春樹《且聽風吟》
Themes
The author thought of the images of the story while watching the Tokyo Yakult Swallows at Meiji Jingu Stadium; he wrote it an hour at a time every night for four months; this became his first novel. When he submitt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to Japanese literary magazines such as Gunzo, the title was Happy Birthday, and White Christmas. The story takes place in 1970 over a period of nineteen days between August 8 and August 28, and is narrated by a twenty-one year old unnamed man. The story contains forty small chapters amounting to 130-pages. The story covers the craft of writing, the Japanese student movement, and, like later Murakami novels, relationships and loss. Like later novels, cooking,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listening to western music are regularly described. The narrator's close friend 'the Rat', around whom the trilogy of the Rat evolves, is a student and bar patron who expresses a general alienation towards society. The narrator describes the fictional American writer Derek Heartfield as a primary influence, citing his pulp science fiction works, and quoting him at several points.
Awards
* Gunzo Literature Prize
《且聽風吟》榮獲第二十二屆群像新人奬。有評委認為:“每一行都沒有多費筆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這是村上春樹的成名作,在日本已售出一百四十餘萬册。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絶望。“ -村上春樹《且聽風吟》
Themes
The author thought of the images of the story while watching the Tokyo Yakult Swallows at Meiji Jingu Stadium; he wrote it an hour at a time every night for four months; this became his first novel. When he submitt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to Japanese literary magazines such as Gunzo, the title was Happy Birthday, and White Christmas. The story takes place in 1970 over a period of nineteen days between August 8 and August 28, and is narrated by a twenty-one year old unnamed man. The story contains forty small chapters amounting to 130-pages. The story covers the craft of writing, the Japanese student movement, and, like later Murakami novels, relationships and loss. Like later novels, cooking,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listening to western music are regularly described. The narrator's close friend 'the Rat', around whom the trilogy of the Rat evolves, is a student and bar patron who expresses a general alienation towards society. The narrator describes the fictional American writer Derek Heartfield as a primary influence, citing his pulp science fiction works, and quoting him at several points.
Awards
* Gunzo Literature Prize
本書是村上春樹最重要的小說之一,與《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合稱為村上春樹三大傑作。小說共40章,單數20章“冷酷仙境”,雙數20 章為“世界盡頭”,這種交叉平行地展開故事情節的手法是村上春樹小說的特徵,而本書是這種特徵最典型的體現。“冷酷仙境”寫兩大黑社會組織在爭奪一個老科學家發明的控製人腦的裝置,老人躲到了地底。主人公 “我”是老人的實驗對象,他受到黑社會的恐嚇,在老人的孫女幫助下,經過了驚心動魄的地底之旅,好容易找到老人,卻被告知由於老人的計算錯誤,他24小時後離開人世,轉往另一世界即“世界盡頭”。“我”回到地面上, 與女友過了最後一夜告別,然後驅車到海邊靜候死的到來。“世界盡頭”是另一番景象,這裏與世隔絶,居民相安無事,但人們沒有心,沒有感情,沒有目標。 “我”一直想逃離這裏,但在即將成功時選擇了留下,因為“我”發現“世界盡頭”其實是“我”自己造出的。本書想象力奇特,藝術水準高超,情節極其荒誕而主題極其嚴肅,用變形的手法寫出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混亂現狀逃避無門的真實心態。
Plot summary
The story is split between parallel narratives. The odd-numbered chapters take place in 'Hard-Boiled Wonderland', although the phrase is not used anywhere in the text, only in page headers. The narrator is a "Calcutec," a human data processor/encryption system who has been trained to use his subconscious as an encryption key. The Calcutecs work for the quasi-governmental System, as opposed to the criminal "Semiotecs" who work for the Factory and who are generally fallen Calcute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s simple: the System protects data while the Semiotecs steal it, although it is suggested that one man might be behind both. The narrator completes an assignment for a mysterious scientist, who is exploring "sound reduction". He works in a laboratory hidden within an anachronistic version of Tokyo's sewer system.
The even-numbered chapters deal with a newcomer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 strange, isolated walled Town depicted in the frontispiece map as being surrounded by a perfect and impenetrable wall. The narrator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accepted into the Town. His shadow has been "cut off" and this shadow lives in the "shadow grounds" where he is not expected to survive the winter. Residents of the town are not allowed to have a shadow, and, it transpires, do not have a mind. Or is it only suppressed? The narrator is assigned quarters and a job as the current "dreamreader": a process intended to remove the traces of mind from the Town. He goes to the Library every evening where, assisted by the Librarian, he learns to read dreams from the skulls of unicorns. These "beasts" passively accept their role, sent out of the Town at night, to their enclosure where many die of cold during the winter.
The two storylines converge, exploring concepts of consciousness, the subconscious and identity.
In the original Japanese, the narrator uses the more formal first-person pronoun watashi to refer to himself in the 'Hard-Boiled Wonderland' narrative and the more intimate boku in the 'End of the World'. Translator Alfred Birnbaum achieved a similar effect in English by putting the 'End of the World' sections in the present tense.
Characters
In both narratives, none of the characters are named. Each is instead referred to by occupation or a general description, such as "the librarian" or "the big guy."
Hard-boiled wonderland
* The narrator - a Calcutec in his mid-thirties (35) who, aside from his unusual profession, lives the life of a typical Tokyo yuppie. Although very observant, he gives little thought to the strangeness of the world around him.
* The old man/the scientist - considered a great yet absent-minded scientist who hires the narrator to process information. He is researching "sound reduction". He has developed a way of reading the subconscious and actually recording it as comprehensible, if unrelated images. He had the inspiration of then editing these images to embed a fictional story into the subconscious of his subjects, one of whom is of course the narrator. He did this by working with the System due to the attractiveness of its facilities, though he disliked working for anyone. He later goes to Finland as said by his granddaughter to escape.
* The granddaughter in pink - the old man’s seventeen year old assistant, caretaker and granddaughter, described as chubby but attractive, invariably dressed in all pink. She did not go to any school as her grandfather tells her it is useless and rather teaches her all she needs to know in life; and thus she knows a couple of languages, how to handle a gun, among other thing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the old man "reduces" her sound, leaving her unable to speak. She tries, without any trace of subtlety, to convince the narrator to sleep with her.
* The librarian - the always-hungry girl who helps the narrator research unicorns and becomes his 48-hour girlfriend.
* Junior and Big Boy - two thugs who, on unknown orders, harass the narrator.
* INKlings - sewer-dwelling people described as "Kappa" who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culture. They are so dangerous the scientist lives in their realm, protected by a repelling device, to keep away from those who want to steal his data. It is said that they worship a fish (and leeches). They also do not eat fresh flesh; rather, once they catch a human, they submerge him in water and wait for him to rot in a few days before eating him.
End of the world
* The narrator - a newcomer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an initiation into the village, his shadow is cut off and his eyes pierced to make him averse to daylight and give him the ability to "read dreams", his allotted task. He cannot remember his former life nor underst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him.
* The narrator's shadow - apparently human in form. He retains the narrator's memory of their former life together, but he is doomed to die, separated as he is, and is harshly (but not cruelly) treated by his custodian, the gatekeeper. Upon his death, the narrator would then cease to have a 'mind'.
* The gatekeeper - the guardian and maintenance foreman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He instructs the narrator in his duties, and keeps the narrator’s shadow effectively a prisoner, putting him to work - disposing of dead beasts who die during winter.
* The librarian - the Town’s librarian who keeps the unicorn skulls in which the "dreams" reside. She assists the narrator in his work. She has no “mind” but her mother did, and the narrator becomes increasingly convinced that her mind is in fact only hidden, not irretrievably los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librarian and the other, in Hard Boiled Wonderland, is never made explicit.
* The colonel - an old man, the narrator's neighbour provides advice and support, and nurses him when he falls sick.
* The caretaker - a young man who tends the power station. An outsider who provides a miniature accordion, a possible key in the narrator's efforts to recover his mind and memories.
Influences
Murakami has often referred to his lov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particular admiration for hard-boiled pioneer Raymond Chandler. 'Hard-Boiled Wonderland' owes much to American "hard-boiled" detective fiction, as well as to science fiction and cyberpunk, but the book does not belong in any of those categories.
The 'end of the world'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Castle by Franz Kafka. Both deal with newcomers to strange villages who are both intrigued and horrified by the behavior of the villagers. The image of losing one's shadow when approaching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found in Knut Hamsun's 1898 novel Victoria. The same idea appeared earlier, in the 1814 story of "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Peter Schlemihl's Remarkable Story") by Adelbert von Chamisso. The theme of the human brain storing encrypted data is found in William Gibson's short story Johnny Mnemonic, but in interviews Murakami says this was not an influence.
Critical acclaim
Jay Rubin, who has translated many of Murakami's later works into English, said that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his favorite Murakami novel and that it "is just a shock after reading the black and white,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that is such the norm in Japan."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was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Tanizaki Prize in 1985.
Book information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English edition) by Haruki Murakami; translated by Alfred Birnbaum.
* Hardcover ISBN 4-7700-1544-5, published in September 1991 by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Paperback ISBN 0-679-74346-4, published on March 2, 1993 by Vintage Press
Plot summary
The story is split between parallel narratives. The odd-numbered chapters take place in 'Hard-Boiled Wonderland', although the phrase is not used anywhere in the text, only in page headers. The narrator is a "Calcutec," a human data processor/encryption system who has been trained to use his subconscious as an encryption key. The Calcutecs work for the quasi-governmental System, as opposed to the criminal "Semiotecs" who work for the Factory and who are generally fallen Calcute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s simple: the System protects data while the Semiotecs steal it, although it is suggested that one man might be behind both. The narrator completes an assignment for a mysterious scientist, who is exploring "sound reduction". He works in a laboratory hidden within an anachronistic version of Tokyo's sewer system.
The even-numbered chapters deal with a newcomer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 strange, isolated walled Town depicted in the frontispiece map as being surrounded by a perfect and impenetrable wall. The narrator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accepted into the Town. His shadow has been "cut off" and this shadow lives in the "shadow grounds" where he is not expected to survive the winter. Residents of the town are not allowed to have a shadow, and, it transpires, do not have a mind. Or is it only suppressed? The narrator is assigned quarters and a job as the current "dreamreader": a process intended to remove the traces of mind from the Town. He goes to the Library every evening where, assisted by the Librarian, he learns to read dreams from the skulls of unicorns. These "beasts" passively accept their role, sent out of the Town at night, to their enclosure where many die of cold during the winter.
The two storylines converge, exploring concepts of consciousness, the subconscious and identity.
In the original Japanese, the narrator uses the more formal first-person pronoun watashi to refer to himself in the 'Hard-Boiled Wonderland' narrative and the more intimate boku in the 'End of the World'. Translator Alfred Birnbaum achieved a similar effect in English by putting the 'End of the World' sections in the present tense.
Characters
In both narratives, none of the characters are named. Each is instead referred to by occupation or a general description, such as "the librarian" or "the big guy."
Hard-boiled wonderland
* The narrator - a Calcutec in his mid-thirties (35) who, aside from his unusual profession, lives the life of a typical Tokyo yuppie. Although very observant, he gives little thought to the strangeness of the world around him.
* The old man/the scientist - considered a great yet absent-minded scientist who hires the narrator to process information. He is researching "sound reduction". He has developed a way of reading the subconscious and actually recording it as comprehensible, if unrelated images. He had the inspiration of then editing these images to embed a fictional story into the subconscious of his subjects, one of whom is of course the narrator. He did this by working with the System due to the attractiveness of its facilities, though he disliked working for anyone. He later goes to Finland as said by his granddaughter to escape.
* The granddaughter in pink - the old man’s seventeen year old assistant, caretaker and granddaughter, described as chubby but attractive, invariably dressed in all pink. She did not go to any school as her grandfather tells her it is useless and rather teaches her all she needs to know in life; and thus she knows a couple of languages, how to handle a gun, among other thing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the old man "reduces" her sound, leaving her unable to speak. She tries, without any trace of subtlety, to convince the narrator to sleep with her.
* The librarian - the always-hungry girl who helps the narrator research unicorns and becomes his 48-hour girlfriend.
* Junior and Big Boy - two thugs who, on unknown orders, harass the narrator.
* INKlings - sewer-dwelling people described as "Kappa" who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culture. They are so dangerous the scientist lives in their realm, protected by a repelling device, to keep away from those who want to steal his data. It is said that they worship a fish (and leeches). They also do not eat fresh flesh; rather, once they catch a human, they submerge him in water and wait for him to rot in a few days before eating him.
End of the world
* The narrator - a newcomer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an initiation into the village, his shadow is cut off and his eyes pierced to make him averse to daylight and give him the ability to "read dreams", his allotted task. He cannot remember his former life nor underst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him.
* The narrator's shadow - apparently human in form. He retains the narrator's memory of their former life together, but he is doomed to die, separated as he is, and is harshly (but not cruelly) treated by his custodian, the gatekeeper. Upon his death, the narrator would then cease to have a 'mind'.
* The gatekeeper - the guardian and maintenance foreman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He instructs the narrator in his duties, and keeps the narrator’s shadow effectively a prisoner, putting him to work - disposing of dead beasts who die during winter.
* The librarian - the Town’s librarian who keeps the unicorn skulls in which the "dreams" reside. She assists the narrator in his work. She has no “mind” but her mother did, and the narrator becomes increasingly convinced that her mind is in fact only hidden, not irretrievably los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librarian and the other, in Hard Boiled Wonderland, is never made explicit.
* The colonel - an old man, the narrator's neighbour provides advice and support, and nurses him when he falls sick.
* The caretaker - a young man who tends the power station. An outsider who provides a miniature accordion, a possible key in the narrator's efforts to recover his mind and memories.
Influences
Murakami has often referred to his lov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particular admiration for hard-boiled pioneer Raymond Chandler. 'Hard-Boiled Wonderland' owes much to American "hard-boiled" detective fiction, as well as to science fiction and cyberpunk, but the book does not belong in any of those categories.
The 'end of the world'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Castle by Franz Kafka. Both deal with newcomers to strange villages who are both intrigued and horrified by the behavior of the villagers. The image of losing one's shadow when approaching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found in Knut Hamsun's 1898 novel Victoria. The same idea appeared earlier, in the 1814 story of "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Peter Schlemihl's Remarkable Story") by Adelbert von Chamisso. The theme of the human brain storing encrypted data is found in William Gibson's short story Johnny Mnemonic, but in interviews Murakami says this was not an influence.
Critical acclaim
Jay Rubin, who has translated many of Murakami's later works into English, said that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his favorite Murakami novel and that it "is just a shock after reading the black and white,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that is such the norm in Japan."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was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Tanizaki Prize in 1985.
Book information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English edition) by Haruki Murakami; translated by Alfred Birnbaum.
* Hardcover ISBN 4-7700-1544-5, published in September 1991 by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Paperback ISBN 0-679-74346-4, published on March 2, 1993 by Vintage Press
《國境以南太陽以西》講述了37歲的男主人公,在東京市區擁有兩傢興旺的酒吧,還有嬌美的妻子,可愛的女兒,他是一位真正的成功人士。但是,他的內心還是感到饑餓幹渴,事業和家庭都填補不了,而讓他那缺憾的部分充盈起來的,是他小學時的女友島本。島本不願吐露自己的經歷、身份、衹希望他就這樣接受眼前的自己,衹把她當成小學時那個愛古典樂的女孩。然而,就在他接受了這不可能接受的條件時,兩人卻在箱根別墅度過了銷魂的一夜。翌晨,她一去杳然、再無蹤跡可尋了。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Hajime, starting from his childhood in a small town in Japan. Here he meets a girl, Shimamoto, who is also an only child and suffers from polio, which causes her to drag her leg as she walks.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together talking about their interests in life and listening to records on Shimamoto's stereo. They join different high schools and grow apart. They are reunited again at the age of 36, Hajime now the father of two children and owner of two successful jazz bars in Aoyama, the trendy part of Tokyo. With Shimamoto never giving any detail as to her own life and appearing only at random intervals, she haunts him as a constant 'what if'. Despite his current situation, meeting Shimamoto again sets off a chain of events that eventually forces Hajime to choose between his wife and family or attempting to recapture the magic of the past.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Hajime, starting from his childhood in a small town in Japan. Here he meets a girl, Shimamoto, who is also an only child and suffers from polio, which causes her to drag her leg as she walks.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together talking about their interests in life and listening to records on Shimamoto's stereo. They join different high schools and grow apart. They are reunited again at the age of 36, Hajime now the father of two children and owner of two successful jazz bars in Aoyama, the trendy part of Tokyo. With Shimamoto never giving any detail as to her own life and appearing only at random intervals, she haunts him as a constant 'what if'. Despite his current situation, meeting Shimamoto again sets off a chain of events that eventually forces Hajime to choose between his wife and family or attempting to recapture the magic of the past.
不僅再度出現了中國人的形象,更以象徵手法,描繪了隱匿於日本社會縱深處的一種“惡”,隱含着作傢對日本民族的批判和對於這個民族未來嚮何處去的擔憂。
書中仍然采用村上春樹最擅長的平行綫結構,以即將去北京留學的女孩瑪麗救助一名被日本惡客凌辱的中國女孩這一情節展開故事。與我們熟悉的村上小說不同,《天黑以後》不再是創造都市的落寞或奇遇,不再是把玩孤獨,取代西方爵士樂和窗外霏霏細雨的是深夜11時52分開始發生在一座現代化大都市裏的惡——因受害一方不敢報警而可能永遠消失在異國夜幕下的惡,掩蓋在衣冠楚楚下的普通人的惡。
天黑以後-簡介 ······
故事發生在鼕天的東京,時間跨度衹有晚上12點到早晨6點七個小時,采用兩條平行綫結構,分別敘述一對年輕的姐妹,一個在黑夜中昏睡,一個在思考和行動。
女孩十九歲,漂亮,是由不法中國人偷運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說開始不久,悲慘場景就出現了:天黑以後她在情愛旅館接客時,因突然來了月經而被一個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臉腫,衣物也被搶走,赤身裸體蜷縮在墻角吞聲掩泣,床單上滿是血跡。半夜在餐館裏獨自看書的女主人公瑪麗因為會講中國話,通過吹長號的大學生高橋的介紹,被旅館女經理找來當翻譯處理這場“麻煩”,故事情節由此鋪展開去。
村上在書中塑造的白川,可以說是日本這個民族“惡”的典型,他敬業、勤奮、文質彬彬,但生活刻板,觀念頑固,施暴後行若無事,還繼續加班,絲毫沒有作惡的意識。著名翻譯傢林少華教授在譯後記中寫道:“這種惡,既不同於恐怖分子的惡和極權主義的惡,又不同於太平洋彼岸霸權主義的惡,更不同於殺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惡,它發生在日本社會又不局限於日本社會,因而是更應警惕的惡。”村上本人在寫完《海邊的卡夫卡》後,就表示自己下回“想寫既是象徵性的又有細部現實感那樣的惡。歸根到底,惡這個東西,是同卑鄙、怯懦、想象力匱乏等素質聯繫在一起的。”
Plot summary
Alienation, a recurring motif in the works of Murakami, is the central theme in this novel set in metropolitan Tokyo over the course of one night. Main characters include Mari, a 19-year-old student, who is spending the night reading in a Denny's. There she meets Takahashi, a trombone-playing student who loves Curtis Fuller's "Five Spot After Dark" song on Blues-ette; Takahashi knows Mari's sister Eri and insists that the group of them have hung out before. Meanwhile, Eri is being watched in her sleep by someone sinister.
Mari crosses ways with a retired female wrestler, now working as a manager in a love hotel (whom Takahashi knows and referred to Mari), a Chinese prostitute who has been beaten and stripped of everything in this same love hotel, and a sadistic computer expert. The story takes place in a world between reality and dream.
Structure
The story is broken down in small chapters of varying length. An added element of interest—and perhaps a post-modern reference—is the fact that the book has a 'real-time' timeline, beginning at the early hours of the night.
Translations
A Russ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5, a Dutch version in 2006, Czech and Polish versions in 2007.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5 and translated by Lai Ming-chu (zh:賴明珠), and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5 and translated by Lin Shaohua (林少華 / 林少华) . It was published in French on January 4, 2007, as Le passage de la nuit by Éditions Belfon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released on May 8, 2007.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pecial limited-edition hardback version exists, only available at Borders bookshops. In 2007 a Romanian version was also published by Polirom under the title In noapte. A Norweg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7 by Pax, translated by Ika Kaminka. A Portuguese version was released on November 2008 under the title "Os Passageiros da Noite" ("The Night Passengers"). In 2009 a Brazilian Portuguese version was released, titled "Após o Anoitecer". A Serb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8. Translator was Nataša Tomić, and it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Kad padne noć. A Pers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9 by Ketebsaraye Nik, translated by Mahdi Ghabraee under the title "Pas az tariki". An Italian version was also released in 2008 by Einaudi, translated by Antonietta Pastore under the title "After Dark".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by Lourdes Porta, titled also "After Dark", was published in 2008 by Tusquets Editores under "Andanzas" series. In 2009, a Hebrew version translated by Mickey Ball was released by Kinneret Zmora Dvir. In 2009 Lithuan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name "Pernakt". It was translated by Ieva Susnytė.
書中仍然采用村上春樹最擅長的平行綫結構,以即將去北京留學的女孩瑪麗救助一名被日本惡客凌辱的中國女孩這一情節展開故事。與我們熟悉的村上小說不同,《天黑以後》不再是創造都市的落寞或奇遇,不再是把玩孤獨,取代西方爵士樂和窗外霏霏細雨的是深夜11時52分開始發生在一座現代化大都市裏的惡——因受害一方不敢報警而可能永遠消失在異國夜幕下的惡,掩蓋在衣冠楚楚下的普通人的惡。
天黑以後-簡介 ······
故事發生在鼕天的東京,時間跨度衹有晚上12點到早晨6點七個小時,采用兩條平行綫結構,分別敘述一對年輕的姐妹,一個在黑夜中昏睡,一個在思考和行動。
女孩十九歲,漂亮,是由不法中國人偷運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說開始不久,悲慘場景就出現了:天黑以後她在情愛旅館接客時,因突然來了月經而被一個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臉腫,衣物也被搶走,赤身裸體蜷縮在墻角吞聲掩泣,床單上滿是血跡。半夜在餐館裏獨自看書的女主人公瑪麗因為會講中國話,通過吹長號的大學生高橋的介紹,被旅館女經理找來當翻譯處理這場“麻煩”,故事情節由此鋪展開去。
村上在書中塑造的白川,可以說是日本這個民族“惡”的典型,他敬業、勤奮、文質彬彬,但生活刻板,觀念頑固,施暴後行若無事,還繼續加班,絲毫沒有作惡的意識。著名翻譯傢林少華教授在譯後記中寫道:“這種惡,既不同於恐怖分子的惡和極權主義的惡,又不同於太平洋彼岸霸權主義的惡,更不同於殺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惡,它發生在日本社會又不局限於日本社會,因而是更應警惕的惡。”村上本人在寫完《海邊的卡夫卡》後,就表示自己下回“想寫既是象徵性的又有細部現實感那樣的惡。歸根到底,惡這個東西,是同卑鄙、怯懦、想象力匱乏等素質聯繫在一起的。”
Plot summary
Alienation, a recurring motif in the works of Murakami, is the central theme in this novel set in metropolitan Tokyo over the course of one night. Main characters include Mari, a 19-year-old student, who is spending the night reading in a Denny's. There she meets Takahashi, a trombone-playing student who loves Curtis Fuller's "Five Spot After Dark" song on Blues-ette; Takahashi knows Mari's sister Eri and insists that the group of them have hung out before. Meanwhile, Eri is being watched in her sleep by someone sinister.
Mari crosses ways with a retired female wrestler, now working as a manager in a love hotel (whom Takahashi knows and referred to Mari), a Chinese prostitute who has been beaten and stripped of everything in this same love hotel, and a sadistic computer expert. The story takes place in a world between reality and dream.
Structure
The story is broken down in small chapters of varying length. An added element of interest—and perhaps a post-modern reference—is the fact that the book has a 'real-time' timeline, beginning at the early hours of the night.
Translations
A Russ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5, a Dutch version in 2006, Czech and Polish versions in 2007.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5 and translated by Lai Ming-chu (zh:賴明珠), and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5 and translated by Lin Shaohua (林少華 / 林少华) . It was published in French on January 4, 2007, as Le passage de la nuit by Éditions Belfon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released on May 8, 2007.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pecial limited-edition hardback version exists, only available at Borders bookshops. In 2007 a Romanian version was also published by Polirom under the title In noapte. A Norweg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7 by Pax, translated by Ika Kaminka. A Portuguese version was released on November 2008 under the title "Os Passageiros da Noite" ("The Night Passengers"). In 2009 a Brazilian Portuguese version was released, titled "Após o Anoitecer". A Serb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8. Translator was Nataša Tomić, and it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Kad padne noć. A Pers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2009 by Ketebsaraye Nik, translated by Mahdi Ghabraee under the title "Pas az tariki". An Italian version was also released in 2008 by Einaudi, translated by Antonietta Pastore under the title "After Dark".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by Lourdes Porta, titled also "After Dark", was published in 2008 by Tusquets Editores under "Andanzas" series. In 2009, a Hebrew version translated by Mickey Ball was released by Kinneret Zmora Dvir. In 2009 Lithuan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name "Pernakt". It was translated by Ieva Susnytė.
本書是作者篇幅最大的小說三部麯。 失業者岡田亨的妻子久美子在其兄長、衆議員,黑暗勢力代表人物綿𠔌升的脅迫下失蹤了。岡田身邊來了許多怪人:女巫師、 “意識娼婦”、失手使男友車禍死亡的少女、舊軍人等。同時也發生了許多怪事。岡田到一口深井裏冥思苦想後,出來在奇怪的母子“肉豆蔻”、“肉桂”的幫助下嚮綿𠔌升挑戰,在虛幻中將其擊傷,久美子又在現實中將其殺死。本書色彩詭異,規模宏大,虛實交叉,被稱為當代的“一千零一夜”。 本書在1997年曾由譯林出版,在讀者中已具有一定影響。
Two chapter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under the titles The Zoo Attack on July 31, 1995, and Another Way to Die on January 20, 1997.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translated by Alfred Birnbaum was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ion The Elephant Vanishes under the title The Wind-up Bird and Tuesday's Women.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 name Noboru Wataya is used in Family Affair of The Elephant Vanishes, while having a similar personality and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 is not related to the one in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of the same name. Noboru Wataya is also used in Jay Rubin's translation of The Elephant Vanishes in The Elephant Vanishes.
Th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was released in three parts, which make up the three "books" of the single volume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1. Dorobō kasasagi hen (泥棒かささぎ編?)
2. Yogen suru tori hen (予言する鳥編?)
3. Torisashi otoko hen (鳥刺し男編?)
For this novel, Murakami received the Yomiuri Literary Award, which was awarded to him by one of his harshest former critics, Oe Kenzaburo.
Plot summary
The novel is about a low-key unemployed man, Toru Okada, whose cat runs away. A chain of events follow that prove that his seemingly mundane boring life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it appears.
Main characters
While this book has many major and minor characters, these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 Toru Okada: The narrator and protagonist, Toru is a passive and often apathetic young man living in suburban Japan. He is Kumiko's husband and continually follows the orders or wishes of others. Currently unemployed, he is the embodiment of passivity.
* Kumiko Okada: Kumiko is Toru's wife and, as the breadwinner of the couple, is the more autonomous of the two. She works in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 Noboru Wataya: Noboru is Kumiko's older brother. He is presented as a mediagenic figure; the public loves him, but Toru cannot stand him. Noboru appears as an academic in the beginning, becomes a politician in the story, and has no apparent personal life. He is said to be hidden behind a façade — all style, and no substance. ("Noboru Wataya" is also the name Toru and Kumiko gave to their pet cat, whom Toru later renames Mackerel, like the fish; the character name also appeared in Family Affair, translated by Jay Rubin, of The Elephant Vanishes collection.)
* May Kasahara: May is a middleteen girl who should be in school, but, by choice, is not. Toru and May carry on a fairly constant exchange throughout a good deal of the novel; when May is not present, she writes to him (though the reader can peruse them, her letters never reach him). Their conversations in person are often bizarre and revolve around death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human life. Even more bizarre is the cheerful and decidedly non-serious air with which these conversations take place.
* Lieutenant Mamiya: Mamiya was an officer during the Japanese military efforts in Manchukuo, and meets Toru while carrying out the particulars of Mr. Honda's will. He has been emotionally scarred by witnessing the flaying of a superior officer and several nights spent in a dried-up well. He tells Toru his story both in person and in letters.
* Malta Kano: Malta Kano is a medium of sorts who changed her name to "Malta" after performing some kind of "austerities" on the island of Malta for some time. She is enlisted by Kumiko to help the Okadas find their missing cat.
* Creta Kano: Malta's younger sister and apprentice of sorts, she describes herself as a "prostitute of the mind." Disturbingly, for Toru, Creta has a nearly identical face and figure to Kumiko.
* Nutmeg Akasaka: Nutmeg first meets Toru as he sits on a bench watching people's faces every day in Shinjuku. The second time they meet she is attracted to the blue-black mark on his right cheek. She and Toru share a few strange coincidences: the wind-up bird in Toru's yard and the blue-black cheek mark appear in Nutmeg's World War II-related stories, and also Nutmeg's father and Lieutenant Mamiya (an acquaintance of Toru's) are linked by World War II. "Nutmeg Akasaka" is a pseudonym she chose for herself after insisting to Toru that her "real" name is irrelevant. Her real name is never mentioned in the novel.
* Cinnamon Akasaka: Cinnamon is Nutmeg's adult son who hasn't spoken since age 6. He communicates through a system of hand movements and mouthed words. Somehow, people who've just met him (who presumably have never lipread or used sign language) find him perfectly comprehensible. "Cinnamon," too, is a pseudonym created by Nutmeg.
Missing chapters
Two chapters from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original three-volume Japanese paperback edition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one of the chapters near the excluded two was moved ahead of another chapter, taking it out of the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order.
The two missing chapters elabor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ru Okada and Creta Kano, and a "hearing" of the wind-up bird as Toru burns a box of Kumiko's belongings.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was carried out by Jay Rubin.
It must also be noted that in addition to very not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Japanese hardcover and paperback editions.
Further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ditions, but these are much more superficial.
The German translation by Giovanni and Ditte Bandini is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ot on the Japanese original.
Book information
* Murakami, Haruki.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translated by Jay Rubin. ISBN 0-679-77543-9.
* Murakami, Haruki.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translated by Jay Rubin. ISBN 1-86046-581-1.
Two chapter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under the titles The Zoo Attack on July 31, 1995, and Another Way to Die on January 20, 1997.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translated by Alfred Birnbaum was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ion The Elephant Vanishes under the title The Wind-up Bird and Tuesday's Women.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 name Noboru Wataya is used in Family Affair of The Elephant Vanishes, while having a similar personality and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 is not related to the one in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of the same name. Noboru Wataya is also used in Jay Rubin's translation of The Elephant Vanishes in The Elephant Vanishes.
Th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was released in three parts, which make up the three "books" of the single volume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1. Dorobō kasasagi hen (泥棒かささぎ編?)
2. Yogen suru tori hen (予言する鳥編?)
3. Torisashi otoko hen (鳥刺し男編?)
For this novel, Murakami received the Yomiuri Literary Award, which was awarded to him by one of his harshest former critics, Oe Kenzaburo.
Plot summary
The novel is about a low-key unemployed man, Toru Okada, whose cat runs away. A chain of events follow that prove that his seemingly mundane boring life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it appears.
Main characters
While this book has many major and minor characters, these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 Toru Okada: The narrator and protagonist, Toru is a passive and often apathetic young man living in suburban Japan. He is Kumiko's husband and continually follows the orders or wishes of others. Currently unemployed, he is the embodiment of passivity.
* Kumiko Okada: Kumiko is Toru's wife and, as the breadwinner of the couple, is the more autonomous of the two. She works in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 Noboru Wataya: Noboru is Kumiko's older brother. He is presented as a mediagenic figure; the public loves him, but Toru cannot stand him. Noboru appears as an academic in the beginning, becomes a politician in the story, and has no apparent personal life. He is said to be hidden behind a façade — all style, and no substance. ("Noboru Wataya" is also the name Toru and Kumiko gave to their pet cat, whom Toru later renames Mackerel, like the fish; the character name also appeared in Family Affair, translated by Jay Rubin, of The Elephant Vanishes collection.)
* May Kasahara: May is a middleteen girl who should be in school, but, by choice, is not. Toru and May carry on a fairly constant exchange throughout a good deal of the novel; when May is not present, she writes to him (though the reader can peruse them, her letters never reach him). Their conversations in person are often bizarre and revolve around death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human life. Even more bizarre is the cheerful and decidedly non-serious air with which these conversations take place.
* Lieutenant Mamiya: Mamiya was an officer during the Japanese military efforts in Manchukuo, and meets Toru while carrying out the particulars of Mr. Honda's will. He has been emotionally scarred by witnessing the flaying of a superior officer and several nights spent in a dried-up well. He tells Toru his story both in person and in letters.
* Malta Kano: Malta Kano is a medium of sorts who changed her name to "Malta" after performing some kind of "austerities" on the island of Malta for some time. She is enlisted by Kumiko to help the Okadas find their missing cat.
* Creta Kano: Malta's younger sister and apprentice of sorts, she describes herself as a "prostitute of the mind." Disturbingly, for Toru, Creta has a nearly identical face and figure to Kumiko.
* Nutmeg Akasaka: Nutmeg first meets Toru as he sits on a bench watching people's faces every day in Shinjuku. The second time they meet she is attracted to the blue-black mark on his right cheek. She and Toru share a few strange coincidences: the wind-up bird in Toru's yard and the blue-black cheek mark appear in Nutmeg's World War II-related stories, and also Nutmeg's father and Lieutenant Mamiya (an acquaintance of Toru's) are linked by World War II. "Nutmeg Akasaka" is a pseudonym she chose for herself after insisting to Toru that her "real" name is irrelevant. Her real name is never mentioned in the novel.
* Cinnamon Akasaka: Cinnamon is Nutmeg's adult son who hasn't spoken since age 6. He communicates through a system of hand movements and mouthed words. Somehow, people who've just met him (who presumably have never lipread or used sign language) find him perfectly comprehensible. "Cinnamon," too, is a pseudonym created by Nutmeg.
Missing chapters
Two chapters from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original three-volume Japanese paperback edition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one of the chapters near the excluded two was moved ahead of another chapter, taking it out of the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order.
The two missing chapters elabor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ru Okada and Creta Kano, and a "hearing" of the wind-up bird as Toru burns a box of Kumiko's belongings.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was carried out by Jay Rubin.
It must also be noted that in addition to very not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Japanese hardcover and paperback editions.
Further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ditions, but these are much more superficial.
The German translation by Giovanni and Ditte Bandini is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ot on the Japanese original.
Book information
* Murakami, Haruki.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translated by Jay Rubin. ISBN 0-679-77543-9.
* Murakami, Haruki.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translated by Jay Rubin. ISBN 1-86046-581-1.
一頭控製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蹤了,它的宿主、黑社會頭子命在旦夕。潦倒的東京青年職員無意中得到羊的照片,不料就此成了黑社會的脅迫對象,攜着女友踏上了尋羊冒險之旅。在北海道的雪山絶地,他終於到了照片的拍攝者——不,那衹是其陰魂,因為這位綽號“鼠”的朋友,已經與那罪惡之源同歸於盡了。
《尋羊冒險記》是村上春樹繼處女作《且聽風吟》 、《1973年的彈珠遊戲》後的第三部小說,與上述兩部作品構成“我與鼠”係列三部麯。《尋羊冒險記》是第三部,用現實與虛幻交織的奇特之筆,打開了日本的新文學之門。小說極富寓言性與神話色彩,作者認為該小說的創作“順利到最後,在恰到火候處止筆”。《尋羊冒險記》是村上的第一部夠規模的長篇,村上因此獲得了野間文藝新人賞。
In A Wild Sheep Chase, Murakami blends elements of Americ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Japanese contexts, exploring post-WWII Japa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e book is part mystery and part fantasy with a postmodern twist.
Plot summary
This mock-detective tale follows an unnamed Japanese man through Tokyo and Hokkaidō in 1978. The passive, chain-smoking main character gets swept away on an adventure that leads him on a hunt for a sheep that hasn’t been seen for years. The apathetic protagonist meets a woman with magically seductive ears and a strange man who dresses as a sheep and talks in slurs; in this way there are elements of Japanese animism or Shinto.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narrator into the hunt and repeated references to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raise connections to "The Red-Headed League."
Sequel
Murakami wrote a sequel to this book, entitled Dance Dance Dance, which also follows the adventures of the unnamed protagonist and the Sheep Man. However, its plot, tone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characters are sufficiently different that Dance Dance Dance can be seen as separate from the "Trilogy of the Rat."
Awards
* Noma Literary Newcomer's Prize
《尋羊冒險記》是村上春樹繼處女作《且聽風吟》 、《1973年的彈珠遊戲》後的第三部小說,與上述兩部作品構成“我與鼠”係列三部麯。《尋羊冒險記》是第三部,用現實與虛幻交織的奇特之筆,打開了日本的新文學之門。小說極富寓言性與神話色彩,作者認為該小說的創作“順利到最後,在恰到火候處止筆”。《尋羊冒險記》是村上的第一部夠規模的長篇,村上因此獲得了野間文藝新人賞。
In A Wild Sheep Chase, Murakami blends elements of Americ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Japanese contexts, exploring post-WWII Japa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e book is part mystery and part fantasy with a postmodern twist.
Plot summary
This mock-detective tale follows an unnamed Japanese man through Tokyo and Hokkaidō in 1978. The passive, chain-smoking main character gets swept away on an adventure that leads him on a hunt for a sheep that hasn’t been seen for years. The apathetic protagonist meets a woman with magically seductive ears and a strange man who dresses as a sheep and talks in slurs; in this way there are elements of Japanese animism or Shinto.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narrator into the hunt and repeated references to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raise connections to "The Red-Headed League."
Sequel
Murakami wrote a sequel to this book, entitled Dance Dance Dance, which also follows the adventures of the unnamed protagonist and the Sheep Man. However, its plot, tone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characters are sufficiently different that Dance Dance Dance can be seen as separate from the "Trilogy of the Rat."
Awards
* Noma Literary Newcomer's Prize
傳說,挪威的森林是一片大得會讓人迷路的森林。那種,人進得去卻出不來的巨大原始森林。
風靡60年代的甲殼蟲樂隊唱出了名聞世界的麯子 Norwegian Wood。“海潮的清香,遙遠的汽笛,女孩肌體的感觸,洗發香波的氣味,傍晚的和風,縹緲的憧憬,以及夏日的夢境.....” 這些組成了村上春樹的世界。那是一種微妙的,無以名之的感受,貼己而朦朧,撩人又莫名。
挪威的森林-小說簡介
1987年村上春樹又以《挪威的森林》為書名寫了一本青春戀愛小說。
這是一部動人心弦的、平緩舒雅的、略帶感傷的、百分之百的戀愛小說。小說主人公渡邊以第一人稱展開他同兩個女孩間的愛情糾葛。渡邊的第一個戀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學木月的女友,後來木月自殺了。一年後渡邊同直子不期而遇並開始交往。此時的直子已變得嫻靜靦腆,美麗晶瑩的眸子裏不時掠過一絲難以捕捉的陰翳。兩人衹是日復一日地在落葉飄零的東京街頭漫無目標地或前或後或並肩行走不止。直子20歲生日的晚上兩人發生了性關係,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嚮。幾個月後直子來信說她住進一傢遠在深山裏的精神療養院。渡邊前去探望時發現直子開始帶有成熟女性的豐腴與嬌美。晚間兩人雖同處一室,但渡邊約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遠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於一次偶然相遇,渡邊開始與低年級的緑子交往。緑子同內嚮的直子截然相反,“簡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來的一頭小鹿”。這期間,渡邊內心十分苦悶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纏綿的病情與柔情,一方面又難以抗拒緑子大膽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傳來直子自殺的噩耗,渡邊失魂魄地四處徒步旅行。最後,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勵下,開始摸索此後的人生。
都說20歲是最好的年華。青蔥歲月裏的驚濤駭浪,也帶着一絲甜蜜的憂傷。我們試圖說清所有的來竜去脈,卻終於在一番掙紮之後發現,當一切都過於清晰、詳盡,反而不知從何說起。幸好有村上春樹,有 Beatles,有——《挪威的森林》。那些平緩舒雅的文字背後,涌動着年輕時代特有的傷感和激情,說出我們一直想說出的話,那些純真年代的——愛的物語
關於青春的記憶,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然而那些歲月裏的感傷、沉醉卻是如此相同,在生命中深深的留下烙印。38歲的渡邊在飛機客艙裏聽到Beatles樂隊的麯子《挪威的森林》時,一下子陷入往事,無法自已。音樂早已了無痕跡的滲入生命,在不設防的時候突然出現,牽動心中微微的疼痛。即使歷經十八年的滄桑,20歲時的風景依然鮮明如昨。渡邊仍可真切地記起那片草地,仍然記得那些塵封已久的往事,那時空氣裏彌漫着青春的芬芳氣息。
渡邊的20歲同大多數人的20歲一樣,上寄宿學校,與三兩個知交一起消磨時光,當然還有,戀愛。日子緩緩地流淌,年輕生命的水流總是新鮮、動蕩的,不時有一些驚心動魄的情節和突如其來的意外。
成長是永遠咀嚼不盡的話題。我們都有相同的體驗——戀愛中的喜悅、甜蜜、憂傷和迷亂,對一切裝模作樣的言行舉止的不滿和嘲笑,難以和外面世界溝通的茫然無措。
我們在渡邊、直子、緑子、木月、永澤、初美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我,看到了你,看到了他,看到了她。在渡邊的睏惑和迷亂中,我們輕觸到一顆纖細易感的心,一如我們自己。
年輕脆弱的心靈有一雙易折的翅膀。直子和木月在自我封閉的“無人島上”長大,想要同化到外部世界中去的努力始終不能成功,最後終究要償還成長的艱辛。木月以自殺的方式解脫,十七歲的生命嘎然停頓;直子在療養院仍然未能治愈自己,也自行中斷了年輕的生命。生與死之間仿佛衹有薄薄的一紙之隔。直子的姐姐和初美雖然是人們眼中出類拔萃的典範,卻也有着難解的心結而走上了不歸路。不同的道路最後卻是殊途同歸。死亡離得如此之近,帶着宿命的悲哀和鉛灰色
的沉重。
然而年輕畢竟是年輕。
渡邊的青春歲月裏仍然風景無限好。除了世外桃源般的療養院裏的直子,仍有一個生動活潑的緑子為他的生活塗上一抹鮮明的色彩。渡邊和緑子在天台上喝酒唱歌,帶着年輕特有的一份悠閑神氣觀望遠處,緑子彈着吉它唱自己寫的歌,歌詞不知所云又生動鮮活。渡邊去醫院探望緑子的父親,嚼着生黃瓜,聲聲脆響中散發着質樸、新鮮的生命力的清香。對於渡邊而言,愛穿短裙、思維跳躍的緑子是他與現實環境相聯繫的媒介,正如當初木月和直子試圖通過他進入外部世界一樣,然而渡邊卻跨過了那道鴻溝。他站在人潮洶涌的大街上,在“哪裏也不是的處所”連連呼喚着緑子。
少年時的渡邊和許多男孩子一樣,有過朦朧的意識和暗暗的念頭。適合穿深藍色連衣裙戴金耳環、風度高貴的初美,對於渡邊是一種從來不曾實現而且永遠不可能實現的憧憬,是少年時代懵懂無知的“自身的一部分”。許許多多似曾相識的片斷從眼前緩緩掠過,帶着溫暖、親切的氣息,喚起心底裏深深的共鳴。
小說以一個個片斷相連接,但並不使人覺得雜亂無章。許許多多日常生活的片斷一一在眼前掠過,喚起熟悉、親切的氣氛,讓人産生心領神會的共鳴。氣氛存在於片斷中,或夾雜在片斷與片斷的留白裏。文字清麗雅緻,筆觸自然流暢,片斷的接續並不妨礙流暢,反而更添加彈性,産生電影畫面的效果。小說中的人物都帶着“都市化”的標識。人物的背景十分簡單,沒有錯綜復雜的人際關係,主人公喜愛的爵士樂麯不斷出現,總是直接引用某個作傢筆下的話語來表達情緒,使得人物平面化、符號化。當渡邊和直子一同在街頭漫無目的地行走,在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群中茫然不知所措,成長的創痛隱隱浮現,身旁洶涌而
過的車流和喧鬧的市聲帶着城市的氣息,周遭全然陌生的人群構成了空曠又擁擠的環境,都市人焦灼、空虛的內心世界,迷亂、脆弱的生存狀態,在作者舉重若輕的敘述背後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Beatles 樂隊的麯子在十八年後依然動人,喚醒了青春的記憶。渡邊細細梳理往事時,感到一陣巨大的悲愴。那份傷感和悲愴源於生命中重要東西的丟失,當時絲毫不曾察覺,意識到這一切時已是多年以後,物是人非。人生的傷感和溫情在字裏行間流淌,讓人和作者一起沉浸在那份情懷之中。成長的艱辛和苦澀是生命中永不褪色的底片,那些熟悉的場景、似曾相識的感受和體驗輕輕撥動心弦,蕩漾起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陣陣震撼心靈的餘音久久回響,如縷不絶。
《挪威的森林》自1987年在日本問世以來,在日本已銷出760餘萬册(1996年統計),這在衹有一億多人口的日本是一個奇跡,平均每十五個日本人就有一人有這本書。在中國的統計數字不一,但常見說法是三百多萬。最近常在上海,有時也去北京出差,看到《挪威的森林》在北京風入鬆、上海書城等著名書店排行榜上,屹立前十名近一年時間,而這股購書熱潮還在如火如荼地高漲着。
書中人物
渡邊---我可是個再普通不過的人。到處有的是。
直子---以前我是這樣活過來的。如今也衹能這樣活下去。
緑子---介於“不充分”和“完全不夠之間吧”。我總是感到饑渴,真想拼着勁兒地得到一次愛......
經典場景
漫步於東京街頭
遇見緑子
午飯後的火災
月光中的裸體
雨中之吻
旅行,直子死了,緑子剩下
呼喚,"我現在哪裏?"
投票
書中提到的
小說:
了不起的蓋茨比
歌麯:
Norwegian Wood
Michelle(米歇爾)
Nowhere Man
Yesterday
爵士樂
作者簡介:
村上春樹,1949年生於日本兵庫縣,早稻田大學戲劇係畢業,1979年以第一部創作小說《聽風的歌》得到當年日本的群像新人奬。獲得野間文藝新人奬和𠔌崎潤一郎奬的作品――《挪 威的森林》――迄今賣了超過700萬本,使作者成為日本最暢銷的作傢。村上春樹曾翻譯F.s cott Fitzgerald,Paul Theroux,John lrving 及Raymond chandler的小說,九十年代 在美國普林頓大學和Tufts University任客座講師。
歌手伍佰也唱了一首叫《挪威的森林》的歌。
挪威的森林
詞麯:吳俊霖
讓我將你心兒摘下
試着將它慢慢溶化
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無瑕
是否依然為我絲絲牽挂
依然愛我無法自拔
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過的地方啊
那裏湖面總是澄清
那裏空氣充滿寧靜
雪白明月照在大地
藏着你不願提起的回憶
(藏着你最深處的秘密)
你說真心總是可以從頭
真愛總是可以長久
為你的眼神還有孤獨時的落寞
是否我衹是你一種寄托
填滿你感情的缺口
心中那片森林何時能讓我停留
或許我 不該問 讓你平靜的心再起漣漪
衹是愛你的心超出了界綫
我想擁有你所有的一切
應該是 我不該問 不該讓你再將往事重提
衹是心中枷鎖 該如何才能解脫
The novel is set in Tokyo during the late 1960s, a time when Japanese students, like those of many other nations, were protesting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order. While it serves as the backdrop against which the events of the novel unfold, Murakami (through the eyes of Toru and Midori) portrays the student movement as largely weak-willed and hypocritical.
Part of the novel was later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ion 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 under the title Firefly.
Norwegian Wood was hugely popular with Japanese youth and made Murakami somewhat of a superstar in his native country (apparently much to his dismay at the time).
Despite its mainstream popularity in Japan, Murakami's established readership saw Norwegian Wood as an unwelcome departure from his by-then established style of energetic prose flavoured with the unexpected and supernatural (as exemplified by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released two years earlier); as translator Jay Rubin observes in the translator's note to the 2000 English edition, Norwegian Wood retains much of the complexity and symbolism characteristic of Murakami's work and is thus "by no means just a love story."
風靡60年代的甲殼蟲樂隊唱出了名聞世界的麯子 Norwegian Wood。“海潮的清香,遙遠的汽笛,女孩肌體的感觸,洗發香波的氣味,傍晚的和風,縹緲的憧憬,以及夏日的夢境.....” 這些組成了村上春樹的世界。那是一種微妙的,無以名之的感受,貼己而朦朧,撩人又莫名。
挪威的森林-小說簡介
1987年村上春樹又以《挪威的森林》為書名寫了一本青春戀愛小說。
這是一部動人心弦的、平緩舒雅的、略帶感傷的、百分之百的戀愛小說。小說主人公渡邊以第一人稱展開他同兩個女孩間的愛情糾葛。渡邊的第一個戀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學木月的女友,後來木月自殺了。一年後渡邊同直子不期而遇並開始交往。此時的直子已變得嫻靜靦腆,美麗晶瑩的眸子裏不時掠過一絲難以捕捉的陰翳。兩人衹是日復一日地在落葉飄零的東京街頭漫無目標地或前或後或並肩行走不止。直子20歲生日的晚上兩人發生了性關係,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嚮。幾個月後直子來信說她住進一傢遠在深山裏的精神療養院。渡邊前去探望時發現直子開始帶有成熟女性的豐腴與嬌美。晚間兩人雖同處一室,但渡邊約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遠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於一次偶然相遇,渡邊開始與低年級的緑子交往。緑子同內嚮的直子截然相反,“簡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來的一頭小鹿”。這期間,渡邊內心十分苦悶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纏綿的病情與柔情,一方面又難以抗拒緑子大膽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傳來直子自殺的噩耗,渡邊失魂魄地四處徒步旅行。最後,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勵下,開始摸索此後的人生。
都說20歲是最好的年華。青蔥歲月裏的驚濤駭浪,也帶着一絲甜蜜的憂傷。我們試圖說清所有的來竜去脈,卻終於在一番掙紮之後發現,當一切都過於清晰、詳盡,反而不知從何說起。幸好有村上春樹,有 Beatles,有——《挪威的森林》。那些平緩舒雅的文字背後,涌動着年輕時代特有的傷感和激情,說出我們一直想說出的話,那些純真年代的——愛的物語
關於青春的記憶,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然而那些歲月裏的感傷、沉醉卻是如此相同,在生命中深深的留下烙印。38歲的渡邊在飛機客艙裏聽到Beatles樂隊的麯子《挪威的森林》時,一下子陷入往事,無法自已。音樂早已了無痕跡的滲入生命,在不設防的時候突然出現,牽動心中微微的疼痛。即使歷經十八年的滄桑,20歲時的風景依然鮮明如昨。渡邊仍可真切地記起那片草地,仍然記得那些塵封已久的往事,那時空氣裏彌漫着青春的芬芳氣息。
渡邊的20歲同大多數人的20歲一樣,上寄宿學校,與三兩個知交一起消磨時光,當然還有,戀愛。日子緩緩地流淌,年輕生命的水流總是新鮮、動蕩的,不時有一些驚心動魄的情節和突如其來的意外。
成長是永遠咀嚼不盡的話題。我們都有相同的體驗——戀愛中的喜悅、甜蜜、憂傷和迷亂,對一切裝模作樣的言行舉止的不滿和嘲笑,難以和外面世界溝通的茫然無措。
我們在渡邊、直子、緑子、木月、永澤、初美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我,看到了你,看到了他,看到了她。在渡邊的睏惑和迷亂中,我們輕觸到一顆纖細易感的心,一如我們自己。
年輕脆弱的心靈有一雙易折的翅膀。直子和木月在自我封閉的“無人島上”長大,想要同化到外部世界中去的努力始終不能成功,最後終究要償還成長的艱辛。木月以自殺的方式解脫,十七歲的生命嘎然停頓;直子在療養院仍然未能治愈自己,也自行中斷了年輕的生命。生與死之間仿佛衹有薄薄的一紙之隔。直子的姐姐和初美雖然是人們眼中出類拔萃的典範,卻也有着難解的心結而走上了不歸路。不同的道路最後卻是殊途同歸。死亡離得如此之近,帶着宿命的悲哀和鉛灰色
的沉重。
然而年輕畢竟是年輕。
渡邊的青春歲月裏仍然風景無限好。除了世外桃源般的療養院裏的直子,仍有一個生動活潑的緑子為他的生活塗上一抹鮮明的色彩。渡邊和緑子在天台上喝酒唱歌,帶着年輕特有的一份悠閑神氣觀望遠處,緑子彈着吉它唱自己寫的歌,歌詞不知所云又生動鮮活。渡邊去醫院探望緑子的父親,嚼着生黃瓜,聲聲脆響中散發着質樸、新鮮的生命力的清香。對於渡邊而言,愛穿短裙、思維跳躍的緑子是他與現實環境相聯繫的媒介,正如當初木月和直子試圖通過他進入外部世界一樣,然而渡邊卻跨過了那道鴻溝。他站在人潮洶涌的大街上,在“哪裏也不是的處所”連連呼喚着緑子。
少年時的渡邊和許多男孩子一樣,有過朦朧的意識和暗暗的念頭。適合穿深藍色連衣裙戴金耳環、風度高貴的初美,對於渡邊是一種從來不曾實現而且永遠不可能實現的憧憬,是少年時代懵懂無知的“自身的一部分”。許許多多似曾相識的片斷從眼前緩緩掠過,帶着溫暖、親切的氣息,喚起心底裏深深的共鳴。
小說以一個個片斷相連接,但並不使人覺得雜亂無章。許許多多日常生活的片斷一一在眼前掠過,喚起熟悉、親切的氣氛,讓人産生心領神會的共鳴。氣氛存在於片斷中,或夾雜在片斷與片斷的留白裏。文字清麗雅緻,筆觸自然流暢,片斷的接續並不妨礙流暢,反而更添加彈性,産生電影畫面的效果。小說中的人物都帶着“都市化”的標識。人物的背景十分簡單,沒有錯綜復雜的人際關係,主人公喜愛的爵士樂麯不斷出現,總是直接引用某個作傢筆下的話語來表達情緒,使得人物平面化、符號化。當渡邊和直子一同在街頭漫無目的地行走,在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群中茫然不知所措,成長的創痛隱隱浮現,身旁洶涌而
過的車流和喧鬧的市聲帶着城市的氣息,周遭全然陌生的人群構成了空曠又擁擠的環境,都市人焦灼、空虛的內心世界,迷亂、脆弱的生存狀態,在作者舉重若輕的敘述背後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Beatles 樂隊的麯子在十八年後依然動人,喚醒了青春的記憶。渡邊細細梳理往事時,感到一陣巨大的悲愴。那份傷感和悲愴源於生命中重要東西的丟失,當時絲毫不曾察覺,意識到這一切時已是多年以後,物是人非。人生的傷感和溫情在字裏行間流淌,讓人和作者一起沉浸在那份情懷之中。成長的艱辛和苦澀是生命中永不褪色的底片,那些熟悉的場景、似曾相識的感受和體驗輕輕撥動心弦,蕩漾起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陣陣震撼心靈的餘音久久回響,如縷不絶。
《挪威的森林》自1987年在日本問世以來,在日本已銷出760餘萬册(1996年統計),這在衹有一億多人口的日本是一個奇跡,平均每十五個日本人就有一人有這本書。在中國的統計數字不一,但常見說法是三百多萬。最近常在上海,有時也去北京出差,看到《挪威的森林》在北京風入鬆、上海書城等著名書店排行榜上,屹立前十名近一年時間,而這股購書熱潮還在如火如荼地高漲着。
書中人物
渡邊---我可是個再普通不過的人。到處有的是。
直子---以前我是這樣活過來的。如今也衹能這樣活下去。
緑子---介於“不充分”和“完全不夠之間吧”。我總是感到饑渴,真想拼着勁兒地得到一次愛......
經典場景
漫步於東京街頭
遇見緑子
午飯後的火災
月光中的裸體
雨中之吻
旅行,直子死了,緑子剩下
呼喚,"我現在哪裏?"
投票
書中提到的
小說:
了不起的蓋茨比
歌麯:
Norwegian Wood
Michelle(米歇爾)
Nowhere Man
Yesterday
爵士樂
作者簡介:
村上春樹,1949年生於日本兵庫縣,早稻田大學戲劇係畢業,1979年以第一部創作小說《聽風的歌》得到當年日本的群像新人奬。獲得野間文藝新人奬和𠔌崎潤一郎奬的作品――《挪 威的森林》――迄今賣了超過700萬本,使作者成為日本最暢銷的作傢。村上春樹曾翻譯F.s cott Fitzgerald,Paul Theroux,John lrving 及Raymond chandler的小說,九十年代 在美國普林頓大學和Tufts University任客座講師。
歌手伍佰也唱了一首叫《挪威的森林》的歌。
挪威的森林
詞麯:吳俊霖
讓我將你心兒摘下
試着將它慢慢溶化
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無瑕
是否依然為我絲絲牽挂
依然愛我無法自拔
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過的地方啊
那裏湖面總是澄清
那裏空氣充滿寧靜
雪白明月照在大地
藏着你不願提起的回憶
(藏着你最深處的秘密)
你說真心總是可以從頭
真愛總是可以長久
為你的眼神還有孤獨時的落寞
是否我衹是你一種寄托
填滿你感情的缺口
心中那片森林何時能讓我停留
或許我 不該問 讓你平靜的心再起漣漪
衹是愛你的心超出了界綫
我想擁有你所有的一切
應該是 我不該問 不該讓你再將往事重提
衹是心中枷鎖 該如何才能解脫
The novel is set in Tokyo during the late 1960s, a time when Japanese students, like those of many other nations, were protesting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order. While it serves as the backdrop against which the events of the novel unfold, Murakami (through the eyes of Toru and Midori) portrays the student movement as largely weak-willed and hypocritical.
Part of the novel was later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ion 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 under the title Firefly.
Norwegian Wood was hugely popular with Japanese youth and made Murakami somewhat of a superstar in his native country (apparently much to his dismay at the time).
Despite its mainstream popularity in Japan, Murakami's established readership saw Norwegian Wood as an unwelcome departure from his by-then established style of energetic prose flavoured with the unexpected and supernatural (as exemplified by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released two years earlier); as translator Jay Rubin observes in the translator's note to the 2000 English edition, Norwegian Wood retains much of the complexity and symbolism characteristic of Murakami's work and is thus "by no means just a love story."
二十二歲那年春天堇有生以來第一次墮入戀情。那是一場以排山倒海之勢掠過無邊草原的竜捲風般迅猛的戀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毀路上一切障礙,又將其接二連三捲上高空……那完全是一種紀念碑式的愛。而愛戀的對象比她年長十七歲,已婚,且同是女性。”這是村上春樹1999年新作《斯普特尼剋戀人》的開頭。小說情境依然那麽孤獨、空虛、無奈、苦悶和悵惘,而作者的筆觸則更神奇地指嚮自己——“自己”究竟是什麽?歸宿在何方?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部自我質疑、自我守望、自我探求的小說,同性戀衹是其藉用的外衣。
Plot summary
The heroine of the novel is an aspiring author named Sumire, who falls in love with an older woman, Miu, who appears to like Sumire for certain qualities, though she has no time for Sumire's aspirations and ideals. The third character is the unnamed narrator,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referred to twice by Sumire only as 'K', who is in love with Sumire, though Sumire does not requite his feelings.
While Sumire is an emotional and spontaneous individual who often appears to be a misfit in society, "K", the narrator, is a person who has through sheer force of will moulded himself into another person, one who integrates seamlessly into the wider society and culture around him, and the transition leaves him emotionally stunted and unable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When Sumire is also, through her interaction with Miu, forcibly shaped into a person other than she is, the transformation is neither permanent nor successful, and Sumire disappears without ever being found or seen again while holidaying with Miu in Greece, with tragic, haunting consequences for Miu in particular.
Themes
Sputnik Sweetheart is essentially a three-character novel. Uncharacteristically slim for a Murakami novel, it is the first novel in which Murakami explores lesbianism in depth, though the principal themes are still familiar ones to the Japanese author's faithful following: the effects of prolonged loneliness and alienation, growing up emotionally stunted in a densely populated and overwhelmingly conformist societ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following one's dreams and clamping down on them in order to assimilate into society.
The book's major themes include loneliness and people's inability to truly know themselves or the people they love. This is symbolized by the recurring metaphor of the Sputnik satellites orbiting at a distance from the earth. As in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and Dance Dance Dance, Murakami uses (or rather, suggests) alternate worlds as a plot device. "K", the narrator, is a markedly different protagonist from those of Murakami's other novels. He is considerably less given to or adept at wisecracks, maintains a respectable and stable profession as a schoolteacher, and is less self-confident and much more introverted and conflicted than any other Murakami protagonist.
Many elements of the plot remain deliberately unresolved, contributing to the idea that true knowledge is elusive, and actual events of the story are obscured in favour of the characters' perceptions.
The book ends with the theme of The Telephone, which appears in numerous books by Murakami, usually when telephoning from a far-away place, whose location is unclear.
In popular culture
The book is mentioned in the movie "Paris, Je T'aime." A passage of the book was also used in channel 4's tv drama Nearly Famous.
Plot summary
The heroine of the novel is an aspiring author named Sumire, who falls in love with an older woman, Miu, who appears to like Sumire for certain qualities, though she has no time for Sumire's aspirations and ideals. The third character is the unnamed narrator,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referred to twice by Sumire only as 'K', who is in love with Sumire, though Sumire does not requite his feelings.
While Sumire is an emotional and spontaneous individual who often appears to be a misfit in society, "K", the narrator, is a person who has through sheer force of will moulded himself into another person, one who integrates seamlessly into the wider society and culture around him, and the transition leaves him emotionally stunted and unable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When Sumire is also, through her interaction with Miu, forcibly shaped into a person other than she is, the transformation is neither permanent nor successful, and Sumire disappears without ever being found or seen again while holidaying with Miu in Greece, with tragic, haunting consequences for Miu in particular.
Themes
Sputnik Sweetheart is essentially a three-character novel. Uncharacteristically slim for a Murakami novel, it is the first novel in which Murakami explores lesbianism in depth, though the principal themes are still familiar ones to the Japanese author's faithful following: the effects of prolonged loneliness and alienation, growing up emotionally stunted in a densely populated and overwhelmingly conformist societ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following one's dreams and clamping down on them in order to assimilate into society.
The book's major themes include loneliness and people's inability to truly know themselves or the people they love. This is symbolized by the recurring metaphor of the Sputnik satellites orbiting at a distance from the earth. As in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and Dance Dance Dance, Murakami uses (or rather, suggests) alternate worlds as a plot device. "K", the narrator, is a markedly different protagonist from those of Murakami's other novels. He is considerably less given to or adept at wisecracks, maintains a respectable and stable profession as a schoolteacher, and is less self-confident and much more introverted and conflicted than any other Murakami protagonist.
Many elements of the plot remain deliberately unresolved, contributing to the idea that true knowledge is elusive, and actual events of the story are obscured in favour of the characters' perceptions.
The book ends with the theme of The Telephone, which appears in numerous books by Murakami, usually when telephoning from a far-away place, whose location is unclear.
In popular culture
The book is mentioned in the movie "Paris, Je T'aime." A passage of the book was also used in channel 4's tv drama Nearly Famous.
《海邊的卡夫卡》的主人公是一位自稱名叫田村卡夫卡——小說始終未交代其真名——的少年。他在十五歲生日前夜獨自離傢出走,乘坐夜行長途巴士遠赴四國。出走的原因是為了逃避父親所作的比俄底浦斯王還要可怕的預言:爾將弒父,將與爾母、爾姐交合。卡夫卡四歲時,母親突然失蹤,帶走了比卡夫卡年長四歲、其實是田村傢養女的姐姐,不知何故卻將親生兒子拋棄。他從未見過母親的照片,甚至連名字也不知道。仿佛是運命在冥冥之中引導,他偶然來到某私立圖書館,遂棲身於此。館長佐伯女士是位四十多歲氣質高雅的美婦,有着波瀾麯折的神秘身世。卡夫卡疑心她是自己的生母,佐伯卻對此不置可否。卡夫卡戀上了佐伯,並與之發生肉體關係。小說還另設一條副綫,副綫的主角是老人中田,他在二戰期間讀小學時,經歷過一次神秘的昏迷事件,從此喪失了記憶,將學過的知識完全忘記,甚至不會認字計數,卻獲得了與貓對話的神秘能力。中田在神智失控的情況下殺死了一個自稱焦尼·沃卡(Johnny Walker)、打扮得酷似那著名威士忌酒商標上所畫的英國紳士的狂人,一路搭車也來到此地。小說共分49章,奇數章基本上用寫實手法講述卡夫卡的故事,偶數章則用魔幻手法展現中田的奇遇。兩種手法交互使用,編織出極富強烈虛構色彩的、奇幻詭詰的現代寓言。佐伯是將這兩個故事聯結為一體的結合點,而弒父的預言似乎最終也未能避免,因為狂人焦尼·沃卡居然是卡夫卡生父喬裝改扮的,真正的兇手也並非中田……
Plot summary
Comprising two distinct but interrelated plots, the narrative run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taking up each plotline in alternating chapters.
The odd chapters tell the 15 year old Kafka's story as he runs away from his father's house to escape an Oedipal curse and to embark upon a quest to find his mother and sister. After a series of adventures, he finds shelter in a quiet, private library in Takamatsu, run by the distant and aloof Miss Saeki and the androgynous Oshima. There he spends his days reading the unabridged Richard Francis Burton translation of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a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Natsume Sōseki until the police begin inquiring after him in connection with a brutal murder.
The even chapters tell Nakata's story. Due to his uncanny abilities, he has found part-time work in his old age as a finder of lost cats (a clear reference to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The case of one particular lost cat puts him on a path that ultimately takes him far away from his home, ending up on the road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He befriends a truck-driver named Hoshino. Hoshino takes him on as a passenger in his truck and soon becomes very attached to the old man.
Nakata and Kafka a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throughout the novel, but their convergence takes place as much on a metaphysical plane as it does in reality and, in fact, that can be said of the novel itself. Due to the Oedipal theme running through much of the novel, Kafka on the Shore has been called a modern Greek tragedy.
Major themes
Kafka on the Shore demonstrates Murakami's typical blend of popular culture, quotidian detail, magical realism, suspense, humor, an involved and at times confusing plot, and potent sexuality. It also features an increased emphasis on Japanese religious traditions, particularly Shinto.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significant departures from the typical protagonist of a Murakami novel, such as Toru Watanabe of Norwegian Wood and Toru Okada of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who are typically in their 20s or 30s and have rather humdrum personalities. However, many of the same themes re-occur in Kafka on the Shore as were first developed in these and other previous novels.
The power and beauty of music as a communicative medium is a central theme of the novel—the very title comes from a pop song Kafka is given on a record in the library. The music of Beethoven, specifically the Archduke Trio is also used as a redemptive metaphor. Among other prominent themes are: the virtues of self-sufficiency and efficiency, the relation of dreams and reality, the specter of the heritage of World War II, the threat of fate, the uncertain grip of prophecy, and the power of nature.
G. W. F. Hegel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book and is referenced directly at one point. Dialectics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in particular play a role.
Characters
Humans
* Kafka Tamura: Clearly named in honor of the Czech writer Franz Kafka, Kafka is a "cool, tall, fifteen-year-old boy lugging a backpack and a bunch of obsessions" and the son of the famous sculptor Koichi Tamura. His mother and sister left the family almost before he became conscious of them. He occasionally interacts with a hectoring, exhortative alter ego "The boy named Crow" (as told in the story, although jackdaw is closer to Czech meaning). Crow tells himself throughout the novel that he must be "the toughest fifteen-year-old in the world."
* Satoru Nakata: Nakata lost many of his mental faculties when, as one of sixteen schoolchildren out on a mushroom-gathering field-trip towar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e was rendered unconscious following a mysterious flash of light in the sky . Unlike the other children, who lost consciousness briefly, Nakata remained unconscious for many weeks, and, upon finally awakening, found that his memory and his ability to read had disappeared, as well as his higher intellectual functions. In their place, Nakata found he was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cats. Nakata and Kafka may also b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person.
* Oshima: A 21-year-old, gay female-to-male transsexual. He is a librarian and an owner of a mountain retreat who becomes close to Kafka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novel; also a haemophiliac.
* Hoshino: A truck driver in his mid-twenties. He befriends Nakata, due to his resemblance to his own grandfather, and transports and assists Nakata towards his uncertain goal.
* Miss Saeki: The manager of a private library, where Oshima works and where Kafka lives through much of the novel. She was previously a singer, and performed the song "Kafka on the Shore", which unites many of the novel's themes and gives it its title. She may also be Kafka's mother.
* Sakura: A young woman Kafka meets on the bus who helps him later on. She may be his sister.
* Johnnie Walker: A cat killer who plans to make a flute out of cats' souls. He may also be Kafka's father, the renowned sculptor Koichi Tamura. His name is taken from Johnnie Walker, a brand of Scotch whisky, and he dresses to appear like the man featured in the brand's logo.
* Colonel Sanders: A "concept" who takes the form of a pimp or hustler. He is named after, and appears similar to, Harland Sanders, the founder and face of Kentucky Fried Chicken.
Cats
* Goma: A lost cat owned by Mrs. Koizumi.
* Kawamura: A cat who was addled after being hit by a bicycle. Though they can communicate, Nakata is unable to understand Kawamura's repetitive and strange sentences.
* Mimi: An intelligent Siamese cat.
* Okawa: A tabby cat.
* Toro: A black cat.
Understanding the novel
After the novel's release, Murakami's Japanese publisher set up a website allowing readers to submit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8,000 questions were received and Murakami responded personally to about 1,200 of them. In an interview posted on his English language website, Murakami states that the secret to understanding the novel lies in reading it multiple times: "Kafka on the Shore contains several riddles, but there aren't any solutions provided. Instead, several of these riddles combine, and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the possibility of a solution takes shape. And the form this solution takes will be different for each reader. To put it another way, the riddles function as part of the solution. It's hard to explain, but that's the kind of novel I set out to write".
Plot summary
Comprising two distinct but interrelated plots, the narrative run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taking up each plotline in alternating chapters.
The odd chapters tell the 15 year old Kafka's story as he runs away from his father's house to escape an Oedipal curse and to embark upon a quest to find his mother and sister. After a series of adventures, he finds shelter in a quiet, private library in Takamatsu, run by the distant and aloof Miss Saeki and the androgynous Oshima. There he spends his days reading the unabridged Richard Francis Burton translation of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a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Natsume Sōseki until the police begin inquiring after him in connection with a brutal murder.
The even chapters tell Nakata's story. Due to his uncanny abilities, he has found part-time work in his old age as a finder of lost cats (a clear reference to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The case of one particular lost cat puts him on a path that ultimately takes him far away from his home, ending up on the road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He befriends a truck-driver named Hoshino. Hoshino takes him on as a passenger in his truck and soon becomes very attached to the old man.
Nakata and Kafka a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throughout the novel, but their convergence takes place as much on a metaphysical plane as it does in reality and, in fact, that can be said of the novel itself. Due to the Oedipal theme running through much of the novel, Kafka on the Shore has been called a modern Greek tragedy.
Major themes
Kafka on the Shore demonstrates Murakami's typical blend of popular culture, quotidian detail, magical realism, suspense, humor, an involved and at times confusing plot, and potent sexuality. It also features an increased emphasis on Japanese religious traditions, particularly Shinto.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significant departures from the typical protagonist of a Murakami novel, such as Toru Watanabe of Norwegian Wood and Toru Okada of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who are typically in their 20s or 30s and have rather humdrum personalities. However, many of the same themes re-occur in Kafka on the Shore as were first developed in these and other previous novels.
The power and beauty of music as a communicative medium is a central theme of the novel—the very title comes from a pop song Kafka is given on a record in the library. The music of Beethoven, specifically the Archduke Trio is also used as a redemptive metaphor. Among other prominent themes are: the virtues of self-sufficiency and efficiency, the relation of dreams and reality, the specter of the heritage of World War II, the threat of fate, the uncertain grip of prophecy, and the power of nature.
G. W. F. Hegel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book and is referenced directly at one point. Dialectics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in particular play a role.
Characters
Humans
* Kafka Tamura: Clearly named in honor of the Czech writer Franz Kafka, Kafka is a "cool, tall, fifteen-year-old boy lugging a backpack and a bunch of obsessions" and the son of the famous sculptor Koichi Tamura. His mother and sister left the family almost before he became conscious of them. He occasionally interacts with a hectoring, exhortative alter ego "The boy named Crow" (as told in the story, although jackdaw is closer to Czech meaning). Crow tells himself throughout the novel that he must be "the toughest fifteen-year-old in the world."
* Satoru Nakata: Nakata lost many of his mental faculties when, as one of sixteen schoolchildren out on a mushroom-gathering field-trip towar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e was rendered unconscious following a mysterious flash of light in the sky . Unlike the other children, who lost consciousness briefly, Nakata remained unconscious for many weeks, and, upon finally awakening, found that his memory and his ability to read had disappeared, as well as his higher intellectual functions. In their place, Nakata found he was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cats. Nakata and Kafka may also b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person.
* Oshima: A 21-year-old, gay female-to-male transsexual. He is a librarian and an owner of a mountain retreat who becomes close to Kafka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novel; also a haemophiliac.
* Hoshino: A truck driver in his mid-twenties. He befriends Nakata, due to his resemblance to his own grandfather, and transports and assists Nakata towards his uncertain goal.
* Miss Saeki: The manager of a private library, where Oshima works and where Kafka lives through much of the novel. She was previously a singer, and performed the song "Kafka on the Shore", which unites many of the novel's themes and gives it its title. She may also be Kafka's mother.
* Sakura: A young woman Kafka meets on the bus who helps him later on. She may be his sister.
* Johnnie Walker: A cat killer who plans to make a flute out of cats' souls. He may also be Kafka's father, the renowned sculptor Koichi Tamura. His name is taken from Johnnie Walker, a brand of Scotch whisky, and he dresses to appear like the man featured in the brand's logo.
* Colonel Sanders: A "concept" who takes the form of a pimp or hustler. He is named after, and appears similar to, Harland Sanders, the founder and face of Kentucky Fried Chicken.
Cats
* Goma: A lost cat owned by Mrs. Koizumi.
* Kawamura: A cat who was addled after being hit by a bicycle. Though they can communicate, Nakata is unable to understand Kawamura's repetitive and strange sentences.
* Mimi: An intelligent Siamese cat.
* Okawa: A tabby cat.
* Toro: A black cat.
Understanding the novel
After the novel's release, Murakami's Japanese publisher set up a website allowing readers to submit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8,000 questions were received and Murakami responded personally to about 1,200 of them. In an interview posted on his English language website, Murakami states that the secret to understanding the novel lies in reading it multiple times: "Kafka on the Shore contains several riddles, but there aren't any solutions provided. Instead, several of these riddles combine, and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the possibility of a solution takes shape. And the form this solution takes will be different for each reader. To put it another way, the riddles function as part of the solution. It's hard to explain, but that's the kind of novel I set out to write".
本書是村上春樹緊接於《挪威的森林》之後發表的又一部重要長篇小說。其內容與《尋羊冒險記》相銜接,主人公“我”與《尋羊冒險記》中的主人公是同一個人。小說分兩條綫索,一條是“我”與老同學、電影明星五反田結識了兩名應召女郎,五反田出於心理扭麯殺死了她們,自己也投海自殺。另一條是“我”結識了孤單的女孩“雪”、她的攝影傢母親 “雨”與“雨”的男友笛剋,但善良的笛剋卻死於車禍。“我”在死亡陰影下過了一段驚魂的日子,最後與一個賓館女服務員相戀並獲得了安全感。
小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性對人的心靈的扭麯以及這種社會下人的精神孤獨和生命的脆弱,在手法上現實與虛幻交織,藝術水準高超。
Dance Dance Dance (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 Dansu dansu dansu?) is the sixth novel by Japanese writer Haruki Murakami. First published in 1988,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lfred Birnbaum was released in 1994. The book is a sequel to Murakami's novel A Wild Sheep Chase, although the plot lines are not entirely contiguous. In 2001, Murakami said that writing Dance Dance Dance had been a healing act after his unexpected fame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Norwegian Wood and that, because of this, he had enjoyed writing Dance more than any other novel.
Plot summary
The novel follows the surreal misadventures of an unnamed protagonist who makes a living as a commercial writer. The protagonist is compelled to return to the Dolphin Hotel, a seedy establishment where he once spent the night with a woman he loved, despite the fact he never even knew her real name. She has since disappeared without a trace, the Dolphin Hotel has been purchased by a large corporation and converted into a slick, fashionable, western-style hotel.
The protagonist begins experiencing dreams in which this woman and the Sheep Man — a strange individual dressed in an old sheep skin who speaks in a monotonous rush — appear to him and lead him to uncover two mysteries. The first is metaphysical in nature, viz. how to survive the unsurvivable. The second is the murder of a call-girl in which an old school friend of the protagonist, now a famous film actor, is a prime suspect. Along the way, the protagonist meets a clairvoyant and troubled 13-year-old girl, her equally troubled parents, a one-armed poet, and a sympathetic receptionist.
Major themes
Several of the novel's themes are hallmarks of Murakami's writing. Dance Dance Dance deals with themes of loss and abandonment, as do many of Murakami's other novels. Often, the male protagonist in a Murakami novel will lose a mother, spouse, or girlfriend. Other common Murakami themes this novel includes are alienation, absurdity and the ultimate discovery of a human connection.
There is a character in the story named Hiraku Makimura, which is an anagram of "Haruki Murakami." Makimura of the novel is also a best selling author.
Differenc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supernatural character known as the Sheep Man speaks differently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character speaks normal Japanese in the original work, but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his speech is written without any spaces between words.
小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性對人的心靈的扭麯以及這種社會下人的精神孤獨和生命的脆弱,在手法上現實與虛幻交織,藝術水準高超。
Dance Dance Dance (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 Dansu dansu dansu?) is the sixth novel by Japanese writer Haruki Murakami. First published in 1988,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lfred Birnbaum was released in 1994. The book is a sequel to Murakami's novel A Wild Sheep Chase, although the plot lines are not entirely contiguous. In 2001, Murakami said that writing Dance Dance Dance had been a healing act after his unexpected fame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Norwegian Wood and that, because of this, he had enjoyed writing Dance more than any other novel.
Plot summary
The novel follows the surreal misadventures of an unnamed protagonist who makes a living as a commercial writer. The protagonist is compelled to return to the Dolphin Hotel, a seedy establishment where he once spent the night with a woman he loved, despite the fact he never even knew her real name. She has since disappeared without a trace, the Dolphin Hotel has been purchased by a large corporation and converted into a slick, fashionable, western-style hotel.
The protagonist begins experiencing dreams in which this woman and the Sheep Man — a strange individual dressed in an old sheep skin who speaks in a monotonous rush — appear to him and lead him to uncover two mysteries. The first is metaphysical in nature, viz. how to survive the unsurvivable. The second is the murder of a call-girl in which an old school friend of the protagonist, now a famous film actor, is a prime suspect. Along the way, the protagonist meets a clairvoyant and troubled 13-year-old girl, her equally troubled parents, a one-armed poet, and a sympathetic receptionist.
Major themes
Several of the novel's themes are hallmarks of Murakami's writing. Dance Dance Dance deals with themes of loss and abandonment, as do many of Murakami's other novels. Often, the male protagonist in a Murakami novel will lose a mother, spouse, or girlfriend. Other common Murakami themes this novel includes are alienation, absurdity and the ultimate discovery of a human connection.
There is a character in the story named Hiraku Makimura, which is an anagram of "Haruki Murakami." Makimura of the novel is also a best selling author.
Differenc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supernatural character known as the Sheep Man speaks differently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character speaks normal Japanese in the original work, but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his speech is written without any spaces between words.
羅馬帝國的崩潰 舞!舞!舞! 看袋鼠的好日子 五月的海岸綫
傢務事 沒落的王國 唐古麗燒餅的盛衰 出擊面包店
雙胞胎與沉默的陸地 雪梨的緑街 冰男 百分百女孩
僵屍 紐約炭礦的悲劇 窗 盲柳與睡女
獵刀 飛機 圖書館奇談 南灣行
開往中國的慢船 意大利粉之年 計程車上的吸血鬼 1973年的彈子球
象的失蹤 羊男的聖誕節 蝸牛
傢務事 沒落的王國 唐古麗燒餅的盛衰 出擊面包店
雙胞胎與沉默的陸地 雪梨的緑街 冰男 百分百女孩
僵屍 紐約炭礦的悲劇 窗 盲柳與睡女
獵刀 飛機 圖書館奇談 南灣行
開往中國的慢船 意大利粉之年 計程車上的吸血鬼 1973年的彈子球
象的失蹤 羊男的聖誕節 蝸牛
藍小說係列
冰男
我和冰男結婚了。我是在某個滑雪場的飯店遇到冰男的。這或許應該說是認識冰男的絶佳地方吧。在許多年輕人擠來擠去非常熱鬧的飯店門廳,坐在離壁爐最遠角落的椅子上,冰男獨自一個人正安靜地看書。雖然已經接近正午時分了,但我覺得鼕天早晨清冷鮮明的光綫獨獨還留在他周圍似的。“嘿,那個人是冰男偌。”我的朋友小聲地告訴我。但那時候所謂的冰男到底是什麽樣的東西我還完全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太知道。衹知道他叫做冰男這回事而已。“一定是用冰做成的。所以叫做冰男哪。”她一本正經地對我說。好象在談幽靈或傳染病患者似的。
冰男個子高高的,頭髮顯得很硬的樣子。從容貌看來好象還很年輕,但那粗粗硬硬鐵絲般的頭髮裏卻隨處混雜着像融剩的殘雪般的白發。顴骨像冰凍的岩石般有棱有角,手指上結了一層永不融化的白霜,但除了這些之外,冰男的外表和一般男人沒有兩樣。或許說不上英俊,但以不同觀點來看時,到也相當有魅力。擁有某種尖銳得刺中人心的東西。尤其是他的眼睛,會讓人這樣的感覺。簡直像鼕天早晨的冰柱般閃耀着寡默而透明的眼神。那是在湊合而成的肉體之中,唯一看得到像真實生命的光輝。我在那裏伫立一會兒,遠遠地望着冰男。但冰男一次也沒擡起頭來。他身體動也不動地一直繼續看著書。簡直像在對自己說身邊沒有任何人在似的。
第二天下午冰男還是在同一個地方同樣地看著書。我到餐廳去吃中飯時,和傍晚前跟大傢滑雪回來時,他都還坐在和前一天同一張椅子上,以同樣的眼神投註在同一本書的書頁上。而且接下來的一天也一樣。天黑之後,夜深之後,他還像窗外的鼕天一樣安靜地坐在那裏,一個人獨自看著書。
第四天下午,我隨便找一個藉口沒去滑雪場。我一個人留在飯店,在門廳徘徊了一會兒。人們都已經出去滑雪了,門廳像被遺棄的街道般空蕩蕩的。門廳的空氣過於溫暖潮濕,混合着奇怪的鬱悶氣味。那是黏在人們靴底運進飯店裏來的,並無意間在暖爐前面咕滋咕滋地融化掉的雪的氣味。我從不同的窗戶嚮外張望,隨手翻一翻報紙。然後走到冰男的旁邊,幹脆鼓起勇氣跟他說話。我說起來算是怕生的人,除非真正有事否則是不會和不認識的人說話的。但那時候我無論如何都想跟冰男說話。那是我住在那傢飯店的最後一夜,如果放過這次機會的話,我想可能再也沒什麽機會能和冰男說話了。
你不滑雪嗎?我盡可能以不經意的聲音問冰男。他慢慢擡起頭來。一副好象聽見很遠地方的風聲似的表情。他以那樣的眼神盯着我看。然後靜靜地搖頭。我不滑雪。衹要這樣一面賞雪一面看書就好了,他說。他的話像漫畫對白的方框一樣在空中化為白雲。我名副其實真的可以憑自己的眼睛看到他說的話。他輕輕摩擦浮在手指上的霜並拂掉。
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些什麽纔好。我臉紅起來,一直靜靜地站在那裏。冰男看着我的眼睛。看得出他似乎極輕微地笑了一下。不過我不太清楚。冰男真的微笑了嗎?或者衹是我這樣覺得而已。你要不要坐下來?冰男說。我們談一談吧。你是不是對我感興趣?想知道所謂的冰男是什麽樣的東西吧?然後他衹輕輕笑了一下。沒關係,你不用擔心。跟我談話是不會感冒的。
就這樣我跟冰男談起話來。我們在門廳角落的沙發上並排坐下,一面眺望窗外飛舞的雪花一面小心客氣地談着。我點了熱可可喝。冰男什麽也沒喝。冰男好象也不比我強,跟我一樣不太擅長說話的樣子。而且我們又沒有共通的話題。我們首先談了天氣。然後談到飯店住得舒不舒服。你是一個人到這裏來的嗎?我問冰男。是啊,冰男回答。冰男問我喜歡滑雪嗎?我回答不怎麽喜歡。我說因為我的朋友們一直邀我一定要一起來所以我纔來的,其實我幾乎不會滑。我非常想知道所謂冰男是怎麽樣的?身體真的是用冰做的嗎?平常都吃些什麽東西?夏天在什麽地方生活?有沒有傢人這一類的事。但冰男並不主動談自己。我也不敢問。我想冰男可能不太想談這種事吧。
代替的是,冰男談到我。真是難以相信,但冰男不知道為什麽對我的事竟然知道得非常詳細。比方我的家庭成員、我的年齡、我的健康狀況、我讀的學校、我所交的朋友等,他無所不知。連我早已忘掉的老早以前的事,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真不明白,我臉紅地說。我覺得自己好象在別人面前脫光了衣服似的。為什麽你這麽清楚我的事呢?我問。你能讀別人的心嗎?
不,我無法讀別人的心。不過我知道,就是知道,冰男說。就像一直註視冰的深處一樣。這樣一直盯着你看時,就可以清楚地看見你的事情。
可以看見我的未來嗎?我試着問。
未來看不見,冰男面無表情地說。並且慢慢地搖頭。我對未來這東西完全不感興趣。正確地說,我沒有所謂未來這個概念。因為冰是沒有未來這東西的。這裏衹有過去被牢牢地封在裏面而已。一切的東西簡直就像活生生鮮明地被封在冰裏面。冰這東西是可以把各種東西這樣子保存起來的。非常清潔、非常清晰。原樣不變地。這是所謂冰的任務,也是本質。
太好了,我說。並微微一笑。我聽了之後放下心來。因為我纔不想知道自己的未來呢。
我們回東京之後又見了幾次面,終於變成每逢周末都約會了。但我們既不去看電影,也不去喝咖啡,連飯都不吃。因為冰男幾乎是不吃所謂食物這東西的。我們兩人每次都在公園長椅坐下來,談各種事情。我們真的談很多話。但冰男老是不談自己。為什麽呢?我試着問他。為什麽你不談自己的事呢?我想知道你多一些,你生在什麽地方?雙親是什麽樣的人?經過什麽樣的過程纔變成冰男的?冰男看了一會兒我的臉。然後慢慢地搖頭。我不知道啊。冰男安靜地以凜然的聲音說。並且朝空中吐出僵硬的白氣。我沒有所謂的過去。我知道所有的過去,保存一切的過去。但我自己卻沒有所謂的過去。我既不知道自己生在哪裏,也不知道雙親的容貌。連是不是有雙親都不知道。連自己的年齡也不知道。連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年齡都不知道。
冰男彷佛黑暗中的冰山般孤獨。
而我則認真地愛上這樣的冰男。冰男不管過去不管未來,衹愛着現在的這個我。而我也愛着沒有過去沒有未來衹有現在的這個冰男。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美妙。而且我們甚至開始談到結婚了。我剛剛滿二十歲。而冰男則是我有生以來認真喜歡的第一個對象。所謂愛冰男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麽?當時我連想都沒想到。不過假定就算對象不是冰男,我想我還是一樣會什麽都不知道吧。
母親和姊姊強烈反對我和冰男結婚。你結婚還太年輕,她們說。首先連對方正確的本性都不知道對嗎?你不是連他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生的都不知道嗎?我們實在對親戚說不出口,說你居然要和這樣的對象結婚。而且你呀,對方是冰男,萬一融化了你怎麽辦呢?她們說。你大概不明白,所謂結婚是必須確實負責的喲。冰男到底會不會負起做丈夫的責任呢?
不過不必擔心這些。冰男並不是用冰做成的。冰男衹是像冰一樣冷而已。所以如果身旁變溫暖了,也不會因此而融化。那冷確實像冰。但那肉體和冰不同。雖然確實很冷,但卻不是奪取別人體溫的那種冷。於是我們結婚了。那是沒有人祝福的婚姻。朋友、父母親、姊妹,誰都沒有為我們的結婚而高興。連結婚典禮也沒有舉行。要辦戶籍,冰男連戶籍也沒有。衹有我們兩個人,决定自己已經結婚了而已。我們買了一個小蛋糕,兩個人把它吃了。那就是我們小小的婚禮。我們租了一間小公寓,冰男為了生活而到保管儲存牛肉的冷凍庫去工作。無論如何他總是比較耐得住寒冷的,不管怎樣勞動都不會感覺疲倦。連食物都不太吃。所以雇主非常喜歡冰男。而且給它比別人優厚的酬勞。沒有人防礙我們,我們也不妨礙任何人,衹有兩個人靜悄悄地過着幸福的日子。
冰男擁抱我時,我會想到某個地方應該靜悄悄地存在着的冰塊。我想冰男大概知道那冰塊存在的地方吧。堅硬的,凍得無比堅硬的冰。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冰塊。但那卻在某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他將那冰的記憶傳達給這個世界。剛開始,冰男擁抱我時,我還感覺猶豫。但不久後我就習慣了。我甚至變得愛被他抱了。他依然完全不談自己的事。也不提他為什麽會變成冰男的。我也什麽都沒問。我們在黑暗中互相擁抱,沉默地共有那巨大的冰。那冰中依然清潔地封存着長達幾億年的全世界所有的過去。
我們的婚姻生活沒有什麽成問題的問題。我們深深相愛着,也沒有什麽妨礙我們的東西。周圍的人似乎不太適應冰男的存在,但隨着時間過去,他們也逐漸開始跟冰男說起話來了。他們開始說,其實所謂的冰男跟普通人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啊。不過當然他們心底下並沒有接受冰男,同樣的也沒有接受和他結婚的我。我們和他們是不同種類的人,不管時間經過多久,那鴻溝都無法填平。
我們之間老是生不出小孩。也許人和冰男之間遺傳因子或什麽很難結合也未可知。但不管怎麽樣,也許沒有小孩也有關係,不久之後我的時間就變得太多而難以打發了。早晨我手腳俐落地把傢事做完之後,就在也沒有其它事可做了。我既沒有可以聊天,或一起出去的朋友,也沒有交往的鄰居。我母親和姊妹因為我和冰男結婚還在生我的氣,不跟我說話。她們認為我是全家的羞恥。我連打電話的對象都沒有。冰男去倉庫做工時,我一直一個人在傢,看看書聽聽音樂。以我的個性來說說與其出去外面,不如比較喜歡留在傢裏,一個人獨處也不覺得特別的難過。不過話雖這麽說,但我畢竟還年輕,那種沒有任何變化的日子每天重複過下去終於也開始覺得痛苦了。令我覺得痛苦的不是無聊。我所不能忍受的是那重複性。在那重複之中,我開始覺得連自己都像被重複的影子一樣了。
於是有一天我對丈夫提議。為了轉換心情兩個人到什麽地方去旅行好嗎?旅行?冰男說。他瞇細了眼睛看我。到底為什麽要去旅行呢?你跟我一起住在這裏不快樂嗎?
不是這樣,我說。我很快樂啊。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問題喲。不過,我很無聊。想到遙遠的地方去,看一看沒看過的東西。吸吸看沒吸過的空氣。你瞭解嗎?而且我們也沒有去過蜜月旅行。我們已經有了儲蓄,而且還有很多休假沒用掉。是應該可以去悠閑旅行的時候了。
冰男深深地嘆了一口像要凍僵的氣。嘆息在空中喀啷一聲變成冰的結晶。他結了霜的修長手指交握在膝上。說的也是,如果你那麽想去旅行的話,我並不反對。雖然我並不覺得旅行是那麽好的事,但衹要你能覺得快樂的話,我做什麽都行,到哪裏都可以。我想冷凍倉庫的工作衹要想休息就可以休息。因為到現在為止一直那樣拼命努力地工作。我想沒有任何問題。不過你想去什麽地方呢?比方說?南極怎麽樣?我說。我選擇南極,是想如果是寒冷的地方冰男大概會有興趣吧。而且老實說,從很久以前我就很想去一次南極看看的。我想看看極光,也想看看企鵝。我想象自己穿著有帽子的毛皮大衣,在極光下,和成群的企鵝玩耍的情景。
我這樣說時,丈夫冰男便一直註視着我的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眼地一直盯着我。就像尖銳的冰柱一樣,穿透我的眼睛直通到腦後去。他沉默地沉思一會兒。終於以僵僵硬硬的聲音說好啊。好啊,如果你這樣希望的話,我們就去南極吧。你真的覺得這樣好嗎?
我點頭。
我想兩星期後我也可以請長假了。在那期間旅行的準備應該來得及吧。這樣真的沒關係嗎?
但我無法立刻回答。因為冰男那冰冷的視綫實在凝視我太久太緊了,使我的頭腦變得冰冷麻痹。
但隨着時間的過去,我開始後悔不該嚮丈夫提出南極之行。不知道為什麽。我覺得自從我口中說出“南極”這字眼以來,丈夫心中好象已經起了什麽變化。丈夫的眼睛比以前變得更像冰柱般尖銳,丈夫的吐氣比以前變得更白,丈夫的手指比以前結了更厚的霜。他好象變得比以前更沉默寡言,更頑固了似的。他現在已經變成完全不吃任何東西了。這使我非常不安。出發旅行的前五天,我鼓起勇氣試着嚮丈夫提議。還是別去南極好嗎?我說。想一想南極畢竟太冷,也許對身體不好。我覺得還是去普通一點的地方比較好。去歐洲好嗎?到西班牙一帶放輕鬆吧。喝喝葡萄酒,吃吃西班牙海鮮飯,看看鬥牛。但丈夫不答應。他註視着遠方一會兒。然後看着我的臉。深深註視我的眼睛。那視綫實在太深了,甚至讓我覺得自己的肉體好象就要那樣消失掉了似的。不,我並不想去西班牙,丈夫冰男斷然地說。雖然覺得抱歉,但西班牙對我來說太熱了,灰塵太多了。食物也太辣。而且我已經買好兩人份到南極去的機票。也為你買了毛皮大衣,附有毛皮的靴子。這一切不能白白浪費呀。事到如今已經不能不去了。
老實說我很害怕。我預感去到南極我們身上可能會發生無法輓回的事。我做了好幾次又好幾次的惡夢。每次都是同樣的夢。我正在散步,卻掉進地面洞開的深穴裏去,沒有人發現,就那樣凍僵了。我被封閉在冰中,一直望着空中。我有意識。但一根手指都動彈不得。那種感覺非常奇怪。知道自己正一刻一刻地化為過去。我沒有所謂未來。衹有過去不斷地纍積重疊下去而已。而且大傢都在註視着這樣的我。他們在看着過去。我是朝嚮後方繼續過去的光景。
然後我醒來。冰男睡在我旁邊。他不發一聲鼻息地睡着。簡直像死掉冰凍的似的。但我愛着冰男。我哭了。我的眼淚滴落在他臉頰上。於是他醒過來擁抱我的身體。我做惡夢了,我說。他在黑暗中慢慢地搖頭。那衹是夢啊,他說。夢是從過去來的東西。不是從未來來的。那不會束縛你。是你束縛着夢,明白嗎?嗯,我說。但我沒有確實的信心。
結果我和丈夫終於上了往南極的飛機。因為無論如何都找不到取消旅行的理由。往南極飛機的飛行員和空中小姐全都話非常少。我想看窗外的光景,但雲層很厚什麽都看不見。不久之後窗子上便結了一層厚厚的冰。丈夫在這期間一直默默地看著書。我心中並沒有現在要去旅行的興奮和喜悅。衹是在做着一旦决定的事衹好確實去做而已。
從飛機扶梯下來,腳接觸到南極的大地時,我感覺到丈夫的身體巨大地搖晃一下。那比一瞬間還短,衹有一瞬間的一半左右,因此沒有任何人註意到。丈夫的臉絲毫沒露出一點變化,但我卻沒有看漏。丈夫體內,有什麽強烈而安靜的搖晃。我一直註視着丈夫的側臉。他在那裏站定下來,眺望天空,望望自己的手,並大口吐着氣。然後看着我的臉,微笑起來。這就是你所期望的土地嗎?他說。是啊,我說。
雖然早有某種程度的預料,但南極卻是個超越一切預想的寂寞土地。那裏幾乎沒有什麽人住。衹有唯一的一個沒有特徵的小村子。村子裏也同樣的衹有一傢沒有特徵的小飯店。南極並不是觀光地。那裏甚至連企鵝的影子都沒有。連極光都看不見。我偶爾試着問路過的人,要到什麽地方纔能看見企鵝。但人們衹是沉默地搖頭而已。他們無法理解我的語言。因此我試着在紙上畫出企鵝的畫。即使這樣他們還是沉默地搖頭而已。我好孤獨。走出村外一步,除了冰就沒有別的了。既沒有書、沒有花、沒有河,也沒有水池。到任何地方,都衹有冰而已。一望無際永無止境,所到之處盡是冰之荒野的無限延伸。
然而丈夫一面口吐着白氣,手指結着霜,以冰柱般的眼睛凝視着遠方,一面毫不厭倦精力充沛地從各種地方走到各種地方。而且立刻記住各種語言,和村子裏的人們以冰般堅硬的聲響互相對話。他們以認真的表情一連交談好幾小時。但我完全無法理解他們到底在那樣熱心地談着什麽。丈夫完全着迷於這個地方了。這裏有吸引丈夫的什麽存在着。剛開始我覺得非常生氣。感覺好象衹有我一個人被遺棄了似的。我感覺好象被丈夫背叛了,忽視了似的。
於是,我終於在被厚冰團團圍繞的沉默世界裏,喪失了一切的力氣。一點一點逐漸地。而且終於連生氣的力氣也喪失了。我感覺的羅盤針般的東西似乎已經遺失在什麽地方。我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時間,失去了自己存在的重量。我不知道這是什麽時候開始什麽時候結束的。但一留神時,我已經一個人無感覺地被封閉在冰的世界中,在喪失所謂色彩的永遠鼕季中了。即使在喪失絶大部份的感覺之後,衹有一點我很清楚。在南極的這個我的丈夫已經不是以前我的丈夫了。並不是說有什麽地方不同。他和過去一樣依然很體貼我,對我溫柔地說話。而且我也很明白那是發自他真心的話。不過我還是知道。冰男已經和我在滑雪場的飯店所遇見的那個冰男不一樣了。但我卻無法嚮誰投訴這件事。南極的人都對他懷有好感,而我說的話他們一句也聽不懂。大傢都吐着白氣,臉上結着霜,以硬梆梆的南極語開着玩笑、高談闊論、唱着歌。我一直一個人窩在飯店的房間裏,眺望着往後幾個月可能都無望放晴的灰色天空,學習着非常麻煩的(而且我不可能記得住的)南極語文法。
飛機場已經沒有飛機了。載我們來的飛機很快便飛走之後,已經沒有一架飛機在那裏着陸。而飛機滑行跑道終被埋在堅硬的厚冰之下。就像我的心一樣。
鼕天來了,丈夫說。非常漫長的鼕天。飛機不會來,船也不會來,一切的一切都會凍結成冰。看來我們衹能等春天來了,他說。
發現自己懷孕是在來到南極三個月左右的時候。我很明白,自己即將生産的小孩會是小冰男。我的子宮凍僵、羊水中混合着薄冰。我可以感覺到自己肚子裏的那種冷。我很明白。那孩子將和父親一樣應該會擁有冰柱般的眼睛,手指上會結着一層霜。而且我也很明白,我們這新的一傢人將永遠不再離開南極。永遠的過去,那毫無辦法的重量,將緊緊地絆住我們的腳。而我們已經再也無法掙脫它了。
現在我幾乎已經沒留下所謂心這東西了。我的溫暖已經極其遙遠地離我而去。有時候我甚至已經忘記那溫暖了。但總算還會哭。我真的是孤伶伶的一個人。置身在全世界中比誰都孤獨而寒冷的地方。我一哭,冰男就吻我的臉頰。於是我的眼淚便化成冰。於是他把那淚的冰拿在手中,把它放在舌頭上。嘿,我愛你喲,他說。這不是謊言。我很明白。冰男是愛我的。但不知從何方吹進來的風,把他凍成白色的話吹往過去再過去而去。我哭。化成冰的眼淚嘩啦嘩啦地繼續流着。在遙遠的冰凍的南極冰冷的傢中。
冰男
我和冰男結婚了。我是在某個滑雪場的飯店遇到冰男的。這或許應該說是認識冰男的絶佳地方吧。在許多年輕人擠來擠去非常熱鬧的飯店門廳,坐在離壁爐最遠角落的椅子上,冰男獨自一個人正安靜地看書。雖然已經接近正午時分了,但我覺得鼕天早晨清冷鮮明的光綫獨獨還留在他周圍似的。“嘿,那個人是冰男偌。”我的朋友小聲地告訴我。但那時候所謂的冰男到底是什麽樣的東西我還完全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太知道。衹知道他叫做冰男這回事而已。“一定是用冰做成的。所以叫做冰男哪。”她一本正經地對我說。好象在談幽靈或傳染病患者似的。
冰男個子高高的,頭髮顯得很硬的樣子。從容貌看來好象還很年輕,但那粗粗硬硬鐵絲般的頭髮裏卻隨處混雜着像融剩的殘雪般的白發。顴骨像冰凍的岩石般有棱有角,手指上結了一層永不融化的白霜,但除了這些之外,冰男的外表和一般男人沒有兩樣。或許說不上英俊,但以不同觀點來看時,到也相當有魅力。擁有某種尖銳得刺中人心的東西。尤其是他的眼睛,會讓人這樣的感覺。簡直像鼕天早晨的冰柱般閃耀着寡默而透明的眼神。那是在湊合而成的肉體之中,唯一看得到像真實生命的光輝。我在那裏伫立一會兒,遠遠地望着冰男。但冰男一次也沒擡起頭來。他身體動也不動地一直繼續看著書。簡直像在對自己說身邊沒有任何人在似的。
第二天下午冰男還是在同一個地方同樣地看著書。我到餐廳去吃中飯時,和傍晚前跟大傢滑雪回來時,他都還坐在和前一天同一張椅子上,以同樣的眼神投註在同一本書的書頁上。而且接下來的一天也一樣。天黑之後,夜深之後,他還像窗外的鼕天一樣安靜地坐在那裏,一個人獨自看著書。
第四天下午,我隨便找一個藉口沒去滑雪場。我一個人留在飯店,在門廳徘徊了一會兒。人們都已經出去滑雪了,門廳像被遺棄的街道般空蕩蕩的。門廳的空氣過於溫暖潮濕,混合着奇怪的鬱悶氣味。那是黏在人們靴底運進飯店裏來的,並無意間在暖爐前面咕滋咕滋地融化掉的雪的氣味。我從不同的窗戶嚮外張望,隨手翻一翻報紙。然後走到冰男的旁邊,幹脆鼓起勇氣跟他說話。我說起來算是怕生的人,除非真正有事否則是不會和不認識的人說話的。但那時候我無論如何都想跟冰男說話。那是我住在那傢飯店的最後一夜,如果放過這次機會的話,我想可能再也沒什麽機會能和冰男說話了。
你不滑雪嗎?我盡可能以不經意的聲音問冰男。他慢慢擡起頭來。一副好象聽見很遠地方的風聲似的表情。他以那樣的眼神盯着我看。然後靜靜地搖頭。我不滑雪。衹要這樣一面賞雪一面看書就好了,他說。他的話像漫畫對白的方框一樣在空中化為白雲。我名副其實真的可以憑自己的眼睛看到他說的話。他輕輕摩擦浮在手指上的霜並拂掉。
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些什麽纔好。我臉紅起來,一直靜靜地站在那裏。冰男看着我的眼睛。看得出他似乎極輕微地笑了一下。不過我不太清楚。冰男真的微笑了嗎?或者衹是我這樣覺得而已。你要不要坐下來?冰男說。我們談一談吧。你是不是對我感興趣?想知道所謂的冰男是什麽樣的東西吧?然後他衹輕輕笑了一下。沒關係,你不用擔心。跟我談話是不會感冒的。
就這樣我跟冰男談起話來。我們在門廳角落的沙發上並排坐下,一面眺望窗外飛舞的雪花一面小心客氣地談着。我點了熱可可喝。冰男什麽也沒喝。冰男好象也不比我強,跟我一樣不太擅長說話的樣子。而且我們又沒有共通的話題。我們首先談了天氣。然後談到飯店住得舒不舒服。你是一個人到這裏來的嗎?我問冰男。是啊,冰男回答。冰男問我喜歡滑雪嗎?我回答不怎麽喜歡。我說因為我的朋友們一直邀我一定要一起來所以我纔來的,其實我幾乎不會滑。我非常想知道所謂冰男是怎麽樣的?身體真的是用冰做的嗎?平常都吃些什麽東西?夏天在什麽地方生活?有沒有傢人這一類的事。但冰男並不主動談自己。我也不敢問。我想冰男可能不太想談這種事吧。
代替的是,冰男談到我。真是難以相信,但冰男不知道為什麽對我的事竟然知道得非常詳細。比方我的家庭成員、我的年齡、我的健康狀況、我讀的學校、我所交的朋友等,他無所不知。連我早已忘掉的老早以前的事,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真不明白,我臉紅地說。我覺得自己好象在別人面前脫光了衣服似的。為什麽你這麽清楚我的事呢?我問。你能讀別人的心嗎?
不,我無法讀別人的心。不過我知道,就是知道,冰男說。就像一直註視冰的深處一樣。這樣一直盯着你看時,就可以清楚地看見你的事情。
可以看見我的未來嗎?我試着問。
未來看不見,冰男面無表情地說。並且慢慢地搖頭。我對未來這東西完全不感興趣。正確地說,我沒有所謂未來這個概念。因為冰是沒有未來這東西的。這裏衹有過去被牢牢地封在裏面而已。一切的東西簡直就像活生生鮮明地被封在冰裏面。冰這東西是可以把各種東西這樣子保存起來的。非常清潔、非常清晰。原樣不變地。這是所謂冰的任務,也是本質。
太好了,我說。並微微一笑。我聽了之後放下心來。因為我纔不想知道自己的未來呢。
我們回東京之後又見了幾次面,終於變成每逢周末都約會了。但我們既不去看電影,也不去喝咖啡,連飯都不吃。因為冰男幾乎是不吃所謂食物這東西的。我們兩人每次都在公園長椅坐下來,談各種事情。我們真的談很多話。但冰男老是不談自己。為什麽呢?我試着問他。為什麽你不談自己的事呢?我想知道你多一些,你生在什麽地方?雙親是什麽樣的人?經過什麽樣的過程纔變成冰男的?冰男看了一會兒我的臉。然後慢慢地搖頭。我不知道啊。冰男安靜地以凜然的聲音說。並且朝空中吐出僵硬的白氣。我沒有所謂的過去。我知道所有的過去,保存一切的過去。但我自己卻沒有所謂的過去。我既不知道自己生在哪裏,也不知道雙親的容貌。連是不是有雙親都不知道。連自己的年齡也不知道。連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年齡都不知道。
冰男彷佛黑暗中的冰山般孤獨。
而我則認真地愛上這樣的冰男。冰男不管過去不管未來,衹愛着現在的這個我。而我也愛着沒有過去沒有未來衹有現在的這個冰男。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美妙。而且我們甚至開始談到結婚了。我剛剛滿二十歲。而冰男則是我有生以來認真喜歡的第一個對象。所謂愛冰男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麽?當時我連想都沒想到。不過假定就算對象不是冰男,我想我還是一樣會什麽都不知道吧。
母親和姊姊強烈反對我和冰男結婚。你結婚還太年輕,她們說。首先連對方正確的本性都不知道對嗎?你不是連他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生的都不知道嗎?我們實在對親戚說不出口,說你居然要和這樣的對象結婚。而且你呀,對方是冰男,萬一融化了你怎麽辦呢?她們說。你大概不明白,所謂結婚是必須確實負責的喲。冰男到底會不會負起做丈夫的責任呢?
不過不必擔心這些。冰男並不是用冰做成的。冰男衹是像冰一樣冷而已。所以如果身旁變溫暖了,也不會因此而融化。那冷確實像冰。但那肉體和冰不同。雖然確實很冷,但卻不是奪取別人體溫的那種冷。於是我們結婚了。那是沒有人祝福的婚姻。朋友、父母親、姊妹,誰都沒有為我們的結婚而高興。連結婚典禮也沒有舉行。要辦戶籍,冰男連戶籍也沒有。衹有我們兩個人,决定自己已經結婚了而已。我們買了一個小蛋糕,兩個人把它吃了。那就是我們小小的婚禮。我們租了一間小公寓,冰男為了生活而到保管儲存牛肉的冷凍庫去工作。無論如何他總是比較耐得住寒冷的,不管怎樣勞動都不會感覺疲倦。連食物都不太吃。所以雇主非常喜歡冰男。而且給它比別人優厚的酬勞。沒有人防礙我們,我們也不妨礙任何人,衹有兩個人靜悄悄地過着幸福的日子。
冰男擁抱我時,我會想到某個地方應該靜悄悄地存在着的冰塊。我想冰男大概知道那冰塊存在的地方吧。堅硬的,凍得無比堅硬的冰。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冰塊。但那卻在某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他將那冰的記憶傳達給這個世界。剛開始,冰男擁抱我時,我還感覺猶豫。但不久後我就習慣了。我甚至變得愛被他抱了。他依然完全不談自己的事。也不提他為什麽會變成冰男的。我也什麽都沒問。我們在黑暗中互相擁抱,沉默地共有那巨大的冰。那冰中依然清潔地封存着長達幾億年的全世界所有的過去。
我們的婚姻生活沒有什麽成問題的問題。我們深深相愛着,也沒有什麽妨礙我們的東西。周圍的人似乎不太適應冰男的存在,但隨着時間過去,他們也逐漸開始跟冰男說起話來了。他們開始說,其實所謂的冰男跟普通人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啊。不過當然他們心底下並沒有接受冰男,同樣的也沒有接受和他結婚的我。我們和他們是不同種類的人,不管時間經過多久,那鴻溝都無法填平。
我們之間老是生不出小孩。也許人和冰男之間遺傳因子或什麽很難結合也未可知。但不管怎麽樣,也許沒有小孩也有關係,不久之後我的時間就變得太多而難以打發了。早晨我手腳俐落地把傢事做完之後,就在也沒有其它事可做了。我既沒有可以聊天,或一起出去的朋友,也沒有交往的鄰居。我母親和姊妹因為我和冰男結婚還在生我的氣,不跟我說話。她們認為我是全家的羞恥。我連打電話的對象都沒有。冰男去倉庫做工時,我一直一個人在傢,看看書聽聽音樂。以我的個性來說說與其出去外面,不如比較喜歡留在傢裏,一個人獨處也不覺得特別的難過。不過話雖這麽說,但我畢竟還年輕,那種沒有任何變化的日子每天重複過下去終於也開始覺得痛苦了。令我覺得痛苦的不是無聊。我所不能忍受的是那重複性。在那重複之中,我開始覺得連自己都像被重複的影子一樣了。
於是有一天我對丈夫提議。為了轉換心情兩個人到什麽地方去旅行好嗎?旅行?冰男說。他瞇細了眼睛看我。到底為什麽要去旅行呢?你跟我一起住在這裏不快樂嗎?
不是這樣,我說。我很快樂啊。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問題喲。不過,我很無聊。想到遙遠的地方去,看一看沒看過的東西。吸吸看沒吸過的空氣。你瞭解嗎?而且我們也沒有去過蜜月旅行。我們已經有了儲蓄,而且還有很多休假沒用掉。是應該可以去悠閑旅行的時候了。
冰男深深地嘆了一口像要凍僵的氣。嘆息在空中喀啷一聲變成冰的結晶。他結了霜的修長手指交握在膝上。說的也是,如果你那麽想去旅行的話,我並不反對。雖然我並不覺得旅行是那麽好的事,但衹要你能覺得快樂的話,我做什麽都行,到哪裏都可以。我想冷凍倉庫的工作衹要想休息就可以休息。因為到現在為止一直那樣拼命努力地工作。我想沒有任何問題。不過你想去什麽地方呢?比方說?南極怎麽樣?我說。我選擇南極,是想如果是寒冷的地方冰男大概會有興趣吧。而且老實說,從很久以前我就很想去一次南極看看的。我想看看極光,也想看看企鵝。我想象自己穿著有帽子的毛皮大衣,在極光下,和成群的企鵝玩耍的情景。
我這樣說時,丈夫冰男便一直註視着我的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眼地一直盯着我。就像尖銳的冰柱一樣,穿透我的眼睛直通到腦後去。他沉默地沉思一會兒。終於以僵僵硬硬的聲音說好啊。好啊,如果你這樣希望的話,我們就去南極吧。你真的覺得這樣好嗎?
我點頭。
我想兩星期後我也可以請長假了。在那期間旅行的準備應該來得及吧。這樣真的沒關係嗎?
但我無法立刻回答。因為冰男那冰冷的視綫實在凝視我太久太緊了,使我的頭腦變得冰冷麻痹。
但隨着時間的過去,我開始後悔不該嚮丈夫提出南極之行。不知道為什麽。我覺得自從我口中說出“南極”這字眼以來,丈夫心中好象已經起了什麽變化。丈夫的眼睛比以前變得更像冰柱般尖銳,丈夫的吐氣比以前變得更白,丈夫的手指比以前結了更厚的霜。他好象變得比以前更沉默寡言,更頑固了似的。他現在已經變成完全不吃任何東西了。這使我非常不安。出發旅行的前五天,我鼓起勇氣試着嚮丈夫提議。還是別去南極好嗎?我說。想一想南極畢竟太冷,也許對身體不好。我覺得還是去普通一點的地方比較好。去歐洲好嗎?到西班牙一帶放輕鬆吧。喝喝葡萄酒,吃吃西班牙海鮮飯,看看鬥牛。但丈夫不答應。他註視着遠方一會兒。然後看着我的臉。深深註視我的眼睛。那視綫實在太深了,甚至讓我覺得自己的肉體好象就要那樣消失掉了似的。不,我並不想去西班牙,丈夫冰男斷然地說。雖然覺得抱歉,但西班牙對我來說太熱了,灰塵太多了。食物也太辣。而且我已經買好兩人份到南極去的機票。也為你買了毛皮大衣,附有毛皮的靴子。這一切不能白白浪費呀。事到如今已經不能不去了。
老實說我很害怕。我預感去到南極我們身上可能會發生無法輓回的事。我做了好幾次又好幾次的惡夢。每次都是同樣的夢。我正在散步,卻掉進地面洞開的深穴裏去,沒有人發現,就那樣凍僵了。我被封閉在冰中,一直望着空中。我有意識。但一根手指都動彈不得。那種感覺非常奇怪。知道自己正一刻一刻地化為過去。我沒有所謂未來。衹有過去不斷地纍積重疊下去而已。而且大傢都在註視着這樣的我。他們在看着過去。我是朝嚮後方繼續過去的光景。
然後我醒來。冰男睡在我旁邊。他不發一聲鼻息地睡着。簡直像死掉冰凍的似的。但我愛着冰男。我哭了。我的眼淚滴落在他臉頰上。於是他醒過來擁抱我的身體。我做惡夢了,我說。他在黑暗中慢慢地搖頭。那衹是夢啊,他說。夢是從過去來的東西。不是從未來來的。那不會束縛你。是你束縛着夢,明白嗎?嗯,我說。但我沒有確實的信心。
結果我和丈夫終於上了往南極的飛機。因為無論如何都找不到取消旅行的理由。往南極飛機的飛行員和空中小姐全都話非常少。我想看窗外的光景,但雲層很厚什麽都看不見。不久之後窗子上便結了一層厚厚的冰。丈夫在這期間一直默默地看著書。我心中並沒有現在要去旅行的興奮和喜悅。衹是在做着一旦决定的事衹好確實去做而已。
從飛機扶梯下來,腳接觸到南極的大地時,我感覺到丈夫的身體巨大地搖晃一下。那比一瞬間還短,衹有一瞬間的一半左右,因此沒有任何人註意到。丈夫的臉絲毫沒露出一點變化,但我卻沒有看漏。丈夫體內,有什麽強烈而安靜的搖晃。我一直註視着丈夫的側臉。他在那裏站定下來,眺望天空,望望自己的手,並大口吐着氣。然後看着我的臉,微笑起來。這就是你所期望的土地嗎?他說。是啊,我說。
雖然早有某種程度的預料,但南極卻是個超越一切預想的寂寞土地。那裏幾乎沒有什麽人住。衹有唯一的一個沒有特徵的小村子。村子裏也同樣的衹有一傢沒有特徵的小飯店。南極並不是觀光地。那裏甚至連企鵝的影子都沒有。連極光都看不見。我偶爾試着問路過的人,要到什麽地方纔能看見企鵝。但人們衹是沉默地搖頭而已。他們無法理解我的語言。因此我試着在紙上畫出企鵝的畫。即使這樣他們還是沉默地搖頭而已。我好孤獨。走出村外一步,除了冰就沒有別的了。既沒有書、沒有花、沒有河,也沒有水池。到任何地方,都衹有冰而已。一望無際永無止境,所到之處盡是冰之荒野的無限延伸。
然而丈夫一面口吐着白氣,手指結着霜,以冰柱般的眼睛凝視着遠方,一面毫不厭倦精力充沛地從各種地方走到各種地方。而且立刻記住各種語言,和村子裏的人們以冰般堅硬的聲響互相對話。他們以認真的表情一連交談好幾小時。但我完全無法理解他們到底在那樣熱心地談着什麽。丈夫完全着迷於這個地方了。這裏有吸引丈夫的什麽存在着。剛開始我覺得非常生氣。感覺好象衹有我一個人被遺棄了似的。我感覺好象被丈夫背叛了,忽視了似的。
於是,我終於在被厚冰團團圍繞的沉默世界裏,喪失了一切的力氣。一點一點逐漸地。而且終於連生氣的力氣也喪失了。我感覺的羅盤針般的東西似乎已經遺失在什麽地方。我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時間,失去了自己存在的重量。我不知道這是什麽時候開始什麽時候結束的。但一留神時,我已經一個人無感覺地被封閉在冰的世界中,在喪失所謂色彩的永遠鼕季中了。即使在喪失絶大部份的感覺之後,衹有一點我很清楚。在南極的這個我的丈夫已經不是以前我的丈夫了。並不是說有什麽地方不同。他和過去一樣依然很體貼我,對我溫柔地說話。而且我也很明白那是發自他真心的話。不過我還是知道。冰男已經和我在滑雪場的飯店所遇見的那個冰男不一樣了。但我卻無法嚮誰投訴這件事。南極的人都對他懷有好感,而我說的話他們一句也聽不懂。大傢都吐着白氣,臉上結着霜,以硬梆梆的南極語開着玩笑、高談闊論、唱着歌。我一直一個人窩在飯店的房間裏,眺望着往後幾個月可能都無望放晴的灰色天空,學習着非常麻煩的(而且我不可能記得住的)南極語文法。
飛機場已經沒有飛機了。載我們來的飛機很快便飛走之後,已經沒有一架飛機在那裏着陸。而飛機滑行跑道終被埋在堅硬的厚冰之下。就像我的心一樣。
鼕天來了,丈夫說。非常漫長的鼕天。飛機不會來,船也不會來,一切的一切都會凍結成冰。看來我們衹能等春天來了,他說。
發現自己懷孕是在來到南極三個月左右的時候。我很明白,自己即將生産的小孩會是小冰男。我的子宮凍僵、羊水中混合着薄冰。我可以感覺到自己肚子裏的那種冷。我很明白。那孩子將和父親一樣應該會擁有冰柱般的眼睛,手指上會結着一層霜。而且我也很明白,我們這新的一傢人將永遠不再離開南極。永遠的過去,那毫無辦法的重量,將緊緊地絆住我們的腳。而我們已經再也無法掙脫它了。
現在我幾乎已經沒留下所謂心這東西了。我的溫暖已經極其遙遠地離我而去。有時候我甚至已經忘記那溫暖了。但總算還會哭。我真的是孤伶伶的一個人。置身在全世界中比誰都孤獨而寒冷的地方。我一哭,冰男就吻我的臉頰。於是我的眼淚便化成冰。於是他把那淚的冰拿在手中,把它放在舌頭上。嘿,我愛你喲,他說。這不是謊言。我很明白。冰男是愛我的。但不知從何方吹進來的風,把他凍成白色的話吹往過去再過去而去。我哭。化成冰的眼淚嘩啦嘩啦地繼續流着。在遙遠的冰凍的南極冰冷的傢中。
四月一個晴朗的早晨,遇見一個百分之百的女孩
作者:村上春樹
譯者:林少華
四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在原宿後街同一個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過。
不諱地說,女孩算不得怎麽漂亮,並無吸引人之處,衣着也不出衆,腦後的頭髮執着地帶有睡覺擠壓的痕跡。年齡也已不小了---應該快有30了。嚴格地說來,恐怕很難稱之為女孩。然而,相距50米開外我便一眼看出:對於我來說,她是個百分之百的女孩。從看見她身姿的那一瞬間,我的胸口便如發生地鳴一般的震顫,口中如沙漠幹得沙沙作響。
或許你也有你的理想女孩。例如喜歡足頸細弱的女孩,畢竟眼睛大的女孩,十指絶對好看的女孩,或不明所以地迷上慢慢花時間進食的女孩。我當然有自己的偏愛。在飯店時就曾看鄰桌一個女孩的鼻形看得發呆。
但要明確勾勒百分之百的女孩形象,任何人都無法做到。我就絶對想不起她長有怎樣的鼻子。甚至是否有鼻子都已記不真切,現在我所能記的,衹有她並非十分漂亮這一點。事情也真是不可思議。
“昨天在路上同一個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過。”我對一個人說。
“唔,”他應道,“人可漂亮?”
“不,不是說這個。”
“那,是合你口味那種類型嘍?”
“記不得了。眼睛什麽樣啦,胸部是大是小啦,統統忘得一幹二淨。”
“莫名其妙啊!”
“是莫名其妙。”
“那麽,”他顯得興味索然,“你做什麽了?搭話了?還是跟蹤了?”
“什麽都沒有做。”我說,“僅僅是擦肩而過。”
她由東往西走,我從西嚮東去,在四月裏一個神清氣爽的早晨。
我想和她說話,哪怕30分鐘也好。想打聽她的身世,也想全盤托出自己的身世。而更重要的,是想弄清導致1981年4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在原宿後街擦肩而過這一命運的原委。裏面肯定充滿和平時代的古老機器般溫馨的秘密。
如此談罷,我們可以找地方吃午飯,看伍迪。愛倫的影片,再順路到賓館裏的酒吧喝雞尾酒什麽的。弄得好,喝完說不定能同她睡上一覺。
可能性在扣擊我的心扉。
我和她之間的距離以近至十五六米了。
問題是,我到底該如何嚮她搭話呢?
“你好!和我說說話可以嗎?哪怕30分鐘也好。”
過於傻氣,簡直象勸人加入保險。
“請問,這一帶有24小時營業的洗衣店嗎?”
這也同樣傻裏傻氣。何況我豈非連洗衣袋都沒帶!有誰能相信我的道白呢?
也許開門見山好些。“你好!你對我可是百分之百的女孩喲!”
不,不成,她恐怕不會相信我的表白。縱然相信,也未必願同我說什麽話。她可能這樣說:即便我對你是百分之百的女孩,你對我可不是百分之百的男人,抱歉!而這是大有可能的。假如陷入這般境地,我肯定全然不知所措。這一打擊說不定使我一蹶不振。我已32歲,所謂上年紀歸根結底便是這麽一回事。
我是在花店門前和她擦肩而過的,那暖暖的小小的氣塊兒觸到我的肌膚。柏油路面灑了水,周圍蕩漾着玫瑰花香。連嚮她打聲招呼我都未能做到。她身穿白毛衣,右手拿一個尚未貼郵票的四方信封。她給誰寫了封信。那般睡眼惺忪,說不定整整寫了一個晚上。那四方信封裏有可能裝有她的全部秘密。
走幾步回頭時,她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群中。
※ ※ ※
當然,今天我已完全清楚當時應怎樣嚮她搭話。但不管怎麽說,那道白實在太長,我篤定表達不好――就是這樣,我所想到的每每不夠實用。
總之,道白自“很久很久以前”開始,而以“你不覺得這是個憂傷的故事嗎”結束。
※ ※ ※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地方有一個少男和一個少女。少男18,少女16。少男算不得英俊,少女也不怎麽漂亮,無非隨處可見的孤獨而平常的少男少女。但兩人一直堅信世上某個地方一定存在百分之百適合自己的少女和少男。是的,兩人相信奇跡,而奇跡果真發生了。
一天兩人在街頭不期而遇。
“真巧!我一直在尋找你。也許你不相信,你對我是百分之百的男孩。從頭到腳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樣。簡直是在做夢。‘
兩人坐在公園長椅上,手拉手,百談不厭。兩人已不再孤獨。百分之百需求對方,百分之百已被對方需求。而百分之百需求對方和百分之百地被對方需求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這已是宇宙奇跡!
但兩人心中掠過一個小小的,的確小而又小的疑慮:夢想如此輕易成真是否就是好事?
交談突然中斷時,少男這樣說道:
“我說,再嘗試一次吧!如果我們兩人真是一對百分之百的戀人的話,肯定還會有一天在哪裏相遇。下次相遇時如果仍覺得對方百分之百,就馬上在那裏結婚,好麽?
“好的。”少女回答。
於是兩人分開,各奔東西。
然而說實在話,根本沒有必要嘗試,純屬多此一舉。為什麽呢?因為兩人的的確確是一對百分之百的戀人,因為那是奇跡般的邂逅。但兩人過於年輕,沒辦法知道這許多。於是無情的命運開始捉弄兩人。
一年鼕天,兩人都染上了那年肆虐的惡性流感。在死亡綫徘徊幾個星期後,過去的記憶喪失殆盡。事情也真是離奇。當兩人睜眼醒來時,腦袋裏猶如d。h勞倫斯少年時代的貯幣盒一樣空空如也。
但這對青年男女畢竟聰穎豁達且極有毅力,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再度獲得了新的知識新的情感,胜任愉快地重返社會生活。啊,我的上帝!這兩人真是無可挑剔!他們完全能夠換乘地鐵,能夠在郵局寄交快信了。並且分別體驗了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八十五的戀愛。
如此一來二去,少男32,少女31歲了。時光以驚人的速度流逝。
四月一個晴朗的早晨,少男為喝折價早咖啡沿原宿後街由西嚮東走,少女為買快信郵票沿同一條街由東嚮西去,兩人恰在路中間失之交臂。失卻的記憶的微光剎那間照亮兩顆心。兩人胸口陡然悸顫,並且得知:
她對我是百分之百的女孩。
他對我是百分之百的男孩。
然而兩人記憶的燭光委實過於微弱,兩人的話語也不似十四年前那般清晰。結果連句話也沒說便擦身而過,徑直消失在人群中,永遠永遠。
你不覺得這是個令人感傷的故事麽?
是的,我本該這樣嚮她搭話。
作者:村上春樹
譯者:林少華
四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在原宿後街同一個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過。
不諱地說,女孩算不得怎麽漂亮,並無吸引人之處,衣着也不出衆,腦後的頭髮執着地帶有睡覺擠壓的痕跡。年齡也已不小了---應該快有30了。嚴格地說來,恐怕很難稱之為女孩。然而,相距50米開外我便一眼看出:對於我來說,她是個百分之百的女孩。從看見她身姿的那一瞬間,我的胸口便如發生地鳴一般的震顫,口中如沙漠幹得沙沙作響。
或許你也有你的理想女孩。例如喜歡足頸細弱的女孩,畢竟眼睛大的女孩,十指絶對好看的女孩,或不明所以地迷上慢慢花時間進食的女孩。我當然有自己的偏愛。在飯店時就曾看鄰桌一個女孩的鼻形看得發呆。
但要明確勾勒百分之百的女孩形象,任何人都無法做到。我就絶對想不起她長有怎樣的鼻子。甚至是否有鼻子都已記不真切,現在我所能記的,衹有她並非十分漂亮這一點。事情也真是不可思議。
“昨天在路上同一個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過。”我對一個人說。
“唔,”他應道,“人可漂亮?”
“不,不是說這個。”
“那,是合你口味那種類型嘍?”
“記不得了。眼睛什麽樣啦,胸部是大是小啦,統統忘得一幹二淨。”
“莫名其妙啊!”
“是莫名其妙。”
“那麽,”他顯得興味索然,“你做什麽了?搭話了?還是跟蹤了?”
“什麽都沒有做。”我說,“僅僅是擦肩而過。”
她由東往西走,我從西嚮東去,在四月裏一個神清氣爽的早晨。
我想和她說話,哪怕30分鐘也好。想打聽她的身世,也想全盤托出自己的身世。而更重要的,是想弄清導致1981年4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在原宿後街擦肩而過這一命運的原委。裏面肯定充滿和平時代的古老機器般溫馨的秘密。
如此談罷,我們可以找地方吃午飯,看伍迪。愛倫的影片,再順路到賓館裏的酒吧喝雞尾酒什麽的。弄得好,喝完說不定能同她睡上一覺。
可能性在扣擊我的心扉。
我和她之間的距離以近至十五六米了。
問題是,我到底該如何嚮她搭話呢?
“你好!和我說說話可以嗎?哪怕30分鐘也好。”
過於傻氣,簡直象勸人加入保險。
“請問,這一帶有24小時營業的洗衣店嗎?”
這也同樣傻裏傻氣。何況我豈非連洗衣袋都沒帶!有誰能相信我的道白呢?
也許開門見山好些。“你好!你對我可是百分之百的女孩喲!”
不,不成,她恐怕不會相信我的表白。縱然相信,也未必願同我說什麽話。她可能這樣說:即便我對你是百分之百的女孩,你對我可不是百分之百的男人,抱歉!而這是大有可能的。假如陷入這般境地,我肯定全然不知所措。這一打擊說不定使我一蹶不振。我已32歲,所謂上年紀歸根結底便是這麽一回事。
我是在花店門前和她擦肩而過的,那暖暖的小小的氣塊兒觸到我的肌膚。柏油路面灑了水,周圍蕩漾着玫瑰花香。連嚮她打聲招呼我都未能做到。她身穿白毛衣,右手拿一個尚未貼郵票的四方信封。她給誰寫了封信。那般睡眼惺忪,說不定整整寫了一個晚上。那四方信封裏有可能裝有她的全部秘密。
走幾步回頭時,她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群中。
※ ※ ※
當然,今天我已完全清楚當時應怎樣嚮她搭話。但不管怎麽說,那道白實在太長,我篤定表達不好――就是這樣,我所想到的每每不夠實用。
總之,道白自“很久很久以前”開始,而以“你不覺得這是個憂傷的故事嗎”結束。
※ ※ ※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地方有一個少男和一個少女。少男18,少女16。少男算不得英俊,少女也不怎麽漂亮,無非隨處可見的孤獨而平常的少男少女。但兩人一直堅信世上某個地方一定存在百分之百適合自己的少女和少男。是的,兩人相信奇跡,而奇跡果真發生了。
一天兩人在街頭不期而遇。
“真巧!我一直在尋找你。也許你不相信,你對我是百分之百的男孩。從頭到腳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樣。簡直是在做夢。‘
兩人坐在公園長椅上,手拉手,百談不厭。兩人已不再孤獨。百分之百需求對方,百分之百已被對方需求。而百分之百需求對方和百分之百地被對方需求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這已是宇宙奇跡!
但兩人心中掠過一個小小的,的確小而又小的疑慮:夢想如此輕易成真是否就是好事?
交談突然中斷時,少男這樣說道:
“我說,再嘗試一次吧!如果我們兩人真是一對百分之百的戀人的話,肯定還會有一天在哪裏相遇。下次相遇時如果仍覺得對方百分之百,就馬上在那裏結婚,好麽?
“好的。”少女回答。
於是兩人分開,各奔東西。
然而說實在話,根本沒有必要嘗試,純屬多此一舉。為什麽呢?因為兩人的的確確是一對百分之百的戀人,因為那是奇跡般的邂逅。但兩人過於年輕,沒辦法知道這許多。於是無情的命運開始捉弄兩人。
一年鼕天,兩人都染上了那年肆虐的惡性流感。在死亡綫徘徊幾個星期後,過去的記憶喪失殆盡。事情也真是離奇。當兩人睜眼醒來時,腦袋裏猶如d。h勞倫斯少年時代的貯幣盒一樣空空如也。
但這對青年男女畢竟聰穎豁達且極有毅力,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再度獲得了新的知識新的情感,胜任愉快地重返社會生活。啊,我的上帝!這兩人真是無可挑剔!他們完全能夠換乘地鐵,能夠在郵局寄交快信了。並且分別體驗了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八十五的戀愛。
如此一來二去,少男32,少女31歲了。時光以驚人的速度流逝。
四月一個晴朗的早晨,少男為喝折價早咖啡沿原宿後街由西嚮東走,少女為買快信郵票沿同一條街由東嚮西去,兩人恰在路中間失之交臂。失卻的記憶的微光剎那間照亮兩顆心。兩人胸口陡然悸顫,並且得知:
她對我是百分之百的女孩。
他對我是百分之百的男孩。
然而兩人記憶的燭光委實過於微弱,兩人的話語也不似十四年前那般清晰。結果連句話也沒說便擦身而過,徑直消失在人群中,永遠永遠。
你不覺得這是個令人感傷的故事麽?
是的,我本該這樣嚮她搭話。
譯者:林少華
大象從鎮上的象捨中失蹤,我是從報紙上知道的。這天,我一如往常地被調至6點30分的鬧鐘叫醒。然後去廚房燒咖啡,烤面包片,打開超短波廣播,啃着面包片在餐桌上攤開晨報。我這人看報總是從第一版依序看下去,因此過了好半天才接觸到關於大象失蹤的報道。第一版報道的是日美貿易摩擦問題和戰略防禦構思,接下去是國內政治版,國際政治版,經濟版,讀者來信版,讀者專欄,不動産廣告版,體育版,再往下纔是地方版。
大象失蹤的報道登在地方版的頭條。標題相當醒目:“××鎮大象去嚮不明”。緊接着是一行小標題:“鎮民人心惶惶,要求追究管理責任”。還有幾名警察驗證無象象捨的照片。沒有象的象捨總好像不大自然。空空蕩蕩,冷冷清清,儼然被掏空五臟六腑後乾燥了的龐大動物。
我撥開落在報紙上的面包屑,專心緻志地逐行閱讀這則報道。上面說人們發現大象失蹤是5月18日(即昨天)下午2時。供食公司的人像往常那樣用卡車為大象運來食物(其主食為鎮立小學的學生們的剩飯),從而發現象捨空空如也。套在象腳上的鐵環依然上着鎖剩在那裏,看來是大象整個把腳拔了出去,失蹤的不僅僅是大象,一直照料大象的男飼養員也一同無影無蹤。
人們最後見到大象和飼養員是前天(即5月17日)傍晚5點多鐘。5個小學生來象捨寫生,5點多之前一直用蠟筆為大象畫像來着。這幾個小學生是大象的最後目擊者,後來再無人見到。因為6點鈴一響,飼養員便將象廣場的門關上,使人們無法入內。
5個小學生異口同聲地作證說,那時無論大象還是飼養員都沒顯出任何異常。大象一如往常乖乖站在廣場中央,不時左右搖晃一次鼻子,眯縫起滿是皺紋的眼睛。它已老態竜鐘,動一下身體都顯得甚是吃力。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馬上癱倒在地上斷氣。
以上便是這則新聞報道的內容。
大象之所以被本鎮(即我居住的鎮)領來飼養,也是因為其年老之故。鎮郊的一座小動物園以經營睏難為由關閉的時候,動物們都已通過動物經紀人之手轉往全國各地。唯獨這頭象由於年紀太老而無法找到主顧,一來哪裏的動物園中象的數量都綽綽有餘,二來沒一處動物園好事並充裕到足以接收一頭似乎馬上就心髒病發作死去的舉步維艱的大象的程度。因此,這頭象便在所有同伴蕩然無存的形同廢墟的動物園裏無所事事地——當然也不是說它原來有什麽事幹——獨自滯留三四個月之久。
無論動物園還是鎮上,對此都相當頭痛。動物園方面已將動物園舊址賣給了房地産商。房地商準備在此建造高層公寓,鎮上也簽發了開發許可證。象的處理越是長期拖而不决所付的利息越高。可是又不能把象殺掉。若是猴子或蝙蝠之類,倒也罷了。但殺一頭大象太容易暴露目標。一旦真相大白,問題就非同小可。於是三方一起商量,達成了關於老年大象處置的協議。(1)象作為鎮有財産免費領養;(2)收容象的設施由房地産商無償提供;(3)飼養員工資由動物園方面負擔。
這就是三方協議的內容。正好是一年前的事。
說起來,我從一開始便對“大象問題”懷有個人興趣。大凡有關象的報道我統統剪了下來。還去旁聽了鎮議會討論大象問題的會議。所以現在我纔可以如此灑脫如此準確地敘述此事的發展過程。話也許有些羅嗦,但“大象問題”的處理很可能同大象失蹤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還是容我記述下來為好。
當鎮長簽署了協議而即將領養大象之時,議會中以在野黨為中心(在此之前我還真不知道鎮議會中有什麽在野黨)掀起了反對運動。
“為什麽本鎮必須領養大象?”他們質問鎮長。其主張可以歸納成以下幾條(條條太多十分抱歉,但我以為這樣容易理解):(1)大象問題屬於動物園與房地産商私營企業之間的問題,鎮政府沒有理由參與;(2)所需管理費、食物費太多;(3)安全問題如何解决?(4)本鎮自費飼養大象的好處何在?
他們拉開論戰架勢——“飼養大象之前,下水道的整治和消防車的購置等鎮政府要做的事情豈非堆積如山?”儘管措詞不算尖刻,但言下之意無非是懷疑鎮長同房地産有幕後交易。
對此,鎮長的意見是這樣的:(1)高層建築群的落成在將極大幅度增加鎮的稅收,大象的飼養費之類自然不成問題,鎮政府參與這樣的項目是理所當然的;(2)象年事已高,食欲亦不很大,到於加害於人的可能性可以說等於零;(3)象一旦死亡,由房地産商作為大象飼養地提供的地皮即為鎮有財産;(4)象可成為鎮的象徵。
經過長時間爭辯討論,鎮上終於决定將大象領養過來。由於自古以來位於城郊住宅地帶,鎮上的居民大多生活較為富裕,鎮財政也夠雄厚。況且人們可以對領養無處可去的大象這一舉措懷有好感。較之下水道和消防車,居民畢竟更容易同情大象。
我也贊成鎮上飼養大象。出現高層建築群固然大殺風景,但自己鎮上能擁有頭大象倒確實不壞。
砍掉山坡上的樹林,把小學一座快要倒塌的體育館移建到這裏作為象捨。一直在動物園照料大象的飼養員跟過來住下。小學生們的殘湯剩飯充作象飼料。於是大象被一輛拖車從封閉的動物園運到新居,在此打發餘生。
我也參加了象捨的落成典禮。鎮長面對大象發表演說(關於本鎮的發展與文化設施的充實),小學生代表朗讀作文(象君,祝你永遠健康雲雲),舉行了大象寫生的評比展覽(大象寫生此後遂成為本鎮小學生美術教育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保留項目),身穿翩然飄然的連衣裙的兩名妙齡女郎(算不上絶代佳人)分別給大象吃了一串香蕉。大象則幾乎紋絲不動地靜靜忍受着這場相當乏味——起碼對象來說毫無意味——的儀式的進行,以近乎麻木不仁的空漠的眼神大口小口吃着香蕉。吃罷,衆人一齊拍手。
象右側的後腳套了一個堅不可摧的沉重鐵環。鐵環連着一條十多米長的粗鐵鏈。鐵鏈的另一端萬無一失地固定在水泥墩上。鐵環和鐵鏈一看就知道其牢不可破,大象縱然花100年時間使出渾身解數也全然奈何不得。
我不大清楚大象是否對這腳鐐心懷不滿。不過至少表面上它對套在自己腳上的鐵鏈漠然置之。它總是以愣愣的眼神望着空間莫可知曉的某一點。每當陣風吹來,耳朵和白色的體毛便輕飄飄搖顫不止。
負責飼養大象的是位瘦小的老人。不知其準確年齡,也許60多歲,也許70有餘。世上有一種人一旦越過某一臨界點便不再受年齡左右,這位老人便是其一。皮膚無論鼕夏都曬得又紅又黑,頭髮又短又硬,眼睛不大。面目並沒有什麽明顯特徵,唯獨嚮左右突出的接近圓形的耳朵使得整張臉相形見小,格外引人註目。
此人絶對談不上冷淡,有人搭話肯定給予圓滿回答,話也說得井井有條。若他願意,也能表現出一副熱情的樣子——儘管使我覺得有幾分勉強。不過原則說來,則像是位沉默寡言的孤獨老人。他看上去喜歡小孩。小孩來時盡可能親切相待,但孩子們卻不大接受老人的好意。
接受這位飼養員好意的衹有大象。他住在緊挨象捨的預製板小屋裏,從早到晚形影不離地照料大象。象與飼養員相處的時間已超過10年,二者關係的親密程度,衹消看雙方每個細微的動作和眼神,即可一目瞭然。飼養員如果想讓呆呆站在同一地方的大象移動一下,衹要站在象的旁邊用手啪啪地輕拍幾下它的前腳並嘀咕一句什麽,大象便不堪重負似地慢慢搖擺着身體,準確移至指定位置,隨即仍如剛纔那樣註視空間的某一點。
每到周末,我就去象捨細心觀察這情形,但還是不能完全理解二者的交流是依據何種原理得以實現的。大象或許能聽懂簡單的人語(畢竟活的時間長),也可能通過拍腳方式來把握對方的意圖。或者具有心靈感應那類特異功能因而懂得飼養員的所思所想也未可知。
一次我問老人;“您是怎樣給大象下命令的呢?”老人笑笑,衹回答“長時間相處的關係”,再沒做更多的解釋。
總之便是這樣平安無事地過了一年,此後象突然失蹤。
我一邊喝第二杯咖啡,一邊將報道再次從頭研究一遍。文章寫得相當奇妙,儼然福爾摩斯敲着煙斗說:“華生,快看呀,這篇報道太有趣了!”
此報道給人以奇妙印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可能支配寫報道記者大腦的睏惑與混亂。而睏惑與混亂顯然起因於情況的非條理性。記者力圖巧妙避開條非理性來寫一篇“地道的”新聞報道,但這反而將他自身的混亂與猶豫推嚮致命的地步。
例如,報道上的措詞是“大象逃脫”。可是通觀全篇報道,顯而易見大象並非什麽逃脫,而明明是“失蹤”。記者將這種自我矛盾表述為“細節上仍有若幹不明確之處”。我則無論如何不認為事情是可以用什麽“細節”什麽“不明確”這類老生常談的字眼敷衍得了的。
首先,問題出在象腳上套的鐵環。鐵環依然上着鎖剩在那裏。最穩妥的推論是:飼養員用鑰匙打開鐵環從象腳摘下,然後又將其鎖好,同象一起逃跑(當然報紙也認識到了這種可能性)。問題是飼養員手中沒有鑰匙。鑰匙僅有兩把。一把為確保安全藏於警察署的保險櫃,另一把收在消防署的保險櫃之中。飼養員(或其它什麽人)不大可能從中偷出鑰匙。縱使萬一偷出,也大可不必把用過的鑰匙特意送回保險櫃——翌日早打開一看,兩把鑰匙全都好好躺在警察署和消防署的保險櫃裏。既然這樣,那麽就是說大象勢必在不使用鑰匙的情況下將腳從堅不可摧的鐵環中撥出,而這除非用鋸將象腿鋸斷,否則絶無可能。
第二個問題是出逃的途徑。象捨與“象廣場”圍了3米多高的堅固柵欄。由於象的安全管理在鎮議會上爭論得沸沸揚揚,鎮政府采取了對一頭老象未免小題大做的警備措施。柵欄是用混凝土和粗鐵棍做成的(費用當然由房地産商出),門口衹有一個,且內側上鎖。象不可能跨過如此要塞般的柵欄跑到外面。
第三個問題是象的足跡。象捨後面是陡峭的山坡,象無法攀登。因此象假如真的用某種手段飛越柵欄,它也衹能經前面的道路逃走。然而鬆軟的沙土路面上沒有留下任何類似象腳印的痕跡。
總而言之,綜合分析這篇滿是令人睏惑和不快措詞的新聞報道,根本看不出事件的結論或實質。
當然,自不待言,報紙也好警察也好鎮長也好至少表面上都不願意承認大象失蹤這一事實。警察正以“象或許被人采取錦囊妙計早有預謀地強行掠出,或許自行逃脫”這樣的判斷進行偵查,並樂觀地預測:“考慮到隱藏大象的睏難程度,事件的解决不過是時間問題”警察還打算請求近郊的獵友會以及自衛隊狙擊部隊出動,一起搜山。
鎮長召開記者招待會(有關記者招待會的報道沒有登在地方版,而出現在全國版的社會版面),就鎮政府警備措施上的疏忽進行道歉。同時鎮長又強調指出:“同全國任何一座動物園的同類設施相比,本鎮的大象管理體製都毫不遜色,較之標準有力得全面得多。”還說:“這是充滿惡意的、危險而且無聊的反社會行為,是絶對不能允許的!”
在野黨的議員重複一年前的論調:“務必追究鎮長同企業串通一氣而將鎮民輕易捲入象處理問題的政治責任。”
一位母親(39歲)以“不安的神情”說:“短時間內不能放心地讓孩子去外面玩了。”
報紙上敘述了本鎮領養大象的前後詳細經過,並附有大象收容設施示意圖。還介紹了大象簡歷,以及同象一起失蹤的飼養員(渡邊升,63歲)的情況。渡邊飼養員是千葉縣館山人,長期在動物園飼養哺乳動物,“由於動物知識豐富為人忠厚誠實,深得有關人員信賴”。象是22年前由非洲東部送來的。準確年齡無人知曉,其為人更是不得而知。
報道的最後,說警察正在嚮鎮民徵求有關大象任何形式的情報。我一面喝第二聽啤酒,一面就此沉思片刻。終歸還是决定不給警察打電話。一來我不大樂意同警察發生關係,二來我不認為警察會相信我提供的情報。嚮那些甚至沒有認真設想過大象失蹤可能性的傢夥,無論說什麽都是徒勞。
我從書架中抽出剪報集,將從報紙上剪下的關於象的報道夾在裏面。隨後洗了洗杯子碟子,去公司上班。
我從nhk晚上7時的新聞節目中看到了搜山的情況。提着裝滿麻醉彈大型來福槍的獵手、自衛隊和警察們把附近的山一個接一個颳篦子似地搜刮一遍,好幾架直升飛機在空中盤旋。雖說是山,但都位於東京郊外的住宅地邊緣,不過是小山包而已。聚集如此之衆,衹消一天即可基本搜尋完畢,再說尋找的對象又不是矮小的殺人鬼而是巨大的非洲象,其可藏身之處自然有限。然而折騰到傍晚也沒找到大象。出現在電視熒屏中的警察署長聲稱“仍將繼續搜尋”。電視新聞的主持人總結道:“是何人如何使大象逃脫,藏於何處,其動機何在,一切都還在深深處於迷宮之中”
此後繼續搜尋數日,大象依舊蹤影皆無,當局連點蛛絲馬跡也未能找到。我每天都細看報紙的報道,大凡所能見到的報道統統用剪刀裁剪下來。就連以大象事件為題材的漫畫也不放過。由此之故,剪報集的容量很快到達極限,而不得不去文具店買一册新的回來。儘管擁有如此數量繁多的報道,卻不包括任何一條我想知道的那類事實。報上寫的全都是些驢唇不對馬嘴一文不值的內容,諸如什麽“依然下落不明”,什麽“搜查人員深感苦惱”,什麽“背後是否有秘密組織”等等。大象失蹤了一周之後,這方面的報道日見減少,直至幾乎銷聲匿跡。周刊上倒是刊載了幾篇嘩衆取寵的報道,有的竟拉出算命先生來,不久也草草收兵了。看上去人們似乎企圖將大象事件強行歸為擁有不少會員的“不解之謎俱樂部”這一範疇之中。一頭年老的象和一個年老的飼養員縱使從這塊土地失去蹤影,也不會對社會的趨勢造成任何影響。地球照樣單調地旋轉,政治傢照樣發表不大可能兌現的聲明,人們照樣打着哈欠去公司上班,孩子們照樣準備應付考試。在這周而復始無休無止的日常波浪之中,人們不可能對一頭去嚮不明的老象永遠興致勃勃。如此一來二去,沒有什麽特殊變異的這幾個月便像窗外行進的疲於奔命的軍隊一樣匆匆過去。
我不時抽時間跑去往日的象捨,觀望已無大象的大象住處。鐵柵欄門上纏了好幾道粗大的鐵鏈,任憑誰都無從入內。從柵欄空隙窺視,象捨門仍被鐵鏈纏繞着。看樣子警察為了彌補無法找見大象所造成的缺憾,而對失去大象後的象捨加強了不必要的警備。四下寂寥,空無人影,唯見一群鴿子在象捨房脊上斂翅歇息。廣場已無人修剪,開始長滿萋萋夏草,仿佛已等得忍無可忍。象捨門上纏繞的鐵鏈使人聯想起森林中牢牢看守着已腐朽得化為廢墟的王宮的巨蟒。大象離去纔不過數月,這場所便蒙上了帶有某種宿命意味的荒涼面影,籠罩在雨雲一般令人窒息的氣氛中。
我那次見到她,9月都已接近尾聲了。這天從早到晚雨下個不停。雨單調而又溫柔細膩,是這一季節常見的雨,它將在地面打下烙印的夏日記憶一點點衝掉。所有的記憶都沿着水溝往下水道往河道流去,進入又黑又深的大海。
我倆是在我公司舉行的産品宣傳酒會上見面的。我在一傢大型電機公司廣告部工作,當時正負責推銷為配合秋季結婚熱和鼕季發奬金時節而生産的係列型廚房電氣用品。主要任務是同幾傢婦女雜志交涉,以使其刊載配合性報道。事情倒不怎麽需要動腦,但須註意對方報道寫得不失分寸,以盡量不讓讀者嗅到廣告味。作為代價,我們可以在雜志上刊登廣告。世上的事就是要互相扶持。
她是一傢以年輕主婦為對象的雜志的編輯,參加酒會是為了采訪——明知是為人推銷的采訪。我正好閑着,便以她為對象,開始講解由意大利著名設計師設計的彩色電冰箱、咖啡機、微波爐和榨汁機。
“至為關鍵的是諧調性。”我說,“無論式樣多好的東西,都必須同周圍保持諧調,不然毫無意思。顔色的諧調,式樣的諧調,功能的諧調——這是當今廚室最需要註意的。據調查,一天之中主婦在廚室的時間最長。對主婦來說,廚室是她的工作崗位,是書齋,是起居室。因此她們都在努力改善廚室環境,使其多少舒服一點。這與大小沒有關係。無論大小,好的廚室原則都衹有一個。那就是簡潔性、功能性、諧調性。而本係列便是依據這一指導思想設計出來的。舉例說來,請看這個烹調板……”
她點着頭,在小筆記本上做着記錄。其實她並非對這類采訪特別懷有興趣,我對烹調板也沒什麽偏愛,我們不過在完成各自的工作而已。
“看來你對廚房裏的事相當熟悉。”她在我講解完後說道。
“工作嘛!”我做出商業性笑容回答。“不過我倒是很喜歡做菜——這與工作無關——做的簡單,但天天做。”
“廚房真的需要諧調性?”她問。
“不是廚房,是廚室。”我糾正道。“本來怎麽都所謂,可公司有這樣那樣的規定。”
“對不起。那麽廚室真的需要諧調性?是你個人的意見?”
“至於我的意見,不解掉領帶是無可奉告的。”我笑着說,“不過今天算是例外。我想就廚室來說,講究諧調性之前,應該備有若幹必不可少的東西。問題是那種因素成不了商品。而在這急功近利的世界上,成不了商品的因素幾乎不具有任何意義。”
“世界果真是急功近利的不成?”
我從衣袋裏掏出香煙,用打火機點燃。
“隨便說說罷了。”我說,“這樣一來,很多事情就容易明白,工作也容易進行。這類似一種遊戲,或曰本質上急功近利,或曰急功近利式的本質——說法五花八門。而且衹有這樣認為,纔不至於招風惹浪,纔不至於出現復雜問題。”
“妙趣橫生的見解!”
“談不上什麽妙趣,人人都這樣看待。”我說,“對了,有一種香檳不算很壞,如何?”
“謝謝,恕不客氣。”
隨後,我和她邊喝香檳邊海闊天空地聊起來,聊着聊着,聊出幾個兩人共同的熟人。不僅如此,我的妹妹同她碰巧畢業於同一所大學。我們於是以幾個這樣的名字為綫索較為順利地展開話題。
她也罷我也罷都是單身。她26,我31。她戴隱形眼鏡,我架着普通鏡片。她贊賞我領帶的顔色,我誇奬她的上衣。我們談起各自所居公寓的租金,也就工資數額和工作內容發了些牢騷。總之我們是相當親密起來了。她是位顧盼生輝的嫵媚女性,絲毫沒有強加於人的味道。我站着同她在那裏談了大約20分鐘,沒有發現任何不可以對她抱有好感的理由。
酒會快結束時,我邀她走進同一賓館裏的酒吧,坐在那裏同她繼續交談。透過酒吧巨大的窗扇,可以看見初秋的雨幕。雨依然無聲無息地下着,遠處街道的光亮糅合着各種各樣的信息。酒吧裏幾乎見不到客人,潮乎乎的沉默統治着四周。她要了達伊吉莉雞尾酒,我要的是加冰蘇格蘭威士忌。
我們一邊喝着各自的杯中物,一邊像多少有些親密起來的初次見面的男女那樣說着在酒吧裏常說的話:大學時代,喜歡的音樂,體育,日常習慣等等。
接着,我提起大象。至於話題為什麽突然轉到大象身上,我已記不起其中關聯。大概談到某種動物,由此聯上了大象。也有可能我是極其無意識地想嚮某人——似可與之暢所欲言的一個人——闡述我對大象失蹤的看法。或者是僅僅藉助酒興也未可知。
話一出口,我便意識到自己提出的是現在最不適宜的話題。我不應該談起什麽大象。怎麽說呢,這個話題早已成為過去。
於是我想馬上收回話頭。糟糕的是她對大象失蹤事件懷有非同一般的興致。我一說自己看過好幾回大象,她便連珠炮似地發出質詢:
“什麽樣的象?你認為是如何逃跑的?平時它吃什麽?有沒有危險?”如此不一而足。對此,我按照報紙上的口徑輕描談寫地解說了一遍。看樣子她從我的口氣中感覺出了異乎尋常的冷淡——我從小就很不善於敷衍。
“象不見的時候大吃一驚吧?”她喝着第二杯達伊吉莉,若無其事地問。“一頭大象居然突然失蹤,肯定誰都始料未及。”
“是啊,或許是。”我拿起一枚碟子裏的炸薯片,分成兩半,吃了一半。男侍轉來,另換了一個煙灰缸。
她饒有興味地註視了一會我的臉。我又叼起一支香煙點燃。本來戒煙已有3年之久,而在大象失蹤之後,又開始重操舊業。
“所謂或許是,就是說關於大象失蹤多少有所預料?”她問。
“談不上什麽預料!”我笑了笑,“一天大象突然消失,這既無先例又無必然性,也不符合事理。”
“不過你這說法可是非常奇特,嗯?我說‘一頭大象居然突然失蹤,肯定誰都始料未及’,你回答‘是啊,或許是’。而一般人是絶不至於這樣回答的。或者說‘一點不錯’,或者說‘說不明白’。”
我嚮她含糊地點了下頭,揚手叫來男侍,讓他再送一杯蘇格蘭威士忌。等威士忌的時間裏,我們暫且保持沉默。
“我說,我不大理解,”她用沉靜的口氣說,“剛纔你還一直說得頭頭是道,在提起大象之前。可一提起大象,你說話就好像一下子變得反常。聽不出你想表達什麽。到底怎麽回事?莫非在大象上面有什麽不好啓齒的地方?還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呢?”
“你的耳朵沒有毛病。”我說。
“那麽說問題在你羅?”
我用手指把酒杯裏的冰塊撥弄得旋轉不止。我喜歡聽冰塊相撞的聲音。
“並未嚴重得要用問題這個字眼。”我說,“不足挂齒的小事。也沒有什麽可嚮別人隱瞞的,不過是因為我沒有把握說透而沒說罷了。如果說是奇特,也確實有點奇特。”
“怎麽奇特?”
我再無退路,衹好喝口威士忌,開始敘說:
“其中一點要指出的是,我恐怕是那頭失蹤大象的最後一個目擊者。我見到大象是5月17日晚上7點左右,得知大象失蹤是第二天近午時分。這段時間再沒有人見過大象。因為傍晚6點象捨就關門了。”
“邏輯上不好明白。”她盯住我的眼睛,“既然象捨已經關門,你怎麽還能見到大象呢?”
“象捨後面是一座懸崖樣的小山。山是私有山,沒有像樣的路可走,上面衹有一個地方可以從後面窺視象捨。而知道這個地方的,想必衹我一人。”
我這一發現完全出於偶然。一個周日下午,我去後山散步迷了路。大致判斷方位行走之間,碰巧走到了這個地方。那是塊平地,大小可供一個睡覺。透過灌木叢空隙朝下一望,下面正是象捨的房脊。房脊稍往下一點有個相當大的通風口,從中可以清楚看到象捨裏面的光景。
從此以後,我經常去那裏觀望進入象捨裏邊的大象,逐漸成了習慣。如果有個問何苦如此不厭其煩,我也回答不好。衹是想看大象的私下表現而已,沒有什麽深刻的理由。
象捨裏黑暗之時,自然看不見大象。但剛入夜時飼養員打開象捨電燈為大象做這做那,我因之得以一一看在眼裏。
我最先註意到的,是象捨中衹剩大象與飼養員時,看上要比在人前那種公開場合表現得遠為親密無間。這點衹消看他們之間一個小小的舉動即可一目瞭然。甚至使人覺得白天時間他們有意剋製感情,以免被人看出彼此的親密程度,而到單獨相守的夜晚便完全無此顧慮。但這不等於說他們在象捨中有什麽特殊舉動。進入象捨之後,大象依然一副呆愣愣的樣子,飼養員也一味地忙他作為飼養員的當務之急:用甲板刷給大象刷洗身體,歸攏拉在地板上的巨大糞團,收拾其吃過的東西。儘管如此,其彼此間結下的信賴感所釀出的獨特的溫馨氛圍不容你無動於衷。飼養員打掃完地板,大象便搖晃着身子在飼養員背部輕輕叩擊幾下。我很喜歡觀看大象的這個動作。
“以前你就喜愛大象?我是說不僅僅限於這頭象……”她問。
“是的,我想是這樣。”我說,“大象這種動物身上有一種撥動我心弦的東西,很早以前就有這個感覺,原因我倒不清楚。”
“所以那天也同樣傍晚一人登後山看象去了,是吧?”她說,“呃——5月……”
“17日,”我接道,“5月17日晚上7點左右。那時節白天變得很長,空中還剩有一點火燒雲。不過象捨裏已經燈火通明。”
“當時象和飼養員都沒有什麽異常?”
“既可以說沒有異常,又可以說有異常。我無法說得準確。因為畢竟不是相距很近。作為目擊者的可靠性也可以說不是很高。”
“到底發生了什麽?”
我喝了一口因冰塊融化而酒味變淡的威士忌。窗外的雨仍下個不止,既不大下,又不小下,儼然一幅永遠一成不變的靜物畫。
“也不是說發生了什麽。”我說,“象和飼養員所作所為一如往常。掃除,吃東西,親昵地挑逗一下,如此而已。平日也是如此。我感到不對頭的衹是其平衡。”
“平衡?”
“就是大小平衡,象和飼養員身體大小的比例。我覺得這種比例較之平時多少有所不同,兩者之差似乎比平時縮小一些。”
她把視綫投在自己手中的達伊吉莉杯上,靜靜註視良久。杯裏冰塊已經化了,如細小的海流試圖鑽進雞尾酒的間隙中去。
“那麽說象的身體變小了?”
“也許是飼養員變大了,也可能雙方同時變化。”
“這點沒告訴警察?”
“當然沒有。”我說,“即使告訴,警察也不會相信,況且我若說出在那種時候從後山看大象,自己都難免受到懷疑。”
“那,比例與平時不同這點可是事實?”
“大概。”我說,“我衹能說是大概。因為沒有證據,而且我說過不止一次——我是從通風口往裏窺的。不過我在同一條件下觀看大象和飼養員不下數十次,我想總不至於在其大小比例上發生錯覺。”
噢,也許眼睛有錯覺。當時我好幾次閉目搖頭,但無論怎麽看象的體積都與平時不同,的確有些縮小。以至一開始我還以為鎮上搞來一頭小象呢。可是又沒聽說過(我絶不會放過有關象的新聞)。既然如此,那麽衹能認為是原來的老象由於某種原因而驟然萎縮。而且仔細看去,象高興似地擡右腳叩擊地面,用多少變細的鼻子撫摸飼養員的後背。
那光景甚是不可思議。從通風口密切註視裏面的時間裏,我覺得象捨之中仿佛流動着唯獨象捨纔有的冷冰冰的另一種時間,並且象和飼養員似乎樂意委身於將彼此捲入——至少已捲入一部分——其中的新生體係。
我註視象捨的時間總共不到30分鐘。象捨的燈比往常關得早,7時30分燈便熄了,所有一切都籠罩在黑暗之中。我在那裏等了一會,等待象捨的燈重新閃亮,但再未閃亮。這便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大象。
“那麽說,你是認為象就勢迅速萎縮變小而從柵欄空隙逃走了?還是認為完全消失了呢?”她問。
“不清楚。”我說,“我衹是力圖多少準確地記起自己親眼見過的場面,此外的事幾乎沒有考慮。眼睛獲得的印象實在太強烈了,坦率地說,我恐怕根本無法從中推導出什麽。”
以上就是我關於大象失蹤說的所有的話。不出我最初所料,這些話作為剛剛相識的年輕男女交談的話題未免過於特殊,況且其本身早已完結。說罷,兩人之間出現了許久的沉默。在談完與其他事幾乎毫不相關的大象失蹤的話之後,我也罷她也罷都不知再提起什麽話題為好。她用手指摩挲雞尾酒杯的邊緣。我則看着杯墊上的印字。反復看了25遍。我還是後悔自己不該提起什麽大象,這並非可以隨便嚮任何人開誠布公那種性質的話。
“過去,傢裏養的一隻貓倒是突然失蹤來着,”過了好久她開口道,“不過貓的失蹤和象的失蹤,看來不是一回事。”
“是啊,從大小來說就無法相比。”我說。
30分鐘,我們在賓館門口告別。她想起把傘丟在了酒吧,我乘電梯幫助她取回。傘是紅褐色的,花紋很大。
“謝謝了!”她說。
“晚安。”我說。
此後我和她再未見面。一次就刊登廣告的細節我們通過電話,那時我很想邀她一起吃飯,但終歸還是作罷。用電話講話的時間裏,驀地覺得這種事怎麽都無所謂。
自從經歷大象失蹤事件以來,我時常出現這種心情。每當做點什麽事情的時候,總是無法在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結果與回避這一行為所可能帶來的結果之間找出二者的差異。我往往感到周圍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這也許是我的錯覺。也許是大象事件之後自己內部的某種平衡分崩離析從而導致外部事物在我眼睛中顯得奇妙反常。責任怕是在我這一方。
我仍然在這急功近利式的世界上依據急功近利式的記憶殘片,到處推銷電冰箱、電烤爐和咖啡機。我越是變得急功近利,産品越是賣得飛快。我們的産品宣傳會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過了我們不無樂觀的預想。我於是得以為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許人們是在世界這個大廚室裏尋求某種諧調性吧。式樣的諧調,顔色的諧調,功能的諧調。
報紙幾乎不再有大象的報道。人們對於自己鎮上曾擁有一頭大象這點似乎都已忘得一幹二淨。仿若廣場上一度茂盛的雜草,業已枯萎,四周開始漾出鼕的氣息。
大象和飼養員徹底失蹤,再不可能返回這裏。
大象從鎮上的象捨中失蹤,我是從報紙上知道的。這天,我一如往常地被調至6點30分的鬧鐘叫醒。然後去廚房燒咖啡,烤面包片,打開超短波廣播,啃着面包片在餐桌上攤開晨報。我這人看報總是從第一版依序看下去,因此過了好半天才接觸到關於大象失蹤的報道。第一版報道的是日美貿易摩擦問題和戰略防禦構思,接下去是國內政治版,國際政治版,經濟版,讀者來信版,讀者專欄,不動産廣告版,體育版,再往下纔是地方版。
大象失蹤的報道登在地方版的頭條。標題相當醒目:“××鎮大象去嚮不明”。緊接着是一行小標題:“鎮民人心惶惶,要求追究管理責任”。還有幾名警察驗證無象象捨的照片。沒有象的象捨總好像不大自然。空空蕩蕩,冷冷清清,儼然被掏空五臟六腑後乾燥了的龐大動物。
我撥開落在報紙上的面包屑,專心緻志地逐行閱讀這則報道。上面說人們發現大象失蹤是5月18日(即昨天)下午2時。供食公司的人像往常那樣用卡車為大象運來食物(其主食為鎮立小學的學生們的剩飯),從而發現象捨空空如也。套在象腳上的鐵環依然上着鎖剩在那裏,看來是大象整個把腳拔了出去,失蹤的不僅僅是大象,一直照料大象的男飼養員也一同無影無蹤。
人們最後見到大象和飼養員是前天(即5月17日)傍晚5點多鐘。5個小學生來象捨寫生,5點多之前一直用蠟筆為大象畫像來着。這幾個小學生是大象的最後目擊者,後來再無人見到。因為6點鈴一響,飼養員便將象廣場的門關上,使人們無法入內。
5個小學生異口同聲地作證說,那時無論大象還是飼養員都沒顯出任何異常。大象一如往常乖乖站在廣場中央,不時左右搖晃一次鼻子,眯縫起滿是皺紋的眼睛。它已老態竜鐘,動一下身體都顯得甚是吃力。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馬上癱倒在地上斷氣。
以上便是這則新聞報道的內容。
大象之所以被本鎮(即我居住的鎮)領來飼養,也是因為其年老之故。鎮郊的一座小動物園以經營睏難為由關閉的時候,動物們都已通過動物經紀人之手轉往全國各地。唯獨這頭象由於年紀太老而無法找到主顧,一來哪裏的動物園中象的數量都綽綽有餘,二來沒一處動物園好事並充裕到足以接收一頭似乎馬上就心髒病發作死去的舉步維艱的大象的程度。因此,這頭象便在所有同伴蕩然無存的形同廢墟的動物園裏無所事事地——當然也不是說它原來有什麽事幹——獨自滯留三四個月之久。
無論動物園還是鎮上,對此都相當頭痛。動物園方面已將動物園舊址賣給了房地産商。房地商準備在此建造高層公寓,鎮上也簽發了開發許可證。象的處理越是長期拖而不决所付的利息越高。可是又不能把象殺掉。若是猴子或蝙蝠之類,倒也罷了。但殺一頭大象太容易暴露目標。一旦真相大白,問題就非同小可。於是三方一起商量,達成了關於老年大象處置的協議。(1)象作為鎮有財産免費領養;(2)收容象的設施由房地産商無償提供;(3)飼養員工資由動物園方面負擔。
這就是三方協議的內容。正好是一年前的事。
說起來,我從一開始便對“大象問題”懷有個人興趣。大凡有關象的報道我統統剪了下來。還去旁聽了鎮議會討論大象問題的會議。所以現在我纔可以如此灑脫如此準確地敘述此事的發展過程。話也許有些羅嗦,但“大象問題”的處理很可能同大象失蹤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還是容我記述下來為好。
當鎮長簽署了協議而即將領養大象之時,議會中以在野黨為中心(在此之前我還真不知道鎮議會中有什麽在野黨)掀起了反對運動。
“為什麽本鎮必須領養大象?”他們質問鎮長。其主張可以歸納成以下幾條(條條太多十分抱歉,但我以為這樣容易理解):(1)大象問題屬於動物園與房地産商私營企業之間的問題,鎮政府沒有理由參與;(2)所需管理費、食物費太多;(3)安全問題如何解决?(4)本鎮自費飼養大象的好處何在?
他們拉開論戰架勢——“飼養大象之前,下水道的整治和消防車的購置等鎮政府要做的事情豈非堆積如山?”儘管措詞不算尖刻,但言下之意無非是懷疑鎮長同房地産有幕後交易。
對此,鎮長的意見是這樣的:(1)高層建築群的落成在將極大幅度增加鎮的稅收,大象的飼養費之類自然不成問題,鎮政府參與這樣的項目是理所當然的;(2)象年事已高,食欲亦不很大,到於加害於人的可能性可以說等於零;(3)象一旦死亡,由房地産商作為大象飼養地提供的地皮即為鎮有財産;(4)象可成為鎮的象徵。
經過長時間爭辯討論,鎮上終於决定將大象領養過來。由於自古以來位於城郊住宅地帶,鎮上的居民大多生活較為富裕,鎮財政也夠雄厚。況且人們可以對領養無處可去的大象這一舉措懷有好感。較之下水道和消防車,居民畢竟更容易同情大象。
我也贊成鎮上飼養大象。出現高層建築群固然大殺風景,但自己鎮上能擁有頭大象倒確實不壞。
砍掉山坡上的樹林,把小學一座快要倒塌的體育館移建到這裏作為象捨。一直在動物園照料大象的飼養員跟過來住下。小學生們的殘湯剩飯充作象飼料。於是大象被一輛拖車從封閉的動物園運到新居,在此打發餘生。
我也參加了象捨的落成典禮。鎮長面對大象發表演說(關於本鎮的發展與文化設施的充實),小學生代表朗讀作文(象君,祝你永遠健康雲雲),舉行了大象寫生的評比展覽(大象寫生此後遂成為本鎮小學生美術教育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保留項目),身穿翩然飄然的連衣裙的兩名妙齡女郎(算不上絶代佳人)分別給大象吃了一串香蕉。大象則幾乎紋絲不動地靜靜忍受着這場相當乏味——起碼對象來說毫無意味——的儀式的進行,以近乎麻木不仁的空漠的眼神大口小口吃着香蕉。吃罷,衆人一齊拍手。
象右側的後腳套了一個堅不可摧的沉重鐵環。鐵環連着一條十多米長的粗鐵鏈。鐵鏈的另一端萬無一失地固定在水泥墩上。鐵環和鐵鏈一看就知道其牢不可破,大象縱然花100年時間使出渾身解數也全然奈何不得。
我不大清楚大象是否對這腳鐐心懷不滿。不過至少表面上它對套在自己腳上的鐵鏈漠然置之。它總是以愣愣的眼神望着空間莫可知曉的某一點。每當陣風吹來,耳朵和白色的體毛便輕飄飄搖顫不止。
負責飼養大象的是位瘦小的老人。不知其準確年齡,也許60多歲,也許70有餘。世上有一種人一旦越過某一臨界點便不再受年齡左右,這位老人便是其一。皮膚無論鼕夏都曬得又紅又黑,頭髮又短又硬,眼睛不大。面目並沒有什麽明顯特徵,唯獨嚮左右突出的接近圓形的耳朵使得整張臉相形見小,格外引人註目。
此人絶對談不上冷淡,有人搭話肯定給予圓滿回答,話也說得井井有條。若他願意,也能表現出一副熱情的樣子——儘管使我覺得有幾分勉強。不過原則說來,則像是位沉默寡言的孤獨老人。他看上去喜歡小孩。小孩來時盡可能親切相待,但孩子們卻不大接受老人的好意。
接受這位飼養員好意的衹有大象。他住在緊挨象捨的預製板小屋裏,從早到晚形影不離地照料大象。象與飼養員相處的時間已超過10年,二者關係的親密程度,衹消看雙方每個細微的動作和眼神,即可一目瞭然。飼養員如果想讓呆呆站在同一地方的大象移動一下,衹要站在象的旁邊用手啪啪地輕拍幾下它的前腳並嘀咕一句什麽,大象便不堪重負似地慢慢搖擺着身體,準確移至指定位置,隨即仍如剛纔那樣註視空間的某一點。
每到周末,我就去象捨細心觀察這情形,但還是不能完全理解二者的交流是依據何種原理得以實現的。大象或許能聽懂簡單的人語(畢竟活的時間長),也可能通過拍腳方式來把握對方的意圖。或者具有心靈感應那類特異功能因而懂得飼養員的所思所想也未可知。
一次我問老人;“您是怎樣給大象下命令的呢?”老人笑笑,衹回答“長時間相處的關係”,再沒做更多的解釋。
總之便是這樣平安無事地過了一年,此後象突然失蹤。
我一邊喝第二杯咖啡,一邊將報道再次從頭研究一遍。文章寫得相當奇妙,儼然福爾摩斯敲着煙斗說:“華生,快看呀,這篇報道太有趣了!”
此報道給人以奇妙印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可能支配寫報道記者大腦的睏惑與混亂。而睏惑與混亂顯然起因於情況的非條理性。記者力圖巧妙避開條非理性來寫一篇“地道的”新聞報道,但這反而將他自身的混亂與猶豫推嚮致命的地步。
例如,報道上的措詞是“大象逃脫”。可是通觀全篇報道,顯而易見大象並非什麽逃脫,而明明是“失蹤”。記者將這種自我矛盾表述為“細節上仍有若幹不明確之處”。我則無論如何不認為事情是可以用什麽“細節”什麽“不明確”這類老生常談的字眼敷衍得了的。
首先,問題出在象腳上套的鐵環。鐵環依然上着鎖剩在那裏。最穩妥的推論是:飼養員用鑰匙打開鐵環從象腳摘下,然後又將其鎖好,同象一起逃跑(當然報紙也認識到了這種可能性)。問題是飼養員手中沒有鑰匙。鑰匙僅有兩把。一把為確保安全藏於警察署的保險櫃,另一把收在消防署的保險櫃之中。飼養員(或其它什麽人)不大可能從中偷出鑰匙。縱使萬一偷出,也大可不必把用過的鑰匙特意送回保險櫃——翌日早打開一看,兩把鑰匙全都好好躺在警察署和消防署的保險櫃裏。既然這樣,那麽就是說大象勢必在不使用鑰匙的情況下將腳從堅不可摧的鐵環中撥出,而這除非用鋸將象腿鋸斷,否則絶無可能。
第二個問題是出逃的途徑。象捨與“象廣場”圍了3米多高的堅固柵欄。由於象的安全管理在鎮議會上爭論得沸沸揚揚,鎮政府采取了對一頭老象未免小題大做的警備措施。柵欄是用混凝土和粗鐵棍做成的(費用當然由房地産商出),門口衹有一個,且內側上鎖。象不可能跨過如此要塞般的柵欄跑到外面。
第三個問題是象的足跡。象捨後面是陡峭的山坡,象無法攀登。因此象假如真的用某種手段飛越柵欄,它也衹能經前面的道路逃走。然而鬆軟的沙土路面上沒有留下任何類似象腳印的痕跡。
總而言之,綜合分析這篇滿是令人睏惑和不快措詞的新聞報道,根本看不出事件的結論或實質。
當然,自不待言,報紙也好警察也好鎮長也好至少表面上都不願意承認大象失蹤這一事實。警察正以“象或許被人采取錦囊妙計早有預謀地強行掠出,或許自行逃脫”這樣的判斷進行偵查,並樂觀地預測:“考慮到隱藏大象的睏難程度,事件的解决不過是時間問題”警察還打算請求近郊的獵友會以及自衛隊狙擊部隊出動,一起搜山。
鎮長召開記者招待會(有關記者招待會的報道沒有登在地方版,而出現在全國版的社會版面),就鎮政府警備措施上的疏忽進行道歉。同時鎮長又強調指出:“同全國任何一座動物園的同類設施相比,本鎮的大象管理體製都毫不遜色,較之標準有力得全面得多。”還說:“這是充滿惡意的、危險而且無聊的反社會行為,是絶對不能允許的!”
在野黨的議員重複一年前的論調:“務必追究鎮長同企業串通一氣而將鎮民輕易捲入象處理問題的政治責任。”
一位母親(39歲)以“不安的神情”說:“短時間內不能放心地讓孩子去外面玩了。”
報紙上敘述了本鎮領養大象的前後詳細經過,並附有大象收容設施示意圖。還介紹了大象簡歷,以及同象一起失蹤的飼養員(渡邊升,63歲)的情況。渡邊飼養員是千葉縣館山人,長期在動物園飼養哺乳動物,“由於動物知識豐富為人忠厚誠實,深得有關人員信賴”。象是22年前由非洲東部送來的。準確年齡無人知曉,其為人更是不得而知。
報道的最後,說警察正在嚮鎮民徵求有關大象任何形式的情報。我一面喝第二聽啤酒,一面就此沉思片刻。終歸還是决定不給警察打電話。一來我不大樂意同警察發生關係,二來我不認為警察會相信我提供的情報。嚮那些甚至沒有認真設想過大象失蹤可能性的傢夥,無論說什麽都是徒勞。
我從書架中抽出剪報集,將從報紙上剪下的關於象的報道夾在裏面。隨後洗了洗杯子碟子,去公司上班。
我從nhk晚上7時的新聞節目中看到了搜山的情況。提着裝滿麻醉彈大型來福槍的獵手、自衛隊和警察們把附近的山一個接一個颳篦子似地搜刮一遍,好幾架直升飛機在空中盤旋。雖說是山,但都位於東京郊外的住宅地邊緣,不過是小山包而已。聚集如此之衆,衹消一天即可基本搜尋完畢,再說尋找的對象又不是矮小的殺人鬼而是巨大的非洲象,其可藏身之處自然有限。然而折騰到傍晚也沒找到大象。出現在電視熒屏中的警察署長聲稱“仍將繼續搜尋”。電視新聞的主持人總結道:“是何人如何使大象逃脫,藏於何處,其動機何在,一切都還在深深處於迷宮之中”
此後繼續搜尋數日,大象依舊蹤影皆無,當局連點蛛絲馬跡也未能找到。我每天都細看報紙的報道,大凡所能見到的報道統統用剪刀裁剪下來。就連以大象事件為題材的漫畫也不放過。由此之故,剪報集的容量很快到達極限,而不得不去文具店買一册新的回來。儘管擁有如此數量繁多的報道,卻不包括任何一條我想知道的那類事實。報上寫的全都是些驢唇不對馬嘴一文不值的內容,諸如什麽“依然下落不明”,什麽“搜查人員深感苦惱”,什麽“背後是否有秘密組織”等等。大象失蹤了一周之後,這方面的報道日見減少,直至幾乎銷聲匿跡。周刊上倒是刊載了幾篇嘩衆取寵的報道,有的竟拉出算命先生來,不久也草草收兵了。看上去人們似乎企圖將大象事件強行歸為擁有不少會員的“不解之謎俱樂部”這一範疇之中。一頭年老的象和一個年老的飼養員縱使從這塊土地失去蹤影,也不會對社會的趨勢造成任何影響。地球照樣單調地旋轉,政治傢照樣發表不大可能兌現的聲明,人們照樣打着哈欠去公司上班,孩子們照樣準備應付考試。在這周而復始無休無止的日常波浪之中,人們不可能對一頭去嚮不明的老象永遠興致勃勃。如此一來二去,沒有什麽特殊變異的這幾個月便像窗外行進的疲於奔命的軍隊一樣匆匆過去。
我不時抽時間跑去往日的象捨,觀望已無大象的大象住處。鐵柵欄門上纏了好幾道粗大的鐵鏈,任憑誰都無從入內。從柵欄空隙窺視,象捨門仍被鐵鏈纏繞着。看樣子警察為了彌補無法找見大象所造成的缺憾,而對失去大象後的象捨加強了不必要的警備。四下寂寥,空無人影,唯見一群鴿子在象捨房脊上斂翅歇息。廣場已無人修剪,開始長滿萋萋夏草,仿佛已等得忍無可忍。象捨門上纏繞的鐵鏈使人聯想起森林中牢牢看守着已腐朽得化為廢墟的王宮的巨蟒。大象離去纔不過數月,這場所便蒙上了帶有某種宿命意味的荒涼面影,籠罩在雨雲一般令人窒息的氣氛中。
我那次見到她,9月都已接近尾聲了。這天從早到晚雨下個不停。雨單調而又溫柔細膩,是這一季節常見的雨,它將在地面打下烙印的夏日記憶一點點衝掉。所有的記憶都沿着水溝往下水道往河道流去,進入又黑又深的大海。
我倆是在我公司舉行的産品宣傳酒會上見面的。我在一傢大型電機公司廣告部工作,當時正負責推銷為配合秋季結婚熱和鼕季發奬金時節而生産的係列型廚房電氣用品。主要任務是同幾傢婦女雜志交涉,以使其刊載配合性報道。事情倒不怎麽需要動腦,但須註意對方報道寫得不失分寸,以盡量不讓讀者嗅到廣告味。作為代價,我們可以在雜志上刊登廣告。世上的事就是要互相扶持。
她是一傢以年輕主婦為對象的雜志的編輯,參加酒會是為了采訪——明知是為人推銷的采訪。我正好閑着,便以她為對象,開始講解由意大利著名設計師設計的彩色電冰箱、咖啡機、微波爐和榨汁機。
“至為關鍵的是諧調性。”我說,“無論式樣多好的東西,都必須同周圍保持諧調,不然毫無意思。顔色的諧調,式樣的諧調,功能的諧調——這是當今廚室最需要註意的。據調查,一天之中主婦在廚室的時間最長。對主婦來說,廚室是她的工作崗位,是書齋,是起居室。因此她們都在努力改善廚室環境,使其多少舒服一點。這與大小沒有關係。無論大小,好的廚室原則都衹有一個。那就是簡潔性、功能性、諧調性。而本係列便是依據這一指導思想設計出來的。舉例說來,請看這個烹調板……”
她點着頭,在小筆記本上做着記錄。其實她並非對這類采訪特別懷有興趣,我對烹調板也沒什麽偏愛,我們不過在完成各自的工作而已。
“看來你對廚房裏的事相當熟悉。”她在我講解完後說道。
“工作嘛!”我做出商業性笑容回答。“不過我倒是很喜歡做菜——這與工作無關——做的簡單,但天天做。”
“廚房真的需要諧調性?”她問。
“不是廚房,是廚室。”我糾正道。“本來怎麽都所謂,可公司有這樣那樣的規定。”
“對不起。那麽廚室真的需要諧調性?是你個人的意見?”
“至於我的意見,不解掉領帶是無可奉告的。”我笑着說,“不過今天算是例外。我想就廚室來說,講究諧調性之前,應該備有若幹必不可少的東西。問題是那種因素成不了商品。而在這急功近利的世界上,成不了商品的因素幾乎不具有任何意義。”
“世界果真是急功近利的不成?”
我從衣袋裏掏出香煙,用打火機點燃。
“隨便說說罷了。”我說,“這樣一來,很多事情就容易明白,工作也容易進行。這類似一種遊戲,或曰本質上急功近利,或曰急功近利式的本質——說法五花八門。而且衹有這樣認為,纔不至於招風惹浪,纔不至於出現復雜問題。”
“妙趣橫生的見解!”
“談不上什麽妙趣,人人都這樣看待。”我說,“對了,有一種香檳不算很壞,如何?”
“謝謝,恕不客氣。”
隨後,我和她邊喝香檳邊海闊天空地聊起來,聊着聊着,聊出幾個兩人共同的熟人。不僅如此,我的妹妹同她碰巧畢業於同一所大學。我們於是以幾個這樣的名字為綫索較為順利地展開話題。
她也罷我也罷都是單身。她26,我31。她戴隱形眼鏡,我架着普通鏡片。她贊賞我領帶的顔色,我誇奬她的上衣。我們談起各自所居公寓的租金,也就工資數額和工作內容發了些牢騷。總之我們是相當親密起來了。她是位顧盼生輝的嫵媚女性,絲毫沒有強加於人的味道。我站着同她在那裏談了大約20分鐘,沒有發現任何不可以對她抱有好感的理由。
酒會快結束時,我邀她走進同一賓館裏的酒吧,坐在那裏同她繼續交談。透過酒吧巨大的窗扇,可以看見初秋的雨幕。雨依然無聲無息地下着,遠處街道的光亮糅合着各種各樣的信息。酒吧裏幾乎見不到客人,潮乎乎的沉默統治着四周。她要了達伊吉莉雞尾酒,我要的是加冰蘇格蘭威士忌。
我們一邊喝着各自的杯中物,一邊像多少有些親密起來的初次見面的男女那樣說着在酒吧裏常說的話:大學時代,喜歡的音樂,體育,日常習慣等等。
接着,我提起大象。至於話題為什麽突然轉到大象身上,我已記不起其中關聯。大概談到某種動物,由此聯上了大象。也有可能我是極其無意識地想嚮某人——似可與之暢所欲言的一個人——闡述我對大象失蹤的看法。或者是僅僅藉助酒興也未可知。
話一出口,我便意識到自己提出的是現在最不適宜的話題。我不應該談起什麽大象。怎麽說呢,這個話題早已成為過去。
於是我想馬上收回話頭。糟糕的是她對大象失蹤事件懷有非同一般的興致。我一說自己看過好幾回大象,她便連珠炮似地發出質詢:
“什麽樣的象?你認為是如何逃跑的?平時它吃什麽?有沒有危險?”如此不一而足。對此,我按照報紙上的口徑輕描談寫地解說了一遍。看樣子她從我的口氣中感覺出了異乎尋常的冷淡——我從小就很不善於敷衍。
“象不見的時候大吃一驚吧?”她喝着第二杯達伊吉莉,若無其事地問。“一頭大象居然突然失蹤,肯定誰都始料未及。”
“是啊,或許是。”我拿起一枚碟子裏的炸薯片,分成兩半,吃了一半。男侍轉來,另換了一個煙灰缸。
她饒有興味地註視了一會我的臉。我又叼起一支香煙點燃。本來戒煙已有3年之久,而在大象失蹤之後,又開始重操舊業。
“所謂或許是,就是說關於大象失蹤多少有所預料?”她問。
“談不上什麽預料!”我笑了笑,“一天大象突然消失,這既無先例又無必然性,也不符合事理。”
“不過你這說法可是非常奇特,嗯?我說‘一頭大象居然突然失蹤,肯定誰都始料未及’,你回答‘是啊,或許是’。而一般人是絶不至於這樣回答的。或者說‘一點不錯’,或者說‘說不明白’。”
我嚮她含糊地點了下頭,揚手叫來男侍,讓他再送一杯蘇格蘭威士忌。等威士忌的時間裏,我們暫且保持沉默。
“我說,我不大理解,”她用沉靜的口氣說,“剛纔你還一直說得頭頭是道,在提起大象之前。可一提起大象,你說話就好像一下子變得反常。聽不出你想表達什麽。到底怎麽回事?莫非在大象上面有什麽不好啓齒的地方?還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呢?”
“你的耳朵沒有毛病。”我說。
“那麽說問題在你羅?”
我用手指把酒杯裏的冰塊撥弄得旋轉不止。我喜歡聽冰塊相撞的聲音。
“並未嚴重得要用問題這個字眼。”我說,“不足挂齒的小事。也沒有什麽可嚮別人隱瞞的,不過是因為我沒有把握說透而沒說罷了。如果說是奇特,也確實有點奇特。”
“怎麽奇特?”
我再無退路,衹好喝口威士忌,開始敘說:
“其中一點要指出的是,我恐怕是那頭失蹤大象的最後一個目擊者。我見到大象是5月17日晚上7點左右,得知大象失蹤是第二天近午時分。這段時間再沒有人見過大象。因為傍晚6點象捨就關門了。”
“邏輯上不好明白。”她盯住我的眼睛,“既然象捨已經關門,你怎麽還能見到大象呢?”
“象捨後面是一座懸崖樣的小山。山是私有山,沒有像樣的路可走,上面衹有一個地方可以從後面窺視象捨。而知道這個地方的,想必衹我一人。”
我這一發現完全出於偶然。一個周日下午,我去後山散步迷了路。大致判斷方位行走之間,碰巧走到了這個地方。那是塊平地,大小可供一個睡覺。透過灌木叢空隙朝下一望,下面正是象捨的房脊。房脊稍往下一點有個相當大的通風口,從中可以清楚看到象捨裏面的光景。
從此以後,我經常去那裏觀望進入象捨裏邊的大象,逐漸成了習慣。如果有個問何苦如此不厭其煩,我也回答不好。衹是想看大象的私下表現而已,沒有什麽深刻的理由。
象捨裏黑暗之時,自然看不見大象。但剛入夜時飼養員打開象捨電燈為大象做這做那,我因之得以一一看在眼裏。
我最先註意到的,是象捨中衹剩大象與飼養員時,看上要比在人前那種公開場合表現得遠為親密無間。這點衹消看他們之間一個小小的舉動即可一目瞭然。甚至使人覺得白天時間他們有意剋製感情,以免被人看出彼此的親密程度,而到單獨相守的夜晚便完全無此顧慮。但這不等於說他們在象捨中有什麽特殊舉動。進入象捨之後,大象依然一副呆愣愣的樣子,飼養員也一味地忙他作為飼養員的當務之急:用甲板刷給大象刷洗身體,歸攏拉在地板上的巨大糞團,收拾其吃過的東西。儘管如此,其彼此間結下的信賴感所釀出的獨特的溫馨氛圍不容你無動於衷。飼養員打掃完地板,大象便搖晃着身子在飼養員背部輕輕叩擊幾下。我很喜歡觀看大象的這個動作。
“以前你就喜愛大象?我是說不僅僅限於這頭象……”她問。
“是的,我想是這樣。”我說,“大象這種動物身上有一種撥動我心弦的東西,很早以前就有這個感覺,原因我倒不清楚。”
“所以那天也同樣傍晚一人登後山看象去了,是吧?”她說,“呃——5月……”
“17日,”我接道,“5月17日晚上7點左右。那時節白天變得很長,空中還剩有一點火燒雲。不過象捨裏已經燈火通明。”
“當時象和飼養員都沒有什麽異常?”
“既可以說沒有異常,又可以說有異常。我無法說得準確。因為畢竟不是相距很近。作為目擊者的可靠性也可以說不是很高。”
“到底發生了什麽?”
我喝了一口因冰塊融化而酒味變淡的威士忌。窗外的雨仍下個不止,既不大下,又不小下,儼然一幅永遠一成不變的靜物畫。
“也不是說發生了什麽。”我說,“象和飼養員所作所為一如往常。掃除,吃東西,親昵地挑逗一下,如此而已。平日也是如此。我感到不對頭的衹是其平衡。”
“平衡?”
“就是大小平衡,象和飼養員身體大小的比例。我覺得這種比例較之平時多少有所不同,兩者之差似乎比平時縮小一些。”
她把視綫投在自己手中的達伊吉莉杯上,靜靜註視良久。杯裏冰塊已經化了,如細小的海流試圖鑽進雞尾酒的間隙中去。
“那麽說象的身體變小了?”
“也許是飼養員變大了,也可能雙方同時變化。”
“這點沒告訴警察?”
“當然沒有。”我說,“即使告訴,警察也不會相信,況且我若說出在那種時候從後山看大象,自己都難免受到懷疑。”
“那,比例與平時不同這點可是事實?”
“大概。”我說,“我衹能說是大概。因為沒有證據,而且我說過不止一次——我是從通風口往裏窺的。不過我在同一條件下觀看大象和飼養員不下數十次,我想總不至於在其大小比例上發生錯覺。”
噢,也許眼睛有錯覺。當時我好幾次閉目搖頭,但無論怎麽看象的體積都與平時不同,的確有些縮小。以至一開始我還以為鎮上搞來一頭小象呢。可是又沒聽說過(我絶不會放過有關象的新聞)。既然如此,那麽衹能認為是原來的老象由於某種原因而驟然萎縮。而且仔細看去,象高興似地擡右腳叩擊地面,用多少變細的鼻子撫摸飼養員的後背。
那光景甚是不可思議。從通風口密切註視裏面的時間裏,我覺得象捨之中仿佛流動着唯獨象捨纔有的冷冰冰的另一種時間,並且象和飼養員似乎樂意委身於將彼此捲入——至少已捲入一部分——其中的新生體係。
我註視象捨的時間總共不到30分鐘。象捨的燈比往常關得早,7時30分燈便熄了,所有一切都籠罩在黑暗之中。我在那裏等了一會,等待象捨的燈重新閃亮,但再未閃亮。這便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大象。
“那麽說,你是認為象就勢迅速萎縮變小而從柵欄空隙逃走了?還是認為完全消失了呢?”她問。
“不清楚。”我說,“我衹是力圖多少準確地記起自己親眼見過的場面,此外的事幾乎沒有考慮。眼睛獲得的印象實在太強烈了,坦率地說,我恐怕根本無法從中推導出什麽。”
以上就是我關於大象失蹤說的所有的話。不出我最初所料,這些話作為剛剛相識的年輕男女交談的話題未免過於特殊,況且其本身早已完結。說罷,兩人之間出現了許久的沉默。在談完與其他事幾乎毫不相關的大象失蹤的話之後,我也罷她也罷都不知再提起什麽話題為好。她用手指摩挲雞尾酒杯的邊緣。我則看着杯墊上的印字。反復看了25遍。我還是後悔自己不該提起什麽大象,這並非可以隨便嚮任何人開誠布公那種性質的話。
“過去,傢裏養的一隻貓倒是突然失蹤來着,”過了好久她開口道,“不過貓的失蹤和象的失蹤,看來不是一回事。”
“是啊,從大小來說就無法相比。”我說。
30分鐘,我們在賓館門口告別。她想起把傘丟在了酒吧,我乘電梯幫助她取回。傘是紅褐色的,花紋很大。
“謝謝了!”她說。
“晚安。”我說。
此後我和她再未見面。一次就刊登廣告的細節我們通過電話,那時我很想邀她一起吃飯,但終歸還是作罷。用電話講話的時間裏,驀地覺得這種事怎麽都無所謂。
自從經歷大象失蹤事件以來,我時常出現這種心情。每當做點什麽事情的時候,總是無法在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結果與回避這一行為所可能帶來的結果之間找出二者的差異。我往往感到周圍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這也許是我的錯覺。也許是大象事件之後自己內部的某種平衡分崩離析從而導致外部事物在我眼睛中顯得奇妙反常。責任怕是在我這一方。
我仍然在這急功近利式的世界上依據急功近利式的記憶殘片,到處推銷電冰箱、電烤爐和咖啡機。我越是變得急功近利,産品越是賣得飛快。我們的産品宣傳會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過了我們不無樂觀的預想。我於是得以為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許人們是在世界這個大廚室裏尋求某種諧調性吧。式樣的諧調,顔色的諧調,功能的諧調。
報紙幾乎不再有大象的報道。人們對於自己鎮上曾擁有一頭大象這點似乎都已忘得一幹二淨。仿若廣場上一度茂盛的雜草,業已枯萎,四周開始漾出鼕的氣息。
大象和飼養員徹底失蹤,再不可能返回這裏。
總之我們應該處於饑餓狀態。不,不是肚子餓,簡直像吞下了宇宙的空白一樣的心情。起先其實是小小的,像甜甜圈中間的洞一樣的小空白,但隨着日子的消逝,它在我們的身體裏漸漸增殖,終於成為不見底的虛無。成為莊重的幕後音樂般的空腹金字塔。
為什麽産生了空腹感呢?當然是由於缺乏食物而來。為什麽會缺乏食物呢?因為沒有相當的等價交換物呢?這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想象力不夠吧。不,空腹感說不定事實上是起因於想象力不足。
無論怎麽說都行。
神、馬剋斯、約翰.藍儂都死了。總之,我們處於肚子饑餓的狀態,結果就是起了歹念、並非空腹感使我們起了歹念,而是歹念使我們為空腹感而走極端。雖然不怎麽搞得清楚,就像存在主義似的。
“唉,我要走下坡路了。”夥伴說。簡單說來他的話意便是如此。
也難怪,我們已整整兩天衹喝水,有一次吃了嚮日葵的葉子,但實在不想再吃了。
因此我們手持菜刀去面包店。面包店在那條商店街的中央,兩鄰是棉被店和文具店。面包店老闆是一個禿頭年逾五十歲的共産黨員。
我們手持菜刀,從容由商店街走嚮面包店,像“日正當中”的感覺。走着走着,漸漸聞到烤面包香。而面包味越濃,我們走嚮邪路的傾斜度越深。襲擊面包度和襲擊共産共産黨員使我們興奮,兩件事同時做,心裏涌起了一種像納粹青年團似的感動。
下午時間不早了,面包店內衹有一個客人,是一個提着舊購物袋、不太機靈的中年歐巴桑。歐巴桑的周圍散發着危險的氣氛。犯罪者的計畫性罪行,往往被不機靈的歐巴桑搞砸了,電視上的犯罪總是如此。我嚮夥伴使個眼神,示意在歐巴桑離開面包店之前,不要有任何舉動。我把菜刀藏在身後,裝出選購面包的樣子。
歐巴桑挑選面包慢得令人昏倒,她如同選購衣櫥和三面鏡般,慎重地把油炸酥皮面包和果醬餡面包夾到淺盤上。但並不是馬上買了結帳,油炸酥皮面包和果醬面包對她來說,不啻是一個論題。或者是遙遠的北極,必須讓她有一段適應的時間。
隨着時間的消逝,首先果醬餡面包從論題的地位滑落下來。為什麽我挑選了果醬面包呢,她搖搖頭,不應該選這種面包的,因為它太甜。
她把果醬面包放回原來的架子上,稍微考慮一下,輕輕夾了兩個新月形面包到淺盤上。新的論題誕生了。冰山微露,春天的陽光從雲層間射下來。
“她還沒挑選好嗎?”我的夥伴小聲說:“連這個老太婆也別放過吧。”
“且慢!”我阻止他。
面包店老闆不管我們,出神地聽着收錄音機裏卡式錄音帶流出的華格納的麯子。共産黨員聽華格納的麯子是否正確,我倒不知道。
歐巴桑依然望着新月形面包和油炸酥皮面包發呆。感覺有點兒奇怪,不自然。新月形面包和油炸酥面包看來根本不可以排成同列。她的樣子像是感覺兩者有什麽相反的思想。宛若冷度調節裝置故障的電冰箱般,放着面包的淺盤在她手上嘎吱嘎吱搖動。當然不是真的搖動,完全是比喻式的--搖動。嘎吱嘎吱嘎吱。
“幹掉吧!”夥伴說。空腹感和華格納和歐巴桑散發出的緊張,使他變得像桃子毛一般敏感。我默默地搖頭。
歐巴桑依然手拿着淺盤,在杜斯妥也夫斯基式的地獄裏彷徨。油炸酥皮面包首先站上演講臺,嚮羅馬市民發表動人心弦的演講。優美的辭句,漂亮的雄辯術、聲音渾厚的男中音......大傢劈劈啪啪鼓掌。其次新月形面包站上演講臺,發表什麽關於交通信號的不得要領的演說。左轉車要看正面的緑燈信號直進,確定有無對嚮車再左轉,諸如此類的演說辭,羅馬市民雖然不大瞭解,但覺得它本來就是難懂的道理,而劈劈啪啪鼓掌。新月形面包獲得的掌聲稍微大些。於是油炸酥皮面包回到原來的架子上。
歐巴桑的淺盤裏極單純的完壁造訪--新月形面包兩個。
於是歐巴桑走出店外。
接下來輪到我們了。
“我們肚子很餓。”我坦白對老闆說。菜刀仍然藏在身後。“而且身無分文。”
“是嗎?”老闆點點頭。
櫃臺上放着一把指甲刀,我們兩人註視着那把指甲刀。那把巨大的指甲刀幾乎可以用來剪禿鷹的爪子,大概是為了開什麽玩笑而造的。
“既然肚子那麽餓,你們吃面包吧!”老闆說。
“可是我們沒有錢。”
“剛纔我聽到了。”老闆感覺無聊般的說。“不要錢,隨便你們吃。”
我再看一眼指甲刀。“可是,我們走上了邪路。”
“嗯嗯。”
“所以我們不接受別人的施捨。”
“嗯。”
“是這樣的。”
“是嗎?”老闆又點點頭。“那麽這樣吧。隨便你們吃面包。但讓我詛咒你們,這樣好嗎?”
“詛咒?怎樣的詛咒?”
“詛咒總是不確實的,但和公共汽車的時刻表不同。”
“喂、且慢!”夥伴插嘴。“我不願意被詛咒。索性把你殺了。”
“且慢且慢。”老闆說:“我不願意被殺。”
“我不願意被詛咒。”夥伴說。
“不過,可以用什麽來做為交換。”我說。
我們望着指甲刀瀋默着。
“怎樣?”老闆開口:“你們喜歡華格納的麯子嗎?”
“不。”我說。
“不喜歡。”夥伴說。
“如果你們喜歡,就讓你們吃面包。”
這話活像是黑暗大陸的傳教師說的,但我立刻同意了。至少比被詛咒強得多。
“喜歡。”我說。
“我喜歡。”夥伴說。
於是我們一邊聽着華格納的麯子,一邊吃面包填飽肚子。
“這出在音樂史上光輝燦爛的‘崔斯坦與易梭德’歌劇,發表於一八五九年,是理解後期華格納不可缺少的重要作品。”老闆讀着解說書。
“嗯哼。”
“噢噢。”
“康古爾國王的侄子崔斯坦代叔父去迎娶已訂婚的易梭德公主,但歸途在船上崔斯坦和易梭德陷入情網。開頭大提琴和雙簧管所奏出的美麗的主題,是這兩個人的愛的旋律。”
兩個小時後,我們彼此滿意地告別。
“明天來聽‘唐懷瑟’(華格納著名的歌劇tannhauser)”老闆說。
回到傢裏,我們心中的虛無感已完全消失了,而想象力就像從慢坡上咕嚕咕嚕滾落下去一般,開始活躍起來。
譯/黃玉燕
取自中國時報
為什麽産生了空腹感呢?當然是由於缺乏食物而來。為什麽會缺乏食物呢?因為沒有相當的等價交換物呢?這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想象力不夠吧。不,空腹感說不定事實上是起因於想象力不足。
無論怎麽說都行。
神、馬剋斯、約翰.藍儂都死了。總之,我們處於肚子饑餓的狀態,結果就是起了歹念、並非空腹感使我們起了歹念,而是歹念使我們為空腹感而走極端。雖然不怎麽搞得清楚,就像存在主義似的。
“唉,我要走下坡路了。”夥伴說。簡單說來他的話意便是如此。
也難怪,我們已整整兩天衹喝水,有一次吃了嚮日葵的葉子,但實在不想再吃了。
因此我們手持菜刀去面包店。面包店在那條商店街的中央,兩鄰是棉被店和文具店。面包店老闆是一個禿頭年逾五十歲的共産黨員。
我們手持菜刀,從容由商店街走嚮面包店,像“日正當中”的感覺。走着走着,漸漸聞到烤面包香。而面包味越濃,我們走嚮邪路的傾斜度越深。襲擊面包度和襲擊共産共産黨員使我們興奮,兩件事同時做,心裏涌起了一種像納粹青年團似的感動。
下午時間不早了,面包店內衹有一個客人,是一個提着舊購物袋、不太機靈的中年歐巴桑。歐巴桑的周圍散發着危險的氣氛。犯罪者的計畫性罪行,往往被不機靈的歐巴桑搞砸了,電視上的犯罪總是如此。我嚮夥伴使個眼神,示意在歐巴桑離開面包店之前,不要有任何舉動。我把菜刀藏在身後,裝出選購面包的樣子。
歐巴桑挑選面包慢得令人昏倒,她如同選購衣櫥和三面鏡般,慎重地把油炸酥皮面包和果醬餡面包夾到淺盤上。但並不是馬上買了結帳,油炸酥皮面包和果醬面包對她來說,不啻是一個論題。或者是遙遠的北極,必須讓她有一段適應的時間。
隨着時間的消逝,首先果醬餡面包從論題的地位滑落下來。為什麽我挑選了果醬面包呢,她搖搖頭,不應該選這種面包的,因為它太甜。
她把果醬面包放回原來的架子上,稍微考慮一下,輕輕夾了兩個新月形面包到淺盤上。新的論題誕生了。冰山微露,春天的陽光從雲層間射下來。
“她還沒挑選好嗎?”我的夥伴小聲說:“連這個老太婆也別放過吧。”
“且慢!”我阻止他。
面包店老闆不管我們,出神地聽着收錄音機裏卡式錄音帶流出的華格納的麯子。共産黨員聽華格納的麯子是否正確,我倒不知道。
歐巴桑依然望着新月形面包和油炸酥皮面包發呆。感覺有點兒奇怪,不自然。新月形面包和油炸酥面包看來根本不可以排成同列。她的樣子像是感覺兩者有什麽相反的思想。宛若冷度調節裝置故障的電冰箱般,放着面包的淺盤在她手上嘎吱嘎吱搖動。當然不是真的搖動,完全是比喻式的--搖動。嘎吱嘎吱嘎吱。
“幹掉吧!”夥伴說。空腹感和華格納和歐巴桑散發出的緊張,使他變得像桃子毛一般敏感。我默默地搖頭。
歐巴桑依然手拿着淺盤,在杜斯妥也夫斯基式的地獄裏彷徨。油炸酥皮面包首先站上演講臺,嚮羅馬市民發表動人心弦的演講。優美的辭句,漂亮的雄辯術、聲音渾厚的男中音......大傢劈劈啪啪鼓掌。其次新月形面包站上演講臺,發表什麽關於交通信號的不得要領的演說。左轉車要看正面的緑燈信號直進,確定有無對嚮車再左轉,諸如此類的演說辭,羅馬市民雖然不大瞭解,但覺得它本來就是難懂的道理,而劈劈啪啪鼓掌。新月形面包獲得的掌聲稍微大些。於是油炸酥皮面包回到原來的架子上。
歐巴桑的淺盤裏極單純的完壁造訪--新月形面包兩個。
於是歐巴桑走出店外。
接下來輪到我們了。
“我們肚子很餓。”我坦白對老闆說。菜刀仍然藏在身後。“而且身無分文。”
“是嗎?”老闆點點頭。
櫃臺上放着一把指甲刀,我們兩人註視着那把指甲刀。那把巨大的指甲刀幾乎可以用來剪禿鷹的爪子,大概是為了開什麽玩笑而造的。
“既然肚子那麽餓,你們吃面包吧!”老闆說。
“可是我們沒有錢。”
“剛纔我聽到了。”老闆感覺無聊般的說。“不要錢,隨便你們吃。”
我再看一眼指甲刀。“可是,我們走上了邪路。”
“嗯嗯。”
“所以我們不接受別人的施捨。”
“嗯。”
“是這樣的。”
“是嗎?”老闆又點點頭。“那麽這樣吧。隨便你們吃面包。但讓我詛咒你們,這樣好嗎?”
“詛咒?怎樣的詛咒?”
“詛咒總是不確實的,但和公共汽車的時刻表不同。”
“喂、且慢!”夥伴插嘴。“我不願意被詛咒。索性把你殺了。”
“且慢且慢。”老闆說:“我不願意被殺。”
“我不願意被詛咒。”夥伴說。
“不過,可以用什麽來做為交換。”我說。
我們望着指甲刀瀋默着。
“怎樣?”老闆開口:“你們喜歡華格納的麯子嗎?”
“不。”我說。
“不喜歡。”夥伴說。
“如果你們喜歡,就讓你們吃面包。”
這話活像是黑暗大陸的傳教師說的,但我立刻同意了。至少比被詛咒強得多。
“喜歡。”我說。
“我喜歡。”夥伴說。
於是我們一邊聽着華格納的麯子,一邊吃面包填飽肚子。
“這出在音樂史上光輝燦爛的‘崔斯坦與易梭德’歌劇,發表於一八五九年,是理解後期華格納不可缺少的重要作品。”老闆讀着解說書。
“嗯哼。”
“噢噢。”
“康古爾國王的侄子崔斯坦代叔父去迎娶已訂婚的易梭德公主,但歸途在船上崔斯坦和易梭德陷入情網。開頭大提琴和雙簧管所奏出的美麗的主題,是這兩個人的愛的旋律。”
兩個小時後,我們彼此滿意地告別。
“明天來聽‘唐懷瑟’(華格納著名的歌劇tannhauser)”老闆說。
回到傢裏,我們心中的虛無感已完全消失了,而想象力就像從慢坡上咕嚕咕嚕滾落下去一般,開始活躍起來。
譯/黃玉燕
取自中國時報
原載:《面包屋再襲擊》.皇冠出版
■譯者:許珀理
那個女人打電話來時,我正站在廚房裏煮着通心粉。在通心粉煮好之前,我和着fm電臺的音樂,吹着羅西尼“鵲賊”序麯的口哨,這是煮通心粉時最合的音樂。
電話鈴響時,我原本不想理會它,繼續煮我的通心粉,因為面快煮好了,而且收音機裏又播放着我最喜歡的倫敦交響樂團的麯子。但是,我還是將瓦斯的火關小一點,右手拿着筷子,到客廳裏去接電話,因為我突然想到或許有朋友要幫我介紹新工作。
“占用你十分鐘的時間。”
唐突地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對不起,”我吃一驚地反問。“你到底要說些什麽呢?”
“我說衹要十分鐘的時間就夠了!”
女人又重複地說了一遍。
我一點兒也認不得這個女人的聲音,因為我對於別人音色的辨認具有絶對的自信,所以我想這一定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女人,她的聲音低沉、柔和,而且語句中沒有重點。
“對不起,請問你是那位!”
我首先表現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模樣。
“這個不重要,我衹要十分鐘的時間就夠了,我想這樣就足夠我們彼此瞭解了。”她快速地說。
“彼此瞭解?”
“我是指精神上!”
她簡潔地回答。
我伸長脖子,探頭看看廚房裏的情形,煮通心粉的鍋子正冒着白蒙蒙的霧氣,好象正指揮着倫敦交響樂團的“鵲賊”。
“可是,非常不巧,我現在正在煮通心粉,已經快煮好了,如果再和你講十分鐘的電話,通心粉大概會被我煮爛了,我想最好是把電話挂斷。”
“通心粉?”女人驚訝地說。“現在纔早上十點半而已,為什麽在早上十點半煮通心粉呢?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管我奇不奇怪,反正都與你不相幹!”我說。“早飯沒吃什麽,我現在餓得很呢!”
“好吧!隨便你了,我現在就挂電話。”
她的聲音突然變得感情非常豐富。“不過我待會兒會再打來。”
“等一下!”我慌忙地說。“如果你是要嚮我推銷什麽的話,打幾百次電話都沒用,我現在正失業中,沒有餘錢買任何東西!”
“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你放心!”她說。
“知道了?你知道什麽?”
“知道你在失業中啊!總之趕快去煮通心粉吧!”
“你到底是──”我正在說話中電話就被切斷了,這種挂電話的方法也實在太唐突了,好象不是挂上話筒,而是用手指按下開關按鈕似的。
我滿腔的感情突然找不到地方宣泄,手握着話筒,茫然地看着前方,過了一會兒纔想起通心粉的事,便重新回到廚房,關掉瓦斯爐的火,將通心粉從鍋子裏撈起來,加上一些西紅柿醬,就開始吃了起來。
或許是因為接電話的緣故,通心粉煮得太軟了,但是並沒有軟到不能吃的地步。
我一邊聽着收音機裏傳出來的音樂,一邊將近二百五十公剋的面一點也不剩地送進胃裏。
我在流理臺洗盤子和鍋子,一邊燒開水,然後,泡了一壺紅茶,一邊想着剛纔那通電話。
彼此瞭解?
到底那個女人為什麽打電話給我呢?而且,那個女人是誰呢?
這一切都像一個謎。我覺得這是一通不認識的人打來的匿名電話,但是一點兒都找不到她的用意到底在那裏。
隨它去吧!──我心裏這樣想着──不論她是什麽樣的女孩,我都不想瞭解,因為這種事情對我毫無用處,對我而言,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份新的工作,而具要趕快確立一個新的生活圈。
但是,坐在客的沙發上的我,雖然看着圖書館藉來的蓮德敦的小說,卻仍然頻頻擡頭看看電話,我對她所說的“花十分鐘彼此瞭解一下”這句話越來越感興趣,十分鐘之內到底能夠瞭解些什麽呢?
從一開始她就提出了十分鐘的時間,讓我覺得她對自已所設定的時間非常有把握,但是,事實上或許可能短過九分鐘,或許長過十一分鐘,就像煮通心粉一樣……。
因為腦子裏老是想着這劇事,連小說的情節都看不下去了,於是我起身做做體操,然後去熨熨襯衫。衹要我覺得腦子裏一片混亂時,就去熨衣服,這是我長久以來的習慣。
我熨襯衫的全部工程一共分然十二個步驟。第一個步驟衣領到第十二個步驟左袖為止,順序絶對不會搞混。我一邊一個個地數着號碼,一邊依照順序熨下去,如果不這麽做的話,就不能將襯衫熨好。
我陶醉在蒸汽聲中,和棉質布料加熱後所發出獨特的香味裏。一共熨了三件襯衫,確認沒有任何縐痕之後,我將它挂回櫥子裏。關掉熨鬥的電源,和熨衣臺一起收起來。這時候我的腦子裏已經清楚多了。
覺得口渴正準備到廚房喝水時,電話又響起來了,我感到有些睏惑,不知該直接去廚房,或者回到客廳裏,但是最後還是回到客廳接起電話。
如果是剛纔那個女人又打電話來的話就要告訴她現在正在熨衣服,必須馬上挂電話。
但是,打電話來的是妻子,我看了一眼放在電視上的時鐘,指針正好指着十一點半。
“你好嗎?”她說。
“很好啊!”我呆呆地說。
“正在做什麽?”
“熨衣服。”
“發生了什麽事?”妻子問。
她的聲音裏帶着些許的緊張,我一覺得混亂時就熨衣服這事情,她是非常瞭解的。
“沒事!衹不過想熨衣服而已,沒有什麽特別的事。”
我說着坐到椅子上,將拿在左手上的聽筒換到右手來。
“你找我有事嗎?”
“嗯!關於工作方的事情,有一個滿不錯的工作機會。”
“喔!”我說。
“你會寫詩嗎?”
“詩?”
我大吃一驚地反問,詩?到底什麽叫做詩呢?
“我的朋友開的雜志社裏準備出版一本針對年輕女孩子的小說雜志,要找一負責個挑選詩的稿件的人,最好能夠每一個月在刊頭上寫一首詩,工作很簡單,待遇也不錯,雖然衹是兼差性質的,不過做得好的話,或許還可以兼任編輯的工作──”“簡單?”我說。“請等一下!我要找的是有關法律事務所的工作,什麽時候又跑出詩詞挑選員這碼子事來了呢?”
“我聽你說過,你高中時喜歡寫些什麽東西。”
“那是新聞!高中新聞!報導足球大賽中那一班獲勝,物理老師在樓跌倒住院療傷,寫一些拉裏拉雜的小事,不是寫詩!我不會寫詩!”
“不是什麽太大不了的詩,衹不過是讓高中女生看的,隨便寫就可以了!”
“不管那一種詩我都不會寫!”
我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理由叫我一定非得會寫詩不可吧!
“唉!”
妻子覺得非常可惜地說:
“可是,你又找不到和法律有關的工作!”
“已經談了好幾傢了,這個星期內會給我回答,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再考慮一下你說的那份工作吧!”
“好吧!就這麽了!今天是星期幾呢?”
“星期二。”
我稍微想了想之後說。
“你能不能幫我到銀行去繳瓦斯費和電話費呢?”
“好啊!我正打算去買晚飯,可以順道去銀行。”
“晚飯想吃什麽呢?”
“嗯!還不知道!”我說。“還沒有决定,買了之後再說。”
“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妻子改變語氣地說。
“這是我自已的想法,我覺得你實在不必再耗費心力找工作了!”
“為什麽?”
我再度驚訝地問。
全世界的女人打電話給我,好象都是為了要叫我大吃一驚似的。
“為什麽不用再找工作了?再三個月我就領不到失業保險金了,我還可以再遊手好閑下去嗎?”
“我有固定的薪水,副業也進展得很順利,而且還有一筆可觀的儲款,衹要不太浪費,一定夠吃的。”
“你是叫我在傢裏做傢事嗎?”
“你不喜歡?”
“我不知道!”
我老實地說,我真的不知道。“我考慮考慮!”
“考慮一下吧!”妻子說。
“貓回來了嗎?”
“貓?”
我反問了之後,纔發現從今天早上起我就將貓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了。
“沒有!好象沒有看到它回來。”
“你能不能到附近去找找看呢?它已經失蹤四天了。”
我沒有響應,衹是將話筒又移到左手。
“我想它大概是在後巷那個空房子的庭院裏吧!那個有小鳥的石雕的庭院。我以前在那裏看過它好幾次,你知道那個地方嗎?”
“不知道!”我說。“你一個人沒事跑那裏去做什麽?而且我以前怎麽從來不曾聽你提起──”“不跟你閑扯了,我要挂電話!還有工作要我處理呢!希望你能順利地找到貓。”
然後她就挂斷了電話。
凝視着聽筒好一陣子之後,纔將它放下。
※ ※ ※
為什妻子會對“後巷”瞭解得這麽清楚呢?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因為進去“後巷”必須翻過一道很高的圍墻,而且,故意做這些事情而進入“後巷”,是毫無意思的。
我到廚房喝水,打開fm的頻道,然候修剪指甲。收音機裏正播放羅勃特?布蘭特的新lp專輯,但是我衹聽了兩首歌,就覺得耳朵發痛,非關掉收音機不可。
接着我到屋檐下檢查貓吃東西用的盤子,發現昨天晚上我裝在盤子裏的魚幹一尾也不少,證明貓還是沒有回來過。
我站在屋檐下,看着明亮的初夏陽光,照着我傢狹窄的庭院,越看就越覺得這實在不是我理想中的庭院。因為在一天裏衹有很短的時間可以照到太陽,所以泥士顯得既黑又濕,而且庭院裏衹有二、三株紫陽花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並不怎麽喜歡紫陽花。
附近的樹林裏,有一種鳥的叫聲,聽起來像被掐到脖子似的,我們就叫它“掐脖子鳥”,這個名字是太太取的,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到底叫什麽,也沒有看過它的長相,不過這些都沒有關係,它還是每天都到附近的叢林來,在我們的世界裏發出它那獨特的叫聲。
為什麽我非得出去找貓不可?我一邊聽着掐脖子鳥的叫聲,心裏一邊想着,即使真的找到貓了,我又能怎樣呢?勸它回傢,或者對它哀求起說:大傢都在心着你,回傢去吧!
唉!算了!我又嘆了一口氣。讓貓到它喜歡居住的地方生活,這不是很好嗎?而我已經三十出頭了,竟然還找不到適當的工作!每天洗衣服,想着晚飯的菜單,還有尋找離傢出走的貓。
從前──我回想着──,我也是一個有着滿腔抱負的人,高中時立志要當律師,而且我的成績也不壞。高中三年級時選舉“模範生”,我是班上的第二高票,後來也順利地進入大學的法學院,當時的我,的確非常的狂傲。
我坐在廚房的桌子前,雙手托着下巴,心裏思忖着:到底是什麽緣故,使我的人生指針開始變得凌亂起來的呢?我不清楚。既不是政治運動受挫,也不是對大學感到失望,更不是交女朋友方面不順利。我衹是照着自已的樣子,平凡地活着。
但是,大學畢業之後,有一天我突然覺得過去的個已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自已。
當初這種感覺衹發生在一些眼睛看不見的小事上,但是,隨着時間纍積,這種感覺越來越時間的纍積,這種感覺越來越嚴重,最後甚至嚴重到令我將自已全部否定掉的地步。
二月開始,我辭掉了法律事務所的工作,我是我從學校畢業後就一直工作的地方,而且並沒有什麽特別的理由。我即不是工作的內容不喜歡,也不是待遇不好,同事之間的相處也很愉快。
法律事務所內的工作正好可以使我發揮所學。
而且,我覺得自已做得很好,理解力快,行動敏捷,不任意抱怨,而且對現實事務又有自已的看法。因此,當我提出辭呈時,老先生──這間事務所的所胝者是一對律師父子,老先生是指父親──表示要替我加薪,希望我能留下來。
但是最後我還是把工作辭掉了,為什麽要辭職?這個理由我也不太清楚,辭職之後的希望和展望,我也沒有仔細想過。衹是藉口說是想準備司法官考試,就順利地將工作辭去,但是事實上我並不是真的想當律師。
我在晚餐時對妻子說:“我想把工作辭掉!”
妻子衹是說:“這樣的啊!”
然後就不再說話了,到底“這樣的啊!”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一點兒也清楚。
看到我也沉默下來時,她說:“想辭就辭吧!”
她接着說:“反正是你自已的人生,你要怎麽過就怎麽過!”
說着一邊將魚骨頭夾在盤子旁。
妻子在服裝設計學校暢無,有一份不錯的待遇,又從做編輯的朋友那裏拿回一些美工的工作回來兼差,收入不壞,而我也可以領半年的失業保險。如果我每天待在傢裏,還可節省下外餐費和交通費,生活應該和上班時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於是我就把工作辭掉了。
十二點半時,我如往當一樣,將亞麻料子的大袋子背在肩膀上,先去銀行了瓦斯和電話費,然後到超級市場買晚餐,再到麥當勞吃了一個起司漢堡,喝了一杯咖啡。
回到傢裏將食品放到冰箱裏時,電話鈴響了,我聽起來覺得鈴聲好象非常焦躁不安,我衹好將切了一半的豆腐暫時先放在桌上,先到客廳去接電話。
“通心粉吃完了吧!”
是早上那個女人。
“吃完了!”我說。
“但是我得去找貓了。”
“不能等十分鐘再去嗎?”
“可以啊!如果衹是十分鐘的話!”
她到底想做什麽?為什麽我非得和這個素不相識的女人聊十分鐘的話不可。
“那麽我們互相瞭解一下吧!”
她靜靜地說。
這個女人──雖然我知道她是一個什麽樣子的女人,我猜想她大概是面嚮電話,坐在椅子上,兩腳交叉地和我講話。
“你到底想怎麽樣?”我說。“即使是相處十年也很難清楚地瞭解對方!”
“試試看,好嗎?”她說。
我脫下手錶,將它改換成馬表,現在已經是十秒鐘了。
“為什麽會找上我?”我問。“為什麽不去找別人而會找上我?”
“這是有理由的。”
她如同何在慢慢咀嚼食物一樣,仔細地說着這句話。
“我認識你。”
“什麽時候?什麽地點?”我問。
“任何時刻,任何地點!”她說。“這些事情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現在,不是嗎?而且,如果要談這些的話,時間很快地就會沒了,如果你不急的話是無所謂啦!”
“你能給我證明嗎?證明你認識我!”
“例如?”
“我的年齡?”
“三十。”
女人立刻回答。
“應該說三十又兩個月,這樣可以嗎?”
我不知該麽纔好,這個女人確實認識我,但是,我卻不記得聽過這樣的聲音,我是從來不會忘記別人的聲音的。我可能會忘記別人的長相、或名字,但是絶對會將聲音牢牢記住。
“這一次換你來想象一下我的模樣了!”
女人用誘惑的口吻說。
“從聲音想象我是一個模樣的女人,可以嗎?這不是你最擅長的嗎?”
“我想不出來!”我而。
“試試看嘛!”女人說。
我看了手錶一眼,還有五秒鐘纔一分,我縡望地嘆了一口氣,就接受她的要求吧!但是,衹要我一讓步,對方就會得寸進尺,這是我從三十年生活中所獲得的經驗──確實如她所說,這曾經是我的特技之一──集中精神去聽對方的聲音。
“二十七、八歲,大學畢業,東京人,小時候生活環境中上。”我說。
“太厲害了!”
她說,電話那頭傳來打火機點煙的聲音。
“再說說看!”
“長得滿漂亮的,至少你自已是這麽認為,但是有一點自卑。個子矮矮,或者乳房小小的。”
“說得像極了!”
她低聲地笑着說。
“結了婚,但是還不太習慣,而且有些問題。沒有問題的女人不會隨意打匿名電話給男人。但是,我還是不認識你,至少沒有和你講過話,所以不管怎麽想,我還是無法想出你的模樣。”
“或許是吧!”
她用平靜的語氣說。
“你對自已的能力如此地有自信?你難道不認為是你的腦子裏有一個致命的死角,否則你怎麽會想不起來我是誰呢?像你這麽聰明、能力又強的人,應該想不起來的啊!”
“你不要替我戴高帽子!”我說。
“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也不是那麽偉大的人,我也有能力所不及的地方,所以纔會越來越走偏人生的方向。”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你,雖然這是過去的事了!”
“那麽,談談過去的事情吧!”我說。
時間兩分五十三秒。
“過去有什麽好談的,我們的事情也不會記錄在歷史上!”
“會成為歷史的!”我說。
或許正如她所說的,我的腦子裏存在着某一個死角,這個死角或者身體裏的任何一個角落,就像一個失去的地底世界,而且,這個死角正是使我的人生觀發生狂亂的原因。
“我現在正在床上呢!”女人說。“剛剛洗完澡,什麽衣服也沒穿。”
什麽衣服也沒穿!那不像春宮電影裏的情節一樣了嗎?
“你覺得我應該穿件內褲比較好呢?還是穿雙褲襪比較好?或者什麽都不要穿!”
“隨你自已高興就好!”我說。“不過,我不喜歡在電話裏談這些,一點趣味都沒有。”
“十分鐘就好了!衹有十分鐘而已,對你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失,而且我們衹不過是一問一答而已。你認為裸體比較好,還是穿上什麽比較好。我什麽衣服都有呢!例如襪帶……”
襪帶?竟然有人穿襪帶,莫非她是“閣樓”雜志的模特兒。
“你最好不要穿衣服,也不要亂動!”我說。
時間是四分鐘。
“而且我的陰毛還是濕的呢!”她說。
“完全攛幹,所以現在還是濕的,熱熱濕濕的,非常柔軟喔!黑亮亮的,非常柔軟,要不要摸摸看!”
“我不喜歡──”“再下面一點也是熱的呢!好象剛熱過的奶油,非常熱的喔!真的喲!你想不想知道我現在是什麽姿勢呢?右膝立起來,左腳橫地打開,像時鐘十點五分的角度,”從說話調來,我知道她所言不假。她真的將兩腿打開成十點五分的角度,而且把陰部弄得濕濕熱熱的。
“摸摸唇,慢慢的,而且是開着的。慢慢的喔!用指腹慢慢的摸,非常慢喔!再用另一隻手玩弄着左邊的乳房,從下面開始輕輕地按摩,乳頭突然的變硬,重複幾次吧!”
我悶不吭聲地將電話挂掉。
然後躺在沙發上,看着天花板,吸了一根煙,馬銀停在五分二十三秒的位置。
我閉上了眼精,出現一幅五顔六色的彩畫。
為什麽會這樣呢?為什麽所有的事情都不對勁了呢?
十分鐘頭後,電話又響了,這一次我並沒有去接,電話響了十五聲之後就挂掉了。
兩點前我越過侹院的圍墻,到後巷去。
※ ※ ※
所謂的“後巷”事實上稱不上是一條後巷,因為它不是一條真正的路。路應該是有入口、出口的。
但是,“後巷”沒有入口、也沒有出口,稱不上,因為至少死鬍同還有個入口。附近的人們為了方便稱呼,就叫它“後巷”。
“後巷”長約二百公尺,寬不到一公尺,再加上路上堆了許多雜七雜八的東西,必須側着身體才能在這裏走動。
據說──這是將房子便宜地租給我們的叔父所說的──“後巷”原本是有出口和入口的,而且具有連接道路與道路的機能,但是,隨着高度成長期的到臨,空地都蓋了新房子,結果道路就越來越狹窄,而住在這裏的人也不喜歡外人在自已的庭院裏鑽進鑽出,於是就將小路者起來?剛開始時大傢衹是利用一些粗動的屏障物,但是漸漸地就有人用水泥墻、或鐵絲網將自已傢門口的庭院圍起來,於是這就變成一條沒有出口,也沒有入口的“後巷”了。
妻子為什麽會到“後巷”去呢?我實在想不出正確的理由,而我自已也衹不過到“後巷”去過一次,更何況她是一個最討厭蜘蛛的人。
但是,不管怎麽再三思考,我的腦子都像一片混亂的糊,越想越亂,頭的兩側也隱隱作痛起來,因為昨天晚上沒有睡好,也因為五月初的暑氣,更因為那通奇怪的電話。
算了!別再鬍思亂想了,還是去找貓吧!與其老是在傢裏,不如到外面去走走,而且至少還有個具體的目的。
初夏的陽光將樹影投映在地面上,因為沒有風的緣故,影子永遠固定地留在地面上一動也不動,看起來像是個古板的宿命論者,任憑外界變化的擺布。
我從樹影下穿過,東一塊西一塊的影子照在的白色襯衫上,彷佛凹凸不平的地球表面。
這附近一片靜寂無聲,靜得彷佛連緑葉行光合作用的呼吸聲都聽得見似的。
天空中飄浮着幾朵小雲,彷佛中世紀的銅版畫的背景裏所描繒的,形狀鮮明而簡潔的雲朵。因為眼前所看見的每一富景象都深刻而鮮豔,這更使我清楚的感覺到體內那股茫然的不存在感正存蠢蠢欲動。而且,天氣實在熱得人受不了。
我穿着t恤、薄薄的棉質褲子,以及網球鞋。但是,在太陽底下走了一長段路之後,我開始覺得腋下、胸前已經沁出汗水了。t恤和褲子都是當天早上纔從衣箱子裏翻出,所以還有一股濃烈的樟腦丸味道,那氣味彷佛一隻衹有翅膀的飛蟲,趁着我呼吸時,會偷偷地飛進我的鼻孔裏。
我小心地穿過兩旁堆置的廢物,慢慢地往前走,邊走時還得一邊小聲地叫着貓的名字。
建築在後巷兩側的房子,彷佛是由比重相異的液體所混合而成似的,簡單地說凸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擁有寬廣庭院的舊式建築,另一種是最近纔新建的新房子。
新房子通常沒有寬闊的庭院,有的甚至連院子也沒有。這些房子的屋檐和後巷之間的距離大概衹夠景一排衣服而已,因此,有些人就會將衣服晾到後巷來,因此,我簡直就是走在濕答答的毛巾、襯衫、被單的行列之中。
從路旁人傢的房裏傳出來的電視聲音、抽水馬桶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不時還傳來陣陣咖哩飯的香味。
相較之下,舊式房子的生活味道就比較感覺不到,圍墻也大多是使用各式各樣的灌木所圍起來的,從木頭的縫隙可以看見寬闊的庭院,而房屋的建築有的是有着長長走廊的日本式房子,有的是有着古銅色屋頂的西式建築,有的則是最近纔改建的摩登建築。但是,不論是那一種建築,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那就是幾乎不見半個住在這裏的人影╡且沒有聽到半點聲音,聞到半點味道,連洗丞的衣物也都完全看不見。
因為一路上所看到的情景對我而言都是既新鮮又有趣的,所以我就一邊慢慢地觀察,一邊緩緩地往“後巷”走去。
有一間房子的庭院裏放置着一棵早已枯黃的聖誕樹;有一間房子的庭院裏則堆滿了玩具──三輪車、套圈圈、塑料劍、橡皮球、烏龜形狀的玩偶。有的庭院裏還有籃球架,有的庭院裏則有蕩鞦韆,或各種陶製的桌子。
還有一戶人傢的大門是一道鋁邊的玻璃落地窗,房裏的佈置可以一覽無遺,房間裏有一套肝紅色的真皮沙發、大型的電視、裝飾用的架子(上面有一個熱帶魚的水槽,和兩個大奬杯),還有一盞裝飾用的藝燈。看起來好象電視連續劇中的場景,非常不切實際。
有一個院子裏放置着一個鐵絲網圍成的大型狗屋,但是,裏面並沒有看到狗的影子,而且門也是敞開着的。
妻子告訴我空房子就在有狗屋的房子前面,因此,我很快地就找到了這間空房子。
這是一間新建的兩層樓房,但是緊閉着的木頭兩棚看起來卻非常的古舊,二樓窗戶的手把也壞掉了,庭院的正中央放置一座高及人胸部的石雕,這座石雕的形狀是一隻欲展翅飛去的鳥,四周則雜草叢生。這衹鳥──雖然我不知道它叫什麽名字──模樣看起來很威武。
除了這座石雕之外,院子裏就沒有其它像裝飾的裝飾品了。
我靠非這面高達胸部的鐵絲網,對着院子裏看了好一會兒。雖然我知道這會是一個貓喜歡的庭院,但是,看了好一陣子都沒有看見貓的影子。屋頂的電視天綫上停着一隻鴿子,發出了單調的叫聲。
石鳥的影子落在叢生雜草堆裏,被分割成零零碎碎的形狀。
我從口袋裏拿出一根煙,點着了火,靠在鐵絲網旁將一整根煙抽完了,這時候電視天綫上的鴿子一直以相同的調子啼叫着。
抽完了一根煙,將它丟在地面上踩熄了之後,我還是靜靜地靠鄉這裏狐索着。我已經腦子裏一片模糊,真想好好的大睡一覺,大概是因為我一直盯着石雕的鳥看的緣故吧!
我突然覺得鳥的影子裏好象發出了一個人的聲音,不知道是誰的聲音,不過,我可以確定是女人的聲音,而且好象是在叫我的。
■譯者:許珀理
那個女人打電話來時,我正站在廚房裏煮着通心粉。在通心粉煮好之前,我和着fm電臺的音樂,吹着羅西尼“鵲賊”序麯的口哨,這是煮通心粉時最合的音樂。
電話鈴響時,我原本不想理會它,繼續煮我的通心粉,因為面快煮好了,而且收音機裏又播放着我最喜歡的倫敦交響樂團的麯子。但是,我還是將瓦斯的火關小一點,右手拿着筷子,到客廳裏去接電話,因為我突然想到或許有朋友要幫我介紹新工作。
“占用你十分鐘的時間。”
唐突地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對不起,”我吃一驚地反問。“你到底要說些什麽呢?”
“我說衹要十分鐘的時間就夠了!”
女人又重複地說了一遍。
我一點兒也認不得這個女人的聲音,因為我對於別人音色的辨認具有絶對的自信,所以我想這一定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女人,她的聲音低沉、柔和,而且語句中沒有重點。
“對不起,請問你是那位!”
我首先表現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模樣。
“這個不重要,我衹要十分鐘的時間就夠了,我想這樣就足夠我們彼此瞭解了。”她快速地說。
“彼此瞭解?”
“我是指精神上!”
她簡潔地回答。
我伸長脖子,探頭看看廚房裏的情形,煮通心粉的鍋子正冒着白蒙蒙的霧氣,好象正指揮着倫敦交響樂團的“鵲賊”。
“可是,非常不巧,我現在正在煮通心粉,已經快煮好了,如果再和你講十分鐘的電話,通心粉大概會被我煮爛了,我想最好是把電話挂斷。”
“通心粉?”女人驚訝地說。“現在纔早上十點半而已,為什麽在早上十點半煮通心粉呢?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管我奇不奇怪,反正都與你不相幹!”我說。“早飯沒吃什麽,我現在餓得很呢!”
“好吧!隨便你了,我現在就挂電話。”
她的聲音突然變得感情非常豐富。“不過我待會兒會再打來。”
“等一下!”我慌忙地說。“如果你是要嚮我推銷什麽的話,打幾百次電話都沒用,我現在正失業中,沒有餘錢買任何東西!”
“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你放心!”她說。
“知道了?你知道什麽?”
“知道你在失業中啊!總之趕快去煮通心粉吧!”
“你到底是──”我正在說話中電話就被切斷了,這種挂電話的方法也實在太唐突了,好象不是挂上話筒,而是用手指按下開關按鈕似的。
我滿腔的感情突然找不到地方宣泄,手握着話筒,茫然地看着前方,過了一會兒纔想起通心粉的事,便重新回到廚房,關掉瓦斯爐的火,將通心粉從鍋子裏撈起來,加上一些西紅柿醬,就開始吃了起來。
或許是因為接電話的緣故,通心粉煮得太軟了,但是並沒有軟到不能吃的地步。
我一邊聽着收音機裏傳出來的音樂,一邊將近二百五十公剋的面一點也不剩地送進胃裏。
我在流理臺洗盤子和鍋子,一邊燒開水,然後,泡了一壺紅茶,一邊想着剛纔那通電話。
彼此瞭解?
到底那個女人為什麽打電話給我呢?而且,那個女人是誰呢?
這一切都像一個謎。我覺得這是一通不認識的人打來的匿名電話,但是一點兒都找不到她的用意到底在那裏。
隨它去吧!──我心裏這樣想着──不論她是什麽樣的女孩,我都不想瞭解,因為這種事情對我毫無用處,對我而言,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份新的工作,而具要趕快確立一個新的生活圈。
但是,坐在客的沙發上的我,雖然看着圖書館藉來的蓮德敦的小說,卻仍然頻頻擡頭看看電話,我對她所說的“花十分鐘彼此瞭解一下”這句話越來越感興趣,十分鐘之內到底能夠瞭解些什麽呢?
從一開始她就提出了十分鐘的時間,讓我覺得她對自已所設定的時間非常有把握,但是,事實上或許可能短過九分鐘,或許長過十一分鐘,就像煮通心粉一樣……。
因為腦子裏老是想着這劇事,連小說的情節都看不下去了,於是我起身做做體操,然後去熨熨襯衫。衹要我覺得腦子裏一片混亂時,就去熨衣服,這是我長久以來的習慣。
我熨襯衫的全部工程一共分然十二個步驟。第一個步驟衣領到第十二個步驟左袖為止,順序絶對不會搞混。我一邊一個個地數着號碼,一邊依照順序熨下去,如果不這麽做的話,就不能將襯衫熨好。
我陶醉在蒸汽聲中,和棉質布料加熱後所發出獨特的香味裏。一共熨了三件襯衫,確認沒有任何縐痕之後,我將它挂回櫥子裏。關掉熨鬥的電源,和熨衣臺一起收起來。這時候我的腦子裏已經清楚多了。
覺得口渴正準備到廚房喝水時,電話又響起來了,我感到有些睏惑,不知該直接去廚房,或者回到客廳裏,但是最後還是回到客廳接起電話。
如果是剛纔那個女人又打電話來的話就要告訴她現在正在熨衣服,必須馬上挂電話。
但是,打電話來的是妻子,我看了一眼放在電視上的時鐘,指針正好指着十一點半。
“你好嗎?”她說。
“很好啊!”我呆呆地說。
“正在做什麽?”
“熨衣服。”
“發生了什麽事?”妻子問。
她的聲音裏帶着些許的緊張,我一覺得混亂時就熨衣服這事情,她是非常瞭解的。
“沒事!衹不過想熨衣服而已,沒有什麽特別的事。”
我說着坐到椅子上,將拿在左手上的聽筒換到右手來。
“你找我有事嗎?”
“嗯!關於工作方的事情,有一個滿不錯的工作機會。”
“喔!”我說。
“你會寫詩嗎?”
“詩?”
我大吃一驚地反問,詩?到底什麽叫做詩呢?
“我的朋友開的雜志社裏準備出版一本針對年輕女孩子的小說雜志,要找一負責個挑選詩的稿件的人,最好能夠每一個月在刊頭上寫一首詩,工作很簡單,待遇也不錯,雖然衹是兼差性質的,不過做得好的話,或許還可以兼任編輯的工作──”“簡單?”我說。“請等一下!我要找的是有關法律事務所的工作,什麽時候又跑出詩詞挑選員這碼子事來了呢?”
“我聽你說過,你高中時喜歡寫些什麽東西。”
“那是新聞!高中新聞!報導足球大賽中那一班獲勝,物理老師在樓跌倒住院療傷,寫一些拉裏拉雜的小事,不是寫詩!我不會寫詩!”
“不是什麽太大不了的詩,衹不過是讓高中女生看的,隨便寫就可以了!”
“不管那一種詩我都不會寫!”
我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理由叫我一定非得會寫詩不可吧!
“唉!”
妻子覺得非常可惜地說:
“可是,你又找不到和法律有關的工作!”
“已經談了好幾傢了,這個星期內會給我回答,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再考慮一下你說的那份工作吧!”
“好吧!就這麽了!今天是星期幾呢?”
“星期二。”
我稍微想了想之後說。
“你能不能幫我到銀行去繳瓦斯費和電話費呢?”
“好啊!我正打算去買晚飯,可以順道去銀行。”
“晚飯想吃什麽呢?”
“嗯!還不知道!”我說。“還沒有决定,買了之後再說。”
“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妻子改變語氣地說。
“這是我自已的想法,我覺得你實在不必再耗費心力找工作了!”
“為什麽?”
我再度驚訝地問。
全世界的女人打電話給我,好象都是為了要叫我大吃一驚似的。
“為什麽不用再找工作了?再三個月我就領不到失業保險金了,我還可以再遊手好閑下去嗎?”
“我有固定的薪水,副業也進展得很順利,而且還有一筆可觀的儲款,衹要不太浪費,一定夠吃的。”
“你是叫我在傢裏做傢事嗎?”
“你不喜歡?”
“我不知道!”
我老實地說,我真的不知道。“我考慮考慮!”
“考慮一下吧!”妻子說。
“貓回來了嗎?”
“貓?”
我反問了之後,纔發現從今天早上起我就將貓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了。
“沒有!好象沒有看到它回來。”
“你能不能到附近去找找看呢?它已經失蹤四天了。”
我沒有響應,衹是將話筒又移到左手。
“我想它大概是在後巷那個空房子的庭院裏吧!那個有小鳥的石雕的庭院。我以前在那裏看過它好幾次,你知道那個地方嗎?”
“不知道!”我說。“你一個人沒事跑那裏去做什麽?而且我以前怎麽從來不曾聽你提起──”“不跟你閑扯了,我要挂電話!還有工作要我處理呢!希望你能順利地找到貓。”
然後她就挂斷了電話。
凝視着聽筒好一陣子之後,纔將它放下。
※ ※ ※
為什妻子會對“後巷”瞭解得這麽清楚呢?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因為進去“後巷”必須翻過一道很高的圍墻,而且,故意做這些事情而進入“後巷”,是毫無意思的。
我到廚房喝水,打開fm的頻道,然候修剪指甲。收音機裏正播放羅勃特?布蘭特的新lp專輯,但是我衹聽了兩首歌,就覺得耳朵發痛,非關掉收音機不可。
接着我到屋檐下檢查貓吃東西用的盤子,發現昨天晚上我裝在盤子裏的魚幹一尾也不少,證明貓還是沒有回來過。
我站在屋檐下,看着明亮的初夏陽光,照着我傢狹窄的庭院,越看就越覺得這實在不是我理想中的庭院。因為在一天裏衹有很短的時間可以照到太陽,所以泥士顯得既黑又濕,而且庭院裏衹有二、三株紫陽花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並不怎麽喜歡紫陽花。
附近的樹林裏,有一種鳥的叫聲,聽起來像被掐到脖子似的,我們就叫它“掐脖子鳥”,這個名字是太太取的,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到底叫什麽,也沒有看過它的長相,不過這些都沒有關係,它還是每天都到附近的叢林來,在我們的世界裏發出它那獨特的叫聲。
為什麽我非得出去找貓不可?我一邊聽着掐脖子鳥的叫聲,心裏一邊想着,即使真的找到貓了,我又能怎樣呢?勸它回傢,或者對它哀求起說:大傢都在心着你,回傢去吧!
唉!算了!我又嘆了一口氣。讓貓到它喜歡居住的地方生活,這不是很好嗎?而我已經三十出頭了,竟然還找不到適當的工作!每天洗衣服,想着晚飯的菜單,還有尋找離傢出走的貓。
從前──我回想着──,我也是一個有着滿腔抱負的人,高中時立志要當律師,而且我的成績也不壞。高中三年級時選舉“模範生”,我是班上的第二高票,後來也順利地進入大學的法學院,當時的我,的確非常的狂傲。
我坐在廚房的桌子前,雙手托着下巴,心裏思忖着:到底是什麽緣故,使我的人生指針開始變得凌亂起來的呢?我不清楚。既不是政治運動受挫,也不是對大學感到失望,更不是交女朋友方面不順利。我衹是照着自已的樣子,平凡地活着。
但是,大學畢業之後,有一天我突然覺得過去的個已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自已。
當初這種感覺衹發生在一些眼睛看不見的小事上,但是,隨着時間纍積,這種感覺越來越時間的纍積,這種感覺越來越嚴重,最後甚至嚴重到令我將自已全部否定掉的地步。
二月開始,我辭掉了法律事務所的工作,我是我從學校畢業後就一直工作的地方,而且並沒有什麽特別的理由。我即不是工作的內容不喜歡,也不是待遇不好,同事之間的相處也很愉快。
法律事務所內的工作正好可以使我發揮所學。
而且,我覺得自已做得很好,理解力快,行動敏捷,不任意抱怨,而且對現實事務又有自已的看法。因此,當我提出辭呈時,老先生──這間事務所的所胝者是一對律師父子,老先生是指父親──表示要替我加薪,希望我能留下來。
但是最後我還是把工作辭掉了,為什麽要辭職?這個理由我也不太清楚,辭職之後的希望和展望,我也沒有仔細想過。衹是藉口說是想準備司法官考試,就順利地將工作辭去,但是事實上我並不是真的想當律師。
我在晚餐時對妻子說:“我想把工作辭掉!”
妻子衹是說:“這樣的啊!”
然後就不再說話了,到底“這樣的啊!”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一點兒也清楚。
看到我也沉默下來時,她說:“想辭就辭吧!”
她接着說:“反正是你自已的人生,你要怎麽過就怎麽過!”
說着一邊將魚骨頭夾在盤子旁。
妻子在服裝設計學校暢無,有一份不錯的待遇,又從做編輯的朋友那裏拿回一些美工的工作回來兼差,收入不壞,而我也可以領半年的失業保險。如果我每天待在傢裏,還可節省下外餐費和交通費,生活應該和上班時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於是我就把工作辭掉了。
十二點半時,我如往當一樣,將亞麻料子的大袋子背在肩膀上,先去銀行了瓦斯和電話費,然後到超級市場買晚餐,再到麥當勞吃了一個起司漢堡,喝了一杯咖啡。
回到傢裏將食品放到冰箱裏時,電話鈴響了,我聽起來覺得鈴聲好象非常焦躁不安,我衹好將切了一半的豆腐暫時先放在桌上,先到客廳去接電話。
“通心粉吃完了吧!”
是早上那個女人。
“吃完了!”我說。
“但是我得去找貓了。”
“不能等十分鐘再去嗎?”
“可以啊!如果衹是十分鐘的話!”
她到底想做什麽?為什麽我非得和這個素不相識的女人聊十分鐘的話不可。
“那麽我們互相瞭解一下吧!”
她靜靜地說。
這個女人──雖然我知道她是一個什麽樣子的女人,我猜想她大概是面嚮電話,坐在椅子上,兩腳交叉地和我講話。
“你到底想怎麽樣?”我說。“即使是相處十年也很難清楚地瞭解對方!”
“試試看,好嗎?”她說。
我脫下手錶,將它改換成馬表,現在已經是十秒鐘了。
“為什麽會找上我?”我問。“為什麽不去找別人而會找上我?”
“這是有理由的。”
她如同何在慢慢咀嚼食物一樣,仔細地說着這句話。
“我認識你。”
“什麽時候?什麽地點?”我問。
“任何時刻,任何地點!”她說。“這些事情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現在,不是嗎?而且,如果要談這些的話,時間很快地就會沒了,如果你不急的話是無所謂啦!”
“你能給我證明嗎?證明你認識我!”
“例如?”
“我的年齡?”
“三十。”
女人立刻回答。
“應該說三十又兩個月,這樣可以嗎?”
我不知該麽纔好,這個女人確實認識我,但是,我卻不記得聽過這樣的聲音,我是從來不會忘記別人的聲音的。我可能會忘記別人的長相、或名字,但是絶對會將聲音牢牢記住。
“這一次換你來想象一下我的模樣了!”
女人用誘惑的口吻說。
“從聲音想象我是一個模樣的女人,可以嗎?這不是你最擅長的嗎?”
“我想不出來!”我而。
“試試看嘛!”女人說。
我看了手錶一眼,還有五秒鐘纔一分,我縡望地嘆了一口氣,就接受她的要求吧!但是,衹要我一讓步,對方就會得寸進尺,這是我從三十年生活中所獲得的經驗──確實如她所說,這曾經是我的特技之一──集中精神去聽對方的聲音。
“二十七、八歲,大學畢業,東京人,小時候生活環境中上。”我說。
“太厲害了!”
她說,電話那頭傳來打火機點煙的聲音。
“再說說看!”
“長得滿漂亮的,至少你自已是這麽認為,但是有一點自卑。個子矮矮,或者乳房小小的。”
“說得像極了!”
她低聲地笑着說。
“結了婚,但是還不太習慣,而且有些問題。沒有問題的女人不會隨意打匿名電話給男人。但是,我還是不認識你,至少沒有和你講過話,所以不管怎麽想,我還是無法想出你的模樣。”
“或許是吧!”
她用平靜的語氣說。
“你對自已的能力如此地有自信?你難道不認為是你的腦子裏有一個致命的死角,否則你怎麽會想不起來我是誰呢?像你這麽聰明、能力又強的人,應該想不起來的啊!”
“你不要替我戴高帽子!”我說。
“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也不是那麽偉大的人,我也有能力所不及的地方,所以纔會越來越走偏人生的方向。”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你,雖然這是過去的事了!”
“那麽,談談過去的事情吧!”我說。
時間兩分五十三秒。
“過去有什麽好談的,我們的事情也不會記錄在歷史上!”
“會成為歷史的!”我說。
或許正如她所說的,我的腦子裏存在着某一個死角,這個死角或者身體裏的任何一個角落,就像一個失去的地底世界,而且,這個死角正是使我的人生觀發生狂亂的原因。
“我現在正在床上呢!”女人說。“剛剛洗完澡,什麽衣服也沒穿。”
什麽衣服也沒穿!那不像春宮電影裏的情節一樣了嗎?
“你覺得我應該穿件內褲比較好呢?還是穿雙褲襪比較好?或者什麽都不要穿!”
“隨你自已高興就好!”我說。“不過,我不喜歡在電話裏談這些,一點趣味都沒有。”
“十分鐘就好了!衹有十分鐘而已,對你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失,而且我們衹不過是一問一答而已。你認為裸體比較好,還是穿上什麽比較好。我什麽衣服都有呢!例如襪帶……”
襪帶?竟然有人穿襪帶,莫非她是“閣樓”雜志的模特兒。
“你最好不要穿衣服,也不要亂動!”我說。
時間是四分鐘。
“而且我的陰毛還是濕的呢!”她說。
“完全攛幹,所以現在還是濕的,熱熱濕濕的,非常柔軟喔!黑亮亮的,非常柔軟,要不要摸摸看!”
“我不喜歡──”“再下面一點也是熱的呢!好象剛熱過的奶油,非常熱的喔!真的喲!你想不想知道我現在是什麽姿勢呢?右膝立起來,左腳橫地打開,像時鐘十點五分的角度,”從說話調來,我知道她所言不假。她真的將兩腿打開成十點五分的角度,而且把陰部弄得濕濕熱熱的。
“摸摸唇,慢慢的,而且是開着的。慢慢的喔!用指腹慢慢的摸,非常慢喔!再用另一隻手玩弄着左邊的乳房,從下面開始輕輕地按摩,乳頭突然的變硬,重複幾次吧!”
我悶不吭聲地將電話挂掉。
然後躺在沙發上,看着天花板,吸了一根煙,馬銀停在五分二十三秒的位置。
我閉上了眼精,出現一幅五顔六色的彩畫。
為什麽會這樣呢?為什麽所有的事情都不對勁了呢?
十分鐘頭後,電話又響了,這一次我並沒有去接,電話響了十五聲之後就挂掉了。
兩點前我越過侹院的圍墻,到後巷去。
※ ※ ※
所謂的“後巷”事實上稱不上是一條後巷,因為它不是一條真正的路。路應該是有入口、出口的。
但是,“後巷”沒有入口、也沒有出口,稱不上,因為至少死鬍同還有個入口。附近的人們為了方便稱呼,就叫它“後巷”。
“後巷”長約二百公尺,寬不到一公尺,再加上路上堆了許多雜七雜八的東西,必須側着身體才能在這裏走動。
據說──這是將房子便宜地租給我們的叔父所說的──“後巷”原本是有出口和入口的,而且具有連接道路與道路的機能,但是,隨着高度成長期的到臨,空地都蓋了新房子,結果道路就越來越狹窄,而住在這裏的人也不喜歡外人在自已的庭院裏鑽進鑽出,於是就將小路者起來?剛開始時大傢衹是利用一些粗動的屏障物,但是漸漸地就有人用水泥墻、或鐵絲網將自已傢門口的庭院圍起來,於是這就變成一條沒有出口,也沒有入口的“後巷”了。
妻子為什麽會到“後巷”去呢?我實在想不出正確的理由,而我自已也衹不過到“後巷”去過一次,更何況她是一個最討厭蜘蛛的人。
但是,不管怎麽再三思考,我的腦子都像一片混亂的糊,越想越亂,頭的兩側也隱隱作痛起來,因為昨天晚上沒有睡好,也因為五月初的暑氣,更因為那通奇怪的電話。
算了!別再鬍思亂想了,還是去找貓吧!與其老是在傢裏,不如到外面去走走,而且至少還有個具體的目的。
初夏的陽光將樹影投映在地面上,因為沒有風的緣故,影子永遠固定地留在地面上一動也不動,看起來像是個古板的宿命論者,任憑外界變化的擺布。
我從樹影下穿過,東一塊西一塊的影子照在的白色襯衫上,彷佛凹凸不平的地球表面。
這附近一片靜寂無聲,靜得彷佛連緑葉行光合作用的呼吸聲都聽得見似的。
天空中飄浮着幾朵小雲,彷佛中世紀的銅版畫的背景裏所描繒的,形狀鮮明而簡潔的雲朵。因為眼前所看見的每一富景象都深刻而鮮豔,這更使我清楚的感覺到體內那股茫然的不存在感正存蠢蠢欲動。而且,天氣實在熱得人受不了。
我穿着t恤、薄薄的棉質褲子,以及網球鞋。但是,在太陽底下走了一長段路之後,我開始覺得腋下、胸前已經沁出汗水了。t恤和褲子都是當天早上纔從衣箱子裏翻出,所以還有一股濃烈的樟腦丸味道,那氣味彷佛一隻衹有翅膀的飛蟲,趁着我呼吸時,會偷偷地飛進我的鼻孔裏。
我小心地穿過兩旁堆置的廢物,慢慢地往前走,邊走時還得一邊小聲地叫着貓的名字。
建築在後巷兩側的房子,彷佛是由比重相異的液體所混合而成似的,簡單地說凸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擁有寬廣庭院的舊式建築,另一種是最近纔新建的新房子。
新房子通常沒有寬闊的庭院,有的甚至連院子也沒有。這些房子的屋檐和後巷之間的距離大概衹夠景一排衣服而已,因此,有些人就會將衣服晾到後巷來,因此,我簡直就是走在濕答答的毛巾、襯衫、被單的行列之中。
從路旁人傢的房裏傳出來的電視聲音、抽水馬桶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不時還傳來陣陣咖哩飯的香味。
相較之下,舊式房子的生活味道就比較感覺不到,圍墻也大多是使用各式各樣的灌木所圍起來的,從木頭的縫隙可以看見寬闊的庭院,而房屋的建築有的是有着長長走廊的日本式房子,有的是有着古銅色屋頂的西式建築,有的則是最近纔改建的摩登建築。但是,不論是那一種建築,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那就是幾乎不見半個住在這裏的人影╡且沒有聽到半點聲音,聞到半點味道,連洗丞的衣物也都完全看不見。
因為一路上所看到的情景對我而言都是既新鮮又有趣的,所以我就一邊慢慢地觀察,一邊緩緩地往“後巷”走去。
有一間房子的庭院裏放置着一棵早已枯黃的聖誕樹;有一間房子的庭院裏則堆滿了玩具──三輪車、套圈圈、塑料劍、橡皮球、烏龜形狀的玩偶。有的庭院裏還有籃球架,有的庭院裏則有蕩鞦韆,或各種陶製的桌子。
還有一戶人傢的大門是一道鋁邊的玻璃落地窗,房裏的佈置可以一覽無遺,房間裏有一套肝紅色的真皮沙發、大型的電視、裝飾用的架子(上面有一個熱帶魚的水槽,和兩個大奬杯),還有一盞裝飾用的藝燈。看起來好象電視連續劇中的場景,非常不切實際。
有一個院子裏放置着一個鐵絲網圍成的大型狗屋,但是,裏面並沒有看到狗的影子,而且門也是敞開着的。
妻子告訴我空房子就在有狗屋的房子前面,因此,我很快地就找到了這間空房子。
這是一間新建的兩層樓房,但是緊閉着的木頭兩棚看起來卻非常的古舊,二樓窗戶的手把也壞掉了,庭院的正中央放置一座高及人胸部的石雕,這座石雕的形狀是一隻欲展翅飛去的鳥,四周則雜草叢生。這衹鳥──雖然我不知道它叫什麽名字──模樣看起來很威武。
除了這座石雕之外,院子裏就沒有其它像裝飾的裝飾品了。
我靠非這面高達胸部的鐵絲網,對着院子裏看了好一會兒。雖然我知道這會是一個貓喜歡的庭院,但是,看了好一陣子都沒有看見貓的影子。屋頂的電視天綫上停着一隻鴿子,發出了單調的叫聲。
石鳥的影子落在叢生雜草堆裏,被分割成零零碎碎的形狀。
我從口袋裏拿出一根煙,點着了火,靠在鐵絲網旁將一整根煙抽完了,這時候電視天綫上的鴿子一直以相同的調子啼叫着。
抽完了一根煙,將它丟在地面上踩熄了之後,我還是靜靜地靠鄉這裏狐索着。我已經腦子裏一片模糊,真想好好的大睡一覺,大概是因為我一直盯着石雕的鳥看的緣故吧!
我突然覺得鳥的影子裏好象發出了一個人的聲音,不知道是誰的聲音,不過,我可以確定是女人的聲音,而且好象是在叫我的。
一八八一年風起雲涌的印地安.希特勒入侵波蘭.再度進入強風世界
■原載:《面包屋再襲擊》.皇冠出版
■譯者:許珀理
(1)羅馬帝國的崩潰
發現開始颳起風這件事情,是在星期天的午後,準確的說,應該是午後兩點七分。
當時我正如同往常一樣─換句話說是如同往常的星期日下午一樣─坐在廚房的桌子前,一邊聽着毫無妨礙的音樂,一邊記着一周的日記;我每天都將發生的事情簡單地記錄下來,等到星期天再將它寫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當我寫完了周二的日記,換句話說,已經完成了三天份的日記時,突然發現窗外颳着猛烈的強風。我不由得不中斷寫日記的工作,將筆蓋套上,到陽臺把曬幹的衣服收了下來。衣服隨着狂風在空中飛舞着,發出了幹裂的聲響。
風勢好象在我不知不覺間慢慢地增強了,當天早上─正確的說法是上午十點四十八分─將洗好的衣服晾到陽臺上去的時候,還沒有發現有任何颳風的跡象,因為我當時心裏想着:“沒有颳半點風,衣服不必用夾子吧!
我可以肯定當時的確沒有颳風。
我將曬幹的衣服整齊地摺叠起來之後,將房間裏的窗戶全部緊緊地關上,關上窗戶之後,幾乎就聽不到一點點風吹的聲音了。窗戶外在一片無聲無息間,樹木─喜馬拉雅杉和慄樹─彷佛一隻耐不住全身發癢的小狗,不停地翻滾着身體。雲朵的碎片像一位眼神兇惡的密使,急速地穿越天空,對面公寓陽臺上還挂着幾件襯衫,像被遺棄的孤兒,緊緊地纏繞在塑料繩上。
好象是臺風來了,我心裏想着。
但是,打開報紙,看看氣象圖,沒有找到任何臺風要來的報導,降雨量也在全年的平均標準以下,從氣象圖上顯示,當時的氣倏就像全盛時期的羅馬帝國一樣,應該是一個非和平的星期天。
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將報紙折好,衣服放進櫥櫃裏,一邊聽着毫無妨礙的音樂,一邊喝着咖啡,而且,一邊喝着咖啡,一邊寫日記。
星期四我和女友上床睡覺,她非常喜歡戴着眼罩做愛,因此她平常總是將飛機上用的眼罩隨身帶着。
雖然我對這一點並沒有特別感到興趣,但是?因為她戴着眼罩的模樣實在很可愛,因此,我對她這樣的舉動也沒有任何異議。反正都是人類,每一個人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比較與衆不同的地方。
我在日記星期四那一頁上,大致就是寫着這些事情,百分之八十是事實,百分之二十是根據我的觀察所獲知的,這是我寫日記時的方針。
星期五我在銀座的書店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係着一條形狀非常奇怪的領帶,條絞的花樣,上面有無數的電話號碼……。
寫到這裏電話鈴響了。
(2)一八八一年風起雲潛的印地安人
電話鈴響時,時鐘正指在二點三十六分的位置,大概是她打來的電話吧……那個喜歡戴眼罩的女朋友!因為她常在星期天到我傢來,而且,來之前也習慣地會打電話,她應該會買晚飯的菜來,我們决定在當天吃烤牡蠣。
總之,電話響起時是下午二時三十六分,鬧鐘就放在電話的旁邊,每當電話鈴響起時,我就會看時鐘一眼,因此,對於時間我記得特別清楚。
但是,我拿起聽筒時,所聽到的衹是一陣強烈的風聲而已。
衹聽見“喔喔喔喔喔哦!”的叫聲,彷佛一八八一年印地安人風起雲潛時的叫聲從聽筒裏傳了出來,他們瘋狂似地燒掉開拓草屋,切斷通訊綫路。破壞糖的交易協約。
“喂!喂!”
我試着出聲說話,但是我的聲音卻被吸進了壓倒性的歷史狂濤之中。
“喂!喂!”
我大聲地叫,結果卻仍然一樣。
在風聲稍微歇的縫隙間,我覺得好象聽見了女人聲音,或許這衹是我的錯覺而已。總之,風勢太強了,而且,或許野牛的數量已經過份地減少了。
我不說一句話,衹是將聽筒靠在耳邊,並且仔細地聽電話綫的另一端有什麽動靜,但是,同樣的狀態持續了近十秒、或二十秒之後,彷佛神經發作到了極點,生命綫突然拉斷了似的,電話被挂斷了,然後留下了冰冷的沉默。
(3)希特勤入侵波蘭
真是糟糕透了!我嘆了一口氣。然後繼續寫着日記,這個星期的日記將要寫完了。
星期六希特勒的裝甲師團入侵波蘭。蟲炸機突然降臨華爾街上空……。
不,錯了!不是這樣的!
希特勒入侵波蘭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事情,不是昨天。
昨天晚上完飯之後,我走進電影院欣賞梅莉?史翠普演的“蘇菲亞的抉擇”,希特勒入侵波蘭是電影中發生的情節。
梅莉?史翠普在電影中與達斯汀?霍夫曼離婚,然後和在火車站中認識的羅勃特?丹尼洛所扮演的士木技師結婚,是一出非常有趣的電影。
我的旁邊坐着一對高中生,彼此撫摸着對方的肚子。高中生認為能夠撫摸肚子已經很不錯了,我在念高中時也曾經做過這種事。
(4)再進入強風世界
上周的日記全部寫完之後,我坐在唱片架前,挑選着適合在狂風吹襲的星期日午後的音樂。結果我選擇了休斯達哥布基的低音小提琴協奏麯,和斯拉與滾石家庭,我認為這些最適合在強風中欣賞,所以一直聽着這兩張唱片。
窗外不時有東西飛來飛去,一件白色床單好象詛咒師的法術似的,從東飛嚮西。細長的白鐵看板左右搖晃着,彷佛是肛門性交的愛好者,挺不起孱弱的脊椎。
我一邊聽着休斯達哥布基的音樂,一邊看着窗外的風景,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膴話旁的鬧鐘指着三點四十八分。
我拿起聽筒前,猜想這回大樣會聽到波音七四七飛機的引擎似的風聲吧!但是,這次卻一點風聲也聽不見。
“喂喂!”女人的聲音。
“喂喂!”我說。
“我可以現在帶着晚飯的菜去你那裏嗎?”我的女朋友說。
她一定會帶着豐盛的菜和眼罩來到我這裏。
“可以呀!不過……”
“要帶鍋子嗎?”
“不到了,我這裏有。”我說。
“但是,怎麽回事呢?沒有聽到半點風聲。”
“嗯!風已經停了。因為中野三點二十五分就停了,我看你那邊大概也快停了吧!”
“大概是吧!”
我挂了電話,從廚房的餐具架子裏找出大鍋子,放在流理臺上洗淨。
風如她的預告在四點五分前就停了,我打開窗戶,眺望窗外的風景,窗戶下一面有一頭大黑狗,不停地聞着地面上的味道,大約聞了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左右底為什麽會這麽做,我也不太瞭解。
但是除了這件事情之外,整個世界的容貌和係統與起風前並沒有兩樣,喜馬拉雅杉和慄樹若無其事地站立在空地上,晾曬的衣物垂挂在塑料上,烏鴉站在電綫桿上不停地拍動翅膀。
這時候,女朋友也到達了我的傢裏,開始動手做晚飯。
她站在廚房洗鍋子,將切成細絲的白菜和豆腐放在一起。
我問她兩點三十六分時是否曾經打過電話給我。
“打了啊!”
她一邊在鍋子裏淘米,一邊說。
“我什麽也聽不見!”我說。
“嗯!是的,風太強了。”
她若無其事地說。
她若無其事地說。
我從冰箱裏拿出一瓶啤酒,坐在餐桌的角就喝了起來。
“可是,為什麽會突然颳起一陣風,然後又完全地靜止呢?”
我問她。
“這個我也不知道!”
她背對着我,一邊剝着蝦殼一邊說。
“關於風的事情,我們不知道的還屬着呢!就像關於古代史、癌癥、海底、宇宙、和性一樣,我們不知道的還多着呢!”
“嗯!”我說。
除此之外,她再也回答什麽,不過我知道這個話題事實上是無法再深入發展下去的,以我衹好死心地看着她做菜。
“我可以摸摸你的肚子嗎?”
我問她。
“待會兒吧!”她說。
在飯做好之前,我為了下周的日記,先簡單地整理一下今發生的事情。
(1)羅馬帝國的崩潰
(2)一八八一年風起雲涌的印地安人
(3)希特勒入侵波蘭
如此一來,即使是下個星期也能正確地想起今底發生了那些事情,能夠如此有係統的記錄一天之內所發生的事情,這是因為我二十二年來成從不間斷的寫日記習慣。不論颳風、或是颳風,我都能將一天描述得栩栩如生。
■原載:《面包屋再襲擊》.皇冠出版
■譯者:許珀理
(1)羅馬帝國的崩潰
發現開始颳起風這件事情,是在星期天的午後,準確的說,應該是午後兩點七分。
當時我正如同往常一樣─換句話說是如同往常的星期日下午一樣─坐在廚房的桌子前,一邊聽着毫無妨礙的音樂,一邊記着一周的日記;我每天都將發生的事情簡單地記錄下來,等到星期天再將它寫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當我寫完了周二的日記,換句話說,已經完成了三天份的日記時,突然發現窗外颳着猛烈的強風。我不由得不中斷寫日記的工作,將筆蓋套上,到陽臺把曬幹的衣服收了下來。衣服隨着狂風在空中飛舞着,發出了幹裂的聲響。
風勢好象在我不知不覺間慢慢地增強了,當天早上─正確的說法是上午十點四十八分─將洗好的衣服晾到陽臺上去的時候,還沒有發現有任何颳風的跡象,因為我當時心裏想着:“沒有颳半點風,衣服不必用夾子吧!
我可以肯定當時的確沒有颳風。
我將曬幹的衣服整齊地摺叠起來之後,將房間裏的窗戶全部緊緊地關上,關上窗戶之後,幾乎就聽不到一點點風吹的聲音了。窗戶外在一片無聲無息間,樹木─喜馬拉雅杉和慄樹─彷佛一隻耐不住全身發癢的小狗,不停地翻滾着身體。雲朵的碎片像一位眼神兇惡的密使,急速地穿越天空,對面公寓陽臺上還挂着幾件襯衫,像被遺棄的孤兒,緊緊地纏繞在塑料繩上。
好象是臺風來了,我心裏想着。
但是,打開報紙,看看氣象圖,沒有找到任何臺風要來的報導,降雨量也在全年的平均標準以下,從氣象圖上顯示,當時的氣倏就像全盛時期的羅馬帝國一樣,應該是一個非和平的星期天。
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將報紙折好,衣服放進櫥櫃裏,一邊聽着毫無妨礙的音樂,一邊喝着咖啡,而且,一邊喝着咖啡,一邊寫日記。
星期四我和女友上床睡覺,她非常喜歡戴着眼罩做愛,因此她平常總是將飛機上用的眼罩隨身帶着。
雖然我對這一點並沒有特別感到興趣,但是?因為她戴着眼罩的模樣實在很可愛,因此,我對她這樣的舉動也沒有任何異議。反正都是人類,每一個人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比較與衆不同的地方。
我在日記星期四那一頁上,大致就是寫着這些事情,百分之八十是事實,百分之二十是根據我的觀察所獲知的,這是我寫日記時的方針。
星期五我在銀座的書店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係着一條形狀非常奇怪的領帶,條絞的花樣,上面有無數的電話號碼……。
寫到這裏電話鈴響了。
(2)一八八一年風起雲潛的印地安人
電話鈴響時,時鐘正指在二點三十六分的位置,大概是她打來的電話吧……那個喜歡戴眼罩的女朋友!因為她常在星期天到我傢來,而且,來之前也習慣地會打電話,她應該會買晚飯的菜來,我們决定在當天吃烤牡蠣。
總之,電話響起時是下午二時三十六分,鬧鐘就放在電話的旁邊,每當電話鈴響起時,我就會看時鐘一眼,因此,對於時間我記得特別清楚。
但是,我拿起聽筒時,所聽到的衹是一陣強烈的風聲而已。
衹聽見“喔喔喔喔喔哦!”的叫聲,彷佛一八八一年印地安人風起雲潛時的叫聲從聽筒裏傳了出來,他們瘋狂似地燒掉開拓草屋,切斷通訊綫路。破壞糖的交易協約。
“喂!喂!”
我試着出聲說話,但是我的聲音卻被吸進了壓倒性的歷史狂濤之中。
“喂!喂!”
我大聲地叫,結果卻仍然一樣。
在風聲稍微歇的縫隙間,我覺得好象聽見了女人聲音,或許這衹是我的錯覺而已。總之,風勢太強了,而且,或許野牛的數量已經過份地減少了。
我不說一句話,衹是將聽筒靠在耳邊,並且仔細地聽電話綫的另一端有什麽動靜,但是,同樣的狀態持續了近十秒、或二十秒之後,彷佛神經發作到了極點,生命綫突然拉斷了似的,電話被挂斷了,然後留下了冰冷的沉默。
(3)希特勤入侵波蘭
真是糟糕透了!我嘆了一口氣。然後繼續寫着日記,這個星期的日記將要寫完了。
星期六希特勒的裝甲師團入侵波蘭。蟲炸機突然降臨華爾街上空……。
不,錯了!不是這樣的!
希特勒入侵波蘭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事情,不是昨天。
昨天晚上完飯之後,我走進電影院欣賞梅莉?史翠普演的“蘇菲亞的抉擇”,希特勒入侵波蘭是電影中發生的情節。
梅莉?史翠普在電影中與達斯汀?霍夫曼離婚,然後和在火車站中認識的羅勃特?丹尼洛所扮演的士木技師結婚,是一出非常有趣的電影。
我的旁邊坐着一對高中生,彼此撫摸着對方的肚子。高中生認為能夠撫摸肚子已經很不錯了,我在念高中時也曾經做過這種事。
(4)再進入強風世界
上周的日記全部寫完之後,我坐在唱片架前,挑選着適合在狂風吹襲的星期日午後的音樂。結果我選擇了休斯達哥布基的低音小提琴協奏麯,和斯拉與滾石家庭,我認為這些最適合在強風中欣賞,所以一直聽着這兩張唱片。
窗外不時有東西飛來飛去,一件白色床單好象詛咒師的法術似的,從東飛嚮西。細長的白鐵看板左右搖晃着,彷佛是肛門性交的愛好者,挺不起孱弱的脊椎。
我一邊聽着休斯達哥布基的音樂,一邊看着窗外的風景,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膴話旁的鬧鐘指着三點四十八分。
我拿起聽筒前,猜想這回大樣會聽到波音七四七飛機的引擎似的風聲吧!但是,這次卻一點風聲也聽不見。
“喂喂!”女人的聲音。
“喂喂!”我說。
“我可以現在帶着晚飯的菜去你那裏嗎?”我的女朋友說。
她一定會帶着豐盛的菜和眼罩來到我這裏。
“可以呀!不過……”
“要帶鍋子嗎?”
“不到了,我這裏有。”我說。
“但是,怎麽回事呢?沒有聽到半點風聲。”
“嗯!風已經停了。因為中野三點二十五分就停了,我看你那邊大概也快停了吧!”
“大概是吧!”
我挂了電話,從廚房的餐具架子裏找出大鍋子,放在流理臺上洗淨。
風如她的預告在四點五分前就停了,我打開窗戶,眺望窗外的風景,窗戶下一面有一頭大黑狗,不停地聞着地面上的味道,大約聞了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左右底為什麽會這麽做,我也不太瞭解。
但是除了這件事情之外,整個世界的容貌和係統與起風前並沒有兩樣,喜馬拉雅杉和慄樹若無其事地站立在空地上,晾曬的衣物垂挂在塑料上,烏鴉站在電綫桿上不停地拍動翅膀。
這時候,女朋友也到達了我的傢裏,開始動手做晚飯。
她站在廚房洗鍋子,將切成細絲的白菜和豆腐放在一起。
我問她兩點三十六分時是否曾經打過電話給我。
“打了啊!”
她一邊在鍋子裏淘米,一邊說。
“我什麽也聽不見!”我說。
“嗯!是的,風太強了。”
她若無其事地說。
她若無其事地說。
我從冰箱裏拿出一瓶啤酒,坐在餐桌的角就喝了起來。
“可是,為什麽會突然颳起一陣風,然後又完全地靜止呢?”
我問她。
“這個我也不知道!”
她背對着我,一邊剝着蝦殼一邊說。
“關於風的事情,我們不知道的還屬着呢!就像關於古代史、癌癥、海底、宇宙、和性一樣,我們不知道的還多着呢!”
“嗯!”我說。
除此之外,她再也回答什麽,不過我知道這個話題事實上是無法再深入發展下去的,以我衹好死心地看着她做菜。
“我可以摸摸你的肚子嗎?”
我問她。
“待會兒吧!”她說。
在飯做好之前,我為了下周的日記,先簡單地整理一下今發生的事情。
(1)羅馬帝國的崩潰
(2)一八八一年風起雲涌的印地安人
(3)希特勒入侵波蘭
如此一來,即使是下個星期也能正確地想起今底發生了那些事情,能夠如此有係統的記錄一天之內所發生的事情,這是因為我二十二年來成從不間斷的寫日記習慣。不論颳風、或是颳風,我都能將一天描述得栩栩如生。
原載:《面包屋再襲擊》.皇冠出版
■譯者:許珀理
(1)
這樣的事在這個世界上,或許是非常普遍的,我對於妹妹的未婚夫始終未曾有過好感,而且,我甚至覺得妹妹竟然會决心和這樣的男人結婚,實在令人感到懷疑。說得坦白一點,我覺得很失望。
或許這樣的想法是我偏狹的性格所造成的。
至少妹妹是這樣認為。然我們表面上都不以此為話題,但是,我對她的未婚夫不太滿意這一點,妹妹也非常瞭解,對於我這樣的想法,妹妹也覺得非常不高興。
“你對事情的看法眼光太狹窄了”妹妹對我說。
當時我們正在談論意大利面,她所說的應該是指我對意大利面的看法眼光太狹窄吧!
但是,妹妹當然不會衹針對意大利面的問題,在意大利面之前還有她的未婚夫,所以,事實上妹妹所指的應該是未婚夫的問題。這種情形就是所謂的藉題發揮。
事情的開端是緣於妹妹邀我一起在星期天的中午吃意大利面,因為我也有點兒想要吃意大利面,於是就隨口說:“好吧!”
於是我們就走進車站前一傢新開的意大利面館,我點了茄香洋蔥意大利面,妹妹點了傳統的意大利肉醬面。
面送上來之前,我一直喝着啤酒,到此為止沒有出現任何問題。這是五月裏的一個星期天,天氣非常晴朗。
問題出在送來的意大利面的味道,面表面看起來是煮熟了,其實心還是硬的,奶油好象是用煮狗食的劣等貨冒充,我勉強吃下了半盤就放棄了。
妹妹擡頭看了我一眼,不說一句話,依舊慢慢地將自己盤中的面吃完。
這時候我一邊欣賞窗外的風景,一邊喝下第二罐的啤酒。
“喂!怎麽剩這麽多就吃不完了,多可惜啊!”
妹妹將她盤子裏的面吃完了之後說。
“太難吃了!”我回答。
“都吃下去一大半,應該不算太難吃吧,衹要稍微忍耐一下,一定可以吃完的!”
“想吃的時候吃,不想吃的時候就不吃,這是我的胃,不是你的胃!”
“這傢店纔剛開張不久,廚房可能還不熟練,你就稍微寬容一下,不行嗎?”
妹妹看着送上來口味清淡的附餐咖啡說。
“雖然你說的也有道理,但是,不好吃的食物就應該將它留下來,這也是一種常識。”
我嚮她說明。
“你是什麽時候開始變得如此偉大的呢?”妹妹說。
“你聽了不舒服是嗎?”我說“口氣這麽不好,是不是生理期?”
“討厭啦!請你不要再說些奇怪的話了!你以前不說這些的。”
“有什麽關係,我對你第一次的月事什麽時候來也都非常清楚。我記得你的第一次來得很晚,媽媽還陪你一起去看醫生呢?”
“你閉嘴不說話也沒有人當你是啞巴!”她說。
我知道她是真的生氣了,所以衹好聽她的話閉上嘴巴。
“大概是你對事情的看法都太偏激了!”
她一邊在咖啡裏水加入了一些奶精,一邊說。
一定是這杯咖啡太難喝了。
“不論什麽事情你衹是將缺點找出來,大肆批判,好的地方你這看都不看。
衹要與你的標準不合,你一概不加以理會,這種情形以旁人的眼光來看就是神經病!”
“這是我自己的人生,與你無關!”我說。
“可是你出口傷人,故意找人麻煩!你這個衹會手淫的傢夥!”
“手淫!”我大吃一驚地說。“你到底在說些什麽?”
“你在念高中的時候經常喜歡手淫,每次都把內褲都髒了,你應該也很清楚,那些東西洗起來是很纍人的,可是你卻一做再做,你不是故意給人添麻煩嗎?”
“我以後會小心一點!”我說“不要再提這件事情了,我有我自己的人生,有我喜歡的東西,有我討厭的東西,這是這我自己都無法改變的啊!”
“但是,你不可以傷人!”妹妹說。
“為什麽你不稍微努力一下呢?為什麽你不往好的地方去看呢?
為什麽你不願意多忍耐一點呢?為什麽你一直都沒有成長呢?”
“我是正在成長!”
我覺得自己已經被傷害了。
“我也要求自己要多忍耐、多往好的方面看,衹是我的觀點和你不一樣罷了!”
“你這種情形衹有傲慢兩個字足以形容,所以你到了二十七歲仍然找不合適的對象!”
“我有女朋友啊!”
“那些人衹不過是睡睡覺罷了!”妹妹說。“不是嗎?每年更換一個睡覺的對象,這樣纔感到快樂嗎?沒有快理想、沒有愛情,也不用相互體諒,這到底有什麽意義呢?和手淫沒有兩樣吧?”
“我哪有一年換一個?”
我毫無力氣地說。
“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妹妹說。
“你能不能稍微認真思考一下,過着認真一點的生活,稍微像個大人的模樣?”
我們的談話到此結束,從此之後,不管我說什麽,她都不願意再回答。
為什麽她會對我産生如此偏激的想法呢?我也不大清楚。大約在一年前,還和我一起生活得非常愉快,而且從來不會反駁過我的想法。她會開始批評我,是在她認識了她的未婚夫之後。
這種事情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和她已經相處了二十三年,雖然每一件事情我們都是率直地商量,但是說起來仍是一對感情相當不錯的兄妹,幾乎從來不曾吵過架。
她知道我手淫的事情,我也知道她初潮的事情;她知道我第一次買保險套的事情(在我十七歲的時候),我也知道她第一次買有蕾絲的內褲時的事情(在她十九歲的時候)。
我和她的朋友約過會(當然沒有上床睡覺),她也和我的朋友約過會(我想應該也應該沒有上床睡過覺),總之我們是在一個非常相同的環境下長大的。
這樣友好的關係,在一年前開始變質,一想到這件事我就越來越生氣。
妹妹說要到車站前的百貨公司看鞋,我衹好一個人回到公寓裏。然後打電話給女朋友,可是她不在傢,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從不在星期天下午兩點鐘突然打電話給她,約她出來見面。
我放下電話筒,翻動記事本,找到了另外一個女孩子的電話,這是一個知道哪裏有狄斯可舞廳的女大學生,她在傢裏。
“出來喝點東西吧!”我邀她。
“纔下午兩點鐘!”
她不耐煩地說。
“時間不是問題!出來喝點柬西,很快就天黑了。”我說。“我知道一個以看夕陽聞名的酒吧,下午三點過後再去的話,就沒找不到好位子了。”
“你這個人真是討厭!”她說。
但是她還是出來了,大概是一個性格親切的人吧!
我將車子沿着海岸過去,一直開到橫濱附近,如約定地,到一個看得見海濱的酒吧。
我在這裏喝了四杯加冰塊的i.w.哈伯酒,她則喝了兩杯香蕉水果酒,看着夕陽。
“你喝了這麽多的酒,還能夠開車嗎?”
她擔心問。
“不要擔心。”我說。“我的酒量好得很,四杯算不得什麽!”
“算了,你最愛吹牛!”她說。
然後我們又回到橫濱吃晚餐,在車子裏我吻了她,邀她一起上旅館,她說:不行啦!
“月經來,還放着衛生棉條呢!”
“拿下來就可以了!”
“別開玩笑了,還有兩天呢!”
算了!我心裏想着。今天到底是什麽日子呢!如果早知道會有這種事情發生,我就不會找她出來了。好久不曾和妹妹一起悠閑地度過一天,我原本打算這個星期天在傢裏陪她的。
“對不起!但是,我絶對沒有騙你哦!”
這個女孩子說。
“沒有關係,別挂在心中,不是你不對,是我不好。”
“我的生理期和你不好有什麽關係?”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我不應在這個時候去找你!”我說。
真的是這樣嗎?難道我真的非得對一個認識不深的女孩子的生理期了若指掌嗎?
我開車將他送回世𠔌田的傢中,中途車子一直喀喀作響,我心裏嘆氣着想着:大概該將它送進修車場裏整修一番了吧!
好象衹要有一件事進行不順利的話,這一整天就會連鎖地不好的方向發展下去似的。
“我最近還能約你出來嗎?”我問。
“約會?或者上旅館?”
“兩個都有!”我坦自地說。“這麽說的話,比較表裏一致,就像牙刷和刷牙一樣。”
“是呀!這是正確的想法!”她說。
“這麽想的話,頭腦比較不會老化。”我說。
“到你傢去如何?不能去玩嗎?”
“不行,因為我和妹妹住在一起,我們早已有約定,我不可以帶女孩子回傢,妹妹也不可以帶男生回來。”
“真的是妹妹嗎?”
“當然是真的,要不然我下次帶戶口簿給你看!”
她笑了笑。
等到這個女孩子消失在她傢的大門口裏,我纔重新發動引擎,回到我住的公寓。
一路上耳邊不停地響着引擎所發出的喀喀聲。
房間裏一車漆黑,我打開車鎖,大聲叫着妹妹的名字,但是她卻不在房間裏。
我心裏想着,已經十點多了,她會到哪裏去呢?
接着我就去找晚報來,但是沒有找到,因為今天是星期天,不送報。
我從冰箱裏拿出一瓶啤酒,和杯子一起拿到客廳。打開錄放機,看着新的連續劇。一邊喝着啤酒,一邊控製聲量的開關,但是,無論如何總是聽不到聲音。這時候我纔發現錄像機早在三天前就壞掉,雖然開了電視,但是聲音仍然無法出來。
在沒有更好的方法之下,我衹好看着無聲的電視畫面,喝着啤酒。
電視正在放映一部古代戰爭電影,羅馬帝國的戰車遠征非洲,炮戰車擊出無聲的大炮,自動槍也發出瀋默的彈音,人們在無言中靜靜地死去。
唉!算了!我又嘆了一聲氣,這大概是當天的第十六次嘆息吧!
(2)
我和妹妹二個人生活在一起,大約是五年前的春天開始的吧!當時我二十二歲,妹妹十八歲;換句話?
a我剛從大學畢業,準備找工作,而妹妹剛高中畢業,準備去念大學。我的父母表示;如果和我住在一起的話,就允許妹妹到東京念大學。妹妹說:沒有關係。我也說:隨便。於是父母就為我們找到了一間有個房間的寬敞公寓,房租由我負擔一半。
前面已經敘述過了,我和妹妹兩個人的感情非常好,兩個人生活在一起絶對不會讓我有任何痛苦的感覺。因為我任職於電機製造公司的廣告部,早上上班的時間比較晚,晚上則比較遲回到傢裏;而妹妹一大早就去上學了,傍晚就回到傢裏。因此,經常是我醒來時,她已經出門;我回到傢裏時,她又已經睡着了;再加上星期六、星期天我都花費在和女孩子的約會上,所以一個星期裏衹有和她說兩三句,但是,我認為這種情形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因為我們幾乎沒有吵架的時間,也沒有空閑去干涉對方的私事。
雖然我想她可能也會有很多不尋常的事發生,但是,我一點也不想說出口,她已經是超過十八歲的女孩子了,想和什麽人上床睡覺,我沒有干涉的權利。
但是,有一次半夜一點到三點,我一直牢牢地握着他的手。我下班之後回到傢裏,看見她坐在廚房的餐桌前哭泣,我推測她會坐在餐桌前哭泣,大概是想要跟我要求什麽東西吧!否則她衹要坐在自己的床上哭就夠了,何必讓我看見呢?雖然我確實是一個?
噶e又任性的人,但是,這樣的事情我還是可以推想得到的。
所以,我就坐在她的身邊,輕輕握住她着手。握着妹妹的手這種事情,自從小學時代一起去抓蜻蜓以來,從來未曾再發生過,妹妹的手比記憶中的─那當然是非常久遠以前的記憶─要大得非常多了。
結果她就這樣一直坐着,不說一句話地哭了兩個小時。她的身體內竟然屯積了這麽多的淚水,這實在太令我驚訝了,要是我的話,大概哭不到兩分鐘全身就幹涸了。
但是,到了三點時我已經開始覺得有些纍,再不結束的話,我也撐不下去了。在這個時候,身為兄長的我,不說句話是不行的,雖然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但是,我還是開口說話。
“我對你的生活完全不想干涉!”我說。“你想要過什麽樣的生活就隨着自己的喜好去過吧!”
妹妹點點頭。
“但是,我一直想給你一句忠告,最好能隨時在皮包裏放一個保險套,你當然有別於那些賣春婦。”
聽我這麽一說,她隨手拿起放在桌上的電話簿,突然用力地朝我丟了過來。
“你憑什麽偷看我的皮包!”
她大聲怒駡。
我知道她這個時候已經氣憤到了極點,為了不使她再受到任何刺激,我當然不能對她說我從來不曾去偷看過她的皮包。
但是,不論如可她是已經停止哭泣,而我也能夠回到自己房間,鑽進被窩裏去。
妹妹大學畢業之後,任職於旅行,但是我們的生活形態仍然沒有絲毫改變。她的上班時間是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非常有規律,而我的上班時間則和一般人回異,中午纔進到辦公室,然後坐在辦公桌前一邊看報紙、一邊吃中飯,下午兩點鐘左右纔開始真正的工作,傍晚又得到廣告公司去談生意,飲酒應酬,每天都必須到了深夜才能回傢。
在旅行社上班的第一年暑假,她和一位女朋友一起到美國西海岸觀光旅行(旅費當然是采用分期付款的)。在這趟美國之旅,她認識了一位年長他很多的計算機工程師。回到日本之後,仍然經常與他見面。雖然這種事情也是非常多見,但是絶對不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因為我對這種瘋g大採購的旅行團一點兒也不感興趣。
自從和那位計算機工程師交往以來,妹妹似乎比以後更為開朗,傢事也收拾得整整齊齊,穿着打扮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她非常喜歡穿工作服,或牛仔褲、卡其裙,現在則換上色彩鮮豔的裙裝,而且每件衣服都親自用手洗,仔細的熨燙,經常自己下廚、打掃房間。
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徵候,如果看到了女孩子有這個徵候,男孩子通常有兩種反應,一種是立刻逃開、一種是馬上下了結婚的决定。
後來妹妹又拿了那位計算機工程師的照片給我看,這是妹妹第一次拿她男友的照片給我看,這也是一種危險的徵候。
照片有兩張,其中一張是在舊金山的海邊照的,妹妹和那位工程師兩人並肩而站,兩個人都面帶盈盈的笑意。
“好漂亮的海岸綫喔!”我說。
“別開玩笑了!”妹妹說。“我是非常嚴肅的。”
“你要我說什麽好呢?”
“你最好什麽也別說!”
我再仔細看一下手上這張照片,如果世界上真有那種一眼看去就令人非常討厭的的話,就是這種臉了。而且,這種計算機技師長得和我高中時代最討厭的社團前輩很像,雖然長相不差,但是故意裝出一副頭腦精明、盛氣凌人的模樣。
“你們上過幾次床了?”我問。
“你鬍說些什麽?”
妹妹說着,滿臉脹紅。
“請你不要老以自己的尺度來衡量這個世界,你以為天底下所有人都和你一樣的嗎?”
第二張照片是回到日本之後纔照的,照片裏衹有計算機工程師一個人,他穿着一件皮背心,靠在一輛大型摩托車上,座椅上永着一頂安全帽,這張臉的表情完全和在舊金山時一模一樣,大概是他再也沒有別的表情了。
“他很喜歡騎機車。”妹妹說。
“我看得出來。”我說。“不喜歡騎機車的人是不會穿這種皮背心的。”
我……大概又是因為個性偏激的緣故所造成的……於喜歡騎機車的人都不具有好感,因為這些人大多比較驕傲,喜歡裝模做樣;但是,對於照片上這個人,我不想加以批評。
我靜靜地把照片還給妹妹。
“可是……”我說。
“可是什麽?”妹妹說。
“可是,你打算怎麽辦呢?”
“不知道!或許會和他結婚吧!”
“他嚮你求婚了嗎?”
“嗯!”她說。“可是我還沒有給他答復。”
“嗯!”我說。
“老實說是因為我覺得我纔剛開始上班而已,還想自己一個人自由地遊樂一番。當然,不同於你那種過於偏激的想法。”
“應該說是健全的想法。”
我強調地說。
“可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好人,和他結婚也不錯。”妹妹說。“所以想問問你的意見。”
我拿起卓上的照片再仔細地再看一次,心裏想:“還是算了吧!”
這是聖誕節前的事情。
(3)
過完年後不久,有一天一大清早九點多鐘,媽媽打電話過來,我正在聽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生在美國”,一邊刷着牙。
母親問我知不知道妹妹交男朋友的事情。
不知道,我說。
母親說她收到妹妹的信,信上說兩個禮拜後妹妹要帶那個男的一起回傢。
“該不是想要結婚了吧!”我說。
“所以我想問看看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媽媽說。“我希望能在見面之前對他多瞭解一點。”
“這個嘛!因為我也沒有和他見過面,對這個人不怎麽清楚,我衹知道是一個年齡滿大的工程師,好象是在ibm或什麽公司上班,公司的名字是三個英文字母,要不然就是nec、或ntt。我衹看過照片,長得不是頂好的,而且又不是我要結婚,所以我對他沒什麽興趣。”
“哪一個大學畢業的?傢住在哪裏?”
“這件事我怎麽會知道呢?”我說。
“你不會去找他見個面,瞭解一下嗎?”
“我不喜歡做這種事情,我的工作太忙,你不會兩禮拜見面之後再問他嗎?”
結果,我比媽媽更早和這位計算機技師碰面。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妹妹說要到他傢去做正式的拜訪,我衹好義不容辭地答應作陪。穿妥白襯衫、係上領帶,再穿上最得意的西裝,就到他傢去了。那是一棟位在古老住宅街道正中央,非常豪華的住傢,院子裏停放着照片上經常看得見的五百cc摩托車。
“哇塞!這麽高級的住宅!”
“今天真的要拜托你,千萬別再玩笑了,正經一點可以嗎?”妹妹說。
“是的!遵命!”我說。
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規矩─稍微太規矩而變得有點兒嚴肅─,而且非常厲害的人,他的父親是石油公司的重要幹部,我的父親在靜岡擁有一座石油的連鎖店,所以這一方面我們之間的關係不算太遠。
他的母親母親用一個高級的盤子,端着茶出來。
我嚮他們規矩地打過招呼之後,遞上瞭瞭我的名片,並且嚮解釋,本來應該由我的父母來拜訪,但是正好他們今天有事不能來,所以就由我來代理,改天他們會正式來拜見二位。
“我聽兒子說過好幾次了,今天看見了果然不假,是一位標緻的小姑娘,而且我知道一定是一位好女孩。”
他的父親說。
我心裏想,他一定是調查得非常詳細了。或許連十六歲都尚未初潮,以及深受便秘所苦這種小事,都知道得一清楚呢!
等到這些客套話都結束之後,他的父親為我倒了一杯白蘭地,這種白蘭地的味道實在美極了,我們一邊喝着,一邊談着各自工作上的事情,妹妹穿着拖鞋踢了我一下,提醒我不要喝得過多。
這時候身為兒子的計算機技師一言不發,緊張地端坐在父親身旁,一眼就可以看,在這個屋檐,他完全受父親大權的支配,他身上穿着一件我以前從來不曾看過,樣式非常奇怪的毛綫衣,毛綫衣裏面是一件顔色非常不諧調的襯衫,看起來讓人覺得這個男孩子很奇怪。
談話告一個段落之後,我看看手錶,已經四點了,於是站起身來,準備告辭。
計算機技師送我們兩個人到車站。
“找個地方一起喝喝茶好嗎?”
他邀請我和妹妹。雖然我對喝茶沒興趣,也不想和穿着這麽奇怪毛綫衣的男孩子同桌,但是,斷然拒絶可能會讓他覺得不好意思,衹好同意三個人一起到附近的咖啡店喝茶。
他和妹妹都點咖啡,點了啤酒,可是這裏沒有賣啤酒,沒有辦法我衹好也喝咖啡。
“今天真是謝謝你,幫了一大忙!”
我嚮我道謝。
“那裏的話,這是我應該的。”
我學着大人的口吻說,因為我已經沒有一點點多餘的力氣開玩笑了。
“常常聽她提起大哥的事。”
大哥?
我用咖啡匙的柄挖挖耳朵,再把它放回桌上。然妹妹又用腳踢了我一腳,但是,我覺得計算機技師應該是不懂這個動作的意義。
“看你們兩個人感情這麽好,實在讓我非常羨慕。”他說。
“一有高興、有趣的事情,我們就互踢彼此的腳。”我說。
計算機技師一副不解的表情。
“他在開玩笑啦!”
妹妹不太高興地說。
“他講話就是這樣的!”
“我是在開玩笑的。”我也說。
“兩個人住在一起,總得彼此分擔傢事,她分到的是洗衣服,我分到的是講笑話。”
這位計算機技師─正確的名字叫做渡邊升─聽了之後也稍微安心地笑了笑。
“氣氛爽朗一點不是很好嗎?我也想擁有一個這樣的家庭,氣氛爽朗是最重要的。”
“說得也是啊!”
我對着妹妹說:
“氣氛爽朗是最重要的,你太神經質了。”
“不要再開玩笑了。”妹妹說。
“我想盡可能在秋天結婚。”渡邊升說。
“結婚儀式還是在秋天舉行最好。”我說。
“還可以叫慄鼠和大熊一起來參加。”
計算機技師哈哈大笑,妹妹卻沒有笑,她好象是真的生氣了。因此,我就推說另外有事,然後起身離席。
回到公寓之後,我打電話給母親,說明了整個事件大致的情形。
“這個男孩還不怎麽壞。”
我一邊掏耳朵一邊說。
“不怎麽壞是什麽意思?”
“意思是說人滿誠實的,至少和我比起來算是老實人。”
“和你當然是沒得比了。”母親說。
“真高興聽到你這麽說我,謝謝了!”
我一邊看着天花板,一邊說。
“那麽,他是哪一個大學畢業的呢?”
“大學?”
“哪一個大學畢業的呢?那個計算機工程師。”
“這種事你可以問問當事人。”
我說着就把電話挂斷。
然後就從冰箱裏拿出一瓶啤酒,心情非常鬱悶地一個人喝着酒。
(4)
為了意大利面而和妹妹吵架的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上午八點半纔起床。
和前一天一樣,天空中沒有半片烏雲,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我覺得好象全完是昨天的延續似的,夜裏一時中斷的人生又重新開始了。
我將汗濕了的睡袍和內褲丟道洗衣槽裏,淋了浴,又剃了鬍須。一邊剃的時候,一邊想着昨天晚上的那個女孩,實在非常懊惱。不過,遇到這種無可抵抗的事情也實在是莫可奈何。不過,以後還有機會,說不定下個星期天一切都會很順利。
我到廚房烤了兩片面包,燒了一壺咖啡,原本想聽聽fm播放的節目,但是想到錄像機的監聽係統已經壞,衹好作罷。改為一邊看報紙的讀書欄,一邊啃着面包。讀書欄裏介紹的新書沒有一本是我想要看的,那裏的書不是關於“年老猶太人的空想與現實交錯所造成的性生活”,就是關於分裂癥治療的歷史性考察,實在搞不懂,報社那些編輯大人為什麽要選擇這樣奇怪的書來介紹。
吃完了一片烤得焦硬的面包之後,把報紙放回桌上,這時候纔發現果醬瓶子下面放着一張紙條。紙條上是妹妹一貫的字跡,她寫着:因為星期天的晚上要叫渡邊升一起來吃晚餐,所以希望我也能夠留在傢裏,和他們一起共進晚餐。
我吃完了早餐,撥撥掉落在襯衫在面包屑,將餐具放進了水槽,打電話到到妹妹上班的旅行社。
妹妹接到電話之後:
“現在我手邊的事情非常忙,十分鐘之後再打電話給你。”
二十分鐘之後果真打電話過來,在這二十分鐘之內,我一共做四十三次的伏地挺身,手腳合計剪了二十根指甲,穿好襯衫、打好領帶、選好了長褲,並且刷了牙,梳了頭髮,打了兩個哈欠。
“你看到我的留言了嗎?”妹妹說。
“看了!”我說“但是,這實在糟糕透,這個星期天我早就好別人約好,如果能夠早一點說的話那就好了。
現在纔知道實在非常可惜。”
“你不要說得那麽可憐!我想你這個約大概是和一個連名字都記不清的女孩子吧!”妹妹語氣冷淡地說。“不可以改在期六嗎?”
“星期六一整天都必須待在錄像室裏,因為現在正在製作電動抹布,所以那一天會非常的忙。”
“那麽就跟她取消好!”
“那麽你來付取消費吧!”我說。“現在是一種非常微妙的階段。”
“沒有那麽微妙吧!”
“雖然不應該是這樣…”我坐在椅子上一邊整理襯衫和領帶,一邊說。“我們不是早就約定好不侵彼此的生活嗎?你和你的未婚夫共進晚餐─我和我的女朋友約會,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好,你一直都沒有和他好好聊過吧,從我們認識以來,你衹和他見過一次面,而且那是四個月的事情,不是這樣嗎?雖然你們也有好幾次見面的機會,可是你每一次都故意逃開,難道你不覺得這樣很不禮貌嗎?他是你妹妹的未婚夫,我求你和他一起吃頓飯,好嗎?”
因為妹妹說話也有她的道理,所以我也衹好默默的無以言對。確實我總是用最自然的方法來逃避和渡邊升見面,而且渡邊升和我之間實在沒有任何共通的話題,我講的笑話他也聽不懂。
“拜托你啦!衹要這一天就好了,從此以後,到這個夏天為止,我不會再去打擾你的性生活了。”妹妹說。
“我的性生活不算什麽啦!”我說。“或許到這個夏天結束之前都不會再發生。”
“不管怎麽樣,請你星期天一定要待在傢裏。”“我無能為力!”我斷然地回絶她。
“說不定他會幫你修理錄像機,那個人在這個方面非常擅長。”
“還有這點好處呢!”
“你不要老想那些奇怪的事!”
妹妹說着就挂斷電話。
我係好領帶就出門上班去了。
這個禮拜一直都是晴朗的好天氣,好象是每天都是每天的延續似的,星期三的晚上,我打電話給我的女友,告訴她為工作忙碌,這個周末不要見面。因為我已經三個禮拜不曾和她見面了,所以她當然不太高興。接着我沒有放下話筒,繼續撥電話給那個女大學生,但是她不在傢,星期四、星期五她都沒有在傢裏。
星期天早上,我八點就被妹妹叫起來了。
“我要洗床單,你不能再睡那麽晚。”她說。
然後就拆下枕頭套和床單,也叫我脫下睡衣,我沒有地方去,衹好進浴室洗個澡,順便颳颳鬍須。我覺得這個傢夥愈來愈像媽媽了,原來女人也和鮭魚一樣,無論過程如何,最後總會回到相同的場所。
洗完澡之後,我穿上一件短褲,套上一件胸前的字幾乎都已褪盡了的t恤,打了一個長長的哈欠,然後開始喝柳橙汁。覺得體內還留存着昨夜的酒精,連報紙也不想看了。桌子上有一個蘇打餅幹的盒,於是我就拿了三、四片來吃,代替早餐。
妹妹將被單放到洗衣機裏,然後就不停地收拾整理我的房間和她自己的房間,整理完了之後,又用洗潔劑擦洗着客廳和廚房的墻壁和地板。
我一直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翻開美國朋友送我的裸女照片,仔細觀察研究一番之後纔發現,女性性器事實上也有大小不同之別,和身高、以及智商是完全一樣的。
“嘿!看你在這裏閑着無聊,不如幫我買東西吧!”
妹妹說着,就硬塞給我一張寫滿採購物品名單的紙條。
“請你不要在這裏看這種書,這個人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把裸照放在桌子上面,瞪着紙條。萵苣、蕃茄、芹菜、沙拉醬、熏魚、洋蔥、濃湯包、馬鈴薯、洋芹菜、牛排肉三片……。
“牛排肉?”我說。“我昨天才吃了牛排,我不想再吃牛排,吃炸肉餅比較好!”
“或許你昨天真的吃了牛排,但是我們沒有吃啊,請你不要那麽自以為是,而且,沒有人會用炸肉餅來招待客人的吧!”
“如果有女孩子請我到她傢裏去吃炸肉餅的話,我一定會非常感動,再端出一盤切得細細長長的白甘籃菜、香濃的味噌湯……這種吃法多麽生活化啊!”
“不管怎麽樣,今天已經决定吃牛排了,殺了我也不願意做炸肉餅你吃,今天你就不要再自以為是,和我們一起吃牛排吧!求求你。”
“好吧!”我說。
雖然有時候我的怨言似乎多了一些,但是歸根究底我還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
我到鄰近的超級市場照着菜單購物,然後又到附近的酒店買了一瓶四千五百圓的香檳,打算以這瓶香檳作為送給他們兩個人的訂婚禮物。我想大概衹有非常親切的人才會為他們設想得如此周到。
回到傢之後,看到我的床上端放着一件摺叠整齊的馬球襯衫,和一件沒有一點點縐紋的棉質長褲。
“換上這套衣服!”妹妹說。
算了!換就換吧!我心裏想着,不說半怨言就把衣服換了下來。不論我還有什麽意見,今天還是順着她的意思,這樣會覺得氣氛和平些。
(5)
渡邊升在下午三點準時出現,當然是騎着摩托車來的。他那輛五百CC機車的排氣聲,遠在五百公尺遠的地方就聽得一清二楚。從陽臺探頭出去往下看,看見他將摩托車停靠在公寓玄關旁,然後脫下了安全帽。非常值得慶幸的是,他在脫下安全帽之後,身上所穿的服裝還算正常。一件花格子衫,配一件白色長褲,再加上一雙咖啡色的鞋,唯一顯得唐突的是鞋子和皮帶的顔色不搭調。
“好象是我們傢大小姐的朋友來了!”
我對着正在流理臺削馬鈴薯皮的妹妹說。
“能不請你先招呼他一下,我現在得忙着廚房的事情。”妹妹說。
“這樣不太好吧!他是為你而來的,更何況我和他也沒有什麽話講,還是讓我來煮飯,你們兩個人去聊天。”
“別胡闹了!你會煮飯嗎?快去招呼客人吧!”
電鈴一響,打開大門,渡邊升就站在門口。我帶他到客廳,讓他坐在沙發上。他帶了一盒特大號的冰淇淋來當做禮物,但是,我們傢的冰箱冷凍庫太小,根本裝不下這麽大盒的冰淇淋。我覺得他像一個還需要照顧的大男孩,到女友的傢做客竟然還帶着冰淇淋。
接着我問他想不想喝啤酒,他回答不喝。
“體質不適合喝酒。”他說。“不知道為什麽,喝一大杯啤酒下肚就覺得很惡心。”
“我在學生時代曾和朋友打賭,喝了一打啤酒,結果購了不少錢。”我說。
“喝完了有什麽感覺呢?”渡邊升問。
“整整兩天小便裏都有啤酒的臭味。”我說。“而且,不停地放屁……”
“喂!請你幫忙看看錄像機吧!”
妹妹好象看見了不吉的煙幕,端了兩杯柳橙汁在桌上說。
“好啊!”他說。
“聽說你很能幹?”我問。
“還好啦!”
他沒有絲毫不高興的回答。
“以前我非常喜歡組合型玩具、或收音機,傢裏有什麽電器壞了,都是由我來修理。錄像機什麽地方壞掉了呢?”
“沒有聲音!”
我拿起遙控器,按下電源讓他瞭解聲音出不來的情形。
他坐在電視機前,一一地去按電視機上的按鈕。
“安培係統壞掉,裏面沒有什麽問題。”
“你怎麽知道的?”
“用歸納法。”他說。
歸納法?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於是他將所的綫路全部拆了下來,一個一個仔細檢查。這時候我從冰箱裏拿出一瓶易開罐的啤酒來,坐在一旁一個人喝。
“喝酒好象是一件滿有趣的事情?”
他一邊用蠃絲起子轉着蠃絲,一邊對我說。
“還好啦!”我說。
“我喝了這麽多的酒,也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因為我來不去比較。”
“我也該練一下了!”
“喝酒也需要練習?”
“嗯!當然啦!”渡邊升說。“很奇怪嗎?”
“一點也不奇怪!先從白酒開始,在一個大玻璃杯裏放進白葡萄酒和冰塊,如果你覺得味道還是太強的話。就再放一點檸檬片,要不然也可以加果汁下去調配成雞尾酒。”
“我會試試。”他說。
“啊!果然毛病出在這裏。”
“那裏?”
“前置安培和電源之間的連結綫,連結綫的左右各有一個固定的安定栓,這個安全栓很容易上下搖動,但是,電視機這麽龐大,應該不會任意搬動的。”
“大是我要打掃時將它移動了。”妹妹說。
“也很有可能!”他說。
“這也是你們公司的産品吧!”妹妹對着我說。“竟然生産出這麽粗糙的産品!”
“又不是我製造的,我衹不過負責廣告而已。”
我小聲地說。
“如果有十字型的起子的話就可以很快地修理好了。”渡邊升說。“有嗎?”
“沒有!”我說。
那種東西怎麽可能會有。
“那麽我騎車出去買吧!衹要有一支十字型起子,傢裏要修理什麽都會很方便的。”
“大概是吧!”
我已經全身都毫無力氣了。
“但是,你知道五金行在那裏嗎?”
“知道!”前面不遠就有一傢。”
渡邊升說。
我又從陽臺探出頭去,看着渡邊升戴上安全帽,騎上摩托車。
“這個人不錯吧!”
妹妹說。
“心太軟了!”我說。
(6)
電視修理好了之後鄉,已經將近五點鐘了,因為他說想要聽點音樂,於是妹妹就放了鬍立歐的唱片。鬍立歐!天哪!我心裏想,算了!反正今天窩囊事已經全都讓我盡了!
“大哥喜歡聽什麽音樂?”渡邊升問。
“我非常喜歡聽這個!”我在說謊。
“除此之外,我還喜歡聽魯斯.史普林斯汀,或者傑夫見剋!”
“那些我都沒聽過!”他說。“也是這類的音樂嗎?”
“差不多。”
接着他就開始述說他現在所屬的設計團,正在開發新的計算機,這個係統可以計算出鐵軌上發生事故時,為了有效的回轉駕駛,最精確的時間。聽他這麽一說,我也覺得這個方法確實很方便,但是,這個原理對我而言簡直就像法語的動詞變化一樣難懂。
他熱心地為我解釋時,我一邊適切地點頭,腦海裏一直想着女人的事。今天到底要和誰一起喝酒,到什麽地方去吃飯,該進那一傢旅館?我一定是天生就對這方面的情有偏好,有人喜歡玩汽車模型,有人喜歡研究計算機程序設計,而我則喜歡和女人上床。這一定有一種超越人力的宿命。
我喝完了第四瓶啤酒時,晚餐纔準備好,烤鮭魚配濃湯、牛排配沙拉、炸薯條,妹妹的手藝一直不壞。
我開了香檳獨飲起來。
“大哥為什麽會到電機工廠上班呢?聽你的談話,似乎對電器的事情不怎麽喜歡。”
渡邊升一邊切着牛排,一邊問。
“這個人上班纔不管公司在做些什麽呢!”妹妹說。“衹要是工作輕鬆,又有吃有玩的,他就會去了。”
“對!說得有理!”
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
“腦子裏衹有玩樂的事情,什麽認真工作、努力嚮上,完全不在他的思考範圍內。”
“和夏天的蟋蟀一樣!”我說。
“但是你喜歡和認真、勤快的人在一起。”
“話不能這麽說。”我說。
“別人的事情和我是不相幹的兩回事,我衹考慮到我自己,別人的事和我完全沒有關係。雖然我確實是一個很下流的人,但是,我絶對不會去幹擾到別人的生活或生活。”
“你絶對不是一個下流的人!”
渡邊升反射性地說了出來。這個傢夥的傢教一定不壞。
“謝謝!”
我說着舉起了酒杯。
“祝你們訂婚愉快!雖然衹有我一個人喝酒好象不太夠意思。”
“婚禮準備在十月舉行。”渡邊升說。
“不過不打算請慄鼠和大熊。”
“沒有關係。”我說。
天哪!這傢夥竟然也會和我開玩笑!
“那麽,要到什麽地方度蜜月呢?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嗎?”
“夏威夷。”
妹妹簡潔地回答。
於是我們就談起飛機的事情,因為我看了幾本飛機失事相關的書,因此在這方面可以嚮他們長篇大論一番。
“飛機破片上的人肉經過太陽烘烤之後,幾乎熟得可以吃呢!”我說。
“喂!吃飯時不要講這種惡心的話!”
妹妹舉起手來,瞪了我一眼說。
“這些話可以去嚮別的女孩子吹牛,不要拿到飯桌上說。”
“大哥還不打算結婚嗎?”
渡邊升插嘴地說。
“沒有機會啊!”
我一邊放了一根炸薯條進去嘴裏,一邊說。
“必須照顧年幼的妹妹,還必須應付一段很長的戰爭。”
“戰爭?”
渡邊升大吃一驚地問:
“什麽戰爭呢?”
“無聊的笑話,別理他!”
妹妹擺擺手,不耐煩地說。
“是無聊的笑話!”
我也說。
“但是,沒有機會這是事實。因為我性格太偏激,不喜歡自己洗襪子,所以一直找不到一個能容忍我這個缺點的女孩。這點和你大大地不同了。”
“為什麽不喜歡洗襪子呢?”
渡邊升問。
“別再開玩笑了!”
妹妹用疲憊的聲音加以說明。
“襪子我每天都有洗啊!”
渡邊升點點頭,大約笑了一秒半左右。我决定下次讓他笑三秒鐘。
“但是她不會一輩子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呀!”
他指的是我妹妹。
“妹妹和哥哥住在一起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麽不可以的呢?”
我說。
“什麽話都是你說的,我可是半句話都沒說!”
妹妹說。
“但是,這不是真實的生活,真正大人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應該是人與人之相誠懇的相處。這五年來確實是和你相處得很和樂、很自由,但是,最近我覺得這不是真正的生活,因為我根本感覺不到生活的本質,你老是想着你自己的事情,想要和你談點正經的事時,你卻老是開玩笑!”
“因為我個性內嚮。”我說。
“是傲慢!”妹妹說。
“內嚮又傲慢!”我一邊倒着香檳,一邊嚮渡邊升說明。
“我是一個內嚮加傲慢的綜合體。”
“我懂你的意思。”
渡邊升點點頭說。
“但是,如果衹剩下你一個人的話……換句話說,如果她和我結婚了的話……大哥你還是不想找一個人結婚嗎?”
“大概是吧!”我說。
“真的?”妹妹問我說。
“如果你真的這麽想的話,我的朋友中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女孩子,可以介紹給你。”
“到時候再說吧!現在仍然太危險了。”
■譯者:許珀理
(1)
這樣的事在這個世界上,或許是非常普遍的,我對於妹妹的未婚夫始終未曾有過好感,而且,我甚至覺得妹妹竟然會决心和這樣的男人結婚,實在令人感到懷疑。說得坦白一點,我覺得很失望。
或許這樣的想法是我偏狹的性格所造成的。
至少妹妹是這樣認為。然我們表面上都不以此為話題,但是,我對她的未婚夫不太滿意這一點,妹妹也非常瞭解,對於我這樣的想法,妹妹也覺得非常不高興。
“你對事情的看法眼光太狹窄了”妹妹對我說。
當時我們正在談論意大利面,她所說的應該是指我對意大利面的看法眼光太狹窄吧!
但是,妹妹當然不會衹針對意大利面的問題,在意大利面之前還有她的未婚夫,所以,事實上妹妹所指的應該是未婚夫的問題。這種情形就是所謂的藉題發揮。
事情的開端是緣於妹妹邀我一起在星期天的中午吃意大利面,因為我也有點兒想要吃意大利面,於是就隨口說:“好吧!”
於是我們就走進車站前一傢新開的意大利面館,我點了茄香洋蔥意大利面,妹妹點了傳統的意大利肉醬面。
面送上來之前,我一直喝着啤酒,到此為止沒有出現任何問題。這是五月裏的一個星期天,天氣非常晴朗。
問題出在送來的意大利面的味道,面表面看起來是煮熟了,其實心還是硬的,奶油好象是用煮狗食的劣等貨冒充,我勉強吃下了半盤就放棄了。
妹妹擡頭看了我一眼,不說一句話,依舊慢慢地將自己盤中的面吃完。
這時候我一邊欣賞窗外的風景,一邊喝下第二罐的啤酒。
“喂!怎麽剩這麽多就吃不完了,多可惜啊!”
妹妹將她盤子裏的面吃完了之後說。
“太難吃了!”我回答。
“都吃下去一大半,應該不算太難吃吧,衹要稍微忍耐一下,一定可以吃完的!”
“想吃的時候吃,不想吃的時候就不吃,這是我的胃,不是你的胃!”
“這傢店纔剛開張不久,廚房可能還不熟練,你就稍微寬容一下,不行嗎?”
妹妹看着送上來口味清淡的附餐咖啡說。
“雖然你說的也有道理,但是,不好吃的食物就應該將它留下來,這也是一種常識。”
我嚮她說明。
“你是什麽時候開始變得如此偉大的呢?”妹妹說。
“你聽了不舒服是嗎?”我說“口氣這麽不好,是不是生理期?”
“討厭啦!請你不要再說些奇怪的話了!你以前不說這些的。”
“有什麽關係,我對你第一次的月事什麽時候來也都非常清楚。我記得你的第一次來得很晚,媽媽還陪你一起去看醫生呢?”
“你閉嘴不說話也沒有人當你是啞巴!”她說。
我知道她是真的生氣了,所以衹好聽她的話閉上嘴巴。
“大概是你對事情的看法都太偏激了!”
她一邊在咖啡裏水加入了一些奶精,一邊說。
一定是這杯咖啡太難喝了。
“不論什麽事情你衹是將缺點找出來,大肆批判,好的地方你這看都不看。
衹要與你的標準不合,你一概不加以理會,這種情形以旁人的眼光來看就是神經病!”
“這是我自己的人生,與你無關!”我說。
“可是你出口傷人,故意找人麻煩!你這個衹會手淫的傢夥!”
“手淫!”我大吃一驚地說。“你到底在說些什麽?”
“你在念高中的時候經常喜歡手淫,每次都把內褲都髒了,你應該也很清楚,那些東西洗起來是很纍人的,可是你卻一做再做,你不是故意給人添麻煩嗎?”
“我以後會小心一點!”我說“不要再提這件事情了,我有我自己的人生,有我喜歡的東西,有我討厭的東西,這是這我自己都無法改變的啊!”
“但是,你不可以傷人!”妹妹說。
“為什麽你不稍微努力一下呢?為什麽你不往好的地方去看呢?
為什麽你不願意多忍耐一點呢?為什麽你一直都沒有成長呢?”
“我是正在成長!”
我覺得自己已經被傷害了。
“我也要求自己要多忍耐、多往好的方面看,衹是我的觀點和你不一樣罷了!”
“你這種情形衹有傲慢兩個字足以形容,所以你到了二十七歲仍然找不合適的對象!”
“我有女朋友啊!”
“那些人衹不過是睡睡覺罷了!”妹妹說。“不是嗎?每年更換一個睡覺的對象,這樣纔感到快樂嗎?沒有快理想、沒有愛情,也不用相互體諒,這到底有什麽意義呢?和手淫沒有兩樣吧?”
“我哪有一年換一個?”
我毫無力氣地說。
“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妹妹說。
“你能不能稍微認真思考一下,過着認真一點的生活,稍微像個大人的模樣?”
我們的談話到此結束,從此之後,不管我說什麽,她都不願意再回答。
為什麽她會對我産生如此偏激的想法呢?我也不大清楚。大約在一年前,還和我一起生活得非常愉快,而且從來不會反駁過我的想法。她會開始批評我,是在她認識了她的未婚夫之後。
這種事情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和她已經相處了二十三年,雖然每一件事情我們都是率直地商量,但是說起來仍是一對感情相當不錯的兄妹,幾乎從來不曾吵過架。
她知道我手淫的事情,我也知道她初潮的事情;她知道我第一次買保險套的事情(在我十七歲的時候),我也知道她第一次買有蕾絲的內褲時的事情(在她十九歲的時候)。
我和她的朋友約過會(當然沒有上床睡覺),她也和我的朋友約過會(我想應該也應該沒有上床睡過覺),總之我們是在一個非常相同的環境下長大的。
這樣友好的關係,在一年前開始變質,一想到這件事我就越來越生氣。
妹妹說要到車站前的百貨公司看鞋,我衹好一個人回到公寓裏。然後打電話給女朋友,可是她不在傢,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從不在星期天下午兩點鐘突然打電話給她,約她出來見面。
我放下電話筒,翻動記事本,找到了另外一個女孩子的電話,這是一個知道哪裏有狄斯可舞廳的女大學生,她在傢裏。
“出來喝點東西吧!”我邀她。
“纔下午兩點鐘!”
她不耐煩地說。
“時間不是問題!出來喝點柬西,很快就天黑了。”我說。“我知道一個以看夕陽聞名的酒吧,下午三點過後再去的話,就沒找不到好位子了。”
“你這個人真是討厭!”她說。
但是她還是出來了,大概是一個性格親切的人吧!
我將車子沿着海岸過去,一直開到橫濱附近,如約定地,到一個看得見海濱的酒吧。
我在這裏喝了四杯加冰塊的i.w.哈伯酒,她則喝了兩杯香蕉水果酒,看着夕陽。
“你喝了這麽多的酒,還能夠開車嗎?”
她擔心問。
“不要擔心。”我說。“我的酒量好得很,四杯算不得什麽!”
“算了,你最愛吹牛!”她說。
然後我們又回到橫濱吃晚餐,在車子裏我吻了她,邀她一起上旅館,她說:不行啦!
“月經來,還放着衛生棉條呢!”
“拿下來就可以了!”
“別開玩笑了,還有兩天呢!”
算了!我心裏想着。今天到底是什麽日子呢!如果早知道會有這種事情發生,我就不會找她出來了。好久不曾和妹妹一起悠閑地度過一天,我原本打算這個星期天在傢裏陪她的。
“對不起!但是,我絶對沒有騙你哦!”
這個女孩子說。
“沒有關係,別挂在心中,不是你不對,是我不好。”
“我的生理期和你不好有什麽關係?”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我不應在這個時候去找你!”我說。
真的是這樣嗎?難道我真的非得對一個認識不深的女孩子的生理期了若指掌嗎?
我開車將他送回世𠔌田的傢中,中途車子一直喀喀作響,我心裏嘆氣着想着:大概該將它送進修車場裏整修一番了吧!
好象衹要有一件事進行不順利的話,這一整天就會連鎖地不好的方向發展下去似的。
“我最近還能約你出來嗎?”我問。
“約會?或者上旅館?”
“兩個都有!”我坦自地說。“這麽說的話,比較表裏一致,就像牙刷和刷牙一樣。”
“是呀!這是正確的想法!”她說。
“這麽想的話,頭腦比較不會老化。”我說。
“到你傢去如何?不能去玩嗎?”
“不行,因為我和妹妹住在一起,我們早已有約定,我不可以帶女孩子回傢,妹妹也不可以帶男生回來。”
“真的是妹妹嗎?”
“當然是真的,要不然我下次帶戶口簿給你看!”
她笑了笑。
等到這個女孩子消失在她傢的大門口裏,我纔重新發動引擎,回到我住的公寓。
一路上耳邊不停地響着引擎所發出的喀喀聲。
房間裏一車漆黑,我打開車鎖,大聲叫着妹妹的名字,但是她卻不在房間裏。
我心裏想着,已經十點多了,她會到哪裏去呢?
接着我就去找晚報來,但是沒有找到,因為今天是星期天,不送報。
我從冰箱裏拿出一瓶啤酒,和杯子一起拿到客廳。打開錄放機,看着新的連續劇。一邊喝着啤酒,一邊控製聲量的開關,但是,無論如何總是聽不到聲音。這時候我纔發現錄像機早在三天前就壞掉,雖然開了電視,但是聲音仍然無法出來。
在沒有更好的方法之下,我衹好看着無聲的電視畫面,喝着啤酒。
電視正在放映一部古代戰爭電影,羅馬帝國的戰車遠征非洲,炮戰車擊出無聲的大炮,自動槍也發出瀋默的彈音,人們在無言中靜靜地死去。
唉!算了!我又嘆了一聲氣,這大概是當天的第十六次嘆息吧!
(2)
我和妹妹二個人生活在一起,大約是五年前的春天開始的吧!當時我二十二歲,妹妹十八歲;換句話?
a我剛從大學畢業,準備找工作,而妹妹剛高中畢業,準備去念大學。我的父母表示;如果和我住在一起的話,就允許妹妹到東京念大學。妹妹說:沒有關係。我也說:隨便。於是父母就為我們找到了一間有個房間的寬敞公寓,房租由我負擔一半。
前面已經敘述過了,我和妹妹兩個人的感情非常好,兩個人生活在一起絶對不會讓我有任何痛苦的感覺。因為我任職於電機製造公司的廣告部,早上上班的時間比較晚,晚上則比較遲回到傢裏;而妹妹一大早就去上學了,傍晚就回到傢裏。因此,經常是我醒來時,她已經出門;我回到傢裏時,她又已經睡着了;再加上星期六、星期天我都花費在和女孩子的約會上,所以一個星期裏衹有和她說兩三句,但是,我認為這種情形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因為我們幾乎沒有吵架的時間,也沒有空閑去干涉對方的私事。
雖然我想她可能也會有很多不尋常的事發生,但是,我一點也不想說出口,她已經是超過十八歲的女孩子了,想和什麽人上床睡覺,我沒有干涉的權利。
但是,有一次半夜一點到三點,我一直牢牢地握着他的手。我下班之後回到傢裏,看見她坐在廚房的餐桌前哭泣,我推測她會坐在餐桌前哭泣,大概是想要跟我要求什麽東西吧!否則她衹要坐在自己的床上哭就夠了,何必讓我看見呢?雖然我確實是一個?
噶e又任性的人,但是,這樣的事情我還是可以推想得到的。
所以,我就坐在她的身邊,輕輕握住她着手。握着妹妹的手這種事情,自從小學時代一起去抓蜻蜓以來,從來未曾再發生過,妹妹的手比記憶中的─那當然是非常久遠以前的記憶─要大得非常多了。
結果她就這樣一直坐着,不說一句話地哭了兩個小時。她的身體內竟然屯積了這麽多的淚水,這實在太令我驚訝了,要是我的話,大概哭不到兩分鐘全身就幹涸了。
但是,到了三點時我已經開始覺得有些纍,再不結束的話,我也撐不下去了。在這個時候,身為兄長的我,不說句話是不行的,雖然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但是,我還是開口說話。
“我對你的生活完全不想干涉!”我說。“你想要過什麽樣的生活就隨着自己的喜好去過吧!”
妹妹點點頭。
“但是,我一直想給你一句忠告,最好能隨時在皮包裏放一個保險套,你當然有別於那些賣春婦。”
聽我這麽一說,她隨手拿起放在桌上的電話簿,突然用力地朝我丟了過來。
“你憑什麽偷看我的皮包!”
她大聲怒駡。
我知道她這個時候已經氣憤到了極點,為了不使她再受到任何刺激,我當然不能對她說我從來不曾去偷看過她的皮包。
但是,不論如可她是已經停止哭泣,而我也能夠回到自己房間,鑽進被窩裏去。
妹妹大學畢業之後,任職於旅行,但是我們的生活形態仍然沒有絲毫改變。她的上班時間是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非常有規律,而我的上班時間則和一般人回異,中午纔進到辦公室,然後坐在辦公桌前一邊看報紙、一邊吃中飯,下午兩點鐘左右纔開始真正的工作,傍晚又得到廣告公司去談生意,飲酒應酬,每天都必須到了深夜才能回傢。
在旅行社上班的第一年暑假,她和一位女朋友一起到美國西海岸觀光旅行(旅費當然是采用分期付款的)。在這趟美國之旅,她認識了一位年長他很多的計算機工程師。回到日本之後,仍然經常與他見面。雖然這種事情也是非常多見,但是絶對不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因為我對這種瘋g大採購的旅行團一點兒也不感興趣。
自從和那位計算機工程師交往以來,妹妹似乎比以後更為開朗,傢事也收拾得整整齊齊,穿着打扮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她非常喜歡穿工作服,或牛仔褲、卡其裙,現在則換上色彩鮮豔的裙裝,而且每件衣服都親自用手洗,仔細的熨燙,經常自己下廚、打掃房間。
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徵候,如果看到了女孩子有這個徵候,男孩子通常有兩種反應,一種是立刻逃開、一種是馬上下了結婚的决定。
後來妹妹又拿了那位計算機工程師的照片給我看,這是妹妹第一次拿她男友的照片給我看,這也是一種危險的徵候。
照片有兩張,其中一張是在舊金山的海邊照的,妹妹和那位工程師兩人並肩而站,兩個人都面帶盈盈的笑意。
“好漂亮的海岸綫喔!”我說。
“別開玩笑了!”妹妹說。“我是非常嚴肅的。”
“你要我說什麽好呢?”
“你最好什麽也別說!”
我再仔細看一下手上這張照片,如果世界上真有那種一眼看去就令人非常討厭的的話,就是這種臉了。而且,這種計算機技師長得和我高中時代最討厭的社團前輩很像,雖然長相不差,但是故意裝出一副頭腦精明、盛氣凌人的模樣。
“你們上過幾次床了?”我問。
“你鬍說些什麽?”
妹妹說着,滿臉脹紅。
“請你不要老以自己的尺度來衡量這個世界,你以為天底下所有人都和你一樣的嗎?”
第二張照片是回到日本之後纔照的,照片裏衹有計算機工程師一個人,他穿着一件皮背心,靠在一輛大型摩托車上,座椅上永着一頂安全帽,這張臉的表情完全和在舊金山時一模一樣,大概是他再也沒有別的表情了。
“他很喜歡騎機車。”妹妹說。
“我看得出來。”我說。“不喜歡騎機車的人是不會穿這種皮背心的。”
我……大概又是因為個性偏激的緣故所造成的……於喜歡騎機車的人都不具有好感,因為這些人大多比較驕傲,喜歡裝模做樣;但是,對於照片上這個人,我不想加以批評。
我靜靜地把照片還給妹妹。
“可是……”我說。
“可是什麽?”妹妹說。
“可是,你打算怎麽辦呢?”
“不知道!或許會和他結婚吧!”
“他嚮你求婚了嗎?”
“嗯!”她說。“可是我還沒有給他答復。”
“嗯!”我說。
“老實說是因為我覺得我纔剛開始上班而已,還想自己一個人自由地遊樂一番。當然,不同於你那種過於偏激的想法。”
“應該說是健全的想法。”
我強調地說。
“可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好人,和他結婚也不錯。”妹妹說。“所以想問問你的意見。”
我拿起卓上的照片再仔細地再看一次,心裏想:“還是算了吧!”
這是聖誕節前的事情。
(3)
過完年後不久,有一天一大清早九點多鐘,媽媽打電話過來,我正在聽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生在美國”,一邊刷着牙。
母親問我知不知道妹妹交男朋友的事情。
不知道,我說。
母親說她收到妹妹的信,信上說兩個禮拜後妹妹要帶那個男的一起回傢。
“該不是想要結婚了吧!”我說。
“所以我想問看看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媽媽說。“我希望能在見面之前對他多瞭解一點。”
“這個嘛!因為我也沒有和他見過面,對這個人不怎麽清楚,我衹知道是一個年齡滿大的工程師,好象是在ibm或什麽公司上班,公司的名字是三個英文字母,要不然就是nec、或ntt。我衹看過照片,長得不是頂好的,而且又不是我要結婚,所以我對他沒什麽興趣。”
“哪一個大學畢業的?傢住在哪裏?”
“這件事我怎麽會知道呢?”我說。
“你不會去找他見個面,瞭解一下嗎?”
“我不喜歡做這種事情,我的工作太忙,你不會兩禮拜見面之後再問他嗎?”
結果,我比媽媽更早和這位計算機技師碰面。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妹妹說要到他傢去做正式的拜訪,我衹好義不容辭地答應作陪。穿妥白襯衫、係上領帶,再穿上最得意的西裝,就到他傢去了。那是一棟位在古老住宅街道正中央,非常豪華的住傢,院子裏停放着照片上經常看得見的五百cc摩托車。
“哇塞!這麽高級的住宅!”
“今天真的要拜托你,千萬別再玩笑了,正經一點可以嗎?”妹妹說。
“是的!遵命!”我說。
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規矩─稍微太規矩而變得有點兒嚴肅─,而且非常厲害的人,他的父親是石油公司的重要幹部,我的父親在靜岡擁有一座石油的連鎖店,所以這一方面我們之間的關係不算太遠。
他的母親母親用一個高級的盤子,端着茶出來。
我嚮他們規矩地打過招呼之後,遞上瞭瞭我的名片,並且嚮解釋,本來應該由我的父母來拜訪,但是正好他們今天有事不能來,所以就由我來代理,改天他們會正式來拜見二位。
“我聽兒子說過好幾次了,今天看見了果然不假,是一位標緻的小姑娘,而且我知道一定是一位好女孩。”
他的父親說。
我心裏想,他一定是調查得非常詳細了。或許連十六歲都尚未初潮,以及深受便秘所苦這種小事,都知道得一清楚呢!
等到這些客套話都結束之後,他的父親為我倒了一杯白蘭地,這種白蘭地的味道實在美極了,我們一邊喝着,一邊談着各自工作上的事情,妹妹穿着拖鞋踢了我一下,提醒我不要喝得過多。
這時候身為兒子的計算機技師一言不發,緊張地端坐在父親身旁,一眼就可以看,在這個屋檐,他完全受父親大權的支配,他身上穿着一件我以前從來不曾看過,樣式非常奇怪的毛綫衣,毛綫衣裏面是一件顔色非常不諧調的襯衫,看起來讓人覺得這個男孩子很奇怪。
談話告一個段落之後,我看看手錶,已經四點了,於是站起身來,準備告辭。
計算機技師送我們兩個人到車站。
“找個地方一起喝喝茶好嗎?”
他邀請我和妹妹。雖然我對喝茶沒興趣,也不想和穿着這麽奇怪毛綫衣的男孩子同桌,但是,斷然拒絶可能會讓他覺得不好意思,衹好同意三個人一起到附近的咖啡店喝茶。
他和妹妹都點咖啡,點了啤酒,可是這裏沒有賣啤酒,沒有辦法我衹好也喝咖啡。
“今天真是謝謝你,幫了一大忙!”
我嚮我道謝。
“那裏的話,這是我應該的。”
我學着大人的口吻說,因為我已經沒有一點點多餘的力氣開玩笑了。
“常常聽她提起大哥的事。”
大哥?
我用咖啡匙的柄挖挖耳朵,再把它放回桌上。然妹妹又用腳踢了我一腳,但是,我覺得計算機技師應該是不懂這個動作的意義。
“看你們兩個人感情這麽好,實在讓我非常羨慕。”他說。
“一有高興、有趣的事情,我們就互踢彼此的腳。”我說。
計算機技師一副不解的表情。
“他在開玩笑啦!”
妹妹不太高興地說。
“他講話就是這樣的!”
“我是在開玩笑的。”我也說。
“兩個人住在一起,總得彼此分擔傢事,她分到的是洗衣服,我分到的是講笑話。”
這位計算機技師─正確的名字叫做渡邊升─聽了之後也稍微安心地笑了笑。
“氣氛爽朗一點不是很好嗎?我也想擁有一個這樣的家庭,氣氛爽朗是最重要的。”
“說得也是啊!”
我對着妹妹說:
“氣氛爽朗是最重要的,你太神經質了。”
“不要再開玩笑了。”妹妹說。
“我想盡可能在秋天結婚。”渡邊升說。
“結婚儀式還是在秋天舉行最好。”我說。
“還可以叫慄鼠和大熊一起來參加。”
計算機技師哈哈大笑,妹妹卻沒有笑,她好象是真的生氣了。因此,我就推說另外有事,然後起身離席。
回到公寓之後,我打電話給母親,說明了整個事件大致的情形。
“這個男孩還不怎麽壞。”
我一邊掏耳朵一邊說。
“不怎麽壞是什麽意思?”
“意思是說人滿誠實的,至少和我比起來算是老實人。”
“和你當然是沒得比了。”母親說。
“真高興聽到你這麽說我,謝謝了!”
我一邊看着天花板,一邊說。
“那麽,他是哪一個大學畢業的呢?”
“大學?”
“哪一個大學畢業的呢?那個計算機工程師。”
“這種事你可以問問當事人。”
我說着就把電話挂斷。
然後就從冰箱裏拿出一瓶啤酒,心情非常鬱悶地一個人喝着酒。
(4)
為了意大利面而和妹妹吵架的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上午八點半纔起床。
和前一天一樣,天空中沒有半片烏雲,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我覺得好象全完是昨天的延續似的,夜裏一時中斷的人生又重新開始了。
我將汗濕了的睡袍和內褲丟道洗衣槽裏,淋了浴,又剃了鬍須。一邊剃的時候,一邊想着昨天晚上的那個女孩,實在非常懊惱。不過,遇到這種無可抵抗的事情也實在是莫可奈何。不過,以後還有機會,說不定下個星期天一切都會很順利。
我到廚房烤了兩片面包,燒了一壺咖啡,原本想聽聽fm播放的節目,但是想到錄像機的監聽係統已經壞,衹好作罷。改為一邊看報紙的讀書欄,一邊啃着面包。讀書欄裏介紹的新書沒有一本是我想要看的,那裏的書不是關於“年老猶太人的空想與現實交錯所造成的性生活”,就是關於分裂癥治療的歷史性考察,實在搞不懂,報社那些編輯大人為什麽要選擇這樣奇怪的書來介紹。
吃完了一片烤得焦硬的面包之後,把報紙放回桌上,這時候纔發現果醬瓶子下面放着一張紙條。紙條上是妹妹一貫的字跡,她寫着:因為星期天的晚上要叫渡邊升一起來吃晚餐,所以希望我也能夠留在傢裏,和他們一起共進晚餐。
我吃完了早餐,撥撥掉落在襯衫在面包屑,將餐具放進了水槽,打電話到到妹妹上班的旅行社。
妹妹接到電話之後:
“現在我手邊的事情非常忙,十分鐘之後再打電話給你。”
二十分鐘之後果真打電話過來,在這二十分鐘之內,我一共做四十三次的伏地挺身,手腳合計剪了二十根指甲,穿好襯衫、打好領帶、選好了長褲,並且刷了牙,梳了頭髮,打了兩個哈欠。
“你看到我的留言了嗎?”妹妹說。
“看了!”我說“但是,這實在糟糕透,這個星期天我早就好別人約好,如果能夠早一點說的話那就好了。
現在纔知道實在非常可惜。”
“你不要說得那麽可憐!我想你這個約大概是和一個連名字都記不清的女孩子吧!”妹妹語氣冷淡地說。“不可以改在期六嗎?”
“星期六一整天都必須待在錄像室裏,因為現在正在製作電動抹布,所以那一天會非常的忙。”
“那麽就跟她取消好!”
“那麽你來付取消費吧!”我說。“現在是一種非常微妙的階段。”
“沒有那麽微妙吧!”
“雖然不應該是這樣…”我坐在椅子上一邊整理襯衫和領帶,一邊說。“我們不是早就約定好不侵彼此的生活嗎?你和你的未婚夫共進晚餐─我和我的女朋友約會,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好,你一直都沒有和他好好聊過吧,從我們認識以來,你衹和他見過一次面,而且那是四個月的事情,不是這樣嗎?雖然你們也有好幾次見面的機會,可是你每一次都故意逃開,難道你不覺得這樣很不禮貌嗎?他是你妹妹的未婚夫,我求你和他一起吃頓飯,好嗎?”
因為妹妹說話也有她的道理,所以我也衹好默默的無以言對。確實我總是用最自然的方法來逃避和渡邊升見面,而且渡邊升和我之間實在沒有任何共通的話題,我講的笑話他也聽不懂。
“拜托你啦!衹要這一天就好了,從此以後,到這個夏天為止,我不會再去打擾你的性生活了。”妹妹說。
“我的性生活不算什麽啦!”我說。“或許到這個夏天結束之前都不會再發生。”
“不管怎麽樣,請你星期天一定要待在傢裏。”“我無能為力!”我斷然地回絶她。
“說不定他會幫你修理錄像機,那個人在這個方面非常擅長。”
“還有這點好處呢!”
“你不要老想那些奇怪的事!”
妹妹說着就挂斷電話。
我係好領帶就出門上班去了。
這個禮拜一直都是晴朗的好天氣,好象是每天都是每天的延續似的,星期三的晚上,我打電話給我的女友,告訴她為工作忙碌,這個周末不要見面。因為我已經三個禮拜不曾和她見面了,所以她當然不太高興。接着我沒有放下話筒,繼續撥電話給那個女大學生,但是她不在傢,星期四、星期五她都沒有在傢裏。
星期天早上,我八點就被妹妹叫起來了。
“我要洗床單,你不能再睡那麽晚。”她說。
然後就拆下枕頭套和床單,也叫我脫下睡衣,我沒有地方去,衹好進浴室洗個澡,順便颳颳鬍須。我覺得這個傢夥愈來愈像媽媽了,原來女人也和鮭魚一樣,無論過程如何,最後總會回到相同的場所。
洗完澡之後,我穿上一件短褲,套上一件胸前的字幾乎都已褪盡了的t恤,打了一個長長的哈欠,然後開始喝柳橙汁。覺得體內還留存着昨夜的酒精,連報紙也不想看了。桌子上有一個蘇打餅幹的盒,於是我就拿了三、四片來吃,代替早餐。
妹妹將被單放到洗衣機裏,然後就不停地收拾整理我的房間和她自己的房間,整理完了之後,又用洗潔劑擦洗着客廳和廚房的墻壁和地板。
我一直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翻開美國朋友送我的裸女照片,仔細觀察研究一番之後纔發現,女性性器事實上也有大小不同之別,和身高、以及智商是完全一樣的。
“嘿!看你在這裏閑着無聊,不如幫我買東西吧!”
妹妹說着,就硬塞給我一張寫滿採購物品名單的紙條。
“請你不要在這裏看這種書,這個人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把裸照放在桌子上面,瞪着紙條。萵苣、蕃茄、芹菜、沙拉醬、熏魚、洋蔥、濃湯包、馬鈴薯、洋芹菜、牛排肉三片……。
“牛排肉?”我說。“我昨天才吃了牛排,我不想再吃牛排,吃炸肉餅比較好!”
“或許你昨天真的吃了牛排,但是我們沒有吃啊,請你不要那麽自以為是,而且,沒有人會用炸肉餅來招待客人的吧!”
“如果有女孩子請我到她傢裏去吃炸肉餅的話,我一定會非常感動,再端出一盤切得細細長長的白甘籃菜、香濃的味噌湯……這種吃法多麽生活化啊!”
“不管怎麽樣,今天已經决定吃牛排了,殺了我也不願意做炸肉餅你吃,今天你就不要再自以為是,和我們一起吃牛排吧!求求你。”
“好吧!”我說。
雖然有時候我的怨言似乎多了一些,但是歸根究底我還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
我到鄰近的超級市場照着菜單購物,然後又到附近的酒店買了一瓶四千五百圓的香檳,打算以這瓶香檳作為送給他們兩個人的訂婚禮物。我想大概衹有非常親切的人才會為他們設想得如此周到。
回到傢之後,看到我的床上端放着一件摺叠整齊的馬球襯衫,和一件沒有一點點縐紋的棉質長褲。
“換上這套衣服!”妹妹說。
算了!換就換吧!我心裏想着,不說半怨言就把衣服換了下來。不論我還有什麽意見,今天還是順着她的意思,這樣會覺得氣氛和平些。
(5)
渡邊升在下午三點準時出現,當然是騎着摩托車來的。他那輛五百CC機車的排氣聲,遠在五百公尺遠的地方就聽得一清二楚。從陽臺探頭出去往下看,看見他將摩托車停靠在公寓玄關旁,然後脫下了安全帽。非常值得慶幸的是,他在脫下安全帽之後,身上所穿的服裝還算正常。一件花格子衫,配一件白色長褲,再加上一雙咖啡色的鞋,唯一顯得唐突的是鞋子和皮帶的顔色不搭調。
“好象是我們傢大小姐的朋友來了!”
我對着正在流理臺削馬鈴薯皮的妹妹說。
“能不請你先招呼他一下,我現在得忙着廚房的事情。”妹妹說。
“這樣不太好吧!他是為你而來的,更何況我和他也沒有什麽話講,還是讓我來煮飯,你們兩個人去聊天。”
“別胡闹了!你會煮飯嗎?快去招呼客人吧!”
電鈴一響,打開大門,渡邊升就站在門口。我帶他到客廳,讓他坐在沙發上。他帶了一盒特大號的冰淇淋來當做禮物,但是,我們傢的冰箱冷凍庫太小,根本裝不下這麽大盒的冰淇淋。我覺得他像一個還需要照顧的大男孩,到女友的傢做客竟然還帶着冰淇淋。
接着我問他想不想喝啤酒,他回答不喝。
“體質不適合喝酒。”他說。“不知道為什麽,喝一大杯啤酒下肚就覺得很惡心。”
“我在學生時代曾和朋友打賭,喝了一打啤酒,結果購了不少錢。”我說。
“喝完了有什麽感覺呢?”渡邊升問。
“整整兩天小便裏都有啤酒的臭味。”我說。“而且,不停地放屁……”
“喂!請你幫忙看看錄像機吧!”
妹妹好象看見了不吉的煙幕,端了兩杯柳橙汁在桌上說。
“好啊!”他說。
“聽說你很能幹?”我問。
“還好啦!”
他沒有絲毫不高興的回答。
“以前我非常喜歡組合型玩具、或收音機,傢裏有什麽電器壞了,都是由我來修理。錄像機什麽地方壞掉了呢?”
“沒有聲音!”
我拿起遙控器,按下電源讓他瞭解聲音出不來的情形。
他坐在電視機前,一一地去按電視機上的按鈕。
“安培係統壞掉,裏面沒有什麽問題。”
“你怎麽知道的?”
“用歸納法。”他說。
歸納法?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於是他將所的綫路全部拆了下來,一個一個仔細檢查。這時候我從冰箱裏拿出一瓶易開罐的啤酒來,坐在一旁一個人喝。
“喝酒好象是一件滿有趣的事情?”
他一邊用蠃絲起子轉着蠃絲,一邊對我說。
“還好啦!”我說。
“我喝了這麽多的酒,也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因為我來不去比較。”
“我也該練一下了!”
“喝酒也需要練習?”
“嗯!當然啦!”渡邊升說。“很奇怪嗎?”
“一點也不奇怪!先從白酒開始,在一個大玻璃杯裏放進白葡萄酒和冰塊,如果你覺得味道還是太強的話。就再放一點檸檬片,要不然也可以加果汁下去調配成雞尾酒。”
“我會試試。”他說。
“啊!果然毛病出在這裏。”
“那裏?”
“前置安培和電源之間的連結綫,連結綫的左右各有一個固定的安定栓,這個安全栓很容易上下搖動,但是,電視機這麽龐大,應該不會任意搬動的。”
“大是我要打掃時將它移動了。”妹妹說。
“也很有可能!”他說。
“這也是你們公司的産品吧!”妹妹對着我說。“竟然生産出這麽粗糙的産品!”
“又不是我製造的,我衹不過負責廣告而已。”
我小聲地說。
“如果有十字型的起子的話就可以很快地修理好了。”渡邊升說。“有嗎?”
“沒有!”我說。
那種東西怎麽可能會有。
“那麽我騎車出去買吧!衹要有一支十字型起子,傢裏要修理什麽都會很方便的。”
“大概是吧!”
我已經全身都毫無力氣了。
“但是,你知道五金行在那裏嗎?”
“知道!”前面不遠就有一傢。”
渡邊升說。
我又從陽臺探出頭去,看着渡邊升戴上安全帽,騎上摩托車。
“這個人不錯吧!”
妹妹說。
“心太軟了!”我說。
(6)
電視修理好了之後鄉,已經將近五點鐘了,因為他說想要聽點音樂,於是妹妹就放了鬍立歐的唱片。鬍立歐!天哪!我心裏想,算了!反正今天窩囊事已經全都讓我盡了!
“大哥喜歡聽什麽音樂?”渡邊升問。
“我非常喜歡聽這個!”我在說謊。
“除此之外,我還喜歡聽魯斯.史普林斯汀,或者傑夫見剋!”
“那些我都沒聽過!”他說。“也是這類的音樂嗎?”
“差不多。”
接着他就開始述說他現在所屬的設計團,正在開發新的計算機,這個係統可以計算出鐵軌上發生事故時,為了有效的回轉駕駛,最精確的時間。聽他這麽一說,我也覺得這個方法確實很方便,但是,這個原理對我而言簡直就像法語的動詞變化一樣難懂。
他熱心地為我解釋時,我一邊適切地點頭,腦海裏一直想着女人的事。今天到底要和誰一起喝酒,到什麽地方去吃飯,該進那一傢旅館?我一定是天生就對這方面的情有偏好,有人喜歡玩汽車模型,有人喜歡研究計算機程序設計,而我則喜歡和女人上床。這一定有一種超越人力的宿命。
我喝完了第四瓶啤酒時,晚餐纔準備好,烤鮭魚配濃湯、牛排配沙拉、炸薯條,妹妹的手藝一直不壞。
我開了香檳獨飲起來。
“大哥為什麽會到電機工廠上班呢?聽你的談話,似乎對電器的事情不怎麽喜歡。”
渡邊升一邊切着牛排,一邊問。
“這個人上班纔不管公司在做些什麽呢!”妹妹說。“衹要是工作輕鬆,又有吃有玩的,他就會去了。”
“對!說得有理!”
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
“腦子裏衹有玩樂的事情,什麽認真工作、努力嚮上,完全不在他的思考範圍內。”
“和夏天的蟋蟀一樣!”我說。
“但是你喜歡和認真、勤快的人在一起。”
“話不能這麽說。”我說。
“別人的事情和我是不相幹的兩回事,我衹考慮到我自己,別人的事和我完全沒有關係。雖然我確實是一個很下流的人,但是,我絶對不會去幹擾到別人的生活或生活。”
“你絶對不是一個下流的人!”
渡邊升反射性地說了出來。這個傢夥的傢教一定不壞。
“謝謝!”
我說着舉起了酒杯。
“祝你們訂婚愉快!雖然衹有我一個人喝酒好象不太夠意思。”
“婚禮準備在十月舉行。”渡邊升說。
“不過不打算請慄鼠和大熊。”
“沒有關係。”我說。
天哪!這傢夥竟然也會和我開玩笑!
“那麽,要到什麽地方度蜜月呢?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嗎?”
“夏威夷。”
妹妹簡潔地回答。
於是我們就談起飛機的事情,因為我看了幾本飛機失事相關的書,因此在這方面可以嚮他們長篇大論一番。
“飛機破片上的人肉經過太陽烘烤之後,幾乎熟得可以吃呢!”我說。
“喂!吃飯時不要講這種惡心的話!”
妹妹舉起手來,瞪了我一眼說。
“這些話可以去嚮別的女孩子吹牛,不要拿到飯桌上說。”
“大哥還不打算結婚嗎?”
渡邊升插嘴地說。
“沒有機會啊!”
我一邊放了一根炸薯條進去嘴裏,一邊說。
“必須照顧年幼的妹妹,還必須應付一段很長的戰爭。”
“戰爭?”
渡邊升大吃一驚地問:
“什麽戰爭呢?”
“無聊的笑話,別理他!”
妹妹擺擺手,不耐煩地說。
“是無聊的笑話!”
我也說。
“但是,沒有機會這是事實。因為我性格太偏激,不喜歡自己洗襪子,所以一直找不到一個能容忍我這個缺點的女孩。這點和你大大地不同了。”
“為什麽不喜歡洗襪子呢?”
渡邊升問。
“別再開玩笑了!”
妹妹用疲憊的聲音加以說明。
“襪子我每天都有洗啊!”
渡邊升點點頭,大約笑了一秒半左右。我决定下次讓他笑三秒鐘。
“但是她不會一輩子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呀!”
他指的是我妹妹。
“妹妹和哥哥住在一起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麽不可以的呢?”
我說。
“什麽話都是你說的,我可是半句話都沒說!”
妹妹說。
“但是,這不是真實的生活,真正大人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應該是人與人之相誠懇的相處。這五年來確實是和你相處得很和樂、很自由,但是,最近我覺得這不是真正的生活,因為我根本感覺不到生活的本質,你老是想着你自己的事情,想要和你談點正經的事時,你卻老是開玩笑!”
“因為我個性內嚮。”我說。
“是傲慢!”妹妹說。
“內嚮又傲慢!”我一邊倒着香檳,一邊嚮渡邊升說明。
“我是一個內嚮加傲慢的綜合體。”
“我懂你的意思。”
渡邊升點點頭說。
“但是,如果衹剩下你一個人的話……換句話說,如果她和我結婚了的話……大哥你還是不想找一個人結婚嗎?”
“大概是吧!”我說。
“真的?”妹妹問我說。
“如果你真的這麽想的話,我的朋友中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女孩子,可以介紹給你。”
“到時候再說吧!現在仍然太危險了。”
原作:村上春樹
■譯者:許珀理
■皇冠《面包屋再襲擊》
(1)
到目前為止我仍然不敢確定,將搶劫面包店的事情,告訴妻子,到底是不是正確的選擇。問題大概是出在缺少一個推斷正確的基準吧!換句話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正確的結果,是由於不正確的選擇所造成的,相反的,有很多不正確的結果,卻是正確的選擇所造成的。為了回避這種不合理性……我想這樣說應該無妨……我們有必要站在一個不做任何選擇的立場上,大致說來,我是依據這樣的思考來過生活的。發生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了。尚未發生的事情仍然未發生。
如果以這個立場來思考每一件事情的話,我將搶劫面包店的事情告訴妻子,這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已經說出去的話就像覆水一樣難收,如果會因為這些話而發生某個事件,那也是既定的事實,永遠無法改變。如果人們會以奇異的眼光來看這個事件的話,我認為應該到事件整體的狀況去探求。但是,不管我是如何來想這件事情,事情永遠是不會改變。這麽說也衹不過是一種想法罷了!
我在妻子面前提起搶劫面包這件事情,是因為我肚子實在餓得受不了,時間是在深夜兩點鐘前,我和妻子在六點鐘時吃了簡便的晚餐,九點半就鑽進被窩裏,閉上眼睛呼呼大睡。但是,在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了什麽,兩人同時睜開眼睛。一醒來時,就立刻覺得肚子餓得令人難以忍受,非得吃點什麽東西不可。
但是冰箱裏可以稱之為食物的東西一點也沒有,衹有沙拉醬、六瓶啤酒、兩顆幹透的洋蔥、奶油和除臭劑。我們在兩個星期前結婚,尚未明確的確立飲食生活的共識,除了飲食問題之外,我們當時尚未確立的事情還很有很多。
我當時在法律事務所上班,妻子在服裝設計學校負責事務方面的工作。我大概是二十八、九歲(不知道為什麽我老是想不起來結婚那年是幾歲)她比我小兩年八個月。我們的生活都非常忙碌,傢對我們而言衹不過是一座立體洞窟。傢裏一團亂七八糟,當然是不會想到需要準備食物的問題。
我們起床進了廚房,不知道該怎麽辨的圍着餐桌坐,我們兩個都餓得再也睡不着了……身體躺下來,肚子更餓……衹好起床找點事情做,但是沒想到這樣肚子更餓。這種強烈的饑餓感到底是怎麻産生的,我們一點兒也找不到原因。我和妻子仍抱着一縷希望,頻頻輪流的去打開冰箱的門,但是,不論打開來看幾次,冰箱的內容都沒有改變,依舊衹是啤酒、洋蔥、奶油和除臭劑。雖然洋蔥炒奶油也是一道頗可口的佳餚,但是我不認為兩顆幹透的洋蔥足以填飽我們的肚子。洋蔥應該是和別的東西一起吃的,它不能算得上是能夠充饑的食物。
“除臭劑炒除臭劑怎麽樣?”
我開玩笑地提出這個建議,妻子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不說半句話。
“開車出去,找一傢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餐館吧!”我說。
“衹要離開了國道,一定可以找到餐館的。”
但是妻子拒絶了我的建議,她說討厭這個在這個時候外出吃飯。
“晚上過了十二點以後,為吃飯而外出,總覺得不太對勁。”她說。
在這個方面她是非常守舊的。
“算了!就讓肚子餓下去吧!”
我嘆了一口氣說。
這大概是剛結婚時纔有的事情,妻子的意見(甚至可以說是主張)竟然像某種啓示似的,在我的耳邊響起。聽她這麽一說,我覺得我的饑餓感,並不是開車沿着國道找一傢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餐館,任意買一些便宜食品充饑的饑餓感,這實在可以說是一種很特殊的饑餓。
特殊的饑餓到底是什麽呢?
我在這裏可以將它提示為一種映象。
我乘着一艘船,漂浮在平靜的海面上;
往下一看,在水中可以看見海底火山的山頂;
雖然海面和山頂之間看起來好象並沒有多少距離,但是不知道下確到底有多遠;
水因為太透明了,以至於找不到絲毫的距離感。
妻子不想上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餐館,我衹好無可奈何地同意:
“算了!就讓肚子餓下去吧!”
在這之後,短短的二到三秒之間,我的腦海裏所浮現大致上就是這些事情。因為我不是心理學家佛洛依德,所以這些映象到底具有什麽意義,我無法做明確的分析,但是,這些屬於啓發性的映象,可以用直覺來加以理解。因此,我不管肚子饑餓的感覺如此地強烈,對於她不肯外出用餐的主張(甚至於可以說是聲明)半自動地表示同意。
毫無辦法,我們衹好喝起啤酒來了,因為,與其吃洋蔥,不如喝啤酒來得方便。妻子並不怎麽喜歡喝啤酒,我喝了六瓶中的四瓶,她衹喝其餘的兩瓶。我正在喝啤酒的時候,妻子像衹餓昏了頭的慄鼠似的,不斷地翻弄着廚房櫥架上的東西,最後好容易在一個塑料袋底找到了四塊奶油餅幹,這是在做冷凍蛋糕時用剩下的,因為潮濕而變軟了,但是我們仍然很慎重的一人分兩塊,將它吃下。
但是非常遺憾的,啤酒和奶油對我們饑餓的肚子並沒有絲毫的助益。
我們不斷的讀着印在啤酒罐上的字,頻頻眺望時鐘,輪流去打開冰箱的門,翻弄著作天的晚報,將掉到桌上的餅幹屑用明信片掃一堆。時間像是吞進魚肚的鉛錘,昏暗而沉重。
“我的肚子從來沒有這麽餓過!”妻子說。
“這種現象和結婚有沒有關係?”
不知道!我心裏想着。或許有關係,或許沒有關係!
妻子又到廚房去,想要找出一點點可以填飽肚子的食物時,我從小船上探出的身子,俯視海底火山的山頂,圍繞小船四周,海水的透明,使我的心情極度的不安,好象心窩深處突然生出一個大窟窿,沒有出口,也沒有入口,衹是一個純粹的空洞。這種體內奇妙的失落感─存在與不存在混淆不清的感覺,和爬到高聳的尖塔頂端,恐懼得顫抖的感覺,似乎有點兒類似。饑餓和懼高癥竟然會有相通的地方,這是一項新的發現。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以前有過相同的經驗。當時和現在一樣,肚子餓得難以忍受。那時候……
“我曾經去搶劫面包店!”
我不知不覺地說出這句話。
“搶劫面包店是怎麽一回事?”
妻子立刻就問。
於是我開始回想搶劫面包店的經過。
(2)
我說着,又啜了一口啤酒。
睡意就像從海底地震所産生的無聲波浪,使我的船受到猛烈的搖晃。
“當然啦!我們是如期的拿到希望獲得的面包!”我繼續說,“但是不管怎麽說,那都是稱不上是犯罪,衹能算是一種交換。因為我們聽了華格那的音樂,纔獲得所需的面包,從法律的角度來,這是一種交易行為。”
“但是,聽華格那的音樂並不能算是工作!”妻子說。
“說得也是!”我說。
“如果當時面包店的老闆要我們洗盤、或者是擦玻璃,我們一定會斷然拒絶,然後毫不猶豫的就搶走了面包。但他並沒有那樣的要求,衹是要我們聽聽華格納的唱片而已,因此我和同伴感到非常睏惑。可是當華格納的音樂一放出來時,我纔發覺和原先預想的完全不一樣,這些音樂廳起來好象是對我們所下的咒語一樣。即使是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認為當初實在不應該接受面包店老闆的要求,衹要依照最初的計畫,拿起刀子威脅他,單純地搶走面包。如果這麽做的話,應該就不會再有問題了。”
“發生什麽問題了嗎?”
我再度用手腕的內側揉揉眼睛。
“是這樣的。”我回答着說。
“雖然這不是眼睛所能清楚看見的具體問題,但是,很多事情都因這事件而慢慢的有所變化,而且發生一次變化之後,就很難再恢復原狀了。最後,我回到大學裏,把該修的課程修完,平安無事的畢業,然後便在法律事務所工作,一邊準備司法考試,接着就和你結婚,以後我再也不會去搶劫面包店了。”
“就這麽結束了嗎?”
“是的!就衹有這些而已。”
我說着,將剩下的啤酒一飲而盡,於是六瓶啤酒全都喝光了,煙灰缸裏剩下六個易開罐的拉環,好象美人魚被殺掉後所留下的鱗片。
當然不會什麽是都不發生的,眼前清清楚楚看得見的具體事情就發生了好幾件,但是,這些事情我並不想對她說。
“你的夥伴現在怎麽了呢?”妻子問。
“不知道!”我回答。
“後來發生了一點點小事,我們就分道揚鏢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連他現在在做些什麽也不知道了!”
妻子沉默了好一會兒,或許她從我的語氣中聽出了什麽令她感到不太明了的事情,但是,她對這點並不再提及。
“搶劫面包店會是你們分手的直接原因嗎?”
“大概是吧!這個事件使我們受到的震驚,比表面上看起來還要嚴重數倍,我們後來連續好幾天一直討論着面包和華格納的相關問題,談得最多的還是我們所做的選擇是否正確這件事,但是,始終沒有結論。如果仔細的想一想,這樣的選擇應該是正確的。不傷到任何人,而且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需求感到滿足,雖然面包店的主人……他為什麽要這麽做,到目前為止我仍然無理解,但是,他可以宣揚華格納的音樂,而我們獲得所需的面包,填飽肚子,這不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嗎?可是我們一直覺得這其中存着一項很大的錯誤,而且個錯誤莫名其妙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了一道非常黑暗的陰影。剛纔我所說的咒語就是這個緣故,毫無疑問地我們是被詛咒了!”
“那個咒語已經消失了嗎?”
我用煙灰缸裏的六個拉環做成一個手錶,套在手脕上。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世界上到處充滿咒語,那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因為那一個咒語的緣故而産生的,這實在非常難以瞭解。”
“不!不會有這種事情的!”妻子瞪大眼睛看着我說。“仔細想一想你就會瞭解!而且,除非是你自己親手將這個咒語解除,否則會像蛀牙一樣。一直折磨到你死為止,不衹是你,我也包括在內!”
“你?”
“是呀!因為我現在是你的妻子!”她說。
“例如我們現在所感到的饑餓,就是這個緣故。結婚之前,我從來不曾這麽餓過,你不覺得這其中有些異常嗎?這一定是你所受到的詛咒,也加臨在我的身上了。”
我點點頭,將套在手脕上的拉環丟回煙灰缸中,她所說的話到底有多少真實度,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有覺得她的話好象很有道理。
已經漸漸遠去的饑餓感,這時又重新回頭,而且,這回的饑餓比以前更加強烈,使得我的腦袋瓜隱隱作痛。胃裏每一個抽痛,都會迅速的傳到腦袋的中央。我的體內好象是由各式各樣復雜的機能所組合成似的。
我又看見了海底火山,海水比剛還要清澈,如果不是很仔細的觀察,連水的存在都感覺不出來,好象小船沒有受到任何的支撐,漂浮在半空中似的。而且海底的石頭一粒粒輪廓非常清楚,好象一伸手就可以將它撿起。
“雖然我和你生活在一起不過半個月左右的時間,但是,我確實感覺身邊一直存在着某種詛咒。”
她說着,眼睛仍一直瞪着我看,雙手交握在桌上。
“當然啦!在你還沒有說之前,我並不知道那是詛咒,但是,現在我已經非常清楚了,你確實是受到了詛咒!”
“你從什地方可以感覺到詛咒呢?”我問。
“我覺得好象是許多年不曾清洗,沾滿了灰塵的窗簾,從天花板上垂下來似的。”
“那大概不是詛咒,而是我自己本身吧!”我笑着說。
她卻沒有笑。
“不是這樣的,我非常清楚不是這樣的!”
“如果真的如你所說,現在還存在有咒語,那我該怎麽辦呢?”我說。
“再去搶劫面包店,而且,現在立刻就去!”
她非常肯定的說。“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去除咒語!”
“現在立刻就去?”我反問她。
“是的,現在立刻就去,趁肚子還餓着的時候,把以前沒有完成的事情都完成。”
“但是,有面包店半夜還營業的嗎?”
“東京這麽大,一定可以找到一傢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面包店。”
(終)
妻子坐進中古的豐田汽車,穿梭在凌晨兩點半的東京街上,尋找面包店。我手握着方向盤,妻子坐在前座,好象道路兩旁的貓頭鷹,在深夜裏露出尖銳的視綫。後座上橫躺着一把硬直、細長的自動式散彈槍,車子每一震動,裝在妻子口袋裏預備用的子彈就會發出幹裂的碰撞聲,除此之外,行李箱裏還放着兩個黑色的滑雪面罩。妻子為什麽會有散彈槍,我也不太清楚。滑雪面罩也是一樣,我和她從來不曾去滑過雪。但是,關於這些她並沒有一一說明,我也不想詢問,衹是覺得結婚生活真是非常奇妙。
可是,儘管我們的裝備如此齊全,我們還是未曾發現一間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面包店。我在深夜裏開着車子,從代代木到新宿,然後再到四𠔌、赤阪、青山、廣尾、六本木、代官山、澀𠔌,看到了深夜東京裏各式各樣的人和商店,就是沒有看見一傢面包店,大概是他們在半夜裏都不烤面包吧!
在途中我們遇到兩次警察的巡邏車,有一輛靜靜的躲在道路旁邊,另外一輛則以比較緩慢的速度,從我們的背後超車而過,這時候我警張得腋下沁滿了汗,妻子則根本不把警車放在眼裏,一心衹想找一傢面包店。每當她身體的角度一改變,口袋裏的子彈就發出碰撞的聲音。
“算了!放棄吧!”我說。“在這麽深的夜裏不會有面包店仍然營業的,這件事情我們應該事先調查清楚。”
“停車!”
妻子突然大叫。
我慌慌張張的踩下車子的煞車器。
“就是這裏了!”
她用平靜的口氣說。
我手仍然放在方向盤上,嚮四周打量一下,在這附近沒有看到一間嚮面包店的商店,路旁的每一傢商店都拉下了鐵門,四處一片靜悄悄的,衹有理發店的霓虹燈在黑暗中仍然旋轉不定,好象一雙足以洞徹這個詭異的深夜的大眼睛。除此之外,在二百公尺左右的前方,還可以看見麥當勞明亮的看板。
“沒有看見面包店呀!”我說。
但是妻子一言不發的打開行李箱,取出了布製的貼布,然後走下車來,我也打開另一側的車門,下了車。妻子蹲在車子的前面,用貼布將車子的車牌號碼貼了起來,大概是預防被人偷記下車牌號碼,然後轉到車子後面,將那裏的車牌也同樣貼起來,手法非常的熟練。我站在一旁看着她,腦子裏一片混亂。
“到那傢麥當勞去吧!”妻子說。
語氣輕鬆得好象晚飯用餐時選擇合適的餐館似的。
“麥當勞不是面包店!”
我反駁地說。
“不過和面包店差不多!”
妻子說着就回到車子上。
“該通融的地方最好能夠通融一下,反正我們已經來到麥當勞前面了。”
我衹好照着她的話,將車子往前開二百公尺左右,停進麥當勞的停車場。停車場裏衹停着一輛紅色閃閃發亮的bluebird。妻子將包裏着毛巾的散彈槍交給了我。
“我從來沒有射過這種玩意兒,我也不想射它!”
我抗議的說。
“你沒有必要開槍啊!衹要拿着它就好了,因為沒有人敢和你抵抗的。”
妻子說。
“可以嗎?照我的話去做,首先,兩個人正大光明的走進店裏,等店員說“歡迎光臨麥當勞”,就立刻將滑雪面罩戴上,清楚了嗎?”
“這一點是非常清楚,但是……”“然後你拿起槍對準店員,叫所有的作業人員和客人都集中在一個地方,動作一定要快,接下的事情就全部看我的。”
“但是……”“你想需要幾個漢堡呢?”
她問我,但沒等我開口就說:
“三十個應該夠了吧?”
“大概夠了!”我說。
我摒氣凝神地街過了散彈槍,稍微打開毛巾一看,這把槍像沙袋一樣重,像暗夜一樣漆黑。
“真的需要拿着這個玩意嗎?”我說。
有一半是問着她,有一半是問着我自己。
“當然要!”她說。
“歡迎光臨麥當勞!”
一位年輕的櫃臺小姐戴着麥當勞的帽子,臉上挂着麥當勞式的微笑對我說。
因為我一直認為這麽深的夜裹在麥當勞不該有女孩子在上班,所以看到她的那一剎那,我感到腦子裏一陣混亂;還好立刻救回過神來,趕緊戴上滑雪的帽子。
櫃臺小姐看我們突然戴上滑雪的帽子,臉上露出了訝異的表情。
這種狀況的應對方法,在“麥當勞待客手册”中應該沒有寫吧!她在說完:“歡迎光臨麥當勞!”之後,雖然還想繼續說下去,但是張大了嘴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臉上還挂着供作用的微笑,可是兩片嘴唇卻慘白得不停顫抖。
我急忙的取下毛巾,拿起了槍,對準顧客席位。在顧客席上衹有一對學生式的情侶,趴在塑料桌子上,睡得非常瀋穩。桌子上他們兩個人的頭和草莓雪客的杯子整齊的排列,彷佛式一個前衛的藝術品。因為兩個人都睡得和死人一樣,所以我想大概不會對我們的作業發生什麽障礙吧!因此,我就將槍對準櫃臺邊。
麥當勞的櫃員總共有三人,櫃臺的小姐大約二十來歲,鵝蛋型的臉蛋;氣色不太好的店長;以及在廚房裏打工的學生。三個人都聚集在收款機前,瞪大眼睛,看着槍口,沒有人大聲嚷嚷,也沒有人要出來抓我們的模樣。因為槍實在太重了,我衹好將手指放在扣板機的地方,槍身放在櫃臺上。
“錢可以統統給你!”
店長用沙啞的聲音說。
“不過十一點十已經全部回收了,現在這裏所剩不多,請你統統拿走吧!我們有保險,沒有關係!”
“請你拉下前面的鐵門,把看板的電燈關掉!”妻子說。
“請等一下!”店長說。
“這一點我不能答應你,因為任意關閉店門我會受到上級的處罰。”
妻子又將相同的命令重複了一次。
“你最好照着她的話去做!”我對他忠告說。
店長滿臉的茫然,看着櫃臺上的槍口,又看看妻子的臉,最後衹好死心的關掉善板上的電燈,把正面的拉們放了下來。我一直提高警覺以防他趁忙亂之際去按警報裝置,可是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麥當勞漢堡連鎖店似乎沒有非常報警裝置,或許他們沒想到會有人想搶劫漢堡店吧!
正面的拉門捲到地面上時,啪……的一聲巨響,自動地上鎖了,可是趴在桌上的一對學生仍然瀋瀋的地睡着。我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曾如此安穩地睡了。
“外帶三十個漢堡!”妻子說。
“這裏的錢足夠你買三十個漢堡,請你拿這些錢到別的地方去買,好嗎?”店長說。
“否則我們的帳簿會非常麻煩,換句話說……”“你最好照着她的話做!”
我又重複了一次。
三個人一起進入了廚房,開始做起三十個漢堡來。打工的學生烤着漢堡肉,店長將它夾進面包中,櫃臺小姐用白色的紙將它包裝起來。這時候四下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我身體倚靠在大型的冰箱上,散彈槍的槍口對準烤漢堡的鐵板,鐵板上並排着一塊快深褐色圓形的漢堡肉,因為煎烤而發出吱吱的聲響。烤肉所發出甜美的香氣好象一群眼睛看不見的小蟲,鑽進我全身的毛孔裏,混入血液中,在我全身的每個角落巡邏,然後最終目的是集結在我身體中心所産生饑餓的空洞中,使我四衹無力,身心疲憊得幾乎要昏厥過去。
真想立刻就抓起一、二個包裏着白色包裝紙,堆積在一旁的漢堡來痛快的大吃一頓,但是,如果我這麽做的話,我們的目的會立刻就被識破,因此,我們衹好等三十個漢堡全部做好之後再說了。
廚房裏非常熾熱,而我們又戴着滑雪面罩,衹好頻頻揮汗了。
三個人一邊做漢堡,偶爾擡起頭來偷偷地描槍口一眼。
我不時地用左手小拇指的指尖挖兩邊的耳朵,因握每當我一緊張起來時,耳朵就會發癢。可是我一挖耳朵,槍身就會不穩定的上下搖動,使得他們三個人的情緒也隨之混亂起來。雖然槍的安全鎖一直牢牢地鎖住,不用擔心會有爆發的情形産生,但是他們三個人並不知道這件事,而我也不打算刻意去告訴他們。
三個人正在做漢堡,而我將槍口對準鐵板看守着,妻子則註意顧客席位那兩位瀋瀋睡着的顧客,一邊屬着做好的漢堡,她將包裝紙包裏好的漢堡整齊的排放在紙袋中,每一個紙袋裝着十五個漢堡。
“你們為什麽非這麽做不可呢?”年輕的櫃臺小姐對我說。
“你們可以把錢搶走,去買你們喜歡的東西,這樣不是更好?可是你們卻偏偏要吃三十個漢堡,你們的用意到底在哪裏呢?”
我一句也回答不出來,衹好對她搖搖頭。
“雖然我們的作為有些惡劣,但是誰叫面包店晚上都不開呢?”妻子對她說明。
“如果面包店開着的話,我們一定去搶面包店的。”
這樣的說明是否能樣他們理解,我覺得非常懷疑,但是,他們從此就不再開口,靜靜地烤着漢堡肉,將漢堡肉夾在面包裏,然後用包裝紙包起來。兩個紙袋裏裝滿了三十個漢堡之後,妻子又嚮櫃臺小姐點了兩大杯的可樂,不過可樂的錢卻是一毛也不差的付清。
“除了面包以外,我們什麽也不搶。”妻子對她說明。
她的頭動了一動,既像是在搖頭,又像是在點頭,大概是兩個動作同時進行吧!我覺得自己非常能夠體會她的心情。
妻子接着從口袋裏拿出綁東西用的細繩子——-她準備得實在太齊全了——-將三個人一起綁在柱子上,三個人大概也領悟了多說無益,乖乖得聽由她擺布了。雖然妻子體貼的詢問他們:“會痛嗎?”
“想去上厠所嗎?”但是他們始終不再說一句話。
我用毛巾包好了槍,妻子兩手提起印有麥當勞標志的紙袋,打開正面的拉門一起走出去。顧客席位上的兩個人這時仍然嚮深海裏的魚一樣,瀋睡在夢中。倒底什麽事情才能夠將他們倆個人從瀋睡中喚起,這個問題令我覺得非常納悶。
車子開了三十分鐘後,停進了一棟適當的大廈停車場,我們輕鬆愉快地吃着漢堡,喝着可樂。我一共塞了六個漢堡進入空洞的胃裏,妻子吃了四個,車子的後座上還留下二十個漢堡。
隨個黎明的到臨,我們認為或許會永遠持續着的饑餓也消失了。太陽最初的光芒將大廈骯髒的墻面染成了騰黃色,“新力牌高傳真音響組合”的巨大廣告塔依舊發出耀眼的閃爍,在不時響起大卡車經過的轟隆聲中,似乎還混雜着鳥叫聲,fen電臺播放着鄉村音樂。我們兩人合抽一根香煙,香煙抽完之後,妻子將頭靠在我的肩上。
“你真的認為有必要做這件事嗎?”我在一次問她。
“當然!”她回答。
然後我衹深呼吸了一口氣就睡着了。她的身體像衹小貓一樣的輕柔。
剩下我一個人之後,我又再度從船上探出身來,窺着海底的景觀,但是,這時候卻在也看不見海底火山的模樣了。水面一片平靜,倒映着藍色的天空,小小的波浪像清風吹拂緩緩搖曳的絹質睡袍似的,輕扣着小船的側板。
我橫躺在船底,閉上了眼睛,等待漲潮將我在運到最適合的地方。
■譯者:許珀理
■皇冠《面包屋再襲擊》
(1)
到目前為止我仍然不敢確定,將搶劫面包店的事情,告訴妻子,到底是不是正確的選擇。問題大概是出在缺少一個推斷正確的基準吧!換句話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正確的結果,是由於不正確的選擇所造成的,相反的,有很多不正確的結果,卻是正確的選擇所造成的。為了回避這種不合理性……我想這樣說應該無妨……我們有必要站在一個不做任何選擇的立場上,大致說來,我是依據這樣的思考來過生活的。發生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了。尚未發生的事情仍然未發生。
如果以這個立場來思考每一件事情的話,我將搶劫面包店的事情告訴妻子,這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已經說出去的話就像覆水一樣難收,如果會因為這些話而發生某個事件,那也是既定的事實,永遠無法改變。如果人們會以奇異的眼光來看這個事件的話,我認為應該到事件整體的狀況去探求。但是,不管我是如何來想這件事情,事情永遠是不會改變。這麽說也衹不過是一種想法罷了!
我在妻子面前提起搶劫面包這件事情,是因為我肚子實在餓得受不了,時間是在深夜兩點鐘前,我和妻子在六點鐘時吃了簡便的晚餐,九點半就鑽進被窩裏,閉上眼睛呼呼大睡。但是,在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了什麽,兩人同時睜開眼睛。一醒來時,就立刻覺得肚子餓得令人難以忍受,非得吃點什麽東西不可。
但是冰箱裏可以稱之為食物的東西一點也沒有,衹有沙拉醬、六瓶啤酒、兩顆幹透的洋蔥、奶油和除臭劑。我們在兩個星期前結婚,尚未明確的確立飲食生活的共識,除了飲食問題之外,我們當時尚未確立的事情還很有很多。
我當時在法律事務所上班,妻子在服裝設計學校負責事務方面的工作。我大概是二十八、九歲(不知道為什麽我老是想不起來結婚那年是幾歲)她比我小兩年八個月。我們的生活都非常忙碌,傢對我們而言衹不過是一座立體洞窟。傢裏一團亂七八糟,當然是不會想到需要準備食物的問題。
我們起床進了廚房,不知道該怎麽辨的圍着餐桌坐,我們兩個都餓得再也睡不着了……身體躺下來,肚子更餓……衹好起床找點事情做,但是沒想到這樣肚子更餓。這種強烈的饑餓感到底是怎麻産生的,我們一點兒也找不到原因。我和妻子仍抱着一縷希望,頻頻輪流的去打開冰箱的門,但是,不論打開來看幾次,冰箱的內容都沒有改變,依舊衹是啤酒、洋蔥、奶油和除臭劑。雖然洋蔥炒奶油也是一道頗可口的佳餚,但是我不認為兩顆幹透的洋蔥足以填飽我們的肚子。洋蔥應該是和別的東西一起吃的,它不能算得上是能夠充饑的食物。
“除臭劑炒除臭劑怎麽樣?”
我開玩笑地提出這個建議,妻子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不說半句話。
“開車出去,找一傢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餐館吧!”我說。
“衹要離開了國道,一定可以找到餐館的。”
但是妻子拒絶了我的建議,她說討厭這個在這個時候外出吃飯。
“晚上過了十二點以後,為吃飯而外出,總覺得不太對勁。”她說。
在這個方面她是非常守舊的。
“算了!就讓肚子餓下去吧!”
我嘆了一口氣說。
這大概是剛結婚時纔有的事情,妻子的意見(甚至可以說是主張)竟然像某種啓示似的,在我的耳邊響起。聽她這麽一說,我覺得我的饑餓感,並不是開車沿着國道找一傢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餐館,任意買一些便宜食品充饑的饑餓感,這實在可以說是一種很特殊的饑餓。
特殊的饑餓到底是什麽呢?
我在這裏可以將它提示為一種映象。
我乘着一艘船,漂浮在平靜的海面上;
往下一看,在水中可以看見海底火山的山頂;
雖然海面和山頂之間看起來好象並沒有多少距離,但是不知道下確到底有多遠;
水因為太透明了,以至於找不到絲毫的距離感。
妻子不想上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餐館,我衹好無可奈何地同意:
“算了!就讓肚子餓下去吧!”
在這之後,短短的二到三秒之間,我的腦海裏所浮現大致上就是這些事情。因為我不是心理學家佛洛依德,所以這些映象到底具有什麽意義,我無法做明確的分析,但是,這些屬於啓發性的映象,可以用直覺來加以理解。因此,我不管肚子饑餓的感覺如此地強烈,對於她不肯外出用餐的主張(甚至於可以說是聲明)半自動地表示同意。
毫無辦法,我們衹好喝起啤酒來了,因為,與其吃洋蔥,不如喝啤酒來得方便。妻子並不怎麽喜歡喝啤酒,我喝了六瓶中的四瓶,她衹喝其餘的兩瓶。我正在喝啤酒的時候,妻子像衹餓昏了頭的慄鼠似的,不斷地翻弄着廚房櫥架上的東西,最後好容易在一個塑料袋底找到了四塊奶油餅幹,這是在做冷凍蛋糕時用剩下的,因為潮濕而變軟了,但是我們仍然很慎重的一人分兩塊,將它吃下。
但是非常遺憾的,啤酒和奶油對我們饑餓的肚子並沒有絲毫的助益。
我們不斷的讀着印在啤酒罐上的字,頻頻眺望時鐘,輪流去打開冰箱的門,翻弄著作天的晚報,將掉到桌上的餅幹屑用明信片掃一堆。時間像是吞進魚肚的鉛錘,昏暗而沉重。
“我的肚子從來沒有這麽餓過!”妻子說。
“這種現象和結婚有沒有關係?”
不知道!我心裏想着。或許有關係,或許沒有關係!
妻子又到廚房去,想要找出一點點可以填飽肚子的食物時,我從小船上探出的身子,俯視海底火山的山頂,圍繞小船四周,海水的透明,使我的心情極度的不安,好象心窩深處突然生出一個大窟窿,沒有出口,也沒有入口,衹是一個純粹的空洞。這種體內奇妙的失落感─存在與不存在混淆不清的感覺,和爬到高聳的尖塔頂端,恐懼得顫抖的感覺,似乎有點兒類似。饑餓和懼高癥竟然會有相通的地方,這是一項新的發現。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以前有過相同的經驗。當時和現在一樣,肚子餓得難以忍受。那時候……
“我曾經去搶劫面包店!”
我不知不覺地說出這句話。
“搶劫面包店是怎麽一回事?”
妻子立刻就問。
於是我開始回想搶劫面包店的經過。
(2)
我說着,又啜了一口啤酒。
睡意就像從海底地震所産生的無聲波浪,使我的船受到猛烈的搖晃。
“當然啦!我們是如期的拿到希望獲得的面包!”我繼續說,“但是不管怎麽說,那都是稱不上是犯罪,衹能算是一種交換。因為我們聽了華格那的音樂,纔獲得所需的面包,從法律的角度來,這是一種交易行為。”
“但是,聽華格那的音樂並不能算是工作!”妻子說。
“說得也是!”我說。
“如果當時面包店的老闆要我們洗盤、或者是擦玻璃,我們一定會斷然拒絶,然後毫不猶豫的就搶走了面包。但他並沒有那樣的要求,衹是要我們聽聽華格納的唱片而已,因此我和同伴感到非常睏惑。可是當華格納的音樂一放出來時,我纔發覺和原先預想的完全不一樣,這些音樂廳起來好象是對我們所下的咒語一樣。即使是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認為當初實在不應該接受面包店老闆的要求,衹要依照最初的計畫,拿起刀子威脅他,單純地搶走面包。如果這麽做的話,應該就不會再有問題了。”
“發生什麽問題了嗎?”
我再度用手腕的內側揉揉眼睛。
“是這樣的。”我回答着說。
“雖然這不是眼睛所能清楚看見的具體問題,但是,很多事情都因這事件而慢慢的有所變化,而且發生一次變化之後,就很難再恢復原狀了。最後,我回到大學裏,把該修的課程修完,平安無事的畢業,然後便在法律事務所工作,一邊準備司法考試,接着就和你結婚,以後我再也不會去搶劫面包店了。”
“就這麽結束了嗎?”
“是的!就衹有這些而已。”
我說着,將剩下的啤酒一飲而盡,於是六瓶啤酒全都喝光了,煙灰缸裏剩下六個易開罐的拉環,好象美人魚被殺掉後所留下的鱗片。
當然不會什麽是都不發生的,眼前清清楚楚看得見的具體事情就發生了好幾件,但是,這些事情我並不想對她說。
“你的夥伴現在怎麽了呢?”妻子問。
“不知道!”我回答。
“後來發生了一點點小事,我們就分道揚鏢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連他現在在做些什麽也不知道了!”
妻子沉默了好一會兒,或許她從我的語氣中聽出了什麽令她感到不太明了的事情,但是,她對這點並不再提及。
“搶劫面包店會是你們分手的直接原因嗎?”
“大概是吧!這個事件使我們受到的震驚,比表面上看起來還要嚴重數倍,我們後來連續好幾天一直討論着面包和華格納的相關問題,談得最多的還是我們所做的選擇是否正確這件事,但是,始終沒有結論。如果仔細的想一想,這樣的選擇應該是正確的。不傷到任何人,而且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需求感到滿足,雖然面包店的主人……他為什麽要這麽做,到目前為止我仍然無理解,但是,他可以宣揚華格納的音樂,而我們獲得所需的面包,填飽肚子,這不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嗎?可是我們一直覺得這其中存着一項很大的錯誤,而且個錯誤莫名其妙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了一道非常黑暗的陰影。剛纔我所說的咒語就是這個緣故,毫無疑問地我們是被詛咒了!”
“那個咒語已經消失了嗎?”
我用煙灰缸裏的六個拉環做成一個手錶,套在手脕上。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世界上到處充滿咒語,那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因為那一個咒語的緣故而産生的,這實在非常難以瞭解。”
“不!不會有這種事情的!”妻子瞪大眼睛看着我說。“仔細想一想你就會瞭解!而且,除非是你自己親手將這個咒語解除,否則會像蛀牙一樣。一直折磨到你死為止,不衹是你,我也包括在內!”
“你?”
“是呀!因為我現在是你的妻子!”她說。
“例如我們現在所感到的饑餓,就是這個緣故。結婚之前,我從來不曾這麽餓過,你不覺得這其中有些異常嗎?這一定是你所受到的詛咒,也加臨在我的身上了。”
我點點頭,將套在手脕上的拉環丟回煙灰缸中,她所說的話到底有多少真實度,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有覺得她的話好象很有道理。
已經漸漸遠去的饑餓感,這時又重新回頭,而且,這回的饑餓比以前更加強烈,使得我的腦袋瓜隱隱作痛。胃裏每一個抽痛,都會迅速的傳到腦袋的中央。我的體內好象是由各式各樣復雜的機能所組合成似的。
我又看見了海底火山,海水比剛還要清澈,如果不是很仔細的觀察,連水的存在都感覺不出來,好象小船沒有受到任何的支撐,漂浮在半空中似的。而且海底的石頭一粒粒輪廓非常清楚,好象一伸手就可以將它撿起。
“雖然我和你生活在一起不過半個月左右的時間,但是,我確實感覺身邊一直存在着某種詛咒。”
她說着,眼睛仍一直瞪着我看,雙手交握在桌上。
“當然啦!在你還沒有說之前,我並不知道那是詛咒,但是,現在我已經非常清楚了,你確實是受到了詛咒!”
“你從什地方可以感覺到詛咒呢?”我問。
“我覺得好象是許多年不曾清洗,沾滿了灰塵的窗簾,從天花板上垂下來似的。”
“那大概不是詛咒,而是我自己本身吧!”我笑着說。
她卻沒有笑。
“不是這樣的,我非常清楚不是這樣的!”
“如果真的如你所說,現在還存在有咒語,那我該怎麽辦呢?”我說。
“再去搶劫面包店,而且,現在立刻就去!”
她非常肯定的說。“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去除咒語!”
“現在立刻就去?”我反問她。
“是的,現在立刻就去,趁肚子還餓着的時候,把以前沒有完成的事情都完成。”
“但是,有面包店半夜還營業的嗎?”
“東京這麽大,一定可以找到一傢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面包店。”
(終)
妻子坐進中古的豐田汽車,穿梭在凌晨兩點半的東京街上,尋找面包店。我手握着方向盤,妻子坐在前座,好象道路兩旁的貓頭鷹,在深夜裏露出尖銳的視綫。後座上橫躺着一把硬直、細長的自動式散彈槍,車子每一震動,裝在妻子口袋裏預備用的子彈就會發出幹裂的碰撞聲,除此之外,行李箱裏還放着兩個黑色的滑雪面罩。妻子為什麽會有散彈槍,我也不太清楚。滑雪面罩也是一樣,我和她從來不曾去滑過雪。但是,關於這些她並沒有一一說明,我也不想詢問,衹是覺得結婚生活真是非常奇妙。
可是,儘管我們的裝備如此齊全,我們還是未曾發現一間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面包店。我在深夜裏開着車子,從代代木到新宿,然後再到四𠔌、赤阪、青山、廣尾、六本木、代官山、澀𠔌,看到了深夜東京裏各式各樣的人和商店,就是沒有看見一傢面包店,大概是他們在半夜裏都不烤面包吧!
在途中我們遇到兩次警察的巡邏車,有一輛靜靜的躲在道路旁邊,另外一輛則以比較緩慢的速度,從我們的背後超車而過,這時候我警張得腋下沁滿了汗,妻子則根本不把警車放在眼裏,一心衹想找一傢面包店。每當她身體的角度一改變,口袋裏的子彈就發出碰撞的聲音。
“算了!放棄吧!”我說。“在這麽深的夜裏不會有面包店仍然營業的,這件事情我們應該事先調查清楚。”
“停車!”
妻子突然大叫。
我慌慌張張的踩下車子的煞車器。
“就是這裏了!”
她用平靜的口氣說。
我手仍然放在方向盤上,嚮四周打量一下,在這附近沒有看到一間嚮面包店的商店,路旁的每一傢商店都拉下了鐵門,四處一片靜悄悄的,衹有理發店的霓虹燈在黑暗中仍然旋轉不定,好象一雙足以洞徹這個詭異的深夜的大眼睛。除此之外,在二百公尺左右的前方,還可以看見麥當勞明亮的看板。
“沒有看見面包店呀!”我說。
但是妻子一言不發的打開行李箱,取出了布製的貼布,然後走下車來,我也打開另一側的車門,下了車。妻子蹲在車子的前面,用貼布將車子的車牌號碼貼了起來,大概是預防被人偷記下車牌號碼,然後轉到車子後面,將那裏的車牌也同樣貼起來,手法非常的熟練。我站在一旁看着她,腦子裏一片混亂。
“到那傢麥當勞去吧!”妻子說。
語氣輕鬆得好象晚飯用餐時選擇合適的餐館似的。
“麥當勞不是面包店!”
我反駁地說。
“不過和面包店差不多!”
妻子說着就回到車子上。
“該通融的地方最好能夠通融一下,反正我們已經來到麥當勞前面了。”
我衹好照着她的話,將車子往前開二百公尺左右,停進麥當勞的停車場。停車場裏衹停着一輛紅色閃閃發亮的bluebird。妻子將包裏着毛巾的散彈槍交給了我。
“我從來沒有射過這種玩意兒,我也不想射它!”
我抗議的說。
“你沒有必要開槍啊!衹要拿着它就好了,因為沒有人敢和你抵抗的。”
妻子說。
“可以嗎?照我的話去做,首先,兩個人正大光明的走進店裏,等店員說“歡迎光臨麥當勞”,就立刻將滑雪面罩戴上,清楚了嗎?”
“這一點是非常清楚,但是……”“然後你拿起槍對準店員,叫所有的作業人員和客人都集中在一個地方,動作一定要快,接下的事情就全部看我的。”
“但是……”“你想需要幾個漢堡呢?”
她問我,但沒等我開口就說:
“三十個應該夠了吧?”
“大概夠了!”我說。
我摒氣凝神地街過了散彈槍,稍微打開毛巾一看,這把槍像沙袋一樣重,像暗夜一樣漆黑。
“真的需要拿着這個玩意嗎?”我說。
有一半是問着她,有一半是問着我自己。
“當然要!”她說。
“歡迎光臨麥當勞!”
一位年輕的櫃臺小姐戴着麥當勞的帽子,臉上挂着麥當勞式的微笑對我說。
因為我一直認為這麽深的夜裹在麥當勞不該有女孩子在上班,所以看到她的那一剎那,我感到腦子裏一陣混亂;還好立刻救回過神來,趕緊戴上滑雪的帽子。
櫃臺小姐看我們突然戴上滑雪的帽子,臉上露出了訝異的表情。
這種狀況的應對方法,在“麥當勞待客手册”中應該沒有寫吧!她在說完:“歡迎光臨麥當勞!”之後,雖然還想繼續說下去,但是張大了嘴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臉上還挂着供作用的微笑,可是兩片嘴唇卻慘白得不停顫抖。
我急忙的取下毛巾,拿起了槍,對準顧客席位。在顧客席上衹有一對學生式的情侶,趴在塑料桌子上,睡得非常瀋穩。桌子上他們兩個人的頭和草莓雪客的杯子整齊的排列,彷佛式一個前衛的藝術品。因為兩個人都睡得和死人一樣,所以我想大概不會對我們的作業發生什麽障礙吧!因此,我就將槍對準櫃臺邊。
麥當勞的櫃員總共有三人,櫃臺的小姐大約二十來歲,鵝蛋型的臉蛋;氣色不太好的店長;以及在廚房裏打工的學生。三個人都聚集在收款機前,瞪大眼睛,看着槍口,沒有人大聲嚷嚷,也沒有人要出來抓我們的模樣。因為槍實在太重了,我衹好將手指放在扣板機的地方,槍身放在櫃臺上。
“錢可以統統給你!”
店長用沙啞的聲音說。
“不過十一點十已經全部回收了,現在這裏所剩不多,請你統統拿走吧!我們有保險,沒有關係!”
“請你拉下前面的鐵門,把看板的電燈關掉!”妻子說。
“請等一下!”店長說。
“這一點我不能答應你,因為任意關閉店門我會受到上級的處罰。”
妻子又將相同的命令重複了一次。
“你最好照着她的話去做!”我對他忠告說。
店長滿臉的茫然,看着櫃臺上的槍口,又看看妻子的臉,最後衹好死心的關掉善板上的電燈,把正面的拉們放了下來。我一直提高警覺以防他趁忙亂之際去按警報裝置,可是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麥當勞漢堡連鎖店似乎沒有非常報警裝置,或許他們沒想到會有人想搶劫漢堡店吧!
正面的拉門捲到地面上時,啪……的一聲巨響,自動地上鎖了,可是趴在桌上的一對學生仍然瀋瀋的地睡着。我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曾如此安穩地睡了。
“外帶三十個漢堡!”妻子說。
“這裏的錢足夠你買三十個漢堡,請你拿這些錢到別的地方去買,好嗎?”店長說。
“否則我們的帳簿會非常麻煩,換句話說……”“你最好照着她的話做!”
我又重複了一次。
三個人一起進入了廚房,開始做起三十個漢堡來。打工的學生烤着漢堡肉,店長將它夾進面包中,櫃臺小姐用白色的紙將它包裝起來。這時候四下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我身體倚靠在大型的冰箱上,散彈槍的槍口對準烤漢堡的鐵板,鐵板上並排着一塊快深褐色圓形的漢堡肉,因為煎烤而發出吱吱的聲響。烤肉所發出甜美的香氣好象一群眼睛看不見的小蟲,鑽進我全身的毛孔裏,混入血液中,在我全身的每個角落巡邏,然後最終目的是集結在我身體中心所産生饑餓的空洞中,使我四衹無力,身心疲憊得幾乎要昏厥過去。
真想立刻就抓起一、二個包裏着白色包裝紙,堆積在一旁的漢堡來痛快的大吃一頓,但是,如果我這麽做的話,我們的目的會立刻就被識破,因此,我們衹好等三十個漢堡全部做好之後再說了。
廚房裏非常熾熱,而我們又戴着滑雪面罩,衹好頻頻揮汗了。
三個人一邊做漢堡,偶爾擡起頭來偷偷地描槍口一眼。
我不時地用左手小拇指的指尖挖兩邊的耳朵,因握每當我一緊張起來時,耳朵就會發癢。可是我一挖耳朵,槍身就會不穩定的上下搖動,使得他們三個人的情緒也隨之混亂起來。雖然槍的安全鎖一直牢牢地鎖住,不用擔心會有爆發的情形産生,但是他們三個人並不知道這件事,而我也不打算刻意去告訴他們。
三個人正在做漢堡,而我將槍口對準鐵板看守着,妻子則註意顧客席位那兩位瀋瀋睡着的顧客,一邊屬着做好的漢堡,她將包裝紙包裏好的漢堡整齊的排放在紙袋中,每一個紙袋裝着十五個漢堡。
“你們為什麽非這麽做不可呢?”年輕的櫃臺小姐對我說。
“你們可以把錢搶走,去買你們喜歡的東西,這樣不是更好?可是你們卻偏偏要吃三十個漢堡,你們的用意到底在哪裏呢?”
我一句也回答不出來,衹好對她搖搖頭。
“雖然我們的作為有些惡劣,但是誰叫面包店晚上都不開呢?”妻子對她說明。
“如果面包店開着的話,我們一定去搶面包店的。”
這樣的說明是否能樣他們理解,我覺得非常懷疑,但是,他們從此就不再開口,靜靜地烤着漢堡肉,將漢堡肉夾在面包裏,然後用包裝紙包起來。兩個紙袋裏裝滿了三十個漢堡之後,妻子又嚮櫃臺小姐點了兩大杯的可樂,不過可樂的錢卻是一毛也不差的付清。
“除了面包以外,我們什麽也不搶。”妻子對她說明。
她的頭動了一動,既像是在搖頭,又像是在點頭,大概是兩個動作同時進行吧!我覺得自己非常能夠體會她的心情。
妻子接着從口袋裏拿出綁東西用的細繩子——-她準備得實在太齊全了——-將三個人一起綁在柱子上,三個人大概也領悟了多說無益,乖乖得聽由她擺布了。雖然妻子體貼的詢問他們:“會痛嗎?”
“想去上厠所嗎?”但是他們始終不再說一句話。
我用毛巾包好了槍,妻子兩手提起印有麥當勞標志的紙袋,打開正面的拉門一起走出去。顧客席位上的兩個人這時仍然嚮深海裏的魚一樣,瀋睡在夢中。倒底什麽事情才能夠將他們倆個人從瀋睡中喚起,這個問題令我覺得非常納悶。
車子開了三十分鐘後,停進了一棟適當的大廈停車場,我們輕鬆愉快地吃着漢堡,喝着可樂。我一共塞了六個漢堡進入空洞的胃裏,妻子吃了四個,車子的後座上還留下二十個漢堡。
隨個黎明的到臨,我們認為或許會永遠持續着的饑餓也消失了。太陽最初的光芒將大廈骯髒的墻面染成了騰黃色,“新力牌高傳真音響組合”的巨大廣告塔依舊發出耀眼的閃爍,在不時響起大卡車經過的轟隆聲中,似乎還混雜着鳥叫聲,fen電臺播放着鄉村音樂。我們兩人合抽一根香煙,香煙抽完之後,妻子將頭靠在我的肩上。
“你真的認為有必要做這件事嗎?”我在一次問她。
“當然!”她回答。
然後我衹深呼吸了一口氣就睡着了。她的身體像衹小貓一樣的輕柔。
剩下我一個人之後,我又再度從船上探出身來,窺着海底的景觀,但是,這時候卻在也看不見海底火山的模樣了。水面一片平靜,倒映着藍色的天空,小小的波浪像清風吹拂緩緩搖曳的絹質睡袍似的,輕扣着小船的側板。
我橫躺在船底,閉上了眼睛,等待漲潮將我在運到最適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