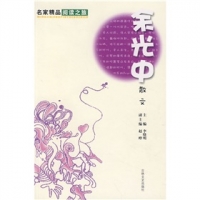从母亲到外遇作者:余光中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有文化,却没听说过武化。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统一那个,都不算文化。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卡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久矣我已被称为“台湾作家”。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例如她的粤腔九音诘屈,已经难解,有时还爱写简体字来考我,而冒犯了她,更会在左报上对我冷嘲热讽,所以开头的几年颇吃了她一点苦头。后来认识渐深,发现了她的真性情,终于转而相悦。不但粤语可解,简体字能读,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兴趣也从美国移向英国,香港更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不但因为港人欧游成风,远比台湾人为早,也因为签证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内地作家出国交流,也多以香港为首站,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巴金、辛笛、柯灵,也开始与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又诋之为文化沙漠。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于香港,五天后举殡,全港下半旗志哀。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不记得其他华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适当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吗?至于近年对六四与钓鱼台的抗议,场面之盛,牺牲之烈,也不像柔驯的殖民地吧。
欧洲开始成为外遇,则在我将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践欧土,是从纽约起飞,而由伦敦入境,绕了一个大圈,已经四十八岁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头,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点“迟暮”,季节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独游。临老而游花都,总不免感觉是辜负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说:“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一个人略谙法国艺术有多风流倜傥,眼底的巴黎总比一般观光嬉客所见要丰盈。“以前只是在印象派的画里见过巴黎,幻而似真;等到亲眼见了法国,却疑身在印象派的画里,真而似幻。”我在《巴黎看画记》一文,就以这一句开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艺都,更是欧洲之都。整个欧洲当然早已“迟暮”了,却依然十分“美人”,也许正因迟暮,美艳更教人怜。而且同属迟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风格差异。例如伦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至于巴黎,则不仅风韵犹存,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
大致说来,北欧的城市比较秀雅,南欧的则比较艳丽;新教的国家清醒中有节制,旧教的国家慵懒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尔摩虽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长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楼塔之类的建筑多以红而带褐的方砖砌成,隔了茫茫烟水,只见灰蒙蒙阴沉沉的一大片,低压在波上。那波涛,也是蓝少黑多,说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南欧的明媚风情在那样的黑涛上是难以想象的:格拉纳达的中世纪“红堡”(alhambra),那种细柱精雕、引泉入室的回教宫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灯,也不会赫现在波罗的海岸。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欧洲的传统建筑之美总会令人仰瞻低回,神游中古。且不论西欧南欧了,即使东欧的小国,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后”,其传统建筑如城堡、宫殿与教堂之类,比起现代的暴发都市来,仍然一派大家风范,耐看得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遭受纳粹的浩劫,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摧尽这些迟暮的美人,一任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在多瑙河边临流照镜,或是战神刀下留情,让布拉格的桥影卧魔涛而横陈。爱伦坡说得好: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希腊不再的光荣
和罗马已逝的盛况。
一切美景若具历史的回响、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令人兴奋,更使人低徊。何况欧洲文化不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浅薄可比。美国再富,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边盖一座罗浮宫吧?怪不得王尔德要说:“善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原载《人生与舞台》)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有文化,却没听说过武化。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统一那个,都不算文化。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卡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久矣我已被称为“台湾作家”。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例如她的粤腔九音诘屈,已经难解,有时还爱写简体字来考我,而冒犯了她,更会在左报上对我冷嘲热讽,所以开头的几年颇吃了她一点苦头。后来认识渐深,发现了她的真性情,终于转而相悦。不但粤语可解,简体字能读,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兴趣也从美国移向英国,香港更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不但因为港人欧游成风,远比台湾人为早,也因为签证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内地作家出国交流,也多以香港为首站,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巴金、辛笛、柯灵,也开始与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又诋之为文化沙漠。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于香港,五天后举殡,全港下半旗志哀。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不记得其他华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适当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吗?至于近年对六四与钓鱼台的抗议,场面之盛,牺牲之烈,也不像柔驯的殖民地吧。
欧洲开始成为外遇,则在我将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践欧土,是从纽约起飞,而由伦敦入境,绕了一个大圈,已经四十八岁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头,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点“迟暮”,季节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独游。临老而游花都,总不免感觉是辜负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说:“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一个人略谙法国艺术有多风流倜傥,眼底的巴黎总比一般观光嬉客所见要丰盈。“以前只是在印象派的画里见过巴黎,幻而似真;等到亲眼见了法国,却疑身在印象派的画里,真而似幻。”我在《巴黎看画记》一文,就以这一句开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艺都,更是欧洲之都。整个欧洲当然早已“迟暮”了,却依然十分“美人”,也许正因迟暮,美艳更教人怜。而且同属迟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风格差异。例如伦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至于巴黎,则不仅风韵犹存,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
大致说来,北欧的城市比较秀雅,南欧的则比较艳丽;新教的国家清醒中有节制,旧教的国家慵懒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尔摩虽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长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楼塔之类的建筑多以红而带褐的方砖砌成,隔了茫茫烟水,只见灰蒙蒙阴沉沉的一大片,低压在波上。那波涛,也是蓝少黑多,说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南欧的明媚风情在那样的黑涛上是难以想象的:格拉纳达的中世纪“红堡”(alhambra),那种细柱精雕、引泉入室的回教宫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灯,也不会赫现在波罗的海岸。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欧洲的传统建筑之美总会令人仰瞻低回,神游中古。且不论西欧南欧了,即使东欧的小国,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后”,其传统建筑如城堡、宫殿与教堂之类,比起现代的暴发都市来,仍然一派大家风范,耐看得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遭受纳粹的浩劫,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摧尽这些迟暮的美人,一任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在多瑙河边临流照镜,或是战神刀下留情,让布拉格的桥影卧魔涛而横陈。爱伦坡说得好: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希腊不再的光荣
和罗马已逝的盛况。
一切美景若具历史的回响、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令人兴奋,更使人低徊。何况欧洲文化不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浅薄可比。美国再富,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边盖一座罗浮宫吧?怪不得王尔德要说:“善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原载《人生与舞台》)
催魂铃
作者:余光中
一百年前发明电话的那人,什么不好姓,偏偏姓“铃”(alexanderbell),真是一大巧合。电话之来,总是从颤颤的一串铃声开始
,那高调,那频率,那精确而间歇的发作,那一叠连声的催促,凡有耳神经的人,没有谁不悚然惊魂,一跃而起的。最吓人的,该是深夜空宅,万籁齐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际,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像恐怖电影里那样。旧小说的所谓“催魂铃”,想来也不过如此了。王维的辋川别墅里,要是装了一架电话,他那些静绝清绝的五言绝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电话,真是现代生活的催魂铃。电话线的天网恢恢,无远弗届,只要一线袅袅相牵,株连所及,我们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无已时。古典诗人常爱夸张杜鹃的鸣声与猿啼之类,说得能催人老。于今猿鸟去人日远,倒是格凛凛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把现代人给催老了。
古人鱼雁往返,今人铃声相迫。鱼来雁去,一个回合短则旬月,长则经年,那天地似乎广阔许多。“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那时如果已有电话,一个电话刘十九就来了,结果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样的佳句。至于“断无消息石榴红”,那种天长地久的等待,当然更有诗意。据说阿根延有一位邮差,生就拉丁民族的洒脱不羁,常把一袋袋的邮件倒在海里,多少叮咛与嘱咐,就此付给了鱼虾。后来这家伙自然吃定了官司。我国早有一位殷洪乔,把人家托带的百多封信全投在江中,还祝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这位逍遥殷公,自己不甘随俗浮沉,却任可怜的函书随波浮沉,结果非但逍遥法外,还上了《世说新语》
,成了任诞趣谭。如果他生在现代,就不能这么任他逍遥,因为现代的大城市里,电话机之多,分布之广,就像工业文明派到家家户户去卧底的奸细,催魂的铃声一响,没有人不条件反射地一跃而起,赶快去接,要是不接,它就跟你没了没完,那高亢而密集的声浪,锲而不舍,就像一排排嚣张的惊叹号一样,滔滔向你卷来。我不相信魏晋名士乍闻电话铃声能不心跳。
至少我就不能。我家的电话,像一切深入敌阵患在心腹的奸细,竟装在我家文化中心的书房里,注定我一夕数惊,不
,数十惊。四个女儿全长大了,连“最小偏怜”的一个竟也超过了“边城”里翠翠的年龄。每天晚上,热门的电视节目过后,进入书房,面对书桌,正要开始我的文化活动,她们的男友们(?)也纷纷出动了。我用问号,是表示存疑,因为人数太多,讲的又全是广东话,我凭什么分别来者是男友还是天真的男同学叱?总之我一生没有听过这么多陌生男子的声音。电话就在我背后响起,当然由我推椅跳接,问明来由,便扬声传呼,辗转召来“他”要找的那个女儿。铃声算是镇下去了,继之而起的却是人声的哼哼唧唧,喃喃喋喋。被铃声惊碎了的静谧,一片片又拼了拢来,却夹上这么一股昵昵尔汝,不听不行、听又不清的涓涓细流,再也拼不完整。世界上最令人分心的声音,还是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家人的语声。开会时主席滔滔的报告,演讲时名人侃侃的大言,都可以充耳不闻,别有用心,更勿论公车上渡轮上不相干的人声鼎沸,唯有这家人耳熟的声音,尤其是向着听筒的切切私语、叨叨独白,欲盖弥彰,似抑实扬,却又间歇不定,笑嗔无常,最能乱人心意。你当然不会认真听下去,可是家人的声音,无论是音色和音调,太亲切了,不听也自入耳,待要听时,却轮到那头说话了,这头只剩下了唯唯诺诺。有意无意之间,一通电话,你听到的只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片面之词”,在朦胧的听觉上,有一种半盲的幻觉。
好不容易等到叮咛一声挂回听筒,还我寂静,正待接上断绪,重新投入工作,铃声响处
,第二个电话又来了。四个女儿加上一个太太,每人晚上四五个电话,催魂铃声便不绝于耳。像一个现代的殷洪乔,我成了五个女人的接线生。有时也想回对方一句“她不在”,或者干脆把电话挂断,又怕侵犯了人权,何况还是女权,在一对五票的劣势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绝望之余,不禁悠然怀古,想没有电话的时代,这世界多么单纯,家庭生活又多么安静
,至少房门一关,外面的世界就闯不进来了,哪像现代人的家里,肘边永远伏着这么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那时候,要通消息,写信便是。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星期三有没有空?”“那么,星期四行不行?”这种事情必须当机立断,沉吟不得,否则对方会认为你有意推托。相比之下,书信往还,中间有绿衣人或蓝衣人作为缓冲,又有洪乔之误周末之阻等等的藉口,可以慢慢考虑,转肘的空间宽得多了。书信之来,及门而止,然后便安详地躺在信箱里等你去取,哪像电话来时,登堂入室,直捣你的心脏,真是迅铃不及掩耳。一日廿四小时,除了更残漏断、英文所谓“小小时辰”之外,谁也抗拒不了那催魂铃武断而坚持的命令,无论你正做着什么,都得立刻放下来,向它“交耳”。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是为接天下之贤士,我们呢,是为接电话。谁没有从浴室里气急败坏地裸奔出来,一手提裤,一手去抢听筒呢?岂料一听之下,对方满口日文,竟是错了号码。
电话动口,书信动手,其实写信更见君子之风。我觉得还是老派的书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优雅形象不用说了,就连现代通信所见的邮差、邮筒、邮票、邮戳之类
,也都有情有韵,动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里,书信成了绝佳的作品,进则可以辉照一代文坛,退则可以怡悦二三知已,所以中国人说它是“心声之献酬”,西洋人说它是“最温柔的艺术”。但自电话普及以后,朋友之间要互酬心声,久已勤于动口而懒于动手,眼看这种温柔的艺术已经日渐没落了。其实现代人写的书信,甚至出于名家笔下的,也没有多少够得上“温柔”两字。
也许有人不服,认为现代人虽爱通话,却也未必疏于通信,圣诞新年期间,人满邮局信满邮袋的景象
,便是一大例证。其实这景象并不乐观,因为年底的函件十之八九都不是写信,只是在印好的贺节词下签名而已。通信“现代化”之后,岂但过年过节,就连贺人结婚、生辰、生子、慰人入院、出院、丧亲之类的场合,也都有印好的公式卡片任你“填表”。“听说你离婚了,是吗?不要灰心,再接再厉,下一个一定美满!”总有一天会出售这样的慰问明信片的。所谓“最温柔的艺术”,在电话普及、社交卡片泛滥的美国,是注定要没落的了。
甚至连情书,“最温柔的艺术”里原应最温柔的一种,怕也温柔不起来了。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里说:“情人们只有在不能喁喁私语时才要写信。情书是一种紧急救济。”他没有料到电话愈来愈发达,情人情急的时候是打电话,不是写情书
,即使山长水远,也可以两头相思一线贯通。以前的情人总不免“肠断萧娘一纸书”,若是“玉当缄札何由达”,就更加可怜了。现代的情人只拨那小小的转盘,不再向尺素之上去娓娓倾诉。麦克鲁恒说得好:“消息端从媒介来”,现代情人的口头盟誓,在十孔盘里转来转去,铃声丁零一响,便已消失在虚空里,怎能转出伟大的爱情来呢?电话来得快,消失得也快,不像文字可以永垂后世,向一代代的痴顽去求印证。我想情书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不要提亚伯拉德和哀绿绮思,即使近如徐志摩和郁达夫的多情,恐也难再。
有人会说:“电话难道就一无好处吗?至少即发即至,随问随答,比通信快得多啊!遇到急事,一通电话可以立刻解决,何必劳动邮差摇其鹅步
,延误时机呢?”这我当然承认,可是我也要问,现代生活的节奏调得这么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用电话去救人,匪徒也可以用电话去害人,大家都快了,快,又有什么意义?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在节奏舒缓的年代,一切都那么天长地久,耿耿不灭,爱情如此,一纸痴昧的情书,贴身三年,也是如此。在高速紧张的年代,一切都即生即灭,随荣随枯,爱情和友情,一切的区区与耿耿,都被机器吞进又吐出,成了车载斗量的消耗品了。电话和电视的恢恢天网,使五洲七海千城万邑缩小成一个“地球村”,四十亿兆民都迫到你肘边成了近郊。人类愈“进步”,这大千世界便愈加缩小。英国记者魏克说,孟买人口号称六百万,但是你在孟买的街头行走时,好像那六百万人全在你身边。据说有一天附带电视的电话机也将流行,那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二○○一年:太空放逐记》的作者克拉克曾说:到一九八六年我们就可以跟火星上的朋友通话,可惜时差是三分钟,不能“对答如流”。我的天,“地球村”还不够,竟要去开发“太阳系村”吗?
野心勃勃的科学家认为,有一天我们甚至可能探访太阳以外的太阳。但人类太空之旅的速限是光速,一位太空人从廿五岁便出发去织女星,长征归来,至少是七十七岁了,即使在途中他能因“冻眠”而不老,世上的亲友只怕也半为鬼了。空间的代价是时间”,一点也不错。我是一个太空片迷,但我的心情颇为矛盾。从“二○○一年”到“第三类接触”,一切太空片都那么美丽、恐怖而又寂寞,令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尤其是寂寞,唉,太寂寞了。人类即使能征服星空,也不过是君临沙漠而已。
长空万古,渺渺星辉,让一切都保持点距离和神秘,可望而不可即,不是更有情吗?留一点余地给神话和迷信吧,何必赶得素娥青女都走投无路,“逼神太甚”呢?宁愿我渺小而宇宙伟大,一切的江河不朽,也不愿进步到无远弗届,把宇宙缩小得不成气象。
对无远弗届的电话与关山阻隔的书信,我的选择也是如此。在英文里,叫朋友打个电话来,是“给我一声铃”。催魂铃吗,不必了。不要给我一声铃,给我一封信吧。●
作者:余光中
一百年前发明电话的那人,什么不好姓,偏偏姓“铃”(alexanderbell),真是一大巧合。电话之来,总是从颤颤的一串铃声开始
,那高调,那频率,那精确而间歇的发作,那一叠连声的催促,凡有耳神经的人,没有谁不悚然惊魂,一跃而起的。最吓人的,该是深夜空宅,万籁齐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际,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像恐怖电影里那样。旧小说的所谓“催魂铃”,想来也不过如此了。王维的辋川别墅里,要是装了一架电话,他那些静绝清绝的五言绝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电话,真是现代生活的催魂铃。电话线的天网恢恢,无远弗届,只要一线袅袅相牵,株连所及,我们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无已时。古典诗人常爱夸张杜鹃的鸣声与猿啼之类,说得能催人老。于今猿鸟去人日远,倒是格凛凛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把现代人给催老了。
古人鱼雁往返,今人铃声相迫。鱼来雁去,一个回合短则旬月,长则经年,那天地似乎广阔许多。“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那时如果已有电话,一个电话刘十九就来了,结果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样的佳句。至于“断无消息石榴红”,那种天长地久的等待,当然更有诗意。据说阿根延有一位邮差,生就拉丁民族的洒脱不羁,常把一袋袋的邮件倒在海里,多少叮咛与嘱咐,就此付给了鱼虾。后来这家伙自然吃定了官司。我国早有一位殷洪乔,把人家托带的百多封信全投在江中,还祝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这位逍遥殷公,自己不甘随俗浮沉,却任可怜的函书随波浮沉,结果非但逍遥法外,还上了《世说新语》
,成了任诞趣谭。如果他生在现代,就不能这么任他逍遥,因为现代的大城市里,电话机之多,分布之广,就像工业文明派到家家户户去卧底的奸细,催魂的铃声一响,没有人不条件反射地一跃而起,赶快去接,要是不接,它就跟你没了没完,那高亢而密集的声浪,锲而不舍,就像一排排嚣张的惊叹号一样,滔滔向你卷来。我不相信魏晋名士乍闻电话铃声能不心跳。
至少我就不能。我家的电话,像一切深入敌阵患在心腹的奸细,竟装在我家文化中心的书房里,注定我一夕数惊,不
,数十惊。四个女儿全长大了,连“最小偏怜”的一个竟也超过了“边城”里翠翠的年龄。每天晚上,热门的电视节目过后,进入书房,面对书桌,正要开始我的文化活动,她们的男友们(?)也纷纷出动了。我用问号,是表示存疑,因为人数太多,讲的又全是广东话,我凭什么分别来者是男友还是天真的男同学叱?总之我一生没有听过这么多陌生男子的声音。电话就在我背后响起,当然由我推椅跳接,问明来由,便扬声传呼,辗转召来“他”要找的那个女儿。铃声算是镇下去了,继之而起的却是人声的哼哼唧唧,喃喃喋喋。被铃声惊碎了的静谧,一片片又拼了拢来,却夹上这么一股昵昵尔汝,不听不行、听又不清的涓涓细流,再也拼不完整。世界上最令人分心的声音,还是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家人的语声。开会时主席滔滔的报告,演讲时名人侃侃的大言,都可以充耳不闻,别有用心,更勿论公车上渡轮上不相干的人声鼎沸,唯有这家人耳熟的声音,尤其是向着听筒的切切私语、叨叨独白,欲盖弥彰,似抑实扬,却又间歇不定,笑嗔无常,最能乱人心意。你当然不会认真听下去,可是家人的声音,无论是音色和音调,太亲切了,不听也自入耳,待要听时,却轮到那头说话了,这头只剩下了唯唯诺诺。有意无意之间,一通电话,你听到的只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片面之词”,在朦胧的听觉上,有一种半盲的幻觉。
好不容易等到叮咛一声挂回听筒,还我寂静,正待接上断绪,重新投入工作,铃声响处
,第二个电话又来了。四个女儿加上一个太太,每人晚上四五个电话,催魂铃声便不绝于耳。像一个现代的殷洪乔,我成了五个女人的接线生。有时也想回对方一句“她不在”,或者干脆把电话挂断,又怕侵犯了人权,何况还是女权,在一对五票的劣势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绝望之余,不禁悠然怀古,想没有电话的时代,这世界多么单纯,家庭生活又多么安静
,至少房门一关,外面的世界就闯不进来了,哪像现代人的家里,肘边永远伏着这么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那时候,要通消息,写信便是。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星期三有没有空?”“那么,星期四行不行?”这种事情必须当机立断,沉吟不得,否则对方会认为你有意推托。相比之下,书信往还,中间有绿衣人或蓝衣人作为缓冲,又有洪乔之误周末之阻等等的藉口,可以慢慢考虑,转肘的空间宽得多了。书信之来,及门而止,然后便安详地躺在信箱里等你去取,哪像电话来时,登堂入室,直捣你的心脏,真是迅铃不及掩耳。一日廿四小时,除了更残漏断、英文所谓“小小时辰”之外,谁也抗拒不了那催魂铃武断而坚持的命令,无论你正做着什么,都得立刻放下来,向它“交耳”。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是为接天下之贤士,我们呢,是为接电话。谁没有从浴室里气急败坏地裸奔出来,一手提裤,一手去抢听筒呢?岂料一听之下,对方满口日文,竟是错了号码。
电话动口,书信动手,其实写信更见君子之风。我觉得还是老派的书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优雅形象不用说了,就连现代通信所见的邮差、邮筒、邮票、邮戳之类
,也都有情有韵,动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里,书信成了绝佳的作品,进则可以辉照一代文坛,退则可以怡悦二三知已,所以中国人说它是“心声之献酬”,西洋人说它是“最温柔的艺术”。但自电话普及以后,朋友之间要互酬心声,久已勤于动口而懒于动手,眼看这种温柔的艺术已经日渐没落了。其实现代人写的书信,甚至出于名家笔下的,也没有多少够得上“温柔”两字。
也许有人不服,认为现代人虽爱通话,却也未必疏于通信,圣诞新年期间,人满邮局信满邮袋的景象
,便是一大例证。其实这景象并不乐观,因为年底的函件十之八九都不是写信,只是在印好的贺节词下签名而已。通信“现代化”之后,岂但过年过节,就连贺人结婚、生辰、生子、慰人入院、出院、丧亲之类的场合,也都有印好的公式卡片任你“填表”。“听说你离婚了,是吗?不要灰心,再接再厉,下一个一定美满!”总有一天会出售这样的慰问明信片的。所谓“最温柔的艺术”,在电话普及、社交卡片泛滥的美国,是注定要没落的了。
甚至连情书,“最温柔的艺术”里原应最温柔的一种,怕也温柔不起来了。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里说:“情人们只有在不能喁喁私语时才要写信。情书是一种紧急救济。”他没有料到电话愈来愈发达,情人情急的时候是打电话,不是写情书
,即使山长水远,也可以两头相思一线贯通。以前的情人总不免“肠断萧娘一纸书”,若是“玉当缄札何由达”,就更加可怜了。现代的情人只拨那小小的转盘,不再向尺素之上去娓娓倾诉。麦克鲁恒说得好:“消息端从媒介来”,现代情人的口头盟誓,在十孔盘里转来转去,铃声丁零一响,便已消失在虚空里,怎能转出伟大的爱情来呢?电话来得快,消失得也快,不像文字可以永垂后世,向一代代的痴顽去求印证。我想情书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不要提亚伯拉德和哀绿绮思,即使近如徐志摩和郁达夫的多情,恐也难再。
有人会说:“电话难道就一无好处吗?至少即发即至,随问随答,比通信快得多啊!遇到急事,一通电话可以立刻解决,何必劳动邮差摇其鹅步
,延误时机呢?”这我当然承认,可是我也要问,现代生活的节奏调得这么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用电话去救人,匪徒也可以用电话去害人,大家都快了,快,又有什么意义?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在节奏舒缓的年代,一切都那么天长地久,耿耿不灭,爱情如此,一纸痴昧的情书,贴身三年,也是如此。在高速紧张的年代,一切都即生即灭,随荣随枯,爱情和友情,一切的区区与耿耿,都被机器吞进又吐出,成了车载斗量的消耗品了。电话和电视的恢恢天网,使五洲七海千城万邑缩小成一个“地球村”,四十亿兆民都迫到你肘边成了近郊。人类愈“进步”,这大千世界便愈加缩小。英国记者魏克说,孟买人口号称六百万,但是你在孟买的街头行走时,好像那六百万人全在你身边。据说有一天附带电视的电话机也将流行,那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二○○一年:太空放逐记》的作者克拉克曾说:到一九八六年我们就可以跟火星上的朋友通话,可惜时差是三分钟,不能“对答如流”。我的天,“地球村”还不够,竟要去开发“太阳系村”吗?
野心勃勃的科学家认为,有一天我们甚至可能探访太阳以外的太阳。但人类太空之旅的速限是光速,一位太空人从廿五岁便出发去织女星,长征归来,至少是七十七岁了,即使在途中他能因“冻眠”而不老,世上的亲友只怕也半为鬼了。空间的代价是时间”,一点也不错。我是一个太空片迷,但我的心情颇为矛盾。从“二○○一年”到“第三类接触”,一切太空片都那么美丽、恐怖而又寂寞,令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尤其是寂寞,唉,太寂寞了。人类即使能征服星空,也不过是君临沙漠而已。
长空万古,渺渺星辉,让一切都保持点距离和神秘,可望而不可即,不是更有情吗?留一点余地给神话和迷信吧,何必赶得素娥青女都走投无路,“逼神太甚”呢?宁愿我渺小而宇宙伟大,一切的江河不朽,也不愿进步到无远弗届,把宇宙缩小得不成气象。
对无远弗届的电话与关山阻隔的书信,我的选择也是如此。在英文里,叫朋友打个电话来,是“给我一声铃”。催魂铃吗,不必了。不要给我一声铃,给我一封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