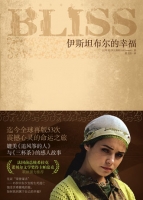言情小说
追风筝的人
《追风筝的人》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
2001年12月
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和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汗,还有我过去那些未曾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金门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飘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
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坐下,想着拉辛汗在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忆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追风筝的人
《追风筝的人》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
2001年12月
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和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汗,还有我过去那些未曾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金门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飘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
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坐下,想着拉辛汗在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忆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追风筝的人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椹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椹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物。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它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条通向两扇锻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尽头则是后院。
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1]Isfaham,伊朗中部城市。[1]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2]Calcutta,印度城市。[2]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
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是“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
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订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镶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纳迪尔国王[1]NadirShah(1883~1933),阿富汗国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杀。[1]在1931年的合影,两年后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枪,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拉辛汗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两人都没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倦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抓着拉辛汗的小指头。
凹壁可通往餐厅,餐厅正中摆着红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绰绰有余。由于爸爸热情好客,确实几乎每隔一周就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用膳。餐厅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色的火焰在里面跳动。
拉开那扇玻璃大滑门,便可走上半圆形的露台;下面是占地两英亩的后院和成排的樱桃树。爸爸和阿里在东边的围墙下辟了个小菜园,种着西红柿、薄荷和胡椒,还有一排从未结实的玉米。哈桑和我总是叫它“病玉米之墙”。
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阴之下便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亲住在里面。
在我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
我在家里住了十八年,但进入阿里和哈桑房间的次数寥寥无几。每当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开了。我穿过那片蔷薇,回到爸爸的广厦去;哈桑则回到他的寒庐,他在那儿出世,在那儿度过一生。我记得它狭小而干净,点着两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屋里两端各摆着一床褥子,一张破旧的赫拉特[1]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1]出产的地毯四边磨损,摆在中间。屋角还有一把三脚凳,一张木头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画画。此外四壁萧然,仅有一幅挂毯,用珠子缀着“Allahuakbar”(真主伟大)的字样。那是爸爸某次去麦什德[2]Mashad,伊朗城市。[2]旅行时给阿里买的。
1964年某个寒冷的冬日,正是在这间小屋,哈桑的母亲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妈妈因为生产时失血过多而谢世,哈桑则在降临人世尚未满七日就失去了母亲。而这种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数阿富汗人看来,简直比死了老娘还要糟糕:她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椹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椹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物。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它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条通向两扇锻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尽头则是后院。
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1]Isfaham,伊朗中部城市。[1]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2]Calcutta,印度城市。[2]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
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是“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
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订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镶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纳迪尔国王[1]NadirShah(1883~1933),阿富汗国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杀。[1]在1931年的合影,两年后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枪,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拉辛汗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两人都没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倦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抓着拉辛汗的小指头。
凹壁可通往餐厅,餐厅正中摆着红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绰绰有余。由于爸爸热情好客,确实几乎每隔一周就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用膳。餐厅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色的火焰在里面跳动。
拉开那扇玻璃大滑门,便可走上半圆形的露台;下面是占地两英亩的后院和成排的樱桃树。爸爸和阿里在东边的围墙下辟了个小菜园,种着西红柿、薄荷和胡椒,还有一排从未结实的玉米。哈桑和我总是叫它“病玉米之墙”。
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阴之下便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亲住在里面。
在我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
我在家里住了十八年,但进入阿里和哈桑房间的次数寥寥无几。每当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开了。我穿过那片蔷薇,回到爸爸的广厦去;哈桑则回到他的寒庐,他在那儿出世,在那儿度过一生。我记得它狭小而干净,点着两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屋里两端各摆着一床褥子,一张破旧的赫拉特[1]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1]出产的地毯四边磨损,摆在中间。屋角还有一把三脚凳,一张木头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画画。此外四壁萧然,仅有一幅挂毯,用珠子缀着“Allahuakbar”(真主伟大)的字样。那是爸爸某次去麦什德[2]Mashad,伊朗城市。[2]旅行时给阿里买的。
1964年某个寒冷的冬日,正是在这间小屋,哈桑的母亲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妈妈因为生产时失血过多而谢世,哈桑则在降临人世尚未满七日就失去了母亲。而这种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数阿富汗人看来,简直比死了老娘还要糟糕:她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