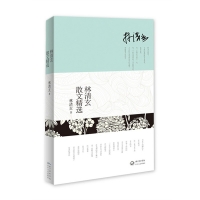文/陳 嵐 這幾年,寫書的人真的越來越多了,但能讓我讀進去的書卻越來越少了。再看看出版行業的報紙,占據着排行榜的書籍無非兩類:一類是被冠予英文名作者、國內市場超常運作的書;一類是美女帥男明星槍手杜撰的書。乍看文壇人才輩出,書市熱熱鬧鬧,然而真正高品味的書籍卻比圖書品種匱乏的計劃經濟年代更難求,陷入了麯高和寡尷尬境地。我看僅從提高全民文化素質來着眼的話,這未必是件好事。 文化的繁榮並不意味着文化的進步。真正的文化進步應該基於主流文化在公衆中的認可度。主流文化的內涵極其深遠,就其作品表現手法而言,要麽宏揚,要麽批判。現在的尷尬是:兩頭都缺。恰恰是“另類”文化成了現象,成了時尚,成了市場,成了尢物。什麽是“另類”?“怪、酷、奇、俗”四個字即可概而括之。明智的讀者也應該能從這四個字當中感受到“另類”文化究竟是什麽樣一種基調。如果這種基調長此以往地占有絶對的受衆群體,這也未必是件好事。 其實,我所說的以批判手法體現主流文化的書籍也不是沒有。比如前些年,批判地域部落群體中人格文化與生活習性之鄙陋的書籍就頗成氣候,因這些書籍大抵格調嚮上,作者大都賦有愛之深、痛之切的之舉,所以受到針砭的地域部落群體,無涉者一笑了之,有涉者大可照書反思,也可爭鳴。這類的書籍再多些,未必不是件好事。 去年初,秦林給我寄來一本他的當時新作,叫《朋友會咬人》。同樣是批判手法,秦林“得罪”了“出門靠朋友”的社會期許,這無疑需要相當的勇氣。我作為該書的讀者之一,就從中找到了好幾個我的朋友的身影,儘管出於某種顧慮,秦林聲言批判的力度有些拘淺,但從該書的入題定位而言,那種“味道”已經出來了。必須承認的是,搞文化批判難度是較大的,它不算冷門,但總是給人帶來沉重。因此批判的客體乃至度的把握,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在這個基礎上能構想出讓人動容的主題,這咱批判就已經成功了一半。我想,像《朋友會咬人》這類的文化批判讀物若能多推出一些,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還是秦林,又給我送“東西”了:這回不是書,是稿子。書名叫《打死不做上海男人》。囑我斧正並作序。一見書名,足知其批判鋒芒,我就和他打趣:“你不做上海男人,沒人逼着你做,你不用死!”你說他回答一句什麽?“有機會我還是想做上海男人的,因為我不會被‘打死’。”妙哉!真是後生可畏!我衹差沒稱他為“智者”了。 和《朋友會咬人》一樣,寫《打死不做上海男人》同樣需要相當的勇氣。這本書洋洋十餘萬言的批判,雖算不上句句珠璣,卻也難覓挖若、嘲諷、漫駡、譏笑和詰難,但這絲毫不會影響文化批判的力度。其中,“關於‘精明’芻議”一篇尤顯個性。作者通過“精”不在“明”處、“精”於算計、“精”於細巧、“門檻精”有多精等四個論點,強有力地支撐了“芻議”的主體,顛覆了多年來根植於人們概念中“上海男人最精明”的社會公論。此外,“一個優勢VS三大弱點”、“舉輕若重的性格標簽”也堪稱重量級批判,文似調侃,又能撓到要命的痛處。這和好比用一張帶菌的砂紙摩挲上海男人的臉的竜應臺的《啊,上海男人》相較,就讓人好接受得多了。讀其文便見拳拳之心,即使發現有過頭之處,也不至於煸着火氣呼啦呼啦往心頭灌了。 如果不生火氣生什麽呢?有則改,無則勉——這句話秦林在書中沒有說到。算是我替他嚮上海男人說了。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是一本文化批判的書。文中鮮見“好話”,這很正常。如果要求這本書像寫八股文那樣,先表揚幾下,再抽幾鞭子。那就不叫文化批判,叫總結報告。況且,作總結報告,嚮來不是搞文化批判的人的風骨。也不是秦林的風骨。 是為序。
上海——這座與北京同稱為中國最大的兩座標志性城市,她但與北京相比,在城市文化背景上卻不在一個檔次:北京是古老的城市;上海是新興的城市。別說和北京比了,即使和她的周邊城市相比,其名望也不及古城蘇州和杭州。當年皇帝詔曰封疆封吏時,江南的地方官員不計其數,生活在“兩江”的老祖宗充其量也就知道在蘇州河“上邦”有一廣出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的小漁村。宋朝時期,小漁村建鎮,隸屬蘇州府管轄。由於此地交通方便,商船廣集,元朝在此設立了行政縣,到明朝時已發展成為國內紡織和手工業的重鎮。清政府在公元1685年設立上海海關,一個國際性大商埠從此發展起來。公元1842年,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清政府送來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這個中國土地上的一塊大肥肉從此以外國殖民地的名義開埠,取名為上海市。 上海開埠之初,由於地理位置的便利,各國的洋人紛紛都選擇這塊風水寶地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國商人到中國經商經出了癮,有很多人幹脆賴着不走,便在上海安傢落戶,生兒育女。一時間,國人怨聲載道,上海土著的女人卻身價猛增,男人沒有做洋人老婆的資本,無奈衹好當洋人幫工、扛活、打雜、跑腿。再後來,周邊十裏八鄉的農民得知在上海可以掙得大洋養傢糊口,便成群結隊地涌入上海,甘打上海當地人的下手。於是,上海男人就自然地介於外地人和洋人之間的“中層”地位。加之中國人生性勤奮、吃苦,上海人當中有一部分人被洋人所相中,便“榮升”管傢、管工、監工、翻譯、轎車夫等職務。外地人屈於生活所迫,不得不甘當上海當地人手下,被剝削、剋扣錢餉之類的事屢屢發生,便形成了外地打工者和上海當地人之間的直接矛盾衝突。隨着時間的推移,外地來滬的人中一部分人成了上海的移民,上海人部落的勢力日漸壯大。“海內外”的矛盾也因此日益加劇、擴散,升級,導致了上海人和外地人水火不相容的局面。上海人(準確地說是上海男人)的德行因此成了人們評論的對象。先是在上海的打工者們在背地裏偷偷的辱駡,後來發展成有志之士(或文人墨客)的關註與公開詬病。 我曾閱讀上海歷史到現在的一些相關資料,發現世人對上海男人的詬病早在清末民初時期就有了。但那時期的詬病似乎僅是針對德行方面的。到了民國三四十年代,隨着衆多憂國憂民的文人墨客親歷上海黑幫勢力的猖獗和一盤散沙似的民心狀態,深為上海的前途而擔憂,紛紛發表檄文,對逢事“關我屁事”的上海人乃至上海男人進行抨擊。建國後一直到現在,上海人的影響力已經遍及全國各地,但衹要上海人所及之處,幾乎無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各種形式的批判,而且人們批判的矛頭絶大部分都是直指上海男人。 時至今日,上海男人在國人當中似乎已經成了一種標識,一種讓上海以外的人茶餘飯後可以隨隨便便編造各種各樣的或素或葷的幽默笑話裏的男主人公的標識。從整個過程看,我覺得有一種跡象頗讓人思量:不管是百餘年前的開埠時期還是百餘年後的國際化大都市,世人對上海這座城市都是贊賞有加的,但一提起這座城市裏的男主人,口氣就變了。變得怎樣了呢?我分析其“變”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先期是從挑剔、嫉妒到開駡;中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批判;後期(現在)是對其劣根“病入膏肓”的嘲諷。無論在文界還是民衆,人們對由“上海男人”簇起的這個“海派帝國”大都是持不屑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