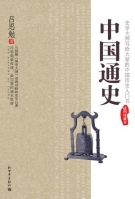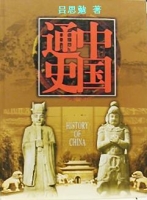吕思勉(1884—1957),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1923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是较早的一部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后又著成《吕著中国通史》两册。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还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书。
吕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其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当时得风气之先,《吕著中国通史》堪称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出版后甚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曾数次重樱可惜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此书的作用和影响很快被独裁、内战和饥饿所掩盖,以致绝版。
本书原上册为文化史,其中叙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学术的历史发展状况、互相关系及特点,范围广博,取精用宏,多独到之见,足资当今学人借鉴;下册为政治史,叙述简明精当,脉络流贯,议论风发,对一般读者熟悉中国历史大有裨益。因此,我们决定将《吕著中国通史》重印出版发行。
为方便读者,我们将此书原来的上下两册合并,按其内容分为上下编,上编称《中国文化史》,下编称《中国政治史》,并将注释形式统一为文中夹注。为保留此书原貌,在重印时,除将繁体竖排本改为简体横排本,以及将因明显排印致错之处予以改正外,其余的一切,如当时的概念、称谓以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部分历史所作的叙述等,均未改动。
1983年,杨宽先生曾主持过“吕氏史学论著编辑组”的工作,并写过一篇“出版说明”,对此书作了很好的评介,现改为本书的“前言”,全文刊出,以期对广大读者研读此书有所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4
吕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其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当时得风气之先,《吕著中国通史》堪称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出版后甚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曾数次重樱可惜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此书的作用和影响很快被独裁、内战和饥饿所掩盖,以致绝版。
本书原上册为文化史,其中叙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学术的历史发展状况、互相关系及特点,范围广博,取精用宏,多独到之见,足资当今学人借鉴;下册为政治史,叙述简明精当,脉络流贯,议论风发,对一般读者熟悉中国历史大有裨益。因此,我们决定将《吕著中国通史》重印出版发行。
为方便读者,我们将此书原来的上下两册合并,按其内容分为上下编,上编称《中国文化史》,下编称《中国政治史》,并将注释形式统一为文中夹注。为保留此书原貌,在重印时,除将繁体竖排本改为简体横排本,以及将因明显排印致错之处予以改正外,其余的一切,如当时的概念、称谓以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部分历史所作的叙述等,均未改动。
1983年,杨宽先生曾主持过“吕氏史学论著编辑组”的工作,并写过一篇“出版说明”,对此书作了很好的评介,现改为本书的“前言”,全文刊出,以期对广大读者研读此书有所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4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
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
作者这部书写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因此书中叙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十分强调汉族对于所谓异族的反抗斗争。这是要请读者注意的。这书最后一章,题为《革命途中的中国》,作者以“大器晚成”这句成语,预祝革命必将成功。同时指出民族前途是光明的,应该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作者果断地说:“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最后引梁任公所译英国文豪拜伦的诗:“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作为全书的总结。作者在这一章中强调当时革命前途的重要问题是“不在对内而在对外”,认为“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
书中有些地方沿用旧的术语,和今天我们通用的术语含义有所不同,例如所说“封建时代”和“封建社会”。“封建”是指分封制,“封建时代”是指春秋以前贵族推行宗法的分封制的阶段,诸如此类,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尚请读者留意。
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杨宽执笔)
一九八三年八月
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
作者这部书写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因此书中叙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十分强调汉族对于所谓异族的反抗斗争。这是要请读者注意的。这书最后一章,题为《革命途中的中国》,作者以“大器晚成”这句成语,预祝革命必将成功。同时指出民族前途是光明的,应该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作者果断地说:“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最后引梁任公所译英国文豪拜伦的诗:“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作为全书的总结。作者在这一章中强调当时革命前途的重要问题是“不在对内而在对外”,认为“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
书中有些地方沿用旧的术语,和今天我们通用的术语含义有所不同,例如所说“封建时代”和“封建社会”。“封建”是指分封制,“封建时代”是指春秋以前贵族推行宗法的分封制的阶段,诸如此类,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尚请读者留意。
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杨宽执笔)
一九八三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