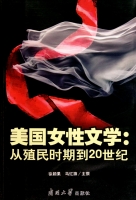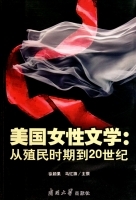我见到了那永恒的本体,
将我的生命充实:
我的眼晴的确看到了天堂
目睹了你所看不见的东西。
——《肉体与灵魂》
很难弄明白安娜·布拉德斯特里特为什么写诗,特别是写下这种散发着美与智慧、并因此至今仍为人们传诵的诗。她的诗是传统的,师承前人但却别具一格,属于她自己。她到美国时还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妇,生活在荒野之中,被大自然和人类的敌意所包围:那原始森林,那无法开垦的土地,以及那桀骜不驯的印地安人。她应命来到这里进行营建、耕种和埋葬。她生了八个孩子,大半生患着慢性玻然而,她却是那个认为女人写作是不务正业——甚至是发疯的时代的第一位美国诗人。
少女时代她在英国故乡的图书馆里读了许多书。她永远忘不了那些她最喜爱的作家:爱德蒙.斯宾塞、乔舒亚。西尔威斯特翻译的杜巴特[1]的作品,特别是弗朗西斯·夸尔斯、菲利浦·锡德尼、迈克尔·德雷顿和汤姆斯·布朗。她读过沃尔特·雷利的《世界史》,罗伯待·伯顿的《悲哀分析》’当然还有《圣经》。她在新世界写下的诗篇,一部分实际上是怀乡感旧之作。她曾为伊丽莎白女皇和锡德尼作过挽诗。但她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动机;努力把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保存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她最令人着迷的品质之一是她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她在一首诗中表达了对不幸生为女人的苦恼:
我憎厌每一张吹毛求疵的簧舌,
说我的手拿针线更加适合,
拿走一支诗人的笔真是大逆不道
他们就这样蔑视女性的智慧:
如果我真写出了好诗,也是白搭
他们会说这是剽窃而来,或是偶然之得。
——《序诗》
诗的语调很有特色。她意志的力量不难理解,布雷兹特里特1612年前后在英国的北安普敦附近出生,十八岁时随父母和她年轻的丈夫、剑桥大学毕业生西蒙移居美国。他们与另外十一户人家同乘“阿百拉”号船渡海。上岸之后与十年前到这里落户的早期移民相遇。据安娜的父亲所说,他们处在一个“令人难过,未曾料及的窘境中。那年的冬季还未到来之前,他们中间便有八人以上死亡。许多活着的人都很虚弱,疾病缠身……”在他们自己度过的第一个冬天里,他“没有桌子,也没有能够用来从事写作的房间,只能坐壁壁炉旁,以膝当桌。”
布拉德斯特里特一家起先在伊普斯威奇安家,后来又到马萨诸塞的北安都沃定居。在这段艰难时期,安娜·布拉德期特里特的信仰既受到了考验,也得到了确立。她一心追求清教徒的共同理想,即:遵循清教徒的先驱对《圣经》所作的苟刻至尊的解释,过着一种严格的基督徒生活以帮助建立起上帝的天国。她对宗教偶尔的怀疑和最终的皈依使她写出了一些最优秀的诗篇,共中以《沉思录》尤为突出。
截止一六四六年,她已经写下了一些长诗,包括辩论四种元素间的相互关系的《四元素》。这是一部冗长无味的作品,仿效西尔威斯特的五步格双行体。其它模仿西尔威斯特翻译的杜巴特的作品,也是根据同样的“四”原则而作:《论人类体质的四种脾性》、《人的四个阶段》、《—年四季》、以及根据雷利的《世界史》所作的《四种君主制》。《人的四个阶段》中的《青春》一诗的确很动人:
许多通宵与无赖、喧闹者、无所事事的人度过
我洗耳恭听所有的秽言脏话:
痛恨那一切想使我聪慧的规劝,
最亲密的朋友便是我的仇敌。
但是对—个生活中充满了意外和新的痛苦与灾难的人来说,这种诗是非常乏味的。她在《一年四季》的结尾对这一点供认不讳:
“我的主题贫乏,脑子不灵/否则你应写出更好的诗句。”
然而她的朋友们并不这样想。她的一个内弟菜弗伦·翰·伍德布里奇,1647年返回英国时瞒着她带回去了她的—些诗稿。这些诗1650年以《美洲新升起的第十个诗神》为标题在英国出版。当安娜·布拉德斯特里特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既担心又高兴,立刻着手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并新增加了一些诗和一首题为《作者致书》的序诗:
你是我的低能生就的先天不足的后代,
出世后在我身边
直到朋友将你夺去,
虽然真挚却欠妥当
将你带到海外公诸于世
使你的衣衫褴褛,从印刷机下滚过
缺点没有减少(却都看得出)……
我把你的脸洗净,却看到更多的不足,
擦去了几点污痕,
依然是处处瑕疵,
拉直你的关节,为的是你能够站稳,
然而你仍象原先那样蹒跚趔趄。
这里所说的孩子指的就是她的诗集,于1678年,也就是她死后的第六年在波士顿刊行问世。
这些诗虽然经过了删改,但仍嫌冗长。她自己的成就表现在她写得较短的一些诗中。一些优秀片段足以能与她同时代的英国佳作相媲美。她并没有创造一种新风格的野心。在《致我亲爱的丈夫》中她写道:
假如二曾等于一那便是我们。
假如丈夫曾被妻子爱戴过,那便是你。
假如曾有妻子从丈夫那儿得到了幸福,
那就与我比吧,妻子们,如果你们能够。
我珍视爱情胜过整矿的金子
或者所有的东方财富。
这都是一些传统的溢美之辞,然而却有着毋庸置疑的诚恳和直率。另一首诗写的是她的孩子们:
我有八只小鸟孵在一个窝,
四只雄,
四只雌,
我呕心沥血将它们喂养大,
没有偷一分懒,省一分钱,
直到最后他们都羽毛丰满:
飞上大树学会了歌唱。
老大展翅飞向了远方离我而去,
我随后送去哀伤的啁啾,
直到他生还,或者我死别……
这首诗的重心由家常事转向世界,表现了她精湛的艺术手法。这些短诗都是有感而发,带着一种几乎是自白式的力量。它们不是练笔之作,虽然节奏平平,但其中的直率坦然却非常真实。
她的信仰经过多次考验,其中最严峻的一次是1666年发生的火灾,大火烧掉了她家的房屋和有藏书八百册的书房。她在为孩子们写的一本散文体书中说:
“多少次撒旦使我对《圣经》的真实性发生了质疑。”火灾之后她竭力想消除这种质疑:
我突然惊起,的确看见那火光,
我的心对着上帝呼唤
给我解除苦恼的力量吧
莫使我孤立无援。
那么,快出来看看
那大火将我的房屋烧光。
当我不再能够看见,
我便感谢那赐予者与收取者的名字,
是它将我的家业化成了灰烬;
事情便是这样,这样很公平合理
这是他自己的财富:不属于我;
我根本不须埋怨。
接着她怀着强烈的忏悔之情详细描写了对一个虔诚的清教徒来说过于热衷的已失去的乐趣:
此处本是箱柜,彼处本是壁橱
那里曾是我最好的贮室,
此刻一切都湮灭烟尘,
从我眼前永远消失。
不会再有宾客相聚,
亦不会在桌上举觞投箸。
在最后一行诗里她宣布她的损失并非损失,
“我的希望和财富存放在天国里”。但诗中压在心底的苦恼却否定了这个声明。这首诗表现的是对意志的考验。后来写的《宗教沉思录》也是这个内容,诗的标题表明了诗的主题:
《发烧的狂热》、《另一次剧烈的痉挛》、《为丈夫的烧伤复愈而作——1666年6月,等等。
有的诗写得份量很轻,但是在形式的范围内,即使使用的是传统的赞美诗形式,也燃烧着一股诚挚的火焰:
我寻找我灵魂所爱的他,
含着眼泪我认真地寻访;
他从天上侧耳倾听,
我的寻访与呼号并未徒劳。
他将我饥饿的灵魂中装满了善,
把我的眼泪收入了他的钵罐,
我的伤口在他的血液里浸洗
于是我的疑惧便一扫而光。
这是一种诚挚的决心与意志,而不是一种诚挚的廉价信仰。这首诗把这—点表现得更加强烈。
她的怀疑在《沉思录》中最终消除了,这部作品达到了她艺术技巧和感情的高峰。在新英格兰的一次散步激发了她的一首长长的冥想诗的灵感。在这首诗中,她将大自然的循环与人生的短暂比较,从而使她对人生的目的进行反省:
当我仰望着黎明的天空,
望着大地(虽然衰老)但仍覆盖着绿色,
石头树木,感觉不到时光,
也不知道什么是年老和爬上额头的皱纹;
每当冬天到来,绿色便消褪,
每当春天回还,大地就更加生气勃勃:
然而人将衰老、死亡,留在把他埋葬的地方。
她在最后一首诗中与燃烧的太阳、暴风雨、饿狼以及其它人世间的危险告别,并且为来世的安息做了一次热情的祈祷:
啊,
我多么盼望休息
在赞美声中高高地升起,
身体将在寂静中沉睡,
眼睛也不再流泪哭泣.....
上帝要我为那天做好准备:
那么来吧,
最亲爱的新郎,来吧。
布拉德斯特里特1672年去世,享年六十岁。她的儿子曾经回忆过她与人世告别时的情景:
“她死的时候患有结核病,瘦得皮包骨头。由于她患有粘膜炎,手臂上也排过脓,给她换过绷带的一个女人说,她从未见过那样的手臂。我最亲爱的母亲说,是的,不过这只手臂将会是一只圣洁的手臂。”
将我的生命充实:
我的眼晴的确看到了天堂
目睹了你所看不见的东西。
——《肉体与灵魂》
很难弄明白安娜·布拉德斯特里特为什么写诗,特别是写下这种散发着美与智慧、并因此至今仍为人们传诵的诗。她的诗是传统的,师承前人但却别具一格,属于她自己。她到美国时还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妇,生活在荒野之中,被大自然和人类的敌意所包围:那原始森林,那无法开垦的土地,以及那桀骜不驯的印地安人。她应命来到这里进行营建、耕种和埋葬。她生了八个孩子,大半生患着慢性玻然而,她却是那个认为女人写作是不务正业——甚至是发疯的时代的第一位美国诗人。
少女时代她在英国故乡的图书馆里读了许多书。她永远忘不了那些她最喜爱的作家:爱德蒙.斯宾塞、乔舒亚。西尔威斯特翻译的杜巴特[1]的作品,特别是弗朗西斯·夸尔斯、菲利浦·锡德尼、迈克尔·德雷顿和汤姆斯·布朗。她读过沃尔特·雷利的《世界史》,罗伯待·伯顿的《悲哀分析》’当然还有《圣经》。她在新世界写下的诗篇,一部分实际上是怀乡感旧之作。她曾为伊丽莎白女皇和锡德尼作过挽诗。但她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动机;努力把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保存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她最令人着迷的品质之一是她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她在一首诗中表达了对不幸生为女人的苦恼:
我憎厌每一张吹毛求疵的簧舌,
说我的手拿针线更加适合,
拿走一支诗人的笔真是大逆不道
他们就这样蔑视女性的智慧:
如果我真写出了好诗,也是白搭
他们会说这是剽窃而来,或是偶然之得。
——《序诗》
诗的语调很有特色。她意志的力量不难理解,布雷兹特里特1612年前后在英国的北安普敦附近出生,十八岁时随父母和她年轻的丈夫、剑桥大学毕业生西蒙移居美国。他们与另外十一户人家同乘“阿百拉”号船渡海。上岸之后与十年前到这里落户的早期移民相遇。据安娜的父亲所说,他们处在一个“令人难过,未曾料及的窘境中。那年的冬季还未到来之前,他们中间便有八人以上死亡。许多活着的人都很虚弱,疾病缠身……”在他们自己度过的第一个冬天里,他“没有桌子,也没有能够用来从事写作的房间,只能坐壁壁炉旁,以膝当桌。”
布拉德斯特里特一家起先在伊普斯威奇安家,后来又到马萨诸塞的北安都沃定居。在这段艰难时期,安娜·布拉德期特里特的信仰既受到了考验,也得到了确立。她一心追求清教徒的共同理想,即:遵循清教徒的先驱对《圣经》所作的苟刻至尊的解释,过着一种严格的基督徒生活以帮助建立起上帝的天国。她对宗教偶尔的怀疑和最终的皈依使她写出了一些最优秀的诗篇,共中以《沉思录》尤为突出。
截止一六四六年,她已经写下了一些长诗,包括辩论四种元素间的相互关系的《四元素》。这是一部冗长无味的作品,仿效西尔威斯特的五步格双行体。其它模仿西尔威斯特翻译的杜巴特的作品,也是根据同样的“四”原则而作:《论人类体质的四种脾性》、《人的四个阶段》、《—年四季》、以及根据雷利的《世界史》所作的《四种君主制》。《人的四个阶段》中的《青春》一诗的确很动人:
许多通宵与无赖、喧闹者、无所事事的人度过
我洗耳恭听所有的秽言脏话:
痛恨那一切想使我聪慧的规劝,
最亲密的朋友便是我的仇敌。
但是对—个生活中充满了意外和新的痛苦与灾难的人来说,这种诗是非常乏味的。她在《一年四季》的结尾对这一点供认不讳:
“我的主题贫乏,脑子不灵/否则你应写出更好的诗句。”
然而她的朋友们并不这样想。她的一个内弟菜弗伦·翰·伍德布里奇,1647年返回英国时瞒着她带回去了她的—些诗稿。这些诗1650年以《美洲新升起的第十个诗神》为标题在英国出版。当安娜·布拉德斯特里特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既担心又高兴,立刻着手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并新增加了一些诗和一首题为《作者致书》的序诗:
你是我的低能生就的先天不足的后代,
出世后在我身边
直到朋友将你夺去,
虽然真挚却欠妥当
将你带到海外公诸于世
使你的衣衫褴褛,从印刷机下滚过
缺点没有减少(却都看得出)……
我把你的脸洗净,却看到更多的不足,
擦去了几点污痕,
依然是处处瑕疵,
拉直你的关节,为的是你能够站稳,
然而你仍象原先那样蹒跚趔趄。
这里所说的孩子指的就是她的诗集,于1678年,也就是她死后的第六年在波士顿刊行问世。
这些诗虽然经过了删改,但仍嫌冗长。她自己的成就表现在她写得较短的一些诗中。一些优秀片段足以能与她同时代的英国佳作相媲美。她并没有创造一种新风格的野心。在《致我亲爱的丈夫》中她写道:
假如二曾等于一那便是我们。
假如丈夫曾被妻子爱戴过,那便是你。
假如曾有妻子从丈夫那儿得到了幸福,
那就与我比吧,妻子们,如果你们能够。
我珍视爱情胜过整矿的金子
或者所有的东方财富。
这都是一些传统的溢美之辞,然而却有着毋庸置疑的诚恳和直率。另一首诗写的是她的孩子们:
我有八只小鸟孵在一个窝,
四只雄,
四只雌,
我呕心沥血将它们喂养大,
没有偷一分懒,省一分钱,
直到最后他们都羽毛丰满:
飞上大树学会了歌唱。
老大展翅飞向了远方离我而去,
我随后送去哀伤的啁啾,
直到他生还,或者我死别……
这首诗的重心由家常事转向世界,表现了她精湛的艺术手法。这些短诗都是有感而发,带着一种几乎是自白式的力量。它们不是练笔之作,虽然节奏平平,但其中的直率坦然却非常真实。
她的信仰经过多次考验,其中最严峻的一次是1666年发生的火灾,大火烧掉了她家的房屋和有藏书八百册的书房。她在为孩子们写的一本散文体书中说:
“多少次撒旦使我对《圣经》的真实性发生了质疑。”火灾之后她竭力想消除这种质疑:
我突然惊起,的确看见那火光,
我的心对着上帝呼唤
给我解除苦恼的力量吧
莫使我孤立无援。
那么,快出来看看
那大火将我的房屋烧光。
当我不再能够看见,
我便感谢那赐予者与收取者的名字,
是它将我的家业化成了灰烬;
事情便是这样,这样很公平合理
这是他自己的财富:不属于我;
我根本不须埋怨。
接着她怀着强烈的忏悔之情详细描写了对一个虔诚的清教徒来说过于热衷的已失去的乐趣:
此处本是箱柜,彼处本是壁橱
那里曾是我最好的贮室,
此刻一切都湮灭烟尘,
从我眼前永远消失。
不会再有宾客相聚,
亦不会在桌上举觞投箸。
在最后一行诗里她宣布她的损失并非损失,
“我的希望和财富存放在天国里”。但诗中压在心底的苦恼却否定了这个声明。这首诗表现的是对意志的考验。后来写的《宗教沉思录》也是这个内容,诗的标题表明了诗的主题:
《发烧的狂热》、《另一次剧烈的痉挛》、《为丈夫的烧伤复愈而作——1666年6月,等等。
有的诗写得份量很轻,但是在形式的范围内,即使使用的是传统的赞美诗形式,也燃烧着一股诚挚的火焰:
我寻找我灵魂所爱的他,
含着眼泪我认真地寻访;
他从天上侧耳倾听,
我的寻访与呼号并未徒劳。
他将我饥饿的灵魂中装满了善,
把我的眼泪收入了他的钵罐,
我的伤口在他的血液里浸洗
于是我的疑惧便一扫而光。
这是一种诚挚的决心与意志,而不是一种诚挚的廉价信仰。这首诗把这—点表现得更加强烈。
她的怀疑在《沉思录》中最终消除了,这部作品达到了她艺术技巧和感情的高峰。在新英格兰的一次散步激发了她的一首长长的冥想诗的灵感。在这首诗中,她将大自然的循环与人生的短暂比较,从而使她对人生的目的进行反省:
当我仰望着黎明的天空,
望着大地(虽然衰老)但仍覆盖着绿色,
石头树木,感觉不到时光,
也不知道什么是年老和爬上额头的皱纹;
每当冬天到来,绿色便消褪,
每当春天回还,大地就更加生气勃勃:
然而人将衰老、死亡,留在把他埋葬的地方。
她在最后一首诗中与燃烧的太阳、暴风雨、饿狼以及其它人世间的危险告别,并且为来世的安息做了一次热情的祈祷:
啊,
我多么盼望休息
在赞美声中高高地升起,
身体将在寂静中沉睡,
眼睛也不再流泪哭泣.....
上帝要我为那天做好准备:
那么来吧,
最亲爱的新郎,来吧。
布拉德斯特里特1672年去世,享年六十岁。她的儿子曾经回忆过她与人世告别时的情景:
“她死的时候患有结核病,瘦得皮包骨头。由于她患有粘膜炎,手臂上也排过脓,给她换过绷带的一个女人说,她从未见过那样的手臂。我最亲爱的母亲说,是的,不过这只手臂将会是一只圣洁的手臂。”
上帝,把煤炭烧红吧:你的爱在我身上燃烧
——《冥想之一》
爱德华·泰勒的作品中有一个奇怪的矛盾:他那感情充沛的诗行竞出自一个清教徒传道士的笔下。然而更使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他虽然曾打定主意死后不发表自己的作品,但却把它们仔细装订起来,交给了一个可靠的入——他的孙子,耶鲁学院的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斯泰尔斯将这些手稿传给了泰勒的曾孙,并由他存在了耶鲁学院的图书馆,直到1937年才为人们发现。尽管泰勒曾叮嘱他的继承人永远不要发表这些诗,但在1939年已有数首见报,其它的诗大多数到1960年才问世。就这样,一位殖民时期的杰出诗人在他逝世两个世纪之后被人们发现了。
泰勒的作品比较粗糙,闪烁着尚未成形的光芒,即使是那些最深思熟虑的诗也很令人吃惊。然而这些诗创造性地把清教徒的思想与富有激情的想象力调合在了一起。如果说泰勒是英国玄学派诗人两代人之后的一位玄学派诗人的话,他除了在技巧上富于独创外,还有其它美德。
他的“朴素风格”是为布道而准备的。在泰勒书房里发现的对于《圣经》的十二条清教徒式的评论来看,他对《圣经》的解释用的是一种寓言式或象征性的方法。他的诗以这些解释为依据,从感觉细节(一个昆虫,一个《索罗门之歌》中的片断)出发,使这种解释能够有一种高超的连贯性,通过沉思反省发现其中的隐义,发现神圣的典范的存在:
我粉碎了的幻想悄然离去
(智慧欺骗了伊甸园)
在上帝园中看见一棵金树。
它的心极其神圣,它的皮是黄金
它那壮丽的肢体,果实累累的枝干和圣人一样坚强
圣人和明亮的天使们密匝匝地高挂其上。
《沉思二十九·约翰,20章,17节》
爱德华·泰勒生于英国的莱斯特郡。二十六岁那年移居到马萨诸塞州。他在英国曾被赶出了学校,不准任教,并不准在牛律或剑桥入学,如果他继续传送或者参加新教的礼拜,他就会有锒铛入狱的危险。
作为一个教师,泰勒的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莱文的底子都相当厚实。毫无疑问,他在课堂上曾用乔治·赫伯特的诗作为写诗的范文。他自己的诗在形式和用词上往往有赫伯特的味道。其他的玄学派诗人对他也有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亨利·沃恩、汤姆斯·特拉赫恩和里察德·克拉肖。与安娜·布雷兹特里特一样,他对西尔威斯特所译的杜巴特和弗朗西斯·夸尔斯的作品都很喜爱。
1668乍他离开英国前往马萨诸塞殖民地,与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大法官的塞缪尔·休厄尔一道在哈佛做研究生。从休厄尔的《日记》中我们知道了那个时期的许多人和事。泰勒原打算毕业后留在哈佛,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到韦斯特菲尔德的一个边疆小镇里做了牧师,并且从此以牧师职业度过了余生。
这个乡镇在波士顿以西的一百多哩处。泰勒曾在一封信中写到:“这些最遥远的沼泽地,除了乡村气息外,一无所有。”他既是牧师,又是镇上的医生,结过两次婚,生了一大堆孩子,但全部都先他死去。
泰勒是一个坚定的加尔文派教徒,相信有一个全能的上帝,选定某些灵魂可以得救。这种得救可以通过毫无保留、毫不动摇的信仰实现,而不是通过善行。地狱的确存在,等待着那些末被选中的人。休厄尔记载过泰勒的一次波土顿之行。在那里作了一次“可以在保罗的十字架前所作的”说教。泰勒对信仰坚定不移。他的忠诚堪称楷模。他很了解所在教堂的教义和历史,写下了《基督教韵律史》、关于化身的十四次说教以及《诗集》。他大约每隔六个星期便以诗的形式写一次沉思录作为他的一部分精神准备。这些诗有二百一十七首之多,以《赴主的晚餐之前的预备性冥想》和《就职日宣道的感想》为题用六行体写成,占据了他全部诗歌的很大一部分。有些诗以日常生活为题:《记一个捕蝇的蜘蛛》、《记一只冻僵的小蜜蜂》、《论婚姻,
以及孩儿之死》。这些诗一律包含着一个道德寓意。有一组诗特意写给一些有名的新英格兰人。有一首长诗,题为《上帝的决心感动了他的选民》,前面有写得很好的序言,渗透着他坚定的加尔文教思想。
这位诗人最高超的技巧是,他能够说出惊人之语,使读者突然看到天堂的景象,通过上帝创造的世界看到与上帝结为一体的景象。虽然诗的粗糙有时难以入耳,但这是我们在爱米勃·狄更生的诗中所见到的那种租糙。如在《记一只冻僵的小蜜蜂》中,当泰勒用普通的形象来表现神秘感时,就能特别感觉到这一点:
她的小脚趾,小指尖
在他的呼吸中麻木
她伸出四肢向着太阳
渴望那火团温暖她的四肢,
她的太阳穴上照射着阳光,
脉管在搏动,脑袋在疼痛
舒展了她纤小的身体,
抚摸着她天鹅绒般的头颅……
泰勒是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家。一如爱米莉·狄更生,他善于使用意外的词,使我们对这些词的恰到好处感到惊讶。小蜜蜂把“脚趾”移到太阳穴上,仿佛“她的小脑壳中是一卷精炼简明的格言”,仿佛“她那天鹅绒的头盔/具有炮塔式的理性”。全诗以有力的双行体结束:“那里我所有的笙管一起鸣响/高奏一曲神圣的赞瞅。”
这种惊讶有时在巧妙发展起来的诗歌形式中本身就有。比如在《记一只捕蝇的蜘蛛》中:
而这愚蠢的苍蝇,
腿被羁绊
你急忙抓住它的喉管
从它的脑后
把它咬死。
最后—行诗是摹拟式的,与行动一样迅速而坚决。有时这种惊讶得自对诗行末尾的戏剧性处理和对句法的仔细安排。泰勒在《教友之乐》中写道;“在升华的天国里,我向尘世/垂下一只耳朵……”。在《致细雨带来的灵魂》中他问道:
我是否应成为一个
闪着野火的铁匠铺
那里我沉闷的精神在铁锤之下
是否会欢腾跳跃?
当铁锤在铁砧上挥动
火球的火花向四方飞舞。
《预备沉思录》既表现了泰勒独特的感染力,也暴露了他在艺术上的局限性。这些定性的沉思练习有时强烈得晦涩,有时又如此深奥,甚至古怪地提供了过分夸张的隐喻和比喻。泰勒的想象力所具有的美感通过装饰了的圣坛、香料、珠宝、香水这些暗示罗马天主教仪式的东西表现了出来。但是对泰勒来说,这些东西用于天上所有,非人间所有。它们是奖赏品:
上帝,但愿我在那个金色的城里,
碧玉当墙,一切都被装饰,流水潺潺,
铺着宝石,大门是透明晶莹的珍珠
街道是赤金,宛如透明的玻璃
我沉闷的灵魂,也许会激动地看见
着迷了的圣人和天使是如何地兴高采烈。
其中的用词也许夸张过度,但与班扬离得不远。另有一个例子:
当这只被送进
柳条笼子,(我们的肉体),啼啭歌唱的,
天堂之鸟啄食了这禁果:就这样
它抛弃了自己的食物,失去了金色的日子,
它坠入天国饥荒的痛苦:
再得不到—丁点食物。
呜呼!呜呼!可怜的鸟,你怎么办?
这些形象虽然很丰富,但部分取自简朴的生活,部分取自《圣经》,遣词造句总的说来很平常。把诗提高一步的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词和形象“抛弃”,“天国的饥荒”’“金色的年华”。日常的隐喻又得以升华了:
你那银色的天空是我的啤酒碗,
我发现上帝要将它盛满。
当泰勒不从身旁的生活中寻找形象时,他便使用起新教传统中的词句和装饰来。他带着特有的热情用《紫罗门之歌》中的《圣经》语言将基督和上帝的选民神秘地结合起来:
我不该嗅你的甜美吗,呵,沙伦玫瑰?
我不该用眼睛向你的美致意?为什么?
你甜蜜的叶子,那美妙的芳香会否关闭?
因我的目光使她们羞怯?
哀哉!为此我的叹息将成为真正的叹息
同样为此奉献在哀愁的圣坛上。
对爱德华·泰勒而言,《圣经》、赫伯特、克拉肖、他对《圣经》的评论,——这些便是他日常生活的内容和语言。最终把这些充满了感性的幻想与这位站在上帝面前衷心尽职的清教徒牧师调和在一起是没有困难的。即使最不调和的隐喻在泰勒那些派生出来的、但却是明白无误的诗中也有一股迷人的恰当感。在《上帝的决心感动了他的选民》的序言中他宣布:
是谁为它铺上一层华盖: 或织好垂帘?
是谁在这滚球场中把太阳滚转?
——《冥想之一》
爱德华·泰勒的作品中有一个奇怪的矛盾:他那感情充沛的诗行竞出自一个清教徒传道士的笔下。然而更使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他虽然曾打定主意死后不发表自己的作品,但却把它们仔细装订起来,交给了一个可靠的入——他的孙子,耶鲁学院的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斯泰尔斯将这些手稿传给了泰勒的曾孙,并由他存在了耶鲁学院的图书馆,直到1937年才为人们发现。尽管泰勒曾叮嘱他的继承人永远不要发表这些诗,但在1939年已有数首见报,其它的诗大多数到1960年才问世。就这样,一位殖民时期的杰出诗人在他逝世两个世纪之后被人们发现了。
泰勒的作品比较粗糙,闪烁着尚未成形的光芒,即使是那些最深思熟虑的诗也很令人吃惊。然而这些诗创造性地把清教徒的思想与富有激情的想象力调合在了一起。如果说泰勒是英国玄学派诗人两代人之后的一位玄学派诗人的话,他除了在技巧上富于独创外,还有其它美德。
他的“朴素风格”是为布道而准备的。在泰勒书房里发现的对于《圣经》的十二条清教徒式的评论来看,他对《圣经》的解释用的是一种寓言式或象征性的方法。他的诗以这些解释为依据,从感觉细节(一个昆虫,一个《索罗门之歌》中的片断)出发,使这种解释能够有一种高超的连贯性,通过沉思反省发现其中的隐义,发现神圣的典范的存在:
我粉碎了的幻想悄然离去
(智慧欺骗了伊甸园)
在上帝园中看见一棵金树。
它的心极其神圣,它的皮是黄金
它那壮丽的肢体,果实累累的枝干和圣人一样坚强
圣人和明亮的天使们密匝匝地高挂其上。
《沉思二十九·约翰,20章,17节》
爱德华·泰勒生于英国的莱斯特郡。二十六岁那年移居到马萨诸塞州。他在英国曾被赶出了学校,不准任教,并不准在牛律或剑桥入学,如果他继续传送或者参加新教的礼拜,他就会有锒铛入狱的危险。
作为一个教师,泰勒的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莱文的底子都相当厚实。毫无疑问,他在课堂上曾用乔治·赫伯特的诗作为写诗的范文。他自己的诗在形式和用词上往往有赫伯特的味道。其他的玄学派诗人对他也有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亨利·沃恩、汤姆斯·特拉赫恩和里察德·克拉肖。与安娜·布雷兹特里特一样,他对西尔威斯特所译的杜巴特和弗朗西斯·夸尔斯的作品都很喜爱。
1668乍他离开英国前往马萨诸塞殖民地,与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大法官的塞缪尔·休厄尔一道在哈佛做研究生。从休厄尔的《日记》中我们知道了那个时期的许多人和事。泰勒原打算毕业后留在哈佛,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到韦斯特菲尔德的一个边疆小镇里做了牧师,并且从此以牧师职业度过了余生。
这个乡镇在波士顿以西的一百多哩处。泰勒曾在一封信中写到:“这些最遥远的沼泽地,除了乡村气息外,一无所有。”他既是牧师,又是镇上的医生,结过两次婚,生了一大堆孩子,但全部都先他死去。
泰勒是一个坚定的加尔文派教徒,相信有一个全能的上帝,选定某些灵魂可以得救。这种得救可以通过毫无保留、毫不动摇的信仰实现,而不是通过善行。地狱的确存在,等待着那些末被选中的人。休厄尔记载过泰勒的一次波土顿之行。在那里作了一次“可以在保罗的十字架前所作的”说教。泰勒对信仰坚定不移。他的忠诚堪称楷模。他很了解所在教堂的教义和历史,写下了《基督教韵律史》、关于化身的十四次说教以及《诗集》。他大约每隔六个星期便以诗的形式写一次沉思录作为他的一部分精神准备。这些诗有二百一十七首之多,以《赴主的晚餐之前的预备性冥想》和《就职日宣道的感想》为题用六行体写成,占据了他全部诗歌的很大一部分。有些诗以日常生活为题:《记一个捕蝇的蜘蛛》、《记一只冻僵的小蜜蜂》、《论婚姻,
以及孩儿之死》。这些诗一律包含着一个道德寓意。有一组诗特意写给一些有名的新英格兰人。有一首长诗,题为《上帝的决心感动了他的选民》,前面有写得很好的序言,渗透着他坚定的加尔文教思想。
这位诗人最高超的技巧是,他能够说出惊人之语,使读者突然看到天堂的景象,通过上帝创造的世界看到与上帝结为一体的景象。虽然诗的粗糙有时难以入耳,但这是我们在爱米勃·狄更生的诗中所见到的那种租糙。如在《记一只冻僵的小蜜蜂》中,当泰勒用普通的形象来表现神秘感时,就能特别感觉到这一点:
她的小脚趾,小指尖
在他的呼吸中麻木
她伸出四肢向着太阳
渴望那火团温暖她的四肢,
她的太阳穴上照射着阳光,
脉管在搏动,脑袋在疼痛
舒展了她纤小的身体,
抚摸着她天鹅绒般的头颅……
泰勒是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家。一如爱米莉·狄更生,他善于使用意外的词,使我们对这些词的恰到好处感到惊讶。小蜜蜂把“脚趾”移到太阳穴上,仿佛“她的小脑壳中是一卷精炼简明的格言”,仿佛“她那天鹅绒的头盔/具有炮塔式的理性”。全诗以有力的双行体结束:“那里我所有的笙管一起鸣响/高奏一曲神圣的赞瞅。”
这种惊讶有时在巧妙发展起来的诗歌形式中本身就有。比如在《记一只捕蝇的蜘蛛》中:
而这愚蠢的苍蝇,
腿被羁绊
你急忙抓住它的喉管
从它的脑后
把它咬死。
最后—行诗是摹拟式的,与行动一样迅速而坚决。有时这种惊讶得自对诗行末尾的戏剧性处理和对句法的仔细安排。泰勒在《教友之乐》中写道;“在升华的天国里,我向尘世/垂下一只耳朵……”。在《致细雨带来的灵魂》中他问道:
我是否应成为一个
闪着野火的铁匠铺
那里我沉闷的精神在铁锤之下
是否会欢腾跳跃?
当铁锤在铁砧上挥动
火球的火花向四方飞舞。
《预备沉思录》既表现了泰勒独特的感染力,也暴露了他在艺术上的局限性。这些定性的沉思练习有时强烈得晦涩,有时又如此深奥,甚至古怪地提供了过分夸张的隐喻和比喻。泰勒的想象力所具有的美感通过装饰了的圣坛、香料、珠宝、香水这些暗示罗马天主教仪式的东西表现了出来。但是对泰勒来说,这些东西用于天上所有,非人间所有。它们是奖赏品:
上帝,但愿我在那个金色的城里,
碧玉当墙,一切都被装饰,流水潺潺,
铺着宝石,大门是透明晶莹的珍珠
街道是赤金,宛如透明的玻璃
我沉闷的灵魂,也许会激动地看见
着迷了的圣人和天使是如何地兴高采烈。
其中的用词也许夸张过度,但与班扬离得不远。另有一个例子:
当这只被送进
柳条笼子,(我们的肉体),啼啭歌唱的,
天堂之鸟啄食了这禁果:就这样
它抛弃了自己的食物,失去了金色的日子,
它坠入天国饥荒的痛苦:
再得不到—丁点食物。
呜呼!呜呼!可怜的鸟,你怎么办?
这些形象虽然很丰富,但部分取自简朴的生活,部分取自《圣经》,遣词造句总的说来很平常。把诗提高一步的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词和形象“抛弃”,“天国的饥荒”’“金色的年华”。日常的隐喻又得以升华了:
你那银色的天空是我的啤酒碗,
我发现上帝要将它盛满。
当泰勒不从身旁的生活中寻找形象时,他便使用起新教传统中的词句和装饰来。他带着特有的热情用《紫罗门之歌》中的《圣经》语言将基督和上帝的选民神秘地结合起来:
我不该嗅你的甜美吗,呵,沙伦玫瑰?
我不该用眼睛向你的美致意?为什么?
你甜蜜的叶子,那美妙的芳香会否关闭?
因我的目光使她们羞怯?
哀哉!为此我的叹息将成为真正的叹息
同样为此奉献在哀愁的圣坛上。
对爱德华·泰勒而言,《圣经》、赫伯特、克拉肖、他对《圣经》的评论,——这些便是他日常生活的内容和语言。最终把这些充满了感性的幻想与这位站在上帝面前衷心尽职的清教徒牧师调和在一起是没有困难的。即使最不调和的隐喻在泰勒那些派生出来的、但却是明白无误的诗中也有一股迷人的恰当感。在《上帝的决心感动了他的选民》的序言中他宣布:
是谁为它铺上一层华盖: 或织好垂帘?
是谁在这滚球场中把太阳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