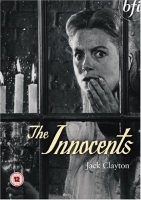声画联姻
周黎明
2006年4月24日,星期一。纽约林肯中心的艾弗瑞·费雪大厅像往常一样挤满了音乐爱好者,但观众比平时的古典乐迷更加年轻。当晚的节目主持人是美国影坛的两大泰斗:马丁·斯科西斯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是谁的演出能够让这两位大导演联袂登场?黑泽明的《梦》曾由斯皮尔伯格监制、斯科西斯参演,因为黑泽明是他俩都非常敬重的前辈;但平时,除了奥斯卡等业内高端活动,很难想像他们两人出席同一个为他人捧场的场合。这次让他们同时登台的,是当今美国电影界的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
威廉斯是斯皮尔伯格的御用配乐家,被很多人视为影史上最成功的电影配乐家,他的崇高地位光从45次奥斯卡提名、5次得奖的记录便可窥见一斑。这场音乐会的前半场,威廉斯率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了伯纳德·赫曼的电影音乐。赫曼是希区柯克的御用配乐家,光是那段《惊魂记》中浴室杀人的锯齿式段落就足以让他流芳百世,何况他还配了《公民凯恩》、《出租车司机》等多部不朽杰作。
音乐会的下半场是威廉斯自己的作品。斯皮尔伯格上场,放映了一段四分钟的《圣战奇兵》追杀戏,但不配音乐。画面虽然精彩绝伦,但略显冗长。然后,斯皮尔伯格把这段戏重新放了一遍,但这次由威廉斯现场演奏他创作的配乐,顿时,画面如虎添翼,气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电影音乐的重要性,没有比这个例子诠释得更清楚的了。如果你不信,只要把电视的音响关闭,尝试一下你最迷恋的电影片断,看看效果打了多少折扣。
很多人喜欢看电影,也喜欢听音乐;但当音乐和画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多数人却常常熟视无睹,好像这些画面是带着音乐一起诞生的。
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忽视电影音乐的影迷。正因如此,我深感展凤所做的工作是多么有价值。
欣赏电影音乐,意味着改变被动的观影习惯,刻意训练自己的耳朵,使之能够从习以为常的声画合一中将音乐分离出来,但又不是绝对的分离,而是把音乐当作审视的主体,看它如何为其他元素服务,如同欣赏一位高超的配角如何为他人配戏。
俗话说: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电影配乐就好比那个伟大的女性,让在外抛头露面的男人(画面)发挥出最佳状态,为整个家庭(影片)创造完美和谐的环境。但正如生活中有女强人,电影中也有不甘当绿叶的音乐,比如在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遨游》中,无论你喜欢与否,音乐是无法忽视的。作为一名古典音乐迷,该片的音乐使用(虽不是原创音乐)令我叹为观止。
电影和音乐都可以用感性的方法来体验,也可以纯理性地分析其技巧。展凤将这两种方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读展凤的文章,仿佛有一位精通电影和音乐的好朋友带你徜徉在艺术的殿堂中,向你娓娓道出其中奥妙,没有教师的居高临下,也没有急于抒情者的自我陶醉。她的文字总是那么耐心,那么容易亲近,但同时又极富知识性。
电影音乐是一个跨专业的领域,可赖以指点迷津的向导并不多。展凤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向导,而且堪称国内影迷在该领域的启蒙者。有了展凤的解说,我们的电影之旅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周黎明
2006年4月24日,星期一。纽约林肯中心的艾弗瑞·费雪大厅像往常一样挤满了音乐爱好者,但观众比平时的古典乐迷更加年轻。当晚的节目主持人是美国影坛的两大泰斗:马丁·斯科西斯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是谁的演出能够让这两位大导演联袂登场?黑泽明的《梦》曾由斯皮尔伯格监制、斯科西斯参演,因为黑泽明是他俩都非常敬重的前辈;但平时,除了奥斯卡等业内高端活动,很难想像他们两人出席同一个为他人捧场的场合。这次让他们同时登台的,是当今美国电影界的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
威廉斯是斯皮尔伯格的御用配乐家,被很多人视为影史上最成功的电影配乐家,他的崇高地位光从45次奥斯卡提名、5次得奖的记录便可窥见一斑。这场音乐会的前半场,威廉斯率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了伯纳德·赫曼的电影音乐。赫曼是希区柯克的御用配乐家,光是那段《惊魂记》中浴室杀人的锯齿式段落就足以让他流芳百世,何况他还配了《公民凯恩》、《出租车司机》等多部不朽杰作。
音乐会的下半场是威廉斯自己的作品。斯皮尔伯格上场,放映了一段四分钟的《圣战奇兵》追杀戏,但不配音乐。画面虽然精彩绝伦,但略显冗长。然后,斯皮尔伯格把这段戏重新放了一遍,但这次由威廉斯现场演奏他创作的配乐,顿时,画面如虎添翼,气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电影音乐的重要性,没有比这个例子诠释得更清楚的了。如果你不信,只要把电视的音响关闭,尝试一下你最迷恋的电影片断,看看效果打了多少折扣。
很多人喜欢看电影,也喜欢听音乐;但当音乐和画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多数人却常常熟视无睹,好像这些画面是带着音乐一起诞生的。
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忽视电影音乐的影迷。正因如此,我深感展凤所做的工作是多么有价值。
欣赏电影音乐,意味着改变被动的观影习惯,刻意训练自己的耳朵,使之能够从习以为常的声画合一中将音乐分离出来,但又不是绝对的分离,而是把音乐当作审视的主体,看它如何为其他元素服务,如同欣赏一位高超的配角如何为他人配戏。
俗话说: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电影配乐就好比那个伟大的女性,让在外抛头露面的男人(画面)发挥出最佳状态,为整个家庭(影片)创造完美和谐的环境。但正如生活中有女强人,电影中也有不甘当绿叶的音乐,比如在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遨游》中,无论你喜欢与否,音乐是无法忽视的。作为一名古典音乐迷,该片的音乐使用(虽不是原创音乐)令我叹为观止。
电影和音乐都可以用感性的方法来体验,也可以纯理性地分析其技巧。展凤将这两种方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读展凤的文章,仿佛有一位精通电影和音乐的好朋友带你徜徉在艺术的殿堂中,向你娓娓道出其中奥妙,没有教师的居高临下,也没有急于抒情者的自我陶醉。她的文字总是那么耐心,那么容易亲近,但同时又极富知识性。
电影音乐是一个跨专业的领域,可赖以指点迷津的向导并不多。展凤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向导,而且堪称国内影迷在该领域的启蒙者。有了展凤的解说,我们的电影之旅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及其
音乐里的终极关怀
前言
八十年代中期,波兰被紊乱与脱序主宰着--它主宰着每个地方、每件事,以至于每个人的生活。紧张、无望的情绪,以及对更恶劣的未来的恐惧,呼之欲出。那时我已开始不时出国转转,观察到整个世界也普遍弥漫着犹豫的感觉。我指的不是政治,而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我感受到大家在礼貌的微笑背后隐藏着对彼此的漠然;还有一种迫人的印象,觉得自己看到愈来愈多不知为何而活的人们……本文所引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文字素材,见基耶斯洛夫斯基,《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唐嘉慧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另亦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伦理的叙事纬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十诫》尝试描述关于十到二十个人的十个故事。这些人各自面临特殊的状况而作挣扎。这些状况都是虚构的,但它们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些人领悟到自己在绕圈子,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太自私、太爱自己和自己的需求,其他人便在背景中消失了。照理说,我们都为所爱的人付出很多,可是,当我们回顾过往,就会看到自己虽然付出了这么多,却从来没有花精神或时间去拥他们入怀,对他们说句好听、温柔的话。我们无瑕谈论感情。我想那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或是我们没有时间感受与感情有密切关系的激情。于是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从我们的指隙间流逝了。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细心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人们羞于谈论自己的生命,因为觉得难堪,不愿揭开旧疮,否则便是害怕自己显得守旧、多愁善感,因此,我们希望在每部影片的开始都暗示主角是被摄影机随意挑中的。我们想在一个有成千上万观众的大运动场里,将集点对准其中一个脸孔。也想到在拥挤的街道上随意挑出一位行人,然后用摄影机一直在跟踪她/他到影片结束。最后我们决定将场景放在一栋大型的国宅里,第一个镜头就拍那上千个一式一样的窗户……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1
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其传记里谈到《十诫》(The Decalogue,1988)的衍生,他某天情绪低落之际,在街上的拐角碰到跟他合写《永无休止》(No End)的律师编剧皮斯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那天天气很冷,皮斯维茨到处游荡,基耶斯洛夫斯基则遗失了一只手套,二人偶遇,闲聊几句,皮斯维茨就没头没脑地对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有人应该拍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应该由你拍。"谁知道呢?只是闲聊间的小点子,一系列十集震惊国际影坛的作品就这样产生了。正如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没有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没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二人心情俱坏,也没有《十诫》。个中充满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味道,生命难以预料,谁都说不清。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那时候,他们都活在沮丧的思绪之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生活下去,或许我们应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
于是,他们想到《旧约圣经》里的"十诫"。在旧约里,一切如此黑白分明,上帝在当中,是永恒、明确、绝对(而非相对)的仲裁,基氏曾说:"旧约里的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很残酷的神。他毫不宽贷,残忍地要求子民服从他定下的一切规矩。"于是,二人想到,落入复杂无常的现今社会,旧约的十条戒律,还足以大派用场,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皮斯维茨所关注的,也是扣紧十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所在。在构思《十诫》的过程中,二人不住地思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何谓诚实?何谓不诚实?它们的本质何在?人们又可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上述种种问题?
《十诫》是十个关乎个人道德困惑的故事,当中人物处身于复杂的道德处境,背负着进退维谷、百感交集的矛盾与无奈。基氏曾说:"在情感的范畴,我们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畴,我们却大大地受到机遇主宰。"故事往往发生在个人的脆弱无力与生命的诡谲无常之间,那是电影里的重要基调。
是的,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的电影音乐,纪念这位我最钟爱的光影大师及其知交电影配乐家普理斯纳(Zbigniew Preisner),二人合作多年[《十诫》以后,就是《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1991)与《蓝白红三部曲》(Three Colors: Blue, White, Red,1993-1994)],每部作品都让我深受触动。我不讳言,基氏的电影与普氏的音乐于我如同宗教如同药,每隔一段时间,我总忍不住要把它们放进碟盘观看、聆听,然后,人就宁静、释怀。2006年3月,正值基氏逝世十周年纪念,一晃眼,十年一觉扬州梦。是时候下笔,零零星星记下二人如何以光影与音乐在《十诫》里书写生命的种种悖论,以作为一种心情的纪录、一份敬仰的纪念。
音乐里的终极关怀
前言
八十年代中期,波兰被紊乱与脱序主宰着--它主宰着每个地方、每件事,以至于每个人的生活。紧张、无望的情绪,以及对更恶劣的未来的恐惧,呼之欲出。那时我已开始不时出国转转,观察到整个世界也普遍弥漫着犹豫的感觉。我指的不是政治,而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我感受到大家在礼貌的微笑背后隐藏着对彼此的漠然;还有一种迫人的印象,觉得自己看到愈来愈多不知为何而活的人们……本文所引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文字素材,见基耶斯洛夫斯基,《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唐嘉慧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另亦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伦理的叙事纬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十诫》尝试描述关于十到二十个人的十个故事。这些人各自面临特殊的状况而作挣扎。这些状况都是虚构的,但它们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些人领悟到自己在绕圈子,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太自私、太爱自己和自己的需求,其他人便在背景中消失了。照理说,我们都为所爱的人付出很多,可是,当我们回顾过往,就会看到自己虽然付出了这么多,却从来没有花精神或时间去拥他们入怀,对他们说句好听、温柔的话。我们无瑕谈论感情。我想那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或是我们没有时间感受与感情有密切关系的激情。于是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从我们的指隙间流逝了。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细心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人们羞于谈论自己的生命,因为觉得难堪,不愿揭开旧疮,否则便是害怕自己显得守旧、多愁善感,因此,我们希望在每部影片的开始都暗示主角是被摄影机随意挑中的。我们想在一个有成千上万观众的大运动场里,将集点对准其中一个脸孔。也想到在拥挤的街道上随意挑出一位行人,然后用摄影机一直在跟踪她/他到影片结束。最后我们决定将场景放在一栋大型的国宅里,第一个镜头就拍那上千个一式一样的窗户……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1
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其传记里谈到《十诫》(The Decalogue,1988)的衍生,他某天情绪低落之际,在街上的拐角碰到跟他合写《永无休止》(No End)的律师编剧皮斯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那天天气很冷,皮斯维茨到处游荡,基耶斯洛夫斯基则遗失了一只手套,二人偶遇,闲聊几句,皮斯维茨就没头没脑地对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有人应该拍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应该由你拍。"谁知道呢?只是闲聊间的小点子,一系列十集震惊国际影坛的作品就这样产生了。正如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没有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没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二人心情俱坏,也没有《十诫》。个中充满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味道,生命难以预料,谁都说不清。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那时候,他们都活在沮丧的思绪之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生活下去,或许我们应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
于是,他们想到《旧约圣经》里的"十诫"。在旧约里,一切如此黑白分明,上帝在当中,是永恒、明确、绝对(而非相对)的仲裁,基氏曾说:"旧约里的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很残酷的神。他毫不宽贷,残忍地要求子民服从他定下的一切规矩。"于是,二人想到,落入复杂无常的现今社会,旧约的十条戒律,还足以大派用场,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皮斯维茨所关注的,也是扣紧十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所在。在构思《十诫》的过程中,二人不住地思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何谓诚实?何谓不诚实?它们的本质何在?人们又可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上述种种问题?
《十诫》是十个关乎个人道德困惑的故事,当中人物处身于复杂的道德处境,背负着进退维谷、百感交集的矛盾与无奈。基氏曾说:"在情感的范畴,我们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畴,我们却大大地受到机遇主宰。"故事往往发生在个人的脆弱无力与生命的诡谲无常之间,那是电影里的重要基调。
是的,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的电影音乐,纪念这位我最钟爱的光影大师及其知交电影配乐家普理斯纳(Zbigniew Preisner),二人合作多年[《十诫》以后,就是《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1991)与《蓝白红三部曲》(Three Colors: Blue, White, Red,1993-1994)],每部作品都让我深受触动。我不讳言,基氏的电影与普氏的音乐于我如同宗教如同药,每隔一段时间,我总忍不住要把它们放进碟盘观看、聆听,然后,人就宁静、释怀。2006年3月,正值基氏逝世十周年纪念,一晃眼,十年一觉扬州梦。是时候下笔,零零星星记下二人如何以光影与音乐在《十诫》里书写生命的种种悖论,以作为一种心情的纪录、一份敬仰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