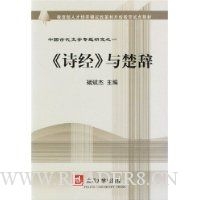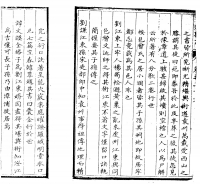刘绪义《诗经》心得
关雎:会错了意的千古绝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周南·关雎
倘若有人在河那边对你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你可千万别会错了意。那一定是一个你从不认识的男子,在调你的情。为什么?倘若是你认识的男子,他绝对不会不喊出你的名字。而且,在这样一种场合,他越是喊得亲热喊得甜蜜,越是能捕获你的欢心。倘若他对你有情,而你对他无意,他也不必感到尴尬。
同时,你绝对不要联想到,这是广西的刘三姐在跟你唱情歌。刘三姐所唱,心中并没有你。她只是一种表演,一种内心情感的发泄。要知道,真正的情歌,只适宜于两个人之间。大庭广众之下唱情歌,十有八九是一种挑逗,你如果愿意被挑逗,你才可以和他渔歌互答。
《关雎》便不是这样一首情歌。
读《诗经》当然不能不读这一首《关雎》。《诗》有四始,《关雎》,风之始也。
什么是“风”呢?《诗经》有十五国风。有关这个“风”字的解释,三千年来,不胜枚举。《毛诗序》是这么解释的:“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是什么东西呢?西汉之时,有四大家传授《诗经》的学者,一是鲁国(诸侯国)的申培。申培是什么人呢?他大约生于公元前219年,死于公元前135年,少年时代跟浮邱伯学诗,做过楚国的中大夫。汉高祖十二年时,刘邦到鲁国还专门接见过他,后被汉文帝拜为博士,汉武帝时,他做到太中大夫。他所传授的《诗经》称鲁诗。他的弟子众多,著名的就有赵绾(做过御史大夫)、孔安国、庆忌等人。一是齐国的辕固,这是个大儒,很有意思。一次,辕固与黄老道家学者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问题。黄生根据君尊臣卑理论认为汤、武并非受命而王,而是弑篡;辕固则强调汤、武乃人心所归,是受命而王。景帝对于两人的观点不置可否,以“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的判语结束了这场学术争论。景帝之母窦太后崇尚黄老之学,好读《老子》书,她向辕固请教,辕固直言不讳地说:“此家人言耳。”说黄老之学是妇道人家没见识说的话,贬道家而扬儒家。窦太后听后大怒,命令他到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暗中相救,才得以脱身。他所传授的诗就称齐诗。一是燕国人韩婴所传授的诗,称为韩诗。他生于约公元前200年,死在公元前130年。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
这三家诗因为用的都是“今文”,就是当时西汉流行的语言文字,因而风行一时。而毛诗晚出,前三家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之时,毛诗只是在民间传播。它是由鲁国人毛亨(人称大毛公)和赵国人毛苌(人称小毛公)所传授的,所以称“毛诗”。而毛诗用的不是当时的文字,是古文,就是秦汉之前的文字。这样一来就有了四家争鸣。这几个人都是饱学之士,有的还是从前朝走过来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国宝级”人物。四家所讲述的诗经都不大一样,互相之间也就存在竞争。偏偏奇怪的是,前三家诗最后都没竞争过后一家,三家都先后消失了,而用古文传授的毛诗反而流传了下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本子,就是“毛诗”。
《毛诗序》又是怎么来的呢?二“毛公”对诗的解释,称“传”;后来东汉一个大儒叫郑玄的,给毛诗做了“笺”,人称“郑笺”,后来元好问有首诗叫作:“诗家只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说的就是西昆体诗虽好,可惜的是缺少像郑玄那样的笺注。后来唐代人孔颖达又做了“疏”。传是对原诗的解释,笺是对传的解释,疏又是对笺的再解释。这三家合起来就成了后来的《毛诗正义》。《正义》里面有序,分大序、小序。小序是列在每一首诗之前的,用来解释各诗的题旨的,大序只有《关雎》一篇才有,相当于后世的总序。小序的作者相传是子夏、毛公,子夏就是孔子的弟子卜商,做过春秋时魏文侯的老师;大序的作者,郑玄认为是子夏,但从朱熹开始,都认为是东汉卫宏。朱熹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说的:“(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范晔又是根据什么认定卫宏作《毛诗序》的呢?不得而知了。如此,我们是信郑玄的还是信范晔、朱熹他们的呢?这很难说清楚。不过,是谁作的我们暂时可以撇开,不管是子夏还是卫宏,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从汉朝开始,《毛诗序》就已存在,并且宋代都接受了《毛诗序》的观点。
关雎:会错了意的千古绝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周南·关雎
倘若有人在河那边对你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你可千万别会错了意。那一定是一个你从不认识的男子,在调你的情。为什么?倘若是你认识的男子,他绝对不会不喊出你的名字。而且,在这样一种场合,他越是喊得亲热喊得甜蜜,越是能捕获你的欢心。倘若他对你有情,而你对他无意,他也不必感到尴尬。
同时,你绝对不要联想到,这是广西的刘三姐在跟你唱情歌。刘三姐所唱,心中并没有你。她只是一种表演,一种内心情感的发泄。要知道,真正的情歌,只适宜于两个人之间。大庭广众之下唱情歌,十有八九是一种挑逗,你如果愿意被挑逗,你才可以和他渔歌互答。
《关雎》便不是这样一首情歌。
读《诗经》当然不能不读这一首《关雎》。《诗》有四始,《关雎》,风之始也。
什么是“风”呢?《诗经》有十五国风。有关这个“风”字的解释,三千年来,不胜枚举。《毛诗序》是这么解释的:“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是什么东西呢?西汉之时,有四大家传授《诗经》的学者,一是鲁国(诸侯国)的申培。申培是什么人呢?他大约生于公元前219年,死于公元前135年,少年时代跟浮邱伯学诗,做过楚国的中大夫。汉高祖十二年时,刘邦到鲁国还专门接见过他,后被汉文帝拜为博士,汉武帝时,他做到太中大夫。他所传授的《诗经》称鲁诗。他的弟子众多,著名的就有赵绾(做过御史大夫)、孔安国、庆忌等人。一是齐国的辕固,这是个大儒,很有意思。一次,辕固与黄老道家学者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问题。黄生根据君尊臣卑理论认为汤、武并非受命而王,而是弑篡;辕固则强调汤、武乃人心所归,是受命而王。景帝对于两人的观点不置可否,以“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的判语结束了这场学术争论。景帝之母窦太后崇尚黄老之学,好读《老子》书,她向辕固请教,辕固直言不讳地说:“此家人言耳。”说黄老之学是妇道人家没见识说的话,贬道家而扬儒家。窦太后听后大怒,命令他到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暗中相救,才得以脱身。他所传授的诗就称齐诗。一是燕国人韩婴所传授的诗,称为韩诗。他生于约公元前200年,死在公元前130年。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
这三家诗因为用的都是“今文”,就是当时西汉流行的语言文字,因而风行一时。而毛诗晚出,前三家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之时,毛诗只是在民间传播。它是由鲁国人毛亨(人称大毛公)和赵国人毛苌(人称小毛公)所传授的,所以称“毛诗”。而毛诗用的不是当时的文字,是古文,就是秦汉之前的文字。这样一来就有了四家争鸣。这几个人都是饱学之士,有的还是从前朝走过来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国宝级”人物。四家所讲述的诗经都不大一样,互相之间也就存在竞争。偏偏奇怪的是,前三家诗最后都没竞争过后一家,三家都先后消失了,而用古文传授的毛诗反而流传了下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本子,就是“毛诗”。
《毛诗序》又是怎么来的呢?二“毛公”对诗的解释,称“传”;后来东汉一个大儒叫郑玄的,给毛诗做了“笺”,人称“郑笺”,后来元好问有首诗叫作:“诗家只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说的就是西昆体诗虽好,可惜的是缺少像郑玄那样的笺注。后来唐代人孔颖达又做了“疏”。传是对原诗的解释,笺是对传的解释,疏又是对笺的再解释。这三家合起来就成了后来的《毛诗正义》。《正义》里面有序,分大序、小序。小序是列在每一首诗之前的,用来解释各诗的题旨的,大序只有《关雎》一篇才有,相当于后世的总序。小序的作者相传是子夏、毛公,子夏就是孔子的弟子卜商,做过春秋时魏文侯的老师;大序的作者,郑玄认为是子夏,但从朱熹开始,都认为是东汉卫宏。朱熹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说的:“(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范晔又是根据什么认定卫宏作《毛诗序》的呢?不得而知了。如此,我们是信郑玄的还是信范晔、朱熹他们的呢?这很难说清楚。不过,是谁作的我们暂时可以撇开,不管是子夏还是卫宏,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从汉朝开始,《毛诗序》就已存在,并且宋代都接受了《毛诗序》的观点。
费了这么多笔墨讲《毛诗序》,似乎无关宏旨,其实大有必要。因为,一篇大序不仅告诉我们古人是怎么理解《关雎》一诗的,更重要的还告诉了我们一部《诗经》的性质和主旨。
这篇大序,先解释了《关雎》。它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毛诗解为后妃为文王寻佳偶;朱熹解为文王寻后妃。不管哪种解释,一个共同点都在于说明文王之行风化,自后妃之美德始。“风”就是风化、教化之意。
值得指出的是,到了后来,关于“风“的解释就开始发生质变。变化之一就是朱熹提出的“风”是民歌说;变化之二就是“诗缘情”说的文学观念突起;变化之三就是后世的革命家对劳动大众的情感迁移。风,也就成了风俗。
朱熹提出民歌说,要否定《诗经》作为圣贤经传的传统观点,一个可能是为他的“四书”张目,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他的天理扫清障碍,而否定圣贤经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乐于见到的成果。把“风”当作民歌,还有理论上的支持,那就是诗缘情的文学观念取代“诗言志”。所谓“风化、教化”即主“言志”;所谓民歌,即主言情。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因而,“风”为民歌说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这一变化,并不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而自然而然的转变,相反,这一转变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是圣贤经传,那么它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普通劳动人民;而既然定性为民歌,那么它的版权无疑则要归属劳动人民了,而这恰恰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能力的有力佐证。这就是《诗经》性质问题的谛奥所在。人类业巳跨进21世纪的门槛,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令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么,《关雎》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首披着情诗外衣的诗。人皆有爱,发乎为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只是人的一种本能。而人有立志,志立于心,心之所志,发言为诗。这便是《诗经》中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毛诗大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关雎》所唱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俨然有那种“美人如花隔云端”的朦胧之境。然而,《诗经》三百篇所歌之美人与淑女是有区别的。美人侧重于她的外在描写,而淑女则往往与君子对举。其意十分明显。
那么,《关雎》所唱的仅仅是一种爱情吗?仅仅是在呼唤自己心中的爱情吗?显然不是,相反,《关雎》抒发的主要是一种志,就是君子对淑女志在必得的感觉,扩而大之就是君侯对贤人的渴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先指认一个对象,一个“淑”字,表明此女之品与德,值得君子向往;而全诗并没有说淑女对君子有什么感情,更谈不上爱,全然是“单相思”。诗人也没有告诉我们,君子最终得到淑女没有。在没有得到“淑女”前,君子“辗转反侧”。末二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显然是君子在辗转反侧的良好愿望:我要是得与淑女匹配,一定要好好对他,这是君子在心里的誓言。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长期以来被视作为孔圣人赋予此诗一种道德规范。这也是错读圣意。倘若真的仅仅是什么君子追求淑女的爱情赞歌,何以哀而不伤?其所以有哀,乃君子之志可哀也。君子之志为何?就在于对美好品德和教化天下的追求。
值得格外指出的就是,《诗经》时代的“君子”绝不是什么女子对男子的通称。什么是君子呢?“君子”一词常见于《尚书》,是对贵族的通称。如“君子所,居无逸”、“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以“君子”称贵族,是家族宗法主义的产物,因而,同样被赋予了天命观念。《诗经》中的“君子”显然是与平头百姓相对的,如“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标准,和小人相对,是整个先秦时代两种人格的规定。孔子给君子规定的三种境界: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己都说做不到。更何况其他什么人呢?
这篇大序,先解释了《关雎》。它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毛诗解为后妃为文王寻佳偶;朱熹解为文王寻后妃。不管哪种解释,一个共同点都在于说明文王之行风化,自后妃之美德始。“风”就是风化、教化之意。
值得指出的是,到了后来,关于“风“的解释就开始发生质变。变化之一就是朱熹提出的“风”是民歌说;变化之二就是“诗缘情”说的文学观念突起;变化之三就是后世的革命家对劳动大众的情感迁移。风,也就成了风俗。
朱熹提出民歌说,要否定《诗经》作为圣贤经传的传统观点,一个可能是为他的“四书”张目,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他的天理扫清障碍,而否定圣贤经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乐于见到的成果。把“风”当作民歌,还有理论上的支持,那就是诗缘情的文学观念取代“诗言志”。所谓“风化、教化”即主“言志”;所谓民歌,即主言情。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因而,“风”为民歌说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这一变化,并不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而自然而然的转变,相反,这一转变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是圣贤经传,那么它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普通劳动人民;而既然定性为民歌,那么它的版权无疑则要归属劳动人民了,而这恰恰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能力的有力佐证。这就是《诗经》性质问题的谛奥所在。人类业巳跨进21世纪的门槛,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令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么,《关雎》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首披着情诗外衣的诗。人皆有爱,发乎为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只是人的一种本能。而人有立志,志立于心,心之所志,发言为诗。这便是《诗经》中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毛诗大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关雎》所唱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俨然有那种“美人如花隔云端”的朦胧之境。然而,《诗经》三百篇所歌之美人与淑女是有区别的。美人侧重于她的外在描写,而淑女则往往与君子对举。其意十分明显。
那么,《关雎》所唱的仅仅是一种爱情吗?仅仅是在呼唤自己心中的爱情吗?显然不是,相反,《关雎》抒发的主要是一种志,就是君子对淑女志在必得的感觉,扩而大之就是君侯对贤人的渴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先指认一个对象,一个“淑”字,表明此女之品与德,值得君子向往;而全诗并没有说淑女对君子有什么感情,更谈不上爱,全然是“单相思”。诗人也没有告诉我们,君子最终得到淑女没有。在没有得到“淑女”前,君子“辗转反侧”。末二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显然是君子在辗转反侧的良好愿望:我要是得与淑女匹配,一定要好好对他,这是君子在心里的誓言。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长期以来被视作为孔圣人赋予此诗一种道德规范。这也是错读圣意。倘若真的仅仅是什么君子追求淑女的爱情赞歌,何以哀而不伤?其所以有哀,乃君子之志可哀也。君子之志为何?就在于对美好品德和教化天下的追求。
值得格外指出的就是,《诗经》时代的“君子”绝不是什么女子对男子的通称。什么是君子呢?“君子”一词常见于《尚书》,是对贵族的通称。如“君子所,居无逸”、“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以“君子”称贵族,是家族宗法主义的产物,因而,同样被赋予了天命观念。《诗经》中的“君子”显然是与平头百姓相对的,如“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标准,和小人相对,是整个先秦时代两种人格的规定。孔子给君子规定的三种境界: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己都说做不到。更何况其他什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