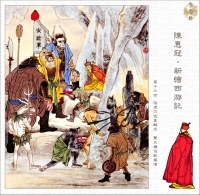(明)陳元之《西遊記序》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莊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若必以莊雅之言求之,則幾乎遺《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餘覽其章近馸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為也。舊有敘,餘讀一過,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豈嫌其丘裏之言與?其敘以猻,猻也;以為心之神。馬,馬也;以為意之馳。八戒,其所戒八也,以為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為賢氣之水。三藏,藏神、藏聲、藏氣之三藏,以為郛郭之主。魔,魔,以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攝。是故撮心以攝魔,攝魔以還理。還理以歸之太初,即心無可攝。此類以為道道成耳。此其書直寓言者哉!彼以為大丹丹數也,東生西成,故西以為紀。披以為濁世不可以莊語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遭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謔笑虐以恣肆。笑謔不可以見世也,故流連比以明意。 於是其言始參差而椒詭可觀;謬悠荒唐,無端莊涘,而談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役已。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捲目梓之,凡二十捲數千萬言有佘,面充敘於餘。餘維太史、漆園之意,道之所存,不欲盡廢,況中慮者哉?故聊為輟其軼敘敘之。不欲其志之盡湮,而使後之人有覽,得其意忘其言也。或曰:“此東野之語,非君子所志。以為史則非信,以為子則非倫,以言道則近誣。吾為吾子之辱。”余曰:“否,否!不然!子以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倫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倫,則子史之誣均。誣均則去此書非遠。餘何從而定之,故以大道觀,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觀,何所不有哉?故以披見非者,非也;以我見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與非者也。是故必兼存之後可。於是兼存焉。”而或者乃示以倌。屬梓成,遵書冠之。 時壬辰夏端四日也。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二十捲捲首、明萬歷間刊本 華陽洞天主人校 金陵世德堂梓行) (明)袁於令《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題詞》 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為怫,未佛皆魔。魔與佛力齊而位逼,絲發之微,關頭匪細。摧挫之極,心性不驚。此《西遊》之所以作也。說者以為寓五行生尅之理,玄門修煉之道。餘謂三教已括於一部,能讀是書者,於其變化橫生之處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問玄機於玉匵,探禪藴於竜藏,乃始有得於心也哉?至於文章之妙,《西遊》、《水遊》實並馳中原。今日雕空鑿影,畫脂鏤冰,嘔心瀝血,斷數莖髭而不得驚人衹字者,何如此書駕虛遊刃,洋洋纚纚數百萬言,而不復一境,不離本宗;日見聞之,厭飫不起;日誦讀之,穎悟自開也!故閑居之士,不可一日無此書。 幔亭過客(按:幔亭、白賓、令昭 ,均為明袁於令的字。) (元)虞集《西遊證道書原序》 餘浮湛史館,鹿鹿丹鉛。一曰有衡嶽紫瓊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來謁,餘與流連浹月,道人將歸,乃出一帙示餘,曰:“此國初丘長春真君所纂《西遊記》也。敢乞公一序以傳。”餘受而讀之,見書中所載乃唐玄奘法師取經事跡。夫取經不始於唐也,自漢迄粱鹹有之,而唐之玄奘為尤著。其所為跋涉險遠,經歷艱難,太宗聖教一序言之已悉,無峽後人贅陳。而餘竊窺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實不玄奘,所紀者在取經,而志實不在取經。特假此以喻大道耳。 猿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陰陽;鬼魑妖邪,亦人世應有之魔障。雖其書離奇浩汗,亡慮數十萬言,面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蓋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則為安心,安心一起,則能作魔,其縱橫變化無所不至,如心猿之稱王、稱聖,而鬧天宮是也;此心收則為真心,真心一見,則能滅魔,其縱橫變化亦無所不至,如心猿之降妖縛怪,而證佛果是也。然則同一心也,放之則其害如彼,收之則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於前,而魔與佛則異矣。故學者但患放心之難收,不患正果之難就,真君之諄諄覺世,其大旨寧外此哉!按真君在太祖時,曾遣侍臣劉仲祿萬裏訪迎,以野服承聖問,促膝論道,一時大被寵脊,有《玄風慶會錄,載之詳矣。 歷朝以來,屢加封號,其所著詩詞甚富,無一非見道之言。 然未有如是書之鴻肆而靈幻者,宜紫瓊道人之寶為枕秘也,乃俗儒不察,或等之《齊諧》稗乘之流,井蛙夏蟲,何足深論。 夫大易,皆取象之文。《南華》多寓言之藴,所由來尚矣。昔之善讀書者,聆周興嗣,性靜心動之句,而獲長生誦。陸士衡山暉澤媚之詞,而悟大道,又何況是書之深切著明者哉! 天歷己巳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集撰 (鐘山黃太鴻笑蒼子西陵汪象旭詹漪子同箋評《新鎸出像古本西遊證道書》捲首 清初刻本) 案:《長春道人西遊記》二捲,文僅二萬字,現存《道藏》中。查清抄本《長春真人西遊記》衹有西溪居土孫錫序,並無虞集序。故知所謂元人虞集《西遊記證道書原序》,乃清人偽作。 (清)野雲主人《增評證道奇書序》 古人往矣,古人不可見,而可見古人之心者,唯在於書。 屬操觚染翰之傢,何時何地,衊有其書,皆煙飛燼滅,淹投而不傳者,必其不足以傳者也。其能傳者,皆古人之精神光焰,自足以呵護而不朽。或有微言奧義,隱而弗彰,則又賴後有解人,為之闡發面揚摧之。其有言雖奧賾,解甚其鮮,而亦卒不泯滅者,則漆園、禦寇之類是也。若夫稗官野乘,不過寄嘻笑怒駡於世俗之中,非有微言奧義,足以不朽,則不過如山鼓一鳴,熒光一耀而已。其旋歸於煙飛燼滅者,固其常事。乃有以《齊諧》野乘之書,傳之奕祀數百之久,而竟不至煙燼者,則可知其精神光焰,自有不可泯滅者在,如《西遊記》是已。餘方稚齒時,得讀《西遊》,見其談詭譎怪,初亦詫而為荒唐。然又疑天壤之大,或真有如是之奇人奇事,而吾之聞見局隘,未之或知也。及夷考史策,則影響茫然,詢之長老,僉曰:此遊戲耳,孺子不足深究也。然餘見其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果無其事,則是人者,纍筆費墨,禍棗災梨,亦頗費經營構撰,而成此巨帙,將安用之?又其中之回目、提綱及詩歌、論贊中,多稱心猿意馬、金公木母等名,似非無謂而漫雲者。既無可與語,唯有中心藏之而已。又數年,既棄製舉業,益泛覽群籍,見有《黃庭》、《二景》、《混元》,《鴻烈》、《抱樸》、《鶡冠》、《悟真》、《參同》堵書,稍加尋繹,雖末測其高深,而天機有勃勃之意。其所論五行繳妙,往往托之神靈男女之間。因憶《西遊》之書,得毋與此相關會耶?取而復讀之,則見其每有針芥之合。餘既不嫻修煉,訪之道流,又無解者,亦未敢遽信以為必爾也。忽得西陵汪澹漪子評本,題之曰《證道奇書》,多列《參同》、《悟真》等書,以為之證,及嘆古人亦有先得我心者,第其評語,與餘意亦未盡同,因重梓乃為增“讀法”數十則而序之。鳴乎!修丹證道面成神仙,自廣成、赤精,黃老以降,載在典籍,非盡誣誕,特仙骨難逢,俗情易溺,誠心求道之人不少概見,而贏政、漢武、文成、武利之屬,上下俱非其人,遂使後人得為口實耳。洪崖先生曰: “子不離行,安知道上有夜行人?”則神仙種子,終亦不絶於世,而火盡薪傳,欲求斯道者,仍不能外於筆墨矣。但伯陽、莊、列之書,雖官道妙而無其階梯,《參同》、《悟真》之類,雖有階梯而語多微奧。全真、雲水之輩、且不能識其端倪,況大衆乎!今長春於獨以修真之秘,衍為《齊諧》稗乘之文,俾黃童白叟,皆可求討其度人度世之心,直與乾坤同其不朽,則自元迄明,數百祀中,雖識者未之前聞,而竟亦不至煙燼而泯滅者,豈非其精神光焰,自足以呵護之耶?今既得澹漪子之闡揚,後或更有進而悉其藴者,則長春子之心,大暴於世,而修丹證道者日益多,則謂此本《西遊記》之功,真在五千、七笈、漆園、禦寇之上也可。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春二月金陵野雲主人題於支瞬居中。 (《西遊證道奇書》捲首 清九如堂刊本) (清)悟元子劉一明《西遊原旨序》 《西遊記》者,元初長春邱真君之所著也。其書闡三教一傢之理,傳性命雙修之道。俗語常言中,暗藏天機;戲謔笑談處,顯露心法。古人所不敢道者,真君道之;古人所不敢泄者,真君泄之。一章一篇,皆從身體力行處寫來;一辭一意,俱在真履實踐中發出。其造化樞紐,修真竅妙,無不詳明且備。可謂拔天根而鑽鬼窟,開生門而閉死戶,實還元返本之源流,歸根復命之階梯。悟之者在儒即可成聖,在釋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不待走十萬八千之路,而三藏真經可取;不必遭八十一難之苦,而一觔鬥雲可過;不必用降魔除怪之法,而一金箍棒可畢。蓋西天取經,演《法華》、《金剛》之三昧;四衆白馬,發《河》、《洛》、《周易》之天機;九九歸真,明《參同》、《悟真》之奧妙;千魔百怪,劈外道旁門之妄作;窮歷異邦,指腳踏實地之工程。三藏收三徒而到西天,能盡性者必須至命,三徒歸三藏而成正果,能了命者更當修性。貞觀十三年上西,十四年回東,貞下有還原之秘要;如來造三藏真經,五聖取一藏傳世,三五有合一之神功。全部要旨,正在於此。其有裨於聖道,啓發乎後學者,豈淺鮮哉?憺[澹]漪道人汪象旭,未達此義,妄議私猜,僅取一葉半簡,以心猿意馬,畢其全旨,且註腳每多戲謔之語,狂妄之詞。咦!此解一出,不特埋沒作者之苦心,亦且大誤後世之志士,使千百世不知《西遊》為何書者,皆自汪氏始。其後蔡、金之輩,亦遵其說而附和解註之。凡此其遺害,尚可言哉?繼此或自為頑空,或指為執相,或疑為閨丹,或猜為吞咽。幹枝百葉,各出其說,憑心造作,奇奇怪怪,不可枚舉。此孔子不得不哭麟,卞和不得不泣玉也。自悟一子陳先生《真詮》一出,諸偽顯然,數百年埋沒之《西遊》,至此方得釋然矣。但其解雖精,其理雖明,而於次第之間,仍未貫通,使當年原旨,不能盡彰,未剋盡美而未盡善耳。予今不揣愚魯,於每回之下,再三推敲,細微解釋。有已經悟一子道破者,茲不復贅,即遺而未解,解而未詳者,逐節釋出,分晰層次,貫串一氣。若包藏卦象,引證經書處,無不—一註明。俾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原始要終,一目瞭然,知此《西遊》,乃三教一傢一理,性命雙修之道,庶不惑於邪說淫辭,誤入外道旁門之塗,至於文墨之工拙,則非予之所計也。 時在乾隆戊寅孟秋三日,榆中棲雲山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自序。 悟元子《指南針》中亦收有此序,與《西遊原旨》中劉序有所不同,附錄於下: 《西遊記》者,元初竜門教祖長春邱真君之所著也。其書闡三教一傢之理,傳性命雙修之道。俗語常言中,暗藏天機;戲謔笑談處,顯露心法。古人所不敢道者,真君道之;古人所不敢泄者,真君泄之。一章一篇,皆從身體力行處寫來;一辭一意,俱在真履實踐中發出。其造化樞紐,修養竅妙,無不詳明且備。可謂拔天根而鑽鬼窟,開生門而閉死戶,實還元返本之源流,歸根復命之階梯。悟之者在儒即可成聖,在釋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不待走十萬八千之路,而三藏真經可取;不必遭八十一難之苦,而一觔鬥雲可過;不必用降妖除怪之法,而一金箍棒可畢。蓋西天取經,演《法華》、《金剛》之三昧;四衆白馬,發《河》、《洛》、《周易》之天機;九九歸真,明《參同》、《悟真》之奧妙;千魔百怪,劈異端旁門之妄作;窮歷異邦,指腳踏實地之工程。三藏收三徒而到西天,能盡性者必須至命,三徒歸三藏而成正果,能了命者還當修性。貞觀十三年上西,十四年回東,貞下有還原之秘要;如來造三藏真經,五聖取一藏傳世,三五有合一之神功。全部要旨,正在於此。其有裨於聖道,啓發乎後學者,豈淺鮮哉?憺漪道人汪象旭,未達此義,妄議私猜,僅取一葉半簡,以心猿意馬,畢其全旨,且註腳每多戲謔之語,妄誕之詞。咦!此解一出,不特埋沒作者之婆心,亦且大誤後世之志士,使千百世不知《西遊》為何書者,皆自汪氏始。其遺害,尚可言乎?繼此或目以頑空,或指為執相,或疑為閨丹。幹枝百葉,各出其說,憑心自造,奇奇怪怪,不可枚舉。此孔子不得不哭麟,卞和不得不泣玉也。我國朝悟一子陳先生《真詮》一出,諸偽顯然,數百年埋沒之《西遊》,至此方得釋然矣。但其解雖精,其理雖明,而於次第之間,仍未貫通,使當年原旨,猶不能盡彰,未剋盡美而未盡善耳。予今不揣愚魯,於每回之下,再三推敲,細微註釋。有已經悟一子道破者,茲不復贅,即遺而未解,解而未詳者,逐節繹出,分晰層次,貫串一氣。若包藏卦象,引證經書處,無不—一釋明。俾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原始要終,一目瞭然,知此《西遊》,乃三教一傢一理,性命雙修之道,庶不惑於邪說淫辭,誤入異端旁門之塗,至於文墨之工拙,則非予之所計也。 時大清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初秋三日 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自敘於金城白道樓。 棲雲山悟元道人西遊原旨敘 《陰符》、《清淨》、《參同契》,丹經也。《西遊》一書,為邱真君著作。人皆豔聞樂道,而未有能知其原旨者。其視《西遊》也,幾等之演義、傳奇而已。餘於戊午之秋,得晤棲雲山悟元道人於蘭山之金天觀,出其《修真辨難》、《陰符》、《參同》諸經註解,蓋以大泄先天之秘,顯示還丹之方。最後出其《西遊原旨》一書,其序其註,其詩其結,使邱真君微言妙義,昭若日星,沛如江海,乃知《西遊》一記,即《陰符》也,即《參同》也,《周易》也,《修真辨難》也。《西遊原旨》之書一出,而一書之原還其原,旨歸其旨,直使萬世之讀《西遊記》者,亦得旨知其旨,原還其原矣。道人之功,夫豈微哉?一燈照幽室,百邪自遁藏。從茲以往,人人讀《西遊》,人人知原旨,人人知原旨,人人得《西遊》。迷津一筏,普渡萬生,可以作人,可以作佛,可以作仙。道不遠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時嘉慶三年中秋前三日,癸卯舉人靈武冰香居士渾然子梁聯第一峰甫題。 悟元子註西遊原旨序 大道傳自太古,問答始於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言簡意該。由漢唐以來,神仙迭出,丹經日廣。然皆發明微妙之旨,言理者多,言事者少。若是,既有悟者,即有昧者。長春邱真人,復以事明理,作《西遊記》以釋厄,欲觀者以事明理,俾學人易悟。後人仍有錯解,不悟立言之精義者。是書行於世,意尚不彰。幸得悟一子陳先生作解註,詳細指出,書中之元妙奧義始明。然註中尚有未便直抉其精藴者,亦有難以筆之於書者。今得悟元子劉先生原旨,其所未備者備,其所未明者明,以補陳註之缺。不但悟一子之註,即成全壁,而長春真人之本意,亦盡闡發宣露,無餘藴矣。使讀《西遊記》之學人,合而觀之,一剎時間,爽然豁然,惺悟於二悟子之悟矣。予本世之武夫魯漢,閱之尚覺開心快意,況世之文人墨士閱之,自必有觸境入處。是二子之註功翼《西遊》,《西遊》之書功翼宗門道教。自茲以往,悟而成道者,吾不知有恆河幾多倍矣。 時在嘉慶六年,歲次辛酉,三月三日,寧夏將軍仍兼甘肅提督豐寧蘇寧阿。 悟元於西遊原旨序 嘗讀《莊子》斫輪之說,而不勝慨然也。聖賢《四書》、《六籍》,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其為世所童而習、幼而安者,盡人而皆然也,顧安得盡人而領聖賢之精髓乎?審如是也,則竜門邱真人《西遊記》一書,又何以讀焉?其事怪誕而不經,其言遊戲而無紀,讀者孰不視為傳奇小說乎?雖然,《莊子》抑又有言矣。“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蓋欲得魚兔,捨筌蹄則無所藉手,既得魚兔,泥筌蹄則何以自然?數百年來,有悟一子之《真詮》,而後讀之者,始知《西遊記》為修煉性命之書矣。然其中有缺焉而未解,解焉而未詳者,則盡美而未盡善也。晉邑悟元子,羽流傑士也。其於《陰符》、《道德》、《參同》、《悟真》,無不究心矣。間嘗三復斯書,二十餘年,細玩白文,詳味詮註,始也由象以求言,由言以求意,繼也得意而忘言,得言而忘象,更著《西遊原旨》,並撰讀法,缺者補之,略者詳之,發悟一子之所未發,明悟一子之所未明,俾後之讀《西遊記》者,以為入門之筌蹄可也;即由是而心領神會,以馴至於得魚忘筌,得免忘蹄焉,亦無不可也。豈必盡如斫輪之說,徒得古人之糟魄已耶? 嘉慶已未仲春月題於竜山書屋,臯邑介庵楊春和。 西遊原旨再序 《原旨》一書,脫稿三十餘年矣。其初,固鎮瑞英謝君即欲刻刊行世,餘因其獨力難成,故未之許。嘉慶二年,乃郎思孝、思弟,欲了父願,摘刻讀法,並結詩一百首,已編於《指南針》中矣,然其意猶有未足也。丙寅秋月,古浪門人樊立之遊宦歸裏,復議付樣,謝氏兄弟,亦遠來送資,時有烏蘭畢君爾德、洮陽劉君煜九、陽峰白子玉峰,一時不謀而合,聞風幫助,餘亦不得不如其願,爰是付樣,使初學者閱之,便分邪正,庶不為旁門麯徑所誤矣。 時大清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春月,素樸散人再敘。 重刊西遊原旨序 道莫備於《易》,而《易》始於一畫,是道之真諦惟一而已矣。一故真,真故一。天地以此位,聖人以此神,而其學天地聖人者,則必渾一與真於一心。一則勿二勿三,真則必誠必信。元微毫釐之界,非虛無寂滅之教所能識也。餘自束發受書時,竊見堯舜十六字之傳,雖歸於執中,實本於惟一。嘗持此旨觀二氏書,非執空之論,即着相之談,腕[ 惋] 惜者久之。數年前遊護國古寺,志永夏公出《西遊》一册示餘。偶一披閱,詭異恢奇,驚駭耳目,第視為傳奇中之怪誕者。及評閱其註釋,言言元妙,字字精微。其間比喻,皆取法於《易》象之旨而成,始知三教同源之論,信不謬也。因詢是書之由,蓋作於長春邱真人,始註者為悟一子,而繼註者則素樸老人悟元子也。夾真人本真以成人,即本真以著書:悟一子之註,固已悟真中之一;素外老人則更悟賓中之元,一中之元也。道之微妙,不如是闡哉?志永夏公不憚馳驅,越數千裏拜老人門下,攜是書歸裏,意欲翻刻流傳,俾學道者皆知正法眼藏。幸得諸善土樂助,勷成盛舉,不獨作者之心,註者之心,皆賴以長存兩間,並使後之覽斯書者,誠知道本於真,真本於一,而主吾心以宰之,則謂是書之為十六字也可,即是謂書之為一畫也亦可。是為序。 時嘉慶二十四年已卯歲長至日 吾山瞿傢鏊撰。 (清)尤侗《西遊真詮序》 三教聖人之書,吾皆得而讀之矣!東魯之書,存心養性之學也;函關之書,修心鍊性之功也;西竺之書,明心見性之旨也。此“心”與“性”,放之則彌於六合,捲之則退藏於密。其揆一也,而莫奇於佛說。吾嘗讀《華嚴》一部而驚焉:一天下也,分而為四;一世界也,纍而為小千、中千、大千。天一而已,有忉利、夜摩諸名;地一而已,有歡喜、離垢諸名。且有輪圍山、香水海、風輪寶焰、日月雲雨、宮殿園林、香花鬘蓋、金銀、琉璃、摩尼之類,無數無量無邊,至於不可說。不可說,總以一言蔽之,曰:一切惟心造而已。 後人有《西遊記》者,殆《華嚴》之外篇也。其言雖幻,可以喻大;其事雖奇,可以證真;其意雖遊戲三昧,而廣大神通具焉。知其說者,三藏即菩薩之化身;行者、八戒、沙僧、竜馬即梵釋天王之分體;所遇牛魔、虎力諸物,即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迦之變相。由此觀之,十萬四千之遠,不過一由旬;十四年之久,不過一剎那。八十一難,正五十三參之反對;三十五部,亦四十二字之餘文也。蓋天下無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則妖治。記《西遊》者,傳《華嚴》之心法也。 雖然,吾於此有疑焉。夫西遊取經,如來教之也;而世傳為丘長春之作。《元史·丘處機》稱為“神仙宗伯”,何慕乎西遊?豈空空玄玄,有殊途同歸者耶!然長春微意,引而不發。今有悟一子陳君起而詮解之,於是鈎《參同》之機,抉《悟真》之奧;收六通於三寶,運十度於五行。將見修多羅中有爐鼎焉,優曇鉢中有梨棗焉,阿闍黎中有嬰兒、奼女焉。彼傢采戰,此傢燒丹,皆波旬說,非佛說也。佛說如是,奇矣。更有奇者,合二氏之妙,而通之於《易》。開以乾坤,交以離坎,乘以姤復,終以既濟、未濟,遂使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會歸於《西遊》一部。一陰一陽,一闔一闢,其為變易也,其為不易也,吾烏乎名之哉? 然則奘之名玄也;空、能、淨之名悟也;兼佛、老之謂也。舉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悟之所以貞夫一也。然老子曰:“道生一。”佛子曰:“萬法歸一。”一而三,三而一者也。以“悟一”之書,告之三教聖人,必有相視而笑者。昌黎有雲:“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孔子者習聞其說,亦曰:‘吾師亦嘗師之雲爾。’”吾師乎,吾不知其為誰乎?若悟一者,豈非三教一大弟子乎!吾故曰:能解《西遊記》者,聖人之徒也。 康熙丙子中秋西堂老人尤侗譔 (清)何廷椿《通易西遊正旨序》 先師張逢源,諱含章,蜀之成都人也。傢貧自力於學,不求聞達於時。學尚簡默,潛心性理,嘗得異人淵源之授,由是造詣益深。復取周、邵請書及河洛圖解,日夜討求,務晰其理。固厭城市囂煩,非可托足,乃徙於峨山下,搆鬥室居焉,顔其額曰與善堂,環堵蕭然,優遊自得,一時慕道之士,多從之遊,平生博涉群籍,探源溯流,以為聖賢仙釋,教本貫通。故自六經以至黃老,無不篤志研宄,而尤遽於《易》所著有《原易篇》、《遵經易註》。又以道經龐雜,學者罔識所歸,故為手輯《道學薪傳》四眷,並梓於世。他如遁甲、堪輿、術數諸學,靡不實獲於心,每示人趨避,輒多奇驗。然其潔身自隱,不妄幹人,以故道學粹然,而當時鮮有識者。餘雖忝侍丹鉛,自愧鈍根鮮語。竊見先師教人入道法門,必以守正卻邪為主。且示之曰,“從古言道之書廣矣,未有以全體示人者。惟元代邱祖所著《西遊》,托幻相以闡精微,力排旁門極弊,誠修持之圭臬,後學之津梁也。”乃就其書手為批註,以明三教一原。書成授於餘,餘拜而讀之,久欲公諸同好,而未之逮焉。先師年登大耄,含笑而終,今已十稔矣,而當時手澤如新。客秋袖至錦垣,將付之剞劂,餘婿嚮氏昆季見之,願為贊襄,共成此舉,經半載而工葳。其書悉遵先師遺稿,第為師門互相傳抄日久,亡其底册,不免有亥塚之訛。 是在學者會心不遠,勿以詞害意焉可已。先師志存闡道,弗以沽名,故並隱其姓名。茲刻亦依原式,以承師旨,而其苦心孤詣,有不可終沒者,特表而出之。是為序。 道光歲次己亥孟夏既望,記於眉山書捨,受業何廷椿謹識。 (《通易西遊記正旨分章註釋》捲首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雨香《西遊記敘言》 《西遊記》無句不真,無句不假,假假真真,隨手鑽來,頭頭是道。看之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思之如抽繭剝蕉,層出不窮。解之以詮,如珠噴星漢,攀不可 階;如錦織雲霞,梭成無縫,雖有遊夏纔也莫贊,況區區駑末?而來悟一子詮是遵 ,好似一做官人官話。夫記也,奚藉乎詮顯,且難畫於詮指,抑敢竟以詮泄。必欲 詮之,必親切有味,始令人觀之心領神合,倘不以詮明記,而或以詮障記,詮有何 味?更有何益? 不但無益於目遊人,亦何益於《西遊記》?是詮之不如無詮,一任《西遊》自 在虛靈,玲玲瓏瓏、活活潑潑之為愈也。蓋全記渡世慈航,分明指示,能靜中參悟 之,原非秘藏不露者。入大海撈針,不得針,另摸一針示人以為即是,不知果是耶 否? 全記不作一浮談贅字,懷明記記不全者,略節要旨,方便記半,以私幸坐井觀 耳。然而撈凡幾度,稿凡幾易,用心亦太睏矣,妄心亦已甚矣。要覓真針是,先須 忘妄心,未曾磨鐵杵,那得綉花針?是耶?否也?亦衹是對月之穿,蹲山之鈎,料 瀛上仙翁海量,定不以蛙鳴科罪。 鹹豐七年丁巳重陽後三日庚寅刀農人雨香盥沐謹識。 (北圖柏林寺分館藏 清抄稿本) (清)王韜《新說西遊記圖像序》 《西遊記》一書,出悟一子手,專在養性修真,煉成內丹,以證大道而登仙籍。所歷三災八難,無非外魔。其足以召外魔者,由於六賊,其足以製六賊者,一心而已。一切魔劫,由心生,即由心滅。此其全書之大旨也。唐三藏元奘法師取經西域,實有其事。此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遙徵,即得經像,薄育旋軔,以十九年春正月達於京邑,謁帝洛陽,曾譯《大唐西域記》十二捲,經歷—百三十八國,多述佛典因果之事。今以新、舊《唐書》核之所序諸國,皆所不載。蓋史所錄者,朝貢之邦;記所言者,經行之地也。記中於俗尚、土風、民情、物産,概在所略。惟是侈陳靈檉,誕漫無稽,儒者病之。後世《西遊記》之作,並不以此為藍本,所歷諸國,亦無一同者,即山川道裏,亦復各異。誠以作者帷憑意造,自有心得。其所述神仙鬼怪,變幻奇詭,光怪陸離,殊出於見見聞聞之外,伯益所不能窮,夷堅所不能志,能於《山海經》錄中別樹一幟,一若宇宙間自有此種異事,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至今膾炙人口。演說者又為之推波助瀾,於是人人心中皆有孫悟空在,世俗無知,至有為之立廟者,而戰鬥勝佛,固明明載於佛經也。不知《齊諧》志怪,多屬寓言;《洞冥》述奇,半皆臆創。莊周昔日以荒唐之詞鳴於楚。 鯤鵬變化,椿靈老壽,此等皆是也。虞初九百,因之益廣已。 此書舊有刊本而少圖像,不能動閱者之目。今餘友味潛主人嗜古好奇,謂必使此書別開生面,花樣一新。特情名手為之繪圖,計書百回為圖百幅,更益以像二十幅,意態生動,須眉躍然見紙上,固足以盡丹青之能事矣。此書一出,宜乎不脛而走,洛陽為之紙貴。或疑《西遊記》為邱處機真人所作,此實非也。元太祖駐兵印度,真人往謁之,於行帳記其所經,書與同名,而實則大相徑庭。以蒲柳仙之淹博,尚且誤二為一,況其它乎?因序《西遊記真詮》,而為辨之如此。 光緒十有四年歲在戊於春王正月下浣長洲王韜序於滬上淞隱廬。
(清)含晶子《西遊記評註序》
《西遊記》一書,為長春邱真人所著。世傳其本以為遊戲之書,人多略之,不知其奧也。孩童喜其平易,多為訣助,予少時亦以為談天炙棵之流耳。雖有悟一子詮解之本,然辭費矣。費則隱,閱者仍昧然,如河漢之渺無津涘也。予近多閱道書,溯源竟委,乃知天地間自有一種道理。近取諸身,尤為切近。道傢脈絡,原本一氣,亦本於吾儒養氣之說。能養氣者,莫如孟子。孟子其傳於子思,以承道統,再後則遂失矣。河圖、洛書,流入道教,陳希夷得之,後由此復歸於儒,濂溪、康節得之,而道教分而為三:一章奏,林靈素等之說也;一符籙,張道陵等之說也;一修煉,則禦女燒丹,如秦漢方士文成、五利之輩,其說愈多,其教愈詭,而人陷溺於中者,世難輩數,良可概也!豈知仙道不外一氣,馴而養之,與吾傢浩然之氣同出異名者也。仙傢分南北二宗,北宗最顯。
邱真人入道最苦,得道最晚,實紹北宗之正派,特著此書,將一生所歷各劫,厲歷舉以示人。其不着為道書,而反歸請佛者,以佛主清淨與道較近。道教灕其真久奧,且陷於邪者,習之不正,足以誤人面病國。故以佛為依歸,而與道書實相表裏,此《西遊記》所由作也。入道之門,修道之序,成道之功,深切著明,無一毫不告學者,其用心亦良苦矣。所言各物,多從譬喻,惟在讀者期心討取,方得蹄筌。其言。太乙金仙,即吾身得氣之初最先一物;其言唐僧曰名三藏者,即吾身所備之三纔也;其育孫行者曰名悟空者,悟得此空,方是真空,其言豬八戒曰名悟能者,悟得此能,由於受戒;其言沙和尚曰名悟淨者,即謂能悟能戒,方是淨土,可以做得和尚矣。人能備此三纔之秀,再得先天真一之氣,以為一心主宰,故行者必用金箍棒。金者,先天之氣;棒者,一心主宰也。再能堅持八戒,以為一體清淨之全,八戒必用九齒釘鈀。九者,老陽也,齒者,堅忍也;釘鈀者,種土之具也。再能調和陰陽二氣,歸於淨土之中,則修道已得,所杖持矣,故沙僧必用寶杖也。三者不可離也:無行者之金,則東方不長,無八戒之木,則西方不成,無沙僧之土以調劑之,則二氣不勻,且反為害。既如是,又須得竜馬之腳力,逐日行之,雖十萬八千裏之程,須臾勿懈,學道而有不成者乎?此全書之大概也。魔者,即心所生也,亦有行道之時,到此一侯,即有此一侯之魔。魔不由心造,所謂道高一丈,魔高十尺,與道懼起,不與道俱滅,馴至無聲無臭,遣於帝載,無所謂魔,亦無所謂道。閱此書者,宜解所未解也。於今讀此全部,隨所見標而識之,以為此書之助。道書傳世者夥矣,或言之末真,或詮之末深,或有聞而未能行,即將所聞,摹之為書,或所聞未得師,即將其語據以為秘,推究其始。惟老、莊、尹、列諸書,久傳於世。此外,《參同》一書,世推丹經之王。再後則張紫陽《悟真篇》,藉藉人口,然《悟真》多隱,其詞亦頗誤世,故白紫清真人謂紫陽傳道不廣,亦謂托端陰陽,稍為采補傢所襲取耳。此書探源《參同》,節取《悟真》,所肓皆親歷之境,所述皆性命之符。予之銓解,雖未面授真人之旨,而不敢臆造,其說實觸類引申,使人易曉,勿隳迷途,與悟一子之詮,若合若離,而闢邪祟正之心,或較悟一子而更切也。謹序簡端,以詔讀者。光緒辛卯六月含晶子自敘。
(光緒壬辰年開鎸《西遊記評註》捲首)
(清)含晶子《西遊記評註序》
《西遊記》一書,為長春邱真人所著。世傳其本以為遊戲之書,人多略之,不知其奧也。孩童喜其平易,多為訣助,予少時亦以為談天炙棵之流耳。雖有悟一子詮解之本,然辭費矣。費則隱,閱者仍昧然,如河漢之渺無津涘也。予近多閱道書,溯源竟委,乃知天地間自有一種道理。近取諸身,尤為切近。道傢脈絡,原本一氣,亦本於吾儒養氣之說。能養氣者,莫如孟子。孟子其傳於子思,以承道統,再後則遂失矣。河圖、洛書,流入道教,陳希夷得之,後由此復歸於儒,濂溪、康節得之,而道教分而為三:一章奏,林靈素等之說也;一符籙,張道陵等之說也;一修煉,則禦女燒丹,如秦漢方士文成、五利之輩,其說愈多,其教愈詭,而人陷溺於中者,世難輩數,良可概也!豈知仙道不外一氣,馴而養之,與吾傢浩然之氣同出異名者也。仙傢分南北二宗,北宗最顯。
邱真人入道最苦,得道最晚,實紹北宗之正派,特著此書,將一生所歷各劫,厲歷舉以示人。其不着為道書,而反歸請佛者,以佛主清淨與道較近。道教灕其真久奧,且陷於邪者,習之不正,足以誤人面病國。故以佛為依歸,而與道書實相表裏,此《西遊記》所由作也。入道之門,修道之序,成道之功,深切著明,無一毫不告學者,其用心亦良苦矣。所言各物,多從譬喻,惟在讀者期心討取,方得蹄筌。其言。太乙金仙,即吾身得氣之初最先一物;其言唐僧曰名三藏者,即吾身所備之三纔也;其育孫行者曰名悟空者,悟得此空,方是真空,其言豬八戒曰名悟能者,悟得此能,由於受戒;其言沙和尚曰名悟淨者,即謂能悟能戒,方是淨土,可以做得和尚矣。人能備此三纔之秀,再得先天真一之氣,以為一心主宰,故行者必用金箍棒。金者,先天之氣;棒者,一心主宰也。再能堅持八戒,以為一體清淨之全,八戒必用九齒釘鈀。九者,老陽也,齒者,堅忍也;釘鈀者,種土之具也。再能調和陰陽二氣,歸於淨土之中,則修道已得,所杖持矣,故沙僧必用寶杖也。三者不可離也:無行者之金,則東方不長,無八戒之木,則西方不成,無沙僧之土以調劑之,則二氣不勻,且反為害。既如是,又須得竜馬之腳力,逐日行之,雖十萬八千裏之程,須臾勿懈,學道而有不成者乎?此全書之大概也。魔者,即心所生也,亦有行道之時,到此一侯,即有此一侯之魔。魔不由心造,所謂道高一丈,魔高十尺,與道懼起,不與道俱滅,馴至無聲無臭,遣於帝載,無所謂魔,亦無所謂道。閱此書者,宜解所未解也。於今讀此全部,隨所見標而識之,以為此書之助。道書傳世者夥矣,或言之末真,或詮之末深,或有聞而未能行,即將所聞,摹之為書,或所聞未得師,即將其語據以為秘,推究其始。惟老、莊、尹、列諸書,久傳於世。此外,《參同》一書,世推丹經之王。再後則張紫陽《悟真篇》,藉藉人口,然《悟真》多隱,其詞亦頗誤世,故白紫清真人謂紫陽傳道不廣,亦謂托端陰陽,稍為采補傢所襲取耳。此書探源《參同》,節取《悟真》,所肓皆親歷之境,所述皆性命之符。予之銓解,雖未面授真人之旨,而不敢臆造,其說實觸類引申,使人易曉,勿隳迷途,與悟一子之詮,若合若離,而闢邪祟正之心,或較悟一子而更切也。謹序簡端,以詔讀者。光緒辛卯六月含晶子自敘。
(光緒壬辰年開鎸《西遊記評註》捲首)
(清)張書紳《新說西遊記》總批
《西遊》一書,古人命為證道書,原是證聖賢儒者之道。
至謂證仙佛之道,則誤矣。何也?如來對三藏雲:“閻閩浮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多淫多佞,多欺多詐,此皆拘蔽中事。”彼仙佛門中,何嘗有此字樣?故前就盂蘭會,以及化金蟬,已將作書的題目大旨,一一點明,且不特此也,就如傳中黑風山、黃風嶺、烏雞國,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國、鳳仙郡,是說道傢那一段修仙?是說僧傢那一種成佛?又何以見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註解,恐其不能確然明白指出。真乃強為渺幻,故作支離,不知《西遊記》者也。長春原念人心不古,身處方外,不能有補,故藉此傳奇,實寓《春秋》之大義,誅其隱微,引以大道,欲使學業煥然一新。無如學者之不惜也,悲夫!
《西遊》又名《釋厄傳》者何也?誠見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無益,竭盡心力,虛度浮生,甚至傷風敗俗,滅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豈非大厄耶?作者悲憫於此,委麯開明,多方點化,必欲其盡歸於正道,不使之復蹈於前愆,非“釋厄”而何?
《西遊》一書,以言仙佛者,不一而足。初不思佛之一途,清靜無為,必至空門寂滅而後成。即仙之一道,雖與不同,然亦不過采煉全真,希徒不死。斯二者,皆遠避人世,惟知獨善一身,以視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關。至於仁義禮智之學,三綱五倫之遭,更不相涉。此仙佛主事也,今《西遊其文無為,是以讀之亦覺無味。《西遊》是把理學演成魔傳,又由魔傳演成文章,一層深似一層,一層奇擬一層,其實《西遊》又是《西遊》,理學又是理學,文章又是文章,三層並行,毫不相背,奇莫奇於此矣。愛理學理,究其淵微;愛熱鬧者,觀其故事;好文墨者,玩其筆意。是豈別種奇書,所可得同日而語也?
《西遊》凡言菩薩如來處,多指心言。故求菩薩正是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正是《西遊》的妙處。聖嘆不知其中之文義,反笑為《西遊》的短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西遊》凡如許的妙論,始終不外一個心字,是一部《西遊》,即是一部《心經》。
通人讀書,衹往通處解,所以愈讀愈明;不通人讀書,衹往不通處解,所以愈讀愈不明。即如鄭莊公名寤生,此原不過作者下此一字,便好起惡字,以與後愛段叔一句,作一文章關照。在讀者,不過看通其文意即了,何必定深究其所生?況此不過一乳名,初無甚緊要關係,在為父母宥,原無所不命,而當日未必亦於此,即有心,在後世就生出許多的議論見解。嗚呼!鄭國遠矣,固不得趨而視之,莊公沒矣,又不能起面問之,若必如是解,則晉文公名重耳,豈真兩重耳朵耶?曹操名阿瞞,豈又瞞其父之所生耶?誠如是,則世更有以雞犬牛羊命名者,不知又當作何解?在古人未必有此事,在後世則強要作此解,不過徒以文字之相害耳,烏足以讀古人之書,烏足以解盲人之書也?
《西遊》一書,不唯理學淵源,正見其文法井井。看他章有章法,字有字法,句有句法,且更部有部法,處處埋伏,回回照應,不獨深於理,實更精於文也。後之批者,非惟不解其理,亦並沒註其文,則有負此書也多矣。
天人性命之學,東山泅水之書,已無不道。詩詞傳賦之文,周秦唐漢之時,已無不作。降而稗官、野史之傳奇,多係小說。雖極其精工靈巧,亦覺其千手雷同,萬章一法,未為千古擅場之極作也。孔子云:“述而不作。”蓋上焉者,不敢作,下焉者,又不肯作。回翔審視,幾無可下筆之處矣。長春計及於此,所以合三者而兼用之,本孔、孟之探心,周、漢之筆墨,演出傳奇錦綉之文章,其中各極其妙,真文境之開山,筆墨之創見。寫一天宮,寫一地府,寫一海藏,寫一西天,皆前代之所閣筆,後世之所絶無,信非學貫天人,文絶地記者,烏足以道其衹字也?自古學已遠,文尚富麗,或以誇多,或以爭幻,此不過一大書店,藏經櫃耳。五尺之村童,錄之有餘,何足以言文,又何足以為奇也?
人生學業不成,皆因物欲多故。外邊的魔障,即是內裏的私欲,故云:“心生,種種魔生也。”若一直寫去,未免腐而無味。看他形容欽食之人,則寫出一蝎子精;言非禮之視,則畫出一多目怪。寫得奇異,狀得更奇異。
《西遊》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起,一路編年紀月,歷敘寒暑,魔怪本於陰陽,剋復順乎四時。此乃以山嶽作硯,雲霞作箋,長虹為筆,氣化為文。讀之如入四時寒暑之中,俯仰其間,而奠識風雲之奧妙也。
天地以太極生兩儀四象,樹木以根本發枝葉花果,人以一心生出仁義禮智,一身行出忠孝廉節。是人生在世,如同天地,如同樹木。則學問文章,原本天地之自然。不是長春作出天地自然之文章,正是天地自然有此文章,不過假長春之筆墨以為之耳。夫天地至大,卻不遍寫。起首落筆第一句,先寫一東勝神州,寫一花果山。真是妙想天開,奇絶千古。夫東勝緊對西天,神州緊對佛天。心之精靈無所不通,故曰神洲;身之德行無所不備,故曰佛天。一東—西,一神一佛,以海比地,以西作天,由花結果,從地升天。自心生海島,樹長神洲,以見根深者葉茂,本固者枝榮。莫不本陰陽之氣化,至理之本然。是以有天地,即有風雲氣化,有樹木,即有枝葉花果;有人,即有仁義禮智之心,忠孝廉節之事。是風雲氣化,乃天地自然之文章;枝葉花果,乃樹木自然之文章,仁義禮智,忠孝廉節,乃人生自然之文章,此方是夫子之文章。人若不讀《西遊》之文章,不知《西遊》之文章,而欲以筆墨堆砌,強為文章,又烏睹所謂文章者也?
《西遊》列傳,大半伏於盂蘭會,此即百樣奇花,千般異果,故云明示根本,指解源流。西粱國,即是口舌兇場;火焰山,謂非是非惡海。貪酒好色,迷失本來之業;爭名奪利,何有西天之路?荊棘叢林,不識法門之要,鳳仙郡裏,怠慢瑜迦之宗。心獨故失,正應不服使喚之文;雙鳥失群,卻是回照多殺之旨。有師有徒,玉華州原非盂蘭會,明德止至善,天竺國已伏化金蟬。白虎嶺至精至細,金(山兜)洞極隱極微。前伏後應,各傳說來俱有源由。條目綱領,首尾看去無不關會。全部數十萬言,無非一西,無非一遊。始終一百回,即此題目,此即部法。
心本虛靈不昧,故曰靈臺。返本還元,以復其本來之初,故曰如來,言如其本來之舊也。足以說靈山衹在心頭,可知如來亦並不在心外。凡如許的妙意,皆有生之所未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何以卻寫出許多的妖怪?蓋人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是為不明其德者一翻。於是忠之德不明,則為臣之道有虧;孝之德不明,則子之道有未盡。以至酒色財氣,七情六欲,爭名奪利,不仁不義,便作出許多的奇形,變出無效的怪狀。所以寫出各種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樣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終不可止,而如來又何以見也?
三藏真經,蓋即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三綱領也。而云西天者,言西方屬金,言其大而且明,以此為取,其德日進於高明。故名其書曰《西遊》,實即《大學》之別名,明德之宗旨。
不唯其書精妙,即此二字,亦見其學問之無窮也。
時藝之文,有一章為一篇者,有一節為一篇者,有數章為一篇者,亦有一字一句為一篇者。面《西遊》亦由是也。以全部而言,《西遊》為題目,全部實是一篇。以列傳言,仁義禮智,酒色財氣,忠孝名利,無不各成其一篇。理精義微,起承轉合,無不各極其天然之妙。是一部《西遊》,可當作時文讀,更可當作古文讀。人能深通《西遊》,不惟立德有本,亦必用筆如神。《西遊》、《西遊》,其有裨於人世也,豈淺鮮哉?
大學之效,有三綱領,五指趣,八條目。天地之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經藏之數,有一萬五千一百軍四十八捲。
其中之三百裏,六百裏、八百裏,十萬八千裏,悉照《大學》之數。故開捲以天地之數起,結尾以經藏之數終。
大學之道,至遠至久,故要經歷十四年,十八萬千裏,以見其道之至大至高,原非近功淺學者之所能造。是以一路西來,無筆不是《大學》,無處不是學道。講大學之道,尤為精極。
古人作書,凡有一篇妙文,其中必寓一段至理,故世未有無題之文也。後人不審其文,不究其理,概以好文字三字混過,不知是祭文、是壽文、是時文,是古文。不知是《出師表》寫出老臣之丹心,還是《陳情衷》作出孝子之天性。古人作書,原如風雲展轉,文理相因;後人批書,竟是秦楚各天,毫不相涉。是古人之作書,原自為古人之書,初不計後人之有批,殊不知後人之批書,衹自為後人之批,並不問古人之所作也。
《西遊》原本,每為後人參改筆削,以自作其聰明,殊不知一字之失實,其理難明,文義不可讀矣。安得古本錄之,以為人心之一快?
或問《西遊記》果為何書?曰實足一部奇文,一部妙文。
其中無題不作,無法不備,乃即長春之一部窗稿,並無別故。
但人海以為方外之元微,而多歧其說,及細究其文藝題目。
則亦無可疑議矣。
按邱長春,名楚(處)機,道傢北宗有七祖,長春乃其中之一。勝跡皆在東海勞山。時應元祖之聘,與弟子一十八人,居於燕京西南之長春宮,故此又稱長春真人,蓋即今之白雲觀也。
元人每作傳奇,多摘取中節二十七題,以發明朱註氣稟人欲之要,文章局面,似迥不同。不知其中之題目,則無絲毫有異。
“西遊”二字,實本《孟子》引《詩》“率西”二字。
物欲不除,氣稟不化,其德不明。其德不明,其民亦不新,至善不可止矣。看他先從氣稟人欲,轉到明德,又由明德,轉到新民,然後結到止至善。一層一層寫來,方見學問之有功夫,更見文章之有次第。
或問一部《西遊記》,為何其中寫了多少的妖魔怪物?夫妖魔怪物,蓋即朱註所謂氣稟人欲之私也。朱註講的渾含,《西遊》實分的詳細。什麽是個氣稟?什麽是個人欲?人如何便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具德便至不明?又必如何方不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迨至不拘不蔽之際,此妖魔之所以盡去,而其德亦不昏矣。是朱註發明聖經,《西遊》實又註解朱註。
氣稟人欲,共擬二十五條,所以亦引二十五個題目,以明具義。凡人有一於此,皆足為大德之纍,而其德已不明,又何以得見本來之所固有,而以止於至善也。
一部《西遊記》,若說是文章,人必不信。再說是經書《大學》文章,人更不信。唯其不信,方見此書之奇。
一部《西遊記》,三大段,一百回,五十二篇,卻首以大學之道一句貫頭。蓋路經十萬八千裏,時歷十四年,莫非大學之道,故開捲即將此句提出,實已包括全部,而下文一百回,三大段,五十二篇,俱從此句生出也。
三藏真經,蓋即明新止至菩,故曰唐三藏。明德即是天理,故曰太白李長庚。《大學》原是大人之學,故云齊天大聖。看他處處抱定,回回提出,實亦文章顧母之法。
三藏真經,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捲,蓋按《大學》之字數而言也。細查《大學》經傳朱註字數;聖經二百零五字,十章一千五百四十八字,小註衹雲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註三幹一百三十三宇,序文五十六字,章傳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宇,尚少一字,其數不符。或計算朱之差,抑亦古今之異,然亦不可得而知矣。
人心衹得一個,道心衹有一條,心顧可多耶?然雲《密多心經》者何哉?蓋密音,靜也,團也,寂默也,聖人以此洗心滌慮,遇藏於密也。多心,即氣稟人欲之私也。必須將此種心,條條滌詵,件件寂默,其德方明,而至善乃可止。此所以為《密多心經》,實剋己之全功也。
一部《心經》,原講君子存理遏遇之要,何以雲色不異空?蓋色乃像也,即指名利富貴之可見者而言。此原身外之物,毫無益於身心性命,雖有若無,故曰不異空。又何以雲空不異色?蓋空即指修己為學之事也。人看是個空的,殊不知道明德立之後,祿位名壽無不在其中,與有者無少間,故曰不異色。由是觀之,人以為色者,不知卻是空,所謂“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者是也。人以為空者,不知卻是色,所謂“富傢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者是也。再觀齊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孰有孰空,人亦可以概悟矣。玉皇張主,蓋言心也;天蓬元帥,實蔽塞此心者也,捲簾大將,開明此心,九齒釘鈀頓開心上之茅塞者也。剋己復禮,原是心上的一部功夫。所以降妖捉怪,純以行者之為首先要務也。
《西遊》每寫一題,源脈必伏於前二章。此乃隔年下種之法,非冒冒而來電。譬如欲寫一豬八戒,先寫一黑熊精;欲與一鐵扇仙,先寫一琵琶洞;欲寫一寶像國,先寫一試撣心。不惟文章與文章接,書理與書理接,而且題目與題目接,妖怪與妖怪接矣。
看他如許一部大書,裏面卻沉沉靜靜,並無一字飛揚,齊齊整整,亦無一回長短。養成學問,練就手筆,讀之最足以收心養性。
古人典籍多矣,何獨《西遊》稱奇?且緇在蕭寺,深為聖門之所不敢,儒流之所迸棄,何況和尚取經,更覺無味,尤屬扯淡平常之甚者也。有何好處,能令海內稱奇?予初讀之,而不見其奇。繼而求之,似有所得。然亦不過謂與世俗之傳奇無異。再進而求之,方知有題有目,似一部鄉會製藝文字。更加竭力細求,始知足一部聖經《大學》文字。迨知是聖經《大學》文字,其妙不可以言,其苦亦不堪再問矣。
《西遊》一書,原是千古疑案,海內一大悶葫蘆。但其為文,有據理直書者,有隱寓者,亦有藉音藉字者,更有止可以章捨而不可以言傳者。
《西遊》一書,原本真西山《大學衍義》而來。但西山止講格緻誠正修齊,末及平治兩條,《西遊》因之而亦如是。後至明祭酒邱瓊山,始續而補之,詳見《大學衍義》。盞西山講的原是一部至精之理學,長春作的卻是一部絶妙之文章,其名雖有不同,而其義則一也。
如來住在雷音,大士又住在潮音,其寓意絶妙,總言學者格物緻知,返本還元,陳誦讀之外,再無別法。後人不悟不求自己之雷音,反求西域之雷音,捨卻自己之潮音,轉尋南海之潮音,其計亦左矣。
嘗言著書難,殊不知解書亦不易。何則?蓋少則不明,多則反酶,而言多語失,以致吹毛求疵,不知淹沒多少好書,批壞無限奇文,良可惜也!
奇書最難讀者,是查無書可查,問無人可問,有如一百件無頭大案,全要在心上細加研究,非得三二年探功,恐不能讀出其中之妙也。
如來何以單要坐蓮臺?蓋蓮取其出污泥而不染,以喻學者返本還元,盡性復初,非去其氣稟人欲,舊染之污,而不得知其本來也。
夫何以為觀音大士?蓋士為學者之通稱,故曰士。觀音乃所以學大人之學者,故稱觀音大士,此指無位者而言,故又稱白衣大土。看他把方外的許多名目,全然附會成一部理學文章,此更覺奇。但不知當原果有此等名號,抑亦後人因作奇書,憑空捏設編造也。
《封神》寫的是道士,固奇;《西遊》引的是釋伽,更奇。細思一部《大學》,其傳十章,一字一句,莫非釋之之文,卻令人讀之,再不作此想,方見奇書假藉埋藏之妙。
曹溪在廣東韶州府東南,內有南華寺,六祖嘗演法於此,乃仙境也。
此書不妙在談天說地,怪異驚人,正妙在循規蹈矩,不背朱註,將一部《大學》,全然藉一釋字脫化出來,再令人意想不到,真正奇絶。
一部《西遊記》,以東字起,西字終,始於萬花店,結於婆羅蜜,所以為花果山,而遂名為《西遊記》也。
(三晉張南薫註《新說西遊記》晉省書業公記藏板)
西遊原旨讀法
一、《西遊》之書,仍歷聖口口相傳、心心相印之大道。古人不敢言者,丘祖言之;古人不敢道者,丘祖道之。大露天機,所關最重。是書在處,有天神守護。讀者須當淨手焚香,誠敬開讀。如覺悶倦,即合捲高供,不得褻慢。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立言,與禪機頗同。其用意處,盡在言外。或藏於俗語常言中,或托於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戲裏,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別其真假。或藉假以發真,或從正以批邪。於變萬化,神出鬼沒,最難測度。
學者須要極深研幾,莫在文字上隔靴搔癢。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神仙之書也,與才子之書不同。才子之書論世道,似真而實假;神仙之書談天道,似假而實真。才子之書尚其文,詞華而理淺;神仙之書尚其意,言淡而理深。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貫通三教一傢之理,在釋則為《金鋼》、《法華》,在儒則為《河》、《洛》、《周易》,在道則為《參同》、《悟真》。故以西天取經,發《金剛》、《法華》之秘;.以九九歸真,闡《參同》、《悟真》之幽;以唐僧師徒,演《河》、《洛》、《周易》之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一案有一案之意,一回有一回之意,一句有一句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真人言不空發,字不虛下。讀者須要行行着意,句句留心,一字不可輕放過去。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世法道法說盡,天時人事說盡。至於學道之法,修行應世之法,無不說盡。乃古今丹經中第一部奇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轉生殺之法,竊造化之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一切執心着意,頑空寂滅之事。學者須要不着心猿意馬、幻身肉囊,當從無形無象處,辨出個真實妙理來,纔不是枉費工夫。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大道,乃先天虛無之學,非一切後天色相之邪術。先將禦女閨丹。爐火燒煉批開,然後窮究正理,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宗公案,或一二回,或三四回,或五六回,多寡不等。其立言主意,皆在分案冠首已明明題說出了。若大意過去,未免無頭無腦,不特妙義難參,即文辭亦難讀看。閱者須要辨清來脈,再看下文,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回妙義,全在提綱二句上。提綱要緊字眼,不過一二字。如首回,“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靈根”即上句字眼,“心性”即下句字眼。可見靈根是靈根,心性是心性,特用心註修靈根,非修心性即修靈根。何等清亮!何等分明!如次回,“悟徹菩提真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悟徹”即上句字眼,“斷魔”即下句字眼。先悟後行,悟以通行,行以驗悟,知行相需,可以歸本合元神矣。篇中千言萬語,變化離合,總不外此提綱之義。回回如此,須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取真經,即取《西遊》之真經。非《西遊》之外,別有真經可取。是不過藉如來傳經,以傳《西遊》耳。能明《西遊》,則如來三藏真經,即在是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宗公案,收束處皆有二句總結,乃全案之骨子。其中無數妙義,皆在此二句上着落,不可輕易放過。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乃三五合一,貞下起元之理。故唐僧貞觀十三年登程,路收三徒,十四年回東,此處最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通關牒文,乃行道者之執照憑信,為全部之大關目。所以有各國寶印,上西而領,回東而交,始終鄭重,須臾不離,大要慎思明辨,方能得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大有破綻處,正是大有口訣處。惟有破綻,然後可以起後人之疑心,不疑不能用心思。此是真人用意深處,下筆妙處。如悟空齊天大聖,曾經八卦爐鍛煉,已成金剛不壞之軀,何以又被五行山壓住?玄奘生於貞觀十三年,經十八年報仇,已是貞觀三十一年,何以取經時又是貞觀十三年?蓮花洞,悟空已將巴山虎、倚海竜打死,老妖已經識破,何以盜葫蘆時,又變倚海竜?此等處大要着意。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通關牒文,有各國寶印,乃《西遊》之妙旨,為修行人安身立命之處,即他傢不死之方。此等處,須要追究出個真正原由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過一難,則必先編年記月,而後敘事,隱寓攢年至月,攢月至日,攢日至時之意。其與取經回東,交還貞觀十三年牒文,同一機關,所謂貞下起元,一時辰內管丹成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着緊合尖處,莫如芭蕉洞、通天河、朱紫國三案。芭蕉洞,言火候次序,至矣盡矣;通天河,辨藥物斤兩,至矣盡矣;朱紫國,寫招攝作用,至矣盡矣。學者若於此處參入,則金丹大道可得其大半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合說者,有分說者。首七回,合說也。自有為而入無為,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無不俱備。其下九十三回,或言正,或言邪,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真,或撥火候之差,不過就一事而分晰之,總不出首七回之妙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即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猴王西牛賀洲學道,窮理也;悟徹菩提妙理,窮理也;斷魔歸本,盡性也;取金箍棒,全身披挂,銷生死簿,作齊天大聖,入八卦爐鍛煉,至命也。觀音度三徒,訪取經人,窮理也;唐僧過雙叉嶺,至兩界山,盡性也;收三徒,過流沙河,至命也。以至群歷異邦,千山萬水,至凌雲渡,無底船,無非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批邪歸正,有證正批邪之筆。如女人國配夫妻,天竺國招駙馬,證正中批邪也;獅駝國降三妖,小西天收黃眉,隱霧山除豹子,批邪歸正也。真人一意雙關,費盡多少老婆心。蓋欲人人成仙,個個作佛耳。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寫正道處,有批旁門處。諸山洞妖精,批旁門也;諸國土君王,寫正道也。此全部本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所稱妖精,有正道中妖精,有邪道中妖精,如小西天、獅駝洞等妖,旁門邪道妖也;如牛魔王、羅剎女、靈感大王、賽太歲、玉兔兒,乃正道中未化之妖,與別的妖不同。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演卦象,有重複者,特因一事而發之,雖卦同而意別,各有所指,故不防重複出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欲示真而批假之法。如欲寫兩界山行者之真虎,而先以雙叉嶺之見虎引之;欲寫東海竜王之真竜,而先以雙叉嶺蛇蟲引之;欲寫蛇盤山之竜馬,而先以唐王之凡馬引之;欲寫行者、八戒之真陰真陽,而先以觀音院之假陰假陽引之;欲寫沙僧之真土,而先以黃風妖之假土引之。通部多用此意。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最難解而極易解者。如三徒已到長生不老之地,何以悟空又被五行山壓住,悟能又有錯投胎,悟淨又貶流沙河,必須皈依佛教,方得正果乎?蓋三徒皈依佛教,是就三徒了命不了性者言;五行山、雲棧洞、流沙河,是就唐僧了性未了命者言。一筆雙寫,示修性者不可不修命,修命者不可不修性之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不同而大同者。如《西遊記》本為唐僧西天取經而名之,何以將悟空公案,著之於前乎?殊不知悟空生身於東勝神洲,如唐僧生身於東土大唐;悟空學道於西牛賀洲,如唐僧取經於西天雷音;悟空明大道而回山,如唐僧得真經而回國;悟空出爐後而入於佛掌,如唐僧傳經後而歸於西天。事不同而理同,總一《西遊》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到極難處,行者即求救於觀音,為《西遊》之大關目,即為修行人之最要着,蓋以性命之學,全在神明覺察之功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前七回,由命以及性,自有為而入無為也;後九十三回,由性以及命,自無為而歸有為也。通部大義。不過如是。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三藏喻太極之體,三徒喻五行之氣。三藏收三徒,太極而統五行也;三徒歸三藏,五行而成太極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言唐僧師徒處,名諱有二,不可一概而論。如玄奘、悟空、悟能、悟淨,言道之體也;三藏、行者、八戒、和尚,言道之用也。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所以一人有二名。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唐僧師徒,有正用,有藉用。如稱陳玄奘、唐三藏、孫悟空、孫行者、豬悟能、豬八戒、沙悟淨、沙和尚,正用也;稱唐僧、行者、呆子、和尚,藉用也。正用專言性命之實理,藉用兼形世間之學人,不得一例混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以三徒,喻外五行之大藥,屬於先天,非後天有形有象之五行可比。須要辨明源頭,不得在肉皮囊上找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三徒,皆具醜相。醜相者,異相也,異相即妙相。正說着醜,行着妙。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三徒到處,人多不識,見之驚疑。此等處,須要細心辨別。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三徒本事不一;沙僧不變,八戒三十六變,行者七十二變。雖說七十二變,其實千變萬化,不可以數計,何則?行者為水中金,乃他傢之真陽,屬命,主剛主動,為生物之祖氣,統七十二候之要津,無物不包,無物不成,全體大用,一以貫之,所以變化萬有,神妙不測。八戒為火中木,乃我傢之真陰,屬性,主柔主靜,為幻身之把柄,衹能變化後天氣質,不能變化先天真寶,變化不全,所以七十二變之中,僅得三十六變也。至於沙僧者,為真土,鎮位中宮,調和陰陽,所以不變。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三徒神兵,大有分曉。八戒、沙僧神兵,隨身而帶。唯行者金箍棒,變綉花針,藏在耳內,用時方可取出。此何以放?夫針把寶杖,雖是法寶,乃以道全形之事,一經師指,自己現成。若金箍棒,乃歷聖口口相傳,附耳低言之旨,係以術延命之法,自虛無中結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縱橫天地莫遮攔,所以藏在耳內。這些子機密妙用,與針鈀、寶杖,天地懸遠。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以三徒喻五行之體,以三兵喻五行之用。五行攢簇,體用俱備。所以能保唐僧取真經,見真佛。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悟空,每到極難處,拔毫毛變化得勝。但毛不一,變化亦不一。或拔腦後毛,或拔左臂毛,或拔右臂毛,或拔兩臂毛,或拔尾上毛,大有分別,不可不細加辨別。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悟空變人物,有自變者,有以棒變者,有以毫毛變者。自變、棒變者,真變也;毫毛變者,假變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稱悟空、稱大聖、稱行者,大有分別,不可一概而論,須要看來脈如何。來脈真,則為真;來脈假,則為假。萬勿以真者作假,假者作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悟空到處,自稱孫外公,又題五百年前公案。孫外公者,內無也;五百年前者,先天也。可知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乃他傢不死之方,非一己所産之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孫悟空成道以後,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大鬧天宮,諸天神將,皆不能勝。何以保唐僧西夭取經,每為妖精所睏?讀者須將此等處,先辨分明,方能尋得出頭義。若糊塗看去,終無會心處。蓋行者之名,係唐僧所起之混名也。混名之名,有以悟的必須行的說者,有以一概修行說者。妖精所睏之行者,是就修行人說,莫得指鹿為馬。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唐僧師徒,每過一國,必要先驗過牒文,用過寶印,纔肯放行。此是取經第一件要緊大事,須要將這個實義,追究出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經人註解者,不可勝數。其中佳解,百中無一。雖悟一子《真詮》,為《西遊》註解第一傢,未免亦有見不到處。讀者不可專看註解,而略正文。須要在正文上看註解,庶不至有以訛傳訛之差。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讀《西遊》,首先在正文上用功夫,翻來覆去,極力參悟,不到嘗出滋味,實有會心處,不肯休歇。郊有所會,再看他人註解,擴充自己識見,則他人所解之臧否可辨,而我所悟之是非亦可知。如此用功,久必深造自得。然亦不可自以為是,尤當求師印證,方能真知灼見,不至有似是而非之差。
以上四十五條,皆讀《西遊》之要法。謹錄捲首,以結知音。願讀者留心焉。
西遊原旨歌
二十年前讀西遊,翻來覆去無根由。自從恩師傳口訣,纔知其中有丹頭。
古今多少學仙客,誰把妙義細追求。願結知音登天漢,泄露天機再闡幽。
先天氣,是靈根,大道不離玄牝門。悟徹妙理歸原本,執兩用中命長存。
還丹到手溫養足,陽極陰生早防惛。趁他一姤奪造化,與天爭權鬼神奔。
觀天道,知消長,陰陽變化憑象罔。收得大藥人鼎爐,七返火足出羅網。
五行渾化見真如,形神俱妙目在享。性命雙修始成真,打破虛空方暢爽。
這個理,教外傳,藥物火候不一般。知的父母生身處,返本還元作佛仙。
愚人不識天爵貴,爭名奪利入黃泉。怎如作福修功得,訪拜明師保天年。
自行人,聽吾勸,腳踏實地休枝蔓。凡竜凡虎急須除,休將性命作妖飯。
翻去五行喚金公,得其一兮可畢萬。神明默運察火候,任重道遠了心願。
心腎氣,非陰陽,金木相並出老莊。除卻假土尋真土,復我原本入中黃。
原本全憑禪心定,培養靈銀壽無疆。不是旁門亂造作,別有自在不死方。
肉屍骸,要看破,莫為饑寒廢功課。道念一差五行分,戒行兩用造化大。
不明正理迷真性,五行相剋受折挫。騰挪變化消群陰,笑他瞎漢都空過。
諸緣滅,見月明,須悟神化是法程。生身母處問邪正,取坎填離死復生。
戒得火性歸自在,除去水性任縱橫。務少搬運功夫客,誰知三教一傢行。
三教理,河圖道,執中精一口難告。金木同功調陰陽,自有而無要深造。
功成自有脫化日,返本還元不老耄。謹防愛欲迷心性,入他圈套失節操。
服經粟,采紅鉛,皆執色相想神仙。誰知大道真寂滅,有體有用是法船。
陰陽調和須順導,水火相濟要倒顛。掃盡心田魔歸正,五行攢處卻萬緣。
戒荊棘,莫談詩,口頭虛文何益之。穩性清心脫舊染,除病修真是良醫。
說甚采戰與燒煉,盡是迷本災毒基。更有師心高傲輩,冒聽冒傳將自欺。
防淫辭,息邪說,壞卻良心壽天折。莫叫失腳無底洞,全要真陰本性潔。
和光混俗運神功,金公扶持隱霧滅。道以德濟始全真,屋漏有欺天不悅。
道為己,德為人,施法度迷方入神。不似利徒多惑衆,自有心傳盜道真。
假裝高明剝民脂,傷天害理總沉淪。陰陽配合金丹訣,依假修真是來因。
未離塵,還有難,莫為口腹被人絆。淺露圭角必招兇,顯晦不測男兒漢。
猿熟馬馴見真如,九還七返壽無算。天人渾化了無生,千靈萬聖都稱贊。
爭道的,仔細參,西遊不是野狐禪。批破一切旁門路,貞下起元指先天。
了性了命有無理,成仙成佛造化篇。急訪明師求口訣,得意忘言去蹄筌。
勇猛精進勤修煉,返老還童壽萬年。
《西遊》一書,古人命為證道書,原是證聖賢儒者之道。
至謂證仙佛之道,則誤矣。何也?如來對三藏雲:“閻閩浮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多淫多佞,多欺多詐,此皆拘蔽中事。”彼仙佛門中,何嘗有此字樣?故前就盂蘭會,以及化金蟬,已將作書的題目大旨,一一點明,且不特此也,就如傳中黑風山、黃風嶺、烏雞國,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國、鳳仙郡,是說道傢那一段修仙?是說僧傢那一種成佛?又何以見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註解,恐其不能確然明白指出。真乃強為渺幻,故作支離,不知《西遊記》者也。長春原念人心不古,身處方外,不能有補,故藉此傳奇,實寓《春秋》之大義,誅其隱微,引以大道,欲使學業煥然一新。無如學者之不惜也,悲夫!
《西遊》又名《釋厄傳》者何也?誠見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無益,竭盡心力,虛度浮生,甚至傷風敗俗,滅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豈非大厄耶?作者悲憫於此,委麯開明,多方點化,必欲其盡歸於正道,不使之復蹈於前愆,非“釋厄”而何?
《西遊》一書,以言仙佛者,不一而足。初不思佛之一途,清靜無為,必至空門寂滅而後成。即仙之一道,雖與不同,然亦不過采煉全真,希徒不死。斯二者,皆遠避人世,惟知獨善一身,以視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關。至於仁義禮智之學,三綱五倫之遭,更不相涉。此仙佛主事也,今《西遊其文無為,是以讀之亦覺無味。《西遊》是把理學演成魔傳,又由魔傳演成文章,一層深似一層,一層奇擬一層,其實《西遊》又是《西遊》,理學又是理學,文章又是文章,三層並行,毫不相背,奇莫奇於此矣。愛理學理,究其淵微;愛熱鬧者,觀其故事;好文墨者,玩其筆意。是豈別種奇書,所可得同日而語也?
《西遊》凡言菩薩如來處,多指心言。故求菩薩正是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正是《西遊》的妙處。聖嘆不知其中之文義,反笑為《西遊》的短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西遊》凡如許的妙論,始終不外一個心字,是一部《西遊》,即是一部《心經》。
通人讀書,衹往通處解,所以愈讀愈明;不通人讀書,衹往不通處解,所以愈讀愈不明。即如鄭莊公名寤生,此原不過作者下此一字,便好起惡字,以與後愛段叔一句,作一文章關照。在讀者,不過看通其文意即了,何必定深究其所生?況此不過一乳名,初無甚緊要關係,在為父母宥,原無所不命,而當日未必亦於此,即有心,在後世就生出許多的議論見解。嗚呼!鄭國遠矣,固不得趨而視之,莊公沒矣,又不能起面問之,若必如是解,則晉文公名重耳,豈真兩重耳朵耶?曹操名阿瞞,豈又瞞其父之所生耶?誠如是,則世更有以雞犬牛羊命名者,不知又當作何解?在古人未必有此事,在後世則強要作此解,不過徒以文字之相害耳,烏足以讀古人之書,烏足以解盲人之書也?
《西遊》一書,不唯理學淵源,正見其文法井井。看他章有章法,字有字法,句有句法,且更部有部法,處處埋伏,回回照應,不獨深於理,實更精於文也。後之批者,非惟不解其理,亦並沒註其文,則有負此書也多矣。
天人性命之學,東山泅水之書,已無不道。詩詞傳賦之文,周秦唐漢之時,已無不作。降而稗官、野史之傳奇,多係小說。雖極其精工靈巧,亦覺其千手雷同,萬章一法,未為千古擅場之極作也。孔子云:“述而不作。”蓋上焉者,不敢作,下焉者,又不肯作。回翔審視,幾無可下筆之處矣。長春計及於此,所以合三者而兼用之,本孔、孟之探心,周、漢之筆墨,演出傳奇錦綉之文章,其中各極其妙,真文境之開山,筆墨之創見。寫一天宮,寫一地府,寫一海藏,寫一西天,皆前代之所閣筆,後世之所絶無,信非學貫天人,文絶地記者,烏足以道其衹字也?自古學已遠,文尚富麗,或以誇多,或以爭幻,此不過一大書店,藏經櫃耳。五尺之村童,錄之有餘,何足以言文,又何足以為奇也?
人生學業不成,皆因物欲多故。外邊的魔障,即是內裏的私欲,故云:“心生,種種魔生也。”若一直寫去,未免腐而無味。看他形容欽食之人,則寫出一蝎子精;言非禮之視,則畫出一多目怪。寫得奇異,狀得更奇異。
《西遊》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起,一路編年紀月,歷敘寒暑,魔怪本於陰陽,剋復順乎四時。此乃以山嶽作硯,雲霞作箋,長虹為筆,氣化為文。讀之如入四時寒暑之中,俯仰其間,而奠識風雲之奧妙也。
天地以太極生兩儀四象,樹木以根本發枝葉花果,人以一心生出仁義禮智,一身行出忠孝廉節。是人生在世,如同天地,如同樹木。則學問文章,原本天地之自然。不是長春作出天地自然之文章,正是天地自然有此文章,不過假長春之筆墨以為之耳。夫天地至大,卻不遍寫。起首落筆第一句,先寫一東勝神州,寫一花果山。真是妙想天開,奇絶千古。夫東勝緊對西天,神州緊對佛天。心之精靈無所不通,故曰神洲;身之德行無所不備,故曰佛天。一東—西,一神一佛,以海比地,以西作天,由花結果,從地升天。自心生海島,樹長神洲,以見根深者葉茂,本固者枝榮。莫不本陰陽之氣化,至理之本然。是以有天地,即有風雲氣化,有樹木,即有枝葉花果;有人,即有仁義禮智之心,忠孝廉節之事。是風雲氣化,乃天地自然之文章;枝葉花果,乃樹木自然之文章,仁義禮智,忠孝廉節,乃人生自然之文章,此方是夫子之文章。人若不讀《西遊》之文章,不知《西遊》之文章,而欲以筆墨堆砌,強為文章,又烏睹所謂文章者也?
《西遊》列傳,大半伏於盂蘭會,此即百樣奇花,千般異果,故云明示根本,指解源流。西粱國,即是口舌兇場;火焰山,謂非是非惡海。貪酒好色,迷失本來之業;爭名奪利,何有西天之路?荊棘叢林,不識法門之要,鳳仙郡裏,怠慢瑜迦之宗。心獨故失,正應不服使喚之文;雙鳥失群,卻是回照多殺之旨。有師有徒,玉華州原非盂蘭會,明德止至善,天竺國已伏化金蟬。白虎嶺至精至細,金(山兜)洞極隱極微。前伏後應,各傳說來俱有源由。條目綱領,首尾看去無不關會。全部數十萬言,無非一西,無非一遊。始終一百回,即此題目,此即部法。
心本虛靈不昧,故曰靈臺。返本還元,以復其本來之初,故曰如來,言如其本來之舊也。足以說靈山衹在心頭,可知如來亦並不在心外。凡如許的妙意,皆有生之所未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何以卻寫出許多的妖怪?蓋人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是為不明其德者一翻。於是忠之德不明,則為臣之道有虧;孝之德不明,則子之道有未盡。以至酒色財氣,七情六欲,爭名奪利,不仁不義,便作出許多的奇形,變出無效的怪狀。所以寫出各種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樣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終不可止,而如來又何以見也?
三藏真經,蓋即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三綱領也。而云西天者,言西方屬金,言其大而且明,以此為取,其德日進於高明。故名其書曰《西遊》,實即《大學》之別名,明德之宗旨。
不唯其書精妙,即此二字,亦見其學問之無窮也。
時藝之文,有一章為一篇者,有一節為一篇者,有數章為一篇者,亦有一字一句為一篇者。面《西遊》亦由是也。以全部而言,《西遊》為題目,全部實是一篇。以列傳言,仁義禮智,酒色財氣,忠孝名利,無不各成其一篇。理精義微,起承轉合,無不各極其天然之妙。是一部《西遊》,可當作時文讀,更可當作古文讀。人能深通《西遊》,不惟立德有本,亦必用筆如神。《西遊》、《西遊》,其有裨於人世也,豈淺鮮哉?
大學之效,有三綱領,五指趣,八條目。天地之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經藏之數,有一萬五千一百軍四十八捲。
其中之三百裏,六百裏、八百裏,十萬八千裏,悉照《大學》之數。故開捲以天地之數起,結尾以經藏之數終。
大學之道,至遠至久,故要經歷十四年,十八萬千裏,以見其道之至大至高,原非近功淺學者之所能造。是以一路西來,無筆不是《大學》,無處不是學道。講大學之道,尤為精極。
古人作書,凡有一篇妙文,其中必寓一段至理,故世未有無題之文也。後人不審其文,不究其理,概以好文字三字混過,不知是祭文、是壽文、是時文,是古文。不知是《出師表》寫出老臣之丹心,還是《陳情衷》作出孝子之天性。古人作書,原如風雲展轉,文理相因;後人批書,竟是秦楚各天,毫不相涉。是古人之作書,原自為古人之書,初不計後人之有批,殊不知後人之批書,衹自為後人之批,並不問古人之所作也。
《西遊》原本,每為後人參改筆削,以自作其聰明,殊不知一字之失實,其理難明,文義不可讀矣。安得古本錄之,以為人心之一快?
或問《西遊記》果為何書?曰實足一部奇文,一部妙文。
其中無題不作,無法不備,乃即長春之一部窗稿,並無別故。
但人海以為方外之元微,而多歧其說,及細究其文藝題目。
則亦無可疑議矣。
按邱長春,名楚(處)機,道傢北宗有七祖,長春乃其中之一。勝跡皆在東海勞山。時應元祖之聘,與弟子一十八人,居於燕京西南之長春宮,故此又稱長春真人,蓋即今之白雲觀也。
元人每作傳奇,多摘取中節二十七題,以發明朱註氣稟人欲之要,文章局面,似迥不同。不知其中之題目,則無絲毫有異。
“西遊”二字,實本《孟子》引《詩》“率西”二字。
物欲不除,氣稟不化,其德不明。其德不明,其民亦不新,至善不可止矣。看他先從氣稟人欲,轉到明德,又由明德,轉到新民,然後結到止至善。一層一層寫來,方見學問之有功夫,更見文章之有次第。
或問一部《西遊記》,為何其中寫了多少的妖魔怪物?夫妖魔怪物,蓋即朱註所謂氣稟人欲之私也。朱註講的渾含,《西遊》實分的詳細。什麽是個氣稟?什麽是個人欲?人如何便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具德便至不明?又必如何方不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迨至不拘不蔽之際,此妖魔之所以盡去,而其德亦不昏矣。是朱註發明聖經,《西遊》實又註解朱註。
氣稟人欲,共擬二十五條,所以亦引二十五個題目,以明具義。凡人有一於此,皆足為大德之纍,而其德已不明,又何以得見本來之所固有,而以止於至善也。
一部《西遊記》,若說是文章,人必不信。再說是經書《大學》文章,人更不信。唯其不信,方見此書之奇。
一部《西遊記》,三大段,一百回,五十二篇,卻首以大學之道一句貫頭。蓋路經十萬八千裏,時歷十四年,莫非大學之道,故開捲即將此句提出,實已包括全部,而下文一百回,三大段,五十二篇,俱從此句生出也。
三藏真經,蓋即明新止至菩,故曰唐三藏。明德即是天理,故曰太白李長庚。《大學》原是大人之學,故云齊天大聖。看他處處抱定,回回提出,實亦文章顧母之法。
三藏真經,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捲,蓋按《大學》之字數而言也。細查《大學》經傳朱註字數;聖經二百零五字,十章一千五百四十八字,小註衹雲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註三幹一百三十三宇,序文五十六字,章傳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宇,尚少一字,其數不符。或計算朱之差,抑亦古今之異,然亦不可得而知矣。
人心衹得一個,道心衹有一條,心顧可多耶?然雲《密多心經》者何哉?蓋密音,靜也,團也,寂默也,聖人以此洗心滌慮,遇藏於密也。多心,即氣稟人欲之私也。必須將此種心,條條滌詵,件件寂默,其德方明,而至善乃可止。此所以為《密多心經》,實剋己之全功也。
一部《心經》,原講君子存理遏遇之要,何以雲色不異空?蓋色乃像也,即指名利富貴之可見者而言。此原身外之物,毫無益於身心性命,雖有若無,故曰不異空。又何以雲空不異色?蓋空即指修己為學之事也。人看是個空的,殊不知道明德立之後,祿位名壽無不在其中,與有者無少間,故曰不異色。由是觀之,人以為色者,不知卻是空,所謂“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者是也。人以為空者,不知卻是色,所謂“富傢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者是也。再觀齊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孰有孰空,人亦可以概悟矣。玉皇張主,蓋言心也;天蓬元帥,實蔽塞此心者也,捲簾大將,開明此心,九齒釘鈀頓開心上之茅塞者也。剋己復禮,原是心上的一部功夫。所以降妖捉怪,純以行者之為首先要務也。
《西遊》每寫一題,源脈必伏於前二章。此乃隔年下種之法,非冒冒而來電。譬如欲寫一豬八戒,先寫一黑熊精;欲與一鐵扇仙,先寫一琵琶洞;欲寫一寶像國,先寫一試撣心。不惟文章與文章接,書理與書理接,而且題目與題目接,妖怪與妖怪接矣。
看他如許一部大書,裏面卻沉沉靜靜,並無一字飛揚,齊齊整整,亦無一回長短。養成學問,練就手筆,讀之最足以收心養性。
古人典籍多矣,何獨《西遊》稱奇?且緇在蕭寺,深為聖門之所不敢,儒流之所迸棄,何況和尚取經,更覺無味,尤屬扯淡平常之甚者也。有何好處,能令海內稱奇?予初讀之,而不見其奇。繼而求之,似有所得。然亦不過謂與世俗之傳奇無異。再進而求之,方知有題有目,似一部鄉會製藝文字。更加竭力細求,始知足一部聖經《大學》文字。迨知是聖經《大學》文字,其妙不可以言,其苦亦不堪再問矣。
《西遊》一書,原是千古疑案,海內一大悶葫蘆。但其為文,有據理直書者,有隱寓者,亦有藉音藉字者,更有止可以章捨而不可以言傳者。
《西遊》一書,原本真西山《大學衍義》而來。但西山止講格緻誠正修齊,末及平治兩條,《西遊》因之而亦如是。後至明祭酒邱瓊山,始續而補之,詳見《大學衍義》。盞西山講的原是一部至精之理學,長春作的卻是一部絶妙之文章,其名雖有不同,而其義則一也。
如來住在雷音,大士又住在潮音,其寓意絶妙,總言學者格物緻知,返本還元,陳誦讀之外,再無別法。後人不悟不求自己之雷音,反求西域之雷音,捨卻自己之潮音,轉尋南海之潮音,其計亦左矣。
嘗言著書難,殊不知解書亦不易。何則?蓋少則不明,多則反酶,而言多語失,以致吹毛求疵,不知淹沒多少好書,批壞無限奇文,良可惜也!
奇書最難讀者,是查無書可查,問無人可問,有如一百件無頭大案,全要在心上細加研究,非得三二年探功,恐不能讀出其中之妙也。
如來何以單要坐蓮臺?蓋蓮取其出污泥而不染,以喻學者返本還元,盡性復初,非去其氣稟人欲,舊染之污,而不得知其本來也。
夫何以為觀音大士?蓋士為學者之通稱,故曰士。觀音乃所以學大人之學者,故稱觀音大士,此指無位者而言,故又稱白衣大土。看他把方外的許多名目,全然附會成一部理學文章,此更覺奇。但不知當原果有此等名號,抑亦後人因作奇書,憑空捏設編造也。
《封神》寫的是道士,固奇;《西遊》引的是釋伽,更奇。細思一部《大學》,其傳十章,一字一句,莫非釋之之文,卻令人讀之,再不作此想,方見奇書假藉埋藏之妙。
曹溪在廣東韶州府東南,內有南華寺,六祖嘗演法於此,乃仙境也。
此書不妙在談天說地,怪異驚人,正妙在循規蹈矩,不背朱註,將一部《大學》,全然藉一釋字脫化出來,再令人意想不到,真正奇絶。
一部《西遊記》,以東字起,西字終,始於萬花店,結於婆羅蜜,所以為花果山,而遂名為《西遊記》也。
(三晉張南薫註《新說西遊記》晉省書業公記藏板)
西遊原旨讀法
一、《西遊》之書,仍歷聖口口相傳、心心相印之大道。古人不敢言者,丘祖言之;古人不敢道者,丘祖道之。大露天機,所關最重。是書在處,有天神守護。讀者須當淨手焚香,誠敬開讀。如覺悶倦,即合捲高供,不得褻慢。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立言,與禪機頗同。其用意處,盡在言外。或藏於俗語常言中,或托於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戲裏,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別其真假。或藉假以發真,或從正以批邪。於變萬化,神出鬼沒,最難測度。
學者須要極深研幾,莫在文字上隔靴搔癢。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神仙之書也,與才子之書不同。才子之書論世道,似真而實假;神仙之書談天道,似假而實真。才子之書尚其文,詞華而理淺;神仙之書尚其意,言淡而理深。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貫通三教一傢之理,在釋則為《金鋼》、《法華》,在儒則為《河》、《洛》、《周易》,在道則為《參同》、《悟真》。故以西天取經,發《金剛》、《法華》之秘;.以九九歸真,闡《參同》、《悟真》之幽;以唐僧師徒,演《河》、《洛》、《周易》之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一案有一案之意,一回有一回之意,一句有一句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真人言不空發,字不虛下。讀者須要行行着意,句句留心,一字不可輕放過去。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世法道法說盡,天時人事說盡。至於學道之法,修行應世之法,無不說盡。乃古今丹經中第一部奇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轉生殺之法,竊造化之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一切執心着意,頑空寂滅之事。學者須要不着心猿意馬、幻身肉囊,當從無形無象處,辨出個真實妙理來,纔不是枉費工夫。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大道,乃先天虛無之學,非一切後天色相之邪術。先將禦女閨丹。爐火燒煉批開,然後窮究正理,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宗公案,或一二回,或三四回,或五六回,多寡不等。其立言主意,皆在分案冠首已明明題說出了。若大意過去,未免無頭無腦,不特妙義難參,即文辭亦難讀看。閱者須要辨清來脈,再看下文,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回妙義,全在提綱二句上。提綱要緊字眼,不過一二字。如首回,“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靈根”即上句字眼,“心性”即下句字眼。可見靈根是靈根,心性是心性,特用心註修靈根,非修心性即修靈根。何等清亮!何等分明!如次回,“悟徹菩提真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悟徹”即上句字眼,“斷魔”即下句字眼。先悟後行,悟以通行,行以驗悟,知行相需,可以歸本合元神矣。篇中千言萬語,變化離合,總不外此提綱之義。回回如此,須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取真經,即取《西遊》之真經。非《西遊》之外,別有真經可取。是不過藉如來傳經,以傳《西遊》耳。能明《西遊》,則如來三藏真經,即在是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宗公案,收束處皆有二句總結,乃全案之骨子。其中無數妙義,皆在此二句上着落,不可輕易放過。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乃三五合一,貞下起元之理。故唐僧貞觀十三年登程,路收三徒,十四年回東,此處最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通關牒文,乃行道者之執照憑信,為全部之大關目。所以有各國寶印,上西而領,回東而交,始終鄭重,須臾不離,大要慎思明辨,方能得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大有破綻處,正是大有口訣處。惟有破綻,然後可以起後人之疑心,不疑不能用心思。此是真人用意深處,下筆妙處。如悟空齊天大聖,曾經八卦爐鍛煉,已成金剛不壞之軀,何以又被五行山壓住?玄奘生於貞觀十三年,經十八年報仇,已是貞觀三十一年,何以取經時又是貞觀十三年?蓮花洞,悟空已將巴山虎、倚海竜打死,老妖已經識破,何以盜葫蘆時,又變倚海竜?此等處大要着意。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通關牒文,有各國寶印,乃《西遊》之妙旨,為修行人安身立命之處,即他傢不死之方。此等處,須要追究出個真正原由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過一難,則必先編年記月,而後敘事,隱寓攢年至月,攢月至日,攢日至時之意。其與取經回東,交還貞觀十三年牒文,同一機關,所謂貞下起元,一時辰內管丹成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着緊合尖處,莫如芭蕉洞、通天河、朱紫國三案。芭蕉洞,言火候次序,至矣盡矣;通天河,辨藥物斤兩,至矣盡矣;朱紫國,寫招攝作用,至矣盡矣。學者若於此處參入,則金丹大道可得其大半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合說者,有分說者。首七回,合說也。自有為而入無為,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無不俱備。其下九十三回,或言正,或言邪,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真,或撥火候之差,不過就一事而分晰之,總不出首七回之妙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即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猴王西牛賀洲學道,窮理也;悟徹菩提妙理,窮理也;斷魔歸本,盡性也;取金箍棒,全身披挂,銷生死簿,作齊天大聖,入八卦爐鍛煉,至命也。觀音度三徒,訪取經人,窮理也;唐僧過雙叉嶺,至兩界山,盡性也;收三徒,過流沙河,至命也。以至群歷異邦,千山萬水,至凌雲渡,無底船,無非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批邪歸正,有證正批邪之筆。如女人國配夫妻,天竺國招駙馬,證正中批邪也;獅駝國降三妖,小西天收黃眉,隱霧山除豹子,批邪歸正也。真人一意雙關,費盡多少老婆心。蓋欲人人成仙,個個作佛耳。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寫正道處,有批旁門處。諸山洞妖精,批旁門也;諸國土君王,寫正道也。此全部本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所稱妖精,有正道中妖精,有邪道中妖精,如小西天、獅駝洞等妖,旁門邪道妖也;如牛魔王、羅剎女、靈感大王、賽太歲、玉兔兒,乃正道中未化之妖,與別的妖不同。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演卦象,有重複者,特因一事而發之,雖卦同而意別,各有所指,故不防重複出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欲示真而批假之法。如欲寫兩界山行者之真虎,而先以雙叉嶺之見虎引之;欲寫東海竜王之真竜,而先以雙叉嶺蛇蟲引之;欲寫蛇盤山之竜馬,而先以唐王之凡馬引之;欲寫行者、八戒之真陰真陽,而先以觀音院之假陰假陽引之;欲寫沙僧之真土,而先以黃風妖之假土引之。通部多用此意。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最難解而極易解者。如三徒已到長生不老之地,何以悟空又被五行山壓住,悟能又有錯投胎,悟淨又貶流沙河,必須皈依佛教,方得正果乎?蓋三徒皈依佛教,是就三徒了命不了性者言;五行山、雲棧洞、流沙河,是就唐僧了性未了命者言。一筆雙寫,示修性者不可不修命,修命者不可不修性之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不同而大同者。如《西遊記》本為唐僧西天取經而名之,何以將悟空公案,著之於前乎?殊不知悟空生身於東勝神洲,如唐僧生身於東土大唐;悟空學道於西牛賀洲,如唐僧取經於西天雷音;悟空明大道而回山,如唐僧得真經而回國;悟空出爐後而入於佛掌,如唐僧傳經後而歸於西天。事不同而理同,總一《西遊》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到極難處,行者即求救於觀音,為《西遊》之大關目,即為修行人之最要着,蓋以性命之學,全在神明覺察之功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前七回,由命以及性,自有為而入無為也;後九十三回,由性以及命,自無為而歸有為也。通部大義。不過如是。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三藏喻太極之體,三徒喻五行之氣。三藏收三徒,太極而統五行也;三徒歸三藏,五行而成太極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言唐僧師徒處,名諱有二,不可一概而論。如玄奘、悟空、悟能、悟淨,言道之體也;三藏、行者、八戒、和尚,言道之用也。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所以一人有二名。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唐僧師徒,有正用,有藉用。如稱陳玄奘、唐三藏、孫悟空、孫行者、豬悟能、豬八戒、沙悟淨、沙和尚,正用也;稱唐僧、行者、呆子、和尚,藉用也。正用專言性命之實理,藉用兼形世間之學人,不得一例混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以三徒,喻外五行之大藥,屬於先天,非後天有形有象之五行可比。須要辨明源頭,不得在肉皮囊上找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三徒,皆具醜相。醜相者,異相也,異相即妙相。正說着醜,行着妙。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三徒到處,人多不識,見之驚疑。此等處,須要細心辨別。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三徒本事不一;沙僧不變,八戒三十六變,行者七十二變。雖說七十二變,其實千變萬化,不可以數計,何則?行者為水中金,乃他傢之真陽,屬命,主剛主動,為生物之祖氣,統七十二候之要津,無物不包,無物不成,全體大用,一以貫之,所以變化萬有,神妙不測。八戒為火中木,乃我傢之真陰,屬性,主柔主靜,為幻身之把柄,衹能變化後天氣質,不能變化先天真寶,變化不全,所以七十二變之中,僅得三十六變也。至於沙僧者,為真土,鎮位中宮,調和陰陽,所以不變。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三徒神兵,大有分曉。八戒、沙僧神兵,隨身而帶。唯行者金箍棒,變綉花針,藏在耳內,用時方可取出。此何以放?夫針把寶杖,雖是法寶,乃以道全形之事,一經師指,自己現成。若金箍棒,乃歷聖口口相傳,附耳低言之旨,係以術延命之法,自虛無中結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縱橫天地莫遮攔,所以藏在耳內。這些子機密妙用,與針鈀、寶杖,天地懸遠。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以三徒喻五行之體,以三兵喻五行之用。五行攢簇,體用俱備。所以能保唐僧取真經,見真佛。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悟空,每到極難處,拔毫毛變化得勝。但毛不一,變化亦不一。或拔腦後毛,或拔左臂毛,或拔右臂毛,或拔兩臂毛,或拔尾上毛,大有分別,不可不細加辨別。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寫悟空變人物,有自變者,有以棒變者,有以毫毛變者。自變、棒變者,真變也;毫毛變者,假變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稱悟空、稱大聖、稱行者,大有分別,不可一概而論,須要看來脈如何。來脈真,則為真;來脈假,則為假。萬勿以真者作假,假者作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悟空到處,自稱孫外公,又題五百年前公案。孫外公者,內無也;五百年前者,先天也。可知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乃他傢不死之方,非一己所産之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孫悟空成道以後,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大鬧天宮,諸天神將,皆不能勝。何以保唐僧西夭取經,每為妖精所睏?讀者須將此等處,先辨分明,方能尋得出頭義。若糊塗看去,終無會心處。蓋行者之名,係唐僧所起之混名也。混名之名,有以悟的必須行的說者,有以一概修行說者。妖精所睏之行者,是就修行人說,莫得指鹿為馬。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唐僧師徒,每過一國,必要先驗過牒文,用過寶印,纔肯放行。此是取經第一件要緊大事,須要將這個實義,追究出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經人註解者,不可勝數。其中佳解,百中無一。雖悟一子《真詮》,為《西遊》註解第一傢,未免亦有見不到處。讀者不可專看註解,而略正文。須要在正文上看註解,庶不至有以訛傳訛之差。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讀《西遊》,首先在正文上用功夫,翻來覆去,極力參悟,不到嘗出滋味,實有會心處,不肯休歇。郊有所會,再看他人註解,擴充自己識見,則他人所解之臧否可辨,而我所悟之是非亦可知。如此用功,久必深造自得。然亦不可自以為是,尤當求師印證,方能真知灼見,不至有似是而非之差。
以上四十五條,皆讀《西遊》之要法。謹錄捲首,以結知音。願讀者留心焉。
西遊原旨歌
二十年前讀西遊,翻來覆去無根由。自從恩師傳口訣,纔知其中有丹頭。
古今多少學仙客,誰把妙義細追求。願結知音登天漢,泄露天機再闡幽。
先天氣,是靈根,大道不離玄牝門。悟徹妙理歸原本,執兩用中命長存。
還丹到手溫養足,陽極陰生早防惛。趁他一姤奪造化,與天爭權鬼神奔。
觀天道,知消長,陰陽變化憑象罔。收得大藥人鼎爐,七返火足出羅網。
五行渾化見真如,形神俱妙目在享。性命雙修始成真,打破虛空方暢爽。
這個理,教外傳,藥物火候不一般。知的父母生身處,返本還元作佛仙。
愚人不識天爵貴,爭名奪利入黃泉。怎如作福修功得,訪拜明師保天年。
自行人,聽吾勸,腳踏實地休枝蔓。凡竜凡虎急須除,休將性命作妖飯。
翻去五行喚金公,得其一兮可畢萬。神明默運察火候,任重道遠了心願。
心腎氣,非陰陽,金木相並出老莊。除卻假土尋真土,復我原本入中黃。
原本全憑禪心定,培養靈銀壽無疆。不是旁門亂造作,別有自在不死方。
肉屍骸,要看破,莫為饑寒廢功課。道念一差五行分,戒行兩用造化大。
不明正理迷真性,五行相剋受折挫。騰挪變化消群陰,笑他瞎漢都空過。
諸緣滅,見月明,須悟神化是法程。生身母處問邪正,取坎填離死復生。
戒得火性歸自在,除去水性任縱橫。務少搬運功夫客,誰知三教一傢行。
三教理,河圖道,執中精一口難告。金木同功調陰陽,自有而無要深造。
功成自有脫化日,返本還元不老耄。謹防愛欲迷心性,入他圈套失節操。
服經粟,采紅鉛,皆執色相想神仙。誰知大道真寂滅,有體有用是法船。
陰陽調和須順導,水火相濟要倒顛。掃盡心田魔歸正,五行攢處卻萬緣。
戒荊棘,莫談詩,口頭虛文何益之。穩性清心脫舊染,除病修真是良醫。
說甚采戰與燒煉,盡是迷本災毒基。更有師心高傲輩,冒聽冒傳將自欺。
防淫辭,息邪說,壞卻良心壽天折。莫叫失腳無底洞,全要真陰本性潔。
和光混俗運神功,金公扶持隱霧滅。道以德濟始全真,屋漏有欺天不悅。
道為己,德為人,施法度迷方入神。不似利徒多惑衆,自有心傳盜道真。
假裝高明剝民脂,傷天害理總沉淪。陰陽配合金丹訣,依假修真是來因。
未離塵,還有難,莫為口腹被人絆。淺露圭角必招兇,顯晦不測男兒漢。
猿熟馬馴見真如,九還七返壽無算。天人渾化了無生,千靈萬聖都稱贊。
爭道的,仔細參,西遊不是野狐禪。批破一切旁門路,貞下起元指先天。
了性了命有無理,成仙成佛造化篇。急訪明師求口訣,得意忘言去蹄筌。
勇猛精進勤修煉,返老還童壽萬年。